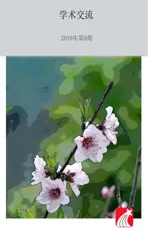论台湾东北作家抗日书写的史诗性、抒情性与纪实性
2016-02-27袁勇麟
董 慧,袁勇麟
(1.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2.福建师范大学 协和学院,福州 350117)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论台湾东北作家抗日书写的史诗性、抒情性与纪实性
董慧1,袁勇麟2
(1.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2.福建师范大学 协和学院,福州 350117)
1949年之后一批东北作家退居台湾,以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感为基础,记载下东北人民的抗日历程。他们的抗日书写以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来展现“史”的宏大与壮阔。在广度上,反映动荡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在深度上,体现了哲学层面对人与自然、与战争、与世界关系的深度思考;以民族精神的升华、诗意细节的描写和情感的深度描绘包蕴“诗”的哲理与内涵;以史实和准确的史料为依据,不仅注重对客观事件、外在环境的描摹,还注重挖掘人物的心理动因,以纪实性和亲历性还原“真”的朴拙与美感。台湾东北作家的抗日书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体现了东北、台湾双重经验,丰富了台湾文学中的书写面向。
史诗性;纪实性;抒情性;台湾东北作家;抗日书写
有一批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赴台的大陆作家,他们或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或在东北有过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来到台湾后,他们继续书写东北题材,丰富了台湾文学中的地域写作。这批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们曾亲历东北的抗日救亡斗争,如司马桑敦和纪刚;第二类是祖籍东北,但少小离家,带着童年的往事或父辈的创伤进行写作的作家,如齐邦媛、梅济民和赵淑敏;第三类是祖籍山东,因长辈们“闯关东”而有过东北经历的作家,如田原。他们都曾耳闻或目睹了日本殖民者对家乡的凌辱和践踏,对东北有着太多割舍不了的浓厚乡情。退居台湾之后,他们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为基础,记载下东北人民的抗日历程,以史诗性和纪实性的文学手段还原了这段历史。
一、追求“史”的宏大与壮阔
史诗性一直是衡量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这类作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民众生活状况,这就需要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入的理解,在构思和创作过程中具有大处落笔、小处着眼的胸怀和气魄。因此,能够写出史诗性作品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成功的作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1]107这里“实际发生的事迹”,指向一种客观存在,即“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1]107。由此分析,“史诗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存在,一是主体精神。能够在记述史实的基础上注入民族的精神,就是在“史”的框架结构中注入“诗”的内蕴。台湾东北作家在书写东北人民的抗日历程时,大多以东北社会生活为描写对象,既包容了东北近现代历史,又彰显出东北特有的民族精神,构建了史诗性的巨著。
“史”的宏大与壮阔主要体现为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以齐邦媛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为例,在时间上,作者书写了自己的家庭从清末民初直至迁移台湾后的漫长历史。从“我”出生一直写到“我”的耄耋之年,其间还追忆了“我父亲”的年轻时代,时间跨度近百年。在空间上,从儿时的东北故乡,写到青少年时期暂居的南京、天津和北京,又写到随着“七七”事变的炮火一路向祖国西南方向的逃离,途经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等多个省份,尝尽流离之苦。大学毕业后,作者来到台湾,辗转台中、台北求职,台湾多处留下了她忙碌的身影。在大跨度的时空挪移中,作品承载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军阀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的逃难流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台湾教育事业和铁路事业的艰难发展。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从张学良出生写起,重点写了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东北军西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西安事变和被蒋介石幽禁等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从1901年到1964年,空间跨度由沈阳、西安、南京,再到江西、安徽、贵州,最后来到台湾新竹、台北。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再现了张学良在民族战争之际对国对民的赤胆忠心。
相对于较长的历史跨度而言,也有作家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呈现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空间的转移中全景式地触及社会现实。梅济民的《北大荒风云》写的就是抗俄斗争、抗日斗争和抗战胜利后的国共矛盾。作者从1929年俄国侵略东北的战争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建国前夕。赵志伟等一批青年历经了在沈阳、北京和旅顺等地的求学过程,在俄、日侵略者的进攻面前,他们纷纷放弃学业,两度投笔从戎,配合土匪万海山带领的“浴血救国军”,或冲锋在大兴安岭雪原的抗敌前线;或伪装成各种角色,在旅顺、哈尔滨等城市窃取敌人的重要情报;或为保存实力,潜隐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种地、打猎,自给自足……东北沃土处处留下了他们斗争的足迹。还有几位作家集中笔力描写了抗日战争。纪刚的《滚滚辽河》叙述了国民党东北地下组织觉觉团在隐蔽战线奋斗的历程:纪刚等几位青年在日伪的统治下,不断穿梭于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东北几个重要城市,将各地抗日机构团结起来,联合作战。赵淑敏的《松花江的浪》追述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两代东北青年辗转黑龙江、北京、南京、重庆等地的抗日史,巨大的空间跨度勾连起整个国家的抗战史,使台湾作家的“东北书写”超越了一般的地域写作。还有的作家以人物为纲,通过个人的命运遭际反映时代变迁。如田原的《这一代》,以东北少年罗小虎的经历串联起“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国共内战,随着主人公漂泊的历程,小说触及东北、山东、福建等地的风土民情。司马桑敦的长篇小说《野马传》是以坤伶之女牟小霞的人生为线索,书写一个天生带有野性的女子如何在东北和山东两地不断以斗争的方式寻找自我又不断碰壁的经历,其间刻画了东北沦陷前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初的社会众生相。
无论是怎样的结构模式,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广度上,力图反映动荡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在深度上,揭示各阶层的思想,并试图挖掘其历史与现实的根源。这些作品时常能够呈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深入思考。
首先,呈现出对战争的思考。对于抗日战争的描写,作家不仅关注战争结局,更关注在战争中展现出的桀骜不驯、反抗压迫的精神特质,鼓励和赞扬无惧生死的战场拼杀,同时也歌颂在残酷战争中显露出的高贵灵魂。战争留给人类的,不仅是情感的创伤,更应该有对人生意义和牺牲价值的重新判断。当世人都在以是非成败谈论英雄的时候,齐邦媛在张大飞墓碑前追忆其惨痛的家世、笃定的信仰和纯洁的情感,最终,她对张大飞的感情由单纯的男女之爱上升为超越生死的敬仰,对其高贵的灵魂给予礼赞。这是超越战争结果的对于战士的最深的关怀和理解。其次,呈现出对人性的思考。非常态的现实生活往往能够凸显人性的不同侧面。有诸如齐世英、王二虎、李繁东一样的钢筋铁骨,也有如油碾子、杨砚飞和杨鲤亭一样的丑陋嘴脸。作品不仅展示了人性,还分析了人性的救赎与求索。《这一代》中的罗小虎由儿时羡慕权势、崇拜金钱到憎恨日本侵略者、自觉加入抗日组织的转变,体现了东北沦陷后孤儿的成长史和思想的成熟史;《大风雪》中的东方曙由贪恋个人情感、对政府卖国行为懵懂静观到对汉奸的辱骂和反抗,反映了沦陷区知识分子由困惑到觉醒的过程;《野马传》中的牟小霞一生都在寻找人生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她从没有向事实低头,她的个人主义是其天性没有被时代大潮淹没的写照,但她的悲剧又是人性的悲歌。最后,呈现出对人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在时代怒潮面前,人究竟应该抛弃一切涌入洪流、投身现实,还是应该抛弃时代、追逐自我呢?如果是前者,人很可能就会在时代中消失,完全成为一朵浪花;如果是后者,虽然找到了自我,却会在现实中碰壁而死。如果说牟小霞是后一种选择的代表的话,那《滚滚辽河》中的纪刚则是前一种人的代表。“九一八”事变让正在读大学的纪刚未来得及多想就加入了地下抗日组织觉觉团。他时刻将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个人不断向革命妥协,大学毕业后就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医学领域,成了一个“消失”的黑人,专门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由于工作的紧张性和危险性,对于每个青年人都向往的爱情,纪刚也只能悄悄远离,以至于在很多年当中,他居然不知道自己究竟爱的是谁。直到抗战胜利了,他才恍然大悟,自己的真爱竟是温柔娇弱的宛如。纪刚完全将自己变成了革命队伍里的螺丝钉,丧失了个性,也丧失了主体意识。他的成功伴随着革命的成功,然而抛弃情感、远离家庭、永远地为革命牺牲就是时代赋予人的唯一使命吗?小说结尾,纪刚随着人流不断地向南迁徙,最终流落台湾,与祖国故乡分离的经历也昭示着与纪刚一样的这一代人的悲剧命运。
以上三方面的思考让作品透过历史真实直达生存本相,是在哲学层面对人与自然、与战争、与世界关系的深度思考。正如《巨流河》结尾的一段书写一样,故事结束了,思考仍在继续:
我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2]587-588
二、包蕴“诗”的哲理与内涵
在展示抗日战争的大事件时,如果只是罗列大量的史实,就会使小说变成教科书,缺乏感染力和审美价值。“史诗性”的作品除了有客观的历史再现,还不能缺少主观的人类精神。或者说,史诗再现仅是一种手段,它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现实的思考展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应局限于只在一个既定场所发生的特殊事迹的有限的一般情况,而是要推广到包括全民族见识的整体”[1]121。这种精神推动着事件的演变、民族的振兴,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一部史诗性巨著中“诗”的哲理与内蕴的集中表现。
这种诗性的张扬首先体现为战争中民族精神的升华。“受辱”和“反抗”是东北近代历史的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伸出刺刀实行对东北的血腥统治,肥沃的良田、丰饶的矿产和三千万憨厚朴实的东北民众全部沦入敌手。民族的苦难和同胞的血泪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危机感,东北人骁勇剽悍、无畏无惧的生命本色,在民族危机面前转化为抗击侵略、抵御外辱的最坚强的力量。《北大荒风云》中的大学生张励民,在战争前夜还在思念受伤住院的母亲,遗憾自己“忠孝不能两全”,但在敌众我寡节节败退的情势下,他竟然敢于抱着地雷以人体炸弹的方式去攻击敌人的坦克,然后在这声巨爆中“不知去向”。《松花江的浪》中,老叔高亮被捕后拒绝了市长职位的诱惑,承受住敌人开水烫、雪水冻的酷刑,最终被刺刀刺死。这种对信仰的执着源自于东北黑土地日积月累的民风,源自于东北人民根性中不屈精神的传承。在这些作品中,青年学生已经将理想主义精神与救国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不是只会伤春悲秋,而是亲身实践着救国理念。《巨流河》中国民党元老齐世英先生,从青少年时代就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舍生忘死,默默无闻地为日寇统治下的父老乡亲做了许多工作……这些青年不仅发出民族斗争的先声,还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觉醒青年的激情和正义首先感染的就是他们的亲人。《北大荒风云》中赵志伟的父亲赵廷祥来呼伦贝尔草原前线看望儿子时,临危受命,充当狙击手,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松花江的浪》中,“我”受到老叔抗日精神的感召,放弃学业,毅然参军;《巨流河》中齐世英先生的妻子虽是农家妇女,却随着丈夫在流亡中不断帮扶东北少年,她那一桌桌浸满亲情的东北饭菜,不知道感动了多少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这些以家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物活动中,表面上看是一种影响,其实是一种传承。以赵廷祥父子关系为例,从情节上看是赵廷祥被赵志伟等青年的救国热情感染,也投入其中,大显身手。其实,赵志伟身上的勇敢、顽强和对于侵略的反抗精神,正源于赵廷祥的性格和精神的遗传。在东北这片饱含着斗争和拼杀的土地上,骁勇剽悍、不平则鸣是一种凝结在骨子里的质素,它必将伴随着时事、世事延续下去。《松花江的浪》中,“我”对老叔高亮精神的继承就是明证。如果从精神传承这个角度去思量这批作品,作家是以“血亲”这种根深蒂固的联系直抵民族的灵魂。又由于“血亲”这一庞大的内涵和外延,将东北的学生、农民、小商人甚至土匪都包容在抗敌救国的事业中。
对于诗性的张扬还体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将赋予诗意的细节描写注入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在史实的广度中增添思考和感悟的深度,让历史变得真实可感。齐邦媛的《巨流河》中就充满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如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但是他“静穆”的观点在1935年遭到鲁迅的批评,他的为人为文,在民族危亡之际都显得不合时宜。齐邦媛就读武汉大学时,朱光潜正担任武大的教务长,又同时担任外文系教授。齐邦媛作为朱光潜的得意弟子,自然有机会窥见其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侧面。他在讲到“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时,会取下眼镜,任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流下满室愕然[2]184;在讲到“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时,表情严肃,很少有手势的他会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2]186-187。这是将诗歌联系自身实际触发的情感涟漪,亦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以实际行动对黑暗的反击。抗日战争当前,冲锋沙场、血刃敌军固然能够保家卫国、彰显正义,这是正确选择,但不是唯一选择。在内忧外患之际,我们除了坚守祖国河山之外,还要尽更大的努力去维系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同样的,没有冲到前线杀敌却坚守在各行各业的芸芸众生,他们对本专业领域的钻研进取,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奉献,也是一种爱国,也是对敌人侵略的一种抗争。正如王德威所言:“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3]能够更全面摹画朱光潜文人情操的,还有他院内那满地落叶。他积攒了好长时间,只为了下雨时,听到风卷起的声音。这个现实场景对于文人而言,比读许多写意的诗句更为生动。其他作品中也镶嵌着许多类似展现人物、体现哲思的细节。《松花江的浪》中,老叔在流亡关内之际,偷偷往老婶碗里夹的一口菜,表达了这个革命战士对于妻子的愧疚和无奈之情,老叔既无力反对这场无爱的包办婚姻,又无法抑制情感上对于真爱的向往,只能在义无反顾的战斗中蹉跎岁月;《松花江畔》中美艳高傲、冷漠苛责的小白蛇,唯独对憨直仗义的王二虎倾诉衷肠,这是她在生存的重压下唯一一次喘息和宣泄,将土匪表面威风、实则艰涩的人生展示出来。这些细节无力推动或改变历史,却丰富了历史,让读者看到了时代的全景。
其二是一以贯之的情感投入。史诗性作品要求作者将个人对历史的独特体验与历史叙述相融合,既有理性的思考,又有感性的抒怀,这样才能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而在这批作品中,情感的投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在客观写实的叙述中自然地流露情感。这种情感由于有客观的叙述作为铺垫,显得水到渠成。比如纪刚的《滚滚辽河》中,当“我”与诗彦雪夜对坐、畅谈人生时,不禁情动:
我不知中了什么邪魔,当她移近我的时候,竟用一只手腕将她扣住,一种想在荒野里奔驰的欲望,饥渴地驱使着我想去接近她那殷红的、火热的……
她没有接受,也没有脱走,只是她把脸紧紧地贴藏在我的胸前;是娇羞?是抗拒?我不知道!我的自制力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哗啦啦——
有些糖果逃落地下。
这种声音并不是巨响惊人,却足以唤醒我的理智,收回我的灵魂。我是做什么的呢?我真悔愧交加,想打自己一万个嘴巴。我把那双可咒诅的手臂高高攀起放在我的脑后,让诗彦可以自由离开而不受外力约束,但她却未想离开,喷火一般的呼吸,仍使我的胸膛感到高热难抗。……
我该如何是好呢……[4]40
小说中经常提及“我”害怕地下工作的危险性会累及他人,所以一直对于男女之情极度克制。而“我”也一直自信可以把控自如,没想到却在这一瞬间“擦枪走火”。这段情感释放的点睛之笔是“我真悔愧交加,想打自己一万个嘴巴”这句心理描写,它让读者明白了“我”的行为完全是不经意间的失控。对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言,情动是正常现象,如果太过于压抑情感,就会导致这种无理性的冲动。叙述中的情感流露让人物变得可观可感,更加真实。
更多的时候,作家会选择借景抒情。东北的林海雪原、山河湖泊、晨风晚霞构成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风景画,在每一处景语之后都是作家的情语,景物实实在在地成为作家情绪的载体。如梅济民的小说《长白山奇谭》中,作者会让王三哥在流水淙淙、春回大地时出场,渲染这位默默奉献、不计名利的大英雄;王汉倬会在嫩江的旖旎风光中追忆自己逝去的青春;牟小霞和许海可以借助大海的狂波酣畅淋漓地相爱……这些景物描写有力地构建了作品的“东北风味”,亦能够抒发“东北情绪”,展现“东北性格”。
最能够展现“东北性格”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有些作家在平实地叙述、审慎地分析之后还觉得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便直接将感情和盘托出。《大风雪》中,孙陵在精细刻画了杨鲤亭等卖国者的丑恶嘴脸后,不禁发出高声控诉:
但是当着一千九百三十年的一月底,——也就是民国二十年旧历除夕将临的这几天,日本军队乘着攻陷双城底余威,而驱兵之下H埠的时候,H埠的这些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双腿动物,是怎样保卫他们底族类和巢穴啊?可耻啊!他们连一只乌鸦——被“人”骂为扁毛畜生的东西——都不如!他们竟企图着在敌人尚未到达H埠之前,就已将自己底窠巢双手奉故了。可耻啊!在禽兽中很少见到的,“人类”中我们竟而见到了!那些“黄帝底子孙们”怎样在称斤论两地向敌人讨着好价钱,来出卖他们这些五千年来繁衍至今的族类!可耻啊!他们不但像一个逆子似地要出卖祖先遗留给他们供作生息繁衍的土地,并且连埋葬在这土地里的祖先底骨骼,他们也都要一道上杆称着出卖给他们底敌人哩!可耻啊![5]
孙陵是带着对于祖国山河的无限爱意来控诉这些卖国求荣的统治者的,他以比喻的手法惟妙惟肖地勾画出卖国者奴颜婢膝的嘴脸,用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来对比这些民族败类的渺小和可耻。这种愤慨使读者亦能借以抒发胸中愤懑,引起强烈共鸣,也使我们得见作者的真性情。“孙陵以这种大悲哀大愤怒来谱写《大风雪》,勾勒人物的丑陋灵魂,不但使小说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也使其艺术达到可以远超《儒林外史》的艺术高度。”[6]当然,在任何一篇作品中,情感的宣泄主要是创造一种抒情的氛围,吸引读者与作者共同思考超越一己悲欢的厚重问题,传达个体独特的情感和思维体验。
三、还原“真”的朴拙与美感
“真”指的就是文学的“纪实性”。作家亲身经历了东北的近现代历史,他们将这种经历完全地还原到创作中,产生了许多贴近史实的作品。还有些作品未必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但是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凭借自己对于历史的了解、科学系统的判断取证,力图用最真实的材料呈现历史原貌并阐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这类纪实性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齐邦媛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和纪刚的自传体小说《滚滚辽河》。
以史实和准确的史料为依据是这类作品的最大特色。司马桑敦写《张学良评传》是因为无意间在台北街头的旧书摊上看到了张学良写的已被查封、难得一见的史实材料《西安事变忏悔录》,由此他决定以史实为基础,写张学良。当时虽然已经是1964年,距“西安事变”过去了28年,可是有关张学良的人和事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他还没动笔,就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资料少而难求[7]394,许多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人物都三缄其口,刻意回避。关键人物的亲属都生活在国外,力求平静的生活,不愿接受采访。二是资料的真实性难以判断。虽然有一些资料,但是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也只能舍弃不用。有些资料貌似真实,但是又无法确定时,作者就会在文中点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作者每处落笔必要根据资料判断之后再行文,他用在查阅、推敲资料上的时间和精力要超出书写时的好多倍。全书以张学良的前半生为重点,记述了“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并依据自己的判断给出了相对中肯的评价。在对人物的记述中,作者力求“不虚美,不隐恶”。评传中的张学良聪明、理解迅速,能够礼贤下士、是非善恶之心清楚、人生观豁达,还能够学习英文、提倡体育、打得一手好网球。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沾染了玩女人、抽大烟、打吗啡等坏习气。对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西安事变”,作者根据史料详细地叙述了全部过程,充分表现了张学良几次进谏不成,不得已才逼蒋抗日的无奈。在写到张学良主动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才对张学良给予了认可和同情:“其实,张学良早在这以前已下定决心要陪蒋回京。他先向东北军将领表示过,这一场大乱子,他为祸首,一切由他一个人承担;另一方面,他准备向南京和向全中国表示,他此次发动事变,决无危害蒋委员长之恶意和争权夺利之野心。”[7]283这种描写让我们看出:“作者并不刻意评论党派的是非;而是出于爱祖国、爱家乡的一片赤诚,记录中国遭受日本侵略那段历史,探讨其中的教训。”[8]
齐邦媛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是其在八十多岁高龄时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书中所写、所感、所思都是作者身临其境的感知,即使是有关其父亲、母亲的叙述也都是有据可循。比如对于其父齐世英的叙事应该都是父女谈话的忠实记录,基本符合史实。这一点也可以参见《齐世英口述自传》*齐世英,等.齐世英口述自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来求证。两部书上记录的史实基本上是没有出入的,只是由于叙述的角度不同,详略观念有异。《滚滚辽河》是纪刚根据自己地下抗日的亲身经历创作的纪实小说,这也可以从《涉大川——纪刚口述传记》和“拓展台湾数位典藏计划”*拓展台湾数位典藏计划.http://content.teldap.tw/index/.得到验证。《滚滚辽河》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现实人物的写照,无论是神秘的负责人、书记长、社长还是罗雷、仲直、方仪等,都可以在地下抗日历史中找到原型。书中详细记录了“觉觉团”为了革命隐姓埋名、宣传抗日、印发传单、联络机构、假结婚、被捕入狱、忍受刑罚甚至以自杀相抵抗的抗日经历。因为太现实了,反而让读者觉得有些枯燥。比如,书中没有我们常常想象的那种刀光剑影的畅快、被人拥戴的光荣和传奇惊险的浪漫,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小心谨慎、与人隔绝的孤独寂寞和与敌智斗的艰辛,好多时候还要背负爱人离去、亲友不解的委屈。虽然他们没有身处为国斗争的最前线,甚至连枪也没开过,却不能磨灭他们为了斗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小说也仅仅想要记录这些事实,如纪刚所言:“我想用小说的笔法描写真实的历史,展现革命奋斗的真人真事、真流血、真牺牲和真感情。”[9]
作家在记述这些历史人物时,不仅注重对客观事件、外在环境的描摹,还注重挖掘人物的心理动因。司马桑敦在写张学良这个人物时,就呈现了其思想转变史。张作霖是张学良的父亲,对其影响至深,作者就一边介绍张作霖的发迹史,一边书写父子的交流,张学良的人生观初步形成。即使是对于历史上至今还有争议的郭松龄,作者也如实地记录其风貌。郭松龄“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经常的手不释卷,字字读书”,“对于战术学,造诣极深,而且他的风采堂堂,口齿伶俐,在课堂上口若悬河,热情奔放,受训学员都对他表示欢迎”[7]11。而后又自然书写了张学良被他吸引的原因:“郭松龄年长他(张学良)十九岁,而且为人正派、严肃、也正是他所需要的可以师事之和兄事之的一种人。”[7]11这种生动的描写就使得人物“活”了起来,枯燥的叙述有了生气。齐邦媛比较注重在叙述中兼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她“远离政治、一心读书”观念的形成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她时常涌起孤独悲凉的情绪是在战火中奔逃的女孩的普遍心迹。有了这些对人物行为动因的描写,才还原了“史诗性”作品“真”的本色。
四、台湾东北作家抗日书写的意义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阐释了一个概念“历史重写本(palimpsest)”。该词源自中世纪书写用的印模,原先刻在印模上的文字可以擦去,然后在上面一次次地重新刻写文字。其实以前刻上的文字从未彻底擦掉,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旧文字就混合在一起:重写本反映了所有被擦除及再次书写上去的总数。[10]不论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呈现方式,还是某个人对于某地、某物或者某种情绪的认知都与“历史重写本”有着相似的地方。它不可能擦掉过去所有的痕迹,也不可能拒绝新事物的影响和入侵,一切的认知结果都是随时间消逝增长、变异及重复的认知总和。对于台湾东北作家抗日书写而言,“东北经验”和“台湾经验”的双重认知都会在其作品中呈现显影,使其成为异于大陆东北书写又异于台湾其他各省籍书写的独特所在。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件,东北又是抗日战争的肇始之地。台湾东北作家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既能够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东北乃至全国人民杀敌卫国、众志成城的雄心壮志,又能够在宏大历史的间隙触及人性和情感。这批作家退居台湾之后,黑土地的浩瀚广阔与临海小岛的狭仄拥挤、年轻时的书生意气与中年后的浮世沧桑、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灵魂的无处安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们更加思念东北原乡。他们对于东北和抗日战争的书写,大多不是在大陆时所作,而是1949年去台湾后带着乡愁对往事的追忆。这些追忆大部分还原了历史真实,还有些夹杂着意识形态和个人情绪的偏颇之作也展现了台湾经验和大陆经验看待抗日战争的不同角度。虽然如此,也不能否定台湾东北作家在史诗性和纪实性这个角度对于抗日书写做出的贡献: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传播,也体现了东北—台湾双重经验,丰富了台湾文学的书写面向。
[1][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齐邦媛.巨流河[M].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3]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与《巨流河》[J].当代作家评论,2012,(1):162.
[4]纪刚.滚滚辽河[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94:40.
[5]孙陵.大风雪(第1部)[M].香港:南华书局,1997:155.
[6]林强.换一副笔墨写东北——孙陵《大风雪》解读[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4):25.
[7]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8]周励,[日]藤田梨那.回望故土——寻找与解读司马桑敦[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09:160.
[9]赵庆华.涉大川:纪刚口述传记[M].台南:台湾文学馆,2011:133.
[10]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
〔责任编辑:曹金钟孙琦〕
2016-03-17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台湾文学中的东北书写”(14E101);牡丹江师范学院博士启动资金项目“台湾文学中的东北书写”(MNUB201501)
董慧(1979-),女,黑龙江加格达奇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台湾文学研究;袁勇麟(1967-),男,福建柘荣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台湾文学研究。
I207.4
A
1000-8284(2016)09-01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