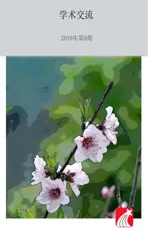供给与需求的辨识博弈——近年来我国关于供给学派的研究状况述要
2016-02-27韩喜平吕玫萱
韩喜平,吕玫萱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130012)
经济学研究
供给与需求的辨识博弈
——近年来我国关于供给学派的研究状况述要
韩喜平,吕玫萱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130012)
基于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本质区别,对近年来关于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及与之有关的主要成果进行梳理发现:我国学者一方面致力于揭示“供给学派”理论问题的本质和演进规律,另一方面关注其对解决实践问题的意义和启示;以“里根经济学”作为例证,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供给学派的面貌和意义,同时也为我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和参考;“新供给经济学”命题的提出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融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尝试构建和发展我国的供给经济理论,据以探讨我国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供给学派的见解,但无论是理论渊源、哲学思维,还是改革路径、宏观经济背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手段、宏观政策主张、利益调整关系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与政策重构。
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学派的研究,我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中央提出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供给学派的兴趣更加浓厚。笔者对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供给学派及与之有关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基本以时间顺序为经,以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等为纬,归纳概括其基本见解和主张,并试图做出适当的评论,期能对人们的思考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关于供给学派:认知与启示
经过研读有关资料,我们注意到,我国学者对供给学派的研究是从基本的认知开始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孙鹏(1998)认为,从供给与需求是否趋于一致和如何趋于一致来看:“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自动相等,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供给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滞胀”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总供给与总需求并非等同。从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来看: “萨伊定律”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正处于蓬勃向上的自由竞争阶段时产生的,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调节,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而供给学派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陷于“滞胀”危机时产生的,它反对国家干预,但不是完全不要国家干预,而是减少国家干预的重要性。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供给学派是萨伊定律的“复活”,而应当是一个新思潮、新流派的涌现。此外,供给学派也不是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二者的政策基础以及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形式和手段等方面都是十分相似的。供给学派之所以会走向没落,是由于它缺乏严密、明确的理论体系。[1]
后来的研究在探讨供给学派的本体问题的同时,也注重对其价值和意义的判断。毛晖(2007)介绍了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认为萨伊定律是该学派的理论基础;供给学派通过主张减税、财政平衡等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激发投资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为高科技革命、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而言,供给学派的各项政策主张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2]钟祥财(2011)评述了供给学派产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产生的不同声音,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供给学派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而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供给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此外,作者还从技术和政策层面对供给学派的思想逻辑与历史渊源作了具体阐述,并认为供给学派所继承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思想。该文还论及了中国对供给学派理论的借鉴以及供给学派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3]李怀玉(2014)从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体系的偏重以及政策主张的影响等方面对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二者在理论上的欠缺和不足,进而总结了二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启示,强调了供给与需求相协调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市场经济需要提高国家干预的水平、规范政府行为,使经济理论与经济环境相匹配等观点。[4]
贾康、苏京春(2014)着重阐述了“供给侧”经济学派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轨迹:第一轮“否定之否定”以19世纪初“萨伊定律”为开端,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到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滞胀”危机,在对“凯恩斯主义”提出巨大挑战后,使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再次脱颖而出;第二轮“否定之否定”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遭遇二战后最严重一轮经济危机后,供给学派理论的应用并没有达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反而出现了严重的赤字问题,使供给学派逐渐受到冷落,凯恩斯主义再次回潮,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在救市过程中又采用了供给管理的手段,这便是供给学派的第二次回归。作者从历史的视角,阐释了供给学派对于“萨伊定律”的追随以及供给学派的演进,并指出了供给学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西斯蒙蒂、马尔萨斯等人的批评与反对。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会导致最终财富极度不公的恶果,还会因为没有区别货币经济和物物交换经济而导致最终的失败。最后,作者认为,沿着供给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结合中国经济学人的已有探索,应可派生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新供给经济学”。[5]
对于供给学派的认识,我国学者一方面致力于揭示理论问题的本质和演进规律,另一方面关注其对解决实践问题的意义和启示。其聚焦点在供给学派同萨伊定律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尽管在诸如供给学派是否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致的看法,即供给学派以“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简单重复。
二、关于“里根经济学”:实证与借鉴
可以说,我国学者对供给学派的关注和研究最早是从所谓“里根经济学”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是在停滞性通货膨胀、高过头的失业率、负增长的生产率以及庞大的预算赤字的背景下产生的。杨德明(1987)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凯恩斯主义面对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并发的情况束手无策,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及合理预期学派“沉渣泛起”;应客观地看待供给学派,在肯定供给学派对于经济繁荣的贡献时,也应注意其政策的局限性,并认为主张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不能完全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因此应正确认识二者对于经济发展不可偏废的作用;供给学派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大部分曾为里根政府所采纳,因而“供给学派”以“里根经济学”著称。[6]
周军翻译了英国作者M·马歇尔、P·阿里斯蒂斯的文章指出,凯恩斯学派衰退的原因在于它所依赖的传导机制——提供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满足社会需要以及不完全向大商业利益妥协的机制——在70年代的经济形势下完全崩溃,使供给学派的经济思想重新为人们所关注;里根经济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供给学派经济学,只是在1982年后,供给经济学成为里根经济学的思想核心,并作为里根政府重要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7]
也有学者将“里根经济学”同所谓“撒切尔主义”放在一起加以考量,试图从中获得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启示。刘军喜(2016)阐述了供给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几次交替更迭,说明了供给学派以减少税收、减少干预、减少福利、减少通胀作为主要政策主张,并以里根的减税政策和撒切尔夫人的国企私有化政策为范例,分析了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在美、英两国的应用如何使两国的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减少政府干预,构建“小政府”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主要内容,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对此应该加以学习与借鉴。[8]
里根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而“你不能跟市场作对”,则被认为是撒切尔主义的精髓。上述例证表明,我国学者对里根经济学的关注,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实证的方法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供给学派的面貌和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我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或参考,但从一开始,我国学者即注意到了供给学派及其主张的局限性,认为政府与市场二者不可偏废。
三、关于新供给经济学:探讨与建议
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的,经济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对实际经济问题的解答。到了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积累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如结构性物价上涨、产能过剩等,破解这些难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切,也成为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契机。贾康等诸位作者(2013)以梳理和考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非凯恩斯主义的学术演进和政策得失为基础,将已有的理论经济学认识与原被理解为分支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贡献融会贯通,同时针对中国的国情与实际,提出了适合中国现代化客观需要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识框架,强调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以有效化解当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9]滕泰(2013)认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阶段,从供给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文章还提出了相应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以及增加有效供给、降低供给成本的房价、物价管理思想;文章还对新供给主义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学术思想进行比较,认为传统供给学派没有提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归纳了传统供给学派的零散建议并将其吸纳到了新供给学派的完整体系中。[10]
贾康、苏京春(2016)评述了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的几次交替兴衰,并归纳了供给学派的几个主要观点;在阐述了植根于中国经济实践对“理性供给管理”的诉求后,提出了不可偏废“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任何一方的新供给经济学,并对新供给经济学的特征、侧重点以及“供给管理”的地位进行了具体论述。[11]金海年(2016)阐明了新供给经济学与供给学派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新供给经济学不仅关注供给,同时也关注需求,并认为需求与供给的作用是非对称的。在具体解释了何为“八双”“五并重”政策后,文章明确提出解除供给约束、规范供给竞争、将供给的外部性内生化、促进供给创新等理论主张。[12]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篇文章都发表于2016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报告》“供给侧改革”栏目中,或可视为关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研究的开局之作。
笔者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学者关于供给学派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笔者认为,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融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尝试构建和发展我国学者自己的供给经济理论,据以探讨我国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应该说,这种探讨和建议也是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的舆论准备。值得强调的是,与供给学派的主张相比,新供给经济学不仅注重供给,而且也十分注重需求,认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它的所谓“从对立走向融合”即是就“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事实上,我国关于供给学派的研究及至所谓“新供给经济学”的构建,主要是因应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对供给与需求二者的意义和作用所进行的思辨与识别,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理论上的博弈。
四、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理论创新与政策重构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此,供给学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有关供给与需求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较早出现并有代表性的文章[13-15]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内容和目标指向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政策解读,其中也涉及了对萨伊定律、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及新供给经济学的探讨和评价。但是,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不应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相混淆,它们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理论渊源不同。贾康、苏京春、裴长洪等学者认为,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支流派,或者是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表现,是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发端。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付小红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裴长洪则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他们共同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解决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的智慧结晶。[16-18]第二,哲学思维不同。付小红认为供给学派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相形之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蕴含着辩证法的大智慧,放眼更为广阔的领域,在统筹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双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总量与结构、增量与存量之间的辩证关系。[18]第三,改革路径不同。付小红与裴长洪认为,供给学派的改革思路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进而实现后危机时代下资本积累的恢复与重建。而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仅要求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坚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主张,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恪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明确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17-18]第四,宏观经济背景不同。贾康、苏京春认为,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滞胀”时期。而对于目前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者们认为产生的宏观背景与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明显不同,中国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增长带来的结构不良的瓶颈制约,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16]第五,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手段不同。有学者指出,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作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在主张供给的同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强调供给和需求是管理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第六,宏观政策主张不同。贾康、苏京春、裴长洪等一致认为,供给学派主要是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不注重全面政策配套问题,可见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涉及面很窄。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者们有不同看法,贾康、苏京春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并不仅仅落在减税一个方面,而是强调税制整体的改造、优化,以及与宏观政策相配套的产业政策、改革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组合;裴长洪则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16-17]第七,利益调整关系不同。裴长洪认为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实际上代表的是大企业和大公司的利益,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盘考虑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尤其重视低收入阶层人民的利益和保护。[17]
笔者认为,明确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者之间的区别,有助于避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以致对改革的方向造成误导;有助于避免因认识的模糊性导致行动的盲目性,防止政策在贯彻和落实过程中的偏差,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平稳的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供给学派的见解,但又与之有着根本区别,可以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及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重构。
[1]孙鹏.供给学派——萨伊定律的否定之否定[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8,(2):41-44.
[2]毛晖.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启示[J].北方经济,2007,(6):91-92.
[3]钟祥财.供给学派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11,(1):123-132.
[4]李怀玉.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比较及启示[J].商业时代,2014,(20):33-34.
[5]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2-16.
[6]杨德明.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J].瞭望周刊,1987,(48):36-37.
[7]M·马歇尔,P·阿里斯蒂斯,周军.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学[J].世界经济文汇,1991,(2):78-80.
[8]刘军喜.里根和撒切尔的供给侧改革[J].支点,2016,(2).
[9]贾康,徐林,李万寿,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J].财政研究,2013,(1):2-15.
[10]滕泰.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世界经济研究,2013,(12):3-8+84.
[11]贾康,苏京春.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新供给经济学”[J].中国经济报告,2016,(1):16-21.
[12]金海年.新供给经济学的主张与应用[J].中国经济报告,2016,(1):31-34.
[13]滕泰.“供给侧改革”拉开大幕---以改革开启中国经济上升新周期[J].中国中小企业,2015,(12):18-21.
[14]刘世锦.供给侧改革不是说需求不重要了[J].中国经贸导刊,2015,(34):26-27.
[15]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领[J].中国金融,2016,(2):14-15.
[16]贾康,苏京春.科学认识供给侧改革——中国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理论实践的区别[N]. 浙江日报,2016-04-11(15).
[17]裴长洪.裴长洪:中国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区别在哪里[EB/OL].(2016-05-19)http://business.sohu.com/20160519/n450277933.shtml.
[18]付小红.道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N].内蒙古日报(汉),2015-01-15(10).
〔责任编辑:巨慧慧〕
2016-07-20
韩喜平(1965-),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
F093.1;F014.32
A
1000-8284(2016)09-01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