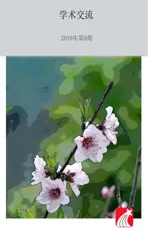挑战与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犯罪治理
2016-02-27张文龙
张文龙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99)
法学研究
挑战与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犯罪治理
张文龙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99)
犯罪风险日益变成一个全球治理问题。全球犯罪风险既对世界各国人口和财产造成严重危险和侵害,也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刑事司法框架造成巨大挑战。同时,英美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霸权问题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犯罪控制模式的全球扩散。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中国对全球犯罪治理的参与和回应,需要坚持保障人权、反对霸权的基本立场,通过升级理论和转变实践,做出一个世界文明大国的全球治理贡献。
全球化;犯罪风险;刑事司法;世界社会;中国
一、问题与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犯罪风险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从互联网到全球贸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全球化作为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对此,一种关于全球化的广泛认识指出:“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1]1全球化深刻塑造着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机会,以致“全球思考,地方行动”都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标语和口号。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分化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较早从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开启。首先是贸易实现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服务以及由此世界市场的出现,这得益于14、15世纪世界航运技术的发展,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无疑是这个贸易全球化过程开端的标志性事件;其次是与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领域发展,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从历次世界金融危机看到;再次是操控贸易与金融的跨国公司兴起,跨国公司不仅直接影响全球贸易和金融,而且还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者,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1]208-391除了经济全球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从政治到文化)都呈现出不同动力、形式和程度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最好被视为一个高度分化的过程,体现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包括政治、军事、法律、生态、犯罪等许多领域)。显然,绝不能把全球化看作一个单纯经济或文化的现象。”[1]17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和平,也带来战争;它既产生财富,也产生贫困;它既创造机会,也创造风险;它既扩张自由,也扩张奴役;它既追求安全,也追求恐怖;它既带来流动,也带来停滞;它既保守,也激进;它既削弱主权,也强化主权;它既形成霸权,也形成反霸权。可见,全球化是一个充满辩证意味的问题。正是这种双重面向,让人们需要警惕全球化的黑暗面,其中,全球犯罪问题尤其值得研究和防范。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全球犯罪莫过于恐怖主义,自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肆虐全球,恐怖犯罪已经成为一种全球风险。因此,打击恐怖犯罪,防范全球恐怖风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除了恐怖犯罪之外,全球犯罪风险[2]还包括跨国洗钱犯罪、跨国人口贩卖与走私犯罪、全球黑帮犯罪、全球网络犯罪、生态-全球犯罪、跨国知识产权犯罪等问题产生的社会风险,因为这些犯罪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游走全球,从而对各民族国家的人口和财产带来危害。因此,预防和控制上述全球犯罪风险,已经成了人类共同体需要共同应对的社会问题。
二、流动的犯罪:对现代刑事司法框架的挑战
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这个世界犯罪治理体系由国家刑事司法和国际刑事司法构成,按照国内法/国际法的二元编码,构建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运作结构和逻辑。[3]然而,随着犯罪的全球流动,全球犯罪风险对于建立在上述“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的现代刑事司法体系形成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既表现为现代刑事司法管辖困境和运作失灵,也表现为英美国家刑事司法霸权及各国刑事司法之间的冲突。
(一)刑事司法体系二重奏:现代国家与犯罪治理
犯罪及其控制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当一个地方社区发生犯罪问题,人们可能依靠地方习俗和宗教仪式来处理犯罪问题,其中包括神明裁判和司法决斗等方式,甚至是由地方人们组成一个陪审团来解决由犯罪产生的纠纷问题,因此,犯罪常常被视为一种侵权行为类型。到了近代社会,尤其在西方社会,犯罪及其控制问题逐渐从地方领主和宗教权威转移到世俗君主的王权控制之中,透过君主立法和王室法庭,犯罪控制权力逐渐被君主所垄断,因为这一方面是维护王室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需要以“国王的和平”名义来维护公共秩序。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生效,犯罪控制和治理的边界就被国家主权构筑起来,同时,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建立和运作,包括检察官制度、现代警察制度、监狱制度,等等。即便从君主时代走向现代民主国家,犯罪控制和治理仍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国家是现代社会应对犯罪问题的标准机制。[4]40
二战之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标志着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兴起。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建立起一种世界人权保护机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透过国际刑事法庭对危害人类犯罪、种族灭绝犯罪、战争犯罪和侵略犯罪等国际罪行进行调查、追诉和审判,使得利用国家主权实施上述侵犯人权罪行的人得到惩罚。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际刑事立法,联合国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刑事法律制度,从危害人类犯罪一直到资助恐怖主义犯罪;另一个方面是国际刑事司法实践,自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后,针对侵犯人权的国际罪行,先后有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建立并运作,而2002年《罗马规约》生效后,一个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得以建立和运作,这标志着国际犯罪治理进入一个新时代。国际刑事司法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是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补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监控,针对滥用国家主权(包括司法主权)行为实施侵犯人权之罪行进行追诉和惩罚。
当前世界犯罪治理体系由国家刑事司法和国际刑事司法构成。这个犯罪治理体系是以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为基础,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现代国家透过国内法/国际法构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体系又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现代刑事司法领域,同样受到上述“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逻辑的支配,因此,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源代码。然而,全球犯罪风险已经对这个二重奏治理体系形成了某种强有力的挑战。9·11恐怖袭击已经例证了这一点,当恐怖分子跨越美国边界对其国内发动袭击时,美国必须突破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国家边界,通过破坏别的国家刑事司法主权来实现其防范和打击全球恐怖犯罪的目标。质言之,全球犯罪风险已经对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主权基础形成挑战。
(二)全球流动的犯罪:对现代刑事司法体系挑战
如何理解全球犯罪对于现代刑事司法框架的挑战?对此,我们试图运用世界社会理论解释全球犯罪的流动性,并进一步分析这种流动性如何对现代刑事司法“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体系构成挑战。
所谓世界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一方面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社会功能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医疗、教育、科学、媒体等;另一方面这些社会功能系统突破民族国家领土边界和文化限制,通过货币、权力、法律、信仰、作品、治疗、教学、真理、信息等一般化的沟通媒介,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沟通与运作。在民族国家时代,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这些社会功能系统承担着全社会的特定功能,比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的规范性期待,政治系统的功能是提供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宗教系统的功能是化解社会的偶连性问题,艺术系统的功能是实现对世界的观察,媒体系统的功能是实现全社会的自我观察,科学系统的功能是发现真理,等等。同时,社会功能子系统按照二元符码来实现系统的社会沟通与运作,比如,法律系统就按照法与非法的二元符码来实现对系统/环境的区分,从而实现系统自身的自我生产。在全球化时代,这些社会子系统开始横向发展突破领土国界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功能系统。质言之,世界社会是由不同的社会功能系统组成的全社会。[5]
在法律系统中,犯罪是被法律标识为非法的领域,这个非法的领域作为法律系统的环境而存在,比如,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是外在于法律系统的内部运作,因为罪犯是不会按照法律规定去行动。相反,法律系统是按照刑法规定来运作,通过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标识,从而把犯罪规定为一种法律惩罚的对象,从而建立起社会的某种规范性期待,比如,不得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等。因此,从法律系统的角度,犯罪是被法律标签的行为,从而建立起人们对罪与非罪的规范性期待。同时,从法律系统的环境来看,作为非法领域的犯罪,则处于一种充满复杂性的图景之中,犯罪活动可能是受到各种社会系统因素的触动而引发:罪犯可能因为经济上的贫困而去盗窃或者抢劫;或者可能因为政治上的夺权而去刺杀议员或者总统,甚至制造大屠杀;或者可能因为教育上的压力而杀害老师或父母,甚至是自杀;或者可能因为艺术表演需要而展示性爱;或者可能因为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实施安乐死;或者可能因为需要制造新闻而实施侵犯他人隐私或名誉的行为,等等。因此,犯罪是上述社会功能系统的产物。所以,当社会功能系统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演变成全球运作的社会系统时,犯罪活动就通过全球性的社会功能系统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传播和游走。
犯罪的全球流动可以表现为犯罪信息、犯罪人口、犯罪组织、犯罪手段、犯罪方法、犯罪空间、犯罪对象、犯罪工具等跨国界的传播和流动。全球犯罪的流动性是指全球犯罪通过上述犯罪构成因素的跨国传播和流动,可以穿透民族国家边界,而全球性的社会功能系统为这一全球流动提供了动力机制。由于社会功能系统穿透主权架构,因此,全球流动的犯罪对于现代主权国家构建的刑事司法系统,造成了以下五个方面挑战。
第一,全球犯罪可能造成国家刑事司法管辖上的困境。现代刑事司法管辖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一个国家通常管辖的犯罪大部分都是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发生,这是现代刑法的属地管辖原则。尽管在现代刑法原理上,还存在属人管辖、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原则,但是,这些管辖原则的运作需要建立在国际刑事合作基础上,因此,一旦不存在国际司法合作,这些管辖原则就不能起作用。比如,A国犯罪组织对B国发动了恐怖袭击,但是,A国与B国之间不存在相关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条约,而且A国也没有对其国内的恐怖组织进行法律制裁,那么,除非A国愿意配合B国的司法行动,否则,B国不可能对A国的恐怖组织进行调查、追诉、审判和惩罚。
第二,全球犯罪可能造成国际刑事司法管辖上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目前国际刑事司法管辖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并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不能对这个国家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管辖,即使这个国家可能存在危害人权的恐怖组织或其他犯罪组织,国际刑事法院也难以行使管辖权;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犯罪仅限于侵略罪、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四种,其他国际犯罪的管辖依然属于主权国家范畴,如资助恐怖主义犯罪、危害国际环境犯罪、非法贩卖毒品犯罪、海盗犯罪等国际犯罪,只能通过国家刑事司法体系来管辖,甚至还需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来支撑,比如,建立国际刑警组织、签署引渡条约,等等。这意味着国际刑事司法对于很多全球犯罪活动并不能进行规制,如全球毒品贸易、国际恐怖主义等。
第三,全球犯罪可能造成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运作失灵。这种失灵主要表现为国家刑事司法管制失灵,要么因为国家本身被犯罪集团俘获,要么因为国家本身进行犯罪却被合法化。一方面国家对犯罪控制权力的垄断,往往可能使得国家成为犯罪的帮凶,比如,在国际环境犯罪领域,跨国公司对亚马孙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往往危害到生态环境,却不会遭到该地区国家刑事立法规制,这种破坏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全球犯罪,甚至被视为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途径。另一方面国家本身合法地实施犯罪,比如,在非法入境方面,由于边境控制,使得跨国人口贩卖与走私犯罪更加猖獗,为了严厉打击这些犯罪,西方国家对边境非法移民的拘留和惩罚,甚至造成了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但是,这种系统性的国家犯罪却以执法名义存在,甚至是以消极执法的方式引发悲剧。比如,欧洲海岸警卫队对一艘载满非法移民的船只不予救援,从而导致这些移民饿死在船上。
第四,全球犯罪可能造成英美国家刑事司法治理霸权。犯罪的全球流动对各国人口和财产造成的危害程度不一,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所以,其遭受全球犯罪危害也最为严重。以恐怖犯罪为例,当前欧美国家深受恐怖犯罪的困扰,自9·11事件以来,欧美国家频繁遭到恐怖袭击。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英美国家提出“全球反恐战争”,以战争方式建立起对国际恐怖犯罪的司法治理,伊拉克国际刑事法庭就是这种英美跨国刑事司法治理的工具。英美这种霸权式的暴力司法模式,不仅严重破坏别的国家司法主权,同时也带来了严重侵犯人权的副作用,比如,空中轰炸战术导致大量平民伤亡,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以超常规引渡方式绑架和逮捕具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在关塔那摩监狱剥夺恐怖分子的基本权利,等等。
第五,全球犯罪可能造成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冲突。犯罪的全球流动对世界各国人口和财产造成的危害,一方面可能促使各国文化形成犯罪观念的趋同,甚至出现从世界文化层面界定犯罪,当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国际罪行就是重要的例证,起码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都是世界各国共同承认的犯罪;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各国犯罪控制的趋异,从而导致各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冲突,当前对恐怖主义规制就是重要例证,一些西方国家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可能会被阿拉伯国家认定为合法组织,相反,一些中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却有可能不在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之列,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界定始终存在冲突和政治分歧,从而导致这样的吊诡: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斗士。这样的悖论不限于恐怖主义,在网络犯罪领域也是如此,一个黑客,既可能是别人眼中的英雄,也可能是国家公敌。
三、控制的文化:英美刑事司法与治理全球化
英美刑事司法在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造,形成了一种犯罪控制的文化,这种“控制的文化”具有明显的“严罚趋向”,其运作策略与措施,重塑了犯罪社会控制的涵括/排斥功能。在21世纪初,为了应对恐怖主义问题,这套深刻塑造刑事司法运作逻辑的“控制的文化”从英美国家向全球扩散,一方面带来了英美跨国刑事司法的新实践,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民族国家刑事司法的理想和原则构成严重挑战。
(一)新自由主义与犯罪控制文化
英美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了一股反福利国家的思潮,这就是以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这股思潮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试图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因此,又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而强调国家干预作用最小化是其核心思想。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引发了欧美福利国家的经济制度改革,而且对整个西方社会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英美两国,一方面创造了社会经济竞争力,使得英美两国在新一轮全球化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并引发其他严重社会问题,如犯罪、自杀、抑郁症、贫困,等等。
在刑事司法领域,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一种犯罪控制文化的兴起。在英美两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比如,弹性化劳动市场结构,一方面带来了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工阶层遭受市场经济波动的威胁。由于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从而引发许多的社会问题,如罢工、环保抗议等,为了应对这些社会问题,从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撤退的国家,开始积极介入刑事司法领域,将社会问题的犯罪化,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在福利国家时代,矫正主义和刑罚福利主义,以治疗取代惩罚、以社会团结取代社会排斥,透过社会包容和福利安全网,来实现犯罪问题的社会治疗。与之相反,新自由主义对英美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却产生了一种犯罪控制文化。这种控制文化建立在“犯罪情结”的基础上,这种情结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的特征:“(1)高犯罪率被视为一项常态的社会事实;(2)对于犯罪问题投入的感情普遍而强烈,包含了着迷、恐惧、愤怒与怨恨等成分;(3)犯罪议题被政治化,并常以情绪性的方式表达;(4)对于被害者与公众安全的关切主导了公共政策;(5)刑事司法国家被视为不足或无效;(6)私人防卫日常措施的普及,私人保全市场的扩大。(7)犯罪意识在媒体、流行文化及建造的环境中都已制度化。”[4]220这种“犯罪情结”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文化事实,甚至是文化脚本,塑造着整个社会的公众和政治家对犯罪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即便犯罪率已经发生变化,也不会让人们对犯罪的态度——恐惧和怨恨——发生变化。
上述控制的文化使英美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策略产生了重要转向,即“严罚的转向”[6]。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监狱成为国家对付犯罪的必要手段,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产生的大量犯罪和越轨行为,监禁措施成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首选。尽管监禁是非常昂贵的反犯罪措施,但是,为了保障公众安全,这种“无害化的隔离措施”已经使得英美两国成为全球监禁率比较高的国家,英国2010年每100 000人口中就有154人被监禁,而美国的监禁率比英国更高,每100 000人口中就有囚犯753人。[6]16-17(2)治安惩罚成为对付犯罪问题的先发制人措施。在英美两国,犯罪破窗理论主张为了防范反社会行为变成严重犯罪问题,有必要从一开始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将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比如,帮派暴力、骚扰行为、恐吓行为等反社会行为,可以透过治安惩罚方式来防范。(3)通过福利措施对边缘人群责任化。由于新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化,边缘人群成了社会治安问题之隐患,如问题少年、妓女、无家可归者、瘾君子等,针对这些边缘人群施加责任,比如,要求其不准吸毒或滥用酒精,若不能遵守规定并有进一步违法行为,就对其实施刑事指控并监禁。(4)通过监控技术对危险人群进行社会排斥。当犯罪成为一种危及社区安全的风险问题时,识别具有风险性的人口并加以社会排斥,从而避免遭到犯罪风险侵害,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防卫理论。通过大量运用社会监控技术如闭路电视、摄像头、网络监控、电话窃听等,英美两国变成了一个“监控社会”,通过对所有可能实施犯罪的风险人口进行识别和社会排斥,来建立社会秩序。
(二)英美刑事司法与治理全球化
新世纪以来,英美新自由主义在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领域的影响开始全球化,形成一种全球“控制的文化”,深刻影响全球刑事司法的发展。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监禁措施成为世界各国应对犯罪问题的主要措施,而且,大量监狱的运营机构都私有化,比如,很多国家边境控制中心都是由私人公司承包经营,并通过拘禁等监禁措施来控制非法入境者;其次,风险控制成为刑事司法运作的实践逻辑,为了控制犯罪风险,刑事司法机构将大量的风险行为或危险行为提前处置,将“犯罪之前”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扩张刑事司法之网,由此,实现犯罪风险管理;再次,犯罪治理与控制的私人化,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犯罪风险,单靠国家刑事司法来应对,显然是不充分的,社会安全技术发展和市场化日渐成熟,大量安保技术被私人企业运用并成为一种商品,比如,高级住宅社区通常都有私人安保公司来维持社区秩序与安全,大量运用现代监控技术,把犯罪、越轨等社会风险与社区分隔开来,特别是大城市无处不在的“监控镜头”,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最后,战争与刑事司法的边界模糊化,[7]由于应对恐怖主义,各国刑事司法机构的运作与战争行为之间的边界逐渐被瓦解,传统警察与军队、司法与战争的边界被跨国反恐怖主义行动所解构,这一点从英美两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可以获得例证。
英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领域的影响,与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有着密切联系。英美国家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的社会问题犯罪化,同样,被复制到全球层面,当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就遭到国际层面的法律规制,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行动,建立起各国反恐怖主义的情报合作和反恐行动。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恐怖行动,虽然有着复杂的政治效应和宗教动机,但是,这与伊斯兰地区穆斯林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无关系,甚至很大程度上这一宗教文明地区的经济衰落刺激了宗教极端分子的恐怖行动,所以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政治挑战,质言之,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世界霸权体系之挑战。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美国联合了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通过发动战争的方式,报复伊斯兰地区的宗教极端组织,试图通过战争与民主模式的输出,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以增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和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英美刑事司法的跨国运作实现了其全球治理层面的霸权,从而突破了民族国家刑事司法的主权限制,构建起美国治理全球化的合法性架构。
虽然英美刑事司法在全球犯罪治理方面贡献了新的合法性架构,但是,由于“反恐战争”对司法与战争边界的侵蚀,使得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刑事司法理想和原则,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危害。为了有效应对恐怖分子,刑事司法中的正当程序要求,通常被简化和省略,打击恐怖分子的功利主义追求,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刑事司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使之沦为“具文”,为国家权力滥用打开方便之门。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侵蚀。为了将犯罪控制变成风险管理,将“犯罪之前”的行为提前处置,使得刑罚之网扩张,导致原来罪刑法定原则对国家权力之限制被突破,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变成严重犯罪风险,被加以严厉的刑事制裁。三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之侵害。英美两国在“反恐战争”期间,为了获取有效的反恐情报,对一些具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或者战俘,实施酷刑和刑讯,造成严重虐囚事件,而且美国利用“非常规引渡”、关塔那摩监狱作为超主权的法外空间,使得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与司法行动蒙上严重的合法性阴影。四是对民族国家刑事司法主权的破坏。司法主权是现代刑事司法基础,英美两国的跨国刑事司法实践,通过战争方式先后破坏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国的司法主权,从而对现代刑事司法的运作权力基础造成破坏,尽管这种破坏是局部性的,但是,这种破坏带来了严重副作用,这一点在当前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兴起的伊斯兰国对该地区猖獗的犯罪与战争行为上可以获得说明,因为这些地区原有刑事司法机构都随萨达姆政权的坍塌而变成废墟,丧失控制力,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犯罪活动,从恐怖主义到人口贩卖,等等。
四、立场与应对:中国如何回应全球犯罪治理
当前中国已经深度卷入全球治理,因为中国近年来的和平崛起,已经使得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深度参与了世界社会的运行和建设。具体而言,首先,在经济上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次,在政治上中国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结构中,对于世界和平与战争的事务,同样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点从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就得以证明;最后,在其他社会领域,如法律、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中国一方面深受世界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对世界社会的结构产生影响。在全球犯罪治理领域,中国社会深受全球犯罪风险的危害,大量跨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对中国社会人口与财产造成了新的社会危险,如网络犯罪、生态犯罪,等等。不仅如此,英美刑事司法产生的霸权问题,同样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与理论产生挑战。因此,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成了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新课题。
(一)立场:保障人权与反对霸权
如何应对全球犯罪治理,已经是当前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不可回避的问题。就目前全球犯罪及其治理产生的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全球犯罪治理与人权保护之间冲突的问题,一个是世界霸权与刑事司法主权之间冲突的问题。同时,这两个问题也是交织在一起,因为世界霸权与世界人权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同时,全球犯罪治理与刑事司法主权之间产生外在矛盾,如何调节矛盾和衡平张力,是全球刑事司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在全球刑事司法领域,中国应当以什么立场进行参与和回应?中国既是全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又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对全球犯罪治理的参与,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因此,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体现中国现代文化对全球治理的独特贡献。
首先,保障人权应当是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立场。首先,打击犯罪,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全球犯罪问题造成严重的人权侵害,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保障人权是犯罪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现代国家刑事司法的权力合法性,正是奠基在人民主权与人权同源同构的基础上。[8]随着人权全球化,跨国犯罪、国际犯罪和全球犯罪这些危害人权的犯罪问题,需要从跨国层面、国际层面和全球层面予以法律规制,在全球治理层面实现对危害人权行为的犯罪化,将深刻改变犯罪控制与治理机制,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就是例证。其次,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参与全球犯罪治理方面,中国刑事司法应当充分保障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为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刑事司法惩罚对象时,如何避免刑事司法运作异化带来的人权侵害,是当前中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面对的重大问题。
其次,从中国贡献角度,反对霸权应当是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立场。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一直受到世界刑事司法潮流的影响与左右,从新中国成立时接受苏联法的影响,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接受日本法、德国法、美国法的影响。因此,似乎很难说中国的贡献。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其文明与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世界社会里,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国家对于全球犯罪问题的应对,自然需要履行自己的世界责任和道义担当,这必然要求中国刑事司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贡献,这种贡献的基本面向就是反对霸权,需要对西方中心主义所形成的霸权进行解构和批判。因此,从反对霸权的角度,中国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做出自己贡献,既是它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也是作为文明国家的权力。
(二)应对:升级理论与转变实践
在具体应对全球犯罪治理方面,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策略,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反对霸权,保障人权的基本立场来看,当前我们中国刑事司法既需要升级理论,也需要转变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应对全球犯罪风险,并在全球犯罪治理领域做出贡献。
在理论层面,当前我们犯罪学和刑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进行思考,在理论思维范式上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国族主义,这种思维范式有两大弊端:一方面容易陷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窠臼之中,将很多社会问题犯罪化,导致过度滥用刑事司法资源来应对,从而使得中国变成一个高度监控化的警察国家,对公民权利和人权自由造成限制;另一方面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孤立状态”,民族国家主权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过度强调民族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就很容易成为国际社会上的“孤岛”,既无法与其他国家交流与对话,也容易造成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无法真正从世界视角反思民族国家框架产生的犯罪问题,如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等等。因此,升级理论,从狭隘的方法论国族主义中解放出来,显得很有必要。晚近兴起的世界社会理论思潮,对于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1)突破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图式,试图从世界社会的视角把握犯罪及其治理;(2)将犯罪治理与人权保障从民族国家框架转变为一种全球治理框架;(3)从世界主义角度重塑刑事司法机制,将根植于国家理性基础上的刑事司法体系重构为保障世界人权的犯罪治理体系。
在实践层面,为了有效应对全球犯罪风险,我国犯罪治理实践既需要学习先进国际经验技术和理论,同时也需要反思自身刑事司法制度问题,真正转变实践。从参与和回应全球犯罪治理实践角度,需要解决以下基本问题,才可能真正转变实践:(1)在保障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如何真正落实和履行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及其国际刑事规制的国际法义务,这意味着中国刑事司法实践需要回应世界人权保障的要求,可以先逐步建立起国内法与国际法相互衔接的机制,通过宪法与刑事法律将国际法义务转变为国内法实践,逐渐改变中国刑事司法实践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理念;(2)从治理范式转变角度,如何从一元化的国家刑事司法实践,转向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协作共治的犯罪治理模式,因为当前全球犯罪风险形成表明单一国家刑事司法治理力量不足有效应对,比如全球网络犯罪、生态-全球犯罪等新型犯罪问题,需要建立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合作治理才能真正有效解决问题,这些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组织、地区跨政府组织、地方社会组织、跨国公司、社区,甚至是公民个人,等等;(3)从全球治理战略角度,如何有效参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虽然当前中国仍然没有加入《罗马规约》,[9]但是,当前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和发展对于未来中国参与全球犯罪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犯罪治理需要从全球战略高度审视当前国际刑事司法发展趋势,通过构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逐步成为国际刑事司法治理的重要支柱和担纲者,通过有效制约世界霸权国家,为全球犯罪治理做出贡献。
[1][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戴维·戈尔德布莱特,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杨雪冬,周红云,陈家刚,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Mark Findlay. Governing through Globalized Crime: Future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M]. Willan Publishing, 2008: 55-86.
[3][英]埃辛·奥赫绪,[意]戴维·奈尔肯. 比较法新论[M].马剑银,鲁楠,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80.
[4]David Garland.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序[M].周盈成,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
[5][德]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的宗教[M].周怡君,等,译. 台北:商周出版,2004:28-29.
[6]EmmaBell. Criminal Justice and Neoliberalism[M].Palgrave Macmillan,2011:114-137.
[7][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M].周遵友,江溯,等,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62-196.
[8][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6-128.
[9]李世光,刘大群,凌岩.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责任编辑:杜娟〕
2016-03-14
张文龙(1983-),男,广东新会人,助理研究员,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犯罪全球化研究。
D917
A
1000-8284(2016)09-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