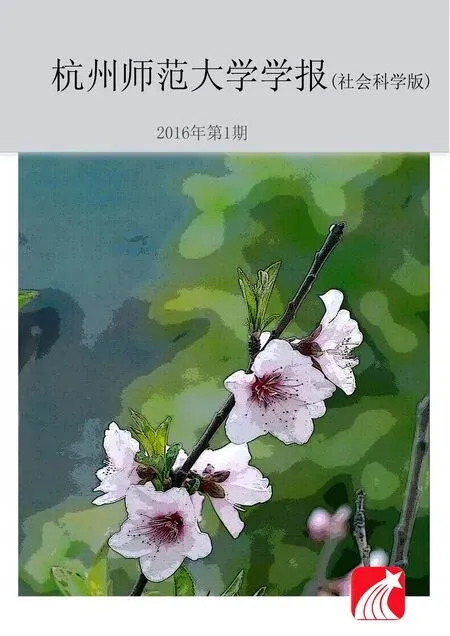杜亚泉:在“动静”与“新旧”之间
2016-02-26鲍文欣
鲍文欣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杜亚泉:在“动静”与“新旧”之间
鲍文欣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坊间流行着把杜亚泉与陈独秀等文化激进主义者断然两分的观点,然而深入的研究将发现,杜亚泉思想中有两条相对独立又互相冲突的线索:强调竞争与互助之辩证运动的普遍进化论和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取向的东西文明比较论。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他的东西“动静”二元论:东西方文明分别发展了普遍进化论中两类不同因素,它们的辩证综合将形成一种新文明。将对东西方文明各自价值的论证整合进“旧-新”的现代时间框架内,是杜亚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这说明杜氏与陈独秀等论敌共享着类似的现代观念框架。但在此种整合中,杜亚泉实际上偏离了对普遍进化论中两种对反因素的辩证理解,这是其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无法在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立足的理论原因。
关键词:杜亚泉;东西文化论战;文化保守主义
在20世纪10年代末那场与陈独秀的论战后,杜亚泉被迫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黯然退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舞台中心。这种戏剧性的结局容易使整个事件都被抹上过于浓重的油彩。因此,并不意外,坊间流行的观点认为,杜亚泉与陈独秀之间是保守与激进、理性与浪漫、以及——作为本文主题的——文明特殊论与一元进步论之间的截然对立,杜氏的退场也就意味着上述二元对立中前一项的失败。也正缘于此,杜亚泉于风气转移后重返人们的视野,翻转为不囿于时流的文化先知。人物品评的浮沉往往提示时代思潮的潮汐往还,而批判的观念史则试图寻觅思潮涌动中相对稳定的预设,这些预设是各思潮之间对话得以可能的前提,亦构成了它们共同的时代特征。正如高瑞泉先生所说: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尽管鼎足而三,但是他们一方面影响乃至创造着近代传统,一方面又大致相近地运作于近代传统的架构之中。[1]
与传统哲学的思辨往往展开于天人之际类似,近代思想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议论虽然不同程度地具有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特征,但这些议论同样需要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中来得到理解。此种框架中的重要组成即是由传统天道中“大化流行”观念转变而来的现代普遍进化观念和世界历史观念。思想家们的具体论题既要从这一框架中获得合法性的论证,也因为各自主张的不同而需要对其进行局部的调整。主要以历史观为中介,传统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在更新了的形式中得到延续。基于这一宏观的判断,本文试图指出,我们过分高估了“东西文化论战”中双方对立的程度。换言之,杜亚泉和陈独秀也共享着类似的观念框架:他们都预设了东西文明的“静-动”区分,都将自己的文明论纳入一个“旧-新”的总体时间框架内,并都诉诸于“新”来论证自身论点的合法性。不同在于,与陈独秀的一元论线性史观相比,杜亚泉关于东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2](P.338)的说法,以及由此而来的调和结论,尤其可以挑动当代中国人的神经。不过,在激赏于此种文明二元论的异彩时,我们需要关注,这一思想是如何在当时共同的精神氛围中被生产出来的。
一
在于1916年发表关于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宣言式文章之前,杜亚泉的思想始终不无犹豫地运行在两条容易互相抵牾的轨道之中。首先,作为深受《天演论》影响的一代人,普遍进化论同样是杜亚泉重要的思想框架:
盖必有物质而后有生命,有生命而后有心灵……但就已有生物之后而言,则无生命之物质,进化而为有生命之物质者,几无限量。据理以推,则再经悠久之时日,必将尽地球之物质而皆有生命,而皆有心灵。[2](PP.7-8)
人类不能自外于这一普遍进化过程。杜亚泉较为明确地区分了作为自然总体的“进化”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作于1901年的《无极太极论》中,他以传统哲学范畴“无极”和“太极”来表述斯宾塞哲学中的“不可知”与“可知”,以“太极”界的扩大来定义人类的进步[2](P.4),并认为:
文明云者,乃即其秩序之极界扩展于至大之谓。最文明之世,万有皆列于秩序之中而已。我汉族历古以来所期望之天国即在是耳。[2](P.5)
文明的进步,一方面是知识的增进,另一方面是秩序的扩展。杜亚泉并未费力去解说此中知识与秩序的关系,而其实“秩序”包括了知识的秩序和伦理的秩序,或许此时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尚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如何,杜亚泉将置“万有”于知识与伦理的秩序之中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终极目标。结合上文来看,他实际上描绘了一幅物质-生命-心灵-秩序的普遍进化图景。
在这一图景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就显得难以忍受了:
吾侪社会之病态,时进时退,与间歇之疟疾无异。……故一治一乱,成为吾侪社会之惯例者,皆社会之病态,而非自然之生理也。[2](PP.251-252)
在传统哲学的主流、尤其是宋明理学中,治乱的循环恰恰被视为是“自然”的,它被认为是“天理”在历史领域显示自身的方式之一。天理与历史的这种关系抑制了传统哲学中的乌托邦倾向。而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预设就在于太平治世不仅可欲,而且现实历史地可能。只有通过现代人的眼光,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才会被视为“非自然”的和“病态”的。在近代的哲学革命中,公羊学、佛学等传统学术在此种现代观念下纷纷激发出原有的乌托邦潜力。杜亚泉则更具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现实感”[3](P.43),他没有急于去描述一个极乐的“大同”世界,也没有为此展开脱离历史现实的理性规划,但从他对传统社会的上述诊断来看,他对激进主义的批评并不依赖于传统的历史洞见,而是发生于中国启蒙思想的内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亚泉与陈独秀等论敌共享着类似的现代时间意识。就历史运行轨迹来说,中国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前提。
不过,杜亚泉的进步观要比单纯的线性史观更为复杂。这首先体现为对“竞争”价值的怀疑。早在《无极太极论》中,他就已提出,除“竞争”之外,“秩序”同样是进化的天则[2](P.5)。此后,他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的对子,例如分化-统整[2](PP.49-53)、竞争-协力[2](P.11)、利己-利他[2](PP.24-25)等等。杜亚泉一方面认为,这些矛盾的互动构成了总体的进化过程:“进化论谓世界进化,尝赖矛盾之两力,对抗进行,此实为矛盾协进最大之显例”[2](P.32)。这一观点既有赫胥黎“宇宙进程”(cosmic process)与“伦理进程”(ethical process)相对抗的进化图式的影子,又受斯宾塞关于进化之“分化”(differentiation)与“统整”(integration)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上述对子中,前后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后项(秩序、统整、协力、利他等)构成了进化的终极目标,杜亚泉有时认为这是一个人力最终无法抗拒的客观过程[2](P.21)。而我们虽然必须懊恼地承认前项(竞争、分化、利己等)作为进化中的动力性因素,在进化的历程中不可或缺,但这种动力——尤其在人类进步领域——在本质上是较为低级和原始的。矛盾对立的最终结果将是矛盾的消除[2](P.229),在这个意义上,二元互动的辩证过程又可被理解为一元的发展史。例如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表现为“爱”与“争”的冲突,而“争”其实是“爱”有所界限的状态[2](P.25),换言之,进化实际上可以被看作“爱”不断扩充至极的过程。只是在其低级阶段,这种扩充必须采取为自己设置对立面的形式来进行,而在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爱”就有可能褪去它沉重的“争”的外衣,获得其本真的形式。表现此种本真形式的文明形态就是世界和平主义[2](P.20)和社会主义[2](P.348)。
二
与此同时,杜亚泉思想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第二条线索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论题。在1902年的《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中,杜亚泉认为:
故世界之文明者,有二大潮流,即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是也。此二大文明,发源不同,性质自异……基于科学而发达之形体的文明,即形而下之文明,则东固输一筹于西;若属于思想道义界之精神的文明,即形而上之文明,东西之孰优孰劣,固未易遽判也。[2](P.327)
从一开始,杜亚泉的文化保守主义论题就已明确地以文明二元论为立论基础,不过在此时他对二元的区分依赖于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形而下”框架,未离十九世纪末“中体西用”论的窠臼。但是,这一文明二元论是与他在同一时期强调的普遍进化论互相冲突的。如果进化-进步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应该在不同文明中以相同的动力学形式展开,无论这种展开由于环境因素而采取了何种多样的外观,这些外观上的差异相较于共同的动力学形式来说只能被视为是浅表的,而决不能是“性质”上的。换言之,我们总是能将不同的文明形态纳入到同一条进化锁链中。杜亚泉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四千年来讲秩序之学而无成,乃仅存秩序之虚褪,且容竞争于虚褪之中。……转以此虚褪之秩序,隘其竞争之域,而为讲竞争者所败,而虚褪亦将灭裂矣。[2](P.5)
所谓秩序之“虚褪”,或许可以理解为:在没有经过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脱离于竞争的秩序。此种秩序无法形成与竞争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只是真正秩序的虚假和退化形式。秩序之“虚褪”造成了竞争在实际上的无序和狭隘,从而反为讲竞争的西方人所败。在这一普遍进化-进步的视野下,东方所谓“形而上”之文明,其实也就是未被“形而下”文明所充实的“虚褪”文明,而虚假的秩序实际上是进化-进步中虚假的成熟形态。于是,所谓“性质”的差异重新被组织到“先进-落后”的历史叙述中。
因此,并不意外的是,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杜亚泉实际上从这一“形上-形下”文明二元论中退却下来,转向一种更为典型的保守主义论述:具有地理决定论色彩的文明多元论和国家有机体论。环境的多样性造成了国家历史和国民心理的多样性[2](P.152),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共同概念”[2](P.255),亦即国民在意义、价值、道德等方面共同的“国是”[2](P.362)。由于这种“国是”是经由历史形成的,因此它具备向历史开放的可变性。当前的改革应该根据民族特色和现实状况来决定,而不能仅仅依据于空洞的学说和寡头的理性。仅就狭义的理论理性来看,大部分理论都能自圆其说,依靠此种理性并不能在诸理论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只会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的盲目境地[2](P.13)。而国民心理是经过无数世代实际生活中的明智选择凝聚而成的,它比这些时髦的理论更具真理性。因此改革必然是渐进的和珍视传统的。由是观之,辛亥后国内乱局的真正根源,是过于急剧的革命导致了原有价值秩序的失范,传统健全理性的破坏,外来诸理论的横行,和由此而来的物欲的过度释放[2](PP.362-366)。这种混乱状况尤其被进化论中那种强调生存竞争的“唯物论”倾向所推波助澜[2](P.54)。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的文明多元论可以发展为相对主义,从而形成对进化-进步普遍历史叙述的冲击:这一叙述作为理性构建的产物,与所有类似的理论相似,并不能切中具体事物在具体情境下的内在本质。退一步说,即使它是有效的,其有效性也必须限制在如下意义上:进化-进步论是某一时期某一民族的精神状况的反映,因此它作为这一民族的精神传统而被保守,但这种有效性决不能越出这一民族有机体之外。而杜亚泉虽然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对生存竞争论在当时社会中的消极作用作了极尖锐的批评,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作为普遍历史的进化-进步观。毋宁说,进化论中的最新进展——“新唯心论”对“唯物论”的胜利[2](P.41)——与文化保守主义结成了联盟,形成了对当时中国社会乱象的批评。
但这种联盟并不稳固。文明多元论相较于“形上-形下”的文明二元论来说,仅仅是弱化了民族历史与普遍历史之间的矛盾。进化-进步过程指向一个社会主义和国际和平主义的终点,这一历史过程始终是一种同化的力量,因此保守主义者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各不相同的传统是各文明由以发生的起点,但终点只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确切知道这种同化过程是从哪个时间点上起始的。竞争论的支持者将全球竞争视为同化过程的起点,因此中国应该放弃原本的和谐思想,去学会竞争;而秩序论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战结束、新唯心论的兴起是这一过程的起点,幸运的是,这回中国不用去学习得太多。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有什么能够不自相矛盾的理由,去说服西方文明放弃对竞争传统的保守呢?换言之,在“新唯心论”和保守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冲突:两者对传统价值的辩护,一个是“向后看”的,一个是“向前看”的。“向后看”的保守主义期望的是一个“不齐而齐”、每个民族都保有其特殊性的国际世界;而“向前看”的进化-进步论想象的是一个分化到极致、亦即统整到极致的世界整体,而这也就意味着放弃各自的民族特色。
因此,此时保守主义与进化-进步论的联合,是以一种民族特殊论为基础的。它认为,在总体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特定的民族代表了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民族传统是值得保守的,而其他民族则需要面对未来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民族特殊论反过来构成了对文明多元论、以及任何保守主义主张本身的消解。究其实质,这种联合可以被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进步论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非西方文明中的映射。
三
我们无法确知,当杜亚泉在十余年后重提东西文明二元论时,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上述理论困难。一战的惨状使他相信被达尔文所激励的那个西方文明已经失败了,但他从未认为进化-进步的普遍历史叙述是需要被挑战的,以强调互助、秩序为特征的“新唯心论”正昭示着新文明的曙光;国内的乱象愈演愈烈,而西化论者们还在积聚思想和宣传上的力量。他本人则无法抵御理论建构的诱惑,也不甘心将中国文明仅仅视为诸多文明中的一种,只是因为地理上的偶然原因,它才被许诺了未来的尊严。无论如何,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杜亚泉发展了早年《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中的倾向,将东西文明重新置入严整的二元对立之中。
以“动-静”来区分东西文明,在当时的中外学者中都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4]。在“形上-形下”之分中将“形而上”归诸中国,其实暗含着某种表扬,而在“动-静”之分中将“静”归诸中国,则往往表示论者批评的态度。例如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5](P.165),同时又将两者纳入到“古代-近代”[5](P.136)的时间序列之中,倾向于对传统进行激进的全盘变革。杜亚泉的动静论所显示的态度当然与之颇为不同,但即使他本人也曾将“幼稚静默”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弱点[2](P.264)。于是,问题就在于,“静”是如何反转为一个优点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需要注意,“动-静”的文明二元论并非是对文明多元论的自然发展。地理环境的复杂性造成了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但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所谓“性质不同”,并非指“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是从诸多不同文明形态中随机抽取出来放在一起的。对这两种文明的描述大致遵循着矛盾律:人为-自然、向外-向内、假定的人格-自然的人格、胜利-道德、战争-和平等等。在文明多元论中更为细致的民族差异——例如法英、中印等等——都不再重要了,“东-西”之分已经穷尽了所有现有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二元论并非来自对诸文明的经验归纳,而是从进化-进步规律中演绎得出:
自然规律本为矛盾之两方面对抗而成,吾国古来仅从大德曰生之一方面,体念上帝之仁慈,而于造物之残酷不仁一方面,则未尝加以考证。实则万物竞争之剧烈,淘汰之峻严,亦自然规律中之甚为显著者也。……中国社会与欧美社会,文明之根柢既不相同,则生活之方法亦自然各异。[2](P.282)
“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分别代表了“自然规律”之矛盾的两方面。与这一区分密切相关的,与其说是东-西的空间观念,还不如说是进化-进步论中的时间观念。杜亚泉很快就明确了这一想法:
平情而论,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而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2](P.346)
就战后的“新文明”看来,所谓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都是“旧文明”。但这两种旧文明正是造成新文明的关键。西方以动力横决天下,在东方则是在几千年的延续中体现了对秩序的尊重,它们构成了普遍历史中的辩证对立因素。这些辩证式的对子原本是从普遍的进化-进步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动力与秩序的辩证运动充满于进化-进步过程的每一个瞬间。而现在它们被赋予了空间的特征:躁动的西方和静谧的东方分别代表了进化过程中的两个面向。正是在这“旧-新”的时间架构下,“静”才被理解为优点:它是地方性文明能够进入世界历史的两张入场券之一。
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巧妙的理论设计。它的要点在于,首先改变普遍历史的动力学结构,其次将保守主义的诉求完全融入于这一普遍历史中去。历史仍然是普遍的,但在进入综合的“新文明”阶段之前,东西文明分有了两种不同的动力学形式,因此东西方的差异不是表层的,而是“性质”上的,所谓秩序的“虚褪”不再需要被纳入到“进步-落后”的单线序列中去。另一方面,这一设计也避免了单一文明的保守主义所涵有的内在悖论,而这是通过将保守主义的论证中心完全转移至“新”来实现的。
在民族历史与普遍历史的纠葛中,杜亚泉决定性地转向了后者,从而形成了他的保守主义的特色。对中国传统之价值的论证,虽然还保留着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多元论的外观,但其论证的中心已经转向了未来。这一传统只是因为构成了普遍历史中的辩证环节,才与西方一道,避免了其他文明沉没于时间洪流中的命运。这无异于是说,先在之物必须通过某种已经被先行确定下来的未来之物才能得到理解。传统之为传统,并非因为它本身就是内在而又超越于时间的不朽性(如朱熹所理解的“天理”那样),而是因为它构成了通往内在于时间的目的的手段。
正缘于此,他需要和新青年们抢夺“新”、“先进”的高地。只有在明确“新”而非“旧”的固有性质之后,“旧”才能得到妥善的保存。
然二十余年以来,时势变迁,人类社会上别有一种新动机发生,西洋之现代文明,乃不适于新时势,而将失其效用。……然以时代关系言之,则不能不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为新,而以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2](PP.401-402)
四
以空间为标识的“东-西”文化论战,其论辩双方都深刻地依赖于“旧-新”的时间观。因此,陈独秀对杜亚泉的批评也围绕着对进化过程的理解展开:
学术之发展,固有分析与综合二种方向,互嬗递变,以赴进化之途。[2](P.394)
这一批评虽然针对“学术之发展”,其实也正中杜亚泉动静文明二元论的要害。“分析-综合”与“分化-统整”类似,都是描述进化-进步过程中动力与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陈独秀强调,两者应是“互嬗递变”的,如果“分化”与“统整”仅仅指“无秩序的竞争”和“无竞争的秩序”,那么它们对进化-进步过程并无意义甚至造成障碍:“《东方》记者之所谓分化,当指异说争鸣之学风,而非谓分析的发展;所谓统整,当指学术思想之统一,而非谓综合的发展;使此观察为不误,则征诸历史,诉之常识,但见分析与综合,在学术发展上有相互促进之功;而不见分化与统整,在进化规范上有调剂相成之事”。[2](P.394)
文明史中同样如此。我们可以问:如果动-静(以及类似的分化-统整、竞争-协力)等等是两个必须同时出现的辩证因素,那么它们如何可能仅仅单独地分别在东西方文明中出现,而只在未来才能综合?或许可以辩护说,“动”、“静”仅是概括两种文明在发展中侧重的比例不同;但高度的统整只有在高度的分化情形下才会出现,那么,我们又有怎样的理由,来抗辩侧重于“静”的东方文明不仅仅是秩序的“虚褪”呢?为了使保守主义的诉求相容于进化-进步的普遍历史叙述,杜亚泉实际上偏离了对进化-进步过程中两种因素的辩证理解:
然进化之规范,由分化与统整二者互相调剂而成。现代思想,其发展而失其统一,就分化而言,可谓之进步,就统整而言,则为退步无疑。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2](P.363)
如此一来,分化与统整就是两个可以独立存在而非对立统一的因素了。这种改写是经不起严格的理论检视的,这是杜亚泉的保守主义思想无法在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立足的理论原因。此后更为流行的是梁漱溟的“三路向”文化哲学。虽然存在各自的缺点,但仅就理论逻辑的一贯和整齐而言,梁说要比杜说更胜一筹。
另一方面,将“静”的特征归诸中国,并不是一种良好的论辩策略。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传统型的文明当然是“静”的;但在传统内部,动静问题同样复杂。例如儒家不太可能将“静”视为最高价值:相对于生存竞争来说,讲求秩序是“静”的,但相对于佛老的虚静无为来说,儒家的淑世态度和健行的人生哲学则是“动”的。如果我们承认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那么“静”就绝非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准确概括。更严重是,如果脱离了动-静文明二元论的框架(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框架并不那么可靠),那么“静”的特征又会被还原为被当时中外学者所广泛批评的缺点:中国原有的文化精神完全不适应以动力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因此根本性的文化变革就无法避免。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后来保守主义思想中动静关系的翻转:从东西文化的二元论转向科学-哲学、知识-智慧的二元论。从自由意志、“理性之运用表现”等角度来看,论理学[6](PP.80-82)、“理性之架构表现”[7](PP.45-54)等等恰恰是“静”的。动静关系的此种翻转提示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入到了更为深刻的层面。
在更为早先的思想家如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那里,文化保守主义诉求与普遍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是不那么清楚的。杜亚泉可以被视为自觉、系统地处理这一问题的早期代表,同时,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以“进化-进步”为核心的现代观念框架所具有的多样化潜力。相较而言,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似乎已较少能体验到杜亚泉在“动-静”与“新-旧”之间的沉重负担。也正缘于此,在文明论叙述更占上风的今天,我们或许需要探询一个与杜亚泉的关怀正好相反的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一种普遍、有序的历史意识?
参考文献:
[1]高瑞泉.熊十力与近代传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
[2]杜亚泉.杜亚泉文存[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3][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M].潘荣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高力克.重评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J].近代史研究,1994,(4).
[5]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吴芳)
Du Yaquan: Between “Kinetic-Static” and “New-Old”
Bao Wen-x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There is a myth about the East-West Cultural Debate that no common ground exists between Du yaquan as a cultural conservative and Chen Duxiu as a cultural radical. However, further study suggests that there were two independent and conflicting clues in Du’s thought: the universal evolutionism focusing on the dialectic movement between struggle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oriented civilization theory. Du’s kinetic-static dualism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lues: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s have separately yielded two different elements in universal evolution, and they will form a new civilization in a dialectical synthesis way. Du’s cultural conservatism features in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s in a modern linear time (New-Old) framework. This means Du shared a similar modern idea framework with his opponents such as Chen. However, Du’s thought deviates the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wo united and opposite elements in the universal evolution. This is the theoretical reason that Du’s cultural conservatism could not find its place i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Key words:Du Yaqun; East-West Cultural Debate; cultural conservatism; “progressive” notion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1.004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1-0024-06
作者简介:鲍文欣(1985-),男,浙江武义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8
主题研讨清末民初中国的学术和思想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