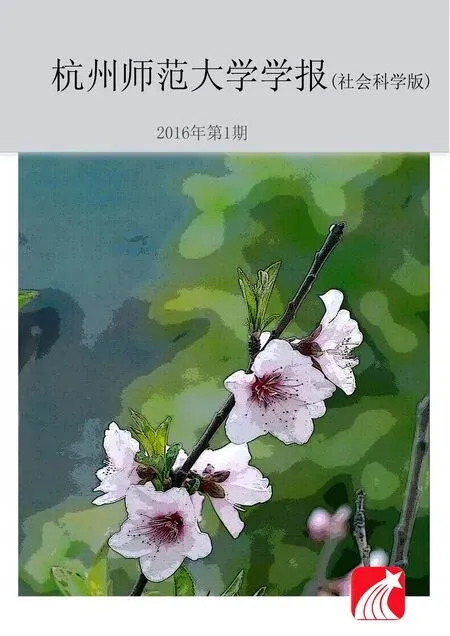“盛世逸民”,或者“多余的人”——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看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2016-03-16曹瑞涛
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文学研究
“盛世逸民”,或者“多余的人”——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看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夏目漱石在其成名作《我是猫》中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明治时代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全景式写真,并将近代意义上的日本知识分子在一个“暴发户型社会”中的尴尬处境特别突显出来,当这些人和得到权力支持的资本家集团发生冲突时,显得格外软弱无力。从某种角度上看,明治时代整个日本社会的进步和退步是并行的,在大改革的年代里,人们往往会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创新和继承兼得并非容易之事。在《我是猫》中,作者将这种贯穿于一个时代的两难情结以喜剧的形式展现出来,于笑声中发人深思。
关键词:日本;明治维新;夏目漱石;《我是猫》;德川时代;知识分子
一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夏目漱石的成名作《我是猫》“是为了提倡写生文的高滨虚子主编的杂志《杜鹃》所创作的写生文”。[1](P.175)如果从日俄战争后占据日本文坛主流地位的法国文学观念来考查,“文”这种类型与“小说”并不相同,“小说的第一要素是情节”,而所谓“文”,漱石本人就以为:“写生文没有什么情节线索,他说道:‘情节是什么?现世中是没有情节线索的。在没有情节线索的现世中硬要理出情节来观之则无从开始的。’”[1](P.178)
然而,《我是猫》也并非全无情节,其叙述结构更不似——如漱石所云——海参般随处可以开始,又随处可以断开,比之“现代小说”重视情节之精彩性,作为“文”的《我是猫》里的情节仅仅是被有意淡化了。所以,作者的叙述尽管显得有些拉拉杂杂,但读者仍然可以从中理出一条虽纤细却不失清晰的线索,即:中学教师苦沙弥与资本家金田之间的斗争史。
追溯这场斗争的源头,全怪苦沙弥的高足:寒月,他莫名其妙地喜欢上金田家的千斤,金田觉得正在大学苦读的寒月若能得个博士头衔,招这女婿就有赚头,便派自己格外嚣张的老婆“鼻子夫人”(她脸上有个夸张的大鼻子)去盘问苦沙弥,叫他估算一下自己这位得意门生是不是块博士的料,不想竟遭了这“穷不死的教员”的白眼,金田大怒,动用一切手段整顿苦沙弥,苦沙弥则以鸡蛋碰石头的勇气积极应战,两人(实际是两帮人)就这么掐了起来。
若按照“现代小说”的路数,你来我去的争斗情节一定会被大书特书,写得格外热闹,可落笔为“文”的漱石更像一位年鉴派历史学家,他仅以聊聊数笔粗描出斗法之大概,将省下的笔墨毫不吝惜地用在对双方人物古怪生活方式不厌其烦的细绘上。恰是通过这种非“小说”式的叙述,整本书才宛若一幅壮阔的浮世绘画作,对明治时代东京城里各色人物来了番全景展示。
循着这幅画卷,可以看到因发明“三缺主义”——“就是要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的意思”[2](P.113)——而暴发的金田一方实力强大,除了嚣张的“鼻子夫人”,还有金田手下悍将铃木藤十郎,此人是苦沙弥旧日同窗,如今跟在金田屁股后面混得风生水起;苦沙弥的邻居二弦琴师、车夫、车夫的老婆等人,都被收买来刺探情报外加游击骚扰;主力进攻部队由“落云馆”中学里的精壮分子组成,他们不断把棒球打进苦沙弥的破园子中;此外,与金田同乡的津木针助、福地细螺两个大人物虽未出场,看架势只要苦沙弥顽抗下去,这二位就能跳出来砸他的饭碗!
苦沙弥一方则显得东倒西歪、弱不禁风,引发战争的寒月是个单纯的书呆子,喜欢就是喜欢,毫无现实算计,而且他整天钻在实验室里研究什么“紫外线对于青蛙眼珠电动作用的影响”;美学家迷亭俨然黔驴一头,只有乱开玩笑、虚张声势吓吓人的本事;筹划“诗剧”的新潮诗人越智东风,思考着“日西文明之比较论”的哲学家杉杨独仙,基本上属于“打酱油”路过的角色,不帮倒忙就很不错了;苦沙弥贤惠的夫人除了搞后勤外,便以唠叨、埋怨的方式表达些对丈夫的关心和支持。
鉴于出场亮相的人物众多,情节线索又格外细微,《我是猫》中那只名为“猫儿”的猫儿便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是借助“猫儿”在两大阵营间神鬼不觉地穿来穿去,才如针线般将暴发户金田一派与苦沙弥及其一波闲散清高的朋友联系在一起。它又像是一面着了魔法的镜子,将金田及其走卒们的丑恶嘴脸,以及苦沙弥和其朋友们精魂中那种古旧与新异的混搭、清高与胆怯的杂糅以及自命超然又尘心未了的窘境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来。
于是,通过“猫儿”的不断旁白,读者在斗争之初就得以知悉那个自信通过手里的“钱力”能够买到“权力”的金田有一种把人不当人看的毛病,一提到苦沙弥便以无比轻蔑的口气说道:“是个当教员的呀”,“仿佛一当了教员,就不论怎样的侮辱也得像木头人一样乖乖地接受下来”。[2](P.104)而“猫儿”的主人苦沙弥居然不受这气,他可以对搞稀奇古怪研究的旧日弟子寒月心生敬意,他能够被博览群书的迷亭唬得一愣一愣,偏偏“对于资本家的尊敬程度却极低。他深信中学教员要比一个资本家伟大得多”。[2](P.74)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苦沙弥的朋友们也都一个德性,所以当美学家迷亭遇到来为金田当说客的铃木藤十郎时,便毫不客气地骂道:“世间还有比知识更贵重的东西么?不待说是没有的。如果用跟知识不相称的东西来酬报知识,事实上只有损害知识的尊严。……金田某某是个什么东西呢,不是把鼻子眼睛都钉在钞票里面的家伙吗?”[2](P.74)那会儿的日本社会正在“殖产兴业”的招牌下拜金之风大盛,对于放着钱不赚,把知识看得如此高贵,又研究些莫名其妙玩意儿的苦沙弥之流,挨了骂的铃木回去向他主子金田一报告,金田八成会骂道:“一群怪物!”
二
苦沙弥和他的朋友们并非什么“怪物”,他们只是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中出现的第一批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已。依丸山真男的意见,传统社会或者说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在古代的埃及帝国,大体具有共同特征。如神官、僧侣、大学博士、中国的读书人,这些都是‘体制知识阶层’。从他们担当的任务来看,他们是社会中正统世界观的垄断性解释者和授予者。”近代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首先是从身份的制度的锚缆中解放出来,再就是从正统世界观的解释和授予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这两种解放是其诞生的前提。‘自由的’知识分子诞生于这两重意义中”。[3](P.107)
明治时代日本“自由的”知识分子就颇符合这两种解放的要求,他们“几乎都是曾仕奉于幕府的蕃书调所、或学问所的知识阶层。萨长藩推翻幕府一方中没有出现多少,反而从幕府一方或佐幕诸藩一方产生了初期的近代知识分子。被打倒一方比较快地被身份抛弃,其处境容易产生一种‘被根除了’的意识”。[3](P.108)特别是这批人中从事文学的,“或是从官僚制的阶梯中落伍者,或是对直接环境(家和乡土)的逃逸者,要不然就是为了弥补政治运动的挫折感才进入文学领域的,不管哪种情况,都背离了日本帝国‘正常’的臣民途径”。[3](PP.55-56)
漱石本人的身世和进学修业的历程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此类知识分子。漱石之父夏目直己本是幕府时代管辖东京早稻田周边的名主,那里有条名为“喜久井町”的街道就是由直己命名,漱石回忆说:“我家的家徽是井字形花纹上画着菊花,因此就以菊花加井来命名这个地方,这就成了喜久井町。”[4](P.74)*日语中“菊”与“喜久”发音相同。入明治朝后直己作为幕府旧人很不得意,以致家境衰败,漱石两岁时就被送到盐原昌之助家当养子,七岁时又因养父母离异被生父赎回,之后因户籍问题夹在养父与生父间,可谓被抛弃了两次,心理上自小就缺乏归属感。
成年后的漱石作为第一批文部省官费留学生被派到英国“研修英语”,同期去德国的芳贺矢一、高山樗牛都被明确要求学习“文学”,漱石则只要求学“英语”。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为:当时德国推行的强硬军国路线合乎明治政要的胃口,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中,描写恋爱婚姻为中心的家庭浪漫小说占着主流地位,日清战争后的‘大日本帝国’是不可能以此联合起国民感情的。不过,为了了解和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使用英语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知识情报,‘英语’是必要的”。[5](P.37)
虽说漱石在英国生活得非常不舒服,可英式自由主义精神还是深深影响了他,在大正三年(1914)学习院辅仁会的演讲中他公开承认:“老实说,我是不喜欢英国的,我讨厌它。但事实确实如此,我没法不实话实说。那么热爱自由,而且那么秩序井然的国家,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日本毕竟无法和它相比。但是它们还不仅仅是自由,他们爱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自由,人们从儿童时代就受到这种社会教育。”[4](P.132)学的是不受重视的英语,又怀有英式自由主义思想,这样的人呆在日本实在逃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
因而,漱石在写作中每每通过细节处看似不经意的勾描,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复杂身世以及无可逃避的孤立感含蓄地表露出来。于是,我们会发现《我是猫》中的苦沙弥闲坐家中时总要穿一件染有家徽的黑布褂,借此标明其“父亲本是旧幕时代近郊的一名村吏”。[2](P.271)寒月的褂子上则配着一条紫色带子,寒月老实交待道:“这根带子确是我祖父征讨长州时用过的。”[2](P.93)*幕府曾在1864、1866年两次出兵征讨作为“勤王倒幕”运动中坚力量的长州藩。迷亭虽然洋派,也有一位仿佛从江户初年穿越来的汉学家伯父,老人家头上依旧盘着个发髻,出门时手里必握一把据说是室町时代流传下来的铁扇,虽然也承认现政府英明,却又不时地念起“将军”的好来。
与此同时,这群古雅之士对外面的新世界不但不拒绝,还有着极大兴趣,他们大量阅读西方启蒙时代的科学、人文著作,甚至亲身去欧美游历、求学,进而在“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6](P.362)这一“誓言”感召下,对自由、民主之类新事业格外热衷起来。然而,朝中在立宪问题上“表现出主张以英国为楷模、立即实行政党内阁的议会中心主义的大隈,与主张逐步实现以君主为中心的宪法的伊藤及井上之间的冲突”。[7](P.92)冲突结果令他们大为失望,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后,英式道路被否定,日本步入普鲁士德国式的绝对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道路!大喇叭里成天叫喊着“大和魂”,从东京到乡下,人们动不动就亢奋地振臂高呼“万岁”,吓得鸡也飞、狗也跳。
漱石对此十分厌烦,他特意安排苦沙弥在朋友诗会时念了首关于“大和魂”的新作。苦沙弥念道:“日本人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着,大喊道:‘大和魂!’”所有人都这么声嘶力竭地大喊,可“到底大和魂是什么东西呢?回答道:就是大和魂呗。回答完就走过去了,走过了几十丈路之后,可以听到哼了一声。”最终,“大和魂像字面所示,就是一种魂。唯其是魂,所以永远是飘飘渺渺的”。[2](P.183)听完这段奇文,平常极爱讽刺挖苦人的迷亭居然没有惯常地乱评一番,大家顾左右言他了一阵子,就匆匆散了。
看来,不论现实中的漱石,还是小说中的苦沙弥及其朋友们,作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双重“解放”后,注定游离于正统意识形态之外,为新政权所排斥。边缘化令人不快,但只要摆正心态,“不爱帝城车马喧,故山归卧掩柴门”,[8](P.41)做一个悠哉悠哉的盛世逸民,自有高格,不失风雅,也是个不错的归宿。可惜,这般逍遥洒脱的生活断断是苦沙弥之流求之不得的,因为日本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特殊的身世使他们大都逃不出旧幕府大部分遗民的劫难:穷!
三
关于“逸民”、“隐士”,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谋隐’无成,才是沦落”。[9](P.5)入明治朝后,旧武士阶层整体处于求显不得、谋隐无成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大抵是“因为武士并不像商人和农民那样(虽然这两者的形式也显然不同),在新社会中有固定的立足点,所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别阶级而继续存在下去。可是他们必须适应这种社会变革,而改行去作中央和地方官吏、小商人、资本家、职业军人、农民、手工艺者、工业工人、政论家、僧侣、教员以及除武士而外的任何职业”。[10](P.83)
改行的结果如何呢?当时重臣阁僚的意见与现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得了伯爵头衔后的大隈重信就认为转型非常成功,他说:“维新变革使士族忽失其常职、世禄、特权,与平民比肩争竞其生存。其中刚愎不适于时势者,反抗新政府虽多作乱以抗新政府,迂愚者虽多暴弃以堕其业,而聪明则咸归于新政府,任其文武官,或按新制度从事于教育子女之务,或用力于农、商、工之实业,开始其适应时势之新生活。其间士族之阶级未曾消灭,维新之后转盛,与庶民增数之情势无所异。”[11](P.1337)
如今学者的描述却是另幅景象。维新后,尽管“与一般平民相比,政府在任用官吏、警察、军人、教师时,对于士族总是优先录用,为之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据周启乾估计,40万户士族中享受到这份特权的仅占10万户左右,大部分旧士族仍趋于贫困化。[12](P.72)在少数富庶地区,如大阪府,“据1881年9月的调查,当时该府所辖士族总户数为3434。其中生活较为安定、找到经营门路的有788户,入官途的287户,占总户数的31%。虽未直面贫困但尚无经营目标的1590户,占全部户数的46%,完全陷入贫困状态的478户,占总户数的14%”。其他大部分地区情况要糟得多,比如在广岛,“据1883年的调查,在全部士族中,生活富裕的上等户占4.9%,生活尚可的中等户占13.7%,生活困难的下等户占78%,生活无着落的无等户占1.6%”。[13](P.224)
维新之初新政府承诺替代各藩来支付武士俸禄,但1874年财政改革时却将禄金与不断上升的大米时价脱钩,导致士族实际收入下降;1876年8月新政府又发布了《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宣布废除对家禄、赏典禄的支付,代之以发给金禄公债证书,急着用钱的武士一旦提前变现,收入则大幅缩水。之后,不少“武士把金禄公债作为资本即便转业到农工商业上,由于他们传统上蔑视这些职业,对这些职业并不熟悉,很多人因为事业失败而失去财产,甚至被讥笑为‘士族的买卖’”。破产武士及其家人的处境十分悲惨,“从1879年5月2日朝野报纸‘茨城县通信’栏目的报道内容可以看到,‘士族女子做私活作娼妓者多,定价白天10钱晚上15钱,可到鸡肉炖锅店、寿司店、豆羹店等上门服务’”。[14](P.46)
由此可知,“维新”根本上讲是一场革命,尽管其中暴力因素被极力压缩,却仍回避不了革命的宿命,即:旧统治阶层整体没落。相对于经济学枯燥的数字,鲜活的文学作品成为史料更为生动的补充,使人们可以真切地听见埋藏在数字里的无数叹息与哭泣之声。在那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以前古诗中才能读到的“朱雀桥”、“乌衣巷”之类典故不再遥远、生疏,国木田独步在《河雾》中就言道:“在日本全国,一般的情况是:不论是哪一个城镇的街道,都有了新的变化;只有士族住的巷才变得更古老了。”[15](P.57)
旧士族无法适应新社会的情况也频频出现在当时许多文学作品中,如《浮云》里主人公内海文三的父亲,在旧幕府当差吃俸,到了“幕府瓦解,王政复古,万民归顺的明治盛世”,蛰居于故乡静冈,终日无所事事,“两臂空有着真阴派剑术的本领,但是不会拿锄使锹;在言谈交际上呢,由于矫揉造作地庄重惯了,一时既不能低三下四地说出个‘是’字来;要挑起担子来吧,又怕玷辱了门庭,惹人家耻笑。于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走,好不容易才在静冈藩的史官处里找到一个职务,真是高兴非常,不过到头来也只是个腰里带着饭盒上班的小差事”。[16](PP.10-11)
在《破戒》里,士族出身的风间敬之进靠做小学教员勉强糊口,一家人过得如叫花子般凄凉,在只差半年就可以领到退休金时又惨遭淘汰,这位潦倒不堪却又端着旧武士架子的老人无奈地叹道:“回想起来,世道变得真快呀,变啦,变啦!……到各处一瞧,古城址大都变成了桑田,所有的士族都完全衰落了。那些凑合着勉强活到今天的人,都是到官场上弄个一官半职,再不然就去学校教书混日子。唉,士族是最没有用处的人啦,说起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17](PP.44-45)
漱石笔下的苦沙弥同样狼狈,虽然他那房租便宜的宅邸孤零零地被五六颗大柏树包围着,不禁让人联想“这里的主人是一位在荒山旷野里、和一只无名的猫儿一同过着安闲岁月的江湖隐士”。[2](P.214)可“猫儿”早就看出来衣服上印着家徽的主人和深山中的猴子没什么两样,因为“捉到深山的猴子是用铁链锁起来的,猴子尽管龇牙咧嘴、乱蹦乱跳,但可以放心,它决伤不了人。至于教员虽然没有被铁链锁住,却被薪水束缚住了”,[2](P.219)尤其如“主人这样不善圆通的人,被免职以后,一定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就非饿死在道旁不可”。[2](P.208)
身为沦落阶层中的一员,又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读了太多不合时宜的书籍,作为知识分子欲隐而不得隐,羞涩的钱囊,窘迫的生计,这就是苦沙弥的七寸所在,无论他的榆木脑袋如何顽固,金田看准这点,便足以教训得他头痛上火,苦沙弥的失败是注定的。
四
有人没落,就有人发迹,当社会上层被维新运动腾空出来后,不愁没人去填充。生力军大多来自旧有统治集团的底层和外围,如丸山真男所云:“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所有方面,近代日本都是暴发户型进升的社会(统治层本身则多由这些暴发户构成)”。[3](P.46)在这暴发户的行列里,除了维新之初一批萨长蕃的低级武士一飞冲天外,最大的“黑马”莫过于整个商人阶层。
明治时代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在一篇论旧商人性格的文章中说:幕府时代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被蔑称作“町人”,处于社会底层,做买卖全得看掌权者的脸色,所以经常要“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18](P.43)只有将如此卑贱的事做周到,生意才可以发达。明治维新后,商人们终于挺直了腰板,不仅不受当权者的盘剥和打压,反而在“殖产兴业”的政策下得到权力越来越多的扶持。
明治初年社会上出现“政商”,即“遵循着政府的振兴实业政策,或者利用政府给予的特权,或者承办政府的任务而形成了巨大资本积累的商人资本”。[19](P.11)明治二十年(1887)后,各大商贾逐渐脱离“政商”身份,开始向“财阀”转型,这种以亲族为纽带的康采恩形态带着浓重的血缘家族性与政治权力交融在一起。到日俄大战前后,随着政党政治的腐败,大商人们甚至“觉得与其不断地慷慨解囊资助有交情的政治家,不如用那些钱去弄个大臣当当,或者当上总理大臣,那才便宜呢。反正一捐款,自己就能成为政治家,最终还会当上大臣,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才有意思。于是,有钱人便开始热衷于政治……”[20](P.624)
虽说商人阶层在新时代咸鱼翻身,不仅得了“资本家”的新名号,还能染指权力,横行于世。可细查其中成员具体变化,则会发现到了明治后期,从德川时代的商家延续下来成为财阀的只有三井和住友两家,“德川时代的商家除这两家之外,还有很多富豪,但其中大部分在明治维新以后都因无法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而没落了。三井和住友之外的所有财阀都起家于幕末维新时期,在经济动乱中抓住机会,他们与德川时代的大商家没有关联。”[21](PP.238-239)所以在翻身的商人阶层内部,自然也是以新生暴发户为主力军,漱石笔下的金田便是其中之一。
“倒幕”运动中许多富商看准时机,果断站在胜利者一方,然而这些富比大名的旧商贾受得了幕府时代的气,竟享不了明治时代的福,纷纷败给白手起家的新生暴发户,着实出人意料!虽说导致这结果的原因十分复杂,不过将视界从明治朝扩大到德川时代,或许能在两朝交替中世风、文化的变化里找到些线索。纵览德川一朝,初期的三代将军是通过武力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封建体制,“从第四代将军家纲开始,经五代纲吉,到六代家宣、七代家继,这六十五年左右的时间(1651-1716)是灿烂的文化和礼教政治的时代。它不仅显示了幕府政治的巨大发展,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进步。”[6](P.289)其后直到幕府灭亡,日本一直处于和平安定状态。
漫长的和平年代里,武士阶层无仗可打,甚至连架也不许打,统统集中在城市里变成纯粹消费者,吃闲饭还能骑在百姓头上,武士特权的合法性开始受到挑战。故而自德川中期开始,为“与自身政治上的统治、支配地位相一致,武士阶级也力求在见识、教养、人格、体力等方面优于三民,尤其是拥有与其他三民俨然有别的、‘高贵’的价值伦理。”[13](P.109)*“其他三民”指与武士所属的士族相别的农、工、商阶层。日本学者家永三郎就明确指出:“明治以后的伦理学家美化为普遍道德、在欧美各国也大肆宣扬的所谓‘武士道’,是江户时代形成的观念形态”。[22](P.89)
依此观念,江户朝的武士们不仅要遵从(哪怕只是表面上)新渡户稻造后来总结出的“义”、“勇”、“仁”、“礼”、“诚”、“名誉”和“忠义”等道德原则,而且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也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情调、越来越贵气。至江户末期,武士们再也不是镰仓、室町时代质朴、粗野、嗜杀成性又极其现实的武夫了,他们成了风雅的学者、诗人、画家、戏剧大师、开宗立派的思想家……总之,他们大多变成了腰里还挂着把刀的文人雅士。也正因这两百年的积淀,才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被排挤出明治权力体系后,能转变为日本社会中第一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旧商贾尽管以利为先,但生活在“武士道”真正盛行的朝代,其行止并非如涩泽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作为明治朝发迹的新财阀,涩泽之言难免厚此薄彼。换一个角度看,在江户中期,江户和大阪的商人们“与德川的经济制度已完全融为一体,并深受为统治者尽忠效劳的统治阶级的儒教观的熏陶。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忠诚信念、自尊感和对社会秩序的尊重与节俭、精打细算和经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23](P.30)由此产生出以“石田心学”为代表的商人伦理,其中“承认武士的伦理是商人伦理的模范。‘武士堪称世人之镜’。‘无论任何事,武士均值得以最佳楷模来效法。’”[13](P.114)
在这些商人伦理的规范下,老一代商贾做生意时会主动考虑诚实、守信、名节等问题,不少人还照着武士的样子附庸起风雅来,学得有模有样。倒是入了明治朝,随着武士阶层整体没落,“武士道”尽管被宣传机构叫得震天响,可那套旧精神体系已经散了架,依附于其上的传统商人伦理体系自然紧跟着散了架。老观念支配下的大商人显得格外迂腐,处处被动,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愿做;而诸多抓住机会的新商户们则无不有种得解放的感觉,旧行规渐渐松弛,背后还有官家撑持,可以放大胆子赚钱了!
于是,金田之流生逢其时,大发不义之财,再用钱来买权,进而买来各阶层人们的崇拜。连文化、知识界的人们也跑来捧场,没有品味的,如苦沙弥的同窗铃木藤十郎,整天跟在金田的屁股后面上蹿下跳;有点品味的,如《虞美人草》中小野清三,更是急不迭地尽起“二十世纪诗人的本分”,“他们日夜在实现文明时代的诗,风花雪月地诗化富贵现实生活。”[24](P.162)
金田之流被这无数献媚的眼神簇拥着,昂首阔步地横行在街头,简直与金田的老婆“鼻子夫人”脸上那个硕大无比的鼻子一样,傲慢霸道地耸立在脸面的中央,肆无忌惮地挤占着嘴巴、眼睛、眉毛的位置,好一幅得意洋洋、理所应当的派头!偏偏一个顽固不化、一身迂腐气的苦沙弥,居然敢和资本家作对,不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又是什么?
五
重新回到关于“文”与“小说”区分的问题上,虽然漱石以“文”的形式来冲击“现代小说”注重情节的叙述方式,可他的目的却不是要恢复“江户文学”的诸种类型,实际上“漱石所要恢复的乃是‘政治小说’式的文学形式,他与试图拒绝参与到明治20年代以后国家体制的建立或‘现代小说’之建立中去的自由民权派残余势力相仿佛。在他的现代小说批判中完全没有那种对江户文学或前现代的乡愁,他是彻底的现代人。”[1](P.190)正因如此,漱石才会在《我是猫》中借助“文”这种传统类型,来全面、充分地揭示出日俄战争以后与国家结托的资本家之霸道、嚣张,在拜金主义冲击下整个社会风气之粗野、庸俗,以及近代日本“自由的”知识分子之无奈、苦闷。相对于自然主义者把明治时代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还原为“人性的丑恶”,漱石则在其前期作品中直面铸成这些错误的现实原因,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性。
当然,漱石也不得不承认:在喜剧舞台上,当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被撕碎给人看时,它们早就在现实生活中把美好理想撕得粉碎。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绪与笑声相伴。漱石借“猫儿”之口叹道:“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功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2](P.238)在这现实面前,继承了德川时期古雅之风,又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熏陶的近代意义上的日本知识分子们,表面上仿佛“盛世逸民”般超然世外,实际上不过是一群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中越来越不合时宜、处境日渐被动的“多余的人”。
最终,对于虽被金田整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提起革命却又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的苦沙弥,还有聚在他那寒宅破屋檐下“像丝瓜一样,随风吹摆,自命超然,但实际上却依然有尘心,有欲念”[2](P.55)的太平盛世的逸民朋友们而言,往后的日子实在没什么精彩故事可写了,连“猫儿”也觉得无聊,学着东家的样子偷喝起啤酒来,只是不胜酒力,几怀下肚就飘飘然栽到大水缸中,挣扎了几下便进入了那“日月晦冥天地粉齑的不可思议的太平世界。”[2](P.378)
参考文献:
[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夏目漱石.我是猫[M].尤炳圻,胡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M].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4]夏目漱石.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M].李正伦,李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张小玲.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坂本太郎.日本史[M].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依田憙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8]夏目漱石.夏目漱石汉诗文集[M].殷旭民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诺曼.日本维新史[M].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1]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12]周启乾.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13]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14]江新兴.近代日本家庭制度研究[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
[15]国木田独步.武藏野[M].吴元坎译.上海:文匯出版社,2011.
[16]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小说集[M].巩长金,石坚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7]岛崎藤村.破戒[M].陈德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8]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19]柴垣和夫.三井和三菱[M].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2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M].郭洪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1]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M].李国庆,刘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2]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刘绩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3]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M].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4]夏目漱石.虞美人草[M].茂吕美耶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吴芳)
A Hermit in a Flourishing Age or a Supernumerary:
On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sume Soseki’sIAmaCat
CAO Rui-t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In Natsume Soseki’s famous novelIamacat, there is a panoramic view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society in Meiji Age. 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in a nouveau riche society. The intellectuals appeared to be so impotent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capitalist group suppor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a sense, progress and retrogression were mixed in Japanese society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as people will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 InIamacat, Natsume Soseki describes comically the dilemma that the intellectuals were impossible to avoid in that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alls for deep thought in laughter.
Key words:Japan; the Meiji Restoration; Natsume Soseki;Iamacat; Tokugawa Era; intellectuals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1.010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1-0071-07
作者简介:曹瑞涛(1973-),男,山西太原人,满族,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现代化问题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