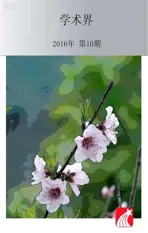“人法地”:《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及现代价值刍议〔*〕——以钱锺书关于《老子》的“两副哲学”观点为中心
2016-02-26○王进
○王 进
(贵州大学 哲学系, 贵州 贵阳 550025)
“人法地”:《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及现代价值刍议〔*〕
——以钱锺书关于《老子》的“两副哲学”观点为中心
○王进
(贵州大学哲学系, 贵州贵阳550025)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人”应该划分为两种人:“大人”(圣人)和“众人”(凡人)。前者属于政治的统治者,他们不仅可以法地,同时也应该法天、道、自然;后者则为被统治者,他们只能法地。政治的对象和基础是凡人,基于天、道和自然的品质特性与人有着巨大的质的差异,如人效法之,将使人抽象化,丧失人之“属地”特性,从而抽调了政治的基础,使政治走上“非政治”的道路。所以,“人法地”成为《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和基础。由此派生出《老子》政治哲学的清醒冷静的现实感。这样的特质使之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底色作用。现代政治要避免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借鉴和反思“人法地”的思想不失为一良好途径。
《老子》政治哲学; “人法地”; “两副哲学”; 冷静清醒的政治态度
在既往的研究中,对《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 中“人法地”的理解,学界目前较为普遍、流行的看法是:“绝不能理解为人只能法地,不能法天、法道、法自然,而应当理解为人既需要法地,因地法天,人亦需法天,因天法道,人亦需法道,最终是人法自然。”〔1〕对此看法,笔者难以苟同。因为这样的理解过于大而化之、一概而论了。若依此之见,惜墨如金的圣人何不直接跨越道破而非要费力费墨如此?对此,正确的理解或许应该是对此处之“人”进行分析界定、区别对待。对一部分人来说,不但可以法地,也可以法天道自然;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只能法地。后者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部分,而政治建构必须以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为对象,由此,对于指导现实政治实践的《老子》政治哲学来说,“人法地”成为《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和关键。《老子》也正是由此介入中国传统政治生活并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今天,吸取“人法地”的思想,对于抗拒现代政治的“癫狂”本性,重建政治的“属地”性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
“人法地”源出于《老子》第二十五章,为了分析的方便,将其全文揭示于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先于天地而生,其本性“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居于“本体”(中文语境之“本体”义)、根本之地位。从此而降,依次而有天、地、人。这一构成秩序等级,乃从上至下的立体结构而非并立之平面。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一个问题,即每一层次所效法的对象问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顺序与道—天—地—人的顺序刚好相反,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下至上。换一种说法就是低一级的仰望、效法高一级的。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样的等级顺序是否可以错乱?也就是说,人是否可以跨越“地”而直接效法“天”“道”甚至“自然”呢?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人、地、天、道和自然各自的品性特质进行分析。 我们循序依次进行考察分析。
人,《尔雅·释名》:“人,仁也,仁生物也。”《说文》的解释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天地之性冣贵者也。冣本作最。……《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按禽兽艸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一看即知,无论是《尔雅》还是《说文》,对人的解释基本都是基于儒家的解释,带有浓厚的形上色彩。
这样的解释与《老子》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去寻找和确定《老子》的解释。但问题接踵而至——纵观《老子》全书,对于“人”并无清晰的、哲学的、抽象的说明和界定。反之,《老子》有的只是对人的类型的划分。观《老子》一书,“人”字一共出现102次,其中以“圣人”词组出现的一共有31次,以“众人”出现的有5次,其余的皆以单词(人)出现。对之进行区分判别,它们可以区分为两类:“圣人”和凡人(普通人),“众人”属于后者。换言之,《老子》并没有抽象和概括出一个可以统摄圣人和凡人的普遍的“人”的定义。如此以来,要清晰地说出《老子》的“人”的观念相当困难。我们只能说,《老子》似乎较为推崇“圣人”,但对某一类型之人的推崇,并不等于就是普遍的“人”的定义。
其次是“地”和“天”。《尔雅·释名》:“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说文》:“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元气初分,轻淸昜为天,重浊侌为地。元者,始也。阴阳大论曰。黄帝问于岐伯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大虚之中者也。黄帝曰,冯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按地之重浊而包举乎轻淸之气中,是以不坠。”两书解释之重点在于说明“地”之形成及其“重浊”特性。“天”则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下面是个正面的人形(大),上面是人头,小篆变成一横。其本义指“人的头顶”。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天,顚也。……顚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偁。……从一大。至高无上。”从“天”的本义来看,天“高”“悬”于人之“顶”上,与人有着巨大之物理空间上的距离。在《老子》一书中,地常与“天”联用为“天地”。分开使用时大多在于需要区分其不同之特性:“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老子》第三十九章),天地因为所得之“道”不同,故有不同之特性,也即所谓天“清”地“宁”。但是天地也具有相同的“不自生”、不自私的特性,所以能够“长且久”——“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
从以上可以看到,传统思想对人、地、天的解释多集中于其各自品质特性方面,但对于其共性则缺少关注和分析。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吸取唯物论的看法。在传统唯物论研究者心目中,老子常常被认为是唯物论者。这样的观点并非不可取,相反它倒是道出了实情。按照此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对天地人三者的共性做出一个概括:天地人三者皆具有物质性,为感性的物质存在。其间之唯一区别仅仅在于三者在存在形态上的差别而已——天的密度较地和人要小和稀薄得多,地和人的密度要大。地广大厚实,人则具体而微。
其次我们来看剩下的“道”和“自然”。一眼就可以看出,相较于具体物质性的天、地、人而言,“道”和“自然”相当“抽象”,不再具有具体的物质性,而是属于思想上的理论建构。这一点相当明显,无须赘述。
总结来看,我们可以将自然、道、天、地和人五者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抽象的“自然”和“道”,二是具体的天、地和人。前者不可见,后者则具体可感。从更大范围的“域中有四大”的角度看,道、天、地和人四者不仅各自存在质的差别,而且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一立体的结构,而非平面的并列关系。从效法的关系来看,存在从低到高的关系,也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现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人是否可以僭越“地”而直接效法“天”“道”甚至“自然”?
二
就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而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人可以跨越“地”而直接效法“天”“道”甚至“自然”。〔2〕在笔者看来,研究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其原因当然众多,但是忽视了上文所言的对人、地、天、道和自然各自性质的区分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立体而非平面)的确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与上述流行观点不同的看法,藉以获得新的启示。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老子王弼注》中言:“人、地、天、道四者累迭而取法乎上,足见自然之不可几及。一、五、六、七、一六、二三章等以天地并称或举天以概地,此则以‘法地’为‘法天’之阶焉;一、一六、二五、三二、四二章等以‘道’为究竟,此则以‘法自然’为‘法道’之归极焉。浑者画,简者繁,所以示人为‘圣’为‘大’之须工夫,明‘我自然’之谈何容易,非谓地、天、道亦如职官之按班分等、更迭仰承而不容超资越序以上达也。尝试论之。恶‘天地’之尚属分别法也,乃标‘混成先天地’之‘道’。然道隐而无迹、朴而无名,不可得而法也;无已,仍法天地。然天地又寥廓苍茫,不知何所法也;无已,法天地间习见常闻之事物。”〔3〕尽管钱先生在此的重点是解释说明“法自然”,并非在于探讨本文之主旨,但我们还是可以借之而获得数点启示。钱先生首先说明,人地天道四者之关系为“累迭”关系,也即上文所言之“立体结构”;次而指出“自然”之“不可几及”之崇高无上性;再而指出“道”的属性“隐而无迹、朴而无名”,从而人“不可得而法”。在此情况下,只有退而求其次,“仍法天地”,但是“天地又寥廓苍茫,不知何所法也”,无可奈何之下,只有“法天地间习见常闻之事物”。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数点新的看法:一是对人地天道相互关系的认识;二是人、地、天、道和自然各自性质的区分,因为各自性质不同,所以效法之对象也相应不同。那么,人到底应该效法什么呢?
诸多前贤关于何以“法地”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有益的启示,但是综观其说,主要在于从人的“德性”建构角度出发〔4〕,而恰好忽视了“地”的最基本的属性——物质性。此基本属性与人恰相对应,从而与人构成“人—地”之相联相关性。人是一个现实、具体的感性的物质存在,并不是抽象的非物质存在。换言之,人的存在具有唯物性。在地、天、道、自然四者之中,唯有“地”和“天”具有与人的物质存在相应之唯物特性。但“天”高悬于人之“头顶”上(“天”的本义),其广阔无限的形态与人有巨大差异,假如人效法之,则将“稀释”人的物质性;“道”与“自然”则抽象而不可闻见,如人效法之,那将使具体的人“抽象”化。无论何种结果,都将使人不再是“人”。人本来立足于“大地”,但“天”“道”和“自然”却使之升腾高举,使之成为高飞云天的诸神或者不可显见之其它存在。但是,政治哲学所指向的却是具体的政治共同体,是具体现实的人类社会,是居于其间的“人”而不是抽象的脱离了社会的神和兽。从更深的角度来看,效法天、道、自然的结果,表面上看,是使人的特质遭到“稀释”和远离大地,但其实质是使人去除了其“属地”的社会性。问题是,对于那些已经丧失了其社会性的人来说,政治的存在是否还有必要与可能?即使有可能,但这样的政治的品质到底将会出现何种情况?毫无疑问,政治将由此走上远离人类实际的“非政治”道路。在这一点上,儒家有类似之眼光。在历史上,儒家历来排斥和打压佛老两教,斥之为“异端邪说”(《近思录》专辟“异端”一章)。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儒家深刻地认识到佛老思想所具有的排斥、消除人的社会性的结果。儒家言,人介于天—地之间,既不完全属于地,也不完全归于天,只有圣人才能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纯粹归于地的只是禽兽,纯粹归于天的只是神。而人既不是兽,也不是神,而只是人。要保持人的特性,人就必须介于天—地之间。如果人跨越了“地”而直接效法天甚至道和自然,那无异于说人已经成为了圣人或者神。由此,政治的对象将由人而转变为神和兽,但如上所言,以神和兽为对象的政治是否能够建立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诚如上文所言,《老子》一书并无对“人”的准确定义,而只是对人做出的类群划分(圣人和凡人)。为什么老子不对人做出一个普遍性的规定,而仅仅是划分人的类型?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问,老子的政治哲学到底属于哪一类人的呢?但我们会迅即发问——难道哲学还分对象吗?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哲学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不适合于针对大众的政治。在这一点上,无独有偶,钱锺书先生在谈到“法自然”时也提出类似的看法:
哲人之高论玄微、大言汗漫,往往可惊四筵而不能践一步,言其行之所不能而行其言之所不许。《战国策·赵策》二苏子谓秦王曰:“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如白马实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儿说、宋人之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藉之虚词,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桓谭《新论》亦曰:“公孙龙谓‘白马非马’,人不能屈。后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此虚言难以夺实也”(《全后汉文》卷一五)。休谟逞其博辩,于“因果”“自我”等无不献疑,扫空而廓清之,顾曲终奏雅,乃曰:“吾既尽破世间法,空诸所有,孑然无依,悄然自伤(that forlorn solitude,in which I am plac’d in my philosophy),不知我何在抑何为我矣(Where am I,or what)。吾乃进食,食毕博戏(I dine,I play a game of backgammon),与友人闲话,游息二、三小时后,重理吾业,遂觉吾持论之肃杀无温、牵强可笑也”(these speculations appear so cold,and strained,and ridiculous)。肯以躬行自破心匠,不打诳语,哲人所罕。若夫高睨大言,乃所谓蓄备两副哲学,一为索居之适,一供群居之便(省略所附外文——引者注),亦所谓哲学家每如营建渠渠夏屋,却不能帡幪入处,而只以一把茅盖顶(Most systematisers are like a man who builds an enor-mous castle and lives in a shack close by)。〔5〕
在钱锺书先生看来,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由此世间也就存在两副哲学:一是用于“索居之适”,也就是适合于个人独处,自娱自乐,换言之,这样的哲学适合于那些离群索居、离开了社会群体的人。假如这样的人要返归社会群体生活,那么这样的哲学肯定不行,而必须换另一副哲学以供“群居之便”。换言之,有两种哲学,一种适合离群索居,一种适合群居社会。以此来看,我们或许就应该思考一个问题,老子的政治哲学到底属于哪一种?是“索居之适”还是“群居之便”?答案当然是包含了这两个方面。对那些可以法天道自然之人而言,老子的思想属于“索居之适”〔6〕;对于那些只能法地之人则是“群居之便”。今天对老子及其后学庄子较为流行的解释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如果按照人人都能够效法天道自然的思路,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解释似乎有道理,但如果按照人只能法地的思路,那么也可以说这样的解释不大靠谱。因为这样的解释首先没有区分这两种哲学,而是以“索居之适”的哲学作为唯一的哲学,既然如此,那么,原子个人的出现和政治社会的解体也就理所当然了。如果按照“人”只能法“地”的思路,我们就可以将人“重置”于社会生活之中,进而重建整个人类政治生活。至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老子不对人提出一个普遍的人的定义,而只是做出人群类型的划分问题了。质言之,老子或许认为,当存在一个普遍的人的定义之时,人们也就容易忽略自身的品性差异,所以只是提出人的类型划分。这一点为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所深刻领会,所以庄子对人进行了更为严格细致的区分,有“圣人”“真人”“神人”“至人”“天人”等。由此以来,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老庄思想中的哪一部分对应于哪一类人?是否老庄思想适合于普遍的人?仅就本文所讨论的“人法地”之中的人而言,他到底是指圣人还是凡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思考:在现实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哪一类型的人群才是大多数?毫无疑问,凡人才是。再进一步而言,政治针对的是具体的人间现实,它的基础和对象必须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由此,效法地的凡人才可能成为老子政治哲学的基础和核心。所以,“人法地”成为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和基础。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世间也有不同于凡人的圣人,他们性情高迈超越,不同于凡人,对此类人而言,老子认为只有他们才可以跨越“地”而直接效法于天道自然。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而凡人才是大多数,为了防止凡人不自知,进而虚骄狂妄,所以老子言“人法地”。至于圣人,由于他们是“教主”,是统治人类社会的人,他们必须要洞察一切,所以他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法天道自然。
这样的解释让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接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用抽象的哲学观念和方法来看待和解释世界了。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要求严格统一、普遍抽象的人的哲学定义,但是,在思想的统一、抽象的背后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群类、性情区别的消失。随着此差别的消失,要求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也就自然产生。但是,“什么是现代民主?曾经有这样的说法,民主与德性共存亡:民主是这样一种政体,其中,所有的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是有德行的人,而因为看起来,德性是需要智慧的,故而,它也是这样一种政体,其中所有的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成年人是有德性而明智的,或者说,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把他们的理性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或者说,它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the)理性的社会。一言以蔽之,民主意味着一种扩大为一种普世皆贵族的贵族制。”〔7〕这样的判断实质上完全是以虚幻的想象代替了眼前的客观事实,“在现代民主出现之前,有人怀疑如此理解的民主是否可能。就像民主理论家中两个最伟大的心智之一所说的那样,‘如果由众神组成的人民存在的话,那么它会民主地自治。一个如此完美的政府对人来说是不适合的。’这个平静而微弱的声音如今已变成一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8〕今天之所以流行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来诠释老子及其后学庄子,实乃诠释者没有严格区分“人法地”之“人”而将之完全单一化为圣人的结果,也就是将之完全理解为可以效法天道自然的高飞云天的诸神和圣人。对于这样已经出离了人间社会的诸神和圣人来说,政治本身可有可无,即使它存在,那也是秩序极为松弛和稀疏的存在。
三
基于“人法地”的政治哲学思想,道家演变出直面现实,冷静理智的政治态度,并且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治理能力,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个意义上说,它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底色。
长期以来,儒家学者对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多有微辞,认为其阳儒阴法,并未完全遵行儒家道术。《汉书》载: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汉书·元帝纪》)
持平而论,宣帝所言实乃实情。纵观西汉帝国之建立巩固,实端赖于黄老之术。学界对此的通行解释是认为此皆因于时势之不得已,比如认为经过长年战争的破坏,民生凋敝,需要休养生息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原因恐怕更多地在于《老子》所具有之政治德性品质所致。以此而论,对宣帝之自我告白当另加看待。依宣帝之见,“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换言之,乃不具清醒之现实感也。相较之下,“宜为吾子”“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则具治国理政之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正是源于《老子》之政治德性品格。对此,司马谈说得相当清楚:
《老子》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老子》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对《老子》推崇备至,这到底是基于其个体喜好、时代思潮还是《老子》自身之政治德性品格所致?在笔者看来,或许原因在于后者。换而言之,《老子》之政治德性品格恰好与政治之品性恰相对应。何谓政治?政治的实质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其基本的要求是秩序的安排,是要使人间社会具有井然之秩序。但是,建立秩序的前提是必须要对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其次是能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此,老子的思想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具体而言,道家形而上之“虚无”本体与形而下之“术”相互为用、互为一体,“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形而上之“虚无”本体开出了形而下之“术”,从而使得道家能够在现实世界开创出一个秩序井然的政治共同体。“《老子》使人精神专一”“《老子》无为”的冷静品格使得道家在纷纭复杂、具体多变的现实世界面前,能够做到处变不惊,拿出具体而微、切实可行的“术”(制度安排、措施采取)来整治现实世界,做到“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道家确定“虚无”为为政之本体,并非为了取消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真正使得政治切实可行,真正确立政治的坚实现实根基。 后起的法家不但深刻领会了《老子》对政治的“秩序”的追求,而且将之发挥到极致之境地。此点也为司马谈所道出: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政治寻求秩序,但是我们知道,建立秩序并非政治之全部,政治也并非完全是法律的构架,“politeia〔政治〕并非法律现象。古典派们是在与‘法律’相对的意义上上使用politeia〔政治〕的。”〔9〕法家对《老子》政治哲学的理解正好限于此陷阱之中,也即它仅仅将政治理解为单纯秩序的建立。这一点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指出。司马谈说“法家严而少恩”“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也言“其极惨礉少恩”。法家何以走到如此之地步?一方面正是《老子》所具有的清醒冷静的政治智慧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治家对《老子》政治哲学的狭隘理解。但无论如何,道家对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也被深具政治哲学眼光的司马迁所看到: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司马迁看来,法家尽管“惨礉少恩”,但在对具体现实的深刻洞察和把握方面则是值得肯定赞扬的,其过错只在于将之推至极致,导致“惨礉少恩”而已。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对法家之短视进行肆意的道德谴责,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法家以一孔之见窥到了政治之一面,法家之过错在于无限地夸大了这一面,盲人摸象,误把这一面视为政治之全体。其次最关键的在于,司马迁极为深刻地洞察到《老子》与法家的内在关联:庄申韩 “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申不害者……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综观庄申韩三家,其所言考之人间事实,皆为不刊之论,而以之思想付诸实际,也为富国强兵之结果。这样的观点在道德理想主义者看来,实在让人沮丧寒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正是法家制定了明目清晰的制度,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制度,拜赐秦汉者众多,但汉承秦制,真正奠基的是法家思想,而正如上文所言,法家思想之来源于老子。
老子思想所具有的清醒冷静的品质使老子深刻地认识到世间实情——庄子也看到了,所以庄子以“人间世”而不是“人世间”来命名他的文章——并且不惜大胆道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天地无所偏爱。即意指天地只是个物理的、自然的存在,并不具有人类般的感情;万物在天地间仅依循着自然的法则运行着,并不像有神论所想象的,以为天地自然法则对某物有所爱顾(或对某物有所嫌弃),其实这只是人类感情的投射作用。”〔10〕当代著名《老子》哲学专家陈鼓应先生的这一解释让我们读来颇感寒凉冷寂。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唯物论所作出的真实事实描绘呢?无论如何,老子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要达到建立秩序这一政治目标,政治家必须要有清醒的现实感。如果政治家没有这一现实感,那么政治将走上狂热之穷途,也正是因此,所以老子强调人法地而不是跨越而法天道自然。当然,如果政治家仅仅将政治局限于纯粹的秩序建立,也当重蹈法家旧辙——此乃题外话,此不赘述。
四
无论何种政治哲学,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其根本目标都在于为人间安排措置一个恰当美好的秩序。无论是思想还是哲学,所指向的目标都是政治与现实。由此,思想与现实、哲学与政治之间当然存在着巨大的距离,通过这个距离,考察的是思想家、政治家的眼力和见识。有的雾里看花,错把海市蜃楼当成现实,有的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在《老子》政治哲学看来,对客观的政治共同体必须要采取冷静的主观态度,对人间现实实情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了解,对之的治理必须基于现实实情,切忌以虚妄不实、理想化的理论眼光来看待和改造政治共同体。这样的观点对于今天的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西方哲学自近代以来是一个日益走火入魔(Philosophy gone mad)的过程,亦即现代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拒绝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自我认识(‘哲学只是认识世界,不是改造世界’),而狂妄地以为整个世界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哲学’来改造。所谓‘从前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现代的哲学则要改造世界’这个著名的表述并不只是某些个别思想家的自大,而是贯穿整个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基本抱负和自觉使命。由此,西方近世以来的‘哲人’不但‘真诚’地追求真理,同时更‘真诚’地要最彻底地按照哲学看到的真理来全面改造不符合真理的整个世界。其结果就是‘哲学’不断批判不符合真理的‘政治’,导致的是‘政治’的日益走火入魔(不断革命),以及‘哲学’本身的日益走火入魔(不断‘批判’)。施特劳斯认为这导致现代性最突出的两个问题,即一方面是‘政治的哲学化’,另一方面则恰恰是‘哲学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philosophy)。……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这种特点实际意味着政治和哲学的双重扭曲,即政治被哲学所扭曲,而哲学又被政治所扭曲。”〔11〕现代政治哲学的如此特性使它完全忽视了古典政治哲学所重视的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际、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距离,使得现代政治架构的基础并非具体的现实世界而是抽象虚构的理论世界,结果造成政治上的巨大灾难。由此,古典政治哲学号召返回“前哲学的、前科学、前理论的赤裸裸的政治世界”。《老子》政治哲学所遵循的“人法地”的核心思想认为,对待现实社会必须要持一种清醒冷静的态度,必须要真正理解和尊重政治共同体中人的实际状况,诸如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人的类型区别(圣人、凡人),不能将之等而同之;政治共同体以凡人为主体,这是政治的主体和基础,也是政治的目标;凡人不是圣人、神人,统治社会的人必须要有后者的眼光和见识,但是他们不能以其所效法和达致的高迈超越境界来治理社会,而是必须以低层次的“地”的品性来治理。现代政治哲学恰好在这些方面与之相反,从而酿成巨大的政治问题。首先,现代政治哲学以抽象的哲学眼光来看待现实,从而抹煞了人的现实差别,客观上看不到人间实情,成了瞎了眼的思想巨人。其次,思想者基于自身“圣人”、神的心性品质,将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假想为圣人,从而提出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最后,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领导者在采取了尊重大众的态度的同时,实际上毫无高远深邃的政治眼光和见识,从而将政治降低为一个纯粹的机械装置而毫无道义价值。凡此种种,皆对人类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我们今天必须正视老子及其道家政治哲学消极的一面,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们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任何政治必然是“大地”的政治,是人的政治,那么,承认和尊重政治及人的“属地”性特征当是政治的首要之义。以“人法地”为核心的老子政治哲学标举的正是这一义。儒家政治哲学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承认和尊重它,但是同时也弥补了其缺陷和不足,从而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
在既往的研究中,对《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 中“人法地”的理解,学界目前较为普遍、流行的看法是:“绝不能理解为人只能法地,不能法天、法道、法自然,而应当理解为人既需要法地,因地法天,人亦需法天,因天法道,人亦需法道,最终是人法自然。”对此看法,笔者难以苟同。因为这样的理解过于大而化之、一概而论了。若依此之见,惜墨如金的圣人何不直接跨越道破而非要费力费墨如此?
注释:
〔1〕孙以楷:《老子通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李若晖先生在引用该句后称“其说是”,对之表示高度赞同。参见李若晖:《“人法地”及其现代意义:新道家发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4〕李若晖:《“人法地”及其现代意义:新道家发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5〕钱锺书:《老子王弼注·法自然》,见氏著:《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4、436-437页。
〔6〕有学者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政治哲学定义为“离‘家’出走的政治哲学”,这当然是一种慧见,但是这样的理解仅仅只是看到老子政治哲学之一面——“法自然”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法地”的一面,换言之,它没有对老子政治哲学所指向的人群大众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参见商原、李刚:《离“家”出走的道家政治哲学》,《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7〕〔8〕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9〕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7-138页。
〔10〕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4页。
〔11〕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导言”第59-60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
王进,哲学博士,贵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政治哲学、经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本文受到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阳明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研究”(批准号:14@ZH054)和2015年度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阳明心学与经学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2015JD005)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