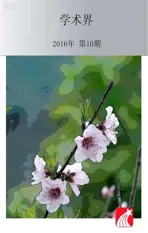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演变论”研究滞后的原因〔*〕
2016-02-26○王澍
○王 澍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学者专论·
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演变论”研究滞后的原因〔*〕
○王澍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
中国古代文体学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但是,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简称“发变论”)的研究却“一枝独后”。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极其匮乏“文体发展演变论”方面的话语资源;而且,传统文体学中还存在着一些妨碍“发变论”研究的不利因素。当今学人继承多,创新少,学术惯性使现当代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因袭了这个缺陷。“发变论”研究本身难度大,不易出成果,学者多避行。于是,“发变论”研究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了。欲振起此项研究,学者们务须加强自觉意识、全体意识、理论意识及理论创新意识,超越尊古意识、实证意识和保守意识。
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演变论;滞后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文学研究被“外部研究”所笼罩。人们关注文学的题材、主题,人民性、革命性、阶级性等成为通用的关键词,而对文学的形式因素不是忽视,就是轻视。文体学研究也因此长期处于停滞或边缘化状态,文体发展演变论研究更无从谈起。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渐渐兴起,并且很快跃升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但是,太阳虽亮,仍有黑子,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总体繁荣之中也仍然存在着“暗斑”或盲点。这主要指的是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以下简称“发变论”)的研究长期严重滞后。“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艺术形式的演变史”,〔1〕所以这方面的研究缺位或不充分,对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文体学等方面的研究而言,都是莫大的遗憾。对此,一些文体学界的专家、学者已经有所警觉,并疾呼跟进。那么,为什么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滞后呢?这一点必须首先搞清楚。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和关键。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也尚未见有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揭示原因了。原因没搞清楚,何谈解决问题?
笔者尝试揭示和分析这些负面因素,以图为中国古代文体发展演变论研究扫清障碍。如果这个意图达不成或达成得不好,那么至少也期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和讨论,以促进问题的解决。不到之处,则欢迎方家指教。
一、中国传统文体学中缺乏“文体发展演变论”方面的话语资源
学术研究最怕言而无证,徙移何依。而文体发变论研究,“与社会背景、创作主体、作品文本等方面的研究相比,文体互动之研究具有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它没有现成的对应史料”,“没有现成的、自在自为的研究资料”。〔2〕“文体互动”研究,实即本文所说的“文体发展演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资料,自古以来奇缺。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论领域,三个大的流派隐隐呈现,即:教化派、审美派、折中派。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强调经国纬政、劝善惩恶及明道载道等外部功能的,为教化派。教化派也可谓实用派。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人们凡事不得不重视实用,以确保群体的生存,所以早期的文艺观,无不偏于教化派。此后,教化派在我国古代文艺领域中也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相比之下,审美派一直较为弱势,但也不绝如缕。审美派在我国古代应该是兴起、中兴和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明代中后期与民国时期。这三个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为少数人专门致力于文艺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同时,思想文化界也较为开放,文化、文学出现阶段性繁荣,审美派也顺势增强存在。受孔儒中庸思想和中和艺术观的影响,折中派在我国古代文艺领域也很有市场。折中就是不偏不倚,兼顾,兼采,调和。从次序上来说,折中派应该是出现在教化派和审美派之后。尤其当两者争论不休、僵持不下时,折中派往往就会应时而出,居中调停。调停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
很显然,上述三派中,只有审美派才最注重“形式”问题,其文体论方面的话语资源也最有价值。事实上,我国文体论方面的话语资源也正是集中于魏晋六朝、明代中后期及民国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其次是折中派。但折中派的文体论大多有点变味。折中派的兼顾折中往往让其理论显得很“拼盘”,很“二手”。可以说,成也折中,败也折中。但折中派的长处是易于被广泛接受,这有利于保存相关的文献资料,便于后人取资和继承。至于教化派,一向重内容、轻形式,文体论方面自亦无足观。但遗憾的是,无论审美派,还是折中派——更不要说教化派——文体发变论方面的理论资源都很奇缺。
受其影响,或者说受历史惯性所致,现当代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对此也缺乏关注和研究。
这里,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先厘清两个极易弄混的近义词:“中国传统文体学”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前者,指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后者,指现当代人对中国古代文体及古代文体论的研究。为便于指称,前者可省称“传统文体学”,后者可省称“古代文体学”。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不相干,但毕竟不同。换言之,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或者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那么,是继承多,还是发展多呢?笔者认为继承较多。继承当然是必须的,但继承多也使“古代文体学”因袭了“传统文体学”的大多数特点——既包括优点,也包括缺点。
总之,传统文体学中较缺乏发变论方面的资源,这使得承传统文体学而来的现当代中国古代文体学也有此缺陷。毕竟,发展都得有个基础。基础薄弱或没有基础,后续的研究就很难展开或无法进行。更糟糕的是:传统文体学不仅缺乏文体发变论方面的研究(这是“无”),而且,还存在着有害于此项研究的因素(这是“负”)。
二、传统文体学还存在妨害发展演变研究的因素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国传统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一般说来,当然是先有文体,然后有文体学。我国先秦时文史哲一体,文体也处于混沌未分状态,后之各种文体彼时始刚刚孕育或萌芽,还远远谈不上成熟或独立,先秦文体学自亦无从谈起。至两汉,文体始大备,文体研究也同时发生并日渐成形。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和文体自觉,文艺形式受到空前的关注和研讨,文体学也臻于成熟。至隋唐,散文理论获得长足进步,尤其是中唐的韩、柳,更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明时期尤其明朝中后期很重视文体辨析,相关的论著较多,显示了文体学的鼎盛。清代及民国时期可谓我国传统文体学的综合与开新时期。
中国传统文体学的发展大势如此。那么,传统文体学中存在着哪些妨碍文体发变论研究的因素呢?
第一,实用论。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实用主义的文艺功能观一直是强势话语,审美主义、形式主义始终甘拜下风。诗教说、乐教说、文以载道、文以载政等说道充斥历代文坛。不关风化体,纵好亦徒然。文艺为这个,为那个,就是忘了“我”。显然,这不利于文体学研究。因为文体或文类主要属于文学形式因素。韦勒克、沃伦:“总的说来,我们的类型概念应该倾向于形式主义一边”,“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文学的’种类,而不是那些同样可以运用到非文学上的题材分类法”。〔3〕可喜的是,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文学本体主义论的抬头,我国的文艺学研究迅速“向内转”,文艺形式开始受到重视,文体论研究亦方兴未艾。
第二,辨体论。中国文论极重“辨体”“尊体”。《文心雕龙》《文章辨体》等很多传统文体著述皆然。“‘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以“‘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4〕辨体、尊体的声势远超浑体、破体,但文体发展演变的关键所系乃在后者。文体融合、文体互动或破体为文是文体发展演变的主要途径。过重“辨体”“尊体”就会阻碍发变论研究。文体发变升级了,于老体不肖了,这就要辨体。所以,辨体的文化逻辑是“复古”。中国文论重视厘清源流,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也易导致重源抑流,“以古为尊”(习近平语)。中国文论罕有纯文学意识,但辨体却很盛行。辨体的潜台词其实是“清理门户”,倾向于文体的纯粹化,排斥混浑,排斥发展和新变。纯文学备受争议,纯文体其实也不恰当。绝对纯粹的文体,世上难觅,因为即便回到孕生之始的原始文体那里也不行。古人讲:“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从文字学上说,“文”的本字就是“纹”或“彣”,其本意就是“错画也,象交文”(《说文解字》),“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文字既如此,纯文体如何可能?不过,辨体也非无价值。辨体是分,浑融是合。但没有分,哪有合?合,也不是要把所有文体都“捆扎”在一起,形成一个“大联合文体”,然后“废弃”其他一切文体。合,是基于分的合。但是分与合毕竟是两码事。分的研究已多,已常,已滥,而合的研究一直罕有。于此笔者呼吁:与其斤斤于辨体,不如孜孜于浑体。辨体是确立,浑体是发展。没有确立,固然无以发展;但没有发展,“确立”也会过时。发展才能更好地确立。
第三,正变论。正变论与辨体论相近,但不同。正变论主要是从内容方面说的,辨体论主要是从形式方面论的。正变论主要与道统相联,辨体论主要与文统相联。文体正变论的思想基础源于《论语》。《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这个“正”主要指内容方面。《论语·卫灵公》提出“放郑声”,《论语·阳货》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郑声”就是“邪”,郑声不正。“雅乐”就是正声,《毛诗大序》:“雅者,正也”。明确的正变论最早出自汉儒关于《诗经》的评论中。《毛诗大序》提出“变风变雅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周政衰乱时期的“风”“雅”即为“变风”“变雅”,与“正风”“正雅”相对。风雅正变的划分,理据或标准大概有三:一曰“政教得失”,政治清明,风雅一般为正,政教衰飒,诗歌一般为变;二是风雅的内容及风格,偏于歌颂的为正,偏于怨刺的为变;三是以时间分界,“正风”“正雅”多出于西周中前期、王朝兴盛时,“变风”“变雅”多出于西周后期、朝政衰朽时。汉人看《诗经》,不过“美”“刺”两端。美者为正,刺者为变。
综上,正变说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方面立论的。后之正变论则主要与(儒家)道统说纠结在一起。其结果是,正变论往往被直接转换为等级论。以《张彦辉文集序》中明代方孝孺之说最有代表性:“虽然,不同者辞也,不可不同者道也……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为难也。呜呼,道与文具至者,其惟圣贤乎!”北宋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讲“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方氏反言之,这是为了强调“道”的地位,方孝孺实际上将文分为三等:一等纯道文,文道具至;二等杂道文,道不纯粹;三等无道文,文道无关。很显然,在方氏看来,第一等才是“正文”,其他皆为“变文”,甚至是“歪文”。
中国古代虽有推尊正变兼备的“正变一体”之说,但强势话语是“以正为尊”,这也正是“正变论”立说的出发点。试想,若不想以正为尊,何必造作正变论呢!可见,正变论是等级论的基论。正变论再往前跨一小步,就是“正宗论”“正统论”,也就是以正为尊的系统化、理论化表述。
当然,严格地说,正变论也不限于内容风格方面,也有从形式方面着眼的。如魏晋六朝人喜论文体的正与变。像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就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有“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之说,等等。当然到后来,五言也被视为正体了。后来还有以诗为正、“诗变而为词”“词为曲所滥觞”〔5〕“以曲承诗,独得正统”“曲之于文,盖诗之遗裔”〔6〕等说法。另外正变论还曾被置换为“雅俗论”“古今论”“通变论”“奇正论”等。雅即正,俗即变;古即正,今即变;通变论、奇正论则较能接受奇变。
但是,无论是从内容方面立论,还是从形式方面立论,正变论都倾向于尊正黜变。如明代胡应麟说:“诗之体以代变也”,但其结果是“诗之格以代降也”(《诗薮·内编》卷一)。“权变”总是不得已的,“变”总是不大好的,所以,研究“变”也就无甚意义,付之阙如是明智的。同时,正变论还造成了文体的人为等级论,“正体”被视为优等,“变体”成了劣等,这既不利于文体的发展,也不利于发变论的育生。在我国文学史上,词、曲、骈文、戏剧、小说、神话等都曾因为内容不纯正,多涉所谓的“淫邪”“诲盗”或“怪力乱神”等而“沦为”末等、下流,长期遇冷。没有或忽略这些文体的“中国传统文体论”,显然只能说是“半拉子文体论”。基于这个半拉子的文体论的文体发变论也就无从建构,就算有,也肯定是成问题的,不足据的。
综上,传统文体学存在种种有害于发变论研究的内容。这些,现当代的文体学也大都因袭下来了。这既是传统文体学的错,也是现当代人的错。错在哪里呢?错在太“复古”了。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古代文体学应该“姓古”还是“姓今”呢?我认为,应该是复姓——既姓古、也姓今,但“今”应当是这个复姓的首字(first name),也就是说,要以今统古,创建或重建现当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明代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墨守古说“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雪涛阁集序》)。其实,文体学也不能不“古而今”也,且“古而今”的重心在“今”。所以,我们要想激活和繁荣发变论研究,就不能怕麻烦,就得放出自己的眼光,尽力超越古人,“创造性地接续”传统。
三、当代研究者知难而退
文体发变论研究是老大难的学术问题。难就难在不仅研究所必须的前期资料奇缺,还因为“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研究”这个问题很抽象。从事此项研究,既要理论,也要考证,眼要大,心要细,要“能把众多文体的聚散生灭、动荡开阖、鱼龙漫衍、千变万化,既具有恢宏气势,又具有微妙细节的全部景观都纳入学术视野”,“要把各种文体的来龙去脉、旁午交通都纳入学术视野或思考维度”,这“对人的精力和智慧都会是一种挑战” 。〔7〕所以,研究者往往望而却步,转而他顾。可见,发变论问题本身的研究难度,也是妨碍其顺利开展的一大绊脚石。人们为了快出成果、出实成果,绕道而行,避难就易、避生就熟、避虚就实,也属人之常情。不过,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构建而言,发变论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赶紧补上。于此,笔者呼吁有志之士打破静默关注,迅速行动起来,迎难而上,群体攻坚,以维护文体学的“领土完整”。愚以为,攻坚的关键在于不要怕劳而无功,无所斩获无所谓,不畏失败方可嘉!
不畏失败、知难而进的精神不仅是可嘉的,更是必须的。既然传统文体论中不仅罕有发变论,而且还有如上所述之诸多妨害因素,那么,我辈要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另起炉灶、重塑金身,甚至“重装系统”(可兼容的),方有可能在揭示文体发展演变的现象及规律方面有所建树。
四、如何振起发展演变论研究
先回顾一下现当代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依时而论,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轫期:20世纪之20-40年代。此期出现了一些古代文论、文学概论及修辞学等方面的著述,其中也有论及文体的。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薛凤昌的《文体论》〔8〕与1946年上海正中书局出版的蒋祖怡的《文体论纂要》可以说是对这些成果的总结性著述,象征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轫。(2)“倒春寒”期:1950-1980年代,即建国后的前30年。此期意识形态轻视文艺形式(虽然文体不只是形式),文体学研究遭遇“倒春寒”,重归边缘化、低潮化,所以此期仅出现一些归纳、介绍传统文体的著述,且为数不多,总体研究非常冷清。(3)重新起步和振兴期:1990年代至今。此期,文体学重新被接续,并渐趋繁荣,如今已成“显学”。这方面的成果较多,从内容上说,可概括为三类:一是古代文体论。有“单体论”,即单论一种文体;有“多体论”,即单个地论述多种甚或全部古代文体的;有“时体论”,即论述某时段的文体的。这些成果出现早,数量多。如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属全体论)等。但无论是单体、多体、甚或全体,此类研究实际上都属于“单体论”。因为这些文体研究都是单个单个地分开进行的。二是古代文体学论。有阐发古代之文体学著述的文体学的,如论《文心雕龙》《文章辨体》等文体学的;有挖掘古代集书、类书及字书的文体学蕴含的,如论《文选》《四库全书》《独断》等文体学意义的;有论某时段的文体学的,如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等。三是古代文体学专题论。即面向整个古代文体学,专论或主论某一方面。包括论文体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关系的,论文体分类的,论文体融渗及破体为文的,规划或反思古代文体学学科的,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很宝贵,都功不可没。
但是,从发变论研究方面说,上述这些研究也都不尽人意。第一,上述第一种研究,即“单体论”,可以说几乎是古代文体学路数的现代重演,《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早就这么做了,只不过今人的单体论后粗转精,在理论化、系统化、文学化等方面有所开拓或有较大提升而已。这类研究,孤立地看待一个个文体,探源溯流,穿越时空,但这种研究至多相当于“单体发展演进论”,而我们要的是“全体的”或“整体的”文体发展演进论,也就是基于所有文体的、宏观的发展演进论。单体论之盛行,还易形成思维惯性,使我们“在考察某一种文体的特点与变异时常用单向度的思维模式”,〔9〕束缚了手脚。第二,上述第二种研究,属于阐释、整理、挖掘古代的文体学资源,与文体发变论研究基本无涉。至于第三种,即专题论研究,其中的“论文体融渗及破体为文”部分,显然属于文体发展演变研究,所以很值得重视。但这方面的研究对古人而言往往也只是“接着说”或“填空说”,虽有一定价值,但又多局限于两种文体(或少数几种文体)之间的交越互渗,仍未实现大的突破,未能就全体文体而言。如果把第一种叫“单体发变论”的话,那么,这一种可以叫两种或少数几种文体“合体发变论”。那么,整体的或全体的发变论呢?规律呢?论者罕有。〔10〕另,专题论多系面向整个文体,其“全体论”路径是开放的、包容的,值得借鉴。第三,总的看,当今古代文体学之发变论研究方面缺乏自觉意识、全体意识、理论意识及理论创新意识。自觉意识就是自觉地以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研究为唯一目标、至高目标,心无旁骛,不避虚空,不畏失败。以往的发变论研究大都做不到这一点。比如,第一种“单体论”研究,笔者认为它只是相当于单体发变论,就是因为论者大都满足于厘清某一种文体的源流正变,何同何异,且往往重源抑流、扬正黜变,总有“辨体”“正体”的味道,何尝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挖掘和发现“文体发展演变及其规律”方面!所以,准确地说,这只是“加长版”的文体论,而非文体发变论。再比如,第三种专题论研究中的“文体融渗及破体为文”论,也仅仅是两种或极少数几种文体之间的互通互渗,远未涵盖所有文体。且此论古人早已有所发明,今人只是“接着说”而已,照此下去也难有突破性发明。全体意识就是说要面对所有文体,研讨其发展演变大势如何,有何规律。共性存在于个性,但个性不等于共性!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系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有机体。这个系统自成一体而相对完满自足……这个系统既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系统内的各种文体又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11〕这个“变动不居”,就是文体的互动推演。但这个“变动不居”的文体活动的“大背景”,不是一两个文体,也不是三五个文体,而是所有的文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全局观”“整体观”,必须全部到位、一个也不能少地观察,以免挂一漏万,如此,方能谈得上揭示总规律。所谓理论意识,也谓此也。或者说,文体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研究,既属文体论,但同时又很可能会突破文体论,上升为普适的、一般的文学理论。换言之,文体论这个小窟窿里,可能会掏出一个大螃蟹来。这一点,很多学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那么,现在就做好思想准备,来掏挖和迎接这个大螃蟹,意识到和相信这个洞里有大螃蟹,然后尽力去掏,这就有可能导致理论创新。否则,就只能跟在古人后面,接着说、综合说、拾遗补缺地说,而不敢超越古人,这样的话,稳有余而创不足,是无法完成本文论题所提出的使命的。第四,还要克服三个意识。为了振兴和繁荣文体发变论研究,我们还要处理好古今关系、中西关系、实证与思辨的关系等问题。换言之,就是要破除或超越尊古意识、实证意识及保守意识。
超越尊古意识。凡是“古代××研究”,大都极易“古代化”“古化”甚至“食古不化”。毕竟,中国历史悠久,先人智商也高,所以各领域里的古圣先贤都很多。这就产生了古今矛盾和古今问题。古代圣贤优秀杰出,尊重是对的。但若尊重过份,就会丧失自我,丧失现代视角,丧失批判意识。宋代王安石讲:“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今人汪曾祺也有句名言:“我与我比我第一”。我的思想我做主!我们就要发扬这样的精神,以今为主,以今统古,古为今用,这样也才能无愧于古圣先贤。
超越实证意识。实证不错,但不宜过头。过重实证,就会排斥思辨。这也是使古代文体发变论研究滞后的一大客观原因!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试想,若一味讲实证,马克思还真难提出共产主义学说呢。事实上,人类文化史上很多伟大的理论是始于假说与空想的。
破除保守意识。这一点主要是中西问题。钱锺书《谈艺录》有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国人的学术自然就有中国特色,何必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以“避西保中”呢。中国特色不等于“对”,它至多是“合适”,也就是情势如此、不得不然。对此,我们要勇于接受,不能自我否定——至此足已,何必人为增重,甚至上纲上线呢。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所论,局限于“内部因素”。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环境的产物,文体的发展演变研究也离不开对社会、政治、文化、传媒、风俗、地理、气候等外部环境或背景因素的省察,尤其是传播技术,与文体的发展演进关系尤密,尤值得重视。但一文一主题,这些只能另文以论了。
注释:
〔1〕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7〕〔9〕〔11〕张仲谋:《论文体互动及其文学史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3〕〔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265页。
〔4〕二语分别出自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汪泓:《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5〕〔清〕吴兴祚:《词律序》,见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6〕〔清〕姚华:《弗堂类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01、305页。
〔8〕此书曾于1939年、1945年两次被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
〔10〕详参笔者:《文体浑和论与巨型文体说》,《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其他人,目前笔者仅见张仲谋有《论文体互动及其文学史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论及“整体发展演变观”。
〔责任编辑:李本红〕
王澍(1967—),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先唐文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浑和与文体演进之关系研究”(16XZW0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