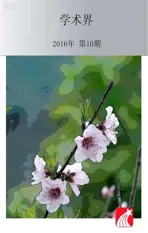论科学艺术之相濡以沫
2016-02-26彭兆荣
○彭兆荣
(1.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 重庆 401331 2.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学人论语·
论科学艺术之相濡以沫
○彭兆荣1,2
(1.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 重庆401331 2.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厦门361005)
“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宛如两条道上跑的车,总走不到一起。然而,艺术史研究并没有给出支持这样认知的理由和证据;恰恰相反,大量事实无不证明二者彼此难分,相濡以沫。值得提示的是,“科学”和“艺术”都是舶来概念,在西方,二者似乎可以相融。本文就科艺之间的“被区隔”的原因以及所产生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科学;艺术;民族志;舶来
一、科艺相拥
“科学”和“艺术”常被人们置于认识的两端:一端是以客观为圭臬;另一端则任由主观放浪。这样的认识往往又与死板教条的学科形制发生关系。笔者忍不住要问,艺术与科学果然似牛郎织女隔绝于银河的两端,形成“二元分隔”之形势吗?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认识?是表述上人为扩大了二者沟壑,还是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误读”?抑或是来自不同学科本位的偏颇所致?本文认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能分置于二端,而且它们一直相濡以沫,根本无法泾渭。值得特别提示,所谓“科学”“艺术”都是舶来物,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们在译介时,已经修改、篡改了它们原来的完整意义,属于“文化误读”现象。另一方面,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变化和变迁,也在二者中注入了大量新质,加之学科形制上的变革,会在它们中加入各种“添加剂”,使之产生新的变化,又经由各种社会渠道的传播,甚至政治宣传上的专断,形成了如此认知上的景观。
回归二者的原生形貌,援引借西方近代史上伟大的博物学家布封对“科学”和“艺术”的关系评说:
对于艺术来说是真实的东西,那么对于科学而言也同样是真实的。只不过是科学没有那么受局限,因为思想是科学的唯一的工具。因为在艺术上,思想是隶属于感官的,而在科学上,思想在统帅着科学,尤其是涉及到认识而非行动,涉及到比较而非仿效的问题时。思想尽管被感官所局限,尽管往往会受到错误的关系的误导,但它仍然不失其纯洁也不失其活跃。〔1〕
布封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是“思想”的反映,“真实”的结果。只不过,其表述与我们观念中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些地方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我们认可布封的评说,那么,说明我们一开始认识这两个概念时就已经出现了偏差和片面化。原因主要是:1.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都是西方舶来之物,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与“本尊”相距很大。2.“科学”在今天的中国完全被“神化”,以至于不能批评,形成了实际上的“异化”。3.“科学”和“艺术”原本具有同质性,都是“客观真实”的反映和呈现,只不过反映和呈现方式不同;当然,它涉及到思维形态的不同问题。4.“科学”与“艺术”越来越向对方走近,尤其在当代艺术的表达实践中。
以“科学”这一语用为例,无论是本体还是概念,都是混杂的,特别是当它与“技术”走到一起,情形更为不堪。另一方面,“科学”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它伴随西方历史进程的演化而变动,最经常出现在诸如“新科学技术”发明和发现的情形中。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韦伯是这样概括的:“近代历史上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产生的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带来了实用技术的后果,同样使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就是精密科学,国家同样将它纳入了自己规范的范围。它带来了理想性后果,也是具有革命性后果。”〔2〕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当然还有殖民主义齐头并进,其中“实用技术”与“精密科学”成了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发动机”。韦伯提到历史上的这种后果,真实地再现于当代中国的现场,即功能性“实用”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科学”范畴的边界设置。二者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遭遇和差异在于:当西方在谈论“科学”的时候,只是论及其对历史变革的“工具”性质和作用,从来没有把“科学”神圣化;然而,当它到了中国,除了使用这一“工具”外,还被历史“神话化”,而且整个过程涂满了“中国颜色”。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很难对“科学”做出准确判断,即使是被“标签”为各种各样“科学家”的人也是如此。虽然这不妨碍人们在各种场合使用这个词。或许正在因为它在概念上的漫无边界,所以使用起来最保险。可这样的结果,早已与“五四”时期的那位“赛先生”相去甚远了,甚至完全不是那位“先生”了。现实生活中,“科学”在语言上的使用更是混乱不堪,意思五花八门。“百度”一下“科学”的定义,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不看还清楚,看了则完全糊涂。其实,“艺术”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本文要申辩的是,无论如何,“科学”与“艺术”并不是人们在一般观念中那样相互抵触,或分处两端,它们的关系是相互拥有、相濡以沫。
反观艺术家的观点,他们并不绝然地将自己置于“科学”的对立面。达·芬奇在他的《艺术手记》中这样说:“绘画完全是一门科学,是自然的嫡生女儿,因为绘画是自然界产生的,确切地说,它是自然的孙女儿;一切已成事物都是自然创造出来的,而这些事物又创造了绘画。”〔3〕达·芬奇的绘画是实验科学的典范,其描绘对象完全按照数字和量度进行,为了画出人体的肌肉,他以解剖学为依据,甚至亲自进行解剖实验;也因此,他将绘画视为高于音乐、雕塑等艺术类型表现形式。艺术家有的时候会根据自己艺术类型的特点,比较其他的艺术类型,进而做出判断。我们相信,音乐家、雕塑家或许并不认可他的观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与“艺术”相融是一个重要特点,西方绘画的写实主义传统与科学“结伴同行”,这个特点一直贯彻在后来的西方历史之中。
就西方历史的发展来看,科学、艺术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比如教堂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诗文等这些与科学、艺术的有关者,深受宗教的影响。就具体的知识体制而言,西方的所谓“七艺”,指大学中的七种学科知识,即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七艺”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创立的学科后来传入罗马并得到发展。至公元4世纪时,“七艺”已被公认为学校的课程。公元5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基督教会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虽然教会对古希腊罗马的这一传统做了巨大的“改编”,以服务于“神”,但仍然保留着“七艺”的形制,并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文艺学科教育)的学习课程。其实,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就是在继承中世纪教会中的“七艺”形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学科开始分化:文科分为文法、文学、历史等;几何学分为几何学和地理学;天文学分为天文学和力学。至17、18世纪,学科进一步分化:辩证法分为逻辑学和伦理学;算术分为算术和代数;几何学分为三角法和几何学;地理学分为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力学分为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总之,在学科的发展史上,中世纪的“七艺”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一段西方历史简谱清楚地说明,“科学—艺术—宗教”是很难做绝然的分离。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特别是新技术的出现,会使传统的“七艺”整体出现更为细致的分化,也会产生此长彼消的变革,比如印刷术的发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七艺”的知识形制,统一性的教堂建筑解体,而艺术和科学却得到了解放,雕塑、绘画、音乐、文学以及印刷术的突飞猛进,这些都宣告了个体探索取代了大规模的自发创造。〔4〕
西方学者对“科艺”范畴讨论在我国影响较大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必在其列,它是较早被译介到中国来的,曾经在很长的时间(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是我国美学、艺术史论、文艺理论界的“普及读物”。这部著作完成于1893年,出版于1894年(1897年英译出版),1984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将其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或许是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或许是那个历史年代的学术著作太缺乏等原因,它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今天重新翻读,有隔世之感。第一章的标题为“艺术科学的目的”。在学术界,这样将“艺术”与“科学”并置摆放,并非特别怪异。格罗塞专门为之做了解释:
“科学”这个名词,现在大都用得很大意的,我们为审慎起见,似乎在承认它之前应该把“艺术科学”是否合乎科学这个光荣的名词,先来加一点考察。科学的职务,是在某一定群的现象的记述和解释,所以每种科学,都可以分成记述和解释两个部分——记述部分,是考究各个特质的实际情况,把它们显示出来;解释部门是把它们来归成一般的法则。这两个部门,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康德表示知觉和概念间的有关系的话,刚巧适合于它们:没有理论的事实是迷糊的,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艺术科学”果真具备着科学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吗?对于这个问题,单就那职务的第一部门来说,是可以作肯定回答的。〔5〕
事实上,格罗塞所使用的“科学”是指“艺术科学的方法”,〔6〕他认为“艺术科学的研究应该扩展到一切民族中间去,对于从前最忽视的民族,尤其应该加以注意……如果我们有能力获得文明民族的艺术科学知识的那一天,那一定要在我们能明了野蛮民族的艺术的性质和情况之后。这正等于在能够解决高等数学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乘法表一样。所以,艺术科学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乃是对于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的研究。为了便于达到这个目的,艺术科学的研究不应该求助于历史或史前时代的研究,而应该从人种学入手。历史是不晓得原始民族的。”〔7〕格罗塞所说的“人种学”就是人类学,〔8〕“人种学”则是我国早期的学术界常常使用的概念。
二、主客相融
格罗塞的提议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对于“科学—艺术”的认识和讨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史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说明的例证,也可说是反证。“例证”指只有人类学才有可能建立起帮助人们了解原始艺术的科学渠道。“反证”的旨意有二:1.不同民族的“艺术”是不同的、多样的。2.指人类学对民族志的讨论出现了将“科学”与“艺术”分隔的趋势。二者都可以在民族志(ethnography)中得到真切的反映。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系统化的组成部分,把人类学家根据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解释完整地加以表现。〔9〕但是,民族志无论作为一种学科原则,还是调查方法,抑或是人类学家个体书写的“作品”,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主张,这也构成了这一学科重要的历史内容。人类学史上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志主张:一个是“科学的民族志”——以客观为生命的民族志;一个是“艺术的民族志”——不排斥主观性表述。
其实,任何事物没有绝对意义的“客观”,也没有绝对意义的“主观”。“实事求是”是人们(带有主观性)根据客观事实所进行的认知行为。众所周知,传统的民族志素以“科学”为圭臬、为标榜。早在19世纪的初、中叶,人类学就被置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被称为“人的科学”。〔10〕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除了确立“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原则外,更对民族志方法,诸如搜集和获取材料上“无可置疑的科学价值”进行规定,并区分不同学科在“科学程度”上的差异等。〔11〕美国“新进化论”代表人物怀特坚持人类学学科诞生时所秉承的“进化论”和“实验科学”学理依据,进一步将其确认为“文化的科学”。〔12〕由于人类学属于“整体研究”,因此,总体上可归入“形态结构的科学”范畴。〔13〕
然而,对人类学的“科学”认定从一开始就潜伏着不言而喻的争议性,无论是就科学的性质抑或是叙事范式都是如此。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异文化、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现在学者面前,这些与人类学家的描述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民族志者从涉足土著社会并与他们接触的那一刻起,到他写出最后文本,不得不以长年的辛苦来穿越这个距离。〔14〕但是,民族志者个体性的“异文化”田野调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填平“个人的主观因素”与“科学的客观原则”之间的距离?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迄今为止仍见仁见智。2.“文献文本”属于文学性表述,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民族志的“文学性”,比如文学的隐喻法、形象表达、叙事等影响了民族志的记录方式,——从最初的观察,到民族志“作品”的完成,到阅读活动中“获得意义”的方式。〔15〕这样,“书写文化”便成为一个民族志无法回避和省略的反思性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田野的“叙事范式”,在20世纪初、中叶,经过连续两、三代人类学家们的努力,已经形成并得到公认。田野调查建立在较长时间(一年以上)的现场经历对于一般民族志(general ethnography)而言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可以保证民族志者与被调查对象朝夕相处,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内部。尽管在人类学家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自己在“对象化”的程度上出现不同的看法:比如过分的“自我的他化”可能被认为是“植入其中”或“沦为研究对象”,从而导致“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主体性迷失。另一方面,深陷其中的人类学家因此减弱了对客观性把握的能力,甚至减退了研究热情。〔16〕这些都属于民族志研究参与体认的原则范畴。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原则,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并未受到根本的质疑和改变。按照帕克的说法,这种研究原则和方法有别于“图书馆式”的研究原则和方法,被形象在描述为“在实际的研究中把你的手弄得脏兮兮的”(getting your hands dirty in real research)。〔17〕据此,民族志者亦被戏称为“现实主义者”(realist);这种批评方法遂被标以“现实主义民族志批评”(critical realist ethnographies)。〔18〕
第二个问题较之第一个问题则完全不同:虽然在表面上它属于“表述”范畴,但由于它不仅关乎民族志者经过“辛劳”获得资料在“真实性”上是否被认可,而且关乎人类学家在身份上属于“科学家”还是“作家”的问题。民族志既然是特定人类学家所写,也就有了“作者”(author)的身份和性质,当然也就少不了表述风格的体现和范式实验的问题。这种被称为“实验民族志”的实践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达到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增强文化的丰富性。〔19〕说到底,民族志的范式变革与当代的知识革命密不可分。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根据其所变化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内的一般性讨论中,它实际上常被赋予“后范式”特征。〔20〕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当他们在田野调查中所面对的那些“原始艺术”时,根据民族志的原则,即“客位主位化”——传统的民族志要求,人类学家在实地和现场要尽量使自己成为调查对象群体中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客观性”;可是“调查者常常忘记科学的逻辑是一种永远达不到的理想——它的目的是找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纯粹的关系,而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和未经证实的观点的影响。科学的逻辑并不是生活的逻辑,每一个人都有使自己不去做某种事情的情绪。”〔21〕这其实也涉及到了当代的实验民族志中所涉及到的主观的、个体的、“艺术性”的问题。简言之,绝对“科学的客观”在民族志的整个实践过程中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因为一开始就是人为的。
“科学的民族志”与“艺术的民族志”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简单两位(主位—客位、主观—客观)之于艺术遗产在存续上的反思。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难道只是“主客”两位的关系吗?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化遗产,包括艺术遗产的关系是“三位关系”,〔22〕中国的文化与艺术遗产是建立在天地人“三才”的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作为一个独立和完整的主体,秉持从“天人互益”原则,并向“天人互惠”发展。〔23〕艺术家的创作本身既要保持个体和个性的独立和自由,又受到天地人的宇宙观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时刻准备着超越自己的人,才能创造出最高的艺术。”〔24〕在艺术境界上,如果达到了像敦煌的音乐—舞蹈—曲调—绘画融为一体的“飞天”宗教境界,才能超越简单的“主客关系”。人类学的例子有助于我们回到“艺术”与“科学”的讨论。如果说艺术的创作要有某种“宗教境界”的话,那么,“科学/宗教”也被纳入讨论范畴。事实上,在西方的学术界,“科学/宗教”也并不被视为简单的两极。
三、虚实相兼
在艺术史研究中,“出神入化”是一个常用的表述,是人们在形容艺术作品时最为常见的一句表彰。如此语用,古代早已有之;比如在谈到中国书法时,明人项穆作如是说:
书之为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书必舒散怀抱,至于如意所愿,斯可称神。书不变化,匪足语神也。所谓神化者,岂复有外于规矩哉?规矩入巧,乃名神化,固不滞不执,有圆通之妙焉。况大造之玄功,宣洩于文字,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25〕
大意是说,书法艺术之真谛在于抒发胸意,在于精神自如。只有到达随心所欲的程度,才可称为出神入化。书法的神化就是天性的自然流露和生动的气势。在艺术表现的层次上,如果到达了“意”与“象”的交织融合,便有了神化的境界。在此,意愿、抒发、气韵、时机、圆通、玄功、规矩缺一不可。这里还涉及到“形式”问题。概而言之,形式之固,功在于形;形式之极,是为无形;形意相合,可达神化。
我们相信,每一个成形的学科都伴随着相应、相关的形式,它也是人们进行分析的重要途径。所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成为艺术理论重要的范畴。所谓“形式分析”,特指专门考量艺术作品内在结构,以及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专业的艺术分析以及“发现”和创造相关的形式分析的方法,也构成了特定学科领域的特色。比如分析绘画艺术,“透视法”是常用的。但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还没有发现“透视法”,因此,画面缺乏立体感。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发现了透视法,从而解决了画面的立体感的问题。这一技艺的使用,一方面为绘画艺术的表现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感;另一方面,也成为绘画艺术在进行“形式分析”时的一个分析因素。〔26〕同时,这些具有“工具”性质的形式特征又配合着特定时代的传统要求。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和造型艺术的形式技艺的产生,也与宗教教会对“神”的形象和形体的要求有关,包括在绘画中对色彩的使用。〔27〕
然而,同样在艺术的表述方法上,中国有自己的一套,以“写实”的方法论,比如人物画在古代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作为摹拟对象为主,虽然我们并不使用所谓的“写实”,却贯彻着中国式“实”的原则,以宋代为例,人物画发展既注重写实的宫廷和民间绘画传统,又注意写意的文人画,使写实人物画达到历史的高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历史上曾经被置于“画工”的范畴,民间画和院体画也具有亦工亦匠的特点。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艺术社会分层。我国自近代以降,特别注重西方绘画艺术的“舶来”方法,比如明朝画家曾鲸,与意大利传教士、著名画家利玛窦切磋人物画技法,融合民间绘画的传统方法,吸收西洋肖像的写实方法,变“透视法”为“凹凸法”开创影响甚广的“波臣派”:与传统画法相同的是同样用淡墨线勾出轮廓和五官部位,强调骨法用笔。与传统绘画不同的是,不是用粉彩渲染,而用淡墨渲染出阴影凹凸。〔28〕
其实,当我们在讨论艺术上的“形式分析”,诸如“透视法”“凹凸法”等工具概念时,我们甚至会产生迷幻感,那“艺术”不分明是“科学”吗?即使我们试图努力地寻找区隔二者的理由,比如在“科学”和“艺术”的两端,前者侧重于遵循“普世性”原则,后者则致力贯彻“个体性”原则等等。不幸的是,恰恰是在艺术领域人们发现使用“透视法”“凹凸法”的科学法则和方法;即从不妨碍形式分析上与“科学”的同质性。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不使用“科学”这样的辞藻。对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而言,比如陆机、刘勰等人,在谈论“神思”的时候,甚至在项穆时代,都根本不需要顾忌是否具有“科学性”,他们可以将艺术说得神乎其神。对于“神思”,今人有许多附会解释,努力将其套上一件“科学思维”的“西装”外衣,很为难。有更多的人说,我们自古就有“科学”。说这句话就像说,“我们自古就有芭蕾。”
确实可以说,中国有自己的科学技术,特别表现在艺术与“百工”剪不断的缘分上。重要的是文化自信。我们原有一整套自己的表述语汇和分析工具。以古代的“画工”之作为例,它既可以是哲学,也可以是技术,当然也可以叫做“艺术”,包含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传统一直被很好地传承下来。以笔者观之,艺术中充满了“科学”——精神、智慧、思维、价值、方法。我们的艺术是自然之物,首先与传统的农耕文明对自然节律的认知、理解和践行相吻合。任何科学的意图都不过是艺术的闲余之作。这才是最高成就的自然造化,因此不需要将“科学”与“艺术”分隔,它们本来共生同体。将二者分隔式认知的现代人是受西方分析时代的“传染”而出现的“问题”;问题是,西人本来也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自我国近代从西方引进这两位“先生”——“赛先生”(科学)、“阿先生”(艺术)以来,我们早就让两位先生穿上了“中式长衫”,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两位先生了。这些概念到了中国,仿佛物种,都要“服”中国的水土,否则便不能存活,或者发生变异。“科学”和“艺术”自然不能例外。
注释:
〔1〕〔法〕布封:《自然史》,陈筱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2〕〔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326-327页。
〔3〕〔意〕达·芬奇:《艺术手记》,载贾晓伟:《美术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4〕〔法〕艾黎·福尔:《法国人眼中的艺术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付众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导言”,第13页。
〔5〕〔7〕〔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17页。
〔6〕〔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二章”。
〔8〕人类学也有四分支说——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笔者。
〔9〕Barfield, T.(eds.)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p.157.
〔10〕〔英〕A. C. 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11〕〔14〕〔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12〕〔美〕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Johnstorn,F.E.& H.Selby.Anthropology:The Biocultural View.U.S.A:Wm.C.Brown Company.1978.p.11.
〔15〕〔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2页。
〔16〕Graburn, N. H. H. The Ethnographic Tourist. In Graham M. S. Dann.(eds.) The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World. Trowbridge: Cromwell Press. 2002.p.21.
〔17〕帕克(Park, R.)192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时对他的学生所做的著名解说。
〔18〕Davies, C. A. Reflexive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9.
〔19〕〔20〕〔美〕乔治·E·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1页。
〔21〕〔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2页。
〔22〕彭兆荣:《体性民族志: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法的探索》,《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23〕〔24〕饶宗颐、池田大作、孙立川:《文化艺术之旅——鼎谈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3、212页。
〔25〕〔明〕项穆:《书法雅言》,李永忠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7页。
〔26〕〔27〕〔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7,338页。
〔28〕周永丰:《千年伊始 百年如初——百年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回顾》,《福建省美术馆》2014年1-2合刊,第11-21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
彭兆荣,博士,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授(一级岗)、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