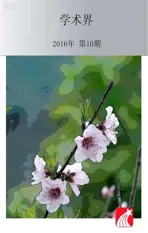论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以南海为例〔*〕 ——与克里斯托弗·莱恩博先生商榷
2016-02-26王玫黎
○王玫黎, 谭 畅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重庆 401120)
论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以南海为例〔*〕
——与克里斯托弗·莱恩博先生商榷
○王玫黎, 谭畅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重庆401120)
闭海或半闭海制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的创新之一。莱恩博认为,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是一项国际义务,中国坚持双边谈判的行为不符合善意合作的要求。实际上,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并不是一项有拘束力的法律义务,而是一项规劝性质的建议。尽管如此,沿岸国仍应以善意协商的方式,努力就《公约》规定的一切海洋事宜达成合作。作为南海这一半闭海的沿岸国之一,在自然资源合作开发的问题上,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并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向有拘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过渡,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争端,这些行为已经尽到善意原则的要求,符合《公约》的规定。
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合作;善意;南海
《哥伦比亚跨国法杂志》2014年第2期(总第52期)刊发了克里斯托弗·莱恩博先生的文章《半闭海的共同开发:中国承担南海自然资源开发的合作义务》。〔1〕该文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文章的基本观点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3条为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时,施加了一项广泛的相互合作的法律义务,所以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承担相互合作的义务。在此基础之上,莱恩博进一步认为,合作义务包括善意协调的义务,而中国坚持的双边谈判由于没有将南海地区的所有声索国纳入同一个谈判体系,而且有拖延之嫌,不符合善意原则,因此声索国有权以中国违反善意为由,单方面提起仲裁。笔者就该文的上述观点与作者莱恩博商榷,首先,结合《公约》的规定,明确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合作的建议性质;其次,结合中国政府的言行,明确了中国善意与声索国开发南海资源的态度。
一、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性质
(一)沿岸国合作性质的争论
197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前夕,海底委员会决定将“闭海或半闭海”列为会议的讨论议题。被誉为“海洋宪章”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系统地编纂了1958年《关于海洋法的日内瓦四公约》和习惯海洋法,还审时度势地创设了新的海洋制度,其中包括《公约》第九部分“闭海或半闭海”。该部分仅仅包含了两个条款:第122条“定义”从法律上界定了“闭海或半闭海”的含义,第123条“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规定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事项。将闭海或半闭海制度纳入《公约》,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样一个特殊地理情形海域的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合作的共识。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些国家主张将一般性海洋规则适用于闭海或半闭海,在适用的过程中兼顾这些海域的特殊性以及沿岸国的利益和需要,以公平方式加以适用。〔2〕这种意见否定了为闭海或半闭海制定特殊规则或将一般性海洋规则进行变通适用的设想,考虑到闭海或半闭海的特殊性,一般性海洋规则在适用时应当遵循“公平”方式。此外,沿岸国应当就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海洋事项开展合作,以应对共同面临的海洋问题。这种意见在缔约国之间达成一致,最终形成了《公约》第123条“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a)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b)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c)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d)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他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
《公约》第123条的达成从事实上确认了闭海或半闭海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闭海或半闭海任何一个沿岸国的活动均可能对其他沿岸国的权利、义务和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特殊的地理状况促使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相互之间产生了通过合作的方式协调其活动的需求和愿望。这种合作究竟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还是一项规劝性的鼓励措施?目前国际法学界对这种合作的性质存在两种观点。
观点一: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莱恩博在其文章中就持有此种观点,他对《公约》第123条的缔约历史进行分析后称,第123条为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时施加了一项广泛的相互合作的法律义务,这是对于“合作”性质的最佳理解。〔3〕我国亦有学者认为,“闭海、半闭海沿岸国开展务实合作不仅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同时也是法定义务”。〔4〕
观点二: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是一项规劝性的鼓励措施。有学者认为,第123条的用语并不能反映出沿岸国之间、或者沿岸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合作是一项强制性的义务,而是暗示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具有规劝性质。〔5〕也有学者认为,第123条的目的在于鼓励沿岸国对闭海或半闭海进行更有效的区域治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为劝导性质,《公约》并没有规定遵守该条款的激励措施,或者违反该条款的惩罚机制,即使某一国家认为不合作才是最符合其利益的做法,其延迟合作或拒绝合作并不会招致严重后果。〔6〕
(二)沿岸国合作性质的分析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要想对第123条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性质得出客观结论,必须对第123条进行系统的条约解释。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条约的解释规则:解释条约时首先采用“解释之通则”,即依据其用语的通常含义进行善意解释,若依此法尚不可确定条约的含义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则采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即结合条约的准备工作和缔约情况进行解释。
首先,我们采用“解释之通则”,即对第123条用语的通常含义,并结合《公约》的上下文及《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进行解释。
第一,第123条用语的基本含义。第123条中用于确定合作性质的关键措辞有两处,分别出现在条款的第一、二句话中,其中《公约》中文文本的措辞为“应合作”与“应尽力……协调”,英文文本的措辞对应为“should cooperate”和“shall endeavour ... to coordinate”。《公约》中文文本两处使用了同样的措辞“应”,“应”宜作“应当”理解,此语虽然与“必须”同属于禁止性规范用语,但是不同于“必须”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绝对性,“应当”属于一般性、原则性的用语,没有绝对的强制性,特殊情况下允许例外的存在。《公约》的英文文本中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助词,情况复杂得多。在MOX Plant仲裁案中,爱尔兰与英国就如何理解should和shall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直接关系到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合作的性质。〔7〕仲裁员James Crawford教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should和shall称为国际律师们最爱玩的游戏,他甚至怀疑第123条中的should和shall可能只是一个印刷异常(typographical oddity)。〔8〕一般地,shall理解为“必须”,表示具有强制力和拘束力,shall endeavour(应尽力)在一定程度上稍微减轻了义务的强制性,但是这并不否定强制性义务的存在。而should的语气不如shall强烈,一般用于涵盖内容较多的规范性的文件中,其强制性较弱,而更多地带有原则性和鼓励性。根据《公约》第320条的规定,《公约》的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但是对第123条用语的分析可以看出,该条款的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在理解上存在不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对第123条进行整体解释。
第二,结合《公约》上下文及其目的和宗旨对第123条进行解释。根据国际法基本理论,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包括两种,即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但造成了国际损害的行为。据此可以推理,若一项行为是国际义务,那么违反该行为的行为或者是一项国际不法行为,或者是一项国际法不加禁止但是造成了实际损害的行为。假设第123条规定的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是一项国际义务,那么,沿岸国不进行合作的行为或者为一项国际不法行为,或者为一项国际法不加禁止但是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显然,沿岸国不进行合作并不会造成任何实际损害。问题的关键在于,沿岸国不进行合作的行为是否为一项国际不法行为?根据国际法委员会于2001年第53届会议上通过《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1条的规定:“一国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因此,任何一项国际不法行为必定引起国际责任的产生。一系列权威国际公约也反复重申,违反国际义务就必然引起国际责任。〔9〕然而,纵观整个《公约》的条款,其中并没有关于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不进行合作将导致责任产生的规定。换言之,第123条虽然要求沿岸国进行合作,但是这种要求并非带有责任后果。所以可以认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不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
显然,采用“解释之通则”并不能够得出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合作性质的准确结论,因此有必要回顾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公约》第123条的缔约历史,分析条款缔结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关键性文件。〔10〕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过程中,《公约》第123条“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的最终成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依时间顺序分别为:《非正式单一谈判案文》第134条,《修订的单一谈判案文》第130条,《非正式综合谈判案文》第123条和《非正式综合谈判案文》(修订稿二)第123条。这四个条款草案的主要内容大致相同,区别在于是否将沿岸国的合作规定为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非正式单一谈判案文》第134条中的关键用语分别为“shall cooperate”和“shall ... Coordinate”,但是在《修订的单一谈判案文》第130条中被相应地修改为“should cooperate”和“shall endeavour ... To coordinate”。对于此项修改,负责“闭海或半闭海”议题的第二委员会的主席解释道,在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问题上,一些国家表示对《非正式单一谈判案文》第134条用语中的强制性有所不满意,所以他认为应当减少合作义务的强制性意味。〔11〕此后,《修订的单一谈判案文》第130条中的用语被一直保留至《公约》第123条的正式条款中。从第123条的缔约历史中可见,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确实应当进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的性质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三)沿岸国合作的双重性质
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性质问题,即便严格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解释规则对《公约》第123条进行解释,亦无法得出确切的、足以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错误适用条约解释规定所致,而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第123条的内容。
实际上,《公约》第123条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条款。第一部分为条款的第一句话,即“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第二部分为条款的余下内容,即“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协调”第(a)至(d)款中所列各项事宜。第一部分要求沿岸国“应合作”(should cooperate),条款的字面含义、上下文解释或补充资料均表明,此项要求非为强制性义务,而且该句中也没有明确沿岸国“应合作”(should cooperate)的领域或具体内容,笔者认为这是《公约》鼓励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就《公约》规定的、涉及海洋问题的所有事项进行合作。此种合作为规劝性质,没有法律强制性。第二部分要求沿岸国为实现合作,“应尽力……协调”(shall endeavour ... to coordinate)列举事宜,虽然上下文解释或补充资料均表明此项义务亦非强制性,但是条款英文文本字面解释似乎暗示了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此处的确存在强制性要求,但是此强制性仅限于要求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尽力协调闭海或半闭海的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以及海洋科学研究政策等列举事宜,在适当情形下,沿岸国还应当尽力邀请其他非沿岸国或者国际组织与其合作,而非强制性要求沿岸国实现合作。综上所述,第123条规定的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并不是一项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义务,而只是一项规劝性建议。同时,第123条强制要求沿岸国尽力协调列举事宜,只要沿岸国善意促成合作,即使合作没有达成,也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
二、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义务内容
(一)沿岸国的四项协调义务
根据上文的分析,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不承担合作义务,仅承担第123条中明确列举事宜的协调义务。
第一,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有义务尽力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活动。此类协调义务的内容既包括了带有政府特征的职责事项,也包括了在许多国家属于私人活动的事项。实际上,“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在《公约》第五部分“专属经济区”和第七部分“公海”中多有涉及,例如第61(2)条要求沿海国采取“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确保生物资源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第63(1)条要求沿海国采取措施以“协调和确保”出现在多个专属经济区内的鱼类种群的“养护和发展”,第117条和第118条要求各国就养护和管理公海生物资源进行合作,第119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养护公海生物资源。
第二,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有义务尽力协调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这项义务与《公约》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规定相一致。其中,第192条规定了所有国家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为实现此目标,第197条号召各国在适当情形下,“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在区域性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区域海洋项目(Regional Seas Programme)已经在包括地中海、加勒比海、黑海、波罗的海、波斯湾等海域开展海洋环境保护的区域性协调活动。
第三,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有义务尽力协调科学研究政策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这里提到的“科学研究”是个广义的概念,实质上在闭海或半闭海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主要为海洋科学研究。《公约》第十三部分详尽地规定了“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第242条要求各国应“促进为和平目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第245条和第246条分别规定了国家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沿海国对在其专属经济区中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具有管辖权。
第四,在适当的情况下,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应当尽力邀请其他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协调上述活动。该项规定承认,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活动可能对其他非沿岸国产生影响,同时还强调通过区域合作协调生物资源养护、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科学研究这三方面事宜的必要性。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或者联合国专门机构通过签署协议或开展活动的方式参与了闭海或半闭海的合作。其中,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主要开展与渔业资源相关的活动,国际海事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要开展与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活动,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下设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要负责主持海洋科学研究的协调管理工作。
(二)自然资源共同开发不是沿岸国的义务
第123条规定的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各项协调义务均不是独立存在于《公约》第九部分中,生物资源养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和区域合作等事宜在《公约》的其他部分均有更为详尽的规定,既然如此,第123条为什么还要就这四项事宜做出重复的规定呢?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缔约国纷纷意识到,与开阔的大洋不同,闭海或半闭海的情况非常特殊。地理上,闭海或半闭海属于相对封闭的系统,与开阔大洋的循环较少;政治上,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家众多,各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复杂的主权纠纷,管辖权范围不确定。闭海或半闭海集中面临诸多海洋问题,既包括领土纠纷和海洋划界争端等主权性事项,也包括环境污染、渔业资源枯竭、海洋科学考察纠纷等非主权性事项。这三类非主权性事项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扩散性”特征,即无论这三种问题发生在闭海或半闭海的任何地方,整个闭海或半闭海区域以及所有的沿岸国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因此,尽管《公约》其他部分对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海洋科学考察事宜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考虑到闭海或半闭海的地理和政治独特性可能放大这三类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公约》缔约国认为仍然有必要在第123条中明确列举这三类事宜,并要求沿岸国承担协调义务,实现沿岸国之间或沿岸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以解决这三类问题给整个闭海或半闭海地区带来的不利影响。
莱恩博在文章中称,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承担合作的义务,南海是《公约》定义下的一个半闭海,作为南海的沿岸国之一,中国承担与其他沿岸国合作共同开发南海自然资源的义务。〔12〕笔者对此并不赞同,莱恩博的此项错误观点源于其对《公约》第123条的错误解读。根据《公约》第123条的规定,闭海或半闭海地区的自然资源共同开发并不是沿岸国的义务。一方面,第123条关于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不过是一项规劝性的建议,自然资源的共同开发只不过是《公约》鼓励的一项行为,而没有上升到法律义务的层面;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共同开发不在第123条明确列举的沿岸国的协调义务之列,沿岸国亦不承担自然资源共同开发的协调义务。因此,中国虽然是《公约》规定的半闭海沿岸国,在南海自然资源开发的问题上,中国不承担与其他沿岸国合作的法律义务。
三、南海合作开发与中国的善意
虽然从国际法角度而言,中国与南海其他沿岸国共同开发自然资源并非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愿意与其他沿岸国共同开发南海的自然资源。中国与数个东盟国家就南海的岛礁主权归属的南海海域划界问题存在争议,但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这是中国为解决南海问题所秉承的善意。
(一)善意是合作的基本要求
善意即good faith,〔13〕我国学者亦将其译为“诚信”〔14〕“诚意”〔15〕等。善意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也是许多国际法律规则的基础。E·左莱尔在其著作《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中称,国际公法中不存在根据善意行为而产生的一般义务,善意不过是一项道义原则。〔16〕客观而言,善意原则兼具“超法律性”(extra-legal)与法律性的双重内在特质。〔17〕法律性是指善意原则是国家履行条约规定的法定义务的要求,《联合国宪章》第2条要求各会员国在履行《宪章》义务时应当秉承善意。《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序言中明确,善意是一项举世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并在第26条中规定,条约当事国应当善意履行条约义务,此为“条约必守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0条规定,缔约国应诚意履行《公约》义务。“超法律性”是指善意原则暗含了诚实、公正和合理等政治性和道德性内涵,〔18〕是国家从事一切与条约相关活动时必须秉承的基本原则。有学者认为,善意的“超法律性”导致其在国际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国际实践表明,由于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天使般的行为,国家所谓的善意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神话。”〔19〕
善意原则从条约的缔结到条约的终止的整个过程中支配着条约,〔20〕缔约国应当就条约的一切规定善意行事,即使该项规定并非条约义务,而仅是条约建议或倡导的行为。《公约》第123条规定的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既没有法律强制性,也没有法律后果,但是善意原则为这项规劝性的建议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沿岸国应当善意地就《公约》规定的所有涉及海洋问题的事宜进行合作,特别是善意地协调第123条中的列举事宜,尽力促成合作。
(二)中国的行为已尽善意原则的要求
莱恩博在其文章中称,中国坚持的双边谈判由于没有将所有声索国纳入谈判体系,而且有拖延之嫌,不符合善意原则,因此声索国有权以中国违反善意为由单方面提起仲裁。〔21〕其观点是对中国政策的错误解读。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方针政策,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为“《宣言》”)向“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过渡,并在坚持双边谈判解决南海争议的基础之上,通过“双轨思路”的实施,促进南海的区域稳定与合作。
第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是拖延战术,而是缓和地区紧张气氛,勾勒出南海共同合作开发的基本框架。“搁置争议”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为解决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主权争议而提出的口头协议,根据习惯国际法,这是一项有效的、有拘束力的协议;1979年提出的“共同开发”则是中国单方面的主张和承诺,不具有法律特征。〔2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时,提议在南海海域运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此提议得到了菲律宾的积极回应。〔23〕实际上,我国主张将争议暂时搁置,目的在于缓和各国的紧张局势,为共同开发创造环境。只有搁置了争议,争端各国才能在谈判中进行良性的对抗和互动,在法律和事实主张上达成共识,并尊重彼此的关切。〔24〕
第二,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向“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过渡,表现出中国善意与南海其他沿岸国合作开发南海的决心。善意谈判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开会或讨论,而是要求参与各国表达对他国权利和利益的“合理关切”(reasonable regard)。具体来说,善意谈判要求参与国家怀有友好的解决分歧的意愿,〔25〕并且应当实质性地开展,不流于形式。〔26〕中国与东盟各国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建议各国不采取使南海争端复杂化或扩大化的行动,并建议在争端解决前,在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开展合作。《宣言》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具体化和制度化,但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此后,中国积极贯彻落实《宣言》第十条,致力于推动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2016年9月召开的东盟峰会上,中国再次积极要求与东盟各国重启“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讨论,这是中国作为《公约》规定的半闭海沿岸国,善意落实相关制度的表现。
第三,南海争端只有通过双边谈判才能获得根本解决,“双轨思路”的提出为中国与南海沿岸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领土主权争端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综合问题,诉诸于法律方法难以得到妥善的解决,政治方法才能最有效并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间的领土和划界争端。〔27〕南海问题直接涉及六国七方,还遭到一些域外国家的间接干涉。考虑到中国与各个直接争议方之间的问题各有特殊之处,因此,只有双边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目前,中国已经通过双边谈判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签订了领土划界协议,并与越南达成了北部湾海域的划界协定。2014年8月,我国提出了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争端,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争议,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是中国在坚持双边谈判基础上,切实维护作为半闭海的南海的和平秩序,并积极谋求区域合作的善意之举。
四、总 结
克里斯托弗·莱恩博先生在其文章中对于《公约》第123条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合作制度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并由此得出了对于中国政策和行为的不实解读,曲解了中国以善意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实现南海合作的意图。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回应:
第一,闭海或半闭海是一类特殊海域,《公约》除了规定一般性法律制度在该海域的适用以外,还特别强调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
第二,经条约解释后可知,《公约》第123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并不是一项法律义务,而是一项规劝性的建议。《公约》建议沿岸国就涉及《公约》的一切海洋问题进行合作,并特别要求沿岸国尽力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以及海洋科学考察活动,并尽力协调非沿岸国或国际组织的参与,以促进合作的实现。
第三,海洋自然资源的合作开发不是《公约》第123条规定的国际义务,中国没有与南海其他沿岸国合作开发南海自然资源的义务,但是中国愿意本着善意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南海其他沿岸国共同合作,开发南海的自然资源。
第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是拖延战术,而是为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和平合作的手段。双边谈判不是为了拒绝与声索国谈判,而是考虑到中国与每一个声索国争议的特殊性,双边方式能更好地解决争端。中国还不遗余力地推动有拘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达成,提议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这一系列行为都反映了中国以善意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态度和决心,中国的行为符合《公约》的规定。
注释:
〔1〕〔3〕〔12〕〔21〕Christopher Linebaugh,“Joint Development in a Semi-Enclosed Sea:China’s Duty to Cooperate in Develop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52,No.2,2014.
〔2〕〔5〕Satya N.Nandan C.B.E.And Shabtai Rosenne(Volume Editors),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A Commentary(Volume III),Articles 86 to 132 and Documentary Annexes,The Hague:Ma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pp.344,357,366.
〔4〕海民、张爱朱:《国际法框架下的南海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第72页。
〔6〕Joshua Owens:《闭海或半闭海制度——北冰洋是半闭海吗?》,《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201页。
〔7〕In th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MOX Plant,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Irish Sea,Ireland v.United Kingdom,Memorial of Ireland,Vol.I,p.143,paras.8.20-8.23,26 July 2002;Counter-Memorial of UK,pp.139-140,paras.6.11-6.13,9 January 2003.
〔8〕In th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MOX Plant,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Irish Sea,Ireland v.United Kingdom,Transcript/Minutes of Proceedings Day Five,17 June 2003,pp.23-24.
〔9〕李寿平:《现代国际责任法律制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10〕Makane Moise Mbengue,“Rules of Interpretation(Article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ICSID Review,Vol.31,No.2,2016,p.389.
〔11〕A.CONF.62/WP.8/Rev.1/Part II,Revised Single Negotiating Text(Part II),1976,Official Records,Vol.V,“Introductory Note”,p.154,para.21.
〔13〕《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中文译本将good faith译为“善意”。
〔14〕〔20〕郑斌:《国际法院与法庭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韩秀丽、蔡从燕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1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文译本将good faith译为“诚意”。
〔16〕〔法〕M·维拉利:《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刘昕生译,《国外法学》1984年第4期,第54页。
〔17〕Andrew D.Mitchell,M Sornarajah,and Tania Voon(eds.),Good Faith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2.
〔18〕赵建文:《条约法上的善意原则》,《当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121页。
〔19〕Bernardo M.Cremades,“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27,No.4,2012,p.779.
〔22〕管建强:《对钓鱼岛主权“搁置争议”的国际法评述》,《学术界》2012年第4期,第111-112页。
〔23〕外交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58.shtml,最后访问:2016年10月12日。
〔24〕张新军:《中国周边海域争端处理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考》,《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第1134页。
〔25〕Steven Reinhold,“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UCL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Vol.2,2013,p.56.
〔26〕John G.Laylin and Rinaldo L.Binachi,“The Role of Adjud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River Disputes:The Lac Lanoux Case”,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3,No.1,1959,p.48.
〔27〕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3条的规定,国际争端之解决方式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等政治方法,以及国际司法或仲裁等法律方法。
〔责任编辑:刘鎏〕
王玫黎(1964—),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畅(1989—),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闭海或半闭海制度研究”(16YJA711700),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区域海洋合作开发制度的国际法问题研究”(CYB16089)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