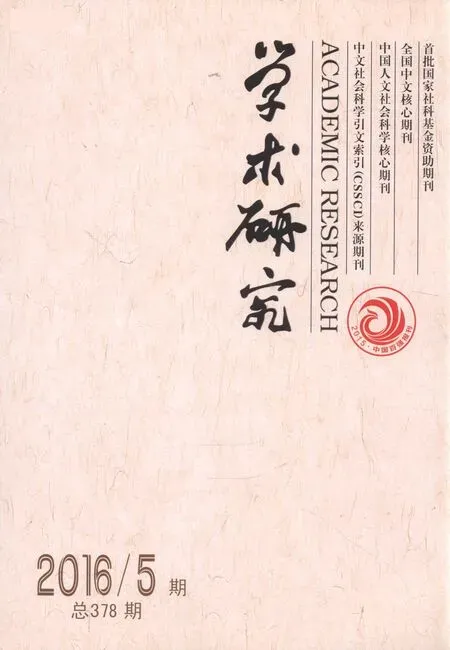王世贞对江西诗的批评*
2016-02-26吴晟
吴晟
王世贞对江西诗的批评*
吴晟
[摘要]明代“后七子”的代表王世贞论诗倡格调说,与明代“前七子”不同,他从才思来谈格调,进一步深入到艺术意境的探讨,以矫江西诗之生涩奇峭,批评宋人资书以为诗,淹没了诗人情性,距真诗甚远。主张师古而不泥古,模拟古人以不犯痕迹者为佳;倘若不能师心独造,所作诗终究是古人面目,已落入第二义,以此药江西诗之模拟剽窃。
[关键词]王世贞格调说师古江西诗生涩奇峭模拟剽窃
*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经典的认同研究”(2014WZDXM021)的阶段性成果。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在明代中叶,他不仅以政术显世,而且是以诗文鸣世的重要作家和文论家,为明代“后七子”之一。《明史》卷287载:“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1]可知他才高望重,名噪天下,海内文士,争趋其门下,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弇州山堂别集》《读书后》等近500卷。《艺苑卮言》为其诗论代表作。
20世纪以来王世贞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生平研究,主要为王世贞编撰年谱;(2)文学研究,热点集中在王世贞是否为《金瓶梅》的作者;(3)对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史学与书画成就等研究。[2]其中王世贞文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论中的格调、情采、性灵及复古思想探讨;关于王世贞对宋诗的态度,有两篇代表性论文。邱美琼《论黄庭坚诗歌在明代的接受》认为,王世贞首先肯定了苏轼、黄庭坚诗歌的创新求变特色,但又指出黄诗刻意务新求巧,不如苏诗于新变中含蓄自然流畅之美,并比较了苏、黄学杜的不同,苏渊源于杜诗五古、排律,自然浑成;黄取法于杜甫歌行,奇崛拗硬。[3]陈颖聪《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指出,王世贞批评宋诗,但没有全盘否定宋诗,看到宋诗对明代诗坛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各个时代的诗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反对以时代肯定诗歌创作的优劣。[4]二文均以苏、黄比较来评判王世贞对宋诗的态度,认为王世贞对黄诗肯定较多。其实二文非专论王世贞对江西诗的批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宋诗指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派诗,不包括苏轼的诗歌;尽管黄庭坚诗歌在明代的唐宋诗之争中呈低落回升、彼消此长态势,但王世贞对江西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一、倡言格调,矫江西诗之生涩奇峭
作为明代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王世贞重举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大旗。《艺苑卮言》卷1云:“李献吉(李梦阳)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5]卷7又云:“而伯承者(李先芳),①李先芳(1511—1594),字伯承。早与李攀龙首倡诗社,后七子兴起,不予七子之列。其诗与李攀龙异曲同工,名为攀龙所掩。前已通余于于鳞(李攀龙),又时时为余言于鳞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6]大历以后的诗歌不必读,宋诗便自然不足观了。
明代前期茶陵派李东阳首创格调说,其《怀麓堂诗话》云:“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侧短长,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7]“诗必有具眼,变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待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8]王世贞对此说有所发展与深入,他说: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9]
李树军这样理解:“才是才能、性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总和;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10]袁震宇、刘明今认为:“此语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由才思产生格调,二是格调为才思的境界。”[11]陈伯海解释说:“诗人的才情形成了诗篇的构思,构思产生了音调,音调的高下又决定着作品的形体规范”,同时他主张:“用特定的形体规范来给诗歌音调立界,更以形体与声音的规范来制约诗人的才思。”[12]萧华荣指出:“显然在他看来,才、思更首要,更主动,调、格不过是才、思的生成物。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和重视调、格对才、思的规范作用,认为‘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境’、‘界’在这里均指疆域、界限、范囿,……他主以调、格规范才、思,不至于流为佚荡无检,即才、思不能损伤调格。”[13]简言之,诗歌的格调即诗歌的体制与规范。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指出:“从才思来谈格调,就进一步深入到艺术意境的探讨。”[14]朱恩彬解释说,“意谓作者才情,通过构思,形成于音节,构成意境,而诗格也就体现在其中了”;进而评价说,“王世贞看到了作品境界的构成与作家才思的关系,接触到了意境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注意到了作家创作主体的作用”。[15]王世贞说:“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完使之然。”[16]作为诗歌格调的篇法、句法、字法之“妙”,最终必须取决于诗歌“兴与境诣、境与天会”,反之,诗歌格调未妙便不能臻于“兴与境诣、境与天会”的佳境、妙境。这从他对沈嘉则诗歌的评论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夫格者,才之御也;调者,气之规也。子之响者,遇境而必触,蓄意而必达。夫是以格不能御才,而气恒溢于调之外。……今子能抑才以就格,完气以成调,几于纯矣。”[17]指出诗人的才、气驾驭并规范着诗歌的格调,而诗歌的格调又反过来制约着诗人的才与气。评价沈诗能够抑制才思以就格,贯注充沛之气以成调,故其音节响亮、体制纯正的格调自然蕴含于生成的诗歌意境之中了。
宋人尚格不主调,“诗格变自苏、黄,固也”。[18]宋人所尚格主要指“超尘出俗的风神、作品的余味、生动传神、以及结构的和谐美等诸方面的意蕴”。[19]宋人“不主调”则主要指江西诗派尤其是黄庭坚有意追求音节不和谐、平仄不协调的拗体诗,以“破弃声律”,造成生涩而不滑熟的陌生化艺术效果,从而表现一种兀傲绝俗的人格。如《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其中颈联平仄为: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平平仄平,不仅使句子拗折有力、生涩奇峭,又与黄几复刚正不阿的性格及作者的愤激之情和谐统一。黄庭坚这类拗体诗还有《病起荆州江亭即事》《谒李材叟兄弟》《谢答闻善绝句》《寄上叔父夷仲》《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兼简履中南玉》《廖致平送绿荔支》《赠郑交》等。张耒评价说:“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声和鸣,浑然天成,有言外意。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20]胡仔辨析说:“古诗不拘声律,自唐至今诗人皆然,初不待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文潜不细考老杜诗,便谓此体‘自吾鲁直始’,非也。鲁直诗本得法于杜少陵,其用老杜此法何疑。”[21]胡氏的批评甚是,黄庭坚“破弃声律、以文为诗”确由杜甫的拗体诗而来,并非首创。王世贞指出,“彼见夫盛唐之诗,格极高、调极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尽变,故独于少陵氏而有合焉”,批评“无论苏公,即黄鲁直,倾奇峭峻,亦多得之少陵,特单薄无深味,蹊径宛然,故离而益相远耳。鲁直不足观也。”[22]同样破弃声律,王世贞却盛赞杜甫诗歌“格极高、调极美”,能“酬物而尽变”,而独诟病黄庭坚诗歌“单薄无深味”而“不足观”,实囿于其诗必盛唐的成见。
世贞云:“山谷《中兴颂》碑后诗,是论宗语。俯仰感慨,不忍再读;迫切诘屈,亦令人易厌。”[23]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赴宜州贬所途经永州时,游浯溪,观颜真卿书元结的《大唐中兴颂》磨崖碑,作《书摩崖碑后》。诗中评论唐玄宗因宠任安禄山以致失国,及肃宗擅自即位并受制于张后、李父以致失为人子之道,用意深刻,足为后世鉴戒。曾季貍《艇斋诗话》评说:“山谷《浯溪碑》诗有史法,古今诗人不至此也。”[24]胡仔推为“杰句伟论,殆为绝唱,后来难复措词矣。”[25]对黄庭坚这首思想深刻、笔力苍劲、风格纯熟之作,王世贞在指出它是“论宗语”,俯仰古今、感慨万千、使人不忍再读的伤感作,之后却批评它措辞急迫严厉、生涩拗折,“令人易厌”。这足见他对其诗歌偏见之深。
王世贞既承认“诗格变自苏、黄”,又批评“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26]故谓黄庭坚诗不如苏。王世贞说过:“余所以抑宋者,为惜其格也。”[27]黄庭坚诗歌以格韵高绝、脱尽流俗著称并为后世公认。在此,王世贞所谓“格”仍然指诗歌的体制与规范,与宋人所谓“格”的内涵有所不同。“愈近愈远”如何理解?试看下面两则诗论:其一,“虽然声响而不调则不和,格尊而亡情实则不称”;[28]其二,“然其高者,以气格声响相高而不根于情实,骤而咏之,若中宫商,阅之若备经纬而已,徐而求之,而无有也”。[29]在王世贞看来,黄庭坚诗歌由于“破弃声律”,失去声响之和谐,造成“格尊”与“亡情实”不相称;即使“以气格声响相高”,但“不根于情实”的作品,最终仍然既不中宫商——无调可言,也不具备经纬——无格可寻。所谓“情实”,即“盖有真我,而后有真诗”,[30]这是王世贞晚年悟罢所得,它已突破了他以前恪守格的体制与规范局限,认识到有真我才有真诗。以此观之,他不满黄诗“愈近愈远”,主要指黄庭坚学习前人,以书本材料为诗,“不根于情实”,淹没了诗人情性,因而距真诗甚远。
明人以格调为核心论诗,欲以高格矫元诗之格卑,以逸调矫宋诗之调舛。“‘格’是诗的词采、对偶等形成的视觉体貌及其所引起的审美感受,‘调’是诗的声律、音韵等形成的听觉律动及其所引起的审美感受”。[31]王世贞论诗评诗特别注重调,他在答胡应麟论诗时说:“累诗格调高秀,声响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家弟畏之固当。……才骋则御之以格,格定则通之以变;气扬则沉之使实,节促则澹之使和。非谓足下所少而进之,进仆所偶得者而已。”[32]美胡应麟诗格调高秀,声响宏朗,入字入事皆古雅。接着,论述了才、格、气、节之关系:以格御才,以变通格;气扬则使之沉实,节促则使之澹和。足见王世贞论诗重视听觉效果,总是离不开节奏音调。明代戏曲发达,戏曲追求音响效果,王世贞是一位精通戏曲的作家和曲论家,《艺苑卮言》附录4卷论及词曲诗画,对南北曲产生及优劣所作评述时有创见。他以“格调高秀”来论诗,重视诗歌的音乐性,与他的戏曲观念和趣尚不无关系。
二、主张师古,药江西诗之剽窃模拟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指出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33]所谓“以才学为诗”即资书以为诗,包括模仿、点窜、化用、改造前人的作品。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4]“以才学为诗”是黄庭坚示以后学的学诗必经门径,却向来遭人诟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无论是杜诗还是韩文,都善于点窜、化用前人作品不留痕迹(谓“无一字无来处”言之过甚),但秘而不宣,黄庭坚却将其说破,并示之与人,故引起公愤;二是江西诗派及后学在点窜、化用前人作品时留下了逊色于原作的口实。批评最尖锐者当属金代王若虚,他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35]王世贞也有类似的批评:
独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而黄鲁直更之曰:“人家围橘柚,秋色老梧桐。”晁无咎极称之。何也?余谓中只改二字,而丑态毕具,真点金作铁手耳。[36]
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陈则云“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陈则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暂香”,陈则云“寒花只自香。”上览可见。[37]
前则材料批评黄庭坚化用李白诗句为“点金成铁”,后则材料批评陈师道化用杜甫诗句属“点金成铁”。两相对照,“丑态毕具”,一览可见。王世贞主张师古,注重学习古诗文的法度规则,认为重视法不能泥于法。《艺苑卮言》卷1云:“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采,各极其造,字法也。”[38]他具体谈及七言律之法颇为精微:“七言律,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耳。发端,盛唐人无不佳者;结颇有之,然亦无转入他调及收顿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39]七言律诗之法,从发端到结束、收放到照应、开阖到抑扬、取象到立意的篇法;从直下到倒插的句法;从虚实到沉响的字法,头头是道,较之江西诗派句法更为具体入微。既然古代诗文有其法度规则可循,师古者就必须遵照恪守,遵守包含了模拟。但王世贞认为:“模拟之妙者,分岐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手,兼之无迹,方为得耳”。[40]他认为王维诗之所以胜出孟浩然诗一筹,“由工入微,不犯痕迹”之故,“所以为佳”。[41]他批评黄、陈诗点窜李、杜诗句“点金成铁”,亦是就模拟痕迹明显而发。
王世贞主张师古,反对模拟剽窃,认为“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但他又认为,模拟古人“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并示以例证:“‘客从远方来’,‘白杨多悲风’,‘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窃也。其次,裒集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黄鲁直宜州用白乐天诸绝句,……然犹彼我趣合,未致足厌。”[42]“黄鲁直宜州用白乐天诸绝句”指黄庭坚《谪居黔南十首》。任注曰:
“近世曾慥端伯作《诗选》(即《宋百家诗选》),载潘邠老事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辄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秩,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端伯所载如此,必有依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43]
任渊也不同意曾慥谓黄庭坚《谪居黔南十首》“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的说法,认为它只是“改易数字”而成,“可为作诗之法”,当包含“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诗法在内。尽管王世贞对黄庭坚点窜杜诗持异议,但对黄庭坚“用白乐天诸绝句”“小加剪裁”的《谪居黔南十首》并不反感,还认为颇投合他的趣味。这说明王世贞在对待模拟化用前人作品这一问题上,是表现得比较辩证、通脱的。
王世贞师古的诗学观受严羽影响颇为明显,《沧浪诗话·诗辨》云:“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44]《艺苑卮言》卷1云:“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45]所谓“师匠宜高”即师古取法要高要严,所谓“捃拾宜博”即师古要兼收并采,他说:“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46]又说:“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47]较之于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诗必盛唐”的观点,取径稍宽。然而毕竟为“诗必盛唐”成见所囿,王世贞固执地坚持“贞元而后,方足覆瓿”,[48]摒弃贞元以后的作品不观,“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后事。此诗家魔障,慎之慎之”。[49]王世贞云:“鲁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50]佛经分为大小二乘。佛说法因人而施,人有智愚,故所说有深浅。其说之广大深赜者为大乘,浅小者为小乘。严羽以禅喻诗:“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51]郭绍虞先生释曰:“辟支、声闻仅求自度,故称小乘。辟支,梵语独觉之义,谓并无师承,独自悟道也。声闻,谓由诵经听法而悟道者。”[52]再联系《艺苑卮言》“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已落第二义矣”,[53]可知王世贞批评黄庭坚虽然善于师古,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但由于受到古人法度的制约而缺乏变通,不能“一师心匠”——按自己的意图去立意构思,“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所作诗终究是古人面目,已落入第二义了,直是傍门外道,不足观也。
晚年王世贞的诗学观不再迷信严羽:“夫古之善治诗者,莫若钟嵘、严仪卿,谓某诗某格、某代、某人,诗出某人法。今乃悟其不尽然。”[54]始悟“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书李西涯乐府后》)。于是他有取于宋、元之诗,其《宋诗选序》云:
自杨、刘作,而有西昆体,永叔、圣俞思以淡易裁之;鲁直出,而又有江西派;眉山氏睥睨其间,最号为雄豪,而不能无利钝;南渡而后,务观、万里辈,亦遂彬彬矣。去宋而为元,稍以轻俊易之。明兴而诸大夫之作,不能无兼采二季(宋、元)之业。而自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显弘、正间,古体乐府非东京而下至三谢,近体非显庆而至大历,俱亡论矣。二季繇是屈矣。吴兴慎待御子正,顾独取《宋诗选》而梓之,以序属余。余故尝从二三君子后抑宋者也,……余所以抑宋者,为惜其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而已。此语于格之外者也。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55]
这是为慎蒙(字子正)所编《宋诗选》而作的序,俨然一篇“宋元明诗歌简史”,当王世贞接触到杨亿、刘筠、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人的宋调,油然顿生彬彬盛矣之感,始悟“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之理,觉得宋诗、元诗亦不妨读,他说:“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中于七言绝句及颔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但所谓差之毫釐,谬之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56]
王世贞虽然突破了前七子的拟古论,但仍固执地坚持其格调说。他认识到宋元诗虽然不可偏废,但毕竟是“格之外者也”,即宋元诗终究不能与盛唐诗同日而语,它只能为我所用,决不可迁就它。他特地说明慎蒙编选宋诗“以序属余”,“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并非嘱我鼓吹张扬宋诗,而是以备创作参照之用。这与其说是慎蒙编选宋诗的初衷,毋宁说是王世贞固守对待宋诗的基本立场。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34页。
[2]鱼茜、姚红卫:《20世纪以来王世贞研究术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邱美琼:《论黄庭坚诗歌在明代的接受》,《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陈颖聪:《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阴山学刊》2012年第2期。
[5][6][9][16][17][22][23][27][28][29][30][32][37][39][40][41][42][45][46][47][48][49][54][55]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
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01、4300、4201、4199、4449、4547、4445、4455、4474-4475、4456、4479、4539、4250、4199、4202、4238、4249-4250、4198、4198、4202、4198、4200、4479、4455页。
[7][8][24][35][38][5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70、1371、296、523、963、964页。
[10]李树军:《王世贞“才、思、调、格”的文体意义》,《江汉论坛》2008年第3期。
[11]袁震宇、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12]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6-337页。
[13][31]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2、241页。
[1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8页。
[15]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703页。
[18][26][36][50][56]王世贞:《艺苑卮言》卷4,傅璇琮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35、235、235-236、235、236页。
[19]凌左义:《黄庭坚“韵”说初探》,《中国韵文学刊》1993年第7期。
[20]王直方:《王直方诗话》引,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1页。
[21][2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卷,第57、58页。
[33][44][51][52]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1、11、14页。
[34]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4页。
[43]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42-443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流寓文化研究·
[编者按]流寓文化研究,经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雷州文化研究基地张学松教授倡导,召开过两次全国专题研讨会,并围绕苏轼流寓经历开过一次国际研讨会。然而,此前研究话题较广,深入具体研究不多。为此,《学术研究》杂志社与该基地合作,2015年12月19日承办了岭南学术论坛第69期:“流寓文士与中古岭南文化研讨会”,以推进流寓文化研究与岭南文化研究的结合与发展。会议围绕岭南作为贬谪官员流放地域的历史上下限、中古岭南文化发展阶段、流寓岭南文士分布情况、流寓岭南文士的身份意识、文化作为及其思想和文风转变、流寓文化理论与流寓文学研究等话题深入研讨。而今年恰逢著名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纪念,故先选编考证汤显祖《粤行五篇》,本刊将陆续刊载与流寓文士及中古文化发展相关的论文。
作者简介吴晟,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1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