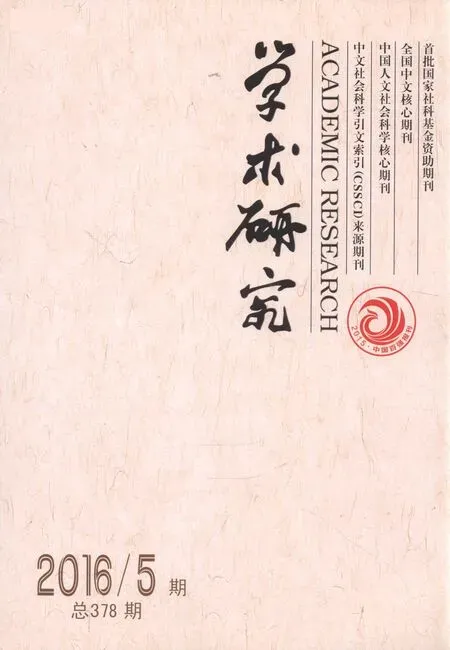《红楼梦》“悲剧”说辨议
2016-02-26张均
张均
《红楼梦》“悲剧”说辨议
张均
[摘要]以西方文论强制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是近年学界普遍反思的问题,将《红楼梦》解读为西方式悲剧是其中典型个案。西方悲剧起于人高于万物、改造万物的自由意志,《红楼梦》则起于人与万物俱逝的痛苦。西方悲剧重在斗争故事,《红楼梦》则系心于回忆的诗学。西方悲剧在故事中安置了自由的成长机制,《红楼梦》则在重重回忆中破除人的执念。反思悲剧以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等西方概念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强制阐释,有利于古代文学研究问题空间的重建。
[关键词]强制阐释《红楼梦》悲剧
最近,以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中国文学现象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反省。不过,多数反省都集中在当代文学研究,实则古代文学研究更见严重。这是因为,现当代文学的兴起、发展的确受益于西方思想的激发,以西释中尚未尝不可,但对作为中国经验的古代文学亦如此为之的话,那跨语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1]的强制阐释现象就必然发生。既然如此,何以古代文学研究反省反而少呢?这大约是因为古代文学研究使用的西方概念往往不是近20年才引入的时新术语(如话语、互文、现代性等),相反,它们(如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悲剧、典型等)输入中国学术系统都已接近百年,业已自然化、中国化。但恰是在此,强制阐释发生得最严重。系统剖析这些基本概念的强制性毋宁是有待展开的重要问题,从悲剧概念之于《红楼梦》的强制阐释可略见一斑。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以后,中经马克思主义与海外红学的相互激荡,“悲剧”论已逐渐成为红学研究中的共识。对此,亦曾有学者表示“尤其不赞成王国维的硬扣的态度”。[2]但悲剧概念之于《红楼梦》是怎样硬扣的,学界并无系统分析,本文拟从动因、策略、机制等方面依次讨论《红楼梦》何以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悲剧,并就古代文学研究问题空间的重建略表意见。
一、《红楼梦》不同于悲剧的叙事动因
研究一部作品,或许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厘清作者何以要讲述这一故事。恰如丁玲所言:“(作家)不是无缘无故的要做一个作家才走向写作生涯的;也绝不是做了一个梦,醒来后便要立志做一个作家的。”[3]厘清了作者动机,才能进一步了解他(她)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去讲故事,何以产生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审美效果。《红楼梦》初看起来的确是讲了一个类似《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向封建礼教发出了第一声抗议”[4]的西方式悲剧,但实则作为“中国传统中最伟大的小说”,[5]它讲述故事的逻辑与西方悲剧风马牛不相及。而其最初的差异,就植根在叙事动因的不同上。要理解这种不同,宜先了解古希腊以来西方人是怎么认识悲剧的。对此,别林斯基认为:“(对于)希腊人来说,生活有其暧昧的、阴沉的一面,他们称之为命运,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甚至要威胁诸神。可是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前面,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了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和生命,却不贬低他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6]这种主、客对立,以人类自由意志与某种外部力量(命运、规律、秩序等)的搏击为内容,旨在肯定人的尊严并通过主人公的毁灭“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7]的悲剧叙述最早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等经典剧作中确立。而在此后,“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或因“极恶之人”的“交构”而产生的人生挣扎,[8]就构成了西方三大悲剧类型(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共同特征。其中,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直接表现为自由意志与外部力量的冲突,性格悲剧则是此冲突在个体性格中的内化。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将悲剧理解为人物内心矛盾的结果,但又认为悲剧最深刻的根源只存在于客观的社会矛盾中,悲剧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9]不难看出,自由意志构成了西方悲剧故事的动因,它们不是为了展示不幸,而是为了凸显人作为宇宙主体的使命感和尊严感,“(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10]这正是徒劳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之所在:“他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他是自己岁月的主人”。[11]亦因此故,西方悲剧中的“英雄人物虽然在一种意义上和外在方面看是失败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高于他周围的世界”,“他们并没有受到击败他的命运的损害”。[12]到了近现代,这种不可摧毁的自由意志更发展为秉有历史自信、挑战秩序、改造社会的强力意志。后者就构成了《红与黑》、《复活》等悲剧的动力。其中,即便主人公最终遭受失败,但作者仍然藉此“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13]成功批判“没有公道”的社会制度、伦理秩序等,甚至向读者揭示了新的出路。可见,展现人作为万物主宰的尊严感或“英勇而骄傲”地推动社会进步,构成了西方悲剧的叙事动因。
那么,《红楼梦》在叙事动因上是否与西方悲剧一样源于自由意志呢?答案是否定的。贾宝玉不但与“人的伟大崇高”无缘,甚至对“我”的存在也不看重。他动辄谈死,动辄就要放弃自己。如第十九回他对袭人说:“好姐姐!好亲姐姐!……只求你们同看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你们爱那里去就那去了。”第三十六回又说:“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显然,贾宝玉的自由意志薄弱得几近于无。因此,他被刘小枫认为是儒家精神“无从克制历史王道中的恶”而“被石化、植物化”[14]的结果。当然,刘小枫可能以为经由与外部力量的斗争而获得崇高是所有人都应经过的精神之路,但曹雪芹等中国古典文人可能并不如此认为。“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斤斤计较于“我”又如何,“崇高”又如何?甚至“推动社会进步”又能如何?到头来,一切抗争、一切“英勇而骄傲”的结局都不外乎“荒冢一堆草没了”。诚然,站在西方立场,可以指责曹雪芹消极、不理解人的高贵。但站在曹的立场,不也同样可以讥笑古希腊人肤浅、泥陷于“我执”和“法执”而不自知么?在此,如果我们不坚持以西律中而按其自身来理解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红楼梦》有其自己充分正当而充满魅力的讲述悲、喜故事(不仅是“悲”事,它既述不幸之爱情又“备极风月繁华之盛”[15])的理由。
《红楼梦》的叙事动因实可从其“十六字纲领”——“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第一回)——获得答案。“因空见色”,据字面理解是指作者因深感虚空故而来呈现这大千色相、讲述那红尘故事,即是说,虚空感构成了《红楼梦》的起因。这使《红楼梦》与西方悲剧貌合神离:看似和后者一样涉及“新与旧的冲突,两种人的冲突,两种思想的冲突”,[16]但其实不甚相干。不过,“云空未必空”,作者倘若真的已入“空”境也就不会“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来完成此“泣血之作”了。所以,“空”应该理解为曹雪芹为深渊般的痛苦紧紧缠绕时希望达到的超越状态。而从他“泪尽而逝”的现实结局看,他终究未能超越,故“因空见色”准确的释义应是“因悲见色”。这正是《红楼梦》的叙事动因,恰如第七十八回所称:“悲则以言志痛。”那么,曹雪芹又有何悲呢?对此,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古人普遍深永的生命痛感,如“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于骐骥之驰过隙也”(《庄子·盗跖》),“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杂诗》),“人生若浮寄,年岁忽蹉跎”(张华《轻薄篇》),“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等等,这种种感伤,都通向古人强烈的生命体验——虚无感。在《桃花扇》研究中,高小康称之为最终的胜利者:“整个作品中的世界观没有向人们哪怕是间接地暗示存在着最终意义上将会胜利的正义——如果说故事中的世界真的有什么最终的胜利者,那就是虚无。”[17]另一方面,曹雪芹个人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也将他推至虚无之前。他“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18]家世之痛,爱情的毁灭,美好事物无可抵挡的流逝,可能都曾使他为浩大的悲伤所包围。《红楼梦》由此诞生:“(他以为)人生无法进入美满的境地。生命现象的本身便是一个悲剧”,“痛苦之余,悲哀之余,他就拿起笔来,用心血写起他的场面广大的故事来。”[19]如果说西方悲剧发端于人的自由、尊严和改造社会的勇气的话,那么《红楼梦》则起源于古人的大绝望。前者希望在斗争中展示人高于万物的尊严甚至征服不义,后则对斗争、征服兴味索然,只是系心于安慰自己痛苦的魂灵。两者差异极大:前者是希望者的文学,后者是绝望者的文学。虽然这并不妨碍它们涉及相似的失败的爱情,但若因此就把古希腊式悲剧硬扣到《红楼梦》上去,无疑是比较严重的强制阐释。
二、《红楼梦》不同于悲剧的故事策略
绝望的文学和希望的文学的不同,在故事策略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西方悲剧性文学发展到19世纪,易卜生式社会悲剧日渐为主。这类悲剧在故事经验层面,往往将斗争作为“可以叙述之事”的重心,多讲述个人与不合理社会制度和伦理秩序之间的冲突,藉以批判社会、吁求进步。《红楼梦》亦往往被悲剧论者如此误读,认为它正是“叛变封建世俗男女相爱的理想结合与恪守贵族家世利益和封建礼法的‘金玉良缘’的尖锐冲突”。[20]这种趋从西方化的答案在两点上大有纰漏。一是有意识忽略西方悲剧完全不需要的“风月繁华之盛”的描写。但这种在悲剧中纯属多余的内容(如宴饮、诗会、节庆等)在《红楼梦》中却铺天盖地、无穷无尽。二是忽略了曹雪芹的叙事动因。易卜生式的悲剧大写斗争,意在批判并改进社会,但曹雪芹对进步、改革并无兴致,相反却沉溺于“人生永恒的悲哀”,“不知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想也想不到怎样悲惨的现实都可以由人们改造的”,[21]因此,《红楼梦》尽管也出现人物矛盾,但它们不会像西方悲剧一样在整体上成为故事的组织逻辑。相反,《红楼梦》的“以言志痛”取资于中国古老的文化和叙事经验。
那么,面对虚无时古代士大夫会如何通过文字安慰自己的灵魂呢?对此,单世联写道:“中国文化是记忆的文化。文学记忆的特征之一,不在于重述既往史事,而在于将往事中的情境和心境以诗的方式予以重现或复苏。在穷困潦倒、寂寞萧条的日子里追怀既往繁华胜境,慨叹人世无常、世事如梦,是中国文人的‘心灵积习’之一。”[22]这是很具深度的观察,包含了古典文学的秘密:记忆,是理解士大夫文化的关键词。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也将“追忆”视为中西文学的根本差异,认为在西方文学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真实和意义上”,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23]藉此,他认为由于“惧怕湮没和消蚀的心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同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往事再现”的作用在于“用残存的碎片”使人“设法构想失去的整体”,“把现在同过去连结起来,把我们引向已经消逝的完整的情景”,从而使“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24]显然,这是与西方悲剧完全不同的故事逻辑:如果说回忆指向业已消失的美好,那么斗争则凭藉对历史的必然要求(历史真实)的拥有而以未来的胜利自居。对于陷溺于深永悲哀的曹雪芹而言,后者不太可能激发他的兴致,而代代相沿的回忆的诗学则更贴近他的心灵。在回忆的诗学中,文人们通过往事再现去捕捉逝去的岁月,通过对生命景象的艺术复活来抵挡美好事物的消失,“生命如急管繁弦,越是美好的越是短促无凭,文字不能把握时间,但它可以呈现出与时光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画面、场景、意境,唤起与过去同样的感受与情绪”。[25]此种回忆的诗学,可见之于唐诗宋词,见之于尺牍小品,也可见之于《红楼梦》这种以小说形式出现的文人作品。
作为长篇小说,《红楼梦》不可能追求唐诗那种“断片的美学”,专以生命瞬间的营造来结构全篇,而是势必要讲叙许多世俗生活故事。甚至这些故事还包含大大小小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不是整部小说的斗争逻辑,相反,它们还和“无事之事”(宴饮、节庆、雅集等)共同服从于回忆的诗学。此即“因空(悲)见色”中的“见色”,亦即往事再现。那么,《红楼梦》是怎样往事再现的呢?这包括两方面特征。一是整体“对照记”。与西方悲剧习于集中写主人公的人生挫败不同,《红楼梦》讲求盛衰俱集、兼呈悲欢:“红楼之作,乃雪芹巢幕侯门,目睹富贵浮云,邯郸一梦。始则繁华及盛,景艳三春,花鸟皆能解语;继则冷落园亭,魂归月夜,鬼魅亦且弄人。”[26]这是大结构层面上的悲欢相错,细结构上亦是如此。譬如,在“景艳三春”期间,香菱、秦可卿、秦钟、贾瑞、金钏等即已相继遭遇人生不幸。及至“冷落园亭”期间,仍有“寄闲情”、“宴海棠”、“沐天恩”、“庆生辰”等欢庆事象。所以,《红楼梦》的往事再现是整体呈现,需要以对照之法阅读。这一点,不少回目已经明确显示出来,如“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等等。二是“对照”中的不对称。《红楼梦》虽兼有悲、喜两面,但喜的数量大大胜过悲的一面,有关寿辰、节日、游园、宴聚、赏花、钓鱼、结社联诗、雅制灯谜乃至嬉戏打闹、争风吃醋之类的描写,构成了其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尤其是“于一切排场,及每人穿着插戴,无不极意摹写”。[27]由西方悲剧观之,衣饰、菜单、礼单和起居陈设之类等细节堆砌不但不必要,甚至不严肃。因此之故,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文人往往不理解这种喜胜于悲的不对称处理,认为“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28]把《红楼梦》硬扣为悲剧的学者则对此则视而不见。那么,对宴饮、嬉闹乃至衣饰、菜单等的铺排真的没有意义么?对此,张爱玲有非同凡响的见解:“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它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29]也就是说,这些细节描写本身即是“以言志痛”的一部分。不过,问题也随之而至:就凭这些排场、穿戴等等物质细节就能抵挡时间的疼痛?而色的另外一面(悲)和抵挡又有什么关系?要回答此问题,须明白《红楼梦》“见色”的色并不止于物质细节和不幸事件,而是另有重要部分——情。这就涉及《红楼梦》往事再现中更为复杂的结构关系:情色对照。
此即“由色生情、返情入色”。《红楼梦》中的色是广大世俗社会,其间美丑并存、清浊难分,那么,作家又如何使之成为可以抵抗内心苦痛的色呢?这通过两层互动完成。一是“由色生情”。小说首先在广大“色世界”里开辟出“情世界”。这个情世界又可分为“有情之天下”和“有情人”。大观园是为有情之天下,园内是青春与美的所在,“花儿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一帮美丽清俊的小儿女在其间结社吟诗、簪花斗草,偶杂些“儿女痴怨”、“捻酸吃醋”。其间姐妹们(包括宝玉)更皆有情人。其中,宝玉的“情不情”是最高的情的境界,“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即是说,对世间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皆以一腔痴情去体贴、去爱,而并不考虑对方是否爱己。甚至,其对象不仅是一切世人,还包括花草、万物。第三十五回有段议论,可见此意:“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这种与万物相体贴的“情世界”构成了《红楼梦》色的核心,也是其用以抵挡时间疼痛的最主要凭藉。二是“返情入色”。实则《红楼梦》用以安慰个我灵魂的不仅是“情世界”,也包括无趣的“色世界”(如菜单、礼单等物质细节)和不那么美好的“色世界”(如“风刀霜剑严相逼”之类人间不幸)。这一点,将大观园内外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世界(如余英时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划分)的悲剧论者难以认可。但“返情入色”在两个层面上完成了这种共同的整体性抵抗。一是有了大观园中那“古往今来厚地高天中的最崇高最圣洁最伟大的情”[30]的照耀,原本无甚趣味的宴饮、衣饰、礼单、起居陈设等物质细节也因为曾是情的物证或受情的拂抚而变得烨烨生辉,二是有了那厚地高天之情,那些或令人憎厌的无情之人、之事,也泛射出若干生命光辉,现出可哀悯的颜色。因此,王熙凤、贾政等都并非批判对象,相反,他们不可避免的毁灭同样让人深感悲悯。
此即《红楼梦》中情与色的“对照记”。情生于色,但又反过来赋予了它有情世界的生气和价值。经此互映,情、色最后融冶一体,美好事物与无趣甚至不美之物打成一片,共同构成了《红楼梦》生机勃勃的“往事”。这种往事再现构成了《红楼梦》回忆的诗学的故事策略,并以情、色互通整体抵抗着时间的疼痛。遗憾的是,悲剧论者往往强制把这整体往事分为肯定和否定两个部分,并认为作者有破旧立新、渴求理想新社会之意。
三、《红楼梦》不同于悲剧的叙述机制
悲剧论者如果未能在故事策略层面看到《红楼梦》的回忆的诗学,那么他们在叙述机制层面继续强制阐释就是必然的。譬如冯其庸对《红楼梦》的理解即是西方化的:“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毁灭”,“是新的生命由于它还未成熟,经不起狂风恶浪的摧折而毁灭,但它健壮的根系和茁壮的幼芽仍在适宜的土壤里保存着”,“只要有适当的气候,它会继续生长,最终长成大树”。[31]这种理解是以西方悲剧叙述机制为前置模式而形成的。其中,宝玉被理解为自由意志之代表者(“还未成熟”的“新的生命”),他的努力尽管被毁灭,但因其追求爱情的意志最终赢得了读者的怜悯和认同,那么仍可以说“(他)并没有受到击败他的命运的损害”,[32]甚至还包孕了自由终将实现的希望。不过,《红楼梦》真的意在通过自由的毁灭来反映“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33]并唤醒希望的幼芽吗?答案是否定的。它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归宿,暗含着“长夜无晨”[34]和“彻底的悲观主义”[35]的基本底色,它无意像西方悲剧那样挑战现实秩序或展示人的伟大崇高,相反,它希望通过繁复的往事再现臻于某种生命境界并最终平复内心痛苦。在此情形下,如果说西方悲剧组织斗争故事的叙述机制在于自由的成长(毁灭),那么《红楼梦》的机制则可用一个佛学概念来表述:破执。破执,意味着破除某种对自己和世界的执著。何谓执著,唯识宗称为“遍计所执性”,即指“以名言来表示种种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本无实体的存在,并执著为实有,而实际上,这是把无实体的执著为有实体的,这样所得的认识是不实在的、错误的”。[36]从佛学看,所谓“人的伟大崇高”或“自由意志”本身即是一种应该去掉的“执”。由此可见,《红楼梦》与西方悲剧几乎逆向而行。那么,《红楼梦》在其回忆的诗学中是怎样破执的呢?
这可从极有隐喻意味的“风月宝鉴”的故事讲起。在第十二回,贾瑞迷恋王熙凤,终致染疾不起。忽一日有跛足道人赠镜一枚,名曰“风月宝鉴”,并特嘱只可照背面而不可照正面。贾瑞照背面,则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忍不住好奇又照正面,却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于是荡悠悠进镜与凤姐交欢。如此恍惚相会,终于死去。贾瑞祖父贾代儒愤而烧镜,谁知镜内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这段故事不可等同于市井风月。《红楼梦》一度以《风月宝鉴》之名流传,亦可见此“妖镜”(贾代儒语)的隐含意味。对此,脂砚斋在“千万不可照正面”一句旁边评道:“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37]从看镜跳跃到看书,脂砚斋是在提醒读者:“风月宝鉴”隐喻着人生与世界的真相。那么,是怎样的真相呢?刘相雨认为:“风月宝鉴的正面是勾引人的凤姐,反面是骼髅;正面是假,反面是真;正面是现象,反面是本质”,因此,风月宝鉴“是一面抽象化的、蕴含着丰富哲理意味的镜子,涵盖了正与反,真与假,现象与本质诸方面的对立统一。”[38]这一分析颇有道理,但对立统一仍出自西方认识论。脂砚斋本意则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如一面镜子,从正面看是青春繁华从反面看是虚无荒凉,正面是“好”反面则为“了”;但繁华与荒凉、好与了,不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世界”,而是“一个世界”的两个面向。是好是了、是有是无、是真是假其实本无区别。如果观察者认为它们区别很大或竟是两个世界,那只表明观察者无力看破所谓“温柔富贵乡”。只能从繁华看见繁华,便是执迷。而能从繁华中嗅出荒凉气息,从有中看见无,并意识到有即是无、欢即是悲,那便达到了破执层次。脂砚斋所谓“会看”即指不执迷于正面(色、美、繁华等)且能把握到它与反面(空、骼楼、荒凉等)互成镜像。倘如此,个人对于生命的认识就会大为提升,就可能达到完满的生命之境。相反,一个人倘若不明白有、无本为一体,好、了原即一物,而一定要把这“一个世界”强分为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并为追求理想而不断和现实斗争的话,那无疑是最糟糕的“执”了。这种执迷,毋宁是西方悲剧作为自由意志故事的本质所在,而《红楼梦》所“破”者也正在此“执”。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悲剧的终点正是《红楼梦》的起点。因此,破执正是“风月宝鉴”的隐喻,亦是《红楼梦》叙述机制之所在。悲剧论者以为《红楼梦》是在一步步在展示宝黛与封建卫道者的斗争、呈现自由的成长,其实不然。单纯就小说线索而论,当然有此一支,但在诸多线索之下,曹雪芹真正用意却在于一步步地破执,一步步地将读者带入有无一体、好了互见的通彻万物的生命境界中去。破除人心之于“好”的执迷,使之从“好”中看到“了”,从“风月宝鉴”的正面看到反面,这才是《红楼梦》的深层机制。
那么,《红楼梦》是如何落实这一机制的呢?可分两层述之。一是僧道设置。“风月宝鉴”系由道士携来,实则僧、道在作品中具有结构性功能。小说中每逢关键节点,僧道便会适时出现,恰如清人姚燮所言:“英莲方在抱,僧道欲度其出家;黛玉三岁,亦欲化之出家,且言外亲不见,方可平安了世;又引宝玉入幻境;又为宝钗作冷香丸方,并与以金锁;又于贾瑞病时,授以风月宝鉴;又于宝玉闹五鬼时,入府祝玉;又于尤三姐死后,度湘莲出家;……一部之书,实一僧一道始终之。”[39]在此,僧道的出现及言论,实在不断提醒读者所谓大观园内外的红尘世界(兼含色、情)与太虚幻境同为一个世界,读者“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遗憾的是,对此功能作用现代知识分子多是不甚了了,反以为是荒诞不经。二是宝玉角色设置。宝玉同样有“度化”读者之用。对此,鲁迅称:“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40]又说:“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41]这是指宝玉动辄谈死,动辄要“化灰化烟”,几乎时刻在提醒读者所谓“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第十三回)通过宝玉与僧道,《红楼梦》最终使人从世界的正面看到它的反面,从“好”中看到“了”,并最终以“了”的平淡与从容来重新面对“好”的现实。有了如此识见,人们就会进入云淡风轻的生命境界:既不会因富贵繁华的不能得到而焦虑不安,亦不会因青春、爱情等美好事物的存逝而大喜大悲。一个人如果到了这等境界,大约可谓破执了。而这正是佛学中的“色即是空”的道理:“色即是空,不待色灭然后为空”(僧肇:《维摩经注》),“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鸠摩罗什译:《维摩经》)。显然,埋藏在《红楼梦》深处的是中国传统的有关生命的内在超越机制,与自由意志的故事大不相干。
四、余论
以上破执机制,兼之前述回忆的诗学的故事策略、以言志痛的叙事动因,共同构成了《红楼梦》与西方悲剧的差异的主要方面。此外,在审美效果上二者也存在消极与积极之别。西方悲剧尽管多述不幸之人生,但其效果则是乐观主义的壮伟,《红楼梦》尽管有叙“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事,但并不激发读者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勃勃的自由意志,而是让人“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42]然而在一个不再那么需要文学承担家国正义的年代,我们也不必以“消极”二字将《红楼梦》所揭橥的中国人灵魂深处幽微的痛苦和深永的美轻易打发。就此而论,《红楼梦》比一般古典文学的“沉静”更消极,也更深刻。沉静是古典诗歌往事再现的美学目标,“自色悟空”显示《红楼梦》也希望平抚时间疼痛之后走向类似虚静之美。但《红楼梦》在此途中却一不小心掉入了某种“虚无的深渊”,[43]未臻虚静反而带来更广大的痛苦。对此,夏志清认为:“曹雪芹表面上写了一个道教的或禅的喜剧,表现了人类在绝望和痛苦中的无希望的纷扰以及至少一个个人的解脱。但只是表面的,因为读者只能感觉到这小说中所描写的痛苦的真实比道家智慧的真实更深地激荡着他的存在。”[44]这缘于并非所有往事再现皆能使人物我两忘继而心灵平静,因为“色即是空”,由艺术再现出来的繁华更如梦幻泡影,它未必能让人从幻像中得到安慰。对于“一往有深情”者,反而是再度提醒那过去已永不再来,是将之一次次地从平静边缘拖入痛苦深渊。如果说小说是“存在的勘探者”(昆德拉语),那么这深渊中深永的灵魂之痛,就显然不是“消极”二字所能概括,更非西方悲剧模式能够完成。由此可见,《红楼梦》在效果、机制、策略、动因等方面皆与西方悲剧相去颇远。悲剧论者仅据爱情失败就把《红楼梦》纳入西方自由意志的故事,不免太过强制阐释,值得深刻反思。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发生着强制阐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等西方概念,更是必要的系统反思对象。未来古代文学研究新的问题空间的打开,对中国人精神的“同情之了解”,不能不说与这些概念的祛魅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张江:《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
[2]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3]丁玲:《作家与大众——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丁玲文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4]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第9期。
[5][44]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7、135页。
[6] [俄]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页。
[8]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0页。
[1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3页。
[11] [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8-139页。
[12][32] [德]谢林:《艺术哲学》,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64、64页。
[13]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
[1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4页。
[15] [清]俞樾:《小浮梅闲话》,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695页。
[16]李希凡:《红楼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88页。
[17][35]高小康:《〈桃花扇〉与中国古典悲剧的演变》,《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18][34][4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07、209、201页。
[19][21]史任远:《贾宝玉的出家·序》,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7、1120页。
[20]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351-352页。
[22][25]单世联:《记忆的力量——〈红楼梦〉意义述论》,《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辑。
[23][24] [美]斯蒂芬·欧文:《追忆》,郑学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3页。
[26]境遍佛声:《读红楼札记》,《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第5页。
[27]周春:《红楼梦约评》,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3页。
[28]陈独秀:《三答钱玄同》,《新青年》1917年第8卷第1号。
[29]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余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0]周汝昌:《〈红楼梦〉与“情文化”》,《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
[31][33]冯其庸:《读〈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5辑。
[36]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0页。
[37]俞平伯编:《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00页。
[38]刘相雨:《谈〈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4辑。
[39] [清]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67页。
[4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
[42]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43]王安忆:《人生戏剧的鉴赏者》,《文汇报》1995年9月21日。
责任编辑:王法敏
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作者简介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I02;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