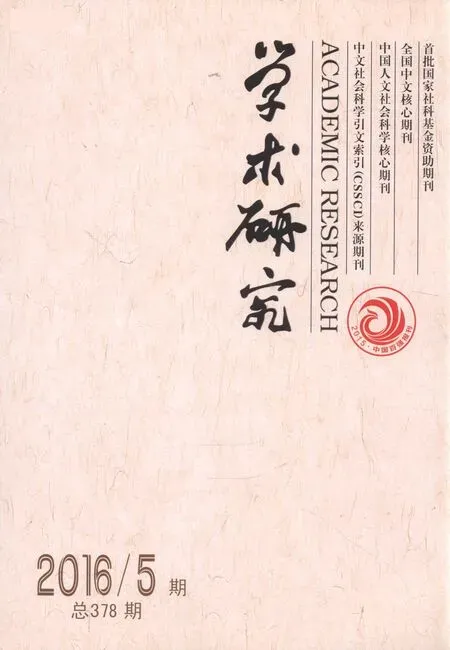场外征用的有限合法性*
2016-02-26蓝国桥
蓝国桥
场外征用的有限合法性*
蓝国桥
[摘要]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划界,是审视场外征用合法与否的关键。纯文学具有无功利性、审美艺术性、形象情感性,它重在建构文学的内宇宙。批评阐释自律性的纯文学,需遵循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反思路线,场外征用是对该路线的严重背离,容易导致强制阐释。征用场外的理论,根源于文论创造力的衰竭、文学感受力的下降,以及非文论欲望的膨胀。场外征用的必然后果,是文论走上异化的歧途。杂文学带有功利性、依附性、综合性,它更在意文学外宇宙的营建。杂糅着哲学、道德、政治、宗教等文化事项,使得纯文学杂而不纯,而杂文学不纯而杂,杂文学必以杂糅性面相展现自身。立足于具体的杂文本,相应地征用哲学、道德、宗教、政治等文化理论,能有效揭示文本意蕴。场外征用是杂文学批评阐释的需要。
[关键词]场外征用强制阐释纯文学杂文学合法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王国维与康德美学中国化研究”(12CZW018)的阶段性成果。
场外征用是批评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场外征用到底合不合法,关键不在于所征用的场外理论是什么,而在于场内的文学是什么——是纯文学还是杂文学。假如我们阐释的是纯文学,场外征用将容易导致强制阐释,而假如我们阐释的是杂文学,场外征用则可以避开强制阐释。前者是非法的,后者是合法的。可见两种文学观的边界划定,是审视场外征用合法与否的关键所在,由此才能看清楚场外征用有限合法性的本来面目。
一、两种文学观的中西生成反思
纯文学是自律性的文学,它所建构起来的是自足的文学内宇宙。侧重内宇宙营造的纯文学,整体上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它具有无功利性。文学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不是为了实现自身之外的目的,比如政治的、道德的、商品的等等,且我们不以功利的态度面对它,而是以无利害的意愿对待它,文学此时即表现出无功利性。其二是它展现出审美艺术性。审美是艺术书写的主要内容,艺术的重要规定便是审美,纯文学的世界中,审美与艺术的边界模糊。审美艺术性所执意凸显的,是对现实的疏离与超越,它因而强调艺术技巧的使用,语言修辞手法的运用,张扬大胆的想象虚构,充满个性的自由书写,汪洋恣肆的情感宣泄,如此等等。其三是它表现出形象情感性。形象的灵动飞扬总充满着不尽的趣味,无论是创造还是欣赏,都无不如此,情感是滋养形象的源头活水,形象是承载情感的媒介,纯文学世界中的形象与情感,始终水乳交融。情感与形象带有明显的个别性,即形象都是单个具体的,而情感多与特定的个人联系起来,不过纯文学中的个别性的情感、形象,总指向某种普遍性的意蕴、意义。纯文学的基本保障是无功利性,它的实现路径是审美艺术性,情感形象性是它的内部显现,三者之间由表及里、逐层推进,建构起光彩迷人的纯文学海市蜃楼。
纯粹文学的海市蜃楼,尽管显得虚无缥缈,然而它的观念却是历史的建构与生成,与中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纯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诉求,就表现得异常迫切强劲。“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面对社会文化的败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深刻地意识到观念的变革方是挽救败局的关键。梁启超热衷并自觉贯彻的趣味教育,王国维血泪捍卫的纯粹精神空间,蔡元培大力提倡并实施的美育,陈寅恪与吴宓对实用国民性的批判,朱光潜、宗白华等理论家长期的美学颖思,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美学的兴起,均为纯文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时期的创造社、沈从文和冰心,以及新时期以来坚持高雅艺术创作的张炜、张承志等,都是纯文学观的自觉践行者。中国纯文学的生成,除了受根植久远的庄禅文化传统影响之外,更主要地还是与心态开放的智识群体自觉融摄西方文化有着内在联系。
西方自近现代以来,无论是具体的创作实践,还是抽象的理论思辨,价值的指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纯文学场。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活动,整体上表现出向内转的态势,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等各种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它们书写得更多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体验性的内在世界,这恰好为纯文学的观念生成,夯实地基、构建平台。西方近现代以来抽象的理论反思,一路凯歌,为纯文学观念生成起到强有力的辩护作用。它们先对活动的主体提出要求,指出活动的主体于心灵上,应与欲望、功利绝缘,如此无欲望、无功利的主体,面对的不是对象的内容,而只是对象的形式、形象,主体与对象所构成的只是纯粹的审美关系。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布洛、克罗齐、克莱夫·贝尔、罗杰·佛莱、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众多的理论个体、流派,无疑都是纯文学观重要的理论辩护者。理论反思与创作实践都共同指证,纯文学观显然已在西方形成、发展。
中西纯文学观念的建构除了带有空间性、结构性特点之外,时间性、历史性的特质同样明显。它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而可在社会历史中寻找到它生成的原因。韦伯指出,西方自近现代以来,理性一再张扬,祛魅不断推进,社会出现了不可避免的世俗化。[1]世俗社会中的恶四处蔓延,是催生纯文学观的动因。中国近现代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遭受的社会文化危机同样前所未见。摆脱社会文化危机的强烈愿景,是中国纯文学观建构的动力。纯文学既然也向社会历史敞开自身,因而纯文学难以将纯粹进行到底。不纯粹的文学便是杂文学。
杂文学与纯文学相比,是他律性的文学,它所经营的已不再是文学的内宇宙,而是文学的外宇宙。杂文学整体上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功用性。判定文学的功用性有无,标准是文学所处的关系,以及主体面对文学的态度。当我们内置功用的态度,迫使文学沦为手段,而实现它之外的目的,且我们以实用的态度面对它,文学必表现出功用性。其二是依附性。依附性是指文学存在的合法性紧紧依附它之外的因素。文学充当实现目的的手段,表明文学业已沦为工具,目的的实现重要,文学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已甘愿退居次要地位,文学并且只有作为工具,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恰是工具性的担当,使文学丧失自身的独立品格。其三是综合性。杂文学之所以显得杂,乃是由于它是多种文化事项的杂糅,它不能以被剥离为纯文学的样式而只能以杂糅的面貌展现自己。文学所需实现的目的多样,而它所要担当的工具不一,使它内置多种的功能,功能的多样性使它具有综合性。杂文学质的规定便是功用性,而依附性则是它的站立姿态,综合性是它的整体面貌,三者之间由低到高、逐层递升,共同建构起杂文学五彩斑斓的世界。
杂文学五彩斑斓杂而不纯,它是文学存在的常态。我们如此来界定常态的杂文学,乃出于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考量。杂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起来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两者的关系之所以紧密,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对生活的体验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是指向生活的整体而不是局部。生活体验的全面性与生活反映的整体性,是导致杂文学斑驳面相生成的逻辑原因。与逻辑略显坚硬不同,历史的演进则多半柔软。杂文学柔软的历史演进,突出地表现为时间跨度长,而在纯文学兴起的语境中,杂文学仍然表现出异常旺盛的生命力。历史时间跨越的漫长,使得杂文学的数量,显得相当庞大。数量巨大的杂文学,展现的方式更是多样,反观古代纯文学如《诗经》、《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则多表现得不够纯粹,它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历史、哲学等;而其他如历史、哲学等诸多的文化样式,同样残留着文学的痕迹。中西历史上涌现的杂文学,呈现出时间跨度长、存在数量巨大、展现方式多样的特点。
二、纯文学与场外征用的非法性
纯文学可分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道”(体)的形态,另一种是“器”(用)的形态。“道”的形态是理论的建构,结果是纯文学观念于中西近现代的形成。“器”的形态是理论建构的依据,它体现于特定的活动与文本当中,近现代以来涌现出的具体纯文学作品,便是“器”的形态展现。或者说存在着两种纯文学,一种是抽象、观念、理论上的纯文学,另一种是具体、现实、现象上的纯文学。因此纯文学的批评阐释,也存在着两种出发点,一种是以抽象的理论、观念、本体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具体、现实、现象为出发点。批评阐释的起点决定路径,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便可延伸出两种不同的批评阐释路径,一种是理论、观念、抽象的路径,另一种则是具体、现实、现象的路径。[2]定于何种出发点,选择何种路径,直接关系到批评阐释的有效性。依此会引申出三个问题。其一是选定哪种出发点与路径,才使得批评阐释有效、理论建构恰当。其二是批评阐释纯文学,征用场外理论的原由何在,非法性的原因何是。其三是宣布场外征用为非法,非法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恰当、合理的选择,是第二种出发点与路径。批评阐释侧重于“点”、“线”,理论建构与“面”相关,“具体”是两者的共性。批评阐释需在具体的点上追问意义,它可以是一首诗歌、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部戏剧作品,可以是某种纯文学的现象,还可以是瞬息万变的创作、欣赏活动。张江说“没有抽象的文学,只有具体的文本”,[3]照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抽象的纯文学,只有具体的文本”,以及具体的活动。“点”上文本、活动显得具体,意义的追问领会却不能止步于此,它需向抽象区域挺进,意义的阐释使得具体迈向抽象,彼此浑然不分,“线”的特点恰好正体现于具体到抽象的上升之路中。理论的建构是更高的抽象,它需要多“点”的支撑,多“线”的交织,它的抽象在“点”与“线”上来回滑动,最终会形成更大的“面”。理论建构“面”的稳固性,与“点”、“线”的多与寡,发生着内在的联系。张江说批评阐释,首先应着手分析单部作品,接着汇聚众多作品,进行详实的统计,最后归纳出理论观点,如此理论的地基才会牢固。因而理论观点的概括力、阐释力,与作品分析的深入性、统计的详实性,构成正比例关系。归纳、概括所走过的,是由具体爬升到抽象的活动,如此的活动便是反思活动。反思活动,是批评阐释与理论建构的不二选择。
批评阐释与理论建构,对象与主体均需在场,反思活动于其中的重要性,可从在场的对象与主体体现出来。反思活动以鲜活的体验为根基,带有相当明显的瞬间性、流动性,是阐释意义获得、领会的可靠路径。反思活动在此首先需穿越的,是生动的纯文学场,以及场内具体的作品,确切地说来,是具体作品中言语意象的森林,以及单个言语意象的树木,这些都相对具体;反思活动的纵深推进,还要逐一反复追问的,是单个的言语意象、单部作品、多部作品的意义,单种意义与意义群的领会,则多半显得抽象。具体(个别)与抽象(一般)的无缝对接,是反思活动的效果。于个别、具体之“器”处,透显一般、抽象之“道”,是文学批评意义衍生的必经路径,文学批评的独特性,恰可体现于“道”与“器”的不分离上。反思对象舒展的特征,受制于主体的本质力量。纯文学场意义的激活领会,由于没有功利的缠绕,主体可全身心融入其中,主体整体机能的付出是必然的。反思活动是意义诞生的源泉,而纯文学的批评阐释、理论建构,均奠基于意义的领会、激活之上,因而它是批评阐释、理论建构的支点。
反思活动支点功能的凸显,尚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它可强化理论的阐释力度。理论观点的归纳概括、提炼生成,经历过数次的反思判断,业已汇聚着众多的个别性、具体性信息,因而当再一次面对具体文学现象时,一方面理论观点可以最低限度地发挥解释功能,另一方面由于现象与理论的一再吻合,理论观点的合理性随之得以增强,理论的生命力也随之得以延续。越是使原先的理论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强化中理论的阐释力度越是得到进一步提高。其二,它是理论的经典化理路。经典的文学理论著述,它的支点都会是反思活动,古今中外几乎无一例外。不以具体文学反思为支点,反思到达不了相应的深度,几乎不可能成为经典。由其一到其二建立起的是因果性联系,彼此关联的紧密性可进而标明反思活动作为支点选择的有效性。
第二种批评阐释、理论建构的模式,它的最后归结点是反思活动,走的是从具体到抽象上升之路。与此相反的情形是,第一种模式的立足点是规定活动,走的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下降之路。历经反思活动,批评阐释、理论建构具有自足性,它只需激活反思者的潜能即可,而第一种模式因支点是抽象的理论,它却需仰仗于其他的理论知识。批评阐释、理论建构疏于发挥反思者自身的力量,不从具体鲜活的文学场出发,而只盲信于外在的力量,依靠外在的力量翩翩起舞,有意在放逐文学场,使之荒芜化成为一块飞地,如此的情形便是场外征用。
规定活动所走的下降之路,迫使批评阐释、理论建构,不得不征用众多的场外理论,致使大量的场外理论涌入场内,制造了理论的众声喧嚣。场外征用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原因之一是理论创造力的缺失。此处的理论指的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创造力的缺失,是指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弱化,进而丧失理论自身的创造活力。理论的主体性弱化,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理论的文学身份模糊,二是指理论的民族身份不清,两者都矮化了理论。批评阐释、理论建构不考虑文学性,它征用其他的非文学理论,容易变得胆大妄为。20世纪西方的文论,便是胆大妄为的典范。它导致的严重后果便是,非文学的理论出现了严重的征用过剩,而文学的理论却意外缺席。文论的民族身份不清,是指民族自主型的文论缺乏,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便是如此。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的民族身份一直模糊不清,文论的核心观念、众多文论观点,多或被迫、或自愿地从西方征用。民族文论创造力的衰弱,是众多西方入侵的原因所在,我们有很多理论,却都不属于本民族的。可见主体性弱化、创造力枯竭,是征用诸多理论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理论欲望的膨胀。理论在此是指非文学理论,非文学理论欲望的膨胀,是指以各种各样抽象的理论为起点,具体的文学材料被强硬拉扯进来,理论运行的机器当中,文学现象只是理论的证明材料。理论征用在先,文本阐释跟进在后,热衷于理论的知识化表达,如此的批评阐释架空了文本,是批评阐释、理论建构的异化。20世纪的西方文论,知识化演绎热情高涨,文论异化的命运在劫难逃。原因之三是文学感受力的钝化。创造力的缺失、理论欲望的膨胀,带来的后果是,具体文本的细读、鲜活现象的反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文学感受力的钝化,使批评阐释、理论建构进入恶性循环,感受力越是被钝化,征用其他理论就越轻巧,而越是征用其他理论,感受力越是被钝化。
第一种模式的出发点,是产生知识的规定活动,依此纯文学的批评阐释、理论建构,势必导致场外征用,致使批评阐释、理论建构,背离、疏远自身的本质,走上异化的迷途。理论的异化,首先表现为理论与文学的对立。理论不是源于对具体文学场的反思,而是抽象横移自其他学科,如哲学、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4]这些学科、理论不包含具体的纯文学现象。不包含文学自然不能阐释文学,非要征用它们来阐释文学,只能扭曲文学以符合理论阐释的要求,此时与其说阐释的是文学,还不如说阐释的是理论自身,是理论本身在自说自话。如此的理论越是繁荣发展,越是与文学毫无瓜葛,越是走上与文学背离的道路。其次,理论的异化,还表现为理论与过程的疏离。文学创作的过程,是由具体上升到抽象,是为具体而找抽象。与创作过程相适应,批评阐释、理论建构的合理道路,走的也是由具体到抽象的上升道路。而场外征用则是从抽象到具体,以征用的理论为起点,迫使文学符合理论,它显然与过程相背离。最后,理论的异化,表现为理论与理论的对立。场外征用的大量理论,未能令人信服地展开批评阐释,它们的产生远离合理的过程,面对具体文本同样无能为力。理论的场外征用很难做到彻底,它容易瓦解理论,把理论引上末路,导致理论把自己从理论那里放逐出去。
三、杂文学与场外征用的合法性
纯文学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是强制阐释论置身的特定语境。受如此语境的深刻影响,强制阐释论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流露出部分的肯定态度。强制阐释论眼中的文学,因而“是人类思想、情感、心理的曲折表达”,它“强调人的主观创造能力”,“是作家独立的主观精神活动”,主观性、情感性意味甚浓。[5]语境、态度、言说三者可表明,强制阐释论更多坚持的是纯文学观。然而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未能看到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存在若干偏颇实在所难免。现实生活的场景无所不包,文学场一旦向现实生活倾斜,它必难以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如果说面对纯文学现象,场外征用大量的非文学理论,以展开批评阐释、理论建构,是种非法的行为的话,那么对杂文学的批评阐释、理论建构,情形会与此不同。杂文学的场外理论,既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征用不问出身的场外理论带有合法性的原因,是因为场外征用的理论事项,与场内的杂文学面貌相吻合,能够揭示、阐释潜藏于场内杂文学的意蕴。杂文学的“杂”与征用理论的“杂”,以杂文本为起点,两相辉映相得益彰,彼此处于相互印证的关系中。合法性问题审视的关键有二,其一是杂文学中“杂”的面相如何显现,其二是理论与杂文学怎样对应。
近现代以前的中西方,文学大多不太纯粹,而是参杂各种文化元素,文学因而是以杂糅的面貌存在。划归文学名义下的东西,包括了多种的文化事项。伊格尔顿指出,“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包括莎士比亚,韦伯斯通,马维尔和弥尔顿;但是它也延伸到培根的论文,邓恩的布道词,班扬的精神自传以及托马斯·布朗所写的无论叫做什么的东西。在必要时,人们甚至可能用文学包括霍布斯的《利维坦》或克拉仁登的《反叛的历史》”,“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与法国文学基本相似,两国的文学包括今天通行的文学、论文、布道词、精神自传、历史、诗学、哲学、书信等等,凡与语言相关的都可囊括在里面。[6]西方17世纪如此,17世纪之前更如此。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文学,与文化并无二致,近人章太炎一语道破,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7]孔子最早使用“文学”一词,所指是文章、博学,是孔门四科之一,说“文学,子由,子夏”,大概子由与子夏于文章、博学方面,表现尤其突出。近现代前后的中西方,以杂糅面相存在的文学,有两种展现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纯文学显得杂而不纯。它有两种表现方式。其一是纯文学观被建构的历史语境中,杂文学的观念演绎、实践依然不消歇停息。观念上康德虽然留恋纯粹美,却又认定美是道德的象征,他于是把美的至高理想,最后是推给了依存美;马克思倡导历史唯物论,坚持文艺社会学,是杂文学观最坚定的维护者。受西学影响的王国维、朱光潜等,对纯文学无不憧憬向往,不过他们对人格依附的杂文学,仍有着很高的评价。实践上近现代以来的中西方,都在强调文学应介入现实,现实指向的作品不断涌现,杂文学的生命力旺盛依旧。其二是以建构的纯文学观为标准,衡量过去的文学作品,当中被判定为纯文学的作品,仍然显得不够纯粹。历史越是久远的作品,情形越是如此。西方文学的开端是《荷马史诗》,《荷马史诗》除了是围绕情感展开的诗,还是久远历史的生动叙述,更是哲学义理的形象阐发。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首先它是诗歌是文学不假,刘经庵因而将之列入纯文学的行列;[8]它还是“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历史,包含《诗经》在内的“六经皆史”,《诗经》中“淫奔之诗”,实是礼、社会制度的体现等,都透显出历史的信息;[9]它更是蕴含着高深的哲学义理,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将《诗经》中的两首诗,一首是“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另一首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视为儒家智慧的根源,反复申引。[10]《荷马史诗》与《诗经》在中西方的历史长河中,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此足以表明,纯文学有杂而不纯的一面。
第二种形态是文学的文化依附性。与第一种形态不同的是,文本存在的整体不能冠之文学的名称,而是另外的文化样式。别的文化样式承载着文学性,或说文学的存在依附于别的文化样式,如分别依附于历史、哲学、宗教、诗学、道德学、政治学等。文学可依附于历史而存在,司马迁《史记》中的文学即依附于历史,历史的描写中有文学性。历史小说既是历史也是小说,文学与历史的边界模糊。哲学表达中不乏文学,中西方无不如此,《论语》、《孟子》、《庄子》是哲学与文学兼具,“柏拉图之《问答篇》、鲁克来谑斯(卢克莱修)之《物性赋》,皆具哲学、文学二者之资格”,哲学与文学的联系水乳交融。[11]文学性还可体现于基督教的《圣经》中。中国诗论中也不乏文学性。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体现着文学的道德诉求,革命文学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文学性弥散于不同的文化样式中。
纯文学的杂而不纯,当中文史哲未分的憧憬,当是不难辨别。文学性散布于文化当中,杂文学的文化依附性,同样昭然若揭。无论是纯文学的杂而不纯,还是杂文学的不纯而杂,两者均可指明文学的杂糅面相。杂文学沾染、整合着众多的文化质素,有历史、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等,对它的批评阐释、理论反思,依然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的行进线路,而行进中征用非文学的道德、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等理论,就不能被简单地宣布为非法。杂文学的场内与理论的场外,处于某种吻合的状态,正是如此的状态,构成理论场外征用合法性的保障。它具体可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杂文学的批评阐释,征用哲学的理论,哲学理论若与文学吻合,理论的征用不能算非法。杂文学中蕴含着哲学义理,对如此特质鲜明的杂文学,展开批评阐释、理论说明,可启用相应的哲学理论。与文本相应的哲学理论,能够揭示潜藏其间的意蕴,批评阐释的展开便是有效的,相应哲学理论的征用,即是合法的举措。相应性的找寻,是合法性衡定的要害。哲学义理的正当性、深刻性,源于哲人对宇宙、人生的反思。作家创作的起点,是他对宇宙、人生的鲜活反思,反思的意义同样可融入到作品中。哲学义理融入杂文学,有三种融入的路径。一是思想家进行文学创作,容易融入哲学思想。西方思想家如席勒、萨特,中国宋明思想家周敦颐、朱熹、王阳明,以及近人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都能在文学创作中融入哲思。二是思想的表达是目的,而文学性处于依附的地位。西方柏拉图的《问答篇》、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与中国的《孟子》、《庄子》等,都能使文学性嵌入思想的表达中。三是形而上学的韵味渗透于作品当中。佛理参悟的《题西林寺壁》,悲凉气息弥漫的《红楼梦》等,即是如此的作品。显然,三种情况,都可使文学与哲学义理有机融合起来。作品中的哲学义理挥之不去,对作品的批评阐释,仰仗于相应的哲学思想,如此的要求不算过分。与哲理融入路径相对应,哲理征用也有三种表现情形。一是阐释思想家的作品,征用他已消融的哲学,有益于作品的解读。萨特的文学作品如《恶心》、《群蝇》、《密室》等,是他存在主义思想的体现,征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可帮助我们有效、合理地解读作品;王国维的诗词创作,受叔本华、康德的影响颇深,欲使批评顺利展开,征用康德、叔本华两人的哲学,并非多余。二是寓言性意味浓厚的作品,征用合适的哲学思想,绝非可有可无。有效推进《庄子》的文学性批评,重要的前提是深入领会庄子的思想,然后征用庄子的思想,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批评卡夫卡的作品如《变形记》,可与异化哲学联系起来。三是具备相应的哲学思想,有助于领会作品的形而上意味。《题西林寺壁》暗藏佛理,征用佛理实属恰当。《红楼梦》悲凉之雾气迷漫,征用悲剧理论,与小说的意味正相吻合。作品的哲理融入保证哲学征用的合法性。作品意蕴的有效揭示,流露出对哲学征用的迫切需要。当然,征用哲学理论的目的,不是演绎理论的正确性,而是揭示作品意蕴的深刻性。
除了蕴含哲理,作品可含有德性。含有德性的作品,自然不够纯粹,那是杂文学。阐释蕴含德性的作品,征用道德的学说,可有助于揭示作品内蕴。征用合法性的契机,是杂文学的场内与场外,于道德上的融会贯通,是场内对场外的敞开,而不是相反,即是说对如此作品的阐释,不是证明道德学说的有效性,而是重在挖掘作品的道德意蕴。儒家重道德,它是中国文化的主线。儒家伦理浸染过的作品,必是杂文学,累积的数量不少。儒家伦理在唐向文学转进,体现于杜甫的诗与韩愈的文,阐释他们的作品,不征用儒家学说,阐释将不得要领。同理,阐释含有宗教、政治指向的作品,征用相关的宗教、政治理论也不能算非法,前提是以具体文本为立足点。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斯·韦伯:《伦理之业》,王容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2]王坤、喻言:《符号的本体意义与文论扩容》,《学术研究》2015年第9期。
[3][4][5]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6]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7]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47页。
[8]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15页。
[9]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10]牟宗三:《康德第三批判讲演录》,卢雪昆整理,杨祖汉校正,《鹅湖月刊》1991年。
[11]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作者简介蓝国桥,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广东湛江,524048)。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