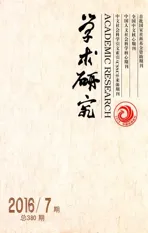论20世纪40年代美华文学的发展及转变*
2016-02-26李亚萍
李亚萍
论20世纪40年代美华文学的发展及转变*
李亚萍
20世纪40年代是美华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由于资料匮乏导致学界对这一阶段美华文学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华侨文阵》、《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新苗》等文艺刊物都是40年代重要的美华文学原发文献,对之梳理总结后发现,抗战后美华文学获得蓬勃发展是由于新型创作者的加入、各类文艺刊物的创办及美华文艺界对华侨青年习作的鼓励等。此期美华文学的中国意识较为突出,也表现出浓厚的本土化意识,建构美国华侨文艺特质的理论诉求。他们强调写作者深入华人社区以写实笔法展现华人的精神面貌,尝试确立美华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特内涵。
美国华侨文学华侨文艺论争本土化
20世纪40年代是美华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如麦礼谦所言 “美国华侨文艺运动的兴起正好显示华人的意识已经从华侨到华人的过程中再跨进了一步”。[1]而此时美华文学也恰处在探讨如何形塑美国华侨文艺风貌的阶段,该问题的探讨与70年代初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陈耀光、徐宗雄等所探寻的华美感性极为类似,都尝试建构美华文学的合法性基础。笔者尝试在原发文献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美华文学的发展做总体性评价,涉及的原发文献有 《华侨文阵》(1941.12—1945.3)、《绿洲》(1945.5—1947.12)、《新苗》(1947.3—1948.3)、《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 (1940.7—1950.12)。
一、40年代美华文学资料整理及研究综述
40年代美华文学的发展概况在一些史论性著述中被论及。麦礼谦长期从事美国华人历史研究,是较早关注此期文艺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研究者。他在专著 《从华侨到华人》中辟一节论及抗战后美国华侨青年文艺运动及文学创作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信息,如 《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对美国华侨文学的培育作用,以及对 《绿洲》《轻骑》《新苗》等文艺刊物的简介等。①麦礼谦先生去世后,他所收集美国华人历史资料均捐赠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中包括40年代 《新苗》。旧金山州立大学谭雅伦曾撰文 《四十年代的华埠文学运动》,[2]论述 《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对1940年代美华文学的贡献。国内学者对这一阶段关注较晚,论述主要借鉴和参考海外的成果。黄万华 《20世纪美华文学的历史轮廓》一文认为美华文学的第一次强劲势头是在二战期间随着华侨抗日文艺兴起而出现的。[3]刘俊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中执笔撰写 “北美华文文学”一章,也简短论及二战后的美国华侨文艺运动。[4]两位基本参照麦礼谦的论述。赵文书在专著 《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尝试梳理美华文学的发展脉络,[5]论及40年代美华文学也主要以 《美亚》(Amerasia)杂志的论文为依据。[6]
文史领域的研究者对40年代美华文学的发展表现出较大兴趣,他们均意识到此期在美华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正如黄万华所言,“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美华文学论述中,都忽略了这一重要环节,而使得对美华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描述变得残损不全”。[7]40年代美华文学亲历者作家黄文湘同样认为此段历史不可忽视,它 “是美国华人文学发展史的一页,如果撇开它不提,是割断了历史”。[8]然而,这段历史因冷战到来而遭封存,当时从事美华文艺运动的前辈们亦四处流散,无从访问,文献的搜集整理尤为困难。
麦礼谦、谭雅伦等研究者收集了部分原始资料,如全套 《新苗》杂志由麦礼谦收集并交由谭雅伦、黄秀玲等进行研究。1982年谭雅伦将一篇评述文章 《华侨文艺十年》①温泉:《华侨文艺十年》,新苗文艺丛书第二期 《突围》,1949年,第44页。温泉是40年代美华作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识,40年代初在 《华侨文阵》率先提出 “华侨文艺”的口号,引起美华文艺界激烈讨论。翻译成英文刊载在 《美亚》杂志,作者温泉以总括评述笔法回顾1939年至40年代末美华文艺发展的概况,其中提及较多文艺刊物及团体,并评选出15部优秀小说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最佳成果展示。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篇全面介绍40年代美华文艺发展的文章,虽局限于面上的铺陈,并未深入各点进行细致探究。麦礼谦在其专著对40年代美华文学概况的论述应是参照了该文的,本文所论及的文献资料也得益于该文的指引。
谭雅伦在挖掘、整理乃至推广40年代美华文学的工作中做了诸多努力。除翻译温泉的 《华侨文艺十年》之外,也十分强调 《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对美华文学的推动作用。1988年在纽约历史华埠研究社的社刊 《布告板》第7期选发了 《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上老梅的五篇短文,其他作者的六首诗和六篇短篇小说,均以中英文对照刊登。这是较早对40年代美华文学原始资料的发布和推广。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文学研究专家黄秀玲最早从原始资料入手对此期文学进行细致研究,她于1984年撰文分析1947—1948年间美国华侨文艺刊物 《新苗》的短篇小说。《战后唐人街的故事——论 〈新苗〉短篇小说》分别从小说语言、道德倾向、历史意义等方面对 《新苗》短篇小说进行细致分析,指出 “《新苗》小说是华美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9]该文在国内发表后,未引起太多关注,该文所写题材较狭窄,当时 《新苗》不为大家所知,国内学界的热点仍在台港文学领域,少有人关注美华文学的历史及相关论述。该文的英文版刊登在1988年第14期 《美亚》上,黄秀玲希望借此引起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并突破华裔英语文学与华文文学之间的分隔局面。
国内仅朱云霞的一篇论文真正论及40年代的美华文艺。《写在家国之外:想象与凝视——以 〈华侨文阵〉为分析对象》分析美国华侨文艺刊物 《华侨文阵》的作品主题及创作风格,她认为这些创作突出呈现了二战期间美国华人的中国情结。[10]该文为40年代美华文学研究有效拓展了美华文学的版图,但论者只就自己搜集到的资料而论,未能将之置于40年代美华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量,有所偏颇。
对40年代美华文学,学界已经关注并有部分研究成果,但未能就具体的文献资料系统全面地论述,甚为遗憾。笔者有幸出国访学,跟随黄秀玲教授进修,得其慷慨赠阅 《新苗》期刊复印件且指引笔者寻找相关资料。笔者在中美两国的图书馆中找到相关资料,已整理出小说、诗歌、散文等近百万字,这些资料因年代久远兼保存不善,都有一定的残缺,因而本文论述也难免会有缺漏。
二、40年代美国华侨文学的发展概况
早期的美国华人社区相当重视对中国文学的传承,谭雅伦在 《金山歌谣集》序言提及旧金山唐人街的诗文创作和文学社团的组建情况及历史渊源。[11]刘伯骥 《美国华侨史》也提到清末民初旧金山各会馆的主席都来自 “国内科名中人,咸以老师称之,受此宿儒影响,侨社讲究文字,习已成风,征联吟诗,不逊于国内”。[12]在旧金山华人社区先后成立过小蓬诗社 (1893)、金山同文社 (1895)、金门吟社(1923)、文华社等,到1967年仍有敦风诗社成立。这些文学延续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特质。1910年至1940年间,在加州旧金山天使岛木屋中留下的百余首中文木刻旧体诗,抒发备受凌辱的思乡情愁。[13]
1917年中国兴起新文学运动,这并未直接影响到美国华人社区,这与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发展有着不同的轨迹。诸多新文学的提倡者和中坚力量都曾在美留学,如胡适、陈衡哲、冰心、闻一多等,但他们与当时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劳工少有往来,正如温泉所说的 “这些唐人街,往往是破旧、污秽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官员、留学生等是不作兴涉足其地的”。1940年之前华人社区的文学在他看来也是 “报纸副刊大抵都抄些祖国 ‘旧餚',填塞篇幅,也一贯地是 ‘某处某生,貌美多情'那一套”,[14]极难脱离旧文学窠臼,更遑论新文学创作了。这种境况直到抗战爆发后才有所改变:国内华侨子弟为避战乱移居美国,他们大多受国内左翼文学的影响,极大促动了美华文学的发展。
第一,华侨文艺创作队伍不断增添新人,逐步壮大。1938年广州和武汉失守,广州附近的华侨子弟移民去海外避战祸,他们受过新式中学教育,有参加抗战的经历,颇有政治意识。如 《华侨文阵》《新苗》的主创人员高木、老竹、百非等以及 《美洲华侨日报》的主笔梅参天、唐明照、李顾鸿,《绿洲》的马赐汝、茫雾,《轻骑》的梁小麦等都在抗战前后进入美国。他们积极联合华人青年,组建文艺社团,创办文艺刊物,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5]他们为美国华侨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现实的文学立场及开放的国际视野影响、改变着美国华人青年。
第二,各文艺社团的成立及文艺刊物的创办推动了美国华侨文学的发展。40年代美国华侨文艺运动较为突出的是纽约和旧金山地区。纽约地区有: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 (青救团)的 《华侨青年》杂志、“曦社”的 《曦社课艺》(油印刊物)、华侨文化社的 《华侨文阵》《新苗》及华侨青年文艺社的《绿洲》等杂志。旧金山地区则有:屋仑野火社的 《野火》、加省华侨青年救国团的 《战斗》(油印刊物)、三藩市青华社的 《青华》、屋仑晓角社的 《晓角》、三藩市华侨青年轻骑文艺社的 《轻骑》等。这些文艺刊物都鼓励华侨青年提笔创作,在文学创作上较为突出的是 《华侨文阵》《绿洲》《新苗》。
《华侨文阵》由1942年底在纽约成立的华侨文化社创办,被认为是 “美洲华侨有史以来第一个纯文艺期刊”。[16]其执笔者为文出于兴趣,“都是一些华侨职业青年,又都是于文艺有嗜痂之好的,既没有‘文章华国'的野心,也没有 ‘卖文为活'的必要;兴之所到,大家写点东西,凑几个钱,就印成了这么的一本,呈现于华侨大众之前”。[17]因自费出版,《华侨文阵》的经济基础不稳定,出版无定期,1945年底便不能为继了。《华侨文阵》的创作以散文、诗歌、小说、文艺评论等为主,其中诗歌散文大都书写海外游子对战地故乡的忧思,文艺评论则面向中美文艺,有书评影评,如高木的 《老舍张天翼合论》、温泉的 《广东文学论》都比较突出。小说选材较为广阔,既表现故土战争,也描画在美华人生活,甚至还将笔触扩展至参与欧洲战场的华裔军旅生活。如周流的 《为祖国的儿女们》讲述一群华人子弟热切想回国抗日的故事,表达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翼不郎的 《夜踱街头》则讲述一华裔子弟如何为父报仇,希冀在美国被平等对待,控诉种族不平等的现实;前长竹的 《色》讲述同为弱势群体的华人和黑人间的矛盾,表述黄黑联合意图。《华侨文阵》的创作当时已颇具水准,选材既观照故土又立足当下,展现华人生活多个层面。《华侨文阵》每期还附有广东方言副刊 《猗彧》,以满足广东移民之需。
《绿洲》是华侨青年文艺社1945年5月4日创办的月刊,共计出版32期。相比 《华侨文阵》,《绿洲》创办者更有远大的文学理想和抱负:“在这文艺生产的供给缺乏得像沙漠上的水一般的华侨社会里,我们是一群需求文艺滋润的渴荒者,我们追求着一个绿洲的呈现”,要在华侨社会里 “用血、汗和泪浸润滋生出一些华侨文艺的根苗,甚至使它绿叶成荫,开花结果”。[18]他们高举 “五四”旗帜,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为榜样,热切关注国内文艺活动,也积极给读者翻译介绍美国文艺界的最新动向,以融合不同文化资源,促进华侨文艺的发展壮大。《绿洲》的文艺创作以短篇小说、诗歌、文艺短评、战地记事等体裁为主,也有部分较为突出的作品,如石留的短篇 《不够体面》、黄仁仕的诗歌 《归国行》《关于诗的》、玲军的 《战地通讯》等。由于是借用 《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出版,每期只有报纸的两个版面,给华侨青年练笔的空间较少,《绿洲》作品大都短小精悍。但 《绿洲》成员比较注重对华侨文艺理论的探讨,数次发起 “华侨文艺”的争论,表现出十分难得的理论探索意识。
《新苗》1947年3月由华侨文化社的一部分社员联合美西的部分青年创办。作为纯文艺月刊,《新苗》的出版较稳定也更成熟,1947至1948年间共出版12期,后改为不定期出版 《新苗》文丛,如 《人间爱》中篇小说选、《突围》等。《新苗》作品以散文、诗歌、小说为主,小说创作成果颇丰,被认为是 “结实累累的华侨文艺园地”。[19]《新苗》与 《华侨文阵》在编者及作者队伍上有一定的承续性,“在新苗上,我们更加致力于建立 ‘华侨文艺'的工作,尽先发表外稿,推荐新人”。[20]与 《华侨文阵》相比,《新苗》散文更具政论特征,语言犀利,直陈抗战后中国腐败的现实,政治上倾向中共。《新苗》小说则立足美国本土,以华侨的生活、工作及奋斗作为表现对象,呈现他们在唐人街内部的不同命运及他们与美国社会的互动。相比 《华侨文阵》《绿洲》等的小说创作,《新苗》小说在语言上有较大突破,篇中人物对话以广东方言为主,形象生动地再现原生态的唐人街生活场景,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创作手法也有突破,如运用心理剖析塑造人物等。其中以 《春宴》《枪手伯胜的奇功》《老泪》《突围》等小说最为成功。黄秀玲认为 “《新苗》小说的确代表了华美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杰出的 ‘积极表现'”。[21]无论是从小说的结构、语言、技巧或是表现主题等方面而言,《新苗》小说都是这时期美华文艺的代表。
第三,华文报纸副刊为美华文学提供平台,《美洲华侨日报》(China Daily News)“新生”副刊对美华文学的培育作用尤为突出。该报于1940年7月8日在纽约华埠由华人衣馆联合会成员共同募捐集资创办,是真正属于美国华侨自己的报纸。在总编辑梅参天的主持下,开辟 “新生”文艺副刊,积极推动美国华侨文学的发展,“《华侨日报》很快成为移民文学作者的摇篮”。[22]“新生”副刊固定在报纸第6版,既关注国内文艺动态,刊载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等的作品,也积极鼓励和培育华侨青年的创作,为华侨文艺的发展开辟新领地。初期推出 “华侨习作专号”,为起步写作的华侨青年提供园地,比如亚初 《未为晚也》、活庐 《人生四十才开始》①这两篇文章都极短,两位作者采用笔名开始练文,都是初试牛刀,所以文字表达还有很多旧习惯。等都是当时的练笔之作,也有较为成熟的创作如老梅的 《百大的故事》《生活的片段》《街头散记》②老梅在 《华侨日报》开辟专栏 “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他不仅给习作者鼓励和发表园地,提倡建立华侨文艺的自身特色,同时也为华侨文艺青年提供范本。这几篇连载都是记录他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黄魂的诗歌创作。“新生”副刊以老人带新人的方式发现和培育了不少华侨文艺青年,还经常借用给文艺社团出版自己的文艺刊物,比如 《华侨青年月刊》《绿洲》《轻骑》等,以扶持这些执着于文艺却又经济困顿的青年。自1949年始,每月都安排一次“华侨文艺”专栏,刊载华侨青年的小说散文,继续致力于培育华侨文艺青年、传递文艺薪火。《美洲华侨日报》由洗衣工人联合创办,总编辑冀贡泉、徐永煐、唐明照等都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联,[23]从其政论时评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其政治倾向,1949年后 “新生”副刊的小说散文倾向更为明显。
抗战后美华文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步走出中国旧式消遣文学的窠臼,在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影响下,既表现华侨与祖国的情感关联,更强调关注与美国华侨生活紧密联系的本地化素材,表现华侨的精神风貌,创作别具特色的美国华侨文学。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华侨文艺界关于 “华侨文艺”的论争,其探讨凸显了华侨文艺界对自身文学样态的自省和对华侨文艺与祖国文艺关系的理解。
三、美国 “华侨文艺”论争及其意义
40年代美国有关 “华侨文艺”的论争持续了4—5年,从命名讨论、文化渊源、题材选择到创作手法的运用等问题都引起了华侨文艺界积极介入。最早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观点的是 《华侨日报》的主编梅参天。1940年7月17日该报创办一周,他用笔名老梅在 “新生”副刊上发表了 《华侨大众文艺》。该文提出了美国华侨文艺的初期理念:从华侨自身的生活出发,以写实的笔法刻写华侨日常生活。他认为华侨大众文艺在美国颇有基础,有大批热爱祖国的青年华侨,华侨生活中的各种经历都可以成为写作素材。他指出 “以华侨生活为本位,华侨社会为背景”的报告文学或小说之类 “做更细致的、更曲折、更繁复的描写的作品”在华侨社会非常缺乏,由此号召华侨青年拿起笔记录和描写自己的生活,“小之如个人的日常生活——衣馆、餐馆、唐人街做生意,或做店员与抗日筹饷的关系;大之如集会、巡行、做国际宣传等等”。[24]老梅还亲身实践,在 “新生”副刊上发表抨击社会现象的短评比如 《金山美梦》,或反映华侨生活困顿的小说 《街头小记》等。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华侨青年日常记录式的文字。
温泉 《广东文学论》一文首先提出 “华侨文学”概念,认为美国华侨文学是广东文学的海外延伸和发展,并提出 “民族主义+西洋民主思想=华侨文学”。[25]纵观40年代美华文学,笔者认为他的 “华侨文学”定义较为偏狭和不准确。首先,认为美国华侨文学是广东文学的海外发展,这带有强烈地方色彩和排他性。尽管美国华侨大部分是广东移民,抗战期间移居广东的文侨也颇多,但不能因此得出上述论断。其次,其等式中反映的应是华侨的现代精神,而不是华侨文学特质。温泉的华侨文学论虽然是广东文学论的附属产品,较浅显粗略,但已涉及华侨文学的双重影响因子,对之后的讨论有启发意义。
《绿洲》同人在 “华侨文艺”的论争中表现最踊跃。在发刊词中就表达了他们建设华侨文艺的决心,表明要用自己的血、汗、泪开辟出 “涓涓溪流,以滋生华侨文艺的根苗”,[26]使其开花结果。在这一期的文章里茫雾等人提出华侨文艺要高举 “五四”旗帜,文艺要反映时代,文艺青年不能躲进象牙塔为艺术而艺术等观点。[27]1945年5月9日雁羽发表 《略谈华侨文艺》一文回应 《绿洲》的观点,非常清晰地界定了华侨文艺的特质及文化渊源,是论战中极为重要的奠基文章。他首先强调华侨文艺的特质是 “反映华侨生活,发扬华侨的精神”。他认为华侨社会目前 “还没有见到具体地反映华侨生活的作品”,《绿洲》的创刊让他看到了希望,对华侨文艺的未来有所期盼,而华侨社会爱好文学的读者可以不用再 “以国内文学刊物为精神食粮了”。其次,雁羽进一步指出华侨文艺必须从中华文化和美国文化中寻求滋养。“这道水源 (精神源泉),也不是限于华侨社会之内,更应该连贯着周围更大的美国社会,去吸收美国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它在文艺上那种大众化姿态;但不是生吞活剥,而是要加以 ‘华侨化'。这样生产出来的华侨文艺才是活泼而有生气的文艺”。[28]雁羽的论述较之温泉的 “华侨文学”论更为清晰,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思想文化渊源上的双重性,而后者所要强调的则是美华文学的当地性、当下性。
雁羽有关 “华侨文艺”的论述得到了一致认可,之后大家都沉浸在华侨文艺的写作实践中。虽然大家都明白华侨文艺须华侨化,表现华侨意识,然而具体写作中仍出现较多问题。1945年9月,老梅语重心长地对 《绿洲》的创作提出建议:“作为华侨文艺的说法,它应该具有其本身的特点。这并不能因为作者是华侨,写作的是文艺,就把它当是华侨文艺看,必须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华侨生活意识形态,无论什么人看去,都可以指出那是我们华侨的面貌,甚至可以拿了这些作品作为研究华侨问题的一种资料。我以为这是我们提出华侨文艺的本旨。”[29]该文结尾号召描写亲身经验。老梅的观点一以贯之,在新生副刊的华侨文艺专栏也以此标准选取刊登稿件。1945年至1946年初是 《华侨日报》新生副刊刊登华侨文艺稿件最频繁时期,平均每月一篇短篇习作,诗歌与散文创作则更多。
1946年 “五四”,《绿洲》创刊一周年,华侨文艺界的同仁们再次对 “华侨文艺”的定义和内涵进行反思与补充,并落实到选材写作等具体细节上。在创刊一周年纪念号上,梅参天进一步深发对华侨文艺的寄望。他赞同雁羽提出的华侨文艺特质,并从取材和写作方法上对华侨文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认为华侨文艺就是要反映 “华侨的面貌,华侨的气息”,为反映这一主题,“大至于整个华侨社会的生活形态,各阶层各行业的华侨意识,小至于个人偶尔在街头的见闻感觉,一天的工作经过,生活的片段回忆”,[30]都可成为写作素材。他还提出淳朴扎实的写作风格,“只要在写作中保持一种本真的体验,不矫饰,就能写出活泼生动的华侨文艺作品”。这些都给华侨文艺做了细致具体的现实主义定位。
《绿洲》同人也对华侨文艺的发展进行总结和反省。顾鸿认为40年代的华侨社会已较十年前有了很大改观,华侨文艺也开始出现新面孔,是值得庆贺的。[31]茫雾认同老梅的观点,一针见血指出了 《绿洲》在华侨文艺创作上的不足,“我们对于发挥华侨文艺这一点,没曾下过真功夫,而只是从皮毛上着手。华侨的现实生活,华侨的血肉与灵魂,都没有痛快淋漓的反映出来”。[32]如茫雾所言,《绿洲》大部分作品仍以关注国内战事及战后状况为主,仅有少数篇幅真正触及华侨社会,如茫雾 《平木桥上的血》、①茫雾:《平木桥上的血》,《绿洲》第四期 (上、下),1945年8月15、16日。徵玲 《唐山信》、②徵玲:《唐山信》,《绿洲》第七期 (上),1945年11月15日。黄文湘 《伟大的爱》③黄文湘:《伟大的爱》,《绿洲》第十期 (上、下),1946年2月15、16日。等,可谓成果寥寥。而且在创作手法及语言表达上都未能超越《华侨文阵》。玲玲赞同茫雾,在 《略论华侨文艺的改进》中亦犀利地指出当时华侨文艺依然注重对国内文学的搬运,因而他对未来提出期望:“今后的华侨文艺运动,不能只是接受过去的传统继续开展,应当结束过去的旧习,去陈出新,拓荒播种,在自己的土地里抽新的芽儿,开新的花朵,结新的果实。”同样他也认为 “只要所写的情节是华侨生活里所有的东西,而富有华侨风味,华侨情调,反映出华侨社会的现实生活,就能亲切动人”。[33]玲玲对 “华侨文艺”的阐述是对雁羽观点的深发,并结合老梅、茫雾等人的观点,十分鲜明地提出了美国华侨文学未来的路向:根植于此地,开出新花结出新的文艺之果。玲玲在该文还提出了建设华侨文艺理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为要求华侨文艺的 ‘质'与 ‘量'上的改进,一种新文艺理论来做基础与领导正是迫切的需要。这种新的文艺理论,在目前就要建立起来。这种理论,光是介绍是不够的;一定还要研究华侨自己的文艺史 (虽然为期短暂),文艺思潮,研究自己的社会动态,研究自己的语言,研究自己的读者,研究自己份内的政治任务。华侨文艺理论,要在广大的华侨生活中产生出来”。[34]对美国华侨文艺理论建构的呼吁是在当时习作与争论的情势中自然生发的,从对华侨文艺的具体论争到理论建设的吁求,标志着40年代美华文学的发展正逐步走上自觉之路。在此号召下,温泉的 《华侨文艺十年》对华侨文艺发展进行了批评总结,并选列15篇华侨小说作为创作模本,展望未来的创作路向。但温泉文中一再强调华侨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关联,这使得华侨文艺又偏向祖国文艺,与雁羽等的观点有所背离,但这不妨碍其成为40年代美华文学中最突出的批评实践成果。
40年代美国华侨文艺界对 “华侨文艺”的论争经历了命名探讨、文化溯源、题材选择、创作手法等的界定及呼吁建设华侨文艺理论等过程。从论争中我们可见当时华侨文艺界人士对自身文学定位的焦虑和探索,也展现了他们试图在海外生发一种独特文学样态的雄心壮志。这些论争为华侨文艺创作提出了具体而微的指向,《新苗》杂志就是在华侨文艺理论指导下结出的硕果。
从不断创办的文艺刊物、发表的诸多文艺作品、对 “华侨文艺”的火热争论,都可见出40年代的华侨文学确实是美华文学史上的第一波高潮,并处于转型阶段。文学创作转型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从消遣的旧式文学观念中逐步转向直面现实、积极改进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从关注故土战事人情转向观照美国当下的华人生活情境;从学习模仿走向自我探索和实践。虽然在此过程中,还没有明确的华人意识呈现,但已萌芽,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逐步完成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意识转变。正是这种走向转型的过渡阶段充满生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才能准确把握美华文学史的丰富复杂性。40年代的华侨文艺工作者努力探寻美国华侨文学的走向,亲身参与文艺实践,并在创作中积累总结创作经验,为理论建设奠定基础,而对华侨文艺理论的建设吁求更突出呈现了该时期美华文学发展的自觉意识。
[1][15]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第320、311-312页。
[2][22]谭雅伦:《四十年代的华埠文学运动》,《布告板》1988年第7期。纽约华人历史学会主办,第1-5页。“纽约华埠历史研究社”社刊 《布告板》推出27页专刊,以纪念40年代的华埠文学。其中刊有该刊总编辑陈国维的文章《华埠文学四十年代及当今》,以及谭雅伦撰写的 《四十年代的华埠文学运动》。同时该刊选发了 《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上老梅的五篇短文,其他作者的六首诗和六个短篇小说。
[3][7]黄万华:《20世纪美华文学的历史轮廓》,《华文文学》2000年第4期。
[4]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5]赵文书:《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7-81页。
[6]Wenquan,“Chinatown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1939-1949)”,trans.Marlon K.Hom,Amerasia 9:1 (1982):83;Sau-ling Cynthia Wong,“Tales of Postwar Chinatown:Short Stories of The Bud,1947-1948”,Amerasia 14:2 (1988):61-79.
[8]黄文湘:《1940年代的美国华人文学——美国华人文学初探之二》,《华人》1987年第5期。
[9][21]黄秀玲:《战后唐人街的故事——论 〈新苗〉短篇小说》,《四海》第8辑,1984年。
[10]朱云霞:《写在家国之外:想象与凝视——以 〈华侨文阵〉为分析对象》,《华文文学》2010年第3期。
[11]Marlon K.Hom,“An Introduction to Cantonese Vernacular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Songs of Golden Mountai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28-38.
[12]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404-406页。
[13]Him Mark Lai,Genny Lim,Judy Yung,Island: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le Island,1910-194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1.
[14][16][19]温泉:《华侨文艺十年》,新苗文艺丛书第二期 《突围》,1949年,第42-60页。
[17]“创刊献词”,《华侨文阵》1942年12月15日,华侨文化社。
[18][26]《绿洲》创刊词,《华侨日报》1945年5月4日 《新生》副刊。
[20]《新苗》第一卷编者的话。
[23]徐庆来编著:《徐永煐纪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24]老梅:《华侨大众文艺》,《华侨日报》1940年7月17日 《新生》副刊。
[25]温泉:《广东文学论》,《华侨文阵》第四期特大号,1944年8月1日,华侨文化社,第4页。
[27]《华侨日报》1945年5月4日 《新生》副刊。
[28]雁羽:《略谈 “华侨文艺”》,《华侨日报》1945年5月9日 《新生》副刊。
[29]老梅:《华侨文艺问题——给华侨青年文艺社诸君一点意见》,《华侨日报》1945年9月17-18日。
[30]老梅:《献给绿洲——重提华侨文艺的问题》,《绿洲》第13期之3,《华侨日报》1946年5月7日。
[31]顾鸿:《文艺节漫谈华侨与文艺》,《绿洲》第13期之6,《华侨日报》1946年5月9日。
[32]茫雾:《绿洲创刊一周年》,《绿洲》第13期之5,《华侨日报》1946年5月8日。
[33][34]玲玲:《略论华侨文艺的改进》,《绿洲》第14期下,《华侨日报》1946年6月16日。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6.7
A
1000-7326(2016)07-0162-07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 “1940年代美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影响”(13YJAZH047)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11&ZD111)的阶段性成果。
李亚萍,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广东广州,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