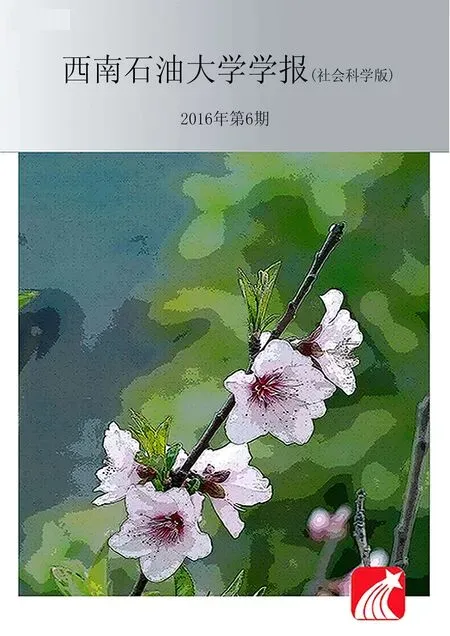论毒品案件“幽灵抗辩”之排解
2016-02-24罗恒
罗恒
上海海警总队情报法制小组,上海 200137
论毒品案件“幽灵抗辩”之排解
罗恒*
上海海警总队情报法制小组,上海 200137
毒品案件中的“幽灵抗辩”可能针对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等成罪要件的控方证明进行阻击,也可能就其刑事责任的大小进行罪轻辩护。针对“幽灵抗辩”,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着不同的分配模式,但被告人提出“幽灵抗辩”而不进行任何举证活动往往会招致诉讼不利结果。基于经验法则、无罪推定原则及毒品案件特殊性的要求,被告人应当承担“幽灵抗辩”所对应的举证责任。面对“幽灵抗辩”,立法上可考虑对毒品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以概括的故意取代“明知”,并规定持有毒品罪的未完成形态以合理分配毒品犯罪的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证明责任的转移并明确被告人证明责任承担范围、合理运用事实推定以及使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法律事实来压缩“幽灵抗辩”的存在空间。
幽灵抗辩;证明责任;无罪推定;事实推定;间接证据
罗恒.论毒品案件“幽灵抗辩”之排解[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6):41-50.
LUO Heng.On Dealing with“Ghost Defense”in Drug Cases[J].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6,18(6):41-50.
引言
刑事诉讼是一个运用证据与证明规则逐步发现案件法律事实,在此基础上依据实体法律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及刑罚的动态过程。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控方承担提出证据以推翻无罪推定的义务,为达到这一目的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争取诉讼有利结果,往往会提出难以查证的辩解,即“幽灵抗辩”,以期使审判者产生怀疑从而阻击犯罪的认定。毒品案件同样不例外,在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制裁较重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常提出“幽灵抗辩”以期瓦解控方的证明体系或者减轻自身的刑事责任,给打击毒品犯罪造成了一定困难,如何应对毒品案件中的“幽灵抗辩”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面对的课题。
1 毒品案件中“幽灵抗辩”的提出与表现
1.1 “幽灵抗辩”的提出
“幽灵抗辩”的说法来源于我国台湾地区一起走私案。当时,执法人员在一艘船上查获了大量走私货物,在法庭上,被告人抗辩称,其是在正常的捕鱼后被强盗强行掳走渔获物而以被查获的走私货物交换。最后,法官认定这一抗辩动摇了控方指控其犯罪的证明基础,构成合理怀疑,判决被告人无罪释放。该案之后,很多被查获的走私嫌疑人均以类似理由进行无罪辩护,而这一辩护理由难以为控方查实推翻,如同幽灵一般难以为人所证实,故被称为“幽灵抗辩”。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幽灵抗辩”亦时有产生,笔者将其总结为由辩方针对控方提出的有罪指控,为推翻其指控或者为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难以查证或者明显违背社会常识的辩解①万毅教授认为幽灵抗辩是指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检察官的有罪指控,为减轻和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难以查证的辩解。对这一定义,笔者认为其覆盖范围不甚全面,“幽灵抗辩”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在审判监督等程序中亦有可能存在。同时,“幽灵抗辩”不仅阻击刑事责任承担,更重要的是动摇刑事责任的基础,即犯罪的认定。。
在毒品案件中,“幽灵抗辩”亦时有产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就是否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是否具有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及是否明知提出难以查证的辩解,造成了毒品案件中控方的证明困难,“幽灵抗辩”应对的关键也就在于破解这类抗辩证伪过程中证明困难的问题。如果对这一问题不及时从法理上进行甄别、分析及破解,无疑将形成政策导向,引发更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这一证明困难提出“幽灵抗辩”以逃避法律制裁②褚福民博士认为,证明困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证明过程存在困难但仍可获取证据进行证明,狭义上则是指无法取得必要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形。毒品案件中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往往是无法取得必要证据的,本文亦从狭义的证明困难角度进行论述。,使毒品案件的侦诉及审判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从目前的实践案例看,从控方证伪难度出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地从否认对案件发生具有主观明知进行辩护,但也存在提出难以查证的理由以否认客观上实施了毒品犯罪等情况。为减轻自己的刑事责任及应当承担的刑罚,也可能会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影响量刑的因素进行抗辩。③影响量刑的因素较多,包括是否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是否为自首立功坦白等,毒品案件中亦存在这些量刑因素,但对于这些量刑情形的证明与其他案件并无特殊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从客观的违法论出发,笔者不赞同目的与动机是主观的违法要件,故将对目的与动机的抗辩纳入对有责性的抗辩之中进行讨论。
1.2 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幽灵抗辩”
构成要件符合性是对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所禁止的行为的第一判断。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提出其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客观行为,并有时通过对行为结果物质表现的隐藏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上即对控方提出的指控阻击,并且这一抗辩很难为控方所证伪。例如,公安人员当场从某甲汽车的后备厢内搜查出海洛因22克,但某甲始终辩称毒品并非其持有,其当日曾驾车送一在赌局中认识的吸毒人员某乙赴棋牌室赌博,不能排除该毒品为某乙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而偷偷放置于车内。鉴于某乙的身份很难查清,加之某甲当天确实出入过棋牌室,其辩解不能彻底证伪,侦监部门只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其做不批捕决定(下称案例1)④本案例来自于姚舟、沈威《幽灵抗辩及其排解机制构建》,《东南法学》,2014年第3期。。
案例1中,尽管当场“人赃俱获”,犯罪嫌疑人有过多次毒品犯罪前科,但是由于行为人拒绝承认其实施了非法持有行为,使得案件遭遇了证明困难。尽管本案的抗辩理由存在诸多不符合社会一般常理之处,如一起打牌却不知其姓名,载其牌友去棋牌室却没有其联系方式,尽管如此,某甲提出的抗辩事由仍然对办案人员的有罪确信产生了一定的动摇。
毒品犯罪中对于实行行为不能实现有效的证据固定以认定案件法律事实的原因在于相关行为认定缺乏直接证据,或相关直接证据证明效力较低,以致为“幽灵抗辩”提供了可乘之机。与对是否明知的抗辩理由对应,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抗辩是对客观的否认。案件中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或者行为人有着较为狡猾的反侦查技术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毒品犯罪组织者与下级马仔仅通过单线面对面方式布置任务时,无疑会使相关案件直接证据材料收集变得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大量间接证据以期说服审判者时,行为人必然会提出没有实行行为的抗辩,使控方精心编织的证据体系受到质疑,毕竟,质疑的难度远小于构建。
1.3 对有责性的“幽灵抗辩”
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行为人对具有违法性认识或者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状态下发生的,在我国目前实务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的责任性要件是目前毒品案件中的难点。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对于有责性的“幽灵抗辩”主要分为没有违法性认知即“不明知”的抗辩和不具有犯罪目的的意志因素抗辩。
从当前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行为人提出主观上“不明知”的抗辩较为常见。以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犯罪为例,行为人必须对行为对象是毒品具有明知,但由于毒品犯罪的隐秘性,各个环节均为秘密进行,司法机关往往不可能收集到直接证据以证明行为人具有主观明知。例如,云南省边境某火车站,公安人员在对下车旅客进行检查时,发现某甲形迹可疑,其座位位于3号车厢,但其却从没有公安人员检查的9号车厢位置下车,经检查,发现其随身携带的背包内有三包毒品,且包裹有可防止缉毒犬嗅出的辣椒粉和胡椒粉,外侧用三条毛巾有规则的包裹。对此,其抗辩称这三包毒品是其朋友让其带的茶叶,其并不知道是毒品,但其无法说出“朋友”的真实姓名、地址等任何信息(下称案例2)。
除了认识因素,目的和动机等意志要素对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对实行行为的法律评价构成直接影响。比如,贩卖毒品罪的成立必须要求行为人具有将毒品贩卖的故意,否则就难以评价为贩卖毒品罪。目的与动机作为行为人主观因素,难以为外界所感知,部分行为人利用不具有毒品犯罪的主观目的或动机来脱罪或者减轻刑事责任。例如,居住在外地的某甲与居住在北京的某乙,通过电子邮件商议毒品买卖事宜。某日,某甲随身携带一公斤海洛因(装在自己的双肩包内),按约定乘火车到达北京西站,某乙按照约定驾驶轿车前往车站接某甲。某甲下车出站后,身背双肩包坐在某乙驾驶的车内。某乙驾驶轿车上四环路后,警察根据事前掌握的线索,拦截某乙驾驶的车辆,抓获某甲与某乙。被抓获时,某甲坐在轿车后部,一直背着装有毒品的双肩包,某乙也没有向某甲支付购买毒品的对价。本案中,某甲构成贩卖毒品罪不成问题,但购买明显超过自用量的毒品的某乙,其坚决否认购入毒品是为了贩卖,辩称购买大量毒品只是为了自己吸食;并且由于按照通说,在某甲与某乙被抓获时,毒品仍处于某甲的控制下,在物理上并没有交付给某乙,对其不能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鉴于毒品犯罪侵害的法益是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权①传统学说认为,毒品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于毒品的管制权,这种观点作为形式的违法性的体现,等于说毒品犯罪违反了国家对于毒品的管制法律,等于什么都没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家对于毒品的管制根本还在于维护国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不受侵犯,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某乙的行为无疑对这一法益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显然进入了刑法调整的领域(下称案例3)。
1.4 对刑事责任承担的“幽灵抗辩”
除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提出“幽灵抗辩”外,鉴于毒品犯罪常见团伙犯罪甚至集团犯罪,很多行为人为减轻其刑事责任,往往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抗辩,以期降低对其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的认定。例如,某甲某丙进行毒品交易时被现场抓获。某甲不否认参与贩卖毒品并供认了其他贩卖毒品行为,但第二次讯问开始供述其多次犯罪行为均是与另一共犯某乙一同贩卖毒品,其只是负责联系并交付毒品给客户,毒品来源及客户信息均由某乙提供,并认为这些犯罪行为不能仅仅由其一人承担责任,坚称由于只是单线联系故无法提供其所供述的某乙具体情况,但对于其基本情况在后面的供述中一直较为稳定(下称案例4)。
2 “幽灵抗辩”对毒品案件刑事证明的影响
2.1 不同诉讼模式对“幽灵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
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方式基于控辩平等武装,同时其无罪推定原则与大陆法系不同,并不是指视同被告人无罪,而认为是一种可以被推翻的认定,在检察官举出证据后即可转为有罪认定,被告人若想推翻这一认定就必须提出积极抗辩。考虑到取证的便利性角度,在其证明理论中,积极抗辩(affirmative defence),也称肯定性辩护,主张在被告人拥有特别知识之阻却违法或阻却责任或减免罪责事由,可公平地被要求负担举证责任之抗辩[1]。肯定性辩护要求被告方提出证据以支持他所主张发生的事情。当事人主义举证责任的目的与功能是形成“争点”(提出证据的责任),并在争点未得到证明而转化为“疑点”时决定证明利益的归属(说服责任)[2]。州法律一般要求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以成功提出肯定性辩护[3],对于说服责任,有的州要求形成争点即可,有的州则要求使控方主张受到动摇,有的州甚至要求达到“证据明确”的标准[4]521-531。
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该诉讼模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的举证责任”与“客观的举证责任”。“主观的举证责任”也称形式的举证责任,指有不利益之虞判断的当事人为摆脱这一不利益判断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也称实质的举证责任,指某一待证事实未能明确证明时,由何方负担不利益判断之责任[4]521-531。大陆法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受到成文法的保护,被告人没有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者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或主张的义务。基于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均为检方证明内容,被告人无主观的举证责任和客观的举证责任。在被告人提出一个积极抗辩却无法举出证明时,证明责任不发生转移,而由法官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即便检察官举出的证据已经足以使被告人被定罪,但法官仍然应当就在庭审中发现的可能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进行调查,以期发现案件真相。如果法官认为被告人提出的抗辩事由没有任何证据线索,无法开展调查或者经依职权调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的,将对被告人作出不利益之判断[5]。当法官依职权进行调查,认为被告人所提抗辩存在“疑点”时,将依据证据调查结果和自由心证原则,判断目前证据和抗辩是否可以形成有罪确信,如果不能,则将做出无罪判决。实践中,法官的调查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受限于法官的调查手段及精力,加之很多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况只有本人才可知晓,外人无法调查,大多数被告人为避免不利后果往往会主动提出证据或线索,法官与检察官天然的信任也使法官对“幽灵抗辩”保持警惕,更加大了被告人败诉的风险。
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就“幽灵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分析后可以看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诉讼模式,被告人在无法举证或者提供线索的情况下贸然提出“幽灵抗辩”,对其本身的诉讼结果都很有可能是不利的。对其而言,提出“幽灵抗辩”除了拖延诉讼进程外毫无别的作用,反而会因此丧失辩诉交易等可能使自己刑事责任和刑罚减轻的机会。毒品犯罪作为世界各国都严厉打击的重罪,在这类案件中控方在案件前期基本都会尽全力将案件证据体系完善,加之该类犯罪过于隐蔽,很多支持抗辩主张的证据或线索可能只有被告人自身知晓,其不积极提出线索、证据反而提出“幽灵抗辩”无疑会使自身处于不利地位,事实无法查明时不利益都将由其承担。
2.2 经验法则与“幽灵抗辩”的证明责任
经验法则(rule of experience)是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与证据法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人们从生活经验根据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总结得出的法则或知识。其既包括一般人日常生活所归纳的常识,也包括某些专门性的知识,如科学、技术、艺术、商贸等方面的专门知识[6]。经验法则是一项裁判法则,是三段论裁判的大前提[7]。裁判规则对于控辩双方而言,显然也具有指引作用。
经验法则之所以能成为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证明方法,就是因为其具有高度盖然性,“幽灵抗辩”名称之由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抗辩理由违背社会一般生活常识。尽管刑事诉讼中没有明确规定经验法则的地位与作用,但毫无疑问,没有哪一位刑事法官会在事实认定上脱离社会常理。控方根据刑事侦查描绘的犯罪“图像”建立在一系列符合社会一般常识的逻辑判断基础上,被告方如果提出的抗辩违背了社会一般常识,显然无法使法官的认定发生动摇,从根本上就没有使争点或者疑点形成,在此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是被告方可能成功脱罪的唯一路径。
2.3 无罪推定原则与“幽灵抗辩”的举证责任
被告人应当就“幽灵抗辩”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这一刑事诉讼法的基础。前文已述,无罪推定原则在不同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理解,“存疑有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原则要求的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解释为检察官承担排除一切怀疑的责任,或者只要被告人制造了疑点就将证明利益归于被告。刑事诉讼中控方的任务是通过证据还原犯罪发生的“图像”,达到法律真实,合理的怀疑必须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作支撑,至少符合社会一般认识方可动摇控方的证明体系,否则,无任何线索或者证据支撑且不符合社会生活常识的辩解无异于诡辩。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认罪有多种表现形式,捏造不存在的抗辩理由是常见手段,不能认为被告人不认罪就是存疑,只要提出抗辩就构成合理怀疑,以“存疑有利于被告”使“幽灵抗辩”为被告人脱罪相当于放纵犯罪,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曲解[8]。正如英国法官丹宁勋爵(Lord Denning)所言,刑事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并不需要达到确信(certainly),但必须达到很高的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意味着连怀疑的影子也要排除,如果允许虚假的可能性妨碍司法的过程,法律就无法有效地保护社会。如果证据如此强而有力以至于没有支持某人的可能性,能够以“当然这是可能的,但却是丝毫不能证明的”理由驳回的话,那么此案的证明就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①Miller V minister of pensions[1947]2 ALL ER372.。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认为被告人不认罪就是疑点本身也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背离,因为这无异于告诉控方定罪必须要取得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如此理解不仅违背了“不得自证其罪”原则,也增加了侦查程序中违法侦查行为产生的可能性。
2.4 毒品案件特殊性对“幽灵抗辩”举证责任的影响
毒品犯罪的特点对被告人提出“幽灵抗辩”时的举证责任有着特殊的影响。
第一,毒品犯罪因其对社会危害较为严重,如:诱发各种犯罪、破坏社会风气、加重艾滋病等恶疾的传播等,因此,在世界各国司法系统中均将其作为重罪予以严厉打击。刑事诉讼具有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两个价值没有疑问,但面对社会治安与犯罪浪潮不同时期的表现,刑事诉讼法不可能不考虑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的价值平衡。毒品案件同样不能忽视人权保障价值,但鉴于毒品犯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主观上证明的难度,如果放任大量“幽灵抗辩”作为行为人脱罪理由,将给社会安全和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刑法权威将大打折扣。
第二,从毒品犯罪案发地看,毒品犯罪均有高发场所和高发地区。在我国,云南、广西等靠近“金三角”的省区、娱乐场所、宾馆等特种行业为毒品犯罪高发地,在这些地区及行业内,禁毒部门进行了大量的禁毒宣传,并对毒品犯罪的作案手段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社会一般公众面对包装较为隐蔽、反常的物品都会想到其是否为毒品,“幽灵抗辩”所提出的理由往往与这些地区或社会的一般公众认识相违背,明显缺乏可采信的事实基础。
第三,毒品犯罪作案手段具有高度隐蔽性,其主观目的及认识只有自己知晓,控方难以用客观证据加以固定。在我国目前刑法理论要求毒品犯罪必须主观明知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控方对被告人提出的所有“幽灵抗辩”都承担证明责任,根本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相反,如果相关抗辩理由所描述事实真实发生,即便被告人因为羁押丧失人身自由不具备独立举证能力,其完全可以针对其抗辩理由中提出的事由说出稳定、详细、符合社会一般规律的线索甚至举出一定的证据,如果这些线索或证据足以使法官对有罪确信发生动摇,证明责任将再次转移到控方。在英国,立法规定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告人接触证据的来源和提供证据的便利性就是实例[9]。
总之,毒品犯罪的特性决定了在该类型的案件中,被告人提出的难以查证的“幽灵抗辩”不具有可信性,不能轻易动摇控方先前就案件进行的证明活动,如果被告人想推翻控方先前的证明有罪证据体系,就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2.5 我国毒品案件中应对“幽灵抗辩”存在的问题
第一,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的举证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除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外,法官作为事实的发现者也拥有除通缉以外的一切调查手段与权力。当被告人提出“幽灵抗辩”时,法官往往依职权宣布休庭,在法庭外进行调查工作,根据调查结果,对证据进行整体观察评价以判断被告人提出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全未提到被告方的证明责任,从形式上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符合无罪推定的要求,但事实上却不符合刑事诉讼尤其是毒品案件中的实际情况,为司法中违背法律精神的变通性操作埋下了隐患。
第二,法律推定效力存疑。为进一步明确毒品犯罪中“明知”的问题,2007年最高法、最高检及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这一解释通过特定客观行为认定主观明知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颁布,被学者认为是法律推定[10]。对此,笔者认为,法律推定本身属于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关系到控辩双方证明责任与证明利益分配,应当属于法律应当明确的事宜;更重要的是,在刑诉法对证明责任分配已经规定的情况下,仍然使用“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本身就涉嫌与法律规则相冲突。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打击毒品等严重犯罪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侦查权力,却并没有对该类案件证明责任重新进行划分,毒品案件中法律推定的效力仍存疑问。
第三,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标准不明确。与推定“证明+认定”的证明模式不同,使用间接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遵循的是“两步式的证明方法”,即首先证明若干间接性证据事实,然后根据间接性事实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待证事实以得出唯一性的结论。毒品犯罪是重罪,在证明锁链上无疑应当更加严密,但在毒品犯罪中使用间接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抗辩“幽灵抗辩”究竟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标准,立法及司法均没有予以明确。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中要求被告人就“幽灵抗辩”等积极抗辩事由承担至少形成疑点的主观证明责任是通常性的做法。为了使违背社会一般常识的抗辩理由动摇控方证明体系,被告人承担一定举证责任往往成为唯一可能的路径且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原则。再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来分析,被告人承担一定举证责任有其正当性。从实然性的角度,法律推定的客观存在以及间接证据运用于诉讼证明都要求被告人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法律不应当简单规定社会运行规则,更多地应当将实践中具有合理性且行之有效的方法纳入法律调整范畴,成为法律规则。
3 以毒品犯罪构成要件立法之完善挤压“幽灵抗辩”存在空间
从我国刑法对于毒品犯罪的立法体系看,对毒品犯罪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均有“封堵”,但仍然存在一定漏洞。从实践案例看,毒品案件中屡现“幽灵抗辩”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上对于毒品犯罪主观认识及实行行为认定上仍然存在疏漏之处。
3.1 以概括的故意取代对于主观明知的要求
第一,现行刑法没有要求毒品犯罪必须明知行为对象是毒品。我国刑法第七章第七节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从法律规则上看,该罪在有责性上必须具有主观故意,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或者持有毒品必须具有主观认识,并希望或者放任危害行为的发生及危害后果的实现。现行部分观点则将该类犯罪有责性要求为具有明确的主观明知,即明确知道行为的对象是毒品并继续实施行为。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难以站得住脚的,违背了对于行为人主观认识内容要求的刑法理论。
成文法没有规定只有具备明确的认识内容才是“明知”,只要是故意,无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都可以成为本罪有责性的形态。认为毒品犯罪中必须明知自己行为的对象是毒品无异于明确只有具备具体的认识内容才能构成刑法上的“明知”。这种观点将对实行行为性质及后果的明知要求为对于行为人主观认识内容明确的认识,将客观的认识异化为主观的认识,这种观点对刑法理论无疑有一定的背离。在运输毒品案件中,受雇人往往受到经济利益驱使,接受委托人巨大财物给付要求以隐蔽的方式运送某一物品,被查获后受雇人辩称其不知运输的是毒品,对于这一案例,司法解释认为其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行为具有明确的法益侵犯性,行为人主观上即便不知运输的是毒品,但肯定知晓其是非法物品,足以定罪量刑。如果所有故意犯罪均要求行为人具备明确甚至是具体的主观认识内容无异于自缚手脚,很多危害行为将轻易逃脱法律制裁。
第二,使用概括的故意符合违法性认识的要求,与毒品犯罪实际情况相符合。概括的故意定义有一定的争论,一般认为,概括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对于故意的具体认识内容并不明知,但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11]。概括故意之概括不在于行为人的意志因素的不明确,而在于认识因素的不明确;在于认识程度之明确,不在于认识内容之明确。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的行为方可构成犯罪,即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这是对刑法的禁止规范或者评价规范违反的认识,而不包括刑罚可罚性、法定刑的认识[12]。因为刑法本身在适用时是评价规范,具体适用属于司法裁判问题,作为事前行为调整规范的刑法只要告诉行为人哪些是法秩序禁止的,司法裁判不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不能认为只有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司法裁判才能按照其主观状态来判定犯罪与刑罚。
具体到毒品犯罪侦办的实际情况,在任何犯罪中去判断行为人主观认识到了什么具体内容都是很困难的,毒品犯罪为减轻自身刑罚也必然会坚决否认自己明知行为对象是毒品,但是其反常表现已经表明其必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为法秩序所禁止。尤其在毒品犯罪高发地区,其主观状态上必然有一定的怀疑,但却为了经济或者其他利益继续这一违法行为,对其定罪是合法合理的。
第三,毒品犯罪中采用概括的故意可以降低控方证明难度。采用概括的故意对行为人主观明知具体内容不作要求后,必然将有效降低控方的证明难度。控方只要证明被告方种种反常行为能表明其认识到自身在从事法秩序所不容许的行为,加上客观行为表现,就可以认定犯罪。
3.2 明确持有行为的未完成形态
非法持有毒品罪作为毒品犯罪的堵截式规定起着严密刑事法网的作用。立法者意图将毒品犯罪的各个环节均予以规制,但是,在对持有行为是否具有未完成形态上未作出特别规定给部分案件中司法证明造成了一定困难。如案例3中某乙在被抓获时因毒品仍处于某甲控制故其未持有毒品,而目前又无法证明其有贩卖毒品罪的责任要件,造成了法律规制的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跳出单纯地解决毒品犯罪的思维桎梏,必须从持有行为入手进行研究。一般认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实行行为是非法持有数量较大的行为,持有作为刑法上相对特殊的行为,能否具有未完成形态是存在争议的,就非法持有毒品罪而言,部分学者认为该罪必须要求对毒品实际占有方可构罪,故不存在未遂等未完成形态[13]。
笔者认为,按照主流观点,刑法上的实行行为并不是仅在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是具有紧迫的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持有作为行为的一种,很难说在正式占有之前不可能对法益构成威胁。从物理上说,行为人若想占有一个物品,不可能没有身体上的动作,并且这一行为有着主观认识的支配。一律否定持有行为不具备未完成形态是武断的,对符合法益侵害紧迫性的未完成形态进行规定绝不违背刑法以及刑法理论。
毒品犯罪中持有行为的设立本身为堵住毒品犯罪环节而设立,在无法证明走私贩卖等实行行为时,至少可以就其占有毒品犯罪行为进行处罚。可是,如果行为人在为实施其他毒品犯罪而未占有毒品时,行为人必然提出“幽灵抗辩”,导致其目的行为证明难度过大而无法证实,加上持有行为的未完成形态未加以明确,那么行为人将轻易逃脱刑罚制裁。所以基于毒品犯罪的严重性,刑事法网必须从严密的角度,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未完成形态予以明确。
3.3 构成要件修正与证明责任分配之联系
从立法角度对毒品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完善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证明责任规定的完善。将主观故意明确为概括的故意,规定持有行为的未完成形态无疑将使控方的证明难度大大降低,使“幽灵抗辩”的存在空间大大压缩。因为行为人可以辩驳其主观上不知道是毒品,但是很难辩驳其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对象为法秩序所禁止,也可以辩称其绝对没有实施诸如贩卖毒品的主观目的,其行为绝对不是贩卖毒品的实行行为,但却无法否认其即将对毒品实施占有。因为一旦被告人提出这些抗辩,将更加违背社会常识与社会规律,即便提出“幽灵抗辩”也很有可能连案件疑点都无法形成,更妄论合理怀疑。如果坚持“幽灵抗辩”,那么对其过于违背社会常识的主张无疑应当进行举证,证实这些抗辩理由有可能存在。
4 以证明规则有效适用对抗“幽灵抗辩”
事实上,在毒品犯罪的立法没有进行修订的情况下,有效利用证明规则,进行证明责任的转移,采用事实推定、法律推定等也是应对各种类型“幽灵抗辩”的有效途径。
4.1 证明责任的转移
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被告人应当就其财产属于合法收入承担证明责任的举证责任倒置不同,举证责任的转移是在控方已经通过证据体系证明了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全部要件,其犯罪行为已经具有高度盖然性时,如果被告人仍坚持提出“幽灵抗辩”则应当就其主张的抗辩理由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不同的情形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也是不同的。
4.1.1 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的情形
毒品犯罪中,行为人一般情况下承担的是主观的证明责任,即提出证据形成疑点或者争点的责任,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方承担客观的举证责任。换言之,被告人有义务对其“幽灵抗辩”提出“说明义务”,即便不能举出积极抗辩的直接证据,但至少也要说明情况并提出相关的线索加以佐证从而使控方已经搭建的有罪认定体系产生合理怀疑。笔者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有效完成了主观的证明责任应当基于以下判断:
第一,抗辩事由本身是否符合自然规律以及社会一般经验与常识。前文已经叙述过,经验法则是判断一项抗辩理由是否可能成立的判断标准。当被告人提出的抗辩事由明显与自然规律或社会一般常识矛盾,又无法提出确切的证据来主张自己的抗辩理由时,法官应当直接裁定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在案例2中,针对被告人的抗辩,法官认为,被告人使用辣椒和胡椒粉包裹毒品且将毒品放置在皮包中间用毛巾有规律地包裹着,明显与茶叶一般的携带方法矛盾,其绕路6节车厢从没有公安人员检查的9号车厢下车也表明了其主观上具有明知,故直接认定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抗辩事由的提出是否与案件现场情况相一致。被告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常常捏造事实并据此提出抗辩以期脱罪,但是很多抗辩理由经过细致耐心的现场勘查是可以被证伪推翻的。案例1中,侦查人员后来对现场勘查笔录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同时进行了侦查实验,证实其毒品放置在堆满某甲个人物品的后备箱中的备用轮胎里,其他人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将毒品放置在如此隐蔽复杂的位置且不被车主人发现,从而证实该抗辩事由与现场情况完全不符合。
第三,抗辩事由是否与行为人自身情况相适应。被告人本人在案件发生时的行动和反应必然要受到自身情况的限制,通过证据材料来审查被告人的抗辩理由是否与其自身情况相适应也是判断其抗辩理由能否成立的重要依据。面对“幽灵抗辩”,办案人员可以结合案件中被告人当时的生理、心理状况,围绕案件现场情况对被告人行为的影响去辩驳抗辩事由。案例4中,针对某甲提出有另一共犯参与贩毒活动且自身作用较低的抗辩理由,办案人员经审查发现某甲对于毒品的种类、特征等认识的确不甚全面,以其认知能力难以全程参与贩毒活动,同时其对某乙的基本情况供述较为稳定,符合毒品犯罪活动的一般规律,故采纳了其抗辩理由。
4.1.2 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的情形
第一,行为人坚持提出的违背自然规律或社会一般经验与常识的“幽灵抗辩”。任何法律推理都是建立在自然规律和社会一般经验与常识的基础上的,法官根据控方的基础事实证明在自然规律的演绎下得出内心确信。比如,在国外某案例中,被告人坚称自己的行为被外星人所控制,如果外星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自己的家人将受到灭顶之灾。这样的抗辩理由显然与社会一般经验与常识相违背,社会为了正常发展不可能容许社会成员随意编造理由而几乎不费吹灰力气就可以脱罪或者减罪。更何况,倘若真的有违背现有的自然规律或社会一般经验与常识的事由发生,必然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理论的重新改写,被告人对当时情况也最为熟知,由其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是必然的。
第二,被告人为推翻法律推定而进行的抗辩。法律推定的本质是法律为了某一目的规定控方在基础事实得到证明的情况下,自然推定出另一事实,被告人为推翻这一推定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人仅仅提出抗辩而不举出证据加以证实的话,法官将不必审视这一抗辩理由所攻击的构成要件是否成立而迳行判决被告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前文已经叙述过,事实推定是法律推定的来源,《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司法解释无论其效力如何,或者以司法解释形式规定法律推定范围是否合适,毒品案件中法律推定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重要的是,持有毒品罪本身也具有法律推定的因素,只要控方完成证明“持有”和“主观明知”而被告人无法反驳,那么都将产生法律推定之效果[14]。
4.2 合理运用事实推定方法
事实推定①事实推定又称裁判上的推定和诉讼上的推定,是指法律授权司法机关或法官根据已知事实和经验法则,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判定待证事实是否属实。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区别:1,产生的方式不同。法律推定是由法律明文规定,而事实推定来自于司法人员根据经验法则的逻辑推理。2,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不同。法律规定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司法者必须适用;而事实推定,司法者可以根据其实践经验自由裁量,决定是否适用。3,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推定主要使用于非刑事诉讼,事实推定则存在于任何诉讼形式之中。4,推定的种类不同。法律推定分为可反驳的推定和不可反驳的推定,而事实推定都是可反驳的推定。有学者认为,事实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的范畴,它同法律推定是有区别的。在事实推定的情形下,司法机关根据已知的事实作出何种判断,由于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需要由审判者根据一般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决定。而对于法律推定,审判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事实。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事实推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实际中用得较多,肯定事实推定,实际上就是肯定审判者在诉讼中的主观能动性,使司法变成一种能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事实推定属于逻辑上的一种演绎推论,它是根据经验规则经逻辑上的演绎而得出的结论,它属于证明评价的范畴。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一直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事实推定在司法实践尤其是毒品案件中是客观存在的。利用推定来认定案件事实是通过证明基础事实,利用经验法则、逻辑法则等推定依据认定推定事实的过程。具有全国影响的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中,一二审法院从南德集团业务真实情况、开具信用证后表现及资金用途来认定牟其中及南德集团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与利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不同的是,法院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其与非法占有有一定证明关系,但不能得出唯一性的结论并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此时,法院选择了可能性最大的情况作为认定的案件事实并容许被告人提出证据加以反驳或进行合理说明,在被告人提出的证据不能推翻这一认定或无法进行合理说明时认定生效[10]。
毒品案件中可以认定被告人具有主观明知的几种情况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其转化为法律推定,但由于案件类型多种多样,司法解释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证明被告人具有主观明知的情况,在具体的案件侦办中必然可能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或其他犯罪构成的推定,毕竟法庭证明不可能达到绝对确信,合理运用事实推定无疑是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同时,经过实践的检验将事实推定转化为法律推定也是合乎客观规律与立法规律的。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推定的适用不能违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毒品案件中,只有证据表明被告人的行为具有毒品犯罪的高度盖然性时,方可适用事实推定并要求被告人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死刑案件中,则有着更高的证明标准要求,可以说在毒品案件中,“应当知道”是毒品的情况不能适用死刑[15]。
4.3 以间接证据认定案件法律真实
使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法律事实采用的是在证明若干基础性事实后,利用逻辑推理认定案件实施过程,基础性事实与待证事实是排他性的一一对应关系。被告人的反驳只是承担辩护权的体现,与法官最后认定是否可以生效无关[10]。
事实推定由于介入了法官选择哪种待证事实作为可能性最大的认定事实的主观认定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而利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法律事实则客观性较强。在毒品案件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间接证据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据锁链来认定案件法律真实。
对于通过间接证据实现对毒品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应当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每一份证据本身是真实、有效,具备证明资格。第二,单个或者其中若干证据的证明力足以证明某一基础事实,并且是排他性的,不存在其他可能性。第三,一个或者基础事实得到证明后,根据一般社会经验法则和自然规律,可以得出唯一性的事实认定结论,不存在其他合理的怀疑。
5 结语
随着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对于毒品案件中时常发生的“幽灵抗辩”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刑事诉讼的过程是证明一个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过程,对于“幽灵抗辩”的排解也必须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阻击。综合刑事诉讼无罪推定、经验法则的规则与毒品犯罪的实际,必须对毒品案件的证明责任进行分配,适当由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除去应然,实践中也应当对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立法上的完善,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明规则达到“法律真实”。
[1]吴巡龙:刑事举证责任与幽灵抗辩[J].月旦法学杂志,2006(6):37-41.
[2]万毅“.幽灵抗辩”之对策研究[J].法商研究,2008(4):79-82.
[3]黄义明.刑事证据法研究[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0:271.
[4]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黄东熊,吴景芳.刑事诉讼法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2002:390.
[6][日]新堂辛司.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75.
[7]张卫平.认识经验法则[J].清华法学,2008(6):129.
[8]方海涛“.幽灵抗辩”与公诉人举证的限度[J].中国检察官,2015(8):62-63.
[9]王以真.英美刑事证据中的证明责任问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42.
[10]褚福民.事实推定的客观存在及其正当性质疑[J].中外法学,2010(5):667-680.
[11]张永红.概括故意研究[J].法律科学,2008(1):79-82.
[1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95-301.
[13]张明楷.刑事疑案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76-382.
[14]姚舟,沈威.幽灵抗辩及其排解机制构造[J].东南法学,2014(3):164-167.
[15]赵秉志,李运才.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限制——基于主观明知认定的视角[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12-115.
编辑:余少成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On Dealing with“Ghost Defense”in Drug Cases
LUO Heng*
Intelligence-legal Team of Shanghai Maritime Police Corps,Shanghai,200137,China
“Ghost defense”in drug cases may block the key prosecution proof for consistency illegality,and responsibility of crime elements,which constitute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in the conviction of crime,or it may affect the measuring of criminal liability.For the“ghost defense”,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civil law system have different patter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but the defendant who proposes“ghost defense”without providing any proof would encounter disadvantageous litigant result.According to rule of thumb,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he special nature of drug cases,the defendant should take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ghost defense.The legislation may consider amending key elements of drug-related crimes,for example,replacing the“deliberate”intention of crime with a more generalized one,and defining the“unfinished”nature of the crime of drug possession for a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n drug crimes.In judicial practice,demonstr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burden of proof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range of the defendant’s burden of proof,rational use of presumption of fact,and the use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ll contribute to restrain the application of“ghost defense”.
ghost defense;burden of proof;presumption of innocence;presumption of fact;circumstantial evidence
10.11885/j.issn.1674-5094.2016.07.17.02
1674-5094(2016)06-0041-10
DF73
A
2016-07-17
罗恒(1988-),男(汉族),安徽铜陵人,执法参谋,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