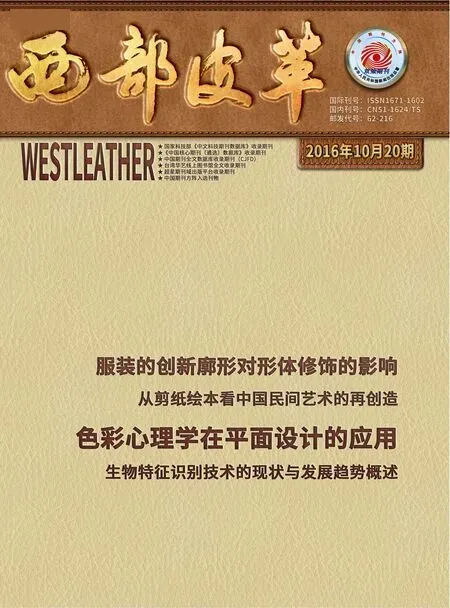精英与流行
2016-02-23李万瑜
李万瑜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0000)
精英与流行
李万瑜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0000)
精英艺术呈现的是思想,流行艺术呈现的是结果,精英艺术呈现的信息少而含蓄,流行艺术呈现的信息多而直白,流行艺术为观众事先分解了艺术,免去了他们消化艺术的过程,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结果的捷径,从而绕开了对欣赏艺术来说十分困难的道路。
沃霍尔;杜尚;《收租院》;《行走的人》
精英有朝一日终会成为流行,而流行永不可成为精英!
精英的特征具有高贵性,而流行的特征具有大众性。精英艺术与流行艺术在相互博弈中发展。艺术起初并不属于普罗大众,自工业革命起,艺术才自降身份,走向普通百姓。由此产生了两种后果,其一,艺术的高贵性丧失了,再也不是高雅的代名词;其二,艺术由大家闺秀变成了小家碧玉。
畅游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长河便是一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画面,例如阎立本官至朝散大夫,吴道子官至内教博士,苏轼进士及第,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这类例子举不胜举。这些画家均在朝廷贡职,都属于上流社会的精英人士。再反观古代西方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到美第奇家族的支持。美第奇家族起初是以金融业发家,后逐渐跻身名门,这个家族曾产生多名教皇和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等都是由他们赞助。
自工业革命开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出现变革。艺术家、艺术品再也不仅是上流社会与精英人士的专利了,大批的普通民众产生了自己的流行文化。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大批的农民放弃土地与牲畜涌向城市,变为无产者。工作时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闲暇时便逐步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艺术。例如波普艺术。
波普艺术即为“pop art”是“popular art”的简写,本意即是流行艺术。1956年汉密尔顿的一幅拼贴画《是什么使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魅力》中,第一次出现了“pop”这一词语。汉密尔顿为“波普”这个词下了定义,即:“流行的、转瞬即逝的、随意消耗的、廉价的、批量生产的、性感的、商业的①”。波普艺术是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使艺术品从价格昂贵的高端收藏品变成价格低廉的普通商品,消费群体扩大,使艺术品彻底变为了消费品。
波普艺术利用商业化的符号或现成品,批量生产,使艺术品更为贴近日常生活。安迪沃霍尔的《布洛里盒子》、《玛丽莲梦露》等就是利用商品包装盒、明星头像等现成品批量复制的作品。作品的内容通俗易懂,制作过程快捷便利,不存在任何技术性问题。沃霍尔所做的就是要消解艺术作为高雅与精英的传统,使艺术褪下高贵的外衣,简单明了的展现给大众,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企及。
追本溯源,将现成品变成为艺术品的鼻祖便是杜尚。杜尚用现成品所作的一系列作品,例如《L、H、O、O、Q》、《泉》等所强调的挪用、语境等观念,被其后的一大批人所模仿、跟风。杜尚本人对艺术所产生的诸多意义都具有创始性。第一次使用现成品(1914年《瓶架》),第一次将小便池搬入美术馆展览(《泉》),第一次以复制品参展(《L、H、O、O、Q》)等等。杜尚是一个争议颇多且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家,他给艺术史的发生与发展带来了诸多可能性,他犹如一位开拓者,去探索艺术的未知领域。
虽然杜尚与沃霍尔都选取现成品作为艺术品,但是杜尚的作品则属于精英艺术,沃霍尔则是流行艺术的代表。沃霍尔的作品所表述的意义,几乎是人人都看的懂,没有太多的深层含义,而杜尚的作品,关注的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更多是艺术品背后所产的思想、语境、场域等。
杜尚的《泉》所产生的含义不仅是一个小便池走进了美术馆,它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在西方社会中“泉”代有性暗示,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曾画过一幅美丽的裸女,命名为《泉》,杜尚选取男性用的小便器,为性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替代品;其次,当小便器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美术馆成为艺术品时,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成为艺术品的?杜尚拓宽了艺术品的概念,使艺术由原来的高贵性走向了普通,甚至低贱;第三,放在美术馆的小便器是艺术品,那在厕所的小便器是物品还是艺术品?这里凸显的是美术馆这一语境或场域。至今模仿杜尚的人多,真正理解杜尚的人少,杜尚是孤独的。
精英艺术所呈现的信息少而含蓄,需要接受者补充的信息多,发挥的想象力多,而流行艺术呈现的信息多而直白,让观者一看即懂。例如让民众同时欣赏两组雕塑,贾科梅蒂《行走的人》与《收租院》两件作品,贾科梅蒂的作品反应人因战争受到的伤害,《收租院》反应人民因地主压迫受到伤害,两件作品展现的都是人们受到的伤害。《收租院》直接将人们受伤害的过程以及结果原原本本的经过艺术化后呈现出来,以致于当时的民众参观完《收租院》后会泪流满面,因为他们直接的感受到了劳苦大众所受到的伤害。而贾科梅蒂是将人体做得纤细无力,他表现的不仅是变形的躯体,而且是心灵的空虚外化在直观肉体上的呈现,又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支撑,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注定是孤独无助的,包含有更多哲学化的深思。
因此《收租院》呈现的是结果,《行走的人》呈现的是思想。《收租院》所面向的观众属于普通大众,百姓在看《收租院》时不需要接受太多的美学教育和哲学熏陶,老少皆宜。《行走的人》是艺术家对整个社会深思后所发出的叹息。《收租院》讲了一个故事,为观众事先分解了艺术,免去了他们消化艺术的过程,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结果的捷径,从而绕开了对欣赏艺术来说十分困难的道路。就雕塑技法而言,对普通观众来说,并不熟悉,所以不重要,但在看《收租院》时看懂了一个故事,符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地主对普通百姓剥削的揭露,无论这是否是事实,至少符合大众思维里所存在的真实,因此民众更喜欢《收租院》,《收租院》是流行艺术或大众艺术,而《行走的人》是精英艺术。
当艺术褪下它神圣的光环时,艺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逐渐通俗化、大众化、流行化,呈现出消费性与娱乐性。但艺术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高贵性与先锋性。因此我们需要阳春白雪与阳阿薤露一起雅俗共赏。
注释:
① 斯皮尔伯利著,刘丽译.波普艺术.中国文联出版社
李万瑜(1992-),女,汉族,甘肃张掖人,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批评与展览。
C9
A
1671-1602(2016)20-01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