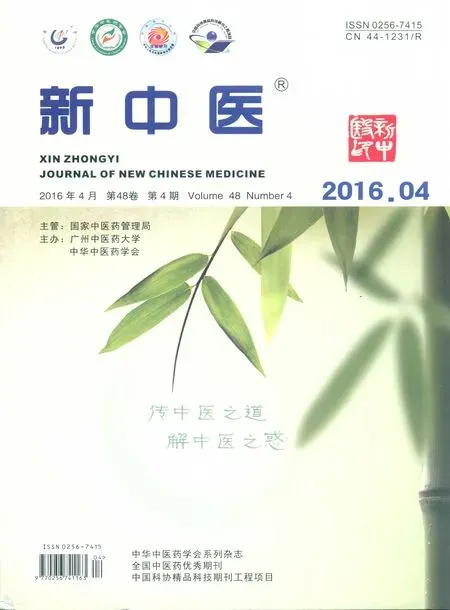针刺守形之难与解决之道
2016-02-21宋瑶林咸明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宋瑶,林咸明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针刺守形之难与解决之道
宋瑶,林咸明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针刺;守形;守神
《灵枢·九针十二原》言:“粗守形,上守神”,此语一出,“守神”即作为上工之道,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而“守形”则被视为粗工拙技,很少提及。明·马莳在《灵枢注》中更指出:“下工泥于形迹,徒守刺法;上工则守人之神。”直言守形即为一味追求刺法,拘泥表象不求甚解。然笔者认为,《内经》所言守形,不仅仅局限于针刺手法,还体现在守疾病之形与穴位之形,“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可见守形虽易陈而难入。笔者试结合临床,浅议针刺守形之难与解决之道,论述如下。
1 “守形”的含义
说文解字将“形”解释为“似,像也”,可知“形”有如雾里看花,似有若无,联系《内经》与针灸临床,可知此处之“形”,不仅仅局限于针之形,还包括病之形与穴之形,正是“形”之含义的复杂性使得守形“易陈而难入”。
1.1守病人之形《灵枢·行针》言“百姓之气血各不同形”,病人有高矮胖瘦之分,所谓肥人多痰湿,瘦人多虚火,更有形容枯槁时候大肉陷下之态。“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就此者,浅而疾之。”且病人之形又与五色、四时紧密联系,凡观五色之殊,当审四时之变。目黄身黄者多黄疸,面色青者多惊风,面苍白肺有疾,脸泛黑属肾水。若春伤于风,常见风邪犯肺之咳嗽与邪犯腠理肌表之瘙痒、面瘫;夏伤于暑,大汗淋漓之中暑病人偏多,而夏季又是人体阳气最旺之时,最适合“以热治寒”“冬病夏治”。若不顺应季节之变,夏刺肌肉,则血气内却;夏刺筋骨,则血气上逆;秋伤于湿,淋浊带下、头目昏沉;冬伤于寒,多发膝痹、腰痛等关节疾病。
此外,同一病人不同年龄段身体特点也不尽相同。《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八八,则齿发去。”《灵枢·逆顺肥瘦》中“年质壮大,血气充盈……深而留之。小儿肝常有余,而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而肺常不足,肾常不足”,皆表明从小儿时期“纯阴纯阳”“稚阴稚阳”之体到“肾气盛”“筋骨隆盛”之青壮年,以及“发鬓颁白”“形体皆极”的中老年,人体机能、形态由盛而衰,不断变化的病人之形也为临证时针灸处方的选择、调整造成难度。
1.2守疾病之形临证过程中,病人的主诉,疾病的表现各种各样。随着科技进步,检查手段和仪器层出不穷,检查报告连篇累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针灸医师对疾病本身的判断。而疾病本身又有“同病异证”与“异病同证”。同是牙疼齿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灵枢·杂病》)。又如薛雪于《湿热病篇》中谈及热病,虽“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但“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外感疾病亦是时刻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素问·热论》)。而单以头胀、头痛、苔黄、心烦易怒、弦脉、面红为主要表现的肝阳上亢一证,却可见于多种疾病,如更年期综合征、脑梗死和高血压病等。
疾病表现复杂加上检查手段繁多,易使诊断医生怵然慌乱,尤其是初入临床的年轻医生,常顾此失彼,或过于依赖各项检查结果,全盘西化,或不顾现代医学方法,对于诸如癌症等重大疾病,难免有漏诊、误诊风险。
1.3守穴之形《经络腧穴学》[1]指出:“腧穴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输注于躯体外部的特殊部位,也是疾病的反应点和针灸等治法的刺激点。”因腧穴“外络于肢节,内属于脏腑”的特点,使其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人体形态、脏腑生理病理状态而改变,有时甚至难以把握,正所谓“视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异所别也”。《灵枢·经水》谈到腧穴定位时如是描述:“夫经脉之大小,血之多少,肤之厚薄,肉之坚脆,及胭之大小,可为度量乎?岐伯答曰: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夫度之人,消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刺乎?审切循打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可见定穴之法,灵活多变,若不知机道,则叩之不发。而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孙思邈《千金翼方》云:“肉之大会为谷,小会为溪。丘、陵,言骨肉之高起者;髎,言其骨之空阔者;俞,言其气之传输……”《千金翼方》又论“穴名府者,神之所居;穴名门户者,深知所出入;穴名屋舍者,神之所安;穴名台者,神之所游观。”可以说,没有长时间反复的临床积累,很难理解溪、丘、陵、俞、府、舍等穴名之针义。腧穴之命名尚有深意,更勿提针刺入穴位之角度与深度,大都只可意会。虽《标幽赋》言“定刺象木,或斜或正”,《针灸大成》云“针阳经者,必卧其针……刺阴分者,必正立其针”,然至于“卧”“立”“斜”“正”之具体操作,却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需后人揣摩领悟。
1.4守针之形守针之形作为守形重点,一直颇受重视。就针具而言,早在《灵枢·官针》便已详细阐述“九针”及其适应症。“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在骨守骨,在筋守筋”,可见针有长短、刺有深浅。小儿及外籍人士较为敏感,多用细针甚至管针;陈伤久痹者针可稍粗;至于梅花针、粗针等,又有特殊操作手法,非一日之功。针具尚且复杂如此,更勿提持针之道。《灵枢·九针十二原》曰:“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者,刺之无殆。”明确持针要坚定而有力,“至其当发,间不容瞳”。
言及刺法与补泻手法,多变使然。仅关于刺法的论述,在《内经》中就有多种,如《素问·刺各执一言要论》说:“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刺皮无伤肉……刺肉无伤脉……刺脉无伤筋……刺筋无伤骨……刺骨无伤髓……”后世刺法的发展变化百出,有以左转为补者,有以右转为泄;有以午前午后分补泻者;有以阴阳经转向不同分补泻者;有以左右身分补泻者;有以男女左右分补泻者等等,莫衷一是,各执一言。还有“九刺”“十二刺”“五刺”等针刺方法,与“九针”呼应,即便是“徒守刺法”,也颇费工夫。若针刺手法不当,误刺损伤血脉、骨髓、内动五脏,又会进一步导致相应神志异常,“针伤筋膜、令人愕视失魂;伤血脉者,令人烦乱失神;伤骨髓者,令人呻吟失志;伤肌肉者,令人四肢不收失智;伤皮毛者,令人上气失魄,此五乱,因针所生”。至于补泻手法,时人体质娇弱,烧山火、透天凉、苍龟探穴、赤凤迎源等刺激性强的补泻古法,常不容易接受,这也对临床疗效及古典针法的传承提出了新的考验。
2 守形之难与解决之道
自《灵枢》起,“守形”一直被认为是指医生单纯重视刺法或固守人体外在之表现,与“守神”之高深相对,显得局限又浅显。如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将《灵枢·小针解》“粗守形者,守刺法也”解释为“守刺规矩之形,故粗”,其中“刺之规矩”即指针刺手法。明代张介宾也言“粗工守形迹之见在也”。但是由于“形”之复杂性、多样性,使得“守形”难以完全落实于临床诊治,影响疗效。笔者认为,守形虽难,却有一定规律可循,以针灸思维为指导,改进定穴用针之法,同时重视“神”对“形”的调节作用,便可形神皆备,化解守形之难题。
2.1守形需以针灸思维为指导针灸的思维模式根于中医思维模式,但又不完全一致,是中医思维模式的发展。如何在中西医并存的今天,发挥中医针灸的治疗优势,是每一位针灸医师所要思考的问题。正如温州娄绍昆先生言“以指示月,指并非月”,各项检查指标如同手指遮于眼前,而医者必须拨云见日,将临床检查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将中医与西方医学相结合。针灸之道尤是如此,一方面,骨骼、肌肉系统疾病是近年来针灸治疗的热点,在治疗此类疾病时,明确人体各肌肉、肌腱解剖位置、起止、损伤点后,有针对性地施以温针灸能促进损伤康复;另一方面,传统针灸理解中,肌肉、肌腱与古之“经筋”理论有相似之处,《灵枢》认为,经筋是十二经脉的附属部分,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络”于筋肉、关节的体现,具有联络四肢百骸、主司关节运动的作用。可见经筋与肌肉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为选穴提供了新的思路。
言及脏腑病,西医之化验单、检查单能为医者提供疾病的大致方向,客观地反映疾病特点,如肺结核、癌症等急需紧急治疗的疾病。就癌症而言,近年来西医也着重强调癌症治疗方案“个体化”,在规范治疗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特殊个体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这正与传统医学“辨证论治”不谋而合。明代医家汪石山指出:“既不识脉,又不察形,但问何病,便针何穴,以致误针成痼疾者有矣。间有获效,亦偶中。”见病只知病,大概便是所谓“下工”之表现。
且病邪入侵人体具有一定的经络规律性与时机性,是通过皮毛—孙脉—络脉—经脉而传及五脏,《素问·缪刺论》:“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极于五脏之次也。”提示治疗时根据不同时机疾病的传变而辨经论治,以望闻问切明辨病之经络,以察舌诊脉审察经络阴阳、表里、虚实,辨别病邪在于皮毛或已传变五脏,从而判断预后。正如《灵枢·终始》说:“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虽病人之病机与病情各异,然若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相结合,便能抓住疾病之本形,守住病之形。
2.2守形需改进定穴用针之法为了达到气至病所,临床上往往采取不同的针刺角度。如《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签尹所》说“转针向上气自上,转针向下气自下,转针向左气自左,转针向右气自右,徐推其针气自在,微引其针气自来。”即针尖的方向可以改变针感传导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林咸明教授[2]认为,针灸取穴定位还需注重“三维立体”,把握针刺角度和深度,如取风池穴治疗颈源性头痛和颈源性眩晕,前者的针刺方向宜朝向颈神经根方向,而后者则宜向寰枢椎之间的椎动脉沟附近进针。在针刺治疗肌腱炎、腱鞘炎等软组织粘连(或损伤)性疾病、疼痛性疾病时,同一个穴位,不同的针刺角度和深度,疗效就可能截然不同,需要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手巧而心审谛。
2.3守形需调神而治形神作为生之本,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内经》云“形神合一”“有诸内必形诸外”,可知“形”与“神”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守形不易,却可以通过治神调神得以形神俱守。狭义的“神”一般是指人体的精神情志,心主神明,脑为元神之府,二者失常,则神失守,病自心生。广义的神则指事物(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现代人由于工作繁忙,精神压力大,往往耗伤精气,损及心神、脑神,破坏了人体自身新陈代谢规律,阴阳失和,终诱发失眠、焦虑等情志疾病。在病理情况下,尤其是脏腑病、痛症患者,又常因痛不得眠,因病致郁,如此恶性循环,不断加重。因此,林咸明教授之调神针法提出,在积极治疗原发病的同时,提倡重视调节神志,以风府、天柱、安眠等枕项部穴位调脑神为先,开“四关”—合谷、太冲以镇静、调阴阳、和营卫,配合“安神六穴”,即耳穴心、肺、神门,体穴迎香、安眠、足三里宁五脏六腑,火旺者重视祛心、肝、胃之火,标本兼顾,神安形定而病自向愈。
3 守形与守神相结合
“形”与“神”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正如张景岳言:“形者神之本,神者形之用;无形则神无以生;无神则形不可活。”可见守形是守神之基,而守神又是守形之升华。针刺时,首先要掌握受病处“形”之表现,准确选穴施针,达到“医必以神,乃见其形,病必以神,气血乃行”,在此基础上,望于外且视于内,察病人体内经气之往来,“目明心开而志先”,神清而目明,一望便自知,则“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同时,针刺得气的感觉难以捉摸,“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素问·宝命全形论篇》)。医者唯有“属意病者,神属勿去”,仔细体会,神定后才能“知病存亡”。
至于患者之神,其心理状态对于疾病的康复也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若精神紧张,“空心恐怯,直立侧而多晕”,而患者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可“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将病之神、形与医之神、形结合,如《针灸大成》云,“医者之心,病者之心,与针相随上下,才能以神动气,以神调形,则病自除”。
自《内经》提出“粗守形,上守神”以来,医家普遍将守神视为重中之重。然与“形”之可见、可触及相比,“神”只可意会而难以捉摸。初学者若一味谈论“守神”,往往囫囵吞枣,难得真义。有经验的针灸医生常着眼于具体,临证施治,辨证定穴用针一气呵成。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完全掌握“守形”之法的基础上,方可由“形”升华至“神”,使“守神”精髓之义自现,水到渠成。
[1]沈雪勇.经络腧穴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8.
[2]林咸明.针灸学习中的三个误区[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3):404-405.
(责任编辑:骆欢欢)
R245.31
A
0256-7415(2016)04-0008-03
10.13457/j.cnki.jncm.2016.04.003
2015-11-05
宋瑶(1991-),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针灸治疗脑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