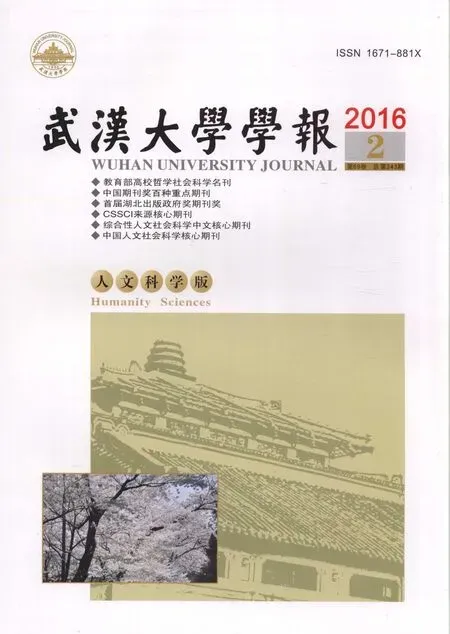馆阁与郎署——文学话语权的争夺与明代文学之流变
2016-02-20薛泉
薛 泉
馆阁与郎署——文学话语权的争夺与明代文学之流变
薛泉
摘要:明代成化、弘治以前,文学多为馆阁垄断,郎署官少有为之,他们与文学权力基本上是绝缘的。其后,郎署文学意识迅速觉醒,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前七子迅速崛起于文坛,明中叶主流文风为之转向,文权开始向郎署分化。“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既是郎署文学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又是前七子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明中期主流学术的转向密切相关,且有一过程。从中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把握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同时也表明,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更加便于推行、强化自己的文学主张。
关键词:郎署文学; 前七子; 明代文学; 文学与权力
前七子是明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迅速崛起于文坛,与当时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可以说,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前七子的兴起、主流文风的转向、文权向郎署的分化。“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中《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913页。,既是郎署文学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又是前七子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 馆阁的垄断与郎署官文学权力之绝缘
郎署,汉、唐时期指宿卫、侍从官员的公署。苏林曰:“郎署,上林中直卫之署。”*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爰盎传》张守节正义引,中华书局1959年,第2741页。颜师古称:“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郎署,并是郎官之曹局耳。”*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载《丛书集成新编》第38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524页。郎署,还可指代皇帝的宿卫、侍从官员。如李密《陈情表》:“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张铣注曰:“郎署,谓尚书郎。”*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第696页。至明代,郎署可指朝廷各部院分职治事的官署。如彭韶《郑教授墓志铭》:“癸酉,京闱得隽者四人,后累科益盛,郎署、谏垣多有居之。”*彭韶:《彭惠安集》卷四,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1页。吴宽《次韵沈主客种竹四首》其三:“坐深郞署下,碧色上衣来。”*吴宽:《匏庵家藏集》卷二,载《四部丛刊初编》本。明人也称在郎署任职的官员为郎署。如丘濬《金侍郎传》:“故事,霜降后会大臣审录重囚,必先召所属郎署,反复详审,有可矜疑者,必具录之。”*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二十,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第403页。李东阳《送吏部侍郎周先生使秦诗序》:“凡遣使……文臣之中,部属官比吏以下各一人,又必有侍从郎署以为之贰。”*李东阳:《文稿》卷九,载《李东阳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496页。所以,明人所谓的郎署,既指朝廷各部院分职治事的官署,又指在郎署任职的官员,后者又可称郎署官。本文兼顾两者之义。
台阁,汉时指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李贤注曰:“台阁,谓尚书也。”*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第1658页。因为尚书台在宫廷之内,故有是称。后来,台阁也泛指中央政府机构。明代所谓的台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台阁,主要指内阁。《明史·职官一》载:洪武十五年(1382),仿照宋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明成祖即位后,特选解缙、胡广、杨荣等人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因“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当时进入内阁的多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内阁不设属官,“不得专制诸司”。仁宗时,因杨士奇、杨荣为东宫旧臣,特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自此“阁职渐崇”,“阁权益重”*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2~1734页。。广义的台阁,则泛指馆阁。罗玘《馆阁寿诗序》云:“今言馆,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罗玘:《圭峰集》卷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第7页。罗氏所说的馆阁,除内阁之外,还包括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等机构。当然,内阁地位最为重要,为馆阁的核心机关。本文所谓台阁,取其广义,故多称馆阁。
成化、弘治以前,馆阁与郎署的职能分工,非常明确。李东阳《叶文庄公集序》称:“今论者无问可不可,文必归之翰林,政必推之法家。”*李东阳:《文稿》卷八,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479页。“法家”主要指在郎署分职治事的官员。储巏《赠少参吴君之官广西叙》称:“近世遂以政事属诸吏,文学属诸儒。”*储巏:《柴墟文集》卷六,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56页。储氏所谓的“儒”,主要指那些博古通今的思想家、政治家,自然包括精通文学的馆阁之臣;“吏”指直接处理政务的一般官员。大致说来,郎署主要“以法相视事”,即以政事为专职,基本上“不敢漫及他语”。馆阁则“以道德文字为事”:一方面,掌管草拟、撰写各类朝廷文书,应人之请代写碑、铭、传、记之类的应用文章;另一方面,又能“喜有庆,行有饯,周旋乎礼乐,而发越乎文章,倡和联属”*李东阳:《文稿》卷二《送翰林编修丁君归省诗序》,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397~398页。,撰写一些颂德、应制、唱和、应酬之类的作品。这里所谓的“文”,当然也包含一些非文学作品。郎署、馆阁职责分工之明确,其实是对郎署文学权力的一种合法性剥夺。也就是说,古文词赋在明初多为馆阁垄断,郎署根本上没有话语权。翰林诸官、内阁大臣,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文学权力的实际操控者。他们享受郎署官所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是天经地义之事。当时在翰林间就流传着这样的话语:“美阶崇秩,休光大业,当属之吾曹;诸先生他所游宦,为吾曹鹰犬耳。”*孙绪:《沙溪集》卷十三《无用闲谈》,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4册,第620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馆阁垄断文学的事实。
馆阁与郎署的分工,馆阁文权的垄断,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得到社会上普遍的认可。一般人以能求得馆阁大臣撰写的碑、铭、传、记之类的文章为荣,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罗玘《馆阁寿诗序》记载,当时所谓的大著作多出自馆阁。有身份的人如果要请人为自家亭、台、楼、阁作“记”、器物作“铭”,必定要到馆阁;请人撰文为祖先称颂功德、为亲人祝寿,必定要到馆阁。到馆阁求文的人,起初总是担心被拒绝;即使有幸为阁臣应承下来,还是顾虑重重,诚惶诚恐,不能确定所求之文最终能否拿到手。因为,毕竟有“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罗玘:《圭峰集》卷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第7页。
郎署、馆阁这一既定的分工,从文学权力的层面说,本来就是施加在郎署官身上的一种“符号暴力”。所谓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现实中,“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页。。郎署官对馆阁与郎署职能分工的认同就是如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定,文章是翰林的职事,并非自己的职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合谋”者以及这种分工的不合理性。同样如此,对这种分工,翰林官也是毫不谦让,受之无愧。赵贞吉《刘文简公文集后叙》有言:“闻长老言……是时诸司勤于案牍,止重吏事,至著作尽诿曰:此翰林事,非吾业。虽诸翰林亦曰:文章吾职也,而不让。”*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5页。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入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赵氏生于正德三年(1507),卒于万历四年(1576),其所“闻长老言”,当主要是指成化、弘治以前的情状。崔铣《漫记》就称:“弘治以前,士攻举业,仕则精法律,勤职事,鲜有博览能文者。”*崔铣:《洹词》卷十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636页。也就说,由于分工的明确、馆阁的垄断,郎署官少有人能从事文学创作,更别说拥有文学话语权了。何乔远《文苑记·李梦阳》就说:“明兴,词赋之业馆阁专之,诸曹郎皆尠习。”*何乔远:《名山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59页。再说,由于职事繁杂,成化、弘治前的郎署官,即使想从事文学创作,也少有余力,无暇兼顾。吴宽《公余韵语序》即云:“士大夫以政事为职者……盖勤于政事如此,又何暇于文词之习哉?”吴宽,成化八年(1472)状元,弘治八年(1495)升吏部右侍郞。出身于翰林的吴宽,任职吏部后,旧习未忘,欲旧业重操,从事文学创作,但因公务繁忙而无暇顾及。即使有闲暇,因无创作氛围,也是“兴致索然,执笔辄废,或终日不能成章”*吴宽:《匏庵家藏集》卷四十二,载《四部丛刊初编》本。。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实际上,当时郎署官即便是有充足的时间、过剩的精力,一般也是不敢公开从事文学创作的,否则会被视为越位、不务正业,从而招致诸多非议。李梦阳从事古文词创作就曾遭到馆阁诸公的无情嘲笑:“此火居者耳。”*何乔远:《名山藏》,第5259页。火居者,就是佛家所说的“优婆塞”。信奉佛道的世俗之人,男的称“优婆塞”,女的叫“优婆夷”。讥讽之意,溢于言表。清人毛奇龄便直言道:“故事,馆阁习文翰,梦阳以诸郎倡起,号召为诗古文词,馆阁笑之。”*毛奇龄:《西河集》卷八十一《列朝备传》,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741页。说到底,个别郎署官这种既欲从事文学创作,又心存顾虑不敢公开为之的矛盾心态,实是馆阁垄断文学的一种社会普化反映。
综上所述,由于馆阁的文学垄断以及郎署官对这种垄断行为的认同,成化、弘治以前的郎署官是没有文学话语权的。从整体上看,他们与文学权力基本上是绝缘的。
二、 郎署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文学话语权的争夺
馆阁臣僚对文学的垄断,很大程度上造成郎署官在学术、文学上的缺失,以至影响到为政。李东阳认为,从政者应该以经史为根基,饰之以才艺,资之以议论,而振之以气节。然而,由于郎署与馆阁的职能分工,文学专属馆阁,郎署官“往往不得以尽其用,用之不尽,乃或从而短之”。他认定,这不是礼遇天下士人之道,“怀此论久矣”*李东阳:《文稿》卷三《送张君汝弼知南安诗序》,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414~415页。,试图有所改变。李东阳一针见血地指出:“今论者无问可不可,文必归之翰林,政必推之法家。”认为持论如此,不容不加以明辨。如果既能持法守律,又能以经籍为根基,以文章为修饰,为政效果会更佳,为天下人所重,并“非人之所难”*李东阳:《文稿》卷八《叶文庄公集序》,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479~480页。。李东阳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必归之翰林”,而是从为政的角度,主张郎署官可适当从事文学活动,以有益于为政。这两篇文章收在《文稿》中,此稿为李东阳“在翰林时作”*杨一清:《怀麓堂稿序》,载《李东阳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2页。。李东阳为天顺八年(1464)进士,弘治七年(1494)八月,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管内阁诰敕*钱振民:《李东阳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因此,至迟弘治七年(1494)前,李东阳就持此论。同样有翰林背景、辈分稍早的岳正,对儒、吏之分也心怀不满。他认为,儒、吏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本来就是可以互补的:“资儒以为吏,斯可矣。”*岳正:《类博稿》卷五《赠和振纲刑部主事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6册,第396页。岳正卒于成化八年(1472)*李东阳:《文稿》卷二十九《外姑宋夫人墓志铭》,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776页。,故最迟此时,他已不满儒吏之分,主张“资儒以为吏”。无论这些言论出于何种目的,客观上都为郎署官可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成化末年,特别是孝宗即位后,优礼文臣,右文尚儒,郎署文学意识迅速觉醒。郎署官开始不满馆阁的文化垄断行为,自觉、主动地倡导、从事文学活动。储巏称:“文学、政事,君子未尝歧而二之”,近世将政事归属于吏,文学归属于儒,并非“覈到之论”*储巏:《柴墟文集》卷六《赠少参吴君之官广西叙》,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第456页。。储巏(1457-1513),字静夫,成化二十年(1484)状元,除南京吏部主事。他对儒、吏之分颇为质疑。他认为,郎署也应有相应的文学、学术修养,应该从事文学活动,文学不应仅是馆阁的专利。故而,他自觉、主动地从事文学创作。
在这种时代氛围与先觉者的濡染下,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为代表的一批后起郎署官,文学意识也随之迅速觉醒,开始倡导、从事文学活动,郎署文学逐渐呈现出活跃的局面。顾璘称:自成化、弘治间,“质文始备”,文学虽然还是“翰苑专门”,但是郎署已渐成气候,实力不容轻觑。其在台省者,起初有邵宝、储巏等开启门户。自此以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朱应登,“岳立宇内,发愤覃精,力绍正宗”,其文已脱却近习,“卓然以秦、汉为法”;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顾氏还称赞郎署官有振兴一代文风之功绩:“郁兴一代之体,功亦伟乎!”*顾璘:《凌溪朱先生墓碑》,载朱应登:《凌溪先生集》卷十八,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第497页。毛奇龄也道:文学活动本应是馆阁的专利,身为郎署官的李梦阳,竟然打破游戏规则,“号召为诗古文词”*毛奇龄:《西河集》卷八十一《列朝备传》,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741页。,并且能得到何景明、边贡、徐祯卿、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人积极响应。可见,郎署官是非常渴望从事文学活动的,并且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投身于文学活动之中。李梦阳早就指出:“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当时他任职郎署,与其倡和的有扬州储巏、赵鹤,无锡钱荣、陈嘉言、秦金,太原乔宇,宜兴杭济、杭淮兄弟,郴州李永敷、何孟春,慈溪杨子器,余姚王守仁,济南边贡等。其后,又有丹阳殷鏊,苏州都穆、徐祯卿,信阳何景明等。在南京,则以顾璘、朱应登最为活跃。“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五十八《朝正倡和诗跋》,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671~1672页。。很显然,李梦阳将当时参与倡和的文人分为两大阵营:郎署与翰林。在他看来,郎署已成为文坛的新生力量。“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这不简单是个“不叙”的问题,其中隐含着他对馆阁垄断文权的不满。
此时,郎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宣传其文学主张,以群体力量从事文学活动,与馆阁争夺文化资本与文学话语权,从而谋得合法性与社会认同。何良俊就称:“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间可谓极盛。李空同、何大复、康浒西、边华泉、徐昌穀,一时共相推毂,倡复古道。”*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35页。也就是说,在弘治、正德间,李梦阳等人相互唱和、共同提携,以群体之力亮相于文坛,其影响力、社会认同度不断提升。据孟洋记载,当时,李梦阳、边贡“以文章雄视都邑”,何景明前去拜访,情趣相投,于是三人开始致力于转变文风。孟洋认为,弘治十五年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等人的倡和,已引发了当时主流文风的转向:“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趋风秦、汉矣。”*孟洋:《孟有涯集》卷十七《中顺大夫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何君墓志铭》,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8册,第282页。康海则进一步加速、强化了这一转向。弘治十五年(1502),康海来京应试。当时正是孝宗皇帝“拔奇抡才,右文兴治”之时,他厌恶“一时为文之陋”,渴求真才雅士。看到康海的应试文章,他倍感欣喜,便对辅臣道:“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于是钦点康海为状元。因为得到孝宗的褒扬,康海的文章引起文人竞相效仿,于是“文体为之一变”*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载张时彻:《皇明文范》卷五十三,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3册,第475页。。可知,康海在进入翰林院前,其文风已迥异于馆阁。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郎署文学意识的浸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也正因如此,有着翰林背景的王九思,文风才发生转向。王九思,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为庶吉士,他自称:在翰林院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王九思:《渼陂集》卷首《渼陂集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3页。。也就是说,王九思诗文起初是学习台阁体的,后来在康海、李梦阳的引导下,改弦易辙,掊击台阁体。至此,前七子的文学影响力、社会认同度进一步增大。
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郭正域所撰《苍霞草序》称:“世之拟古文者,遂不胜其凌厉谇语,大略用汉人、唐人以胜宋人,合诸缙绅暨诸草泽,以胜词林。”*叶向高:《苍霞草》卷首,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页。主要说的是前七子以“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文学主张,对抗台阁,崛起于文坛。这一主张,也是郎署文学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万历三十三年(1605),王图《槐野先生存笥稿序》道:“而士大夫不在馆阁及布衣之雄,率乞灵秦、汉人口吻,与词林争胜。”*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首,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也是针对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官而言。他们以秦汉为宗,积极主动地宣传、推销自家文学主张,刻意倡导一种与台阁有别的文风,以争胜于词林,这是他们为争夺文化资本、文学话语权而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因此引起了馆阁大老的不满。据李梦阳《凌溪先生墓志铭》,朱应登与“江东三才”(顾璘、刘麟、徐祯卿)并驾齐驱,很多文士乐于与之结交,“而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于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五,第1281~1282页。。这虽是李梦阳追忆前事所为,但也是事发时心声的自然流露。他借朱应登的遭遇发泄对馆阁的不满,颇有迁怒之嫌。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靳贵:《戒庵文集》卷六《怀麓堂文集后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5册,第522页。,李梦阳所谓的“柄文者”自然主要指他。陈田就指明:“柄文者谓茶陵也。”*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36页。康海中状元后,以翰林庶吉士身份加入郎署官倡和之列,对抗台阁体,与馆阁争夺文学话语权,更是引起阁臣的强烈反感。当时,李东阳执掌文柄,一时为文者,多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康海却不模效,并与王九思、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组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这实是对台阁体的不敬与鄙视,阁臣对此殊为不满。由“益大衔之”*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载张时彻:《皇明文范》卷五十三,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3册,第476页。见出李东阳等台阁大老对其不满时日已久,且程度在不断加深。
康海丧母后,其与馆阁争夺文学话语权的行为更具威力。据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正德三年(1508),康海丁母忧,他打破当时惯例,请李梦阳撰写墓表,段德光作传,而“不求内阁文”。这严重冒犯了阁臣的权威,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为此,李东阳极其不满,因康海等人为文多称“子”字,故称其文为“子字股”*张时彻:《皇明文范》卷五十三,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3册,第476页。。当时“大衔之”者,并非李东阳一人。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也记载此事:康海自述行状,请二三友人、门生撰写墓表碑传,并刊刻成集,题名为“康长公世行叙述”。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将其“遍送馆阁诸公,诸公见之,无弗怪且怒者”*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中,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911~912页。,这无疑是向馆阁大佬公开叫板。可见,康海等人的行为,已对台阁造成不小的冲击。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茶陵派分道扬镳。这也成为康海、李梦阳等人日后落职、蒙受打击的由头。王九思称,当时李东阳为内阁重臣,平日妒恨康海,趁机“落公为民”*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中《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第912页。。何良俊也称,康海丧母后,请李梦阳作墓碑,王九思、段德光作墓志与传。李东阳闻知后大为不平,于是借刘瑾事件做文章,康海“遂落籍”*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第126页。。前七子得罪阁臣,双方文学主张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胡缵宗就说:弘治间,李梦阳“谓诗必宗杜甫”,康海“谓文必祖马、迁而下”,学士大夫多靡然从之,二人因此得罪了李东阳等“世之君子”*胡缵宗:《西玄诗集叙》,载马汝骥:《西玄诗集》卷首,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3册,第654页。。也就是说,李梦阳、康海等人以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与馆阁争夺文化资本与文学话语权,最终得罪了馆阁重臣。李梦阳、康海等人也因此与李东阳茶陵派彻底决裂,自立门庭。周亮工《孙高阳先生全集序》云:“文章一道,自宋以来,权归馆阁”,即使李梦阳等人“极力争之,而终不能胜。但其流为舂容蔓衍,总不脱宋人气习”*孙承宗:《高阳集》卷首,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4册,第12页。。平心而论,周氏之论并不客观。实际上,前七子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绩迅速崛起于文坛,直接导致当时主流文风转向,已脱却宋人“气习”。这一转向,标志着文权开始由馆阁向郎署分化。陆树声《中江先生全集序》指出:当时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讨论秦、汉,扬扢风雅,执牛耳以凌厉词坛,宇内谭艺士率向往之”*莫如忠:《崇兰馆集》卷首,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4册,第376页。。这实际上已经暗示出成化、弘治以降,文权开始向郎署分化,而且出现倾斜的趋势。郭正域《苍霞草序》称:“往者王司寇遗余书:‘文章之权,原在台阁,后稍旁落。’”*叶向高:《苍霞草》卷首,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第5页。王司寇,即王世贞。他已指出当时文权开始旁落的现象。陈田则明确指出:“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35页。陈氏所言有些武断,王世贞“稍旁落”的话语更准确些。客观地说,此时文权已开始向郎署分化,甚至有倾斜趋势;至嘉靖、隆庆、万历间,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文权逐渐下移至郎署。黄道周《漳浦集》即云:“嘉靖初年,议臣鸷起,文章之道散于曹僚,王弇州、李历下为之归墟。”*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二十二,第2659页。隆庆二年(1568)进士于慎行《海岳山房存稿叙》称:“今世言文章者,多谓此道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第2442页。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汪道昆《翏翏集序》云:“大方家有言:当世之诗盛矣,顾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五,载《续修四库全书》1347册,第97页。俞安期《愍知》诗序曰:“自丁丑纳交……甫五年……是时,弇州王公与公论文,慨我明斯道,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俞安期:《翏翏集》卷一,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3册,第12~13页。丁丑,即万历五年(1577)。这实际上已承认,文权已在郎署。
可以说,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前七子迅速崛起于明中叶的文坛,当时主流文风宗尚为之转向、文权已开始向郎署分化。而文风转向、文权分化与“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主张的提出直接相关。
三、 前七子的崛起与“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提出
“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文学主张,既是郎署文学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也是前七子迅速崛起于文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明中叶主流学术转向密切相关,且有一过程。
从总体上看,成化、弘治以前,明代主流学术思想基本上是程朱理学的天下。此时,文学创作上,文多模仿欧、曾,很少有人效法先秦、两汉;诗歌多法盛唐。成化、弘治以来,由于政治危机不断加剧、程朱理学日趋僵化、陈献章学术思想勃兴,明代主流学术思想开始转型。明人的思想与审美情趣也随之发生变化,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求新求变的意识日渐浓郁。特别是“成化以后,学者多肆其胸臆,以为自得”*黄佐:《翰林记》卷十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第982页。。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就是这一主流学术思想浸润下的产物。表现在文学上,文人更加崇尚博学,喜欢猎奇,追逐新异,为诗作文不再限于法唐宗宋,不少人已将目光溯至六朝、汉魏、先秦。于是,文坛上出现诸调杂陈的格局。
从古文层面来看,到明中期,取法欧、曾为文时日已长,各种类型的弊病积聚已多。正如李东阳《叶文庄公集序》所言:“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余,而先陷于缓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尔见缕。”*李东阳:《文稿》卷八,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479页。李东阳已清醒地意识到学欧、曾产生的弊端,并有意识地加以变革。受前人启发,他较早谈及先秦、两汉古文。如《曾文定公祠堂记》云:“古之所谓著述者,自六经迄于孟氏。若韩子不免为词章之文,而所谓翼道禆治,则有不可掩也。”*李东阳:《文稿》卷十二,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535页。在《篁墩文集序》一文中,他从为政的角度,已意识到先秦、两汉古文的重要性。另外,他还宣称“班生世有汉文章”*李东阳:《诗稿》卷十八《送杨志仁宪副之山东》,载《李东阳集》第1册,第328页。、“两都风物汉文章”*李东阳:《诗后稿》卷七《石学士珤之任南京》,载《李东阳集》第2册,第886页。。尽管如此,在其古文统系中,韩、欧、朱文仍是为文之圭臬。身为台阁重臣,他没能以秦汉文风彻底变革台阁体,其文依然是台阁体的延续。不过,此时已有人将目光正式投至先秦、两汉古文,以纠补学唐宗宋所造成的“细弱”之病。王鏊为文“必先秦两汉为法”*文征明:《文徵明集》卷二十八《太傅王文恪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64页。,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弥补、纠正时人学欧、苏产生的流弊。王鏊卒于“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文征明:《文徵明集》卷二十八《太傅王文恪公传》,第661页。,故其为文“必先秦两汉为法”,有可能在七子之前。黄佐就言之凿凿:“成化中,学士王鏊以《左传》体裁倡。弘治末年,修撰康海辈以先秦、两汉倡,稍有和者,文体盖至是三变矣。”*黄佐:《翰林记》卷十九,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第1073页。陆釴称张泰,为文“直欲追两汉、先秦以上”。张泰,成化十六年(1480)升任修撰,月余后“得暴疾,呕血数升而卒”*陆釴:《大明故翰林院修撰张亨甫先生墓志铭》,载张泰:《沧洲集》附录,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册,第636页。。其为文“直欲追两汉、先秦以上”,必在此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泰、王鏊实已开前七子“文必先秦、两汉”之先声。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林俊倡言:写作古文必须削去近习,“专志六经、鲁论,翼以孟氏书,参以《榖梁》《国语》《离骚》《史记》,以集文章之大成”*林俊:《见素集》卷一《两汉书疏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7册,第10页。。至此,“文必先秦、两汉”之说已呼之欲出。不仅如此,为纠补古文学唐宋所生的流弊,还有人开始从事先秦、两汉典籍的刊刻与宣传。钱福即有言:当今承平已久,文章炽兴,“有识者或病其过于细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汉之佚书而梓之”*钱福:《钱太史鹤滩稿》卷三《陆贾新语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6册,第135页。。据何景明记载,孙继芳曾经从他论学,“尝索古书无刻本者以传”。何景明告诉他:“古书自六经下,先秦两汉之文,其刻而传者,亦足读之矣。”*何景明:《何大复集》卷三十四《海叟集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95页。这样,一些先前不太被重视,甚至是有违正统的先秦、两汉典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刊行于世。前七子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先秦、两汉典籍的宣传与刊刻中。《战国策》的刊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战国策》所载,多是当时谋臣策士的倾危之术。汉代只有司马迁、班固、刘向研究过它,从唐代到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都有所忌讳,不敢明言。一旦有人谈论苏秦、张仪之说,就会被视为“魍魉魑魅”。故而,该书一直无善本流传。到弘治、正德年间,“乃刻于大梁,而李献吉序之,为始显。近刻于金陵,为再显”*穆文熙:《七雄策纂序》,载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一十二,第2130页。。《战国策》因李梦阳作序而流传益广,尽管李梦阳宣称:“予读《战国策》,而知经之难明也。”*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刻战国策序》,第1415页。当时秦、汉思潮涌动的势头不言而明。可惜的是,李东阳没能以之彻底变革台阁体。而前七子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先机,在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倡导“文必先秦、两汉”。
从诗歌层面而论,当时诗坛是诸调杂陈。为诗宗法汉、魏、晋、盛唐者有之,甚至这几者集于一人之身,如张琦“古诗祖汉、晋,律诗祖盛唐,而参以赵宋诸家之体”*林俊:《见素集》卷五《白斋诗集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7册,第46页。。但此时以秦、汉为法者并不多见:“学者一二,或谈汉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无疑异其间。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何景明:《何大复集》卷三十四《汉魏诗集序》,第593页。师法中晚唐、宋、元诗者,也有之。李东阳为诗就“出入宋、元,溯流唐代”*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第7307页。。胡应麟总括当时诗坛宗尚为:“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兴。”*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45页。朱彝尊亦云:“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60页。这就是说,至成化、弘治时,诗坛已呈现取法多端的局势。从整体上看,还是唐、宋调相杂为主流,恰如李梦阳评论杨一清诗所云:“唐、宋调杂,今古格混。”*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六十二《奉邃庵先生书》其七,第1775页。这主要是为了纠正学盛唐之弊。明代自高棅倡导诗法盛唐以来,“学者终身钻研,吐语相协,不过得唐人之一支耳”*桑悦:《跋唐诗品汇》,载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一十二,第2127页。,极易导致雷同。况且,宗法盛唐时日一长,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流于卑弱。因此,不少文士有意求新求变,另寻路径。汉魏、六朝、中晚唐、宋、元诗,家数众多,风格多样,选择师法对象的余地相对较大,避免雷同也就容易些,有人趋而从之也是自然之理。学宋本是为纠正宗唐所导致的“空疏卑弱,熟软枯淡”,然而依旧收效甚微,也是流弊迭出。吴宽所言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问题之根本。模仿他人作品,终极目标应是铸就自家风格。若仅停留在机械模拟层面,以求其似,无论学唐还是宗宋,都会流弊丛生。为了纠正当时诗坛诸调杂陈、汉魏盛唐之音沉寂不显的情势,前七子在“学者一二,或谈汉魏,然非心知其意”的基础上,重申以汉魏、盛唐为宗,并以其鲜明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绩,确立起一种新的诗风。
前七子对自己转变文风之举甚为自得。康海《渼陂先生集序》称:“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六人即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王廷相、徐祯卿、边贡,再加上康海本人,是为前七子。康海认定,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引发了当时主流文风的转向:“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康海:《对山文集》卷三,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23~124页。乔宁《何先生传》也称:弘、正间,何景明与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边贡一起“始一变趋古,其文类《国策》、《史记》,诗类汉魏盛唐。于是明兴诗文,足起千载之衰,而何、李最为大家,今学士家称曰‘何李’,或称曰‘李何’,屹然一代山斗云”*何景明:《何大复集》附录,第667页。。乔氏之论虽有过誉之嫌,但毕竟点出了以何、李为代表的前七子转变文风的事实。《四库全书总目·古城集》亦言:“北地、信阳之说兴,而文章亦一变。”*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1494页。概而言之,前七子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倡导了一种新文风:即古文由墨守欧、曾,转向以先秦、两汉为宗;诗歌由诸调杂陈,转至以汉魏、盛唐为法。
从上文不难看出,前七子转变文风也是文学自身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四、 结语
郎署文学意识觉醒背景下前七子的崛起过程,实质上就是郎署与馆阁争夺文学话语权的过程。前七子以“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策略与馆阁争夺文学话语权,使文学权力突破馆阁的垄断与封锁,开始向郎署分化,并逐渐朝着有利于郎署的方向倾斜,同时也使这一主张得以进一步强化,从而引发了主流文风的转向。文学话语权,作为权力的一种,其作用与意义在此得以凸显。换言之,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更加便于推行、强化自己的主张。再说,文学权力与政治权力并非互不相干。馆阁垄断文权,以合法的形式剥夺郎署的文学权力,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馆阁的这种文学权力本就具有政治权力的某些性质。况且,馆阁重臣本身就是文学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双重拥有者。文学话语权的争夺,时常会超出文学本身,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甚至裂变成政治排挤和人身攻击。尤其是那些双重权力的拥有者,为维护既得利益,在行使文学权力的同时,他们往往还动用政治权力排斥异己。李东阳对康海、王九思等人的打压就是鲜活的明证。前七子也难以免俗,他们位卑身轻,为回击馆阁重臣的文学压迫与政治迫害而流于人身攻击。如王九思,为宣泄一己之愤,作《杜甫游春》杂剧,以李林甫来影射、攻击李东阳。李梦阳也心怀怨恨,甚至在李东阳去世后仍然余恨未已,以朱应登的遭遇为借口,将“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五《凌溪先生墓志铭》,第1282页。归罪于李东阳,显然有些过激,有人身攻击意味。另外,前七子与馆阁文学话语权的争夺,不单是文学观点相左的问题,还是两种不同类型人格冲突的一种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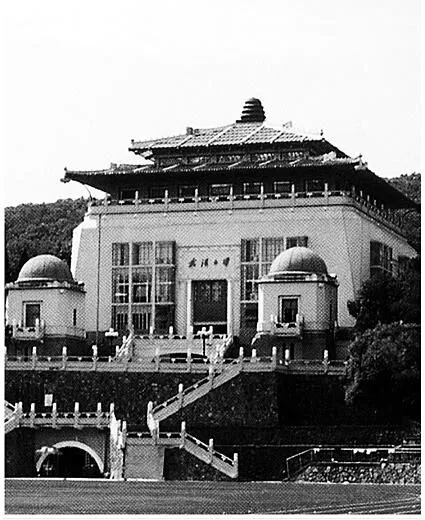
The Group of Civil Government andLangshu(郎署)——Competing for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Changes of Literature in Ming Dynasty
XueQuan(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t was not until Chenghua(成化) and Hongzhi(弘治) period of Ming Dynasty, officials were offered opportunities to do literary creations of which they had been long deprived before due to the cultural monopoly of Hanlin(翰林) Forum and Cabinet composers. With the awakening of the Langshu(郞署) Officials’ literary awareness, Qianqizi(前七子) soon became prominent in the literary arena, shifting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trend of the Mid-Ming Dynasty and diverging literary right to the official. “Prose being of Qin-Han style, and poem of Han, Wei, and Tang style” shows not only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the awakening of Langshu(郞署)Official literary awareness but also one of primary factors for the booming of Qianqizi(前七子). The proposal of this literary standpoi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trend of Ming Dynasty and endures a period of development, from which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nd grasp some features and regularities of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M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hows that who has the right of speech, who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to implement and strengthen their own literary ideas.
Key words:Langshu(郞署) Official literature; Qianqizi(前七子); literature of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and power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2.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ZW064)
●作者地址:薛泉,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口 海南 571158。Email:xuequan7169@ sina.com。
●责任编辑:涂文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