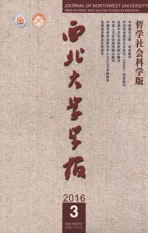叙利亚阿萨德时期威权主义与政治稳定探析
2016-02-20王新刚
王新刚,马 帅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历史研究】
叙利亚阿萨德时期威权主义与政治稳定探析
王新刚,马帅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1970年后叙利亚在阿萨德领导下,重树政治威权及其政治合法性,重建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借助意识形态控制以及务实的内外政策,实现了长达30年的政治稳定。但是,在阿萨德威权主义统治下,由于政治民主缺失,经济发展迟缓,阿拉维宗派主义专权以及地缘政治环境险恶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叙利亚又成为一个稳中有忧的国家。
关键词:阿萨德; 威权主义;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宗派主义;地缘政治
叙利亚在“阿萨德上台之前,20年间政坛几乎每年都在政变,统治者自身难保,国家饱受大国与强邻干涉欺压”[1]。1970年11月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上台执政后重建政治威权及其政治合法性,叙利亚摆脱了动荡的“普力夺社会”*普力夺社会,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仅军人干政,而且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详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 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版,第175-181页。,实现了长达30年的政治稳定。但是阿萨德构建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真正解决叙利亚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等矛盾,反而在建构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埋下了新的隐患。因此,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又成为一个“稳中有忧”的国家。
一、叙利亚威权政治及其内在结构
1970年11月13日至16日,阿萨德发动不流血政变登台执政。为了巩固政权,阿萨德上台后,通过重塑政治权威及其政治合法性,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该体制最大特点是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权的中坚力量是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及行政官僚机构,即所谓“三大支柱”。人民议会、全国进步阵线、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则作为阿萨德权力结构的辅助机制,满足政权对社会成员的整合和控制。
(一)总统集团
阿萨德于1971年当选总统,同年当选复兴党总书记并在此后连任,直至2000年病逝一直都是历次总统选举的唯一当选人,并始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73年宪法赋予总统行政、军事、立法、外交等方面的绝对权力。除了宪法赋予总统的广泛职权外,阿萨德作为复兴党领袖同时兼任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及地区委员会总书记,并且担任政治协商组织——全国进步阵线主席。由此可见,阿萨德实际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凌驾于“三大支柱”之上,牢牢占据着权力的顶端。
另一方面,现实政治运作中,阿萨德的周围还有一个由其家族势力及亲信下属组成的小集团,与总统共同形成一个权力中心,利用并凌驾于军队、复兴党和行政机构之上实行统治。这个亲信集团称为“贾马阿”*贾马阿,阿拉伯语意为“集团”。详见[以]摩西·马奥茨著, 殷罡等译:《阿萨德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该亲信集团忠诚团结,对阿萨德言听计从,贯彻执行阿萨德的所有重要决策。
(二)三大支柱
阿萨德为确保一党制总统威权体制下的政治秩序,构筑了庞大且忠诚于政权的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及其行政官僚机构,并将其转变为阿萨德统治下的三大权力支柱。
第一,军事安全机构。军事安全机构是阿萨德体制最忠诚且最主要的捍卫者,它由军队、警察宪兵和安全情报等部门构成,规模庞大且自成体系,并主要由阿萨德的近亲,或来自阿萨德所属的马塔维拉部落家族成员指挥。这一体系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镇压反政府力量及巩固阿萨德个人权力的重任,是叙利亚国家与阿萨德政权的重要支柱。第二,复兴党组织机构。1973年宪法第八条规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2](P467)。复兴党拥有众多的党员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纲领就是国家的主导思想与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机构发挥着凝聚精英、调控权力和整合社会的重要职能。政府、军队的要害部门均由复兴党党员担任领导职务,而且主要社会团体如工会、商会、妇联、各类行业联合会及高等院校的负责人也均由党员出任。第三,行政官僚机构。在总统高度垄断权力的体制下,叙利亚国家行政官僚机构的实权相对较小。尽管如此,其作用和地位亦不容忽视。除了行使行政与社会管理职能外,官僚机构重要作用体现在控制、整合社会、吸纳中产阶级,维护政权统治。
(三)辅助机制
人民议会、全国进步阵线、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是阿萨德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改革的结果,虽然这些机构组织处于威权体制下,但是它们的存在使阿萨德政权有别于此前的军人独裁统治,并且扩大了政权基础。
第一,人民议会。1973年宪法确认人民议会是国家立法机关。其职能是:提名总统人选、通过法律、讨论内阁政策、接受和批准议员辞呈、撤销对内阁成员的信任、通过国家预算与发展计划、批准有关国家安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等[3](P251)。然而,人民议会处于政治决策的边缘,没有真正的立法权,仅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尽管如此,议会在维护阿萨德政权合法性、扩大政治参与方面仍发挥着难以替代的政治功能。第二,全国进步阵线。它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协商机构,是联系全国所有政治力量的重要平台。全国进步阵线名义上是为了增强进步力量之间最大限度的团结,以共同对抗犹太复国主义,但实际上旨在笼络控制其他政党,孤立复兴党的敌对势力,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第三,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叙利亚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数量众多,均在执政党控制之下,为半官方或半政府机构。“除了工会,这些组织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它们被设立是为确保政权从上到下对社会的控制。”[4](P10)
阿萨德正是通过构建一整套独特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同时借助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务实的内外政策等实现了叙利亚国家政治的稳定。
二、叙利亚威权主义与政治稳定的构建
(一)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有效性
“威权主义政体是介于民主政治和专制体制之间一种较为温和的过渡形式。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政治选择,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社会秩序,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之目的。”[5](P7)阿萨德政权之所以能长治久安,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力集中。阿萨德执政前叙利亚是典型的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多元分裂社会,权力支离破碎,权威衰朽缺失。在这一环境中,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或争夺更多的利益而展开角逐。在此背景下,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才能树立起政府威信,建立强大国家。“现代化通常不仅需要将权力从地方的、贵族的和宗教的集团手中转到世俗的中央国家机构中,而且需要将权威集中到国家机构中的某一个人手中。”[5](P142)一方面,阿萨德通过合法的权力体系树立个人威权,维护政治稳定,无论是宪法还是复兴党纲领以及全国进步阵线章程都从国家层面奠定了阿萨德高度专权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超凡的人格魅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阿萨德家族势力及亲信集团,以阿拉维少数派人士为主体,建立起以他为核心的权力体系,确保其统治地位的稳固。
第二,强化政府能力。亨廷顿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建设一个具备强大能力的政府是维持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6](P1)在阿萨德体制下,以阿萨德为核心的总统集团牢牢居于权力的中心,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和行政官僚机构则构成政权的三大支柱,它们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构筑起强大的政府,有效地控制着政治权力,约束着政治冲突,维持着政治稳定。
第三,吸纳社会力量。阿萨德体制下,人民议会通过议席的分配满足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参政需求,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全国进步阵线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协商机构,将其他具备政治能量的政党笼络到复兴党控制之下,巧妙地将党派冲突转化为执政党内部矛盾。各类社会团体及群众组织实际上是国家机器的延伸和扩大,满足政权对社会的控制。阿萨德时代的辅助机构发挥了吸纳社会力量的功能,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的积极因素。
(二)意识形态的统一
阿萨德上台后,大力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用统一的意识形态构建国家认同,建立政权合法性。
第一,意识形态为政权合法性的塑造提供了理论支持。复兴党的复兴社会主义理论将“阿拉伯统一”思想置于首位。而多年来阿萨德一直沉浸在“阿拉伯统一”的梦想中,并且凭借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名正言顺地控制着权力和国家。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以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作指导而建立的,阿萨德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阿拉伯复兴主义理论之上[7](P25)。
第二,意识形态有助于促进政教关系的平衡。在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阿拉伯社会,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不能脱离其固有的文化环境。复兴社会主义强调它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尽可能在伊斯兰文化价值体系内对复兴社会主义进行阐释。自执政以来,在复兴主义与伊斯兰教相统一的原则下,阿萨德努力避免宗教与政治的对抗,以便实现宗教与政治协调的局面。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要妥善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从而为实现国家的稳定创造条件[8](P138)。
第三,意识形态对政治认同的实现具有感召力。在叙利亚,国家不仅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构建中如何协调宗教与世俗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同时也面临不同族裔群体宗教与教派矛盾对统一国家认同的分化与消解的问题。政治权力需要制度、法律等强制方式以外,还必须造就公民的心理和情感的支持。“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9](P188),这种意愿即政治认同。阿萨德时代,逊尼派对阿拉维少数派的统治地位甚为不满,政权时刻面临政治认同的严峻挑战。而阿萨德则通过阿拉伯民族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民族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加强国家的政治认同,将民族国家认同置于族裔认同之上。
(三)外交政策务实
阿萨德时代,“叙利亚政权一切外交政策都是由阿萨德1970年夺取政权之后建构的特殊政治制度的产物”[10](P6)。阿萨德本着“务实”精神以“国家民族主义”理论为指导,为叙利亚制定了外交策略,在中东事务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为争取政治和安全利益,进而为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发挥了作用。
首先,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坚决抗击以色列侵略或侵略威胁,巩固政治合法性。阿萨德上台时,叙利亚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六五”战争惨败丢失战略要地戈兰高地,纳赛尔去世阿拉伯世界主心骨缺失。阿萨德执政后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与埃及联手发动“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这被看作是阿萨德的“丰功伟绩”。埃以媾和后,叙利亚成为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最重要的前线国家。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中,阿萨德坚持“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始终不与以色列单独媾和。阿萨德的强硬立场一方面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并成为中东外交强国,另一方面转移了国内反对派的视线,增强了国内凝聚力。
其次,崇尚务实主义,周旋于美苏之间,寻求战略平衡点。阿萨德外交目标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特点是灵活、务实,表现为在美苏之间寻求战略平衡。冷战期间,美苏在中东激烈争夺,叙利亚作为苏联在中东的“桥头堡”,曾获得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援助。然而,为了避免过渡依赖苏联,阿萨德也加强与西方的联系。1974年6月,叙利亚恢复与美国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终结后,阿萨德再次主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再次,阿萨德执政后,积极发展、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971年叙利亚加入由埃及、利比亚、苏丹建立的《的黎波里宪章》组织。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阿萨德对黎巴嫩问题予以特殊重视,谋求建立叙黎“特殊关系”。1978年10月,同为阿拉伯复兴党执政的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签订了联合行动宪章,并成立最高政治委员会和统一政治领导机构[11](P186)。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又与伊朗结成战略同盟,使叙利亚获得了在伊朗和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两伊之间,充当调解人的特殊地位。
上述务实的外交举措,为阿萨德在国内外赢得了声誉,特别是在国内为复兴党政权赢得了政治合法性的资本。
三、威权主义的内在困境与政治失序
阿萨德体制下,民主政治的缺失与经济发展的迟缓,导致叙利亚现代化进程的滞后。当国家统治机器停滞僵化,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政治危机也就随之而来。此外,国内政治稳定与长期尖锐的教派冲突相关,又与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相联系,并困扰着叙利亚,使其成为一个稳中有忧的国家。
(一)政治民主化的滞后
在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阿萨德推行政治稳定优先型的发展战略。在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未能从本质上促成相应的政治变革,而政治发展严重滞后,又造成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极度不和谐。政权内部不断衍生诸多令民众深恶痛绝的痼疾:个人专断的猖獗,权力运行不透明;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当权者疯狂敛财,官宦腐败成风。这些痼疾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最终演变为诱发政治乃至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首先,权力垄断导致政治参与渠道阻塞。长期以来,阿萨德个人及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社会治理依靠血缘和主从关系形成了裙带网络和势力。特别是阿萨德家族、亲信及部落成员占据军事安全、复兴党及政府的关键职位,形成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另一方面,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诉求难以在体制内得到满足,导致大量社会精英没有机会参与管理,政治系统的压力难以疏解,进而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其次,任人唯亲致使政治腐败。在阿萨德体制下,“政府高层官员、部长、省长、复兴党书记、军队警察安全机构指挥、群众组织及国有企业管理者等群体凌驾于国家中产阶级之上,他们以与总统阿萨德的族裔和忠诚关系获得权位,利用政治经济大权谋取私利”[12](P33-34),导致权力腐败蔓延;另一方面阿拉维派成为“暴发户”的事实更加招致逊尼派实业界不满,进而造成阿拉维派与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之间裂痕日益加深。
再次,贪权恋栈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阿萨德长期执掌党政军大权,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并且通过权力安排实行“政权世袭制”。这无疑违背了当初的民主誓言,破坏了总统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正如亨廷顿所言:“与军人政权和一党体制中的政治领袖相比,个人独裁体制中的政治领袖更不愿意自愿地放弃权力。”[13](P115)伴随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支撑阿萨德政权的意识形态——复兴社会主义的衰微,叙利亚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与统治者的贪权恋栈的矛盾造成政治合法性的剥落。阿萨德家族式专权统治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形。
(二)经济弊病严重
政治局势的稳定与否最终必然要追溯到经济和社会根源上,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政治基础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阿萨德虽然凭借渐进的经济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体制自身的弊病与僵化必然导致经济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阿萨德执政后虽然给予私营经济一定的空间,但国营经济依然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然而大多数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落后、效益低下、设备陈旧、亏损严重。金融税收体制严重滞后,私营企业想得到贷款困难重重,企业逃税现象普遍存在。政府高层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分歧严重,改革又面临既得利益阶层的层层阻力。同时政府部门管理人才严重缺乏,办事效率低下,许多政策措施难以有效执行。
第二,叙利亚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严重依赖国际资本,从而形成了依赖外国援助的“乞讨经济”。援助主要来自海湾产油国以及美苏等大国,这些援助弥补了外汇收支不足。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使畸形的经济结构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深受石油价格和地缘政治影响,缺乏自主性,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地位。
第三,叙利亚是阿以冲突的核心国家,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历次阿以战争的失败促使叙利亚决心大力发展国防,这无疑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阿萨德不惜耗巨资建设军队,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力求军事上与以色列达到战略平衡。1970年11月阿萨德宣布:叙利亚新预算的71%将用于军队建设和武器装备[14](P86)。 1990年至1994年,叙利亚国防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54.5%,是中东国家国防开支之最[15](P372)。
第四,“专制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遭遇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16](P9)叙利亚也是如此,由于政治制度滞后,腐败在政府和国有部门迅速扩散,财富大多被最高领导人的亲朋至友、官僚和权贵瓜分。“合法性也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如果好处只给处于社会顶端的寡头小集团,没有得到广泛的分享,反而会动员社会群体奋起反对既有的政治制度。”[17](P464)严重的穷富悬殊与分配不均令民众强烈不满,阿萨德政权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认同感也就不断地被消解。
(三)教派矛盾日趋尖锐
中东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最严峻的挑战是宗教问题[18](P396)。这一现象在叙利亚更为突出。叙利亚教派林立且民族众多,彼此之间历史上的隔阂与冲突难以化解,委任统治时期宗主国又施以“分而治之”的政策,致使教派矛盾更加纷繁复杂。阿萨德政权的世俗化特征和阿拉维派属性,使得教派矛盾必将伴随着阿萨德体制的始终,进而困扰着国家政治稳定。
第一,阿萨德执政期间世俗化的复兴党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削弱了国家的伊斯兰性质,另一方面也触犯了逊尼派的利益。同时,阿拉维派的统治地位更是招致逊尼派的怨恨。虽然阿萨德执政时通过压制和安抚两种手段将教派矛盾及冲突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但是教派矛盾无疑是削弱政权合法性与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第二,叙利亚穆兄会联合城市中下阶层逊尼派穆斯林,在1976年至1982年间不断在叙利亚境内制造恐怖袭击,长期威胁着社会稳定[19](P145-146)。而1982年哈马血案更是在伊斯兰等反对派势力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进而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第三,叙利亚穆兄会作为阿萨德政权的主要政治宗教反对派,其活动长期受到周边敌视阿萨德政权的国家如伊拉克、沙特等国资助。阿萨德认为20世纪80年代国内叛乱是沙特境内穆兄会暗中发动的,这更加剧了叙利亚与沙特两国的隔阂。而伊拉克复兴党政权与阿萨德政权的交恶由来已久,其政府向叙利亚穆兄会提供军事装备与财政援助,企图推翻阿萨德政府[20](P66)。哈马起义失败后,叙利亚穆兄弟会以反对派身份流亡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并继续联络国内外反对派开展反政府活动。
(四)地缘政治复杂
长期以来,复杂的国际关系与纵横交错的地缘政治一直是中东地区难以获得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叙利亚地处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国逐鹿的场所。冷战时期,叙利亚是美苏在中东地区争霸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前线国家。阿萨德时代叙利亚虽然摆脱了弱势的国际地位,成为影响中东事务的政治大国,但其国内政治进程和稳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影响。
第一,叙以矛盾是影响叙利亚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复国运动引发了阿以双方的长期冲突,阿以冲突是战后中东地区基本矛盾之一。叙利亚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其长期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叙以矛盾最突出最现实的问题是戈兰高地。“六五”战争中失去戈兰高地后,叙利亚一直图谋收复失地,但时至今日仍未偿所愿。叙以矛盾引发的武装冲突与战争,致使叙利亚承受了巨大的战争负担,并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也助长了民间反政府活动的蔓延,是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二,美苏争霸严重威胁叙利亚的独立自主与国内稳定。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外部势力尤其是大国必然在这里展开争夺,而大国争夺又必然对叙利亚的政治稳定产生重要影响。阿萨德执政时期,由于美苏在中东地区争夺异常激烈,阿萨德不得不周旋于二者之间寻求利益平衡。阿萨德上台初期,美苏为了各自战略利益都竭力在阿以之间维持“不战不和”局面。这既不利于叙利亚收复失地,也不利于国内稳定。此后,阿萨德依附于苏联抗衡以色列,但是 “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之间将会时时发生矛盾”[21](P62)。叙利亚很难在叙以冲突的实质性问题上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苏联对其援助往往会附加一定的政治条件,进而影响阿萨德政权在国内的政局声誉。另外,叙美关系长期紧张,一方面美国支持以色列招致叙利亚国内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另一方面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长期对其制裁,致使叙利亚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苏联解体,一方面使叙利亚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一家独大的局面随之形成,致使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飙升,这对叙利亚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阿萨德谋求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这一外交政策取向却又招致国内宗教反对派的强烈诋毁。
第三,阿拉伯世界内部冲突致使叙利亚地缘环境更趋复杂。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两伊战争中阿萨德联合伊朗制衡伊拉克,这一立场与阿拉伯国家立场相左。另外,阿萨德个人与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冲突,一方面使以色列渔翁得利,另一方面招致阿拉伯世界与国内反对派的不满。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一直招致黎国内反对派的抵制与阿拉伯世界的指责,伴随黎巴嫩对叙利亚认同感的逐渐消失,叙利亚愈发陷入“黎巴嫩困境”。而叙利亚与埃及双边关系则在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之后严重恶化。
亨廷顿曾经指出:“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6](P17)伴随“奇里斯马”领袖的逝去,国家出现“权威真空”,加之民众日益增长的参政热情,体制的专制色彩越来越引发民众不满,而政权的阿拉维宗派主义特征更招致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愤恨甚至反抗,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今天叙利亚乱局的渊薮。
参考文献:
[1] PIPES D. Syria after Asad[EB/OL]. Middle East Quarterly, February 1987, http://www.meforum.org/pipes/177/syria-after-asad.
[2] 姜士林, 陈玮. 世界宪法大全[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
[3] 王新刚.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 GALVANI J. Syria and the Baath Party[R]. MERIP Reports,1974,25.
[5] MYERS R. Persist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M]. Munich: GRIN Verlag, 2009.
[6]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7]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8] 王新刚.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及其理论与实践[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
[9]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0] Syria and the Shiites: Al-Asad′s Policy in Lebanon[J]. Third World Quarterly,1990,(2).
[11] 王京烈. 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12] PERTHES V.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Baath:A Look at Syria′s Upper Class[J]. Middle East Report, 1991,21.
[13] 塞缪尔·P·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欧阳景根,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4] 严庭国. 当代叙利亚社会与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15] 彭树智.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16] 戴维·E·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M]. 陈尧,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7]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M].毛俊杰,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8] 彭树智. 中东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19]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3.
[20] HOPWPOOD D. Syria 1945-1986:Politics and Society[M]. London,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21] 甄荣. 试论叙苏关系及其特点[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1984, (4).
[责任编辑刘炜评]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Syrian Asad’s Age
WANG Xin-gang, MA Shuai
(SchoolofHistory,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Abstract:After 1970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sad, Syria reestablished its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and reconstructed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By ideology control and pragmatic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Syria sustained political stability for as long as 30 years. However, under the governess of Asad’s authoritarianism, Syria was a nation in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troubles due to its deficiency of democracy, slow development of economy, monopoly of Alawite sectarianism and the evil geopolitics, etc. After the death of Asad, Bashal succeeded his father’s political heritage, but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y and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 decreased sharply.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lost its control on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is is the inner abyss of current chaos in Syria.
Key words:Asad;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stability; ideology; sectarianism; geopolitics
收稿日期:2015-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A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新刚,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叙利亚问题、中东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K376.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