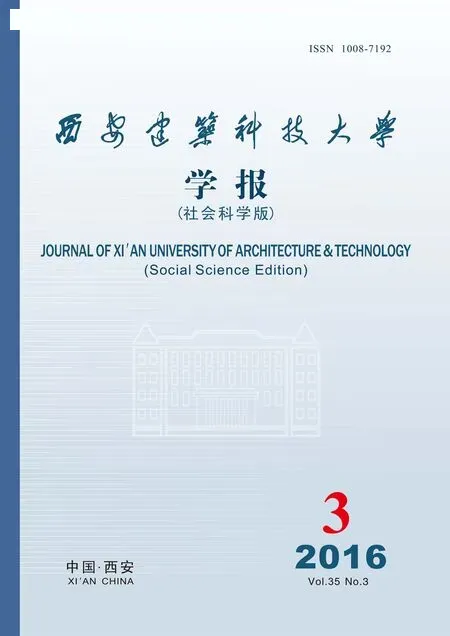乡土书写的“善”与“恶”
——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边城》为例
2016-02-19刘蓉
刘 蓉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1]。在《呐喊》与《彷徨》两本集子当中,“那未经充分开发与充分言说的精芜并存善恶交织又充满神秘气氛的广大乡村与乡村人的世界,构成了鲁迅精神内部巨大冲突与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对都市社会与文化主潮进行质疑与批判的丰富资源和动力之一。”[2]25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大潮之下,在启蒙话语的思想关照之下,乡土文学的书写在鲁迅笔下自然地成为了“改造国民性文学”,对乡土中国的人民以及乡土中国的文化进行审视,可以说鲁迅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之路,可是《故乡》却以温情的童年叙述成为了鲁迅乡土世界的独特存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知识分子和乡土书写成为文学的两大主题,这时的沈从文似乎企图承接启蒙时期的乡土书写。但是,在沈从文这里,乡村和城市成为对立的两级,城市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产物不具备启蒙的意义,他采取的是和主流知识分子相悖反的写作姿态,以近乎一种“反启蒙”的姿态在否定城市启蒙意义的同时,通过对家乡纯与美的描绘来展示乡土的“原始精神”。《边城》成为了其典范性的文本,文中对于故乡湘西的叙述意在呼唤原始纯美的生命和力,呼唤人性与热情,企图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对故乡资源的挖掘中,鲁迅与沈从文均展现出各自的叙述图景。但是,两者同归于 20世纪初乡土小说的创作实践,不同审美策略关照下意旨存在其融合之处。
一、各自笔下的乡土世界
1.“没落贵族”的乡村挽歌
鲁迅凭借其敏锐的感知能力,为我们展现出了家乡浙江的生活图景。《祝福》里祭祀的礼仪,《孔乙己》里咸丰茶馆的规矩,《社戏》里去赵庄看戏的风俗,这一切全于鲁迅的笔下展现出浓厚的民俗色彩。然而在《故乡》中,作者对于祭祀的描写:“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贡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3]57就是这寥寥几笔写尽了自己对于故乡祭祀的全部记忆,似乎在鲁迅这里是有意而为之,但其实他对乡村生活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对于鲁迅来说,“他在主观上并不想有意突出小说人物的地方性特征,其主要目的在于借乡村人物来表现整体的国民共性。”[4]279如此随笔式的勾勒,就会导致一个悖论的存在:在乡土中国里风俗与人密不可分,环境的淡化与人物的典型刻画存在矛盾。
2.“乡野粗人”的乡村赞歌
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对他而言,湘西世界的描绘是他的重心所在。仅仅一篇《边城》:茶峒码头,吊脚水楼,端午赛舟,正月十五放炮点灯……这一切景物风俗的描写全部融入在小说人物与情节的刻画之中,甚至已经超过了小说情节及内容的篇幅。《边城》中即使是妓女,在风俗淳朴的边城,也永远那么纯粹;翠翠的母亲未婚先孕,生下翠翠后随夫而去。在这样真挚的爱情下,传统的道德也为其让步。不同于鲁迅,他笔下的湘西并没有寄托着改造国民性的负累,就在这样的湘西世界中,作者构建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他的湘西世界歌唱着灵魂的赞歌。
都是故乡,在鲁迅和沈从文笔下,一个轮廓清晰,一个“内容翔实”;一个冷峻犀利,一个饱含温情。情感基调似乎也因为这样的描绘而产生区别,进而引发出对于故乡不同的审美关照。
二、不同审美关照下的叙写策略
鲁迅执着地以浙东故乡的乡镇生活为模本,然而少年时代在家乡受尽冷漠和奚落的独特遭遇使鲁迅对于家乡的憎恶之感成为一种主体情愫。对于故土的爱的情感被这样的憎恶之情所压制,同时,在家庭的大变故下,鲁迅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5]自序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之所以能够以冷峻的视角展现乡土中国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的原因,他从有限的外部了解,发挥他的艺术创作,从而更广泛地了解社会,更深刻地思索着人生,描述和剖露乡村人的外在生存状态和内在精神存在方式,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深刻的批判。《故乡》中,对于搬家期间每日必来的杨二嫂的鄙夷,面对成年闰土时的尴尬,有许多话“但又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一声“老爷”,鲁迅道出了在封建等级思想侵蚀下人与人之间“可悲的厚障壁”。然而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对于这些国民性“恶”的揭示,都是基于自己与故乡的童年记忆进行比较的结果。
对于故乡,每个人都有那一层不能言说的情感。在近似于恶的叙述外表下,鲁迅对于故乡浓切的情感却隐含其中。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以眷眷乡土之情为弘扬故乡文化尽心尽力。1928年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叙写着这种难以忘却的记忆。1931年,身处于白色恐怖的都市上海,在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愤懑中透漏出浓浓的思乡之情。不能否认,鲁迅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其自身的启蒙意识迫使他对于乡土中国的种种“恶”进行揭示,可是不难发现的是《离婚》、《祝福》、《肥皂》等这些乡土文本均呈现出作者对于乡土书写的紧张感。然而,乡土中国所培养下的乡土情感是不易被抹杀的,因此这种抒写的紧张感消融在《故乡》中对于童年时期故乡以及故乡人的描绘之中,轻松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抒情性的鲁迅。《故乡》当中,鲁迅称故乡以外的一切地方为“谋食的异地”;听闻儿时的伙伴闰土要来时,作者“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当他以成年少爷的身份描写现实的故乡时,我们看到了他对传统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但全文的抒情环境让鲁迅流露出的是对少年乡土世界逝去的悲凉与惋惜。因此,在鲁迅极为冰冷近乎于残忍的表述方式下包裹着一颗充满乡土情感的爱心,以冷漠的叙述策略传达着最激昂、最愤慨、最热烈的情感,而其中的同情之心也到达极点。
同样描写故乡湘西的沈从文,在不同于鲁迅的审美策略下,似乎简单了许多。故乡的景物人情,都以其自身的美传达出作者对于故乡善的期许。沈从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至真至美的湘西世界,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渡船老人将渡船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主人公翠翠“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祖父女之情,天保傩送的兄弟之情,傩送与翠翠朦胧的爱情,这一切都融合在湘西唯美的山水之中。在沈从文的叙事策略指导下,湘西作为城市的对立物而存在,湘西世界为我们找到了人性的存在方式。在这里,不需要启蒙的参与,“原始精神”就足以呈现完美的人性。
然而,沈从文的“乡土梦其实做的很累,从这梦境产生之日起,种种惊扰着与侵蚀着作者的梦境使之无法酣睡,聒噪之声此起彼伏,最终惊醒了做梦的主人。”他自己也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被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6]64沈从文自始至终以乡下人的身份自称,他1923年只身入京,在北京大学旁听,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了一种“彷徨”的境地,刚刚入京的他还未参与,就直接陷入困境。他并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狂热与激进,有的只是落潮后的迷茫与怅惘。因此,当身处异乡的他看到了物欲横流的城市图景,就更加促使他怀念故乡湘西的淳朴与真实。他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城市文化,糜烂的都市生活成为其湘西叙述的对比之物。在随后的“湘西”系列散文中,看到了沈从文企图为我们展现故乡湘西的完美图景。但是,在这背后隐伏的悲伤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五四”落潮后的怅惘,时代性的辗转徘徊。沈从文也不例外,他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道:“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那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7]363可是,他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境况下为我们点燃一丝希望之光,这是沈从文的初衷。
任何一位作家对于乡土的那份情结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在批判视野下鲁迅对于乡土中国以及中国国民的那份温情。从至真、至善、至美角度致力于对湘西纯粹书写的沈从文,他们两者的乡土描写虽然文本的外在叙述图景不同,但是,不同的抒写策略下展现出的是对国家和同胞当下及未来期盼性的美好祝愿,对于残酷的当下表达出深刻的憎恶与批判。
三、批判以后的归属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能看到鲁迅对故乡充满了一种十分复杂矛盾的情感,热爱与憎恨、眷恋与鄙视、悲哀与哀怨、希望与失望,都始终矛盾的交织在一起。鲁迅的作品从来都不是消闲的物品,他以其辛辣冷酷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了旧时代中国国民性之“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鲁迅结构文章的总体思路。然而,鲁迅冷峻的批判下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改造国民性的措施,他所做的就是挖掘国民的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故乡》“少年闰土不但以充满活力的心灵吸引着少年鲁迅, 而且以丰富的知识和广博的见闻使他感到敬佩和钦羡”[8]。然而经历生活折磨的闰土变得迟钝、麻木,可是鲁迅仍旧期待与儿时玩伴的相遇,即使产生隔膜,“我”仍旧怀以希望,希望水生、宏儿不再像自己和闰土一样,儿时的玩伴间最终产生难以逾越的厚厚障壁,并且期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在经历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之后,在体味了乡村人精神状态的悲凉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希冀。可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故乡》的最后,作者将这样的希望也进行了怀疑:“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65鲁迅更多地为我们提供的是现实的教训,我们所期许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不得而知,他只是敬告我们,我们所期许的生活不应该是什么样。
“湘西世界”的创造,可以说是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他对整个世界文学的贡献。他执拗地为湘西谱写颂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没有国民性“恶”的负累,《边城》努力将现实阻挡在文本之外。文中的“湘西世界”就是这个“乡下人”想象的世界,一个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世界。然而无数人怀揣着对于原始纯粹家园的向往而被湘西世界所浸染,从这里得到精神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它是沈从文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然而《边城》中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末尾一笔不仅写出了作者的隐忧,更展现出翠翠对于情人归来的希冀,这更是作者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希冀。在隐忧之下,不同于鲁迅的冷峻批判,他为我们构建了“湘西世界”的美好图景。我们不去追究沈从文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建构,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在面对自身、城市、国家的悲惨境遇,对于湘西人生方式的推崇,并借此重建民族品格。因此,湘西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慰藉,湘西人成为一代人的理想人格的寄托。我们不去追究这样的构建到底作用几何,我们看到的是,他在继承前辈们对于民族品格、祖国未来的探讨之后企图给出的解决策略。
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的观念,乡土对于国人的情感熏染是难以低估的。文学对于乡土中国的描绘,经历五四直至今天仍不绝如缕,在对于乡土中国的关照中,《故乡》与《边城》在不同的审美及叙述策略下,却为我们提供了相同的精神愿景,即对于善、美的人性或者说是国民性的殷切期盼。但是鲁迅用“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沈从文用“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样一种近乎相同的文本语言叙述尽了各自的乡土世界。作者都企图为我们找寻批判后的精神归属,但是这样的精神归属却一直在等待被实现的旅途之中。也许这就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意义之所在。
[1]严家炎. 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J]. 文学评论,1981(5):9-12.
[2]杨剑龙. 鲁迅的乡土世界[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3]鲁迅. 呐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杨剑龙. 鲁迅的乡土世界[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5]鲁迅. 呐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范家进. 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
[7]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8]王富仁.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216-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