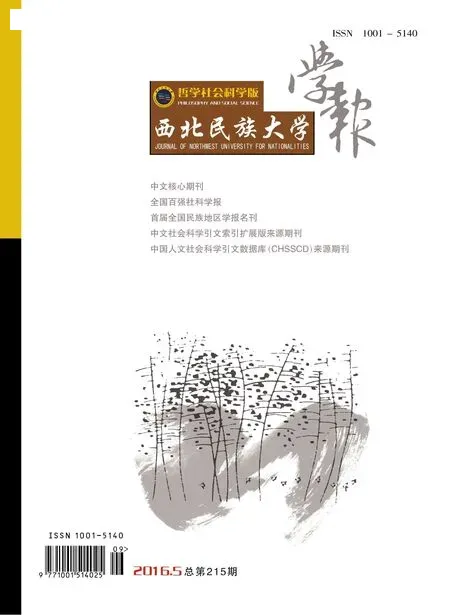宋代域外行记形塑“他者”形象之策略
——以使金行记为中心
2016-02-19阮怡
阮 怡
(四川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韩国延世大学 中国研究院,韩国 首尔 03722)
宋代域外行记形塑“他者”形象之策略
——以使金行记为中心
阮怡
(四川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韩国延世大学 中国研究院,韩国 首尔 03722)
域外行记不仅记录了跨越不同地理空间的过程,也记录了旅行者从一文化空间进入另一文化空间的情感体验。行记中存在大量关于异国形象的记载并不是简单的先验于文本的对异国现实的复制品,而是旅行者在自身的社会文化、伦理情感等因素影响下对异国所作的想象性描述,这一点在宋代的使金行记中得到突出体现。在宋人关于金国“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下,作家筛选出女真族粗疏无文、遗民人心思汉、金地荒凉破败等特点来塑造金国形象,总体呈现出负面、丑陋的形象,透过对金国形象的描述,宋人完成了对自身文化大国形象的塑造。
使金行记;社会集体想象;女真族;遗民;金地;形象
行记是笔记文体的一个分支,这类文章多用于记载长时间、长距离、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它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民情以及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体验。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个时期都有人以此记录自己的旅行见闻,到了宋代,随着海外关系的拓展、交聘制度的完善,宋人常往返于中国和周边国家、民族地区,记录下自己的跨界旅行经历,产生了不少域外行记。近年来,这些行记文献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史研究者的关注,不少学者探讨其在地理、交通、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价值,如周宏伟的《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张劲的《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苑分布》①周宏伟的《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张劲的《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苑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2月。等文,他们都是以行记作为反映当时域外生活情景的真实可靠材料来探讨其历史文献价值,而对行记描写中的文化想象成分却少有人关注。旅行是一次空间位移的转变,域外旅行记不仅记录了跨越不同地理空间的过程,也记录了旅行者从一文化空间进入另一文化空间的情感体验。域外行记中存在大量关于异国和异国人物的描写,对异国形象的记载并不是简单的先验于文本的对异国现实的复制品,而是旅行者在自身的社会文化、伦理情感等因素影响下对异国所作的想象性描述,是旅行者将自身文化与所到之处的异国文化差异比较下的产物。这种形象是“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和异国人体貌特征及一切人种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总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1]。金是与南宋并立的政权,不少宋朝官员都曾出使金国并撰有行记,本文以使金行记为例,通过对使金行记中记载的有关金地的人物、风俗、城市建筑、器物等要素的分析,阐明行记作者在文本中采取了哪些策略来塑造金国形象。
一、女真形象——粗疏无文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女真族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以北的多种民族之一,族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人,战国以后称为“挹娄”,魏晋隋唐时期又称作“勿吉”“靺鞨”,五代时期,靺鞨中的一支黑水靺鞨称为女真。*参见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对女真族的来源的介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他们长期以狩猎、游牧为生产手段,经济发展缓慢,与汉族统治的南宋地区分属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原地区的汉民族长期处在农耕文明的生产形态中,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儒家的“华夷观”。他们以中原汉族为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离中心越远的地区越荒芜,在那里生活的民族也越野蛮落后。在这种尊华卑夷、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下,女真人被宋人视为是周边众多落后民族之一,金国成为宋人眼中的“他者”。*霍柔在《当代文学理论术语汇编》一书中称:“人们将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种制度定义为他者。是将他们置于人们所认定的自己所属的常态或惯例的体系之外。于是,这样一种通过分类来进行排外的过程就成了某些意识形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见Jeremy Hawthorn. A Glooss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ewyork: Routledge,Chapman and Hall.1994.P207。在宋人眼里早已形成了女真族是野蛮落后、需要接受中原文化教化的异族的“社会集体想象”。*[法]让·马克·莫哈认为:“从哲学、历史观念来看,社会集体想象物基本上被理解为对(在社会—历史和心理方面)基本上不确的面目/形式/形象的不断创造。只有从这些面目形式/形象出发,才能研究‘某物’。我们称之为‘现实’和‘理性’的东西为其研究对象。很可能所有对异国的描述都处于这一层面。然而,文学史家仍可将社会集体想象物等同于文化生活范畴,并把它定义为是对一个社会(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集体描述的总和,即是构成,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参见《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30页。而且古代中国与周边民族国家建立了以朝贡关系为主的外交关系,在宋人眼中,女真族本应是按期前来朝贡,接受宋朝安抚、教化的夷狄,而现实中,女真族不仅不向宋称臣进贡,甚至举兵入侵宗主国,迫使宋王朝偏居南方一隅并向女真称臣、称侄,昔日的藩属国成为宗主国,这让宋人对女真族充满恐惧。当踏上金国土地,宋人在对金国实际感知的基础之上加上想象之辞,塑造了宋人“集体记忆”制约下的女真族形象。
使金旅行记中刻画的女真人残暴、凶狠。北宋末年金灭辽后,钟邦直出使金国至接近宋金边界处的蓟州听闻“自甲辰年(1124年),金人杂奚人,直入城劫虏。毎边人告急,宣抚使王安中则戒之曰:‘莫生事。’四月之内,凡三至,尽屠军民,一火而去”[2]。此时蓟州已归还宋朝,王安中被任命为燕山府路宣抚使,总管燕山府事。战乱期间,辽朝人逃入宋境的很多,金人却常常借遣回逃亡者之机南下残暴地烧杀抢掠,而宋代官员恐招惹是非,只能忍气吞声、不予理睬。宋人出使金国常耳闻目睹女真人的这类暴行,再加之对女真族野蛮落后的社会集体想象,使得他们常常以想象之辞来打量女真人。钟邦直在经显州时见契丹人坟墓被毁就联想到是女真人所为,他说:“契丹兀欲葬于此山(医巫闾山),离州(显州)七里,别建乾州,以奉陵寝。今尽为金人毁掘。”[3]钟邦直使金正值金灭辽之后不久,战乱后城池破败、百姓生活艰难,盗墓往往可收获意想不到的财富,盗墓者也有可能是当地百姓,而钟邦直受到“女真族残暴”的先入之见的影响,认为掘坟这种暴行只有女真人才做得出来。
宋人对女真族的饮食、服饰、音乐亦充满了负面评价。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曰:“乐作,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筝、笙、[竹秦]、箜篌、大鼓、拍板,曲调与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太阔,声遂下,而管、笛声高。韵多不合,每拍声后继一小声。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观也。”[4]《北行日录》曰:“乐人大率学本朝,惟杖鼓色皆幞头红锦帕首鹅黄,衣紫裳,装束甚异。乐声焦急,歌曲几如哀挽,应和者尤可怪笑。”[5]《北辕录》亦记使金途中“有羌管从后,声顿凄怨。永夜修途,行人为之感怆”[6]。他们认为女真乐舞“殊不可观”,歌曲如哀婉之乐、声调凄凉使人感伤。女真族的乐舞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汉族差异明显,两者同质的因素较少。宋人总是以自身的审美观为标准来对待异族文化,因而女真乐舞只能得到否定性的评价。此外,宋人出使金国,路途遥远、前程未卜,面对完全陌生的异国风物,心情更加沉重,异族音乐被投射上使金文人惆怅的心情,成为了一曲哀婉、凄楚之音。
在宋金军事力量较量中宋弱于金,这是宋代士大夫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他们踏上金国的土地这种屈辱感尤其强烈,这使得他们努力搜寻中华文化泽被四夷的例证,来加强对自我文化大国身份的认同。如《北行日录》详细描述了楼钥一行正月初一入金朝贺正旦的场景,一一记录了各种朝拜的礼仪,然后总结道“进御酒时却不起立,余皆如本朝之仪”[7],言下之意金朝即使在军事上暂时处于领先,但文化上相当落后,只能蹈袭中华文化,并不值得一提。当他们看到与中原礼仪制度不相同的事物总是嗤之以鼻,如范成大《揽辔录》记载金朝官制仿造汉族建立,设有三师、三司之职,尚书省、六部等机构,又设置佩服之制,设文散官、武散官等官位,并且仿汉族使用年号,他评价道:“虏既蹂躏中原,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虏主既端坐得国,其徒益治文,为以眩饰之。”[8]其认为女真族学中华制度只能得其皮毛,将其作为其野蛮统治的装饰物,而无法继承精髓。
使金文人总是以一种天朝上国的态度俯视女真族的各种行为、习俗,不断地凸显女真族粗疏野蛮的形象,以他族文化的野蛮落后一次次考量自身的文化身份,中原文化的优势不断得到加强。
二、遗民形象——人心思汉
宋室南渡,北方广大地区的汉族百姓沦陷在金的统治区域下,使金文人以自身的眼光审视沦陷区的遗民形象,认为他们虽久陷金地不得不接受异族的统治,却仍然心念故土,渴望宋朝君主早日北定中原。旅行记中多次记载了宋使经过金地受到当地百姓欢迎的情形。如楼钥至宋旧东京城见“都人列观,间有耆婆,服饰甚异,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员也。’”[9]。显然,围观的百姓既有女真人,亦会有汉人;既有因好奇来围观者,亦有因思念故土来围观者,但在使金文人眼里,所有的围观者都成为了人心向汉的遗民。遗民围观南宋使臣,或行礼拜见之,或表达他们见到宋代官员后悲喜交加的感叹,刻画了他们眷念赵宋王室的形象。
范成大经相州,亦见同样的情景,他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10]并作《翠楼》一诗,云:“连袵成帷迓汉官,翠楼沽酒满城欢。白头翁媪相扶拜,垂老从今几度看!”[11]描绘了整个相州城内欢天喜地、遗民争先恐后拜见宋使的情形。范成大还在此地作《相州》一诗云:“秃巾髽髻老扶车,茹痛含辛说乱华。赖有乡人聊刷耻,魏公原是鲁东家。”[12]魏公指相州人韩琦,宋仁宗时期曾率兵抵御西夏获得胜利,迫使元昊向宋称臣。全诗借相州老车夫的口吻指斥金人的统治是以夷乱华,渴望南宋王朝有如韩琦那样的能臣早日收复中原。在范成大眼里,遗民虽长期处于金朝的统治之下,内心却始终排斥金人,思汉之心未变。
使金文人还认为金地的遗民仍然保留着中原的礼仪规范,是人心向汉的表现。如楼钥在旧东京城遇负责接待宋使的承应人,称:“承应人各与少香茶、红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13]承应人为汉人,虽久受异族文化侵染,但仍然保留了中原礼数和汉人的语音,这让宋朝的士大夫既感伤又欣慰。
范成大经过邯郸县特别提及邯郸人的抗金活动,曰:“邯郸人健武,逆亮死时遮杀其归卒以待王师。”*范成大《揽辔录》节文,见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592页。邯郸人至今虽仍被金统治,但他们却不忘中原文化,“春时倾城出祭赵王,歌舞其上”[14],以中原贤明君主赵武灵王为祭祀对象来表达对故土文化的眷念之情。
范成大至真定府见到此处仍有北宋京师的旧乐工表演中原乐舞,程卓《使金录》亦云:“已时卓等赴宴,见舞《高平曲》,他处尽变虏乐,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故也。”[15]对此,范成大评价到:“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幺。”[16]认为京师的旧乐工虽然年龄已大,却始终不愿演奏虏乐,仍然依念中原故曲,在乐舞中寄托着遗民的黍离之悲。
使金文人在旅行记中试图塑造一个人心思汉的群体,他们希望看到中原百姓能永远固守向汉情结,以宋为衣食父母,因而当范成大见到旧北宋东京城内汉人身着胡装、尽用薙发结辫的女真发式时,他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鸱鸮,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17]他认为束发戴冠才是儒家礼教文明的象征,久陷胡地的汉人已长期浸染胡俗,渐渐遗忘了原有的中华礼仪规范。字里行间透露出范成大唯恐中原久陷,遗民人心渐变,向汉的情绪慢慢淡化的担忧之情。
实际上,中原百姓改习女真的发式、服饰等习俗并不代表人心的改变,而是在金人推行薙发左衽政策下的被迫行为。女真族占据广大的中原地区,如何统治在文化上远远优于自己的汉民族成为女真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女真统治者试图通过使汉人改从女真之习俗来改变其人心,因而强制汉人薙发左衽。在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围攻汴京时就颁布了改俗令,“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18]。宋室南渡,淮河以北大面积地区沦为金国所有,金朝则在更大范围之内推行汉人习女真俗的措施,“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皆死”[1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是时知代州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即斩之。其后知赵州韩常知觧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莫可胜纪。”[20]在发式、服饰上稍不合金朝的制度,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在此类高压政策下,中原百姓为保全性命不得不遵从女真人要求改俗的命令。范成大基于中原百姓都应保留汉俗、留念宋王朝的遗民想象,对汉人改从蛮夷之冠的行为过度的敏感,从而误读了汉人改习胡俗这一历史现象。
此外,使金文人记载了金地的遗民窘困、艰辛的生活情形。如楼钥至金南京城,听闻金地遗民的生活情形,他说:
承应人有及见承平者,多能言旧事,后生者亦云:“见父母备说,有言,其父嘱之曰:‘我已矣!汝辈当见快活时。’岂知擔阁三四十年,犹未得见!”多是市中提瓶人言:“倡优尚有五百,余亦有旦望接送礼数。”又言:“旧日衣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毁抹旧告,为戎虏驱役,号闲粮官,不复有俸,仰其子弟,就末作以自给。”有旧亲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钱二贯,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劳。”语及旧事,泫然不能已。[21]
沦陷金地的遗民为金人驱使,不堪劳役,俸禄微博,只能屈辱苟活。楼钥前往胙城县途中“遇老父,云女壻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为始,凡物力五十贯者招一军,不及五十贯者,率数户共之,下至一二千者亦不免。毎一军费八十缗,纳钱于官,以供此费”[22]。陷金百姓既要服兵役,又要承担繁重的军费开销,生活非常窘迫。程卓的《使金录》作于蒙金交战之后,行记中亦屡屡提及遗民生活的贫穷艰辛。他至真定府云:“途中遇差诸路人丁,往添筑燕城,无日不见运粮草军,往来牛马或毙,即载车中。车夫怨言征取之扰,自常赋外,有曰和籴,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23]听闻多位车夫抱怨金国的苛捐杂税繁重。
遗民对金朝统治下的生活状况怨声载道,而对宋朝的统治充满向往之情,如《北行日录》记载了一马姓承应人自叙在金的生活情形:虽有“校尉名目”,但“无差遣,多只监本州酒税务。又言并无俸禄,只以所收课额之余以自给,虽至多不问;若有亏欠,至鬻妻子以偿亦不恤。……若以宋朝法度,未说别事,且得俸禄养家,又得寸进,以自别吏民。今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高,未免箠楚,成甚活路”[24]。对宋朝的制度心怀眷念之情。《使金录》亦载一位修车木工云:“此间官司不恤民,一应工役,自备工食,及合用竹木等费,子孙不敢世其业。”[25]将遗民在金统治下生活的艰难不堪与宋朝统治的美好情形相对比,赋予宋朝的统治无比的优越性,以展现金朝的统治是不得民心的,沦陷金地的百姓仍然渴望回到宋朝的统治中。
“制作一个异国‘形象’时,作家并未复制现实。他筛选出一定数目的特点,这些是作家认为适用于‘他’要进行的异国描述的成分。”[26]使金文人特意筛选出“遗民欢迎宋使”“遗民仍保留中原礼仪文化”“遗民在金地生活艰辛”等三个特点塑造了人心思汉的遗民形象,更进一步印证了女真人残暴、野蛮、粗疏无文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
三、金地形象——荒凉破败
使金旅行记中描绘了金统治地区一片荒凉的景象。北宋末期钟邦直使金时描述金地的情景曰:“山(燕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出关(榆关)来才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卤弥望,黄茅白草,莫知亘极,岂天设此限南北也。”[27]燕山本是我国中温带与北温带的自然地理分界线。燕山以北地区气候寒冷,远离海洋,大兴安岭等山脉阻挡了东部太平洋吹来的湿润空气而形成干旱地带,土地贫瘠,境内多草地、沙漠,以畜牧业为主;而燕山以南地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暖热多雨,四季气候分明,土壤较燕山以北地区肥沃,以种植农作物为主。自然的地理分界线在宋朝使臣看来却成了区分华夷的界限,燕山以南物产丰饶,以北土地贫瘠,这是天意所致。他们带着女真族是蛮夷之族的先入之见踏上金的领土,当见到不同于自身生活的北国风光时,便对北地的自然地理特点进行了具有强烈种族情感的阐释。
南宋使金文人更详细地展现了金地的萧索之景。范成大至金朝南京城(原北宋旧京开封城)评论称:“炀王亮徙居燕山,始以为南都。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市肆,皆茍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28]旧日繁华的京城一片萧索、死气沉沉、人烟稀少。当他经过旧东京城外宜春苑时,仅见“颓垣荒草而已”[29],其创作《宜春苑》一诗云:“狐冢獾蹊满路隅,行人犹作御园呼。连昌尚有花临砌,肠断宜春寸草无。”[30]曾经风光无限的御园如今除去满眼荒草,只有狐、獾之类的野兽在荒墟坟墓间穿行,让人心酸。他进入旧东京城内所见亦“弥望悉荒墟”[31],并作《相国寺》一诗曰:“倾檐缺吻护奎文,金碧浮图暗古尘。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32]
北宋东京城内的相国寺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33]。金朝统治中原后,相国寺仍然维持了其经贸中心的地位,每月定期开寺贸易,但范成大对金地繁荣的商贸景象丝毫不感兴趣,只曰:“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34]寺中所卖尽为羊裘狼帽一类女真族喜爱的商品,而他希望见到的是北宋时期宋人在此交易汉人货物的盛况。“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35],女真人眼中繁荣的商业贸易场景在范成大眼里成为宋代经济文化衰落的表征,因而他感叹到“傾檐缺吻,无复旧观”[36]。
他经过金水河时见到“河中卧石礧磈,皆艮岳所遗”[37],由此感叹到“谁怜磊磊河中石,曾上君王万岁山”[38]。宋徽宗时期营建万岁山,命朱勔等人在全国搜求奇花异石,并组织专门的船队“花石纲”负责调运花石入京,建造寿山艮岳,集天下瑰奇怪异之石、精美珍贵之花木于一体,大兴亭台楼阁、雕栏曲槛,成为北宋史上最优美的宫廷苑囿。这里曾经是帝王精心营建的游玩场所,如今只剩下在河水冲击之下的数块凌乱的大石头。他经过浚州又见到“旧治已沦水中”,*范成大《揽辔录》节文,见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592页。周辉使金云“自过泗,地皆荒瘠”[39],程卓亦云“早顿栾城,县极萧条”[40]。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周辉、程卓等人都一再地渲染金地破败不堪的景象。事实上,金朝统治中原后,战事停息,百姓生活渐渐安定,经济也逐渐发展。以河南开封城为例,据吴松弟《中国人口史》一书统计,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的人口密度为15.1户/平方公里,而金泰和七年(1207年)增长到20.8户/平方公里[41]。从北宋到金统治时期开封城人口密度呈上升趋势。范成大、周辉使金在泰和七年之前,他们使金时开封人口也许还未达到泰和七年的水平,但也并非完全如使金文人所描述的旧开封城内人物极其稀疏的场景。此外中原地区的城镇经济在金统治时期亦有显著发展,如黄久约在《涿州重修文宣王庙》文中称河北涿州“州治当南北之冲,四方行旅取道往来十率八九,使客冠盖,旁午晨夕,疲于迎接以为常”[42]。王伋在《云锦亭记》中称安州:“舟车交辏,水行陆走无往不通,贸迁有无,可殖厥货,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43]描绘出金境内的州郡一派商业繁荣、旅客众多的生机勃勃的气象。又如河北保州至金末虽受到蒙金战争影响,但仍显示出城市的繁荣景象,“保当南北之冲,乱后荒空者十余年。公(按:指金人柔德刚,后归元,封安肃公)乃剗荆榛、立市井、通商贩、招流亡,不数年官府第舍奂然一新,向者井泉咸卤,不可饮食,遂引鸡距一亩二泉,凿城门而入,疏为长河,以流秽浊,楼观相望、陂池映带,若图画然,遂为燕南一大都会”[44]。不难想象,金地既有荒凉落后之地,亦有繁荣发达之地,但使金文人受到金人的统治是蛮夷之族的统治,必定不会长久的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因而总是忽略金地的繁荣景象,只是以一系列的荒残之景勾勒出一幅破败的图画,旨在表达这样一种意图:金地是不适人居的,只有宋人才能统治好这片地区,金人对此地的统治实为一种沉沦,终究会灭亡,中原地区不会长久沦陷。
使金文人作为同一个阐释群体在对金地的描述中,呈现出强烈的一致性,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在一致性中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如在范成大前一年使金的楼钥虽也提到金地荒凉的景象,如涿州州治“门庑陋甚,馆驿尤湫隘”[45],但他也记载了金地的不少地方市井繁庶,如称宿州城“城中人物颇繁庶,麫每斤二百一十,粟、谷每斗百二十,粟、米倍之。陌以六十,大寺数所,皆承平时物。酒楼二所,甚伟,其一跨街,榜曰‘清平’,护以苇蓆,市肆列观无禁,老者或以手加额而拜,有倒卧脚引书铺,般贩官局汤药、蔡五经家饼子、风药”[46]。
楼钥与范成大对同一地点的描述也有不同。两人都记载了曹操修筑的讲武城及其受到金人增封的七十二冢,*范成大使金,作《七十二冢》一诗,诗下小注云:“在讲武城外,曹操冢也。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见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二,第151页。)范成大云:“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传云操冢正在古寺中。”[47]“散在数里间”表达出散乱无层次的情形。范成大在此还作《讲武城》及《七十二冢》诗,云:“阿瞒虓武盖刘孙,千古还将鬼蜮论。纵有周遭遗堞在,不如鱼复阵图尊。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48]前诗认为讲武城虽存,但曹操的名声低下,不如诸葛亮受到世人的尊敬。后诗认为曹操性情多疑,善猜忌,所建七十二疑冢实无必要,金人却对曹操冢加以增封,引以为知音,从而可见出金人诡谋深算的性格。范成大基于对“女真族狡猾贪婪”的集体记忆,对讲武城和曹操冢进行了否定性评价。楼钥经过讲武城,描述到:“(讲武城)犹有壁垒,气象雄壮。有将台甚高。城外高丘相望,号七十二冢,世传曹公之葬,以此惑后人,使不至发掘,或云其家数世所葬。有庙屋甚雄,即曹公祠也。”[49]以“气象雄壮”“庙屋甚雄”等正面词语来描述讲武城和曹公祠,“高丘相望”一词也展现了井然有序的情形。
如果说范成大、周辉、程卓等使金文人塑造的金地的荒凉形象是在宋朝语境下关于女真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的复制品,那么楼钥对金地的肯定性描述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集体想象的框架而进行的创造活动,是具有独创性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代表人之一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认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而集体描述是由产生形象的社会制作的。”(见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使金旅行记中的女真人粗疏无文;沦陷区的遗民生活悲惨、人心思汉;金地一片荒凉破败。遗民形象和金地形象更进一步佐证了女真族野蛮无教化的形象,三者共同构成了金国形象,总体呈现出负面、丑陋的形象。对金国形象的描述一方面是金国某种现实社会图景的反映,另一方面,它是宋人在既有的关于金国的社会集体想象基础之上,以文化泱泱大国的姿态言说出来的形象。透过对金国形象的描述,宋人完成了对自身文化大国形象的塑造,使金文人以他们在场的成分(对金国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金国),*法国学者保尔·利科提出形象学研究的两根轴,第一根轴为在场和缺席轴,“在这第一根轴的一端,形象指称的是它仅仅是痕迹的感觉,这是在在场变弱的意义上;趋于此端的形象,被看作弱印象,所有再现想象的理论都在这一端展现出来。在同一根轴的另一端,形象基本上是按照缺席,按照在场的他者构思的”。(见保尔·利科《在话语和行动中的想象》,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页)通过不断地否定他者,从而加强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
[2][3][4][27]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M].[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O)[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1,143,144,143.[5][7][9][13][21][22][24][45][46][49]楼钥.攻媿集[M].四部丛刊354册(卷一一一)[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6][39]周辉.北辕录[M].说郛三种(宛委山堂本卷五六)[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10][14][17][28][29][31][36][47]范成大.揽辔录[M].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C].北京:中华书局,2002.16,3,14,12,12,11,11,12,13.[11][12][16][30][32][34][38][48]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8,148,151,146,148,148,149,151.
[15][23][25][40]程卓.使金录[M].续修四库全书(第42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佚名.大金吊伐录校补[M].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1.82.
[19]熊克.中兴小纪[M].丛书集成初编(第3859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5.54.
[2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576.[26]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想象到集体想象物[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8.
[33]王栐.燕翼诒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35]布吕奈尔.形象与人民心理学[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3.
[41]吴松弟.中国人口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98.
[42][43]张金吾.金文最[M].续修四库全书(第165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90,235.
[4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15.
(责任编辑李晓丽责任校对李晓丽)
2016-05-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宋代旅行记研究”(项目编号:14CZW02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成果(项目编号:2015M570793)
阮怡(1984—),女,四川成都人,讲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宋代文学研究。
K206.6
A
1001-5140(2016)05-009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