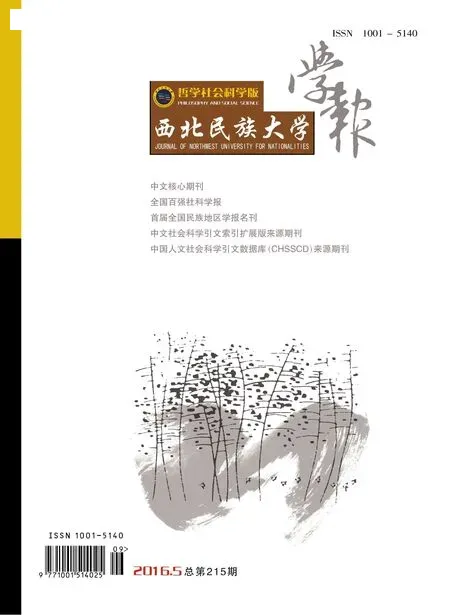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
2016-02-19管彦波
管彦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
管彦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唐统治者在深刻总结历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在具体经略边疆的过程中主要推行的是有利于增强周边民族对唐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繁荣的怀柔与安抚之策,但唐统治者在强调怀柔与安抚的同时并没有废弃军事防御与征讨,讲究的是“恩威并举”。
唐朝;怀柔与安抚;防御与征讨;安边策略
在中世纪李渊缔造的大唐帝国存续的三个多世纪中,其恢宏的气势和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通过一系列“武功文治”安边策略的推行,建立了“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的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一、唐统治者对治边历史经验的认识
古人关于行政疆域及对周边民族的认识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明显的在理论上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一是以华夏为中心联系四方民族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念;二是强调夷夏之别、端正王朝正朔的所谓“春秋观念”。这两种理论流派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演进中,作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甚至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又相互转化。但就整体的演变趋势而言,随着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进程的推进,民族融合、交往的加强,夷夏一体或华夷一体的大一统观念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思想,为古代的政治家们制定边疆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魏晋南北朝民族大分裂、大融合、大汇聚、大迁徙之后重新走向统一的隋唐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唐的开国者及其后继者们对夷夏一体或华夷一体的大一统观念、对周边民族的认识较之以往的统治者整体上有所提高和升华,如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家族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家族,李渊在开基创业过程中也曾得到不少民族上层的相助,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比较客观,少有重汉轻夷的思想。李渊之后的唐太宗更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他反对把“夷狄”划归为异类,反对以汉族的服饰、礼仪、伦理道德及生活方式为标准去衡量和规范少数民族,针对历史上“贵中华,贱夷狄”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观念,明确提出了“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2]的主张。唐太宗这种视夷狄与华夏为一家的民族观,为其后继者们奉行不辍,对唐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的开国君主们能够对夷夏一体或华夷一体的思想有更深刻认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没有很好地处理和化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民族间纷争、冲突乃至战争时常发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的历史教训有了清醒认识;同时,他们又亲眼目睹隋朝的灭亡,十分清楚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隋炀帝纵欲无厌,兴兵辽左,急敛暴欲,由是而起”,“不戢自焚,遂亡其国。”[3]正是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各民族采取“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4];“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以威恩羁縻之”[5]的怀柔政策。由于唐王朝所推行的以怀柔与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安边政策,在经略边疆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唐朝才实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6]的盛世局面。
二、唐朝主要的安边策略:怀柔与安抚
唐朝的开国者们在深刻总结历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从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出发,基本上沿袭了历史上怀柔与安抚的安边策略。
在古代,怀柔是指用政治手段来笼络其他的族群或地方政权,使之归附,意思与之相近而又有所区别的一个词是含有束缚、笼络使之不生异心之意的羁縻。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使用怀柔之策和羁縻之法来治理边疆并非是唐代的首创和发明,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新的内容。
大唐的缔造者李渊在东征西讨、剪除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建立李唐王朝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经隋末战乱人户流离、经济崩溃、人心思定的世态民情,深知“抚民以静”、“绥之以德”的紧迫性,所以在立国伊始就明确提出了“使民安静”和“怀柔远人”的主张,并于武德二年(619年)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其诏曰:“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日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译,美周邦之长筭。有隋季世,黩武耀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朕祗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其吐谷浑已修职贡,高句丽远送诚款,契丹、靺鞨,咸求内附,因而镇抚,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和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7]
这个根据当时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深刻反思隋炀帝治边政策,表示要革除前朝旧弊、接受隋朝因为穷兵黩武而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制定的诏令,是以承认周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差异为前提,体现了以怀柔为主、于民以静的安抚思想,成为李渊的后继者们在协调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时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李渊之后的唐太宗在一系列气势恢宏的开疆拓土过程中,可以说是怀柔与安抚治边思想的成功实践者。早在其即位之初的武德九年(626年)就曾对萧王瑀说:“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8]贞观元年(627年),岭南酋帅冯盎、谈殿等互相攻击,诸州乃奏冯盎反,太宗本欲派兵前往征讨,后在谏议大夫魏征的劝说下,派李公掩持节慰谕,冯盎受感化,遣子随使入朝,“一介之使,而岭南遂安,胜十万之师。”[9]后益州僚人骚动,都督李轨奏请出兵讨伐,太宗不允,指出“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耶!”[10]贞观三年(629年)招抚党项羌后,“其酋长细封步赖即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11]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指出,“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来降服,或曰未归附,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12]又《旧唐书》卷3记载,贞观二十年(654年)八月,太宗“幸灵州……铁勒、回纥……等十一姓名遣使朝贡。……乞置汉官……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于是,北荒悉平。”
唐太宗不仅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奉行怀柔与安抚的治边政策,而且他还对边疆少数民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如贞观十八年(644年)他对群臣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阳黎,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其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13]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4]这些史料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唐太宗认为对待少数民族不应该互相猜忌,而应该积极安抚、施以德泽。同时,他还认为边疆之患不在少数民族,而在于中原王朝的措施策略和民心,这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边疆之患在于夷狄的看法。
唐前期,高祖、太宗等大唐的贤君们对周边民族的怀柔与招抚是分时段、分区域灵活运用的。一般而言,对西部和西北地区唐采取的是以进攻、开拓、镇守为主导的策略,而在西南、岭南地区普通的做法是推行怀柔招抚的治边策略,即通过本地区本民族最有影响的酋帅进行宣谕抚定,尽量不动用武力。如武德初,韦仁寿检校南宁州都督,设立8州17县以羁縻抚慰之。武德四年(621年),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招抚96州得户60余万。太宗即位之初,益州都督窦轨奏称僚反,请发兵讨之,太宗不许,说:“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15]太宗之后的许多唐统治者,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时继续贯彻这一基本方针,所以我们看到在有关唐代的文献典籍中,唐王朝派出的被冠之以“安抚”“宣慰”“诏谕”“抚纳”“抚慰”“绥辑”“慰安”“驰抚”“怀辑”“慰晓”“临抚”等不同名称的安抚使,可谓是不绝于史。
当然,尽管唐统治者所推行的怀柔与安抚的治边政策基本上贯穿于唐王朝存续的近300年间,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帝王和不同的形势下,怀柔与安抚中所表现出来的“威”与“惠”是有不同侧重点的,即威服与怀柔的色彩有浓淡之别。这些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怀柔与安抚思想,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主要通过以下诸种形式呈现出来。
1.对一些内附的边疆少数民族,绥纳内徙,妥善安置。一般而言,唐廷对臣服的周边各族不改变其居住地、生产生活习惯和社会组织结构,只是在其地设置一些羁縻府州,仍旧任命本民族的首领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当边疆民族大批内迁时,唐廷则是在缘边诸州设置许多都督府、州来妥善安置之。对于这些侨置的羁縻府州,他们的户口不入边州籍账,同样以羁縻府州的形式管辖。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把东突厥10万降户安置在河南、朔方之境,从幽州至灵州之间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颉利地置定襄、云中二都督府。与此同时,太宗为了很好地“怀辑”、“安抚”东突厥降户,还分别封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为怀德郡王、怀化郡王,“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16]自安置东突厥降户后,绥纳内附民族成为唐廷安抚周边民族的一种惯例。贞观六年(632年)唐廷把内迁的铁勒部落六千余家安置在甘、凉之间,拜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十年(636年)又把内附的突厥部落万余家安置在灵州北境,拜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调露元年(679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17]
2.因势利导,妥善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或边疆民族内部的冲突与纠纷。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首领的上层或各种地方政治势力之间,常常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彼此互相兼并,矛盾冲突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唐廷为了自身边疆的稳定,不会坐视不管听任矛盾激化,而是积极下诏调停,并派出使节前往招抚,责令边疆各民族首领,“各保所部,无相争伐。”
典型的事例如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今云南省楚雄以东至滇、黔、桂和滇、越交界处的一些民族首领之间发生了纠纷,唐中央派安道训持皇帝的诏书前往“宣问”,设法加以调停。当时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是这样说的,“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指唐朝),并识王化。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审察,亦有事由。或都府(指安南都护府、姚州都督府、戎州都督府)不平,处置有失,或朋仇相嫌,经营损害。既无控告,自不安宁。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则既渐风化,亦当彼革蛮俗。有须陈请,何不奏闻。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训往彼宣问,并令口具。有闻便可一一奏闻。秋中已凉,卿及百姓并平安!”可以说,有唐一代像这样的招抚屡见史载。如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内乱,其王被杀,新立的诺曷钵年幼无法控制局面,大臣争权不已,太宗遂派侯君集前往安抚。十五年(641年)吐谷浑再乱,唐廷又遣唐俭为安抚使持节抚慰。在唐中宗时(705年-709年),海南“崖、振五州首领更相侵掠,民苦于兵”,于是,朝廷派岭南采访使宋庆礼深入黎洞,谕之以理,使黎洞之间“释仇相亲,州土以安,罢戍卒五千。”[18]又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由于岭南节度使赵昌对海南俚僚“推恩示信”,使“琼管儋、崖、振、万安等州峒俚来归,进五州六十二峒归降图。”
3.无论是内附还是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可汗、国王、酋长以及他们的子弟,一旦入朝,唐朝大都要对其封官加爵,授予显赫的官职,享受和汉官一样的待遇,并允许其子孙袭其职。如武德三年(620年)牂牁蛮首领龙羽请内附,被授牂牁刺史,封夜郎郡公。武德七年(624年)韦仁寿招抚云南各族后,“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贞观三年(629年)突厥的突利可汗自请入朝,太宗优待之,并于次年授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四年(630年)唐平定东突厥汗国,太宗不仅归还颉利可汗的家属,还封其为右卫大将军,死后赠其为归义王。同时,“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19]二十二年(648年)奚族首领可度者归附,唐拜其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授楼烦县公,赐姓李。契丹酋长窟哥归附,唐拜其为左卫将军兼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永徽元年(650年)唐升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为右骁骑大将军,并令他回国为王,且赐物一千段。与此同时,唐朝还大量起用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为政府官员和将领,使之直接服务于朝廷。据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唐代外族出身人物表”统计,唐代少数民族出身的大臣被封为王和郡王的15人,公爵26人,被任命为宰相一级的21人,元帅和副元帅5人,大将军和将军20人,节度使49人[20]。
4.减免边疆民族地区的赋税。大唐的开国君主们鉴于隋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悟出了“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的道理,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尤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21],所以在高祖和太宗执政时就实行了轻徭簿赋、抚民以静的方针,注重减轻边疆民族地区的负担。他们为了安抚内附或征服的边疆少数民族,缓和民族矛盾,对他们往往是免征或少征税,各羁縻州的户口大多不加登记,即使是某些羁縻州登记了也不呈报户部。在广大的羁縻府州内,“荒梗无户口”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的府州“并无税赋供输,州县相承,唯图上标名额而已。”[22]但是,羁縻府州内的居民,无论夷夏都是唐朝的编户齐民。德宗时期还特别规定诸州的“夷僚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两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23]而“诸国蕃胡内附者”据资产多少区分为九等,按上、中、下三等输轻税。唐王朝这种有别于内地的赋税政策,确实对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如德宗时南诏清平官郑回曾对南诏王异牟寻说:“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仪,以息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苦,利莫大焉。”[24]
上述基于怀柔与安抚治边思想之下的一系列措施在边疆地区的广泛推行,不仅减少了各族之间的冲突,缓和了民族矛盾,还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唐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
三、怀柔与安抚政策并非废弃军事防御与征讨
唐朝根据边疆与内地不同的经济特点与社会结构,在归附的边疆民族地区设置大量的有别于内地州县的羁縻府州,并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通过和亲、册封等不同的手段,极力安抚周边民族。但是,在怀之以文德、羁縻而受之的同时,并不是说在边疆地区就不需要军事防御与征讨了。
由于边疆与内地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边地游牧经济的脆弱性,都决定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矛盾冲突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所以自秦汉以来成功的经验是,强调怀柔招抚并不是放弃军事上的防御;相反,怀柔与安抚政策的顺利推行则是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对于这种攻守之间、攻弛之际所蕴涵的深奥的政治军事艺术,对于“恩”与“威”的辩证关系,唐代的明君贤臣们是拿捏得比较到位的。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他下诏说:“安人静俗,文教为先;禁暴惩凶,武略斯重。”[25]高祖之后的太宗也认为,“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妄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26]又《旧唐书·回纥传》史臣云:“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陀,而回纥兴焉。太宗幸灵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其仪何哉?盖以为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甚矣!”这段史臣评语中强调了唐朝民族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是怀柔即“惠”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威”即威慑、震慑。
深谙文武之道的唐代明君贤臣们在处理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和”与“战”的关系时,处处都表现出恩威兼顾的思想。具体如下:
唐朝立国之初,突厥势大,控弦百万,数掠边境,危及唐王朝社稷,但由于李唐王朝刚刚建立,尚无力对抗突厥,于是便采取积极防御以求和的方针,与突厥盟誓,约为昆弟,嫁公主给突厥,形成翁婿、甥舅关系,借以稳定突厥。尽管如此,在武德五年(622年)突厥大举南犯时,有人主张避免与突厥交战,而中书令封彝则认为,“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能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和,则恩威兼著矣。”[27]高祖采纳了封彝的建议,击败突厥而求和。唐太宗即位后,经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国力大增,武备更强,于是在贞观四年(630年)以武力削平了突厥对北疆的威胁。唐高宗末年,降唐的突厥人乘唐朝竭力攻伐高丽和对付西部吐蕃的侵扰、北方兵力被大量抽调之机,建立后突厥汗国,并不断派兵南寇边州,屡败唐军,成为唐朝北边的大患。唐高宗驾崩后,由于武则天推行消极防御的政策,致使后突厥汗国日益强盛,屡屡南下抢掠边州人畜和财物,对唐朝的北部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唐中宗复位后积极加强边防,修筑了攻守兼备、防守与巡游相结合的三受降城防御体系,抑制了后突厥的南侵势头。这说明在安定北部边境时,唐朝所采取的是征讨与防御并重的措施。
在处理与薛延驼的关系时,针对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势力不断强大的薛延驼,在朝廷安排已经归降的突厥旧部的过程中从中作梗,不希望归降之突厥返回漠南,唐太宗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命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可汗一封玺书。“颉利既败,其部落咸来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僚,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国贵尚礼仪,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于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28]唐太宗诏发这份玺书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唐廷出兵边塞,主要是为了打击叛离的少数民族首领,而一旦这些民族归附大唐则一视同仁,给予抚恤,还其故地,保其繁衍;二是希望边疆各民族首领各保其土,和睦相处,不得相互侵扰,否则朝廷则出兵征讨。玺书发出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是奉命北返的李思摩被诏书感动,并与突厥其他降部迁往漠南,于是漠北至西北地区,“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触木昆等国皆附之。”[29]二是薛延陀藐视天可汗的权威,发兵南下,屡扰唐境。
针对薛延陀踰漠而下犯唐内地的实情,贞观十六年(642年)薛延陀夷男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匹,太宗在与左右侍臣讨论解决薛延陀问题时再次提及了征伐与抚慰之策。他说:“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策也。未知何者为先?”[30]后来,唐太宗采取先讨后抚之策,经过精心准备后出师薛延驼,并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在诺真水一战中大获全胜。唐军获胜后,太宗在训斥薛延陀的使者时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经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31]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军彻底击破薛延陀,在处理薛延陀与大漠地区各部族的关系中仍然是本着“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原则,对“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铁勒十一部落进行了妥当的安置。
在处理与吐谷浑、吐蕃的关系上也表现了安抚、怀柔与防御、征讨并重的安边策略。唐太宗贞观初年,吐谷浑伏允可汗在遣使朝贡并向太宗请婚的同时,还派兵抢掠鄯、廓等州,既不尊王来迎亲,又拘留唐使,“肆情拒命,抗衡上国”,于是朝廷发兵征讨,“穷其巢穴”。吐蕃与唐王朝相争了200多年,在长期的对峙中双方实力彼消此长,吐蕃常要掳掠边州,唐则报之以征讨和防御,但是谁也不能消灭谁,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各自政治、军事力量完成了由盛而衰的转变。当双方矛盾处于缓和之时,或者是在争斗的间隙,唐也没有忘记采用册封、盟誓、和亲等怀柔政策来调整双方的关系。
对高昌的招抚与征讨。地处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本是汉代车师前王廷,汉魏均在此设置管辖,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贞观初年即已朝贡,太宗对高昌王麴文泰的赏赐甚为丰厚,其妻宇文氏请属王室,唐即赐之姓李并封为常乐公主。但随着唐朝对西域统治的加强,高昌与唐朝的冲突渐渐增多,不仅与西突厥相通,不再应诏纳贡,还屡屡阻塞西域诸国入朝之路,寇掠商旅和朝贡者,甚至“文泰犹为不轨,敢兴异图事,上无忠款之节,御下逞残忍之志”,“缮造宫室,劳役日兴,修营舆辇,僭侈无度,法令深刻,赋敛无度”,并大言“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何为拜其使者!”[32]于是,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军讨服之,并将其地改设为西州。
唐朝对岭南地区的开拓与经略,主要推行的是招抚政策。据史载,河间王孝恭“迁襄州道行台左仆射。时岭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绥辑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号令畅南海也。”[33]但当岭南地区出现叛乱仍没有放弃使用武力平叛。如贞观十二年(638年)钧州僚叛,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明州山僚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十四年(640年)广州都督党仁弘率兵讨之,虏男女7 000余人[34]。又公元789年唐岭南节度使曾派遣其属下孟京会同崖州刺史张少逸,领兵讨伐琼州不服从唐政权管辖的俚洞酋豪,并于海南“建立城栅,屯集官军”,有效地加强了对海南的统治。
由上面我们所举的具体事例可以看出,唐王朝在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所采取的怀柔与安抚之策,是以强大的武力和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胜而后和,恩威兼著”,即在武力平定和威服的基础上又转而采取招抚、怀柔等平和的手段,通过和亲、册封、赏赐等各种不同的安抚措施,有效地把边疆各民族都纳入大唐的版图之下,维持了“四夷怀服”的多民族国家局面,实现了“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郡县”[35]的宏伟气势。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8·地理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7.368.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125.
[3][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9·北狄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7.1368.
[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5·回纥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7.1331.
[6][21][26][唐]吴兢.贞观政要集校[Z].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290,11,484.
[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689.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017.
[9][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021,6021.
[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南蛮下[Z].北京:中华书局,1997.1614.
[1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西戎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7.1350.
[1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217-6218.
[13][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198,6198.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077.
[1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7·地理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7.267-268.
[1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0·宋庆礼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7.1153.
[1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Z].北京:中华书局,1997.1318.
[20]肖之兴.隋唐两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A].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52-173.
[2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9·剑南西道[Z].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木刻本;转引自陈国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南疆羁縻州管理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23][唐]李林甫.唐六典[Z].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77.
[2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7·南诏蛮[Z].北京:中华书局,1997.1347.
[25][宋]王钦若.册府元龟[Z].北京:中华书局,1960.1896.
[2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高祖武德五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5954.
[28][2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一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137,6137.
[3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铁勒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7.1364.
[3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6·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Z].北京:中华书局,1956.6172.
[3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Z].北京:中华书局,1960.2386.
[3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6·礼乐六[Z].北京:中华书局,1997.119.
[3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下·南平僚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7.1614.
[35][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75.
(责任编辑贺卫光责任校对肇英杰)
On Tang Dynasty'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in Strategies of Frontier Placation
Guan Yanb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By comprehensively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frontier management in past dynasties, Tang Dynasty mainly implemented conciliation and placation strategies, which helped frontier people develop centripetal force and cohes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ang Dynasty, and which were also beneficial for frontier stability and unity of multiple-nationality state. However, while stressing conciliation and placation, the rulers of Tang Dynasty did not discard military defense and punitive expedition, that is,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Tang Dynasty; conciliation and placation; defense and punitive expedition; strategy of frontier placation
2016-05-29
管彦波(1967—),男,云南宣威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历史地理、生态人类学研究。
K242
A
1001-5140(2016)05-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