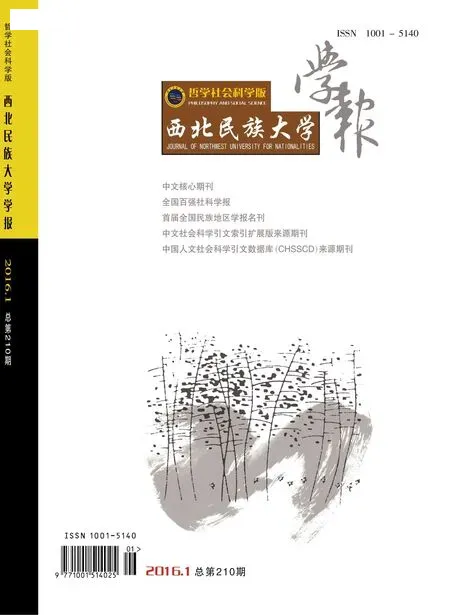早期中国伊斯兰教遗迹引发的思考
2016-02-19王宇洁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 宗教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 100872)
早期中国伊斯兰教遗迹引发的思考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 宗教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 100872)

[摘要]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亚与西亚的贸易古道,也是伊斯兰信仰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不论是在中国广袤的西部,还是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丝绸之路途径的地方依然留有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早期的重要印迹。根据伊斯兰教研究者的考证,这些印迹及与之相关的传说有时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它们将域外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记忆连接在一起,塑造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反映出穆斯林世界与中国交往的重要历史片段。
[关键词]中国伊斯兰教;丝绸之路;加法尔·萨迪克麻札;先贤墓
延续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更是一条人类文明融汇贯通、相互交融、相互学习的通道。随着古代陆地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外域宗教相继入华,而中国本土信仰亦假道外传,可以说,宗教的传播和互动是丝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天,不论是在域内还是域外,丝绸之路沿线众多的历史遗迹依然诉说着悠远的历史。而在这其中,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发展留下的印迹正是其中最为灿烂的一部分。
可以说,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贸易古道,也是伊斯兰信仰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不论是在中国广袤的西部,还是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丝绸之路途径的地方依然留有伊斯兰传入中国早期的重要印迹。根据今天学者们的考证,这些物质印迹和相关传说有些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有些则不能与历史完全吻合。但是,早期伊斯兰教遗迹中均寄托了中国穆斯林深厚的宗教情感,并形塑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记忆,更是穆斯林世界与中国穆斯林互动的一种表现。本文就以中国新疆地区和沿海各地几座伊斯兰教早期遗迹、特别是历史名人陵墓为例,对此予以分析。
一
在伊斯兰教对于基本宗教功课的规定中,拜谒圣贤的陵墓并不是一项必须的宗教义务。在正统的伊斯兰教义里面,对于如何对待圣贤的陵墓也无明确规定。但是,随着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尊重历史上那些曾对伊斯兰教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辈,并以拜谒其陵墓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穆斯林中的常见习俗。对于很多中国穆斯林来说,尊重和敬仰圣贤、以拜谒陵墓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宗教情感,也是自身宗教文化传统中重要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穆斯林先贤的陵墓,并成为各地穆斯林经常拜谒的地方。
在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新疆,就有不少围绕着穆斯林先辈的故事而出现的麻札。在众多的麻札中,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加法尔·萨迪克麻札尤其引人瞩目。自19世纪后期起,来自英国、法国、俄罗斯的旅行家在其记述中就多次提到了这座麻札。他们根据当时掌管麻札的宗教人士的叙述,对麻札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在别夫佐夫(1889-1890年游历此地)的记录中,麻札的管理人这样陈述麻札的历史:这座麻札里埋葬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加法尔·萨迪克。他公元890年前后出生在麦地那,为了传播伊斯兰教来到了中亚的布哈拉,而后到了喀什噶尔,并一直向叶尔羌和和田地区进军。由于当地佛教力量的反对,他们被和田地方领主的大军所追杀,最后在尼雅河畔受重伤去世。他的战友洗净了他的遗体,葬在了此地。后代虔诚的穆斯林又在墓上建起了清真寺。由此形成了加法尔·萨迪克麻札。[1]
1891年,迪特尔尤·德·朗斯调查团在去西藏探险的途中,从和田到了尼雅,访问了这座像“沙海中的浮标”一样的麻札。管理麻札所属马德拉萨(经文学校)的谢赫告诉他们,这里埋葬的是哈里发阿里的第五代子孙加法尔。他为了传播伊斯兰教来到了和田,在这里与和田王进行了决战。双方兵力悬殊,真主降了暴风和沙尘掩护了加法尔一方,但是最终双方两败俱伤。血战的痕迹被真主降下的大沙暴全部掩埋。直到两个世纪之后,一些中国穆斯林发现了伊玛目倒下的地方,在这里建起了麻札和清真寺,而后又建立了马德拉萨。[2]
之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队员橘瑞超(Tachibana Zuicho)都曾访问过这座麻札,并留下了详细的记述。[3]
二
日本中亚史学家佐口透(Saguchi Toru)在《新疆穆斯林研究》一书中,对别夫佐夫和迪特尔尤的记录进行了分析,他说:“殉教故事有一些不同之处,特别是关于加法尔·萨迪克的出身,两资料有若干不同。”[4]他所认为的差异就是,前者的记录认为加法尔·萨迪克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而后者则说他是伊玛目阿里的第五世孙。但是,如果我们对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的历史有了解的话,就知道他所认为的这一差异并不是问题,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嫁给了伊玛目阿里,所以阿里与法蒂玛的后裔本身就是先知流传在世的惟一一支血脉。加法尔·萨迪克本人确实既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六世孙,又是阿里的五世孙。
但是同样的,对伊斯兰教历史的了解让我们知道这座所谓的加法尔·萨迪克麻札不可能是什叶派所尊奉的第六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陵墓。加法尔·萨迪克原名为加法尔·伊本·穆罕默德,他是第五伊玛目之子,生于公元702年,被称为“诚实者”,故常被称为“加法尔·萨迪克”。在他任伊玛目期间,遵循其父辈疏远政治的态度,把主要精力放在研习宗教思想上,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宗教学者之一。跟随他学习的,不仅有什叶派信徒,还有逊尼派信徒。据传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中的哈乃斐学派的奠基人阿布·哈尼法和马立克学派的奠基人马立克都曾就教于他门下。他通过授课讲学培养出的圣训学者和其他宗教学者多达4000余人。而他和第五伊玛目传述下来的圣训要比其他所有伊玛目传述的总和还多。
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一生中并不曾涉足和田。他先是被伍麦叶哈里发囚禁于大马士革,而后又被阿拔斯哈里发软禁于萨马拉(Samarra),时刻监视。最后他被获准回到麦地那,在幽居中度过了余生,一直到公元765年去世,而后安葬在了那里。
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无疑是值得后世穆斯林尊重的。但是他对伊斯兰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渊博的宗教学识,而不是像中国穆斯林所传说的那样率领士兵一路东行,到今天的新疆一带来传播伊斯兰教。当地穆斯林关于加法尔·萨迪克的传说,无论是其发生的时间,还是具体事迹,都与真正的第六伊玛目无法吻合。也就是说,加法尔·萨迪克麻札里埋葬的,并不是第六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
后人根据考证,一般认为这座麻札大约建成于公元12世纪,也就是新疆地区第一个伊斯兰教王朝——喀喇汗朝战胜信仰佛教的于阗那段时期。喀喇汗朝的军队确实与于阗的李氏王朝在尼雅河畔有过一场决定性的战争。[5]据此推测,应该有早期的穆斯林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被就地安葬在附近。因而,我们可以推测麻札里确实埋葬着殉教者,而且很可能是领导这场战争的首领。不过,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第六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
喀喇汗朝的主体是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之所以皈依伊斯兰教,与当时中亚萨曼王朝的影响密不可分。[6]在现有对萨曼王朝的研究中,多显示这个王朝以波斯人为主体,崇尚波斯文化,但是尊奉的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推行的是哈乃斐派教法。在受到萨曼王朝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的土地上,一座埋葬着此前殉教者的陵墓却被附会成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陵墓,并最终发展成为著名的宗教圣地,其原因究竟在哪里?目前的资料和研究无法向我们显示这段历史的全部面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和田地区,除了最大加法尔·萨迪克麻札之外,还有以什叶派的第四伊玛目到第十二伊玛目命名的九座麻札。[7]虽然这些麻札不可能是什叶派诸位伊玛目的陵墓,但是为什么它们会如此密集地出现在这里,或许正体现出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多来源、而非单一来源的典型特征。而揭示中国伊斯兰教如何在域外影响下兼容并蓄地发展出今天的形态,或许是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然,除了这些托伪的麻札,南疆还有大量真实的麻札,比如萨杜克汗麻札、阿帕克和卓麻札等等。对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历史的追溯,也许并不能仅限于早期来自萨曼王朝的影响,之后来自中亚的苏非派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对麻札的历史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得出这座麻札里安葬的并不是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结论,并不会影响这座麻札在穆斯林中间的威望。每年夏秋两季,都会有来自新疆各地的穆斯林前来此地拜谒。当地穆斯林中间更是传说,只要虔诚的来此朝拜七次,就等于去麦加圣地一次。可以说,加法尔·萨迪克虽然没有埋葬在这里,但是他却以这种方式在中国穆斯林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
我们把眼光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会发现虽然距离遥远,但加法尔·萨迪克麻札并不是一个特例。由于早期的穆斯林来华,多从商业贸易口岸而入,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也留有类似的清真寺、圣墓等早期穆斯林留下的遗迹,还有与此相关的丰富的历史传说。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以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为标志。但是根据学者的研究,在此之前,东南沿海商埠——比如广州,就已经有外来穆斯林生活和居住。在广州,就留有怀圣寺、怀圣寺塔和宛葛思墓等早期中国伊斯兰教遗迹,且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最古老的清真寺塔建筑和最为古老的清真先贤墓。[8]
据中国穆斯林的民间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宛葛思曾在唐贞观年间被派到中国传教。他在广州城西(今光塔街)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作为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因寺内建有高塔一座,被称为光塔寺。这座塔既有“五鼓登绝顶呼号”、即唤礼之用,又被用来“祈风信”,并“夜则燃火、以导归帆”。据称,为怀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该寺改名为“怀圣寺”,此塔也被称为“怀圣塔”。宛葛思在广州去世后,门徒将他葬在广州城北桂花岗。墓室呈上圆下方的拱形,形如悬钟,墓里如有响声,语声相应,移时方止,因此既俗称“回回坟”,又称“响坟”。广州解放后该墓地正式改称为“清真先贤古墓”。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城,自唐代开埠即为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宋元时期,泉州享誉世界,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媲美。《马可波罗游记》记录此地“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而自遥远的马格里布而来的伊本·白图泰,则记载此地织造锦缎和丝绸,“房舍位于花园中央”“穆斯林单居一城”。今天这里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遗迹依然随处可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坐落于城市中心的清净寺,以及泉州郊区的灵山圣墓。据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条》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按照这一说法,民间传说灵山墓中埋葬的就是穆罕默德先知派来的两位贤士。
广州怀圣寺、回回坟,以及泉州的清净寺、灵山圣墓,其传说的来历都与早期来华的穆斯林有关。关于怀圣寺的历史,学界一直有唐建说和宋建说之争[9~10]。而对于回回坟中安葬之人是否确实为圣人舅父宛葛思,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亦有远赴阿拉伯地区留学的中国穆斯林学者,试图从当地文献中对这一人物的身份进行考证。关于宛葛思来华的时间,则有隋开皇中、隋开皇七年、唐贞观初年等不同说法。迄今为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确认广州清真先贤墓中人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属关系。有学者从阿拉伯史书中考证指出,作为先知舅父的艾布·宛葛思终生未到过中国。更有学者认为,公元904年,唐王任命的宁远将军艾卜·我葛仕(宛葛思之别译)为中国穆斯林所熟知,此人被误传为先知的亲属宛葛思。[11]
至于泉州清净寺和灵山圣墓的建造年代,学术界也存在广泛争议。杨鸿勋先生主唐武德说,庄为玑先生主唐永徽说,桑原骘藏主唐中叶至北宋说,而张星烺先生则认为是唐末宋初之后建造,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建造年代在9世纪以后至元代之间,[12]其时间跨度有数百年之久。鉴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少持谨严态度的史家认为伊斯兰教传入泉州,乃是中唐、也即8世纪中期之后的事情。[13]而穆罕默德先知传教乃是公元610年至632年之间,因而灵山圣墓中所葬之人,不可能为先知穆罕默德所派遣的两位贤人。
可以说,目前的研究尚无法确认这些陵墓中安息之人是受先知穆罕默德派遣来华的。正如加法尔·萨迪克麻札里面埋葬的不是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一样,不论是广州的宛葛思墓,还是泉州的两大贤人之墓,里面埋葬的都不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14]。尽管如此,研究者同时还发现最晚从元代时起,先知穆罕默德命弟子前来中国各地传教、并创建清真寺这种“回回家言”,逐渐成为广州、泉州等地清真寺和先贤古墓碑刻、匾联的常见内容。到了明嘉靖年间,这些教内说法“陆续被广东、福建地方史书乃至《明史》所采用或有条件采用,并在采用过程中、或采用前使中心情节发生某种变化”。[15]李兴华老师在对中国东南沿海历史名城的研究中指出,由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在许多情况下,以教内的口头传说、特别是流传历史较久的口头传说为基础,再结合有关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取舍作出初步的推断,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选择。[16]这也是对中国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但是自蒙元时期,广州穆斯林已经开始将怀圣寺和宛葛思墓作为“小圣地”来守护和崇敬。宛葛思墓在元政府支持下得到大规模的修整,并有专人守寺护墓。广州穆斯林尊宛葛思为“大人”,将他归真的日子、即伊斯兰教历11月27日作为纪念宛葛思、拜先贤墓的日子,并像过节一样举行“大人忌”等一系列纪念活动。而灵山圣墓,一样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元代以来,这里就受到穆斯林的崇敬和保护。满载货物的阿拉伯商船在起航之前,船上的穆斯林常来墓前瞻仰辞行,诵念《古兰经》并作“都阿”,祈求真主的赐福。航海家郑和在永乐15年第五次出海之前,也专程来泉州灵山拜谒先贤。
也许有人会说,托伪的历史遗迹说明不了中国穆斯林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联系。但是从历史记忆的形塑来看,这些历史遗迹恰恰说明早期来华的穆斯林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外来的穆斯林曾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影响着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并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将域外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记忆连接在一起。
在中国穆斯林对早期遗迹的历史讲述之中,或有不完全真实之处。但是它们之间均有一个惊人的共同之处,就是将曾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发挥作用的重要人物与伊斯兰世界身份更为崇高的人物、比如先知穆罕默德、比如什叶派的诸位伊玛目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发展出生动的、细节性的传说。这些传说以一种看似不真实的方式,塑造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反映着穆斯林世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片段。
躺在这些先贤古墓中的或许并不是中国穆斯林传说中的那个人,但是他或者他们肯定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早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当地的穆斯林,并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后期的中国穆斯林,将他们的历史和背景追溯到更远、更为高贵的层面,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这些穆斯林先辈们的一种纪念。这些伊斯兰教历史上伟大人物之陵墓,至今依然受到中国穆斯林的保护,这其中寄托的是中国穆斯林对早期来华的穆斯林先贤的尊重。
正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指出,古代的史实多由神话转化而来,层累形成。“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可以说,历史书写是累积形成的。人们对历史的追溯和重复,实际上是在对历史和自身身份进行新的塑造,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史中时有所见。在本文中提到的几处伊斯兰教早期遗迹及其相关传说和历史中,发生的正是类似的情形。
结语
今天,“一带一路”战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宏阔视野。在这一视野之中审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众多穆斯林人口多数国家的关系,关注这一战略与中国伊斯兰教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关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两千多万人口在这一战略推进过程中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已经成为一项紧要的任务。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正是陆地和海上双重丝绸之路的架设,为今天的中国与众多以穆斯林人口为多数的伊斯兰国家建立起了沟通的纽带。这些遍布“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伊斯兰教遗迹,既是历史上中外交流的证据,更是实现今日之互联互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夫佐夫.别夫佐夫探险记[M].佟玉泉,佟松柏 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74-75.
[2][4]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M].章莹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8-84,83,
[3]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M].柳洪亮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80.
[5]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201-211.
[6]陈慧生.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79.
[7]韩中义.西域苏非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59.
[8][15]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J].回族研究,2011,(1).
[9]陈泽弘.“广州怀圣寺光塔建造年代考”[J].岭南文史,2002,(4).
[10]廖大珂.“广州怀圣塔建筑年代考”[J].南洋问题研究,1990,(1).
[11][12]林翠如,庄景辉.“泉州伊斯兰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考”[J].海交史研究,2000,(1).
[13][16]李兴华.“泉州伊斯兰教研究”[J].回族研究,2010,(2).
[14]李兴华.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6-123.
(责任编辑洮石责任校对包宝泉)
[作者简介]王宇洁(1970-),女,陕西千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学、伊斯兰教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30
[中图分类号]B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1-0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