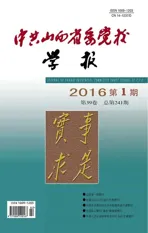社会制约:权力监督的有效形式
2016-02-17邸晓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天津300191
邸晓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天津 300191)
社会制约:权力监督的有效形式
邸晓星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天津300191)
〔摘要〕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德制权及以民制权。比较而言,以民制权的监督与制约方式体现了人民在权力运作中的主动性和基础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还存在主体不健全、缺乏理性与共识等问题。为此,完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需要适度放权,鼓励与培育社会制约主体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社会共识,提高社会监督制约的理性与有效性;此外,还需要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形成监督与制约的合力。
〔关键词〕社会制约;公共权力;社会共识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内外压力下由政府及执政党自觉推动的,这种做法有利于规避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保持政治秩序和社会的稳定,但却容易形成一个权力强大、无所不为的全能政府。为此,如何有效地对公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不仅是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作为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社会制约
权力具有两面性,它既是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的手段,又是对人民权利造成侵害的最大威胁。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使用权力的人以及权力运行的制度与规范。孟德斯鸠曾说,“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的权力滥用”,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势必会造成对人民权利的侵犯。因此,如何对权力进行约束,发挥权力的善性,就成为人们不断思索的一个问题,并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思想。大致而言,权力制约思想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主张通过法律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思想。该思想强调法的统治与法律至上,主张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规范公权力运行的边界与流程,从而达到防止公权力滥用的目的。这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所倡导的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方式。二是主张通过权力内部结构设置,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该思想注重制度的重要性,其出发点是“制度优于人性”,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必然导致暴政和腐败。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国家权力被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每种权力(机构)都有防御与制衡其他权力的手段,通过三权分离与制衡达到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和权力滥用的目的。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所倡导的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方式。三是主张通过权力主体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约束自身用权的思想。该思想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把外在的权力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行权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伦理道德人格,用道德的力量、内在的约束限制权力主体的外在用权行为,以防止权力的异化与滥用,这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所倡导的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方式。四是主张通过人民权利监督制约权力的思想。该思想强调通过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发挥公民从外部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的作用,这也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一种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倡导的自下而上的以民制权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方式。
与其他权力监督与制约方式相比,以民制权更能体现人民在权力监督与制约中的主动性和基础作用。政府权力滥用的直接利益受损者就是人民,所以人民在防止权力滥用上是最坚决、最可靠的主体力量。毛泽东特别强调这种制约监督权力范式,积极倡导“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西方学者J.凯恩也曾指出,(人民)如一只独立之眼,监督着国家,使国家不至于沦为专制〔2〕。人民作为监督的主体,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加之监督对象(政府权力)的集中性,可以形成一种“全包围”式的制约环境,这不仅从制度上更从心理上对监督对象造成一种压力,进而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同时,鼓励政治组织、社会团体与公民广泛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促使政府通过谈判、说服等协商方式与民众共同决定政策,既可以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实现合法的政治输入建立平台,又可以通过团体自治形成积极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培育具有自治能力和民主精神的社会公民。
二、我国实施社会制约的客观条件与现实问题
(一)社会制约的必要性与客观条件
其一,社会制约的必要性。社会团体在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单个人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通常是弱小的,但通过结合成为组织,弱小的个体就会获得加倍的力量而变得强大,进而成为制约公权力的重要因素。从我国的政治实践来看,通过社会力量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具有现实必要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其负责和受其监督,在这一制度制定之初,人们普遍存在对于立法权不受监督容易导致滥用的担心。但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告诉人们,最需要警惕的不是立法权的滥用,而是行政权的膨胀,人大对行政机关缺乏实际有效的制约手段,因而使得对行政权的制约效果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制约作用,就成为遏制行政权滥用的一种必然选择。
其二,社会制约的客观条件。从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来看,通过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具有可行性。一方面,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不同的利益需求,与此相应,社会分化为多元的利益群体,人们之间的交往也逐渐以利益为纽带,通过成立不同的组织来反映利益诉求,利益团体在整合成员需求的同时也具备了成员所赋予的权利和资源,从而具有了影响政府政策的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开放型社会、电子网络的普及也为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公民和社会团体不仅可以通过选举实现政治参与,还可以通过网络投票、公众舆论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影响政府决策。而且,在互联网环境下,政府行为及国家公务人员的活动还可以迅速被媒体和公民所了解,一旦发现存在权力滥用的现象,势必会在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压力。如对“表哥”“表嫂”“房叔”等事件的揭露,正是人民群众利用互联网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体现。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正是为了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了实现人民对于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
(二)实施社会制约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社会监督主体不健全。在社会监督过程中,单个公民通过结合成政治组织、社会团体等形式就会获得加倍的力量,进而对公权力进行制约。我国古代社会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传统下,家族和国家紧密相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社会团体没有产生的空间,难以形成组建社团的社会传统。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开始到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再到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状况,中国的社会事业主要依靠政府的主导与推动,包括社会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双重管制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自由发展。尽管自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取消了这一制度,但要形成积极表达、广泛参与的政治氛围,取得以社会制约公权力保障民权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适度放权、减少限制、降低门槛。
另一方面,社会监督与制约过程缺乏理性与共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同样,社会监督与制约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但这种力量一旦失去理性与控制,往往会具有破坏性与颠覆性。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与有效的监督手段,但同时由于网络用户信息的匿名性、群体责任的扩散性、即时互动性等特性,导致在一些事件上出现网络舆论非理性化现象。例如在2010年发生的“我爸是李刚”事件,随着事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网友直接“恶言相向”,更有甚者,发动人肉搜索,对当事人隐私“一挖再挖”,虽然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却侵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真假难辨的“一边倒”的信息更激化了公众的愤怒情绪。此外,在当下社会多元化发展趋势下,矛盾凸显、利益分化、看法多样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也已经是社会常态。在新常态下缺乏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基本共识极容易引发矛盾的深化。突出表现为作为社会监督重要的主体之一,部分媒体违背“探究事实,多方求证”的原则,不以纾解矛盾、促进不同群体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形成共识为目的,而以先入为主贴标签、编故事的方式迎合社会情绪,围观起哄、煽风点火,极易引发误解加深、对立扩大。
三、增强社会制约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适度放权,鼓励与培育社会制约主体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现代化进程等因素,社会组织在社会结构、发展程度、功能作用和运作模式等方面都明显依附于政府。为此,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都需要政府更加主动地作出让渡和制度设计。首先,政府主动转变观念,从根本上消除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误区,改变担心社会组织做大做强后会成为党和政府对立面的观念。其次,适度放权,责权分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当前,简政放权更多的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政府向市场放权,但政府向社会放权仍然不足。所以,在政府放权中需要充分重视中国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价值,对社会组织的建立、管制等方面予以适度松绑,加大社会建设力度,一些完全具备社会组织功能的事业单位应改造成脱离政府的社会组织,让其在法律轨道内健康成长。通过多管齐下,重新发现社会,培育好社会组织,为社会监督与制约公权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主体保障。
(二)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社会共识
以权力制约权力容易引起权力机构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而以社会制约权力则容易形成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西方民主理论学者罗伯特·达尔曾指出,“正如对于个人一样,对于组织而言,独立或自治也会有产生危害的机会”〔3〕。即便建立了民主形式甚至形成了民主运作的习惯,但如果没有社会各党派在基本原则和认同上的共识,党派间的斗争和多元团体间的竞争就会变成极端的对立和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导致社会的分裂。在人民权利主体之间同样如此,即便形成了民主政治参与的形式与习惯,但如果没有对于社会发展基本原则的认同与共识,多元团体间的竞争同样会变成极端的对立和冲突,各种组织出于自身利益而影响公共决策甚至会导致“最终控制”的让渡,形成国家政权机关无法对各种组织实行有效控制,公众权利被异化的结果。为此,在权力与权力间增进共识,可以减少政策冲突,在权利与权力间、人民团体内部形成共识可以避免公共议程的扭曲。我国正在步入多元社会,人民内部的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必须吸取其他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教训,发挥我国整体主义思想有利的一面,在国家权力机关内部凝聚共同而坚定的政治信仰,在利益分化、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中,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重大发展问题上增进社会共识,从而有效避免公共政策的扭曲。
(三)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相结合,共同发挥制约作用
各种权力制约方式既有优势也有缺陷,加之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因此从政治实践来看,基本上不存在单纯依靠某一种权力制约方式的现象。我国目前的权力制约方式主要有法律监督、党内监督、人大监督、人民监督等,相对而言,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制约主要通过影响、说服等“温和”的措施,依靠利害关系、舆论压力等促使政府权力作出妥协与让步,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因此,单纯地依靠社会力量无法有效地制约权力滥用或防止权力腐败,只有将社会制约和法律监督、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等具有强制力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机结合,才能切实增强权力制约的实效性。
总之,“主权在民”不仅仅体现为主权归属的主体是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来源于人民,同时意味着人民能够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权力的运转,人民能够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在我国积极倡导人民参与的社会制约机制,不仅可以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体现人民主权原则,还可以培育具有自治能力和民主精神的政治公民,为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奠定基础。同时,作为社会制约的主体,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必须不断走向理性与成熟,才能保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29.
〔2〕J. Keane.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M〕.London:Verso,1988:49-51.
〔3〕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周军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
责任编辑文丁
〔作者简介〕邸晓星(1984-),女,河北深泽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5-员2-15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6)01-01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