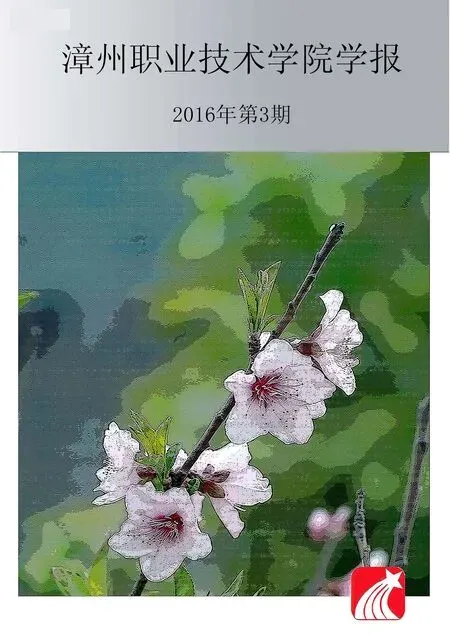环境风险与健康研究述评
2016-02-16颜彦洋
颜彦洋
环境风险与健康研究述评
颜彦洋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环境风险与健康的关系已成为跨学科讨论的热点。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以自然科学学科和以社会科学学科为视角的研究间存在立场差异:前者主要基于真实主义立场讨论环境-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后者则是真实主义立场和建构主义立场并存,重在探讨人们对二者关系认识的形成机制。环境风险与健康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地区间差异和人群间差异进行两方面进行呈现。基于文献回顾,提出了对环境风险与健康研究的展望。
环境风险;健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述评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类突发事故的发生,例如,早在1984年发生于印度的帕博尔农药厂爆炸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以及2015年发生于漳州古雷的PX项目爆炸事件等。风险语义已经逐渐超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风险被生产出来,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其中,环境风险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其影响不仅是当前一代[1]。
环境问题凸显的初期,人们只注重环境危害产生后的治理,但很多有害物质一旦进入环境,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2]。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已成为各大环境事件发生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对国内外有关环境风险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进一步厘清环境风险的内涵,总结环境风险与健康关系研究中不同学科视角的差异,从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地区间差异和人群间差异的角度出发梳理现有研究的成果,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环境风险与健康研究回顾
(一)环境风险的内涵
对环境风险的界定,学界大致遵循两种路径:流行病学、工程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更倾向于使用建立在对不良后果和发生概率的测量基础上的量化定义,如“环境风险(ER)=事故发生概率(P)*事故造成的后果(C)”,即将其定义为“由自发的自然原因或人类活动引起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3]。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部分遵循上述的量化定义路径,也有一部分对风险或环境风险进行“意义”上的理解,认为环境风险是被建构的。“环境风险”的定性特征主要包括了危险公平性、利益明确性、个人与家庭的涉入感、媒体的关注、对危害后果的防范信心等,是各方影响的综合体现,是被人所“感知”到的环境风险[4]。
融合上述两种路径,可以将环境风险定义为,由自然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并通过自然生态环境的媒介作用,对经济、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等构成威胁的一种潜在危险状态。环境风险是社会建构和科学评估的双重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能引发危害后果”两个特征。
环境风险广泛存在于人类生产与生活中,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例如,从风险源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化学风险、物理风险和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按照环境风险的承受对象划分,可分为人群风险、设备风险和生态风险。其中,健康风险是人群风险中最重要的内容[2]。
(二)环境风险研究概况: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研究视角
1.自然科学视角下的环境风险研究
环境风险研究起源于对自然灾害后果的认识与评价,研究初期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例如环境学、地质学等学科。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已对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67年,Glibert等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从单纯的地学领域向多个学科延伸。后来,学术界对环境风险的研究从自然灾害环境风险延伸至人为环境风险,尤其是重大技术引发的环境风险。例如1975年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提出了《核电站风险报告》,系统地建立概率风险评价法,并在后来发生的核电站事故中被证实[5]。目前,自然科学领域的环境风险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环境风险评价体系,评价内容包括:源项分析、危害判定,剂量-反映评价、暴露评价、风险表征等,并以此为据对环境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相关探讨[6][7]。
自然科学领域对环境风险的研究多是建立于真实主义立场上,将环境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当成真实存在的客体进行研究,并力图建立一套环境风险评价指标,将环境事件与各种可能的不良后果进行因果关联或相关性分析,健康风险是环境风险评估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与生态风险、经济风险等维度共存。
2.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环境风险研究
从社会科学视角对环境风险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学、传播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中。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较少探讨环境风险的指标体系。国内研究中,对环境风险的探讨集中于三个层面:第一,环境风险(议题)的呈现。例如,探讨环境问题中各主体,如企业、政府、居民、媒体对环境风险议题认知差异,以及在风险议题建构中各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过程[8][9];第二,环境风险的传播。行政学领域探讨了政府环境风险信息公开与民众之间的博弈过程,分析环境风险信息公开的类型和民众参与对风险信息公开的作用[10]。传播学注重探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环境风险议题的写作特点,具体包括话语特征、风险修辞、写作角度、角色设置、框架选择等[11][12];二是环境风险的传播特征,如基于风险社会扩大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各主体传播环境风险的特征进行讨论[13]。第三,环境风险管理与风险沟通,这一主题的研究集中于行政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中。有的学者注重探讨政府在风险防治中如何强化责任与规范管理,如何健全法律机制[14][15];有的学者则探讨了民众、政府、企业在风险沟通中的定位,指出民众与企业积极参与风险沟通的重要性,并强调风险沟通的时机选择应在风险未发生之时[8],另外,风险的理性沟通与各方信任的构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6]。
在社会科学领域,环境风险研究的出发点具有双重性——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并存。以真实主义立场为出发点的社会科学研究重在讨论如何对环境可能存有的不良后果进行干预,包括评估、防范、管理与制度完善等。以建构主义立场为出发点的社会科学研究更为细致地考察具有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特性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特定的环境状况被认定为不可接受的、有危险的,由此,形成了“危机状况”[17]。基于这一前提,环境事件与其潜在后果的关联方式、关联程度、各主体在建构风险过程中的作用、环境风险的呈现方式,人们如何理解环境事件与不良后果的关联以及人们的理解方式对应对行为的影响等议题成为建构主义者关注的重点。
由表3实验结果可知,用复合溶葡萄球菌酶溶液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白色念珠菌作用1、5 和10 min 的杀灭率均能达到100%。表明复合溶葡萄球菌酶溶液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白色念珠菌的杀菌效果理想。
从研究成果数量上,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环境(风险)与健康关系的成果量远不及自然科学。囿于社会科学学科知识的边界限制,现有研究尚不足以从科学的角度直接验证二者的关联,更多的是以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依托,探讨人们是如何理解疾病与环境之间的关联的,抑或辅以定量统计方法,结合自然科学研究资料对事件-健康后果的关联进行归纳,并利用有关理论作进一步的解释。
接着,笔者将结合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梳理国内外学者研究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学术成果,并从两个角度进行呈现:环境风险对健康影响的地区间差异和环境风险对健康影响的人群间差异。
(三)环境风险与健康研究成果
1.环境风险与健康关系的地区间差异
国外学者对环境风险与健康关系的研究部分存在于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当中,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发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内环境风险的分布不同,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对城市之间的健康影响差异的探讨,如Stevens等人结合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健康调查数据、环境危害因素对传染病的相关影响指标对各地区死亡率的大小进行比较,发现在墨西哥社区中不安全的水、燃料以及空气中的颗粒物对人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较大[18]。对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探讨,Lee的研究发现有色人种居住的社区面临更多的环境风险,居民罹患各类疾病比例较高[19]。对国家间差异的探讨,如Passchier-Vermeer的研究发现,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噪音暴露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20]。
我国环境风险对健康影响的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诸多学科对这一主题予以重视。城市居民主要受到垃圾焚烧、水污染、车辆废气排放、燃料燃烧释放的颗粒物等环境问题的威胁,使得罹患呼吸道疾病、肝癌、肠癌的人群比例增高[21][22]。然而,农村居民所面临的环境风险与健康问题和城市居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学者将农民称作“环境弱势群体”。为保证经济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和整体环境利益,农民环境权受到抑制甚至面临生存窘境,他们承担着与其所享受的权利不对等的环境义务[23]。整体而言,农村居民承受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问题要高于城市居民,他们面临着环境的不公正[24]。基于这一情况,笔者主要以“癌症村”的研究为例,对农村环境与健康问题研究的部分文献进行梳理。
“癌症村”一词在探讨我国农村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研究中较为多见,“癌症村”是媒体、政府和居民共同建构的话语,并非科学定义。它将“污染-健康-农村”融合为一个整体,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环境风险在我国城乡分布中的农村偏向。人类学者陈阿江曾总结了广东、江西、浙江地区中四个癌症村的背景情况,提出“污染-癌症”的关系认定处于一个连续谱中,分为若干依次递进的层次:(1)完全不确定(2)有较多依据与猜测;(3)对二者关系有确定的认识,即证实二者有关联。不同村庄的居民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受到外部认识(媒体、科学家和民间组织的知识)的影响较大,处在连续谱两极之间。另外,村民应对环境风险的行动方式主要经济因素和社会结构的制约[25]。他在另一项研究中,通过田野调查和统计资料分析,从“内”与“外”两个维度对淮河流域村民患癌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除了外源污染为代表的“外因”,村民日常生活的“内因”也可能致癌,并指出,对“内”、“外”关注的重心差异将会影响人们的疾病认知和应对方式[26]。另一位人类学者Wainwright以村民认知的角度探讨癌症的归因。研究发现,只有当把癌症归因于水污染会产生有利结果时,人们才倾向于把环境与癌症进行因果关联[27]。
这两位人类学者对环境与癌症关系的探讨遵循不同路径:前者结合统计数据和自然科学研究资料试图以真实主义的立场探究癌症产生的“内因”与“外因”,然而这种尝试缺乏严谨的论证过程,结论的可靠性有待商榷;后者从建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环境与癌症的关联是人们责任归因认知的一个维度且产生这种认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一研究思路巧妙地扬社会科学之长且避社会科学之短。
2.环境风险与健康关系的人群间差异
环境风险与健康问题的人群间差异除了在上述城乡地区所代表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存有差异外,拥有不同种族、年龄、贫富状况特征的人群在遭受环境引发的健康问题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
年龄层面。不少学者认为儿童是环境风险中的脆弱群体,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环境风险对其造成的危害比成年人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国内较早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业区的污染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影响,如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降低,姊妹染色体互换率高,相比较下,成人对污染的抵御力高于儿童[28]。国外学者Zartarian等人的研究发现,儿童是农药暴露的敏感人群,即使对化学物质集中接触较少,但由于他们的皮肤面积和体重比率、正在发育的各类器官、可渗透的皮肤以及较高的新陈代谢都会使他们比成年人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29]。
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层面。多数研究表明,有色人种与低收入人群是环境风险暴露的高危对象,同时也面临更严峻的健康问题。来自新西兰和英国的研究表明,低收入社区的人由于居住条件和外在环境比高收入社区差,更可能遭受不良环境所带来的健康危害[30] [31]。Evans则以铅暴露为例,综合考察了不同种族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在环境健康风险中的暴露情况,研究发现,住在城市中的非洲裔美国人中穷人的孩子高暴露于铅,而这种铅暴露会在两代之间传播,对儿童身体的影响持续到成年[32]。
职业层面。研究表明,工厂和农场中暴露于化学药品的工作人员是在环境风险中受到较大健康威胁的群体。例如,Metzger的研究发现,那些经常混合农药、装载农药的工人面临较大的健康风险[33]。Goldman等人的调查则发现,从事化学材料生产工作的父母可能通过工作服将化学物品带进家里,并把工作场域的环境风险携带到家庭中,进而影响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的健康[34]。
二、环境风险与健康研究展望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环境(风险)与健康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尝试着对两大学科背景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讨论环境风险研究的学科视角差异,并从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的两个层面——地区间差异和人群间差异对现有研究进行归纳。
环境风险研究的学科视角差异中,自然科学研究主要以真实主义立场为出发点,通过实验法、定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环境-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尤其重视环境风险评价,把实现有效的风险评估、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作为最终目标。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则体现出双重性——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并存。其中,基于真实主义立场的研究由于学科知识体系的限制,多是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实地调研资料对二者关系进行归纳与分析,论证方式以归纳法为主,结论难以推广且可信度较低。而基于建构主义立场进行的研究则巧妙地规避社会科学在探讨环境-健康关系的知识短板,多以研究人们应对环境风险的方式为最终落脚点,考察人们在面临环境风险的过程中如何建立环境与疾病的关联。在科学关系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究人们如何理解这些变量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媒体、政府或企业如何去呈现这一关系,以及人们如何应对风险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但现有研究中,这类研究仍十分有限,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从现有研究的视角选择和研究结果的呈现上看,环境风险与健康问题的探讨集中于片状或条块的探讨,即认为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制度安排、(种族)文化、生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环境风险分布不公正的现象,并以疾病的表现作为环境分布不公的重要依据对此进行探讨。然而,与工业的、阶级的社会相比,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分配要均匀得多。“贫困是分等级的,化学烟雾是平等”[35],学术界亟需对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风险与健康问题予以重视,目前鲜有这一主题的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面临科学关系不甚明确的议题时,应在掌握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发挥学科优势,以更规范、更严谨的实证研究去探讨人们如何认知环境与健康的关系,这种认知方式受何种因素的影响以及人们如何采取行动。或者,可以进一步探讨环境-健康关系的争论中各主体间的博弈过程,这对完善环境风险管理和实现理性的风险沟通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视野的选择上,学者们应尽可能地以全球生态公民的身份开展研究,重视跨区域或全球性环境风险的研究,对风险分布区域化和按人群划分的固有观念提出挑战。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毛小苓,刘阳生. 国内外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进展[J].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03, 11(3): 266-273.
[3]杜锁军. 国内外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进展[J].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06, 31(4): 193-194.
[4] Covello V T, Merkhoher M W.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approaches for assessing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s[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5] Keith S, Environmental hazard: assessing risk and reducing disaster [J].1992,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3(3):422.
[6]陈立新. 环境风险评价方法刍议[J]. 重庆环境科学, 1993 (4): 21-23.
[7]李跃宇,卢彬,宋永会,彭剑峰. 基于公众健康的大气环境风险源定量分级方法[J]. 环境科学研究, 2012, 25(1): 83-88.
[8]龚文娟. 约制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J]. 社会, 2013(1):161-194.
[9]李栋. 环境风险议题建构与互动研究——以“雾霾天气事件”为例[D]. 云南师范大学,2014.
[10]石磊,杜子超,王东波. 环境风险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的博弈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5(4): 93-100.
[11]王积龙. 西方环境新闻的风险写作[J]. 社会科学研究, 2009(1): 190-196.
[12]贾广惠. 环境风险传播议题的设置角色变迁[J]. 当代传播, 2012(5):36.
[13]邱鸿峰. 环境风险的社会扩大与政府传播[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8):105-117.
[14]张士萍. 论环境风险防治中政府责任的强化[D]. 吉林大学, 2013.
[15]蔡守秋. 论政府防治环境风险的法律机制[J]. 公民与法:法学版, 2011(10):2.
[16]陈寒. 浅谈我国环境风险沟通现状——以厦门市垃圾处理场建设为例[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79-81.
[17][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洪大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 Stevens G A, Dias R H, Ezzati M. The effects of 3 environmental risks on mortality disparities across Mexican communitie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 105(44): 16860-16865.
[19]Lee C. Environmental justice: building a unified vision of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02, 110(Suppl 2): 141.
[20]Passchier-Vermeer W, Passchier W F. Noise exposure and public health[J].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2000,108(Suppl 1): 123.
[21]杨维,赵文吉,宫兆宁,等. 北京城区可吸入颗粒物分布与呼吸系统疾病相关分析[J]. 环境科学, 2013, 34(1): 237-243.
[22]胥卫平,曹子栋,胡健. 西安市水污染人群健康损害评价[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4(2):37-41.
[23]李淑文,郭海霞,任大鹏. 环境正义视角下农民环境弱势群体地位分析[J]. 生产力研究, 2011(4):41-42.
[24]郭琰. 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J]. 学术论坛, 2008, 31(7):38-41.
[25]陈阿江,程鹏立. “癌症-污染” 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 “癌症村” 的经验研究[J]. 学海, 2011(3):30-41.
[26]陈阿江. “癌症村” 内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18.
[27] Wainwright, A. L. 2010,“癌症村”的人类学研究:村民对责任归属的认识与应对策略.选自Holdaway, L. 等(主编).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39-262.
[28]李凤英,钟磊石,王清江,等. 工业区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J]. 环境与健康杂志, 1993, 10(3): 97-99.
[29] Zartarian V G, Leckie J O. Dermal exposure: the missing link[J].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Industrial Medicine, 1998, 2(39): 78.
[30] Brainard J S, Jones A P, Bateman I J, et al. Modelling environmental equity: access to air quality in Birmingham, England[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4): 695-716.
[31] Pearce J, Kingham S.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in New Zealand: A national study of air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J]. Geoforum, 2008, 39(2): 980-993.
[32] Evans D T, Fullilove M T, Green L, et al.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protective actions among minority women in Northern Manhattan[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02, 110(Suppl 2): 271.
[33] Metzger R, Delgado J L, Herrell R.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Hispanic children[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995, 103(Suppl 6): 25.
[34] Goldman L, Eskenazi B, Bradman A, et al. Risk behaviors for pesticide exposure among pregnant women living in farmworker households in Salinas, California[J]. 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2004, 45(6): 491-499.
[35][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 洪大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马圳炜)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Risk and Health
YAN Yan-ya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Th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risk and health have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cus. Through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science is different from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The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science based on real socialist position to discuss the causality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eases. 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the research based on both real position and constructive stance, which emphasis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health. The studies mainly pres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two angles--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Based on the review, this thesis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environmental risk; health; natur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review
C913
A
1673-1417(2016)03-0053-06 doi:10.13908/j.cnki.issn1673-1417.2016.03.0011
2016-05-10
颜彦洋(1992—),女,福建泉州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