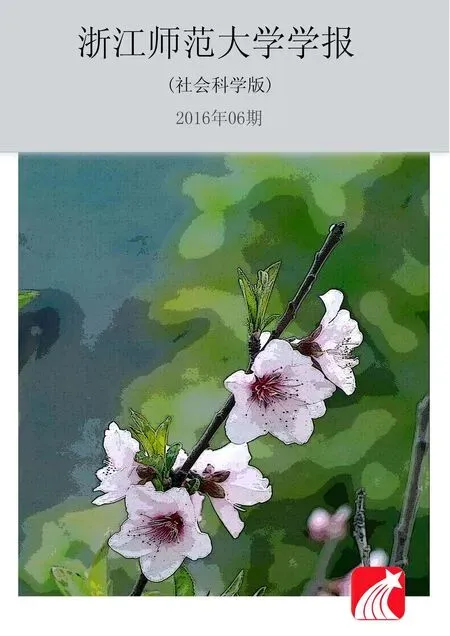《太平广记》编纂与宋初三教合一文化观念*
2016-02-16曾礼军
曾礼军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太平广记》编纂与宋初三教合一文化观念*
曾礼军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任何典籍编纂都具有时代性,都是在特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并且体现和反映了时代文化精神和编纂者主观意图。《太平广记》编纂以“道-释-儒”的“三教合一”板块结构来统绪类目和辑录文本,这种鲜明的编纂特征与宋初“三教合一”的文化新态势及《太平广记》诏修者的宗教文化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有着“三教合一”的文化整合意义。
《太平广记》;编纂;宋初;三教合一
《太平广记》是由宋太宗诏令李昉等儒臣编纂而成的类书体小说总集,共有92个类目500卷。向来为精英阶层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轻视和鄙弃的“怪力乱神”小说第一次受到了官方的重视和整理。《太平广记》编纂的突出特点是以“道-释-儒”的“三教合一”板块结构来统绪类目和辑录文本,这种编纂特点一方面是受到宋初“三教合一”文化新态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太平广记》诏修者重视文化典籍编纂以贯穿“三教合一”的文化整合目的。《太平广记》研究往往侧重于内在的文本探讨,而对于其编纂,特别是编纂的宗教性特征则少有问津,本文拟从宋初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对《太平广记》编纂作一分析。
一、《太平广记》编纂的“三教合一”文化特征
《太平广记》是一部宗教文化内涵丰富、宗教特征鲜明的类书体小说总集,其编纂的突出文化特征就是以“道-释-儒”的“三教合一”板块结构来统绪类目编排和辑录小说文本。由于类目编排是类书编纂的灵魂和主脑,它不仅统绪着类书辑录的文本,而且其类目分类及其编排次序体现了编纂者“对知识与思想的整合与规范”[1]454的文化意图和目的,因此《太平广记》编纂的文化特征可以从其类目编排来考察。
第一,从类目编排的结构来看,《太平广记》类目编排总体上呈现出“道-释-儒”三教“合一”的板块结构。(1)道教类目排在第一板块,包括“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和“异人”等类目。道教类目编排遵循“仙-道-人”的编排顺序,突出了神仙崇拜的道教文化本质。(2)佛教类目排在第二板块,包括“异僧”“释证”“报应”等类目。佛教类目编排典型地体现了佛教“三宝”灵验的文化内涵,三个类目分别契合了佛教三宝的“僧宝”“佛宝”和“法宝”。(3)第三板块是儒文化类目,这一板块是对传统类书类目编排的继承和创新,而传统类书编纂主要是为了建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知识体系,突出“敬天尊君的正统思想”,[2]41强化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故此处概称为儒文化类目。
儒文化类目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符命类目,包括“征应”“定数”“感应”和“谶应”等类目;二是人事类目,包括“名贤”(讽谏附)“廉俭”(吝啬附)“气义”“知人”“精察”“俊辩”(幼敏附)“幼敏”“器量”“贡举”(氏族附)“铨选”“职官”“权幸”“将帅”(杂谲智附)“骁勇”“豪侠”“博物”“文章”“才名”(好尚附)“儒行”(怜才、高逸附)“乐”“书”“画”“算术”“卜筮”“医”“相”“伎巧”(绝艺附)“博戏”“器玩”“酒”(酒量、嗜酒附)“食”(能食、菲食附)“交友”“奢侈”“诡诈”“谄佞”“谬误”(遗忘附)“治生”(贪附)“褊急”“诙谐”“嘲诮”“嗤鄙”“无赖”“轻簿”“酷暴”“妇人”“情感”“童仆奴婢”等类目;三是神怪类目,包括“梦”“巫”“幻术”“妖妄”“神”(淫祠)“鬼”“神魂”“妖怪”(人妖附)“精怪”“灵异”“再生”“悟前生”“冢墓”“铭记”等类目;四是物体类目,包括“雷”“雨”(风虹附)“山”(溪附)“石”(坡沙附)“水”(井附)“宝”“草木”(文理木附)“龙”“虎”“畜兽”“狐”“蛇”“禽鸟”“水族”“昆虫”等类目。
儒文化类目编排遵循的是由“天命”到“人事”、由“生”到“死”、由“人”到“物”的编排顺序。这种编排顺序实际上是传统类书编排体例的体现,如《艺文类聚》即按“天、地、人、事、物”的部类顺序来编排类目,遵循的也是由“天”到“人”、由“人”到“物”的编排原则,体现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体的知识体系建构。儒文化类目编排主体上侧重于人事伦理的知识建构,同时又包含了小传统的神怪信仰,弥补伦理道德无法触及的地方,以满足大众个体所需的精神信仰。事实上,“儒”本身也与鬼神文化关系密切,起源于通鬼神的巫祝。章太炎、胡适、徐中舒、葛兆光等前贤时哲从各个角度作过论述。所以《说文解字》曰:“儒,柔也。术士之称。”而此后的郊社祭祀、宗庙礼制都与鬼神文化有关,只不过这种鬼神信仰是礼制化的宗教信仰。因此,神怪类目是编纂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类书不可或缺的知识内容,《太平广记》对此作了继承。
除了上述三个板块外,《太平广记》最后还有“蛮夷”“杂传记”“杂录”等三个类目作为全书的补充。前者是基于夷夏文化对应的补充,后两者是基于小说文体性质的补充。
第二,从类目编排的顺序来看,《太平广记》类目编排凸显了道释宗教的地位优先性。道教类目被编排在第一个板块,体现了道教最优先的地位;佛教类目被编排在第二个板块,体现了佛教次优先的地位。宗教类目处于优先的位置折射了诏修者和编纂者对于道释宗教的偏爱和重视。
第三,从类目编排的比重来看,《太平广记》类目编排坚持了儒文化类目的主体性。虽然道释宗教类目被编排在优先的位置,但儒文化类目的比重是最大的。从类目的数量来看,道教类目有5个,占全书92个类目的5.3%;佛教类目有3个,占全书的3.2%;而儒文化类目有81个,占全书的88.1%。从类目所辑引文的卷数来看,道教类目辑有86卷,占全书500卷的17.2%;佛教类目辑有48卷,占全书的9.6%;而儒文化类目辑有345卷,占全书的69.0%。儒文化类目比重最大体现了儒家文化居于主体地位的文化观念,尽管道释宗教文化受到格外的重视,但儒家文化知识体系仍是《太平广记》编纂的主导内容。
概而言之,《太平广记》类目编排总体上呈“道-释-儒”三教合一的板块结构,同时又体现了道释类目优先性和儒文化类目主体性等特点,其编纂有着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
《太平广记》是第一部经官方手段编纂的类书体小说总集,具有官方主流意识与民间小传统文化互动的性质。所以《太平广记》编纂的“三教合一”文化特征还可以通过与历代官方编纂的类书和私家著录的小说集进行比较来探讨。
官方的类书编纂对佛道宗教文化的采纳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大致而言,唐代以前的类书编纂基本上没有涉及佛道内容,唐代开始采纳佛道内容,到宋初更为重视。试以唐初《艺文类聚》和宋初《太平御览》两书为例。《艺文类聚》是由唐高祖李渊诏令欧阳询领衔编纂的一部重要类书,全书46部100卷。《艺文类聚》在总结前代类书编纂的基础上,按“天、地、人、事、物”的部类顺序来编排类目,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3]60-61成为类书编纂的成熟范本。该书第一次编排了宗教类目,融合了佛道文化内容。《艺文类聚》的佛道宗教类目有“内典部”和“灵异部”两个,其中“内典部”分布在卷七六和卷七七,“灵异部”分布在卷七八和卷七九,两者分别处于46个部类中的第32部和第33部。从其编排顺序可以看出,宗教类目被编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葛兆光先生指出:“把佛教、道教相关的知识放在靠后的位置,并且只给予各二卷的篇幅,似乎既表明了佛教与道教在七世纪知识与思想话语系统中不可忽略的存在,又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佛教与道教的贬抑与排挤。”[1]457《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是同时同批人员编纂而成的,共有55部1 000卷,也是按“天、地、人、事、物”传统类书的类目顺序组织编纂。其中,佛道宗教类目也是两个,“道部”21卷,卷六五九至卷六七九;“释部”6卷,卷六五三至卷六五八。两者分别处于55个部类中的第21部和第22部,紧接着“天、地、人”类目之后编排,位置也十分靠前。这体现了宋初主流意识形态对佛道宗教文化的重视和采纳的主动性,与《太平广记》编纂重视佛道宗教的态度相一致。官方类书编纂对佛道宗教类目编排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但总体上并未形成一个“三教合一”的编排结构。这是因为官方编纂的普通类书是一种百科全书性质的典籍,主要是为了建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知识体系,佛道宗教虽然越来越为统治者所重视,但只能作为儒家知识体系的补充成分。《太平广记》与官方类书编纂最大的区别就是把作为儒家知识体系补充成分的佛道类目独立出来,并提前到类目编排的最前列,形成“三教合一”的编排结构。如果说官方类书编纂是偏向于文化大传统的整合,那么《太平广记》编纂则是文化小传统的整合,因而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板块结构。而佛道宗教类目的优先性则体现了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自信。
私家著述(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编著)的小说集是《太平广记》成书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因为《太平广记》的核心内容就是小说文本的辑录。古代小说虽然被视为怪力乱神之说,但佛教内容被小说书写直到南北朝才开始,此前是以传统鬼神和仙道内容为主体。[4]因此考察小说集中的“三教”内容,唐代小说集是重点。唐代小说集很多是按题材内容来分类辑撰的,但很少有标目者,以类目统绪文本的小说集以段成式《酉阳杂俎》为典型。《酉阳杂俎》共有二十卷,每卷都有标目。《酉阳杂俎》卷一“忠志”“礼异”是以儒家知识为主体,分别叙君臣佚事和礼仪异事;卷二“玉格”“壶史”是以道教故事为主体,叙仙道变幻之事;卷三“贝编”是以佛道故事为主体,叙佛门故事。此后,接着叙人事、鬼神和物体之异事。其中,卷四至卷一三侧重于人事生活的故事,卷一四和卷一五侧重于鬼神怪异的故事,卷一六至卷二○侧重于动植物的故事。由此可知,《酉阳杂俎》有了初步的“三教合一”编排结构,但还限于局部性的,只出现在前三卷中,并且编排的优先性是儒家而不是佛道宗教。这一方面表明《太平广记》的编排体例有其文化渊源性,不是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则表明唐代私家小说集编撰所体现的“三教”文化融合还不够充分,缺乏系统性,虽为小传统的民间著述却隐藏着以儒家为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
综上所述,《太平广记》编纂体例是在继承官方传统类书编纂体例和私家小说集编撰体例基础上的文化创新,不仅以“三教合一”结构编排类目,而且突出了宗教类目优先和儒文化类目的主体性,有着独特的文化个性。
二、《太平广记》编纂的“三教合一”文化成因
《太平广记》编纂的“三教合一”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宋初“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新态势和宋初统治者对于道释宗教的个人偏好密切相关。
三教合一是一个历史过程。黄心川认为儒释道“三教”发展经历了由“三教一致”到“三教鼎立”再到“三教合一”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是在排斥和斗争中求“一致”,隋唐则在意识形态进而在政治上形成“鼎立”态势,“宋元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见深,‘合一’的思潮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5]严耀中进一步指出:“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到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6]29其中,作为过渡性的中间阶段隋唐两宋时期,“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6]31而宋初就处于这样一个由三教鼎立趋向三教交融的重要转折时期。
儒释道“三教”总体上呈现出由“外”向“内”转型的文化发展态势,佛教的禅宗、道教的内丹学和儒学的“内圣”化即是“三教”向“内”转型的具体表现。“三教”向内转型使得“心性”论成为“三教”会通和合一的基本理论。所谓“心性”论即是心性之学,“心”被认为是认知主体,“性”则被认为是世界本体,心性之学是关于世界的认知论和本体论的理论和学说。佛教心性论强调通过“心”来觉悟万物为幻有,世界是“性空”的。传统儒学心性论注重伦理道德的文化内涵,孟子主张性本善,重视“尽心知性”,荀子主张性本恶,重视“化性起伪”。与佛教“性空”的本体心性论相比,传统儒学之“性”实为伦理道德概念,而不是世界本体指向。道教心性论强调通过身体内在的“丹炉”修炼来达到长生不死的生命追求,是自然人性论。“心性”论成为“三教合一”的会通理论,其会通和“合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三教”尤以儒释两家为主体,通过对“心性”论的改造和重构,使之成为“三教”都能够共同接受并引导其发展的理论基础。
以“心性”论为基础的“三教合一”自中晚唐就已经开始。如李翱曰:“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7]107“李翱用《易》之本体论描述‘诚’,使‘诚’也抽象为形而上的本体;同时,李翱还赋于诚以‘广大清明,照乎天地’的佛性色彩。”[8]这里体现了儒学向佛学心性论的借鉴和学习。同样,佛教也通过心性论来自觉地与儒学进行沟通。如延寿说:“三教虽殊,若法界收之,则无别原也。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总而言之,不离法界,其犹百川归于大海。”[9]608此处“法界”即是“心”,“一心法界,法界一心”。[9]544
到了宋初,尤以宋真宗朝为时间标志,在心性论的“三教合一”过程中,儒家开始掌握了理论重构的主导权,而佛道两家则自觉地朝着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方向发展。如张载明确提出“心统性情”说:“心统性情也。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10]374据此,张载从“天人合一”“体用一源”的观点出发,对佛教的“性空”“幻有”进行了釜底抽薪的批判。张载批判道:“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幽明不能举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11]670“性空”“幻有”的批判直指佛教理论的要害,凸显了儒学的强势和会通“三教”的能力。与儒家对佛教的理论批判相反,佛道两家则重视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导向性。如契嵩“把禅宗的心性说作为融合儒佛的理论基础,用‘圣人同心’来论证佛教与儒家并存的合理性;用‘自信其心’将外在的宗教信仰转变成对自我本心或本性的信仰。”[12]301他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老(按:‘老’,《大正藏》本作‘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13]660“圣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则为诚常,为诚善,为诚孝,为诚忠,为诚仁,为诚慈,为诚和,为诚明。”[13]656张伯端在《悟真篇》中也宣称“教虽分三,道乃归一”,[14]973在“心性”论的基础上,他强调修道养真还需与道德修养相结合:“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14]1015“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14]1008此后,随着宋明理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儒学为主导、佛道为两翼的“三教合一”的文化新格局。
《太平广记》成书虽略早于张载心性论的提出,但它与中晚唐以来以“心性”理论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文化大趋势是一致的,并且是处于儒学开始掌握理论重构主导权的临界点上。因此,《太平广记》以“三教合一”的类目结构来辑录宗教性和志怪性的文言小说,不仅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态势,而且蕴含了“三教合一”的文化精神。显然,《太平广记》的编纂结构是受到了“三教合一”文化观念的影响。
《太平广记》“三教合一”的编纂结构中突出了宗教类目的优先性,特别是道教类目的优先性。这与宋初两位开国皇帝对宗教的独特偏好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宋初两位开国皇帝政权的夺得都不具有“合法性”,他们需要特定的理论为其政权“合法性”进行论证和鼓吹,而佛道两教分别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佛教制造了“麻衣和尚谶言”和“定光佛出世谶言”,论证了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合法性”和“奉天承运”。“麻衣和尚谶言”见于《邵氏闻见录》卷七和《佛祖统记》卷四三,指出赵匡胤具有“天子气”,“当有真主出兴”。麻衣和尚谶言“表明太祖有作天子的定数”,象征着“太祖皇权的天意垂示”。[15]20“定光佛出世”谶言见于《曲洧旧闻》卷一,认为赵匡胤是“定光佛后身”。定光佛出世谶言则表明宋太祖“已取得佛陀的神格而以‘现在佛’的身份君临天下”。[15]36宋太宗赵光义的皇位是从其兄长赵匡胤手上篡夺过来的,所谓“烛影斧声”之谜即是对这种篡权行为的模糊表述。对此,邓广铭作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宋太宗即位“纯属篡夺性质,已是不容怀疑的定论”。[16]128因此,宋太宗的皇位和政权的“合法性”一如其兄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一样,令人置疑。而道教制造的“翊圣将军谶言”正好能够破除这种质疑。“翊圣将军谶言”见于《宋朝事实》卷七,叙述“真君”神高调宣扬“晋王有仁心”,当为“宋朝第二主”。“翊圣将军谶言”表明宋太宗承继皇位和政权亦是天意所示,具有“合法性”。佛道宗教为宋初两位开国皇帝的政权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和鼓吹,因此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尊宠。这种宗教尊宠表现在《太平广记》编纂上则是宗教类目置于前列,尤其是道教对于宋太宗皇位合法性的鼓吹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其类目被编排在最前列。
但宋初统治者崇教而不溺于教,并不是真正信教。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就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17]554基于此,宋太宗对梁武帝舍身为奴的溺佛态度进行了批判:“梁武舍身为寺家奴,百官率钱收赎,又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见之甚,为后代笑。”[17]554统治者不但不信教,当宗教行为触犯他们所规定的范围时,他们还会对宗教进行打压甚至毁弃。如宋太祖于开宝八年,诏令禁止举行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及夜集士女等佛事活动,因为其“深为亵黩,无益修持”。[18]又如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记载,宋太宗淳化五年,《大乘秘藏经》二卷,译出不久,就发现该书有65处“文义乖戾”,太宗当即下诏将《大乘秘藏经》“对众焚弃”,认为“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正法也。”宋初统治者真正强调的是文德致治,提倡儒学。《宋朝事实》卷三曰:“太宗笃好儒学。”[19]101宋太宗自己则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19]101因此,《太平广记》编纂的宗教类目虽然置于优先地位,但类目的数量和卷数却较少,而儒文化类目则居于主体地位。
总之,《太平广记》编纂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既反映了宋初三教合一的文化新态势,又体现了诏修者的主体意识和思想观念,有着特定的文化原因。
三、《太平广记》编纂的“三教合一”文化意义
《太平广记》编纂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整合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三教合一”的神道设教意义。
官方的典籍编纂往往有着很强的政治和文化功利目的,其根本核心即是适合王权统治的需要,因而典籍编纂本质上是在一定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文化整合,具有文化整合的意义。每当王朝兴替或皇位承传后,统治者都热衷于典籍的编纂与整理。从魏文帝曹丕诏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皇览》,到隋炀帝杨坚授意编纂《长洲玉镜》,再到唐高祖李渊诏修《艺文类聚》都是如此。典籍编纂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整合,一是以典籍编纂的方式对原有典籍文献进行辑采和删弃;二是贯穿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重组典籍文本和分配文献比例。《太平广记》编纂是第一次以官方手段对向来为精英阶层和主流意识所轻视的“怪力乱神”小说文本进行的编纂和整理,体现了宋初文化大一统的整合不仅局限于文化大传统当中,还触及到了文化小传统。《太平广记》编纂的文化整合主要体现在观念贯通和文献采辑两方面。
从观念贯通来看,《太平广记》编纂以“道-释-儒”的“三教合一”板块结构贯通着“三教合一”文化观念,并以儒家思想观念重新整合和梳理文化小传统中“三教”内涵。《太平广记》的道释类目编排和文本辑录虽然置于优先地位,但其编纂只突出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而未对道释宗教作全面的宣扬。道教类目和文本主要突出修身长生的神仙崇拜,“神仙”和“女仙”两个类目辑有文本共70卷,远远多于其他道教类目,约占道教类目总卷数的81%。佛教类目和文本主要突出赏善罚恶的因果报应,“异僧”“释证”和“报应”三个类目所辑文本都重在宣讲因果报应思想。这些观念虽是道释宗教文化的核心内涵,但也十分有利于导向儒家伦理道德的宣传,形成“三教合一”文化观念。《太平广记》儒文化类目和文本虽处于第三板块,但数量占绝对多数,体现了“三教合一”中的主体性。儒文化类目和文本也有其文化侧重点,即强调命数天定观念和修德向善行为。儒文化类目以“征应”“定数”“感应”和“谶应”等符命类目置于前列,辑录“君命天授”和“仕运天定”的小说文本,凸显了王权统治的合法性。此后的人事类目和神怪类目,则由天命转到人事,形成由“生”至“死”的生命历程,突出了修德向善的儒家伦理道德。因此,《太平广记》“三教合一”的编纂是经过了特定的文化“过滤”,呈现出以儒家文化融合佛道观念的倾向性,暗寓着鼓吹王权统治合法性的观念,有明显的文化整合意图。
从文献辑录来看,《太平广记》编纂非常注重引书的“经典化”,即《太平广记》编纂的引书虽然有近470部之多,但全书的文本辑录主要集中在少数引书上。这从相关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太平广记》引文9篇以下的引书有358部,占全部引书的76.8%,其引文共有757篇,占《太平广记》全部文本7 127篇的10.6%;引文10篇以上的引书有108部,占全部引书的23.2%,其引文占到全书的89.4%。即近八成的引书只承担《太平广记》全部引文的一成多点,而仅两成的引书却承担了全书引文的近九成。由此可见,《太平广记》引书虽广,重点却分明,引书有着鲜明的“经典性”。
这种引书的“经典化”实质上就是通过文献辑录进行文化整合,因为《太平广记》引书的辑录有其内在的原则。一是注重引书的文化影响力,其辑录文本较多的引书往往是文化影响较大的典籍。如道教性质的引书以葛洪和杜光庭的著作较多,其中葛洪《神仙传》60篇、《抱朴子》31篇,杜光庭《录异传》79篇、《仙传拾遗》58篇、《墉城集仙录》29篇、《神仙感遇传》27篇。无论是葛洪还是杜光庭,都对道教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注重道教理论通俗化和文学化。这些典籍对神仙思想起过重要鼓吹作用。[20]二是重视引书的文化导向性,那些有利于王权统治的引书往往辑录的文本较多。如戴孚《广异记》强调“著明圣道”,注重“观象设教”之功,[21]75其辑录的文本有310篇之多。根据这些原则辑录文本,《太平广记》的文献采辑既突出了典籍的文化“经典性”,又导向了典籍的文化“功用性”,有着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
《太平广记》编纂还体现了宋初统治者以典籍编纂的形式进行神道设教的宗教文化诉求,有着宗教教化的意义。
神道设教的文化观念源远流长。《易·观卦·彖辞》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礼记·祭义》曰:“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墨子·明鬼》曰:“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神道之所以能够起到教化的作用,一是鬼神能够赏善罚恶,由于“人们有鬼神信仰,为了得到鬼神的奖赏而避免鬼神的惩罚,人们才敬事尽责,不敢做违背道德的事情。所以,鬼神信仰是推行道德、治国理民之必需。”[22]魏源就指出:“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23]125二是宗教道德与伦理道德具有一致性的地方。如佛教戒律的核心宗旨就是宣扬“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这本身就是劝人向善。宋太宗尊宠道释宗教,除了鼓吹其政权合法性外,还看重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宋朝事实》卷三载宋太宗读《老子》时,对侍臣曰:“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方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19]101-102后来,宋真宗对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进行了概括。他说:“至于道、释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耶?”[17]1419“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24]405
《太平广记》以“道-释-儒”三教合一的板块结构分类辑纂先秦至宋初的宗教小说文本,有着丰富的宗教文化内容,因而也具有神道设教的教化意义。《太平广记》的神道设教作用主要是通过分类辑录宗教小说题材的编纂来实现的。以类目统绪文本,分类辑录宗教小说,能够固化小说题材的类型化观念。这不仅对人们阅读视感造成很强的冲击力,使人“看到厌而不厌”,而且赋予了同类小说题材以较为稳固的思想主旨和文化观念。如“报应”类目辑录的三十三卷小说文本,反复申说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观念。阅读者通过对小说的阅读和欣赏,较为容易形成去恶向善的思想观念,因而有利于王权的教化和统治。特别是《太平广记》的宗教小说辑纂有意导向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贯通,更有利于圣道教化。李昉《太平广记表》曰:“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古今。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25]卷首所谓“启迪聪明,鉴照古今”,即是包括神道设教在内的治世教化;所谓“圣人之道”即是教化的目标指向;所谓“通儒”即是要重视“怪力乱神”小说的文化作用。所以,《太平广记》编纂也隐藏着以编纂促教化的文化意图和意义。
由于小说在古代终究是“怪力乱神”之说,宋初时仍然不为精英阶层所广泛接受,再加上小说的神道设教远不如宗教本身明显,《太平广记》编纂的宗教教化作用并不十分明显。王应麟《玉海》卷五四指出,《太平广记》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诏令镂板后,“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墨板藏太清楼”。因此,《太平广记》并未充分发挥其治世教化作用。但作为一种“三教合一”的文化整合意图却十分明显,因为《太平广记》体现了宋初“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精神和诏修者的文化导向。从这方面讲,探讨《太平广记》编纂对于分析宋初三教合一的文化观念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戚志芬.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夏南强.类书通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4]严耀中.关于《搜神记》中佛教内容的质疑[J].中华文史论丛,2009(3):99-109.
[5]黄心川.“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J].哲学研究,1998(8):25-31.
[6]严耀中.论“三教”到“三教合一”[M]//佛教与三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7]李翱.李文公集: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王锟.试论李翱心性论思想体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8-11.
[9]延寿.宗境录[M]//大正藏:第4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
[10]张载.性理拾遗[M]//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张载.正蒙·太和[M]//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史[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7.
[13]契嵩.辅教编·广原教[M]//大正藏:第52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
[14]张伯端.悟真篇[M]//道藏: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5]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05.
[16]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赵匡胤.禁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诏[M]//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李攸.宋朝事实[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20]曾礼军.《太平广记》中神仙的考量与分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6):120-124.
[2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2]魏长领.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J].郑州大学学报,2004,37(2):109-115.
[23]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四[M]//大正藏: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
[25]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责任编辑 张丽珍)
The Compilation ofT’ai-p’ingKuang-chian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Syncretic Influences of Three Religion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ZENG Lijun
(CenterforStudiesofSoutheast-ChinaCulture,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The compilations of ancient books ma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because they a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pecific ideology and cultural values and represent the cultural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compiler’s subjective intent.T’ai-p’ingKuang-chiwas compiled with the plate tectonics of the syncretic influences of three religions, which were Ta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The compiling features ofT’ai-p’ingKuang-chi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syncretic influences of three religion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nd the religious ideas of the compiler ofT’ai-p’ingKuang-chi. Meainwhile, the bookT’ai-p’ingKuang-chicarried the misss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T’ai-p’ingKuang-chi; the compilatio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 syncretic influences of three religions
2015-10-10
曾礼军(1970-),男,江西吉安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宗教文化视阈下的《太平广记》研究”(10YJC751003)
I207.419
A
1001-5035(2016)06-00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