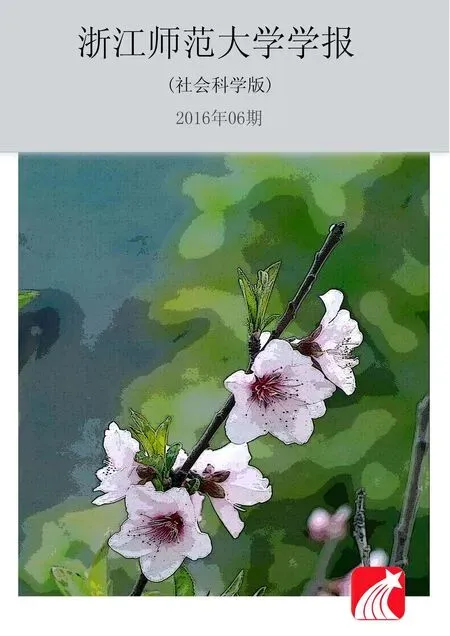文献特征的多元考察与误题译经译者的确定——以同本异译《阿育王传》《阿育王经》为例*
2016-12-12王浩垒
王浩垒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文献特征的多元考察与误题译经译者的确定
——以同本异译《阿育王传》《阿育王经》为例*
王浩垒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阿育王传》及其异译《阿育王经》的译者尚存争议。多重文献证据可证题名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至迟东晋已见,十卷《阿育王经》为梁代僧伽婆罗译。文献证据直观性强,历代经录呈现一定的体系性,也存在收录内容繁杂、不够完整、不能详细译经的具体内容等局限,但佛教类书、音义及其他佛教文献则在内容上恰与之形成了互补互证。文献特征的多元考察为误题译经的断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阿育王传》;《阿育王经》;文献;断代
题名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五卷或七卷,①以下简称“《传》”)与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十卷,以下简称“《经》”)是两部异译经,因两经译出的时代、地域及其口语性较强的特点,其对译经史、汉语史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目前两经的译者却仍存争议:一是吕澂认为《传》为“梁僧伽婆罗译”、《经》则是西晋安法钦译,[1]朱庆之、[2]刘开骅[3]等袭之;二是视《传》为西晋安法钦译经,如常盘大定、[4]高观如、[5]陈士强、[6]俞理明、[7]方一新、[8]徐正考[9]等;三是认为《传》的译者为西晋安法钦并不可信,如小野玄妙,[10]卢巧琴、颜洽茂[11]等。文献考察一般作为鉴别疑、佚经译者的首要步骤。本文拟对佛教经录、类书、音义等文献材料进行多元考察,描述《传》《经》在文献著录方面的特征,重在总结文献在考辨译经时代方面的特点。
一、经录著录《传》《经》的基本情况
《传》《经》的译者,历代经录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隋法经等《众经目录》(594年)一系观点
隋法经等《众经目录》一系认为五卷或七卷本《阿育王传》为梁译,但未提十卷本《阿育王经》。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卷6:“《阿育王传》五卷(梁天监年(502—519年)僧伽婆罗杨州译)。”(55/146a)②隋彦琮《众经目录》、唐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同之,但卷数上增录了七卷本。隋彦琮《众经目录》卷2:“《阿育王传》五卷(或七卷),梁天监年僧伽婆罗于杨州译。”(55/161c)
(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597年)一系观点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一系较早同时记载了两部译经:一是东晋竺道祖《晋世杂录》云五卷本《大阿育王经》出西晋惠帝光熙年(306年);二是梁宝唱《宝唱录》认为十卷本《阿育王经》(亦名《大阿育王经》)乃梁僧伽婆罗所译;三是续袭隋法经等《众经目录》中五卷或七卷本《阿育王传》为梁译的观点。《历代三宝纪》卷6“译经西晋”:“《大阿育王经》五卷(光熙年出,见竺道祖《晋世杂录》③)。”乃“惠帝世,安息国沙门安法钦,太康年于洛阳译。”(49/65a)又卷11“译经齐梁周”:“《阿育王经》十卷(天监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于扬都寿光殿译……见《宝唱录》)。”(49/98b)但又云:“《阿育王传》五卷(天监年第二译,与魏世出者小异)。”(49/98b)并指出:“正观寺扶南沙门僧伽婆罗……以天监五年被勅征召,于扬都寿光殿及正观寺、占云馆三处译上件经,其本并是曼陀罗从扶南国赍来献上,陀终没后,罗专事翻译,勅令沙门宝唱、慧超、僧智、法云及袁昙允等笔受。……并《宝唱录》及《名僧传》载。”(49/98b)《历代三宝纪》提供了几个重要信息:其一,西晋安法钦译五卷本《大阿育王经》较早见于东晋竺道祖《晋世杂录》。其二,梁僧伽婆罗译十卷《阿育王经》较早载于《宝唱录》,而宝唱正是其译经的“笔受者”。其三,指出梁天监年第二译五卷本《阿育王传》与“魏世出者”稍异。
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唐明佺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对两经的著录大致同《历代三宝记》。但道宣、明佺二录袭彦琮、静泰录,增收了僧伽婆罗译七卷本《阿育王传》,《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0:“《阿育王传》一部七卷(或五卷,一百一十五纸)右梁天监年僧伽婆罗于杨州译。出《内典录》。”(55/436a)《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较早提出安法钦译五卷本《大阿育王经》和梁僧伽婆罗译的十卷《阿育王经》为异译经,如卷5:“《大阿育王经》一部五卷,右西晋惠帝代光熙年,安息国沙门安法钦于洛阳译;《大阿育王经》一部十卷(或无大字),右梁天监十一年,沙门僧伽婆罗于杨都寿光殿,帝自执笔译。出《长房录》。以前二经同本别译。”(55/400b)
(三)唐智昇《开元释教录》(730年)观点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对两经的流变进行了梳理,认为五卷或七卷《阿育王传》与五卷本《大阿育王经》即同一本,为初译;十卷本《(大)阿育王经》为第二译。该经卷13云:“《阿育王经》十卷(或加大字),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罗译(《拾遗编》入第二译);《阿育王传》七卷(亦云《大阿育王经》,或五卷),西晋安息三藏安法钦译(第一译)。右二《传》同本异译。……(长房等录复云‘僧伽婆罗更出《育王传》五卷’者,误也。前《经》即《传》,不合重载。)”(55/623a)该说与现入藏的《传》(五卷或七卷)、《经》(十卷)的情况吻合。
另,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录有“《小阿育王经》一卷”(卷4“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55/33c)、“《大阿育王经》一卷(云佛在波罗奈者)”(卷5“新集安公疑经录第二”,55/38c)、“《释迦龙宫佛髭塔记第三十》(出《阿育王经》)”(卷12“释迦谱目录序第四”,55/38a)等与两经经名密切相关的译经,但这些均与《传》《经》无关。
综上:1.可信度高的东晋道安录、梁僧祐录中并没有《传》《经》的记载,但东晋、梁时可能有其他版本的《阿育王经》;隋法经对《传》的误录被后人沿袭,直到唐智昇录得以纠正,抄袭的习惯使经录形成了不同体系;隋费长房录虽然堆砌错杂,但其信息量大、时间上也相对较早。2.十卷本《阿育王经》,又名《大阿育王经》,为梁僧伽婆罗所译较可信。题名西晋安法钦出五卷或七卷《阿育王传》,东晋应为五卷《大阿育王经》,④后人比照梁译十卷本重新对之分章断句,形成《历代三宝纪》“天监年第二译,与魏世出者小异”的五卷《阿育王传》(实即今七卷《传》,“稍异”应是五卷、七卷本在篇章顺序上的差异),因与梁出《(大)阿育王经》重名,故改名为传。3.经录的局限是未能记录译经的具体内容。
二、佛教类书引录《传》《经》的基本情况
佛教类书是对前代佛教文献进行摘抄并分类编纂的总集类著作。我们主要考察《经律异相》《法苑珠林》两部类书的引用内容与现存入藏《传》《经》的一致性。
(一)梁宝唱等《经律异相》仅引《阿育王经》
《经律异相》成于梁天监十五年(516年),由僧旻、宝唱等人编纂修订而成,共50卷。该书引名“阿育王经”者26次,“阿育王传”者1次;与今本《传》《经》比较,所引“阿育王经”中有25次共21篇可在十卷本《阿育王经》中找到对应,如下表1所示:[12]

表1 《经律异相》与十卷《阿育王经》内容对比

表2 《法苑珠林》与七卷《阿育王传》内容对比
(二)唐道世《法苑珠林》只引《阿育王传》
《法苑珠林》由道世于唐总章元年(668年)编纂完毕,共100篇。与《经律异相》不同,该书引题名“阿育王经”者11次,⑥其中10次出自七卷《阿育王传》(《法苑珠林》未注明引用卷次,此以七卷本《传》为例),而不见引十卷《阿育王经》,两经内容对应如上表2所示。
(三)两部类书所引其他以“阿育王经”“阿育王传”等命名的译经与今本《传》《经》无关
《经律异相》卷6“善容王造石像五”:“《阿育王传》云:‘阿育王闻弟得道,深心欢喜,稽首礼敬……造石像一躯,高丈六,即山为龛室。’”(53/30b)卷6“天人龙分舍利起塔一”文后亦云出“《阿育王经》”。但这两处的内容与《传》《经》的关系不大,实与梁僧祐编集的《释迦谱》(五卷本)中的《阿育王弟出家造石像记第二十五》《释迦龙宫佛髭塔记》等内容相同。⑦
《法苑珠林》卷37引“大阿育王经”“育王传”各1次,查与《传》《经》无关。又,卷40引“阿育王经”1次、卷84引“阿育王传”1次,亦均袭《释迦谱》。
比较发现:1.类书弥补了经录不能见到译经内容的局限。十卷本《阿育王经》、五卷或七卷本《阿育王传》(唐道世辑录的名为《阿育王经》,但不明卷次)的内容与今本一致;类书中有别于《传》《经》的有关阿育王因缘故事的他译本,《释迦谱》均有记录,说明梁僧祐时代这些译本可能是存在的。2.梁宝唱等的《经律异相》也未录《传》。以上与经录的记载相合。
三、《一切经音义》所录词语与今本《传》《经》的比较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76收录了《阿育王传》1-7卷和《阿育王经》1-10卷的词语,现将《一切经音义》所收两经词语与今本《传》《经》的对应情况列表统计如下表3和表4。对比下表3和表4,《慧琳音义》所收《传》《经》的词语与今本两经卷次上一致,且所收词条基本相同。有异文的部分,除异体字外,有的是义同形近字造成的差异(如“掣”与“挈”、“杷”与“爬”),有的是因形近而误所致(如“了”与“子”、“施”与“於”), 多数是《慧琳音义》认为原经文用字失误而造成的差别(这种情况音义在说解时称“经文作”)。
据上:1.音义弥补了类书《法苑珠林》不引卷次的不足,可见唐代七卷本《传》、十卷本《经》的卷次均与今本一致。2.《阿育王传》《阿育王经》经名唐后期开始定型。3.音义未收录经录、类书中著录的其他译本,这些译本在唐代可能已经散佚。

表3 《一切经音义》与七卷本《阿育王传》的对应

表4 《一切经音义》与十卷本《阿育王经》的对应
四、《付法藏因缘传》对《传》的引用及其时代
(一)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主要以《传》等译经为基础编纂而来
《付法藏因缘传》从卷1“摩诃迦叶”至卷5“提多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袭自《传》,⑧特别是人名、地名等专名译名,如“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拘那罗/真金鬘”“得叉尸罗/鸡头末寺”等均为直接沿用。
(二)吉迦夜共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是经录所记现存的唯一版本
现存经录中,《付法藏因缘传》较早见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卷2:“《杂宝藏经》十三卷(阙)、《付法藏因缘经》六卷(阙)、《方便心论》二卷(阙)。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472年),共僧正释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此三经并未至京都。”[13]可见,僧祐并未见到六卷本《付法藏因缘经》。隋法经等《众经目录》、隋彦琮《众经目录》、唐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则称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付法藏传》四卷或六卷。隋彦琮《众经目录》卷2:“《付法藏传》四卷(或六卷),后魏世沙门吉迦夜共昙曜译。”(55/161c)
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唐智昇《开元释教录》等则认为《付法藏因缘传》有三种译本:初译《付法藏经》(六卷),刘宋宝云出,较早见于北魏《李廓录》;第二译《付法藏传》(四卷),北魏昙曜译,较早载于北魏《菩提流支录》;第三译为吉迦夜共昙曜的《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或四卷),较早见于道慧《宋齐录》。唯存第三译。《历代三宝纪》卷10“译经宋”:“《付法藏经》六卷(见《李廓录》)……文帝世,凉州沙门宝云……后还长安复至江左,晚出诸经多云刊定。”(49/89c)又,卷9“译经西秦北凉元魏高齐陈氏”:“《付法藏传》四卷(见《菩提流支录》)……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诏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凌废欣今载兴,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庶使法藏住持无绝。”(49/85a)又“《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或四卷,因缘广异曜(宋、元、明本作‘昙曜’)自出者)……宋明帝世,西域沙门吉迦夜,魏言何事,延兴二年,为沙门统释昙曜于北台重译,刘孝标笔受。见道慧《宋齐录》。”(49/85b)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6 “吉迦夜”:“《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或无因缘字,亦云《付法藏经》。或四卷,或云二卷,⑨见道慧《宋齐录》。第三出,与宋智严、魏昙曜出者同本,亦见《僧祐录》。”(55/540a)
(三)唐道世《法苑珠林》所引“付法藏传(经)”均与今本同
《付法藏因缘传》不被梁宝唱《经律异相》收录,而唐道世《法苑珠林》引《付法藏传》5次(《法苑珠林》卷30、32、53、91)、“付法藏经”11次(《法苑珠林》卷1、5、17、19、22、33、42、77、88、98、99),其所引均源自今吉迦夜共昙曜译六卷本《付法藏因缘传》(卷30、卷88为总述内容,无具体章节对应,《法苑珠林》卷17/77/22、卷53/32/99、卷91、卷1/19/42、卷5/98、卷33分别引自《付法藏因缘传》卷6、卷5、卷4、卷3、卷2、卷1)。
(四)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录六卷本《付法藏传》与今本同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75(此部分系《玄应音义》)收录了六卷本《付法藏传》卷1、4、5、6的词语,共6条。其中,除卷1“即睎”与今本《付法藏因缘传》卷1的“则晞”(50/300b)不同外,他如卷4“窘急”、卷5“摩啅罗”“眼睑”“锱铢”、卷6“纯粹”“羸惙”均与后者在次序和分卷上完全相同。
可见:1.《付法藏因缘传》历史上还有《付法藏经》《付法藏传》《付法藏因缘经》诸名,卷数上有六卷、四卷本等,初译、二译全部散佚,仅吉迦夜共昙曜译六卷本现存。2.吉迦夜共昙曜译六卷《付法藏因缘传》,为北魏所出无疑,此时《传》应已在北方存在,可证隋法经录一系及吕澂等人观点的偏误。
五、结 语
(一)历代经录著录具有一定的规律
历代经录是考察译经译者最直接的证据,就本文讨论的对象来看,隋法经等《众经目录》、隋彦琮等《众经目录》、唐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是一体系;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唐明佺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所录内容大致相当;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唐智昇《开元释教录》较为可信,祐录可能会遗漏一些东晋以来的北方译经,后者则更为全面。但经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1.有的经录出自众手,堆砌讹误现象较多,再加上译经节译本以及人为改动较多,所录译经经名和卷数往往比较繁杂,且经录大都未详译经的内容。如经录中与《阿育王传(经)》相关的就有《小阿育王经》《大阿育王经》《阿育王传》《阿育王经》《育王传》等经名,卷数上有一卷、五卷、七卷、十卷诸本;与《付法藏因缘传》相关的有《付法藏经》《付法藏因缘经》《付法藏传》诸名,卷数上有六卷、四卷本等。2.收录的不完整性。由于南北地域隔阂或囿于个人见识,某些经书可能会被漏收,如隋法经等《众经目录》等经录就未收梁译十卷本《阿育王经》,流传于北魏的五卷本《阿育王传》同样不被梁《出三藏记集》收入。
(二)佛教类书、音义等与经录可多重互证
不同的文献典籍,因体例等因素的影响,著录内容各有特色。针对经录未详译经内容的局限,佛教类书、音义等文献,为我们的深入考察提供了另一路径。例如,魏晋南北朝时可能有别于现存《传》《经》的其他阿育王因缘故事的译本,《出三藏记集》等经录只记经名,而《释迦谱》《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就较为详细,多次印证《大阿育王经》(一卷)、《小阿育王经》(一卷)、《育王传》等跟今本《传》《经》的关系不大;《出三藏记集》未录五卷本《阿育王传》,注明《付法藏因缘传》等三部北魏译经“未至京都”,而以上四经在梁代佛教类书《经律异相》也未辑录,但《付法藏因缘传》却证实了《阿育王传》在梁以前已存在于北方,说明了经书流传的地域特征;《经律异相》《法苑珠林》从内容上、《一切经音义》从卷次上证实了经录中的五卷或七卷《阿育王传(经)》、十卷《阿育王经》与现存《传》《经》的一致性等。
(三)文献可为误题译经的断代提供直接证据
文献证据可证题名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至迟东晋已见,十卷《阿育王经》为梁代僧伽婆罗译经。梁译十卷《阿育王经》,并见于梁代的《宝唱录》《经律异相》,三者出自同一时代、同一地域;《阿育王传》原为五卷《大阿育王经》,较早载于东晋《晋世杂录》,南北朝时期在北方流传,北魏的《付法藏因缘传》(472年)大部分内容抄袭了该经,后因十卷《(大)阿育王经》译出,时人比照梁译十卷本对五卷《大阿育王经》的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即“天监年第二译”,因与梁译本重名,故改为《阿育王传》,而这个新编辑的本子应即是七卷本。但针对学者的质疑,文献证据尚不能确切证实《阿育王传》是否出自西晋,我们则拟另文从语言等方面进行考察。
注释:
①七卷、五卷本《阿育王传》内容相同,七卷本是其五卷本比照十卷《阿育王经》的章节重新进行了划分。今入藏者宋、元、明、宫等诸本是五卷本,赵城金藏、高丽藏是七卷本。参王浩垒《同本异译〈阿育王传〉与〈阿育王经〉词汇比较研究》,浙江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31-32页。
②本文所引佛经均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55、146、a分别表示册数,页码,栏次,下同。
③该录成于晋末宋初。梁启超云:“道流、道祖者,慧远弟子,安公再传也。流草创《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卷,《河西录》亦名《梁录》,未成而卒,祖续成之,即诸录所引《道祖录》是也。”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36/2009年第290页。
④小野玄妙认为安法钦未见于道安、僧祐二人目录,凭《晋世杂录》不足证实该经确为西晋安法钦译。参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杨白衣译,新文丰出版公司1936/1983年第 47页。
⑤“3次”表示《经律异相》卷6“《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二》”和卷24“《阿育四分王始终造业十二》”共出现了3次“出《阿育王经》第一卷”,这些引用的内容可在十卷本《阿育王经》卷1中找到对应。下同。
⑥卷37“敬塔篇第三十·引证部第二”为“阿育经”,宋、元、明本作“阿育王经”。
⑦《释迦谱》卷3“阿育王弟出家造石像记第二十五”:“《阿育王传》云:‘阿育王闻弟得道,深心欢喜,稽首礼敬……造石像一躯,高丈六,即于山龛石室供养。’”(50/67b)。
⑧参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6页。据邱琳《〈付法藏因缘传〉与源出经比较研究》(浙江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第18-20页),《付法藏因缘传》摘录了《阿育王传》《贤愚经》等七部源出经,源出经上自东汉,下至北魏。
⑨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卷6:“《付法藏传》四卷或七卷,后魏世沙门吉迦夜共昙曜译。”(55/146a)据邱琳《〈付法藏因缘传〉与源出经比较研究》(浙江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15页)考证,经录中该经二卷、七卷的说法并不可靠。
[1]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M].济南:齐鲁书社,1980:73.
[2]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169.
[3]刘开骅.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211.
[4]常盘大定.后汉より宋齐に至る译经总录[M].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8:699.
[5]高观如.阿育王经[J].中国佛教,1989(4):12-13.
[6]陈士强.佛典精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06.
[7]俞理明.佛典文献语言[M].成都:巴蜀书社,1993:60.
[8]方一新.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以早期汉译佛经鉴别为中心[J].语文研究:2009(2):8-16.
[9]徐正考,黄娜.语言特征的考察与“误题”译经译者的确定——以《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为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2):160-167.
[10]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M].杨白衣,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36/1983:47.
[11]卢巧琴,颜洽茂.中古译经年代与“感染生义”的判别[J].中国语文,2010(1):83-85.
[12]王浩垒.同本异译《阿育王传》与《阿育王经》词汇比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16.
[13]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62.
(责任编辑 张丽珍)
Plural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of Buddhism Sutra:With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AYuWangZhuanandAYuWangJingas Examples
WANG Haole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Who traslatedAYuWangZhuanandAYuWangJingis still a question. The multiple-document evidence can confirmAYuWangZhuan, which indicated over its cover that the translator was An Fa-qin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was at the latest translated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AYuWangJing(10volumes) was translated by Sengjia Poluo of the Liang Dynasty. Documents provide vivid evidence and the record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can be presented in a systematic way. However, they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the content is multifarious, incomplete, and not detailed enough. Buddhist sutra, Buddhist music and other Buddhist literature, however, are complementary to Buddhist scriptures. Plural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opic of dating translation.
AYuWangZhuan;AYuWangJing; literature; dating
2015-10-01
王浩垒(1983-),男,河南襄城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今训汇纂·明清卷”(12JJD740014);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同本异译《阿育王传》与《阿育王经》词汇比较研究”
B948
A
1001-5035(2016)06-008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