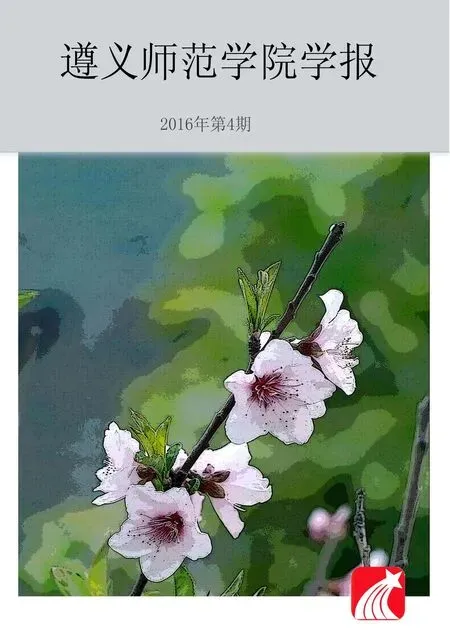土司文化的界定、特点与价值
2016-02-14李良品袁娅琴
李良品,袁娅琴
(1.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408100;2.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土司文化的界定、特点与价值
李良品1,袁娅琴2
(1.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408100;2.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土司文化是指由中央王朝与西南、中南及西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与土司制度密切相关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土司文化的特点有四:多元性、丰富性、民族性和不可再生性。土司文化蕴含着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教育价值、艺术价值、资源(经济)价值等多重价值。
土司文化;界定;特点;价值
[主持人语]自本刊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两篇阐述“土司文化”定义、内涵的文章,并组织对“土司文化”这一概念进行讨论以来,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新华文摘》做了观点摘录,一些专家学者也积极撰文,阐述各自的看法。本期从中选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李良品的《土司文化的界定、特点与价值》,作者认为:土司文化是指由中央王朝与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体现出多元性、丰富性、民族性、不可再生性的特点,具有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教育价值等多重价值。另一篇是彭福荣的《也谈土司文化的内涵》,作者认为:土司文化的内涵应包括土司制度文化、土司政治文化、土司教育文化、土司民族民间文化,而每一部分又都包括了丰富的内容,极具研究价值,值得深入探讨。作者虽未专门探讨“土司文化”的定义,但从文章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与李良品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两位作者多年研究土司制度,且研究成果也多涉及土司文化,因而对“土司文化”的定义、内涵有自己的见解。他们的看法或许与前一期发表的文章不尽相同,这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是学术探讨,就会有不同见解。我们这里并不想对此做任何评判,只是提供深入探讨的平台,希望通过百家争鸣,把“土司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内涵讨论清楚,在今后的使用中规范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世愉)
在元明清及民国时期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土司制度在西南、中南及西北地区的实施,各地土司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种既被土司集团、也被当地民众共同接受的理念及行为,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土司文化。
一、土司文化的界定
“土司文化”作为学术术语,最先出现在余嘉华[1]的论文中。刘强、卫光辉在《古老而又年轻的江外
土司文化》中结合云南省各地土司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土司文化是生活在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土司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是边疆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2]其实,这也并非是对土司文化的界定。
(一)早期对“土司文化”的界定
2009年,李良玉先生在《土司与土司文化研究刍议》中认为:“土司文化是历任土司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接受汉民族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使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得到不断的修正,逐渐形成了一种被社会集团成员共同接受的理念及行为,形成了特有的土司文化。”[3]之后,成臻铭认为,土司文化是指在漫长的土司时期,由中央王朝和土司区各族民众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土司文化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具有多元性、原生性、本土性特点的民族文化。”土司文化具有“封建性”、“民族性”、“家族性”、“政治等级性”等“传统性”特点,融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于一体,是土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经典文化和贵族政治文化。[4]
(二)近期对“土司文化”的界定
李世愉先生认为以上阐述失之于宽泛,并非严格的定义[5]。罗维庆在《土司文化的边际界定》中认为:“土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阶段性反映;家族文化是土司文化的组成部分;移民文化是土司文化的外来补充。”[6]这也并非是对土司文化的界定。李世愉先生在《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一文中认为,从目前对“土司文化”的使用来看,主要有“土司时期的文化”、“土司地区的文化”与“土司制度的文化”三种用法,但三者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土司时期的文化”突出的是土司文化的历史性;“土司地区的文化”突出的是土司文化的地域性;土司制度文化则兼容两者,突出了土司文化的本质属性。严格来说,土司文化应该称之为土司制度文化。他将土司文化界定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李先生指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和存续的一种历史现象,土司文化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族文化、乡土文化。[5]李世愉先生在《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中认为,土司文化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然产生于推行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二是产生并存续于土司制度推行的历史时期,三是与土司制度密切相关。[5]应该说,李世愉先生的这个界定比较符合实际。
(三)土司文化的学术规定
著者结合李先生提出的三个条件,拟对土司文化界定为:土司文化是指由中央王朝与西南、中南及西北各土司区各族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与土司制度密切相关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土司文化是元明清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民族地区土司政治、中原文化传播和儒家伦常观念与少数民族区域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土司文化是民族经典文化和地方贵族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家族文化、政治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统一体,特点鲜明而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和智慧启发作用。土司文化在原土司地区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行方式和生产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随着播州海龙屯、永顺老司城和唐崖土司城等成功入列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土司文化的整理、挖掘与利用将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也为世界了解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
二、土司文化的特点
土司文化是受中央政府、土司政治以及儒家文化和地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民族经典文化和地方贵族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家族文化、政治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统一体,具有多种特点。
(一)多元性
任何一个土司所传承的文化,都具有多元性。明清时期每个土司承载和传承的心态文化时刻影响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土司区内部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感。从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家族制订的条规、族谱以及诗文的内容看,其心态文化体现出多样性。第一,推崇和传播儒家文化。如播州杨氏土司在元明等朝致力于振兴学校和中原文化传播,杨汉英在元朝初年振兴儒学。明代初年,播州杨氏土司受明太祖朱元璋“诏诸土司皆立儒学”的影响,将中原文化教育惠及土民。杨铿于洪武十三年(1380)建播州长官司学,于永乐四年(1406)升宣慰使司学。杨相于嘉靖元年(1522)得明世宗赐《四书
集注》,儒家经典被用作播州地区生员的教材。可见,明代播州土司实施的学校教育受到中央王朝的高度关注,且文教日兴,使土司家族子弟的汉文化水平得到提升,获有不菲的成就。元代杨汉英“究心濂洛之学”,并有《明哲要览》、《桃溪内外集》等著述而成为学者和诗人。杨升执政时期“明断宽裕”,疑难“博询于众”,后九次赴京朝觐而得永乐皇帝“屡赐玺书褒奖”,杨纲、杨辉等土司颇有文艺才华。播州杨氏土司不仅在教育本族子弟和地方学子时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而且他们的诗文中也蕴含和渗透了尊儒重道、忠君报国等思想,这些都是播州杨氏土司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念。第二,注重宗教信仰。如播州杨氏土司就采取儒、释和道兼容并蓄的态度,使之呈现出混杂合流的特征。据有关史料记载,元明时期,播州杨氏土司先后修建万寿寺、普济庵、大德护国寺、净土庵、普慧寺、桃溪寺、茅衙寺等30余座佛寺;还十分重视道教,元天历二年(1329)大报天正一宫被毁后,杨嘉真重建,其后屡毁屡建,直至杨氏土司灭亡时消失。明正德十二年(1517)冬,播州宣慰使杨斌弃官修道,于城北高坪紫霞山建先天观修行。杨氏这种高超处理技巧,不仅加速了儒释道巫混杂合流的步伐,而且对播州杨氏家族统治地区的文化影响甚大。[7]P270-274
(二)丰富性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任何一个土司家族的文化均十分丰富。如满足各地土司、土司家族及辖区民众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包括建筑类、生产生活类、物产类、服饰类、饮食类、交通类、兵器类、娱乐类、办公用具等类型,各种类型又包括很多小类。在贵州水西地区,其交通方面素有“九驿”“十桥”之说。所谓“九驿”,就是洪武十七年(1384)奢香修建的“龙场九驿”,这些驿站后来成为水西安氏土司连接重庆、毕节和贵阳的交通大动脉,也成为地方土司与中央政府交流、交通的纽带和管道。而“水西十桥”实际上有二十几座,分别是贵州宣慰司安观和安国亨于成化年间(1465―1487)和万历年间(1573―1620),主持修建。[8]在广西忻城的莫氏土司衙署建筑群装饰中的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卍”、“寿”等文字字样,不仅体现了明清时期广西壮族土司阶层追求“福、禄、寿”的思想观念[9]P262-265,而且更彰显了土司文化的丰富性。
(三)民族性
土司文化由于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文化自然具有少数民族的烙印。因此,土司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某一个具体少数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化和精英文化。在现存的诸多土司文物中,诸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奢香夫人墓、大屯土司庄园、开阳马头寨古建筑群、孟连宣抚司署、南甸宣抚司署、兔峨土司衙署、叶枝土司衙署、纳楼长官司署、陇西世族庄园、莫土司衙署、卓克基土司官寨、沃日土司官寨经楼与碉楼、鲁土司衙门旧址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施南宣抚司土司皇城、邦角山官衙署、刀安仁墓、岑氏土司古建筑群、瓦氏夫人墓、巴底土司官寨等无一不是它所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经典杰作。据史料载,明清时期的“贵州宣慰府”有“九层八院”,所谓“九层”为沿中轴线往上依次排列九间大殿,“八院”即是从第二殿开始的等八个四合院落,包括更苴栋谷、恩奥栋谷、菲柯栋谷、够葛栋谷、拜项栋谷、姆骂栋谷、更兹栋谷、吉略栋谷、布摩栋谷等九间大殿,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整个宣慰府室内装饰及陈设都是依据彝族传统风格修建而成,无不散发出彝族“龙虎文化”的神秘光芒。
(四)不可再生性
所谓的“不可再生性”是指尽管我国有异常丰富的土司文化资源,如管理不善而遭到严重破坏,则无法真正复原。在榜上有名的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如纳雍县水西宣慰府遗址,甘肃永登县鲁土司衙门旧址、湖南保靖县洛浦土司故城遗址、贵州岑巩木召庄园遗址和九层衙门遗址等,均属不可再生性的土司文化。何谓“遗址”?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前面所列的这些遗址,主要是元明清时期各地土司为不同用途所营建的包括宫殿、官署、寺庙、作坊以及范围更大的村寨、城堡、烽燧等各类残迹建筑群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旧城址,这些遗址已经不可再生,无疑是我国土司文化的巨大悲哀。通过对这些土司遗址的调查发掘,可以揭示元明清时期的遗迹,进而考察有关土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
三、土司文化的价值
葛政委在《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凝练与表达》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土司文化遗产的最高价值和核心价值问题,并且认为土司文化遗产的最高价值和核心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三处土司遗产是中世纪时期全球山地传统城市的代表;二是三处土司遗址见证了世界上一种独特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衰亡;三是三处土司遗址反映了13-18世纪中国西南多族群独特的社会文化面貌。[10]笔者认为,这很有独创性。其实,土司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价值。
(一)思想价值
土司文化作为一种遗产,它反映了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道德、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观念。无论是永顺老司城、唐崖土司城、遵义海龙屯,还是孟连宣抚司署、南甸宣抚司署、叶枝土司衙署、兔峨土司衙署、纳楼长官司署等,无不昭示着一个努力维护中央王朝正统和国家统一的边缘或边疆少数民族的爱国情怀。《中华覃氏志》所载湖北利川土司《覃氏家谱》之“家规”就包括存心、修身、敬祖先、孝父母、敦手足、正家室、务耕读、和族邻、择师友、维风俗计10条,每一条的思想价值极高,如“务耕读”条云:“君子当尽其在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若勤耕而得富,则非不义之富也。若读而得贵,则非不义之贵也。古昔盛时有井田,以安天下之野人,故衣食足而国无游惰。有学校以教天下之士子,故礼义兴而朝多圣贤。秦汉而后田由民置,学尚虚文。然既生于世,即不得不勤耕苦读也。吾族朴者,宜归农。毋辞胼胝之劳,将仰足以事,俯足以畜,不期其富而自富矣;秀者,宜归学,毋畏就将之苦,则太上立德,其次立言,不期贵而自贵矣。”[11]P73湖北利川覃氏土司在与中央政府以及汉族地区的交往过程中,不仅良性互动,积极学习汉族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从这些家规、家训、家禁等规定中反映出明清两代覃氏土司独特的哲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思想。[10]
(二)历史价值
作为物态文化代表的土司遗址和土司衙署,它具有见证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治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历史价值。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之一,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与发展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如遵义海龙屯完整地见证了由唐代至清代中央政府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再到明末的“改土归流”的历史变迁。永顺老司城同样是湘西少数民族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与变迁的见证者。[10]作为土司文化重要内容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料文献,不仅系统地反映了元明清时期中国土司制度的起源、发展、兴盛与衰亡的历程,真实地记录了历代中央王朝、各级官府、各级土司与乡村社会的社会变迁、民族关系、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而且是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元明清时期近七百余年我国土司制度的实况及对社会影响的珍贵资料。
(三)学术价值
作为以历史学为基础的土司文化,其学术价值主要是指包括土司制度在内的土司文化在自身发展中的价值,土司文化如果一旦在研究领域的理论、史实与方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那么它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是土司制度的学术价值。土司制度的研究可以将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军事学及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相结合,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构建“土司学”的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在学术理论方面,可以通过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土司制度的深入研究,深入探寻中国土司制度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实施过程中的差异,彻底厘清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中南、西北少数民族各方面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二是土司遗址的学术价值。一些土司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可以起到补史证史的作用。如遵义海龙屯的考古发现,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缺失或歪曲所留下的遗憾。众所周知,播州杨氏土司家族以及播州土司历史,大多数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都过于简略,即使现在可考的文献资料,也基本上是以“成王败寇”立言。无论是李化龙的《平播全书》,还是张廷玉的《明史》,以及其他存世文献的立言者均是属于胜利者一方,而对于失败者一方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以及播州土司历史却少有全面而客观的记载。甚至“改土归流”后的社会舆论和大量传世诗文,也都按照官方的意志进行褒贬和撰写,这就使得对播州杨氏家族和播州土司历史的研究难免带有许多主观主义色彩。不过,随着播州土司文化遗存的陆续发掘,特别是海龙屯上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高坪杨氏墓葬群中出土的《杨文神道碑》等珍贵文物,记载着众多关于杨氏家族和播州土司历史的发展情况,它不仅对研究播州土司制度、杨氏家族历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以弥补杨氏家族以及播州土司历史研究中传统文献记载缺失或歪曲所留下的遗
憾,使史学界对杨氏家族以及播州土司的研究回归历史本原。[12]
(四)教育价值
土司文化中处处彰显出厚重的“忠孝文化”、国家认同意识以及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价值。一是忠孝教育。忠于国家、孝敬父母,是其重要内容。如施南《覃氏族谱》之“家训”中“孝父母”条有如下内容:“诚以父母之恩,虽碎骨犹难酬也。今则人情不同,往往爱子恒觉有余,而爱亲常若不足。不知今日吾为人父,而吾之爱子如是,其至而迥异。吾为人子,吾亲之爱,吾身夫亦何独不然。且吾之于子,教养婚娶,为日甚长。而吾之于亲,年华筋骨,为欢无几,若能及时尽孝,则敦本重伦,亦或庶几近之矣。不然,亲有饥寒而漠焉置之,亲有疾痛而淡焉忘之,纵功名盖世,富贵惊天,而本宽先拔衾影,能无自惭?语云:五伦莫重于亲,百行莫先于孝,正此谓也。”[13]P24二是认同教育。明清时期的很多土司在以身份职权得到中央政府认同后确立对国家的认同,他们即使处江湖之远,但每逢中央王朝的政权更迭,均能审时度势、迅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主动归附中央王朝,且按例朝贡、奉调出征,通过各种活动,使得自己的土司身份认同愈加强烈,国家观念亦沉淀在土司文化的历史之中。如施南《覃氏族谱》之“家训”包括孝父母、和兄弟、厚宗族、睦乡里、严闺阃、保祖茔、勤读书、端士品、重农事、急饷糈、尚节俭、解仇忿、慎交游、恤使从等条目,无一不是对国家主流认同后的精辟归纳。如“端士品”条云:“国家设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砥砺名节。俾读书士子,忠君孝亲,持已不亏,秉礼守义,应世无惭。乃迩来士,风不端佻,达成习侍,青衿为护符,辄敢籍事生波,以刀笔为能技,遂尔成风打码,甚至隐粮占产、夺婚,掳良种种刁险,毫无顾忌,不知一行有败百行,可疑片言欺心,终身莫补,吾族士习切勿踵此积弊。”[13]P26由此可见,施南覃氏土司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自觉接受礼治观念,儒家文化认同的升华使覃氏土司的国家认同逐步加深,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和忠顺已深入骨髓。三是爱国教育。据文献载,明清时期的很多土司,当面临外来入侵或国内叛乱时,众多土司总是打着“卫道”、“勤王”、“援辽”、“平叛”等旗号,以爱国主义为依归,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如石砫土司秦良玉在平定奢祟明叛乱、收复重庆的战斗中,她带领的军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尽心竭力,功勋卓著。[14]正是由于各地土司以“忠孝、认同、爱国”作为在当地的执政理念,从而促进了土司地区社会稳定,使各地土司的统治长盛不衰。
(五)艺术价值
作为物态文化的土司遗产具有多种艺术价值。如一些现存的土司衙署拥有丰富多样的建筑、绘画、雕塑等土司文化遗产,人们在游览时可以感受到艺术之美、文化之美。如永顺老司城考古发现的不少瓷片或装饰品,可让人遐想中世纪的传统工艺之美。在唐崖土司遗址,明代的石人石马、牌坊仍然保留至今,可让人感叹唐崖覃氏土司为国奔走尽忠之美。[10]在遵义海龙屯,人们可以感受到具有和谐、悲壮、残缺之美。一是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从选址来看,海龙屯三面环水,一面衔山,四面群山环绕,屯在中央,形似群山环抱的“莲花”,是崇山峻岭中的一朵耀目奇葩。其选址完全符合阳宅“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空间模式,既考虑了先天风水自然因素,又考虑了后天城堡防务之需,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二是军事城堡残缺之美。经过“平播之役”毁灭性的打击和四百余年风雨沧桑的销蚀,海龙屯当年盛世繁华之景早已不再,遗留在屯上的只有九个残缺的关口、残垣断壁的围墙,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勾魂夺魄之美。[12]在云南等地的一些现存的土司衙署,却留给人们的是另外一种审美艺术。南甸宣抚司署的布局和建筑形式仿照清代的藩台、臬台衙门,是四进宫殿式建筑群,具有“正立春秋”的特点。整个司署占地面积原为10625平方米,坐东南向西北,沿一条长130余米的中轴线上,由西北向东南依次排列大堂(审判厅)、二堂(议事厅)、三堂(会厅)、正堂(土司办公、起居处所),每进两侧附设厢楼,形成互相连通但又相对独立的四合院式。整座司署分为四个主院,十个旁院,共四十七幢一百四十九间房屋,计有粮库、军械库、监狱、佛堂、学堂、戏楼、绣楼、八角楼、字堂、经书堂以及花园、练兵场等建筑。现存的四进主院落的主体建筑为面阔五间,抬梁式土木结构,单檐硬山顶,青色筒瓦屋面,左右两侧又分布有各类亭阁、楼堂、庭院、花园等附属建筑,组成一组主次分明、高低有致的宫殿式建筑群。南甸宣抚司署是目前国内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傣族土司衙署之一,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15]P70-71又如陇川宣抚使衙署布局、格式也系仿照清代的藩台、臬台所建,为四进的宫殿式建筑群,规模宏大,气
势不凡。现存的第四进正殿及左右厢房坐东北朝西南,排列有正殿,两侧厢楼、厅堂等,呈四合院式。正殿建在较高的石砌台基上,面阔五间,抬梁式土木结构,单檐硬山顶式屋顶,筒瓦屋面。内檐拱形天花,呈穹隆式,梁柱间雕梁画栋,枋头作龙凤圆雕,梁垫、雀替部分作透雕,门窗作各种花饰,墙壁绘山水画,格调典雅,富丽堂皇。正殿前后布有走廊,过道铺孔雀,白鹭纹饰浮雕地砖。陇川宣抚使衙署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15]P72这些土司衙署给人们留下了建筑之美、雕塑之美和绘画之美。
(六)资源(经济)价值
我国的土司文化遗产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拥有大量的资源价值。在国家记录在案的土司文物保护单位中,现有世界文化遗产三个,即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六个,即湖北鹤峰容美土司遗址,贵州大方县奢香夫人墓、毕节大屯土司庄园、开阳马头寨古建筑群,云南广南侬氏土司衙署、孟连宣抚司署、梁河南甸宣抚司署、兰坪兔峨土司衙署、维西叶枝土司衙署、建水纳楼长官司署、新平陇西世族庄园,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四川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和直波碉楼、小金县沃日土司官寨经楼与碉楼,甘肃永登县鲁土司衙门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十个,即湖北省宣恩县施南宣抚司土司皇城和猫儿堡土司墓群,湖南省保靖洛浦土司故城遗址,贵州省岑巩木召庄园遗址、纳雍县水西宣慰府遗址、大方县九层衙门遗址和千岁衢及摩崖石刻、遵义高坪杨氏墓群(包括杨辉墓、杨烈墓)、道真明真安州城垣、黄平岩门司城垣,云南省景东卫城遗址、陇川县邦角山官衙署、宣威市倘可巡检衙署、盈江县刀安仁墓,广西西林县岑氏土司古建筑群、靖西县旧州岑氏土司墓群和瓦氏夫人墓,四川省丹巴县巴底土司官寨;此外,还有六十余处区县级土司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土司文化遗存包括土司治所、城堡、官寨、衙署建筑
群、庄园、墓葬(群)以及石刻、城垣、经堂等其他单一功能的土司建筑[16],它们既是文化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在土司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这些土司文化遗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其经济价值会自然地得到一定的开发。因此,这些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具有资源价值,而且也具有经济价值。
总之,正是因为土司文化具有这些特点与价值,所以成功获批世界文化遗产。在后申遗时代,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保护与有效利用土司文化的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建构土司文化遗产“五位一体”的保护与利用系统,让政府组织、企业行业、各类学校、专家学者、人民群众等不同组织共同发挥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作用。
[1]余嘉华.雪山文脉传千古——兼谈土司文化评价的几个问题[J].民族艺术研究,1996,(2):38-45.
[2]刘强,卫光辉.古老而又年轻的江外土司文化[J].创造,2001,(8):31-32.
[3]李良玉.土司与土司文化研究刍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3):132-134.
[4]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0,(1):86-95.
[5]李世愉.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2):16-20.
[6]罗维庆.土司文化的边际界定[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2):21-24.
[7]李良品,李思睿,余仙桥.播州杨氏土司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8]龙春燕.水西土司物质文化述论[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5):13-19.
[9]韦业猷.忻城土司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10]葛政委.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凝练与表达[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5):8-12.
[11]中华覃氏志(利川卷)编纂领导小组.中华覃氏志(利川卷)[Z].利川:中华覃氏志(利川卷)编纂委员会,2005.
[12]魏登云,陈季君.论播州土司文化遗产及其价值[J].攀登,2015,(5):120-128.
[13]覃章义.施南覃氏族谱校注[Z].恩施:恩施日报社印刷厂,2016.
[14]李良品,冉建红,吴冬梅.石柱“秦良玉文化”的类型、成因与保护[J].重庆社会科学,2007,(11):114-118.
[15]吴高仪.德宏州文化艺术志[Z].昆明:云南科技印刷厂,2001.
[16]李敏.土司系列遗产的国内外同类遗产对比分析[J].中国文化遗产,2014,(6):22-31.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Definition,Feature and Values of Tusi Culture
LI liang-pin1,YUAN Ya-qin2
(1.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y and Culture along Wujiang River Basin,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Fuling 408100,China;2.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Tusi Culture,closely related to Tusi system,refers to the totality of material culture,system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which is created by the feudalist governments and the peoples in the Tusi areas in southwest,central south and northwest of China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usi culture is featured by diversity,richness,nationality and ir.Besides,tusi culture contains many values like thought,academy,education,art,resources,etc.
tusi culture;definition;feature;values
K03
A
1009-3583(2016)-0013-06
2016-05-15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16BMZ017)阶段性成果
李良品,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袁娅琴,女,重庆酉阳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