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的《管子》两英译本比较
2016-02-14孔海燕
孔海燕
(山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淄博255000)
文化比较
跨文化视角下的《管子》两英译本比较
孔海燕
(山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淄博255000)
文章从跨文化翻译的视角对比了美国汉学家李克和中国学者翟江月的《管子》英译本。李克的翻译重在介绍,鲜加评论,旁征博引,考证精详。其特色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力求形式对等。翟江月的译本采用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力求功能对等;她的译文语言平实,易于理解。两个译本各具特色,也各有不足,但是都为“中学西传”做出了重大贡献。
跨文化翻译;管子;异化;归化;形式对等;功能对等
比较全面的《管子》英文译本至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汉学家李克(Walter Allyn Rickett)的译本,分别在1985年和1998年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另一个是鲁东大学文学院翟江月教授的译本,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是《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一部分。两个译本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本文试图从跨文化翻译的视角来对比这两个英文译本。
一、跨文化翻译视角下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一)两英译本作者比较
《管子》两个英译本的作者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也不同。两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肯定会对他们各自的译作产生影响。
李克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21年10月26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1948年他携妻子李又安(Adele Rickett)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汉语并教授英语。1955年回到美国,此后一直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系任教。
李克在《管子》方面的工作始于1948年,但是,他对翻译方面的尝试是1954年在南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路易斯迈夫瑞克( Lewis Maverick) 指导下开始的。1955年他回到美国后,将八篇译文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的基础,后来把它扩展到十二篇,1965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管子〉:早期中国思想的一个宝库》。1985年《管子》的第一卷译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1996年他完成了《管子》的第二卷译文并于1998年出版。
翟江月,1970年出生,鲁东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精通国学,专注于中华文化典籍的整理、注解与翻译。她在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研究方向均为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博士毕业后曾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工作。自2005年起在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工作,先后讲授过“中国古代文学”“先秦诸子散文研究”“汉英英汉口译”等课程。自2005年起独立完成 “大中华文库”之《朱子语类选译》《吕氏春秋》《管子》《战国策》《淮南子》的今译、英译。她具有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精通英语、德语[2]。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李克精通汉语,英语是他的母语,在英语的运用和遣词造句方面他肯定会技高一筹。翟江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翻译过多部中国典籍,在对《管子》原著的理解方面肯定会更加精准。李克历经40多年翻译了一部作品,一定是考证精详,他的译作决不是那种缺乏对中国了解的草率之作,但是百密也难免会有一疏。翟江月从2005年到2012年7年间翻译了5部中国典籍,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多产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除工作之外还能翻译多部作品,确实令人钦佩,但是对作品的处理有些地方难免会显得粗糙。两人分别来自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一定会在译著中有所体现。
(二)《管子》两个译本翻译特色对比及分析
1.李克译本特色分析
李克的翻译“重在介绍,鲜加评论,旁征博引,考证精详”[3]。李译本的翻译特色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力求形式对等。身为汉学家,李克熟悉中国文化,也知道翻译过程中文化传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翻译《管子》时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策略,对中国文化因素的处理采取源语文化认同原则,保存源语的异国情调和异域色彩,同时更多地保留了语言文化的民族性。他的译本可以让外国读者领略更多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这种以源文化为取向的异化翻译策略主要可以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看出来。对于众多的文化负载词,他主要采取了直译法和加注法,这样既可以向读者呈现中国的异质文化,又照顾了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
例1: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军令行[4]2。
If the sovereign complies with the rules [regarding proper dress and expenditure], the six relationships will be secure. If the four cardinal virtues prevail, the prince’s orders will be carried out[5]52.
李克把“六亲”以直译的方式译为“six relationships”, “四维”译为“four cardinal virtues”。为了更好地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六亲”的含义,他在注释中给出了两种解释:“六亲”指“父、母、兄、弟、妻、子、女”或者“父子、兄弟、夫妻”。他对“四维”也做了注释,而且更加详细,从其原意——系在渔网四角把渔网提起来的绳子,到其在本文中的含义——指四种主要的德行“礼、义、廉、耻”。除此之外,“six relationships”和“four cardinal virtues”在形式上采取对偶的方式,与原文一致。
李克译本(以下简称李译本)的“异化策略”还体现在译文中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一些词语,他采用了音译加注法,即汉语拼音和汉字共同使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特色。译文中的汉字给读者带来了更浓厚的异域色彩,例如:
例2: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飞蓬之问,不在所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4]16-17。
Exquisitely lovely are the wild goose and swan; and so the people sing to them. Stately were the many officers [of Zhou周], and so the people of Yin殷 were converted by them. Advising him were the irresponsible vagabonds. Those lacking talent were welcomed as guests. Gathered around him were the swallows and sparrows [among men].Those who carried out the way were disregarded[5]67-68.
李译本在语言和形式上力求与原文一致,把“鸿鹄”和“燕雀”这种具有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具有比喻意义的词也直译出来,然后用脚注进行解释。“鸿鹄”翻译成“the wild goose and swan”,“燕雀”翻译成“the swallows and sparrows”,译文与原文形式、意义完全相同。“殷”“周”用了拼音加汉字的译法,这种翻译方法保既留了原文的特色,又展现了“异域文本语言和文化差异”[6]111,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形式对等”是李译本的特色之一。“形式对等” 要求译文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尽可能的与原文保持一致;“要求读者将自己溶入原文文化圈,对其风俗礼仪、思维模式、表达习惯等了如指掌,以原文文化一员的角色来阅读译文”[7]。李译本在语言形式和语言风格上都与原文尽可能的保持一致,这种“形式对等”更多地体现在对偶句和有节律的语言中,例如:
例3: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维君之节[4]12。
Be like Earth. Be like Heaven.
What partiality or favoritism have they?
Be like the moon. Be like the sun.
Such is the constancy of a prince[5]56.
例4: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4]44。
When planning for one year,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planting grain.
When planning for ten years,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planting trees.
When planning for a lifetime,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planting men[5]96.
例3中原著采用了“诗经体”,使用了比兴手法,四字一节,朗朗上口。译文也使用了诗歌的形式,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原著保持一致,忠实地反映了原文面貌。例4原著用排比和对仗的手段论述了管子的人才培养观,译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式,用三个完全相同的句式与原文形式对等。
除了“异化策略”和“形式对等”之外,李译本也采用了“归化策略”,即“以目标语为归宿的原则”[8]。“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9]李译本中的归化策略主要体现在:(1)对文章的小标题做了调整。李克根据现代文体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把小标题放在前面例如:《牧民》 中分为“国颂”“四维”“四顺”“十一经”“六亲五法”五个小节。《管子》原著中,小节题目放在后面,每一小节结束后另起一行写到“右国颂”“右四顺”等。翻译成现代文则是“以上是国颂” “以上是四颂”。原著的这种编排既不符合现代文体,读起来感觉内容也不够清晰。李译本对这种编排做了调整,把小标题放在前面。调整后的文章让人感觉主题突出,重点鲜明,而且符合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的阅读习惯。《立政》《乘马》《七法》和《幼官图》等也采用了这种编排。(2)李对部分小标题做了修正。《牧民》原文中有一小标题为“六亲五法”,李克根据原文内容及考证,改成了“四亲五法”(four categories to be observed and five rules)。在注释中他提到:六亲与文章内容不符,因为文章内容是论述如何治理“家,乡,国,天下”,所以他把“六亲”改为“四亲”。(3)李克对原著篇目顺序适当调整,重新安排,把“经”与“解”编在一起。例如,把《形势解》编在《形势》之后,把《立政九败解》编在《立政》之后等,而且逐句对应。此外,他还把《宙合》篇明确地分为“经”和“解” 两大部分,使之一一对应[3],这些作法,方便了读者,也体现了美国学者严谨、认真的态度。
尽管在翻译过程中,李克竭力忠实于原著,但是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某些传统文化的不可翻译性,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意义、修辞或语用方面的损失。为了弥补这种损失,李克使用了多种翻译补偿策略。“翻译补偿是一种翻译技巧。译者意识到的某些损失可以通过运用某些手段进行补偿,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10]翻译补偿分“译文内部补偿”和“译文外部补偿”。译文内部补偿主要是指在译文内部对句子的增补;译文外部补偿则是指在译文正文外部进行补偿,主要包括对译文整体、原作者等的注释、附录以及译者所加的前言、后记等,也包括译者对译文的某个词、句子、段落所加的脚注、尾注。李克在翻译过程中大量使用补偿策略。如例1,作者添加了(regarding proper dress and expenditure)来增补,使整个句子更加完整。这是一种文内补偿。大量的文外补偿是李译本一大特色。每篇译文前都有引言,对该篇的主旨大意简要介绍。“引言论证了文献的哲学倾向(它是属于墨家、儒家、道家、法家,还是其他的哲学流派),指出本篇文献与其他文献之间的关系, 并且推断它可能的成文年代。在每篇译著的注释中, 附有许多资料、解释和订正。”[11]以《幼官》为例,在正文前有21页的介绍,除此之外,译者还添加了214处脚注。这些文内、文外补偿既有效弥补了文化损失,又有助于译文读者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2.翟江月译本的特色
翟江月实际上做了两种翻译,她先对《管子》做了语内翻译——把原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再做语际翻译——把现代汉语翻译成英语。翟江月翻译的目的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译文以受众接受与认可为目标。在英译技巧方面,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兴趣、价值观、接受能力等,既要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又要符合英语言国家的文化习惯。所以,翟江月译本(以下简称翟译本)采用了归化与异化有机结合的策略,译文力求功能对等。
翟译本在思想、内容和形式上都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重在传达《管子》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如上文例2,翟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The singing of the wild swan is responded by the eulogy of the common people to praise the virtues of their sovereign. The court is full of sensible and capable persons, so even people of the overthrow the Shang Dynasty are deeply moved by its benevolent policy. No one will pay attention to rumors. No one will give importance to trifles[4]18.
翟译本把“鸿鹄”直译成“the wild swan”,把“殷民”意译成“people of the overthrow the Shang Dynasty”,使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更容易理解。而后两句话“飞蓬之问,不在所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摒弃了原文中的对偶结构和比喻修辞,采用两个陈述句“No one will pay attention to rumors;No one will give importance to trifles”,使晦涩难懂的文字变得一目了然。这是翻译结构和语义的归化。翟译本通过高度归化方法,使《管子》的核心思想跨越较少的文化障碍得到较大程度的传达。翟译本虽然在形式上与原文有较大的差异,但是较好地实现了“功能对等”。
翟译本注重“功能对等”,重“神”不重“形”。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认为:“语言交际不仅仅是为了传达信息,而是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因此,翻译是不光要注意作为信息载体的语码形式及其转换,还应考虑译文与原文功能上是否一致。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功能对等,而不是形式对等。”[12]188翟译本很好地体现了奈达的这一理论。《管子》原著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句子平仄押韵,而翟译本中很少使用诗歌化的或节律性的语言。上文例3,翟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The sovereign should behave himself just like Heaven and Earth doing everything without partiality. The sovereign should behave himself just like Heaven and Earth illuminating everything without bias[4]13.
原著中的四个小短句,翟江月翻译成了两个长句子。虽然句式不同,但传达了相同的思想。第三个小句子“如日如月”,翟译本仍然翻译成了“just like Heaven and Earth”,笔者怀疑是误译(下文会提到)。
为了达到“功能对等”,翟译本在很多地方使用了阐释的方法进行意译。先理解原著,然后用阐释性语言进行解释。例如:
例5:帝王者,审所先后[4]276。
Sovereign are people who should weigh a situation scrupulously to decide what kind of things are of more importance and value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handled first, and what kind of things are of less importance and value and therefore can be postponed[4]277.
从以上译文可以看出,翟译本对该句话详细地进行了解释,使原文内容变得好理解,而且也易于被译文读者接受。
“功能对等”是翟译本的主要特色,但是“形式对等”也没有被舍弃。这也正是翟译本“归化与异化有机结合的体现”。如上文例4是这样翻译的:
In making a one-year plan, the best thing is to grow crops; in making a ten-year plan, the best thing is to plant trees; and in making a hundred-year plan, the best thing is to edify people[4]45.
这一句的翻译与原文句式完全相同,从形式和内容上传递了原文的风貌。
用词朴素、平实是翟译本的另一个特色。翟译本使用了地道普通的英文词汇和句法结构,客观上降低外了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难度。她避免使用生涩词,用普通的英文词汇自然地传达文意。如:
例6: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憾乎若有从治[4]286。
Sages use their wisdom in this way: they make it appear to be muddleheaded, huge and round, so that no one can manage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intentions they have, and they make it appear to be as chaos as floss, however, it also seems that there must be a way to make it clear and neat[4]287.
这句话原文晦涩难懂,“沌沌乎”“豚豚乎”这种表达方法连母语是汉语的人都难以理解,更不要说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的西方人了。翟译本中这句话的内容非常清楚,几乎没有任何的理解障碍。总之,阐释式的归化意译加上地道平实的用词,使翟译本易读易解,提高了译文读者阅读的接受性。
二、两译本的局限性
(一)李译本的局限性
李虽然是汉学家,但是汉语毕竟不是其母语,虽然其译本考证精细,但是难免对原文的理解有些地方会有偏差。
例7: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4]296。
If, when serving relatives, wives and children are given everything, respect for the father will decline. If, when serving the prince, the prince is pleased with the work [of his ministers], so their families are enriched, the activity of [ his ministers] will decline[5]223.
显然,李对原文的理解有偏差。他把“亲”翻译成“relatives”,理解显然不够准确。此处应该是指“父母双亲”, 而不是亲属。“有好业”,李译成“the prince is pleased with the work [of his ministers] 君主对他的工作感到满意”,这种理解显然有误。翟译本对“有好业”的语内翻译是“有了自己的产业”。因此她翻译成“obtained significant properties”。笔者查阅了几个版本的管子译注,均与翟译本一致。另外,“爵禄满则忠衰矣”,这句话李译本直接没有翻译出来。“忠孝”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维系国家和家庭不可或缺的纽带。原文中传达的思想是:在“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庭和产业之后”,“忠孝、德行”会衰退,李译本没能完整、正确的传达这一思想。李译本中这种由于文化等因素,翻译不够准确的地方还有很多,再比如:
例8: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4]64。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month of spring, the prince himself shall listen to the court…At the end of the last month of winter, the prince shall listen to court…[5]105
很显然,“孟春之朝,季冬之夕”在此指的是年初和年末两个时间。李把“孟春之朝”翻译成“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month of spring”与原文相对应。但是春天开始的时间由于地域不同而不同,容易引起歧义,不如翻译成“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更确切一些。同样地,把“季冬之夕”翻译成“At the end of the last month of winter”,虽然形式上与原文对等,但是容易引起歧义。
由于《管子》成书于2500多年前,其语言与现代英语既有“时空错位”,又有“文化错位”,所以很难保持译著在风格和特色上与原文一致,例如:李克把“士” 译为“gentry” (绅士),可能会造成误解, 因为“gentry”也可解释为轻率或缺乏经验的人[11];把“君主”翻译成“prince”,虽然“prince”有小国的君主、诸侯的意思,但是现代人更多的把这个词译做“王子”;把《枢言》中的“国有宝,有器,有用”中的“用”翻译成“media of exchange”,交换媒介,原文中是指“珠玉等财宝”,这种翻译给人的感觉过于西化和过于现代化。
(二)翟译本的局限性
翟译本过于注重“功能对等”,忽视了必要的“形式对等”,译文缺少了应有的美感。如例8翟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During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the sovereign should hold court in person. …during the end of the third month of the winter, the sovereign should hold court in person to discuss the criminal law and penalties…[4]65
“孟春之朝,季冬之夕”原文对仗工整,而且不难理解。但是翟译本把“孟春之朝”翻译成“During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却把“季冬之夕”翻译成 “during the end of the third month of the winter”,冬天的第三个月末。 这种时间的表达方法不确切,让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很难理解到底是指什么时间。如果把“季冬之夕”翻译成“during the end the last month of the year”,与“孟春之朝”“During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相照应,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很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例1中翟译本把“六亲”译 为“all his relatives”,把“四维”译成了“four reins”,也属于这种情况,忽略了形式上的对等。翟译本中这种问题还有很多。
翟译本中多处地方使用阐释性翻译,有些属于过度阐释,导致译文臃长,失去了原文的精炼之美,如例5原著只有7个字“帝王者,审所先后”,而翟译本却使用了45个字,事实上,这45个字都是对“审所先后”这四个字所做的阐释。“《管子》其文约,其义微”[13]344,“其言贵简,不漫不凡”[14]148,翟译本的过度阐释失去了原著的语言风格。
翟译本中有些关键的文化负载词,前后用词不一致,给译文读者造成不必要的理解困难。例如:在《牧民》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翟译本把“耻”译为“sense of honor”[4]5。但是在《权修》中“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耻”却翻译成“sense of shame”[4]47,而在《枢言》中“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有耻也者”却被意译成“some are supervisors”[4]294。“耻”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使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法让译文读者无所适从。而李译本这三个地方均翻译成“sense of shame”。再比如“鸿鹄”,该词在《管子》原著中出现过很多次,如在例2中,翟译成“the wild swan”,而在《霸形》中,“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在此句中翟译成“the swan geese”[4]567。鸿鹄是古人对大雁、天鹅之类飞行极为高远鸟类的通称。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使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鸿鹄”是比喻“志向远大的人”,鸿鹄之志也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文化负载词,前后翻译应该相同。
另外,翟译本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翻译错误,这种错误可能是粗心,也可能是排版错误。如上文提到的例3 中,“如月如日”,翟译本仍然翻译成了“just like Heaven and Earth”(如天如地),而紧跟其后的动名词却是“illuminating”(照亮),该词正好与“Sun and Moon”相搭配。由此可见,此处是一粗心错误,也有可能是印刷错误。
总之,李译本和翟译本在翻译中各具特色。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二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李译本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力求形式对等;翟译本是归化与异化有机结合,译文力求功能对等。李译本广泛使用补偿策略,翟译本大量运用阐释手段。虽然两个译本各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都为“中学西传”[6]117,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1]李克.管子研究在西方[J].管子学刊,1989,(2).
[2]翟江月的个人介绍[EB/OL].鲁东大学研究生处官网, [2016-03-20]. http://www.grad.ldu.edu.cn/dscx/person.asp?uid=D0000065.
[3]冯禹.《管子》英译本评介[J].管子学刊,1998,(2).
[4]翟江月.管子[Z]//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Rickett,W.A. 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 Volume One[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6]徐珺.汉文化经典外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曹青.奈达理论与跨文化翻译[J]. 浙江大学学报,1995,(9).
[8]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9]李宗政.《管子》外译研究概述[J].管子学刊,2014,(2).
[10]刘琳,梁颖.从文化翻译理论视角看汉英典籍翻译信息补偿[J].鸡西大学学报, 2013,(5).
[11]罗宾.评李克译注《管子: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J].管子学刊,1989,(4).
[12]许力生.语言研究的文化视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5.
[13]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4]章沧授.先秦诸子散文艺术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张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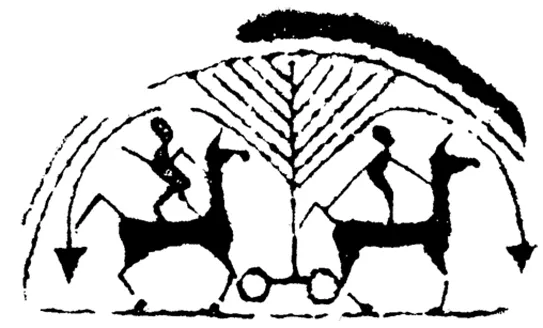
2016-09-13
孔海燕(1970—),山东曲阜人,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和英语语言教育。
B226.1;G04
A
1002-3828(2016)04-01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