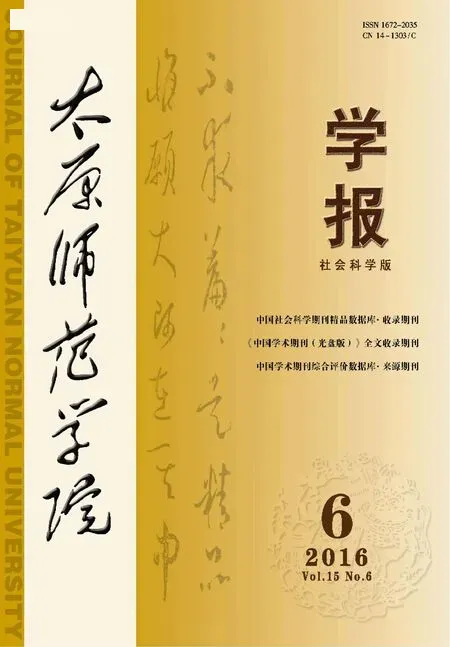《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官僚主义”的再思考
2016-02-13王晓瑜
王晓瑜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文学】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官僚主义”的再思考
王晓瑜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刘世吾与官僚主义的表层特征有诸多不合,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者,而是一个深谙权谋的权术玩得纯熟的干练官僚。刘世吾用权术手段收服了韩常新,在与林震的交往中也使用了恩威并施的权谋手段,并利用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威胁林震。工作中,刘世吾的能力异化为一种捕捉上司意图的能力,这成为其工作的中心内容与动力。刘世吾性格形成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场权谋文化的浸染。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官僚主义;刘世吾;权谋;权谋文化
在以“干预”生活为明旨的特定“双百”文学语境中问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早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视角下被阐释的。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文学语境的变迁,这样一种政治色彩很浓的阐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许多的接近文学本身的富有学术性的阐释随之不断出现。但是本文中,笔者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探讨仍然要从“官僚主义”这一“陈旧”的话题谈起。
何为“官僚主义”呢?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1]418-422
“官僚主义”一般可以理解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的瞎指挥等作风。它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
对照以上特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韩常新显然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王清泉也与此有诸多的吻合,组织部长李宗秦在其位不谋其政,甚至区委书记周润祥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也有明显的官僚主义味道。林震参加的组织部的第一次部务会议“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2]34,他们工作的组织部似乎也弥散着官僚主义的气氛。但是官僚主义的这些特征却显然不能涵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刘世吾。刘世吾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上述官僚主义的表现与特征和刘世吾有着诸多的不合。刘世吾最为接近的形象似乎是“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但刘世吾事务主义者的形象主要来自于他的自述:“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2]40林震眼中的刘世吾并不是这样,林震第一次见刘世吾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悉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2]29
作为组织部的实际负责人,组织部的一切都处于刘世吾的掌控之中,尽管作为生命个体的刘世吾经常是呆在办公室中足不出户,然而刘世吾的“场力”却弥散于整个组织部中,刘世吾无处不在,组织部的所有人员都处于刘世吾的监控之中。初到组织部的林震想把自己了解到的有关麻袋厂的问题向刘世吾反映,未等林震开口,刘世吾就说王清泉“下棋呢还是打扑克?”“他老兄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2]35——王清泉的一切行为都在远离麻袋厂、坐在组织部办公室里的刘世吾的监控之下,那么作为刘世吾的下属在刘世吾的眼皮子底下工作的林震不更是“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吗?”所以,刘世吾在此看起来是在谈王清泉,而实际也是对新来者林震的一种告诫:你的所作所为也都在我的监控之中。
刘世吾工作极多,常常同一个时间好几个电括催他去开会,但他还是一会儿就看完了《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把书转借给了韩常新;而且,他已经把前一个月公布的拼音文字草案学会了,开始在开会时用拼音文字作记录了。
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上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2]34
刘世吾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是游刃有余、有张有弛、举重若轻,丝毫看不出他所说的“忙”。与昏聩无能、敷衍塞责、装腔作势、官气十足……这样一些我们惯常理解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不同,刘世吾显然是个精明能干的官员。然而隐藏在刘世吾精明强干之后的是比这样一些表层化的显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更可怕的东西——官场权术或曰权谋,这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官僚主义。刘世吾性格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官场权谋文化有很大关系。
刘世吾对其工作可以说轻车熟路,毫不费力,丝毫没有事务主义者的手忙脚乱。林震到组织部不久,就形成了对刘世吾“最突出和新鲜的印象”[2]34:
对于刘世吾与韩常新,刘世吾在漫不经心间已完成了对韩常新的控制。刘世吾漫不经心地边查阅文件边听韩常新汇报,这样一种状态会使韩常新放松警惕,露出更多的破绽,对这样的破绽“突然指出”[2]34会使得韩常新猝不及防,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刘世吾的审视之下,刘世吾的手法相当老道,几乎可以说是一招毙敌。之后刘世吾便再无下文,并不深入追究,如果从权术斗争的角度看,这时已是胜负判然,不需要更多的言语,而韩常新的的破绽在此已不是需纠正的“工作失误”,而是成为捏在刘世吾手中的“把柄”,随着这样的“把柄”不断地聚集,刘世吾可以随时出手致韩常新于死地。有这样的“把柄”在手,任韩常新“比领导还像领导”[2]30在别人面前人五人六装腔作势,一到刘世吾面前也只能是服服帖帖。韩常新“恢复了常态,有声有色地汇报下去”,[2]34也只能是表面地故作镇定以掩饰其内心的慌乱。
在林震初进组织部第一次见到刘世吾时,刘世吾的表现就满是权谋的色彩,刘世吾对林震的第一次接见就是恩威并施。林震去见刘世吾时,刘世吾与林震的谈话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是谈工作,然后是谈生活。刘世吾在用“锐利的眼光”[2]29迅速地审视过林震的党员登记表后,就开始大谈组织部的工作,尽管刘世吾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2]30但是这样的谈话无疑是庄重肃穆的,而且这样的言说是单向的,林震只能是处于下位的聆听者。这种以“相当深奥的概念”[2]30为内容的话语致使“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2]30这是一种代表组织的上者用“组织”的语言对下者的训诫,通过这样的训诫,组织部的主人之于组织部的新进者的组织的代言人的身份得以确立,在林震面前,刘世吾借此立威。而刘世吾的精明在于刘世吾不想如韩常新一样“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2]30,不想以高高在上、官气十足这样的浅薄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示人,因此在立威之后就马上要显现出自己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关心下属的一面,在训诫完成之后,立即“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2]30与林震谈生活:询问“有没有对象”[2]30、谈工作之余的读书。刘世吾在拉开与林震的距离之后又试图拉近与林震的距离,立威之后示恩,以此让下者感受到上者的关怀。这种立威与示恩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即是种玄妙的“官场艺术”,比如说,先后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因为示恩必须以立威为前提,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关心下属等品质只有在上者与下者的官场等级关系确立以后才有意义。对于这样的“官场艺术”刘世吾操弄得相当熟练。
在韩常新与林震发生争执的党小组会上,刘世吾“在一定关头起扭转局面”[2]36作用的发言,其背后包含着更可怕的逻辑:
刘世吾的权术还表现在,其对上级意图的揣摸上,用毕光明的说法叫做“上本位观念”,上级的意图是刘世吾工作的动力,也是其工作的中心内容,对此,毕光明这样分析:
目前辣椒辣度的测定方法中,国标(GB 10783-2008)法[2,3]测定辣椒碱含量,存在使用巨毒药品、重复性差等问题;Scoville感官评定法[4,5]存在测试环境限制较多、主观成分较大的问题;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6-8]的操作环境难以摸索,体系难以建立,并且仪器维护费用较高,且不便于田间应用。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便携式的快速、准确、稳定的检测技术。
城市空间高楼耸立、人口密集,地面绿化受到严峻限制,向建筑的“第五立面”索取绿色,营建屋顶花园,是改善生态和人居环境的一条崭新途径.屋顶面积大约占城市面积的20%~30%,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屋顶绿化是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最有效的方法.屋顶绿化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绿量和绿化面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提升空气质量,而且还可以保护建筑材料、降低噪音、减少能耗,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贡献已被各方认可,也必将成为我国城市绿化的一个新方向.
对于沉浸于刘世吾“真诚”叙述氛围中的林震而言,这完全是猝不及防的,“停止了夹肉”[2]40、“颤抖着手放下了筷子”[2]41,内心的慌乱显而易见。这与前边收服韩常新的手法——“一面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的材料,听着听着却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韩常新不自然地笑着,刘世吾的眼睛捉摸不定地闪着光,但刘世吾并不深入追究”[2]34——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种利用私生活说事的手段虽然有些不够光明,但对于达到目的却是非常有效的,1955年丁玲、陈企霞事件中,陈企霞就是因之而被逼就范的。林震尽管涉世未深,也明白其中的分量,小说这样描写离开馄饨铺后的林震:
离开馄饨铺,雨已经停了,星光从黑云下面迅速地露出来,风更凉了,积水潺潺地从马路两边的泄水池流下去。林震迷惘地跑回宿舍,好像喝了酒的不是刘世吾,倒是他。同宿舍的同志都睡得很甜,粗短的和细长的鼾声此起彼伏。林震坐在床上,摸着湿了的裤脚,难过,难过,说不清为什么要难过。眼前浮现了赵慧文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他还是个毛小伙子,他什么也没经历过,什么都不懂。他走近窗子,把脸紧贴在外面沾满了水珠的冰冷的玻璃上。[2]41
当然,科史哲领域的情况较为复杂,这是因为科史哲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因而有一部分研究内容被SSCI和SCI同时收录。为了客观地介绍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期刊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界定科史哲学者的学术水平,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方面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笔者将结合自身的科技史学学科背景,借助2007~2016年期间WOS数据库的科技史类和科技哲学类英文期刊数据,借助社交网络和知识图谱软件SATI和NETDRAW,将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分类反映国际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学科的刊物、学者、机构分布情况以及整体知识架构。
(2) Logistic回归以液化概率50%作为液化和非液化区分时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87.7%,这与其他的研究结果相近;虽然准确率为非连续变量,但该结果可作为砂土地震液化确定性分析的一个参考。
而最具权谋味道的是刘世吾与林震在馄饨铺中的谈话。不可否认,这次谈话中刘世吾不完全是虚伪的,其中不乏真情的流露,然而只要注意这次谈话的背景——这次谈话发生在区委常委会即将讨论麻袋厂的问题之时——就不难发现其隐含的意义:刘世吾试图阻止不谙组织部隐性规则的新来者林震在区委常委会上口无遮拦的发言。从后来刘世吾的劝阻失败后林震在区常委会上的发言及发言后会议的状态看,这样的发言无疑会打破刘世吾等“组织”中已非常娴熟且习以为常的会议的“套路”,显现出会议“不团结”、“不圆满”的一面,把参会的组织部诸人以及组织部甚至于组织部的上级领导者猝不及防地置于尴尬的境地,因而也受到了所有参会者一致的围堵。这样的阻止首先从规劝开始,刘世吾先从其年轻时的经历谈起,也许这确实是刘世吾的真情流露,然而也不难发现刘世吾规劝方式选择的“机心”所在,刘世吾自己的真实感情也成为刘世吾自己利用的工具。这样的“曾经的青年人”的故事显然很容易拉近青年人林震与刘世吾的心理距离,刘世吾学生领袖时的“往事”也很容易引起刚离开学生生活的青年人林震的共鸣,这样动情的叙说很容易解除对方的戒备心理使其沉浸于情感之中而疏于理性的防范。刘世吾在与林震的对话中也有自责,然而这样的自责也有着这样的意义:通过“自责”营构的“坦诚”话语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刘世吾以“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2]40结束自己的“成长”叙事,对自己失去“热情”的自责结语同时又是对林震“经验”欠缺的提醒,刘世吾始终在努力以自己从“年轻”、“热情”到“经验丰富”的成长经历的示范效应来获得林震对自己及组织部生存现状的认同,直接但却迫近的目标即是使林震放弃在区委常委会上的冲动行为,按组织部中的潜在规则行事。然而这种规劝结果显然是难以预期的,所以当林震“开始被他深刻和真诚的抒发所感动了”[2]40的时候,刘世吾突然抛出了对于林震极具杀伤力的武器: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据我看,赵慧文对你的感情有些不……”[2]40
总而言之,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受到了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影响,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现状能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管理水平等。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实际上就是微生物或者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食品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普通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两大类:第一是不同食品之间作用生成的有毒物质,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第二是人为添加了一些影响健康的物质,所以必须加强食品安全质量管理工作力度。
他工作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这里,“指示”不同于“传阅文件”,后者是一般性的,无关大局,而前者来自于“上面”,是从权力中心那里递贯下来的,它决定着政体中枢神经的脉动。[2]52
上级的意图是刘世吾工作的动力,也是其工作的中心内容,刘世吾的聪明才智很大部分耗在对上级意图的捕捉上,于是他的工作能力也就逐渐异化为一种捕捉上司意图的能力。在处理麻袋厂问题上,刘世吾所谓“时机”成熟与否实际即取决于上级意图。刘世吾时刻都在敏锐地捕捉上级意图的蛛丝马迹,这是他决策的依据。麻袋厂问题处理的契机来自于《北京日报》刊登的一封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的读者来信,介于党报“党的喉舌”的定位,以“显明的标题”登出的这封读者来信透露出来的是比区组织部甚至比区委更高的组织的“声音”,更何况还加有从口气看是体现来自更高级别的领导者的意图非常明显的“按语”:“……有关领导部门应迅速作认真的检查……”[2]39小说这样描写刘世吾:“他把报纸拿给刘世吾看,刘世吾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抖一抖报纸,客观地说:‘好,开刀了!’”[2]40一则简单的读者来信刘世吾要看几遍,显然是要捕捉并确认来自“上边”的声音。所以说,麻袋厂问题解决的时机并不取决于王清泉问题有多严重,也不取决于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问题是主要的,更不取决于工人的不满有多强烈,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者的意图,刘世吾的精明强干很大程度上在于不露痕迹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所以,刘世吾一再说自己忙,但这不是事务主义者的忙,时刻注视并捕捉任何能透露权力高层的意图的蛛丝马迹才是刘世吾的“真忙”。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本身存在潜在的偏倚;其次,本研究为单中心、鼻咽癌好发地区收集的病例,这可能影响模型的广泛适用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多中心、多地区数据收集验证。
在刘世吾面前几乎是落荒而逃,显然此时的林震内心已是张皇失措,不难看出刘世吾关于赵慧文的话题的震撼性力量。尽管林震后来未听从刘世吾的劝阻,仍然坚持在区委常委会上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然而其后林震也不得不立即清理自己与赵慧文的关系,林震接受赵慧文的邀请去赵家,其实是要将自己与赵慧文的关系作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这种意向也获得了赵慧文心照不宣的回应,赵慧文把两人的关系界定为:“你是我所尊敬的顶好的朋友,但你还是孩子”、“你像是我弟弟”、“就这些了还有什么呢?还能有什么呢?”[2]41-42这既是给予两人交往之中模糊不清的地方的一种清晰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把其中的男女情爱的含义排除出去(对于林震而言,这是他与刘世吾交锋时自身存在的最危险的“罩门”),同时这样的界定也是对两人以后的交往划定的界限。对这种关系的清理是林震采取下一步反抗的前提,林震走进周润祥的办公室之前必须告别赵慧文,因为刘世吾以对林震私生活的介入这样的权谋手段已成功地把赵慧文从林震的支持力量转化为林震的负累。
请林震同志想一想:第一,魏鹤鸣是不是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呢?很难说没有。那么魏鹤鸣那样积极地去召集座谈会,可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目的呢?我看不一定完全不可能。第二,参加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复杂别有用心的分子呢?这也应该考虑到。第三,开这样一个会,会不会在群众里造成一种王清泉快要挨整了的印象因而天下大乱了呢?等等。[2]36
这分明是种从动机出发的有罪推定,这样一种“动机论”的威力在于,不但可通过把关注重点从事件本身向当事人动机的悄悄转移回避对事件本身的曲折是非探讨,而且通过这样看似严密的推理其实可给任何人都能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本来是讨论王清泉的问题,但是经刘世吾的语言操弄有问题的反倒变成魏鹤鸣。而“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2]35的论调则是推卸责任、文过饰非、化过为功的利器。
刘世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者,而是一个深谙权谋的权术玩得纯熟的干练的官僚形象。他与韩常新这样的浅薄的官僚主义者相比有着难以为人觉察的隐蔽性,但是其危害却绝不下于后者。
为防止机器人在无条件执行前行巡检命令时因运动性物体干涉导致撞击危险的发生,并且希望机器人能够具有自主检测障碍物采取主动措施的功能,在机器人前部使用了红外测距传感器模块(GP2Y0A02YK0F),即红外避障模块.该模块不受电磁波的干扰,不受周围可见光的影响,为非噪声源,不会对工厂的检测设备造成干扰,故可以在昼夜进行工作[6].
关于刘世吾的性格成因,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中,唐挚先生把它归之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3]9,新时期以来,谢泳提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刘世吾是陷在组织部里的‘学生’”,刘世吾的性格是因为同化于“党文化”而形成的,[4]32毕光明认为刘世吾是“被组织,被革命话语所异化”[5]50。这些都有道理,都注意到了刘世吾性格形成群体意识方面的原因(阶级原因与文化原因),但笔者却认为,另外一个原因也应注意,那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相当悠久而发达的官场权谋文化。
在中国春秋战国的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曾经出现过纷繁的多元竞存的文化景象,但是从秦帝国便开始了一元独尊的文化专制,然而在春秋战国出现的多种文化样态中,建立起一元独尊的文化“王朝”的只有两家:儒家与法家。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自不必说。法家文化“王朝”尽管仅在秦代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儒家文化“王朝”所取代,但法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并没有因之而结束,许多学者提出,汉以后被定为一尊的儒家文化其实是外儒内法,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官方文化其实是儒与法的集合体。这两种文化的内容尽管有诸多不同,但是都注重“经世致用”文化,而在如何实现“经世致用”上,两者都选择了借助于政治统治者的力量来完成。而要被政治统治者所选择,其中必须有对政治统治者维护统治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必然导致这两家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设想为政治统治者来思考问题,因而,这两家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一种以“上”以“主”为本位的“谋士”文化,统治术或曰权术就必然成为这两种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或曰核心内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所产生的强大的控制性的影响力自然会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权谋文化极大地发达。另外,中国也是文官制度建立最早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也有足够长的时间与空间发展出相当成熟的官场文化,这种成熟的文化显现出极强的吸附与感染能力。
对于一个革命政党和其成员而言,在革命阶段,处在下者的位置,这样的官场权谋文化是作为旧秩序的组成部分而被置于需反抗破除的范围,较容易与自身区隔开来。但是一旦革命成功,新的秩序建立之后,当需要从革命时的“理想与激情”状态中沉静下来,用一种新的精神状态新的方式维护新的秩序时,革命政党与革命者由于在社会格局中的位置变化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对这样一种以上为本位的权谋文化产生某种不自觉的认同,这也就是来自离权力中心较远的学校的青年革命者林震身上比离权力中心较近的组织部里的先到者刘世吾等保留更多的革命时代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种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文化用于维护某种秩序而非破坏某种秩序时有着相当神奇的效用,因此,对于刚刚成为社会管理者的“刘世吾”们而言,对这种旧治理方式的借用要比摸索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方便容易得多,而且从短期来看也有效得多。所以当刘世吾们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组织部,在成长为一个精明强干的“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时,同样潜藏着一种“蜕化”的危险:被悠久的官场权谋文化所俘获,成为权术玩得纯熟的干练官僚。而当刘世吾们的场力弥散于“组织部”中时,官场权谋文化有可能取代革命文化成为“组织部”中的控制性力量,“组织部”也有蜕化为旧式衙门的危险。因而,在古老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吸收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固然重要,然而切不可忽视对传统文化中惰性文化的清理。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J].人民文学,1956(9).
[3] 唐挚.谈刘世吾性格及其它[J].文艺学习,1957(3).
[4] 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J].南方文坛,2002(6).
[5] 毕光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J].中文自学指导,2005(5).
【责任编辑 冯自变】
Reflection on Bureaucratism in Wang Meng’s Novel
“The Newcomer in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WANG Xiao-yu
(LiteratureInstitute,TaiyuanNormalUniversity,Jinzhong030619,China)
In the novel “Newcomer in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Liu Shiwu seems not a typical bureaucrat. In fact, he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tactics and is skilled at playing at it in dealing with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colleges and his superior. He is more capable of fathoming out his superior’s intention than doing work itself. Such character is sha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of political tacti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Newcomer in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bureaucratism; Liu Shiwu; political tactics; the culture of political tactics
2016-06-07
王晓瑜(1971-),男,山西临县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1672-2035(2016)06-0074-05
I207.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