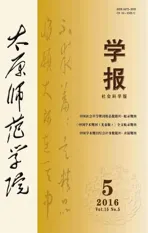巫山神女文学形象由来及其与后世两大神话之渊源
2016-02-13张洁宇
张洁宇
【文学】
巫山神女文学形象由来及其与后世两大神话之渊源
张洁宇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巫山神女的文学形象历来多认为出自于宋玉《高唐赋》与《神女赋》。然考察历代归属,发现这一形象是在《山海经》中的帝女“女尸”与《九歌·山鬼》中的“山鬼”两大原型基础之上塑造而成的,到宋玉时才得以定型。同时,这一形象经过长期的演变,不仅以精魂为草的幻化开启了后世的“蘨草神话”,还影响了后世的望夫石传说。
巫山神女;文学形象;望夫石传说;蘨草神话
关于巫山神女这一形象的来源,学界已提出很多说法,这些说法包含了文学、宗教、风俗传说等各种因素,从而使巫山神女原型有多种解释,但单独从文学角度探讨其形象来源的研究却显不足。鉴于此,笔者拟针对其文学形象的由来进行整体梳理,并就以巫山神女为原型的两种幻化,探讨其与望夫石传说和“蘨草神话”这两大神话母题的关系。
一、巫山神女文学形象的由来
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塑造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女神,她居住在高唐之台、巫山之阳,后世称之为巫山神女。巫山神女在《高唐赋序》中有过一段自我介绍,李善注《文选》在江淹《别赋》中提到:
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为灵芝。[1]754
这段介绍,交代了神女的身世与经历:巫山神女原为炎帝的小女儿,未嫁而亡,死后封于巫山,精魂化为灵芝草。
在此之前,《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曾记载:
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蘨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2]165
这段话记述了炎帝之女“女尸”死后在姑媱之山化为蘨草的传说。对比两段,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描述的相似之处——同为炎帝之女,死后同样封于一座山,同样化为灵草。可见,宋玉在塑造巫山神女这一文学形象时,很有可能借鉴了“女尸”形象。从帝女到山神,这种经历的转变,正为宋玉二赋提供了神话的因子,也为神女提供了身份的来源。
至明代,杨慎《跋赵文敏公书<巫山词>》对宋玉借鉴《山海经》曾有过讨论,他说:
古传记称,帝之季女瑶姬,精魂化草,实为灵芝。宋玉本此以托讽。后世词人,转加缘饰,重葩累藻,不越此意。[3]354
这里的“古传记”即《山海经》,杨慎也认为宋玉塑造的巫山神女借鉴了帝女“女尸”的身份,并指出宋玉借此故事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可见,《山海经》的记载是宋玉创作巫山神女形象的一大来源,为宋玉提供了明显的借鉴。
另外,宋玉笔下巫山神女的形象除了借鉴《山海经》中的帝女身份和传奇经历之外,在塑造其风貌与性格上又取材于屈原的《山鬼》。屈原笔下的“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宋玉的笔下的巫山神女:“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对比之下,两位神女相似的神情风貌跃然纸上。此外,二人同处巫山,同为巫山山神,同样渴望爱情(神女“愿荐枕席”,“山鬼”则是“芳杜若”)……种种相关,并非只是巧合。
清人顾成天也认为巫山神女与屈原的“山鬼”形象存在很大关联,在其《楚辞九歌解》中曾提到:
又《山鬼》篇云:楚襄王游云梦,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4]3099
据此可知,屈原笔下的巫山山神“山鬼”,很有可能是巫山神女原型的来源之一。屈宋二人同为楚国人,文学作品的描写内容还都局限于楚地的风土人情,《山海经》中姑媱之山与巫山的转变,也在情理之中。
再者,《山海经》中的“女尸”形象较为简单朴素,宋玉想要塑造他心目中的神女,“女尸”的风貌远远不及,于是他借鉴了屈原《山鬼》中描写的那位巫山女山神,将“山鬼”的风貌与“女尸”的身份相结合,塑造成了具有楚地风情的巫山女神,她妩媚动人、风姿绰约,她身份高贵、经历传奇,这便是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巫山神女这一文学形象,其身份和经历源于《山海经》中的帝女“女尸”,其神情风貌则来源于屈原《山鬼》中的巫山山神,二者形象衍化而成了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并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具有传奇浪漫色彩的典型形象。
二、巫山神女与后世两大神话之渊源
1.神女“化石”与望夫石传说
巫山神女“化石”的传说来源于其曾帮助大禹治水的一段经历。《山海经·大荒南经》载:
袁珂先生认为:“‘云雨之山’即巫山,‘禹攻云雨’神话,当即禹巫山治水之神话也。”[5]377大禹曾经在巫山治理过洪水,那么,巫山神女传说与大禹治水神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联系。隋唐之际,道教发展,我们可以在许多的道教故事中窥见这一传说的详细记载,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载: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瑶姬。……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禹尝诣之崇巘之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千态万状,不可亲也。……隔峰有神女石,即所化之身也。[6]178
这是唐代被道教化了的神女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大禹治水曾求助巫山神女。神女变化多端,时而为云时而为雨。“顾盼之际,化而为石”、“隔峰有神女石,即所化之身也”则道出了她还能够化作石头,细读“顾盼”二字,正有“望”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神女能够“化石”,且是一块“望石”。
“望石”与望夫石的联系似乎不太明朗,但望夫石传说则与大禹治水神话相关的另一个传说——塗山氏传说关系密切。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说:
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7]117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云:
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塗山氏曰:“欲晌,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塗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8]190
塗山氏化石生子的故事被后人认为是望夫石传说的滥觞,关于塗山氏,她与巫山神女存在许多关联。这些联系,龙耀宏先生在其文《“云雨”与巫山神话考释:文学·神话·礼仪》一文中有过明确说明:首先,巫山神女封于巫山之阳,塗山氏在塗山之阳;其次,《山鬼》中的巫山神女一直在等待自己的爱人归来,塗山氏作《候人歌》,候禹归来;其三,巫山神女是在楚王巡游高唐之时与之相遇并自荐枕席,塗山氏在禹巡省南土之时命人候之并与禹成为夫妻;其四,巫山神女的精魂可以化为服之媚人的蘨草,塗山氏则是能媚人的九尾狐的化身;最后,巫山神女在治水时化为神女石,塗山氏也在大禹治水时产子化石。[9]
此外,关于由巫山神女精魂而化的蘨草,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说:
为人所爱也。《传》曰:“人服,媚之如是。”一名荒夫草。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还记载:
又东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棃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状如,白华黑实,泽如蘡薁,其名曰蘨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2]169
郭璞注:
次玉者也。启母化为石而生启,枉此山。见《淮南子》。
郝懿行笺疏:
郭注《穆天子传》云:“太室之山、嵩高山,启母枉此山化为石。而子启亦登仙,故其上有启石也。”皆见《归藏》及《淮南子》。[10]271
按郭璞所注,蘨草即荒夫草,神女精魂所化,“荒夫”即没有丈夫的意思,这与她未嫁而亡相照应。李道和曾在其文章中大胆地提到“‘荒夫草’也可能直接就是‘望夫草’的音讹”[11],且蘨草周围又多“启母石”,“启母石”本身就是塗山氏所化望夫石。塗山氏既为望夫石传说的滥觞,巫山神女又与其存在莫大关联,那么巫山神女与望夫石传说的关系自不待言。
2.神女“化草”与“蘨草神话”
《山海经》中帝女“女尸”死后化为蘨草的传说开创了后世灵芝仙草幻化的先河,即后世所称的“蘨草神话”。关于“蘨草神话”的发展演变,最早的当是屈原所作的《九歌·山鬼》。
“山鬼”不仅是巫山神女多情风貌的原始化身,她“采三秀兮于山间”的生活活动,也是精魂化草的最早实证。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曾将“采三秀兮于山间”一句翻译为“巫山采灵芝”,灵芝,即是其精魂化成的蘨草。在屈原笔下,生长于巫山的灵芝草和采灵芝的女山神同为一人,她的形体化为山石,还要每天采集由她的精魂化成的灵芝草,她品性高洁却只能顾影自怜、孤芳自赏,正是屈原借“山鬼”对自身形象的表达。
两汉魏晋乃至隋唐以来的志怪传奇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异类幻化故事和传说,但真正与“蘨草神话”相关的仙草幻化类型的故事却少之又少。这种空缺一直延续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出现后,“蘨草神话”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
曹雪芹的《红楼梦》开篇便讲述了三生石畔一棵绛珠仙草幻化成人,转世以眼泪报恩的故事。“绛珠仙草”所幻化的人就是小说的女主角林黛玉。关于林黛玉神话原型意象的记叙,《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均曾提到:
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12]14-15
一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了出来!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12]184-185
第三支《枉凝眸》:“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12]191
《红楼梦大辞典》中对“绛珠草”的解释为:“有大红珠状果实的仙草。绛:大红,或即为灵芝草。”“阆苑仙葩”的“葩”字,《说文》云:“葩,华也。”“仙葩”即“仙华”,“华”又为“花”的古字,由此看来,绛珠草就是生有大红珠状果实的灵芝仙草。上文已经提及,灵芝仙草为巫山神女之精魂,绛珠仙草既为灵芝仙草,那么绛珠仙子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是巫山神女。曹雪芹借助巫山神女这一神话原型,为《红楼梦》中的人物添加了神话的因子,这一点,与宋玉异曲同工。而且,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形象之时,多次写到她的“草木之质”来暗合其特殊身份,其人物塑造无论是品性外貌还是情感命运、居住环境,都与巫山神女十分契合。这一点,前人研究颇多,故笔者不再赘述。
三、小结
本文主要探讨了巫山神女文学形象的由来与演变。笔者在排除宗教、民俗、文化等因素的干扰下,对巫山神女的形象单从文学角度进行一次系统解读,用较为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巫山神女这一神话原型进行了综合研究。笔者认为,无论是起源于《山海经》的帝女“女尸”、改编于屈原笔下的“山鬼”,还是曹雪芹笔下的“绛珠仙草”林黛玉,巫山神女的文学形象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与两大神话传说的渊源联系,更是让这一形象家喻户晓。在人们心目中,它不仅是浪漫多情与楚王相恋的痴情神女,还是帮助大禹治水、守卫家园的正义女神;不仅是精魂不息的灵芝仙草,还是“顾盼化石”的神女峰。总之,巫山神女这一形象,有待于我们深入解读。
[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二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方韬(译注).山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郭超.四库全书精华·集部(第一卷)[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楚辞类存目十一·楚辞九歌解[G].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5]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道藏(第十八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7]吕不韦(撰),冀昀(译注).吕氏春秋[M].北京:线装书局,2007.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龙耀宏.“云雨”与巫山神话考释:文学·神话·礼仪[J].文学遗产,1990(4).
[10]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85.
[11]李道和.试论作为望夫石传说原型的塗山氏传说[J].民族艺术研究,2003(6).
[12]曹雪芹.《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南图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琴】
ZHANG Jie-yu
(CollegeofLiberalArts,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Origin of Wushan Goddess Image and Relation to Later Two Myths
The image of Wushan goddess is always thought to be from Song Yu’s “Gaotang fu” and “Goddess fu”. However, after tracing back, the author finds that it is shaped based on two prototypes of a princess in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and “my alter ego” in “Nine songs”, later on it is set in Song Yu’s work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volution, it helps the creation of two myths of “Spiritual grass” and “Frowning rock”.
Wushan goddess; literary image; frowning rock; spiritual grass
2016-05-28
张洁宇(1992-),女,河北保定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6)05-0073-04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