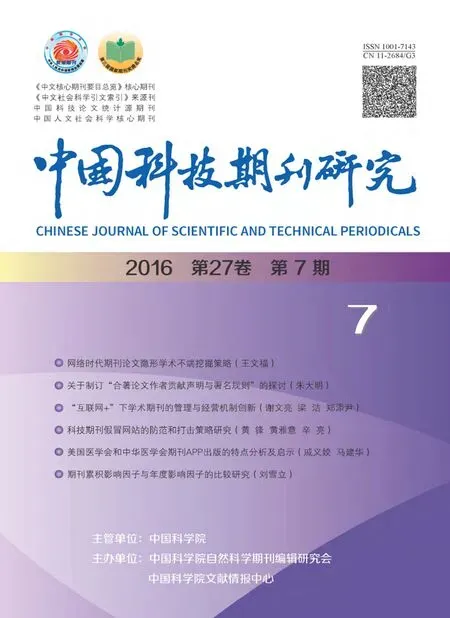《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问题新探及修订建议
——以文字复制比检测为参照
2016-02-13丁明刚
■丁明刚
巢湖学院图书馆,安徽省巢湖市半汤路1号 238024
2015年12月1日《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1](简称“新规则”)正式实施,与2005 年颁布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2](简称“老规则”)相比,尽管该规则在题名、适用范围和用途、术语及定义等方面作了重要的技术改变[1]Ⅲ,实用性增强,但不少规定却对文字复制比的检出率、检准率和检全率存在着不利的影响,与之相关的主要问题有:部分术语界定不准确,著录格式中若干选择项目、非电子出版物“出版”日期的标注形式、“著者—出版年制”等的规定不科学,部分规定前后不一致,多数示例不明晰不统一,引用文字未规定标识等。
通观新规则颁布以来的研究文章[3-10],涉及上述问题的主要研究有:韩云波[4]、陈海燕[7]对“参考文献”的定义及分类提出质疑;余丁对文献类型标识代码、电子资源“更新或修改日期”与个别责任者等的著录示例提出质疑[9];韩云波建议废止两类参考文献的区分、将其他责任者及其责任等任选项改为必备项、引用日期不予标注或不作为必备项、著录时尽量保持文献原貌[4];丁明刚认为“引用日期”应作为必备项发挥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10]。这些质疑与建议触及了新规则中存在的部分悬疑问题,虽然不乏高见与合理性,但不少分析似乎缺乏更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和更加彻底的解决办法,问题的存在无疑会影响文字复制比检测的成效。尽管新规则不是为检测制定和服务的,文字复制比检测也并不能完全直接地判定文章的学术不端,但检测对参考文献的引证和著录具有很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两者有着高度的契合,新规则是对引证的规范与指导,文字复制比检测是对引证的核查与评判。
鉴于此,笔者以文字复制比检测为参照,根据检测对引用文献的引用日期、引用文字、引文来源等三要素的要求,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新规则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修订完善的方法和建议,一定程度上地增强了新规则的确定性、准确性、实用性和权威性,从术语界定、著录规则与格式优化、著录要素归属等方面试图解决规则制订中的一些悬疑问题,促进了新规则与文字复制比检测的相互作用与有效融合,以期更好地为编辑出版、学术研究和科研评价等工作提供参考。
1 检测对引用文献使用的需求
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核查论著中的引用文献去揭示引文的来源及使用量,为评判学术规范与不端提供依据。它对文献引用主要有三方面的“要求”:(1)引用日期明确。著者引用文献发生于终稿投出日之前,该日因而成为文字复制的逻辑上的时间终点[11];检测发生于编辑部收稿及文稿发表后,若要确定文字复制比,首先必须确定著者引用文献的确切日期。当引用文献明确标注了“引用日期”后,著者的引用时间便可进一步准确定位[10],进而构成“引用日期-引用文献-引文”的引用事实链和证据链,以便有效地对引用文献与非引用文献进行初步的取舍。(2)引文与其出处文献对应一致,标识清晰。核查是通过“引用文献”与“引用文字”的关联比对来确定文字复制率的,因此,引文必须与其出处文献对应一致,才能形成“引文标识-引文-引用文献-引文页码”的引用核查链,使引文的标识符、文字、文献、页码等要素成为文字复制核查的表象性印迹。(3)引用文献著录规范。检测要求引用文献著录要素齐全准确、格式规范、结构简练,以便清晰地再现源文献的来源与核查路径。上述三方面表明,检测核查必须依据引用文献的引用日期、引文量、引文来源等三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呈现又必须充分依赖参考文献的著录与标识,唯此,才能从形式上使检测与核查便捷、快速和准确。
2 新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其修订建议
2.1 “参考文献”的定义及分类
”是新规则的核心概念,其定义准确通俗才能使著者应用明确,这也是检测对著录的潜在要求,但新规则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却侧重于文献的著录与列举[1]Ⅲ,未指出其用途。 (1)“参考”具有引用、查阅、参看三种含义[12],从 GB/T7714—1987、2005、2015三个版本的实际使用看,该系列规则均主要针对“引用文献”,即“引用”是“参考”最主要的功用,“参考文献”的定义理应突出“引用”的涵义及要求,这在GB/T7714—2005版中早已作了较为准确的界定[2]1,因此,从利于著者使用和检测需要考虑,宜将此定义修改为“撰写论文、著作等过程中引用或参阅后予以著录和标识的文献”。(2)新规则首次将“参考文献”分为“引文参考文献”和“阅读型参考文献”,比老规则单纯将“参考文献”界定为“引用文献”有所进步,但该分类使得“阅读”“引用”与“参考”概念间出现了包涵与重复的问题,不够简练与明晰。很明显,新规则意在将“参考文献”区分为“引用文献”和“非引用文献”。由于检测是对引用文献的核查,“阅读型参考文献”非“引用文献”,与检测无关,可以不加列举,因此,“参考文献”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和命名为“参阅文献”(或“阅读文献”)和“引用文献”两种类型。这里,“参阅文献”(或“阅读文献”)专指著者撰文中阅读而未引用的文献,若列举,旨在展示非引用文献研读数量,或推荐读者查阅;“引用文献”专指著者撰文中征引的文献,须列出,旨在显示研究脉络、提供引证证据和核查依据。目前,“引用文献”成为学术期刊参考文献的主体或全部,多数期刊以“参考文献”列出,有的以“引用文献”列举(如《国际新闻界》);而 “参阅文献”与“引用文献”列举形式则较多[11]。
2.2 参考文献的著录
检测是借助“源”文献对引文进行核查的,引文的核查主要依据于引用文献的著者、载体、面世日期、查询路径、页码等信息,这就要求参考文献著录要素齐全、格式正确、结构合理。目前,新规则在著录的要素、格式等方面规定的还不够严谨,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示例不一致,对检测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2.2.1 “责任者不详”的用替代词语标注
所有的责任者及其责任是著者著作权的具体体现,也是检测核查的重要依据,应该作为必备项著录[4]。新规则规定“无责任者或责任者情况不明的文献,‘主要责任者项’应注明‘佚名’或与之相应的词。凡采用顺序编码制组织的参考文献可省略此项,直接著录题名”[1]9。 若省略“责任者”,会使参考文献因缺此关键项而在检测时被认为是漏著,最终判为学术不规范,因此,建议单个作者不详时一律标注“佚名”,作者为机构、团体时标注其名称。
2.2.2 “多个出版地”应如实著录
新规则规定“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只著录第一个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1]10,这种规定不符合文献出版的实际情况。尽管出版地在文献检测中不是主要要素,但它对于核查文献来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无论出版地有多少个,只要是文献上标注的,都应该如实照录。同时,“出版地”作为版权信息,应该准确、完整、如实地著录,这也是尊重著者知识产权的具体表现。
2.2.3 “选择项目”应尽量减少或取消
新规则规定“参考文献设必备项目和选择项目。凡是标注‘任选’字样的著录项目系参考文献的选择项目”[1]2。在规则第4部分多处规定“文献类型标识(任选)”“其它责任者(任选)”“年卷期或其他标识(任选)”[1]2-6。 然而,一方面,“为便于他人准确识别文献类型,方便计算机精确地对文献分类统计,对引用文献标注文献类型和载体类型很有价值”[13]73;另一方面,实际检测中,文献类型标识、其它责任者、年卷期或其他标识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决定着检测核查路径的选择和方法的应用。例如,对于普通图书、学术集刊、舆图、档案、数据集等未被检测系统比对库收录的引用文献,如果不标注其文献类型标识,则会使检测者无法确定文献来源而难以核查。因此,对于检测必要的要素,应予著录,尽可能减少或不采用选择项目[4],以增强检测的便捷性和准确性。
2.2.4 文献的“面世日期”统一置于“()”内
文献的“面世日期”是指文献出版、公布、更新、修改等开始公开传播于社会的日期。文字复制比检测报告上几乎都显示出了引用文献的面世日期,该日期对于判定作者引文引用日期的先后及真实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作者引用临近投稿日出版的文献时,在检测系统比对文献数据库未能及时收录到该文献而无法检测出该引用文献时,著录时若标注该文献的面世日期,就能够通过“引用日期”与“面世日期”的比较从时间逻辑上明确区分出“引用”与“抄袭”。
目前,新规则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1)规定标注专利文献的“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1]6、电子资源的“更新或修改日期”[1]7,而对于专著、期刊等具有明确出版日期的公开出版物以及新增的档案、舆图、数据集等类型文献[1]21却不作规定。 (2)4.6.2示例中将电子资源的“更新或修改日期”置于“()”内[1]7,而同样可以作为“电子资源”出现的专利文献其著录格式示例[1]6中,却没有将“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置于“()”内,这种前后不一致将使作者无所适从。(3)“7.2参考文献标识符号”规定“非公元纪年的出版年” 置于 “( )” 内[1]8,而8.4.3.3规定“出版年无法确定时,估计的出版年应置于方括号内(示例 3:[1936])”[1]11,这一规定不仅与上述面世日期处理不一致,而且,易于与“[引用日期]”相混淆。这些缺陷使得检测时难以甄别引用文献及其引用日期。
因此,建议规定所有文献引用时必须标注“面世日期”并统一放于“()”内,以便与“[引用日期]”相区别。为此,“7.2参考文献标识符号”中“()”的使用规定[1]8宜修改为“用于期刊年卷期标识中的期号、报纸的版次、文献出版或公开的日期(含非公元纪年的出版年、版权年、印刷年和估计的出版年)”,对于“估计的出版年”,准确起见,可以适当添加“估计”“估值”等字样,形如“(1936 估计/估值)”。
2.2.5 “引用文献”与“非引用文献”应明确分列
检测不仅要求将“参考文献”明确区分为“引用文献”与“非引用文献”,而且,还要求将它们在论著的文末、页脚、文中等处按照一定的顺序列举出来,使其在“面”上得以清晰呈现,以便阅览。遗憾的是,新规则没有规定将“引用文献”与“非引用文献”分开排列。目前,不少学术期刊仍然将“引用文献”与“参阅文献”和注释性文字混排在一起,造成检测时人工核查“参考文献”很不方便,且可能增加文字复制比[14]。因此,新规则应该明确规定“引用文献”与“参阅文献”及注释性文字严格区分并分别列出,这也有利于有效地解决脚注时参考文献等自动编码的难题[1]14。
2.3 引文与其引用文献的对应性应予强化
检测要求引用文献能够明确提供核查的来源或路径,引文能够清晰地呈现引证印迹,以便对引用文献与非引用文献进行取舍。这就要求引文标识必须明确揭示引文与其引用文献间的一对一、多对一的关系,这种对应关系除了通过引用著录予以揭示外,更需要通过引文序化、标注引用页码和引用日期等来进一步揭示,使引用得以在这些“点”上进一步显现。
2.3.1 引文与引用文献的对应
引文主要通过文中顺序编码制的“序号”或著者—出版年制的“(著者,出版年)”来标识。从著录与检测实际看,顺序编码制使用居多,著者—出版年制使用较少。众所周知,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是有先后顺序的,顺序编码制正是按照这种顺序来罗列参考文献的,这种做法便于文字复制比检测时快捷准确地将引文与其引用文献对应起来进行核查。而著者—出版年制则将参考文献表按著者字顺和出版年排序,即不按照文献引用的先后顺序排列,这不仅使不熟悉字顺的作者难以对参考文献排序列表,而且使参考文献与引文不能清晰、准确地对应起来;“参考文献未编码,不便于进行对应的追踪检索;没有明确的引文数量,不便于进行计量分析”[15];著录与标识的重复文字较多;引文标注的“作者,出版年”在检测时易于产生歧义,如作者姓名为两字时,核查时从CNKI期刊数据库中可能会检索到包括该姓名的三字姓名及同名者的文献,对于该作者在该年有多篇文献发表时,无法迅速确定引文究竟出自哪篇。这些缺陷直接导致检测时引文与其引用文献核查困难,影响了引证文献核查的时效性和准确率。
鉴于此,从便于检测考虑,建议对其进行序化处理:(1)引用文献按照引文先后顺序列表;(2)仿照顺序编码制编码,在文中“(著者—出版年)”的“出版年”的右上角用“[1]”“[2]”等作角标,引用文献表中的对应文献起首处标注相同的序号,再依先后顺序排列,10.2.3[1]15参考文献表中用以区别同一著者同一年出版的多篇文献的字母a、b、c等可以省略,引用页码仍按 10.2.4[1]15的规定在序号后标注。按此方法,笔者尝试对若干个采用“著者—出版年制”的参考文献表进行序化处理,然后再检测,发现文字复制的检出率与未序化前的相同,但对引文及其引用文献的比对核查则更为明晰、便易和准确。因此,这种革新将会从根本上消除该类型参考文献表在使用与核查中的弊端,使其更为实用和普及。
2.3.2 引文与其所在原文献页码的对应
检测时,报告单上会显示出引用的具体文字,这些文字须在原文献具体页码上进行核查。引用文献著录时若标注了该页码,则会使读者、检测者及时准确地找到引文在原文献中的准确位置,以便对引文的文字使用量、引证技巧等作出研判,这对于检测尤为重要。目前,科技期刊在参考文献页码标注上非常混乱,多数刊物标注论文等单篇文献的起止页码、图书的引用页码、报纸的版面(相当于“页码”)。同样的,新规则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1)规定专著著录时标注“引文页码”,但在其后的示例[5-11,13,15]中却未标注[1]3(电子资源著录的规定也如此[1]7);规定标注专著中“析出文献的页码”[1]4,究竟是指引文页码还是起止页码?(2)连续出版物[1]5、专利文献[1]6的著录未规定标注“引用页码”,而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要求著录“年卷期标识及页码”[1]5,此“页码”也指代不明。(3)附录 A“著录格式示例”[1]17-20中许多文献都未列出具体引用页码,其中,或一类文献全不列出(如A.2[1]17-18、A.5[1]18-19),或一类文献部分列出(如A.1[1]17、A.9[1]20)。 这些规定及示例明显不符合检测的要求,既然新规则明确规定“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1]Ⅲ,那么,所有的引文文献无论出自何种载体文献,只要有页码,都应该明确标注其引文所在原文献的具体页码,即“引文页码”。这一点对于文献核查最为重要。
2.3.3 引文、引用文献与引用时间的对应
新规则在著录项目必备性方面将老规则规定的“引用日期(联机文献必备,其它电子文献任选)”改为“引用日期”[1]Ⅲ,并在各类文献著录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示范,表明今后所有“引用文献”后都须标注“引用日期”。尽管著者引证的随机性很大可能导致引文时间的界定比较复杂[4],但其撰著过程中同步地将确定引证的内容标注上出处文献及引用日期是完全可行的,这不仅是新规则的要求,同时也是学术规范化的表现[10]。依据这些日期去检测,可以使文字复制的判断与取舍更为准确便利[10]。然而,新规则中除了电子文献外,其它类型文献均未标注引用日期,这对于检测核查最为不利。为此,建议规则今后修订时规定在各类文献著录项目中必须列出“引用日期”,并将部分出版物参考文献标注的实为“引用日期”的“查检日期”“检索日期”等统一规定称为“引用日期”并予以标注。
2.4 明确标识引文的使用量
根据引用文字的使用量,引用可分为照抄型、提取型、指示型三种形式。照抄型引用属于直接引用,引用的文字量直接转化为复制率;提取型引用、指示型引用属于间接引用;指示型引用几乎不产生复制率,提取型引用是摘录式、碎片化的引用,可以大大降低复制率。作者在与检测的博弈中,一般都倾向于采用后两种引用方式,这无疑会增加学术不端的机会。文字复制比检测是通过指纹比对技术来确定复制文字量进而得出文字复制率的,它认可的是“照抄式引用”,比对认定可准确到几个字,因此实质上是对直接引用的检测。从引文标识看,文中引文处标注的序号或“(著者,出版年)”只能大致显示引文所在的位置,不能揭示引用的文字量。这对于核查引文量是不利的。对于直接引用的文字量,国内外有关文献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规定。例如,美国《芝加哥手册》规定:“凡使用他人原话在3个连续词以上,都要使用直接引号,否则即使注明出处,仍视为抄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引用,凡从他人作品中得来的材料和观点都必须注明出处,否则即为抄袭”[13]8。就检测而言,通过参考文献著录标明引文出处重要,而以适当的符号标出引用文字则更为重要。因此,建议规则增设双引号(“”)作为“引文标识符”,补充入“7著录用符号”中,以便规定将直接引用的文字置入其中。这样,不仅可以巧妙地显示出引用文字量,有利于区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引用文字量及引文使用程度,而且,还有利于直观辨别引用部分与非引用部分,对引用进行质性分析,规范引证行为,实现引文在文字使用“量”上的必要显现,使检测更为顺利和准确。
3 结语
新规则系参考ISO 690:2010(E)《信息和文献参考文献和信息资源引用指南》研制的[1]Ⅲ,该指南“存在大量不完备、纰漏甚至自相矛盾之处”[9],如“未规定参考文献或引文的著录格式,所列举的众多示例也未对著录格式和标识符号的使用做出规定”[13]16,作为国际指南这些似可理解和接受,但新规则作为基础性、通用性的国家标准不仅出现了较多的因审批、编辑、校样、出版等不甚严谨而产生的“非原则性”的差错[13]77,而且在技术标准、著录格式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适合检测要求的问题,这与国标应有的准确性、严谨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的高标准要求不相符。以文字复制比检测来审视,尽管新规则对该指南进行了“取舍和改良”[9],但同时也过多地默认和接纳了其不确定性,采用“应”“宜”“可”等动词去表述条款,设置出应严格执行的要求型条款、供选择执行的陈述型条款和建议执行的推荐型条款,供著录参考文献时灵活选择[13]18,这就难免导致了规则中部分项目和示例的模棱两可和模糊不定。因此,新规则修订时,既要参考相关国内外标准,同时也应适当参照文字复制比检测、著作权保护等的实际需要。应该看到,以文字复制比检测为参照,对新规则的修订与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提供新依据,明确新标准,能够深入有效地解决部分悬疑问题;第二,提供新思路,拓展其路径,提升技术水平;第三,以确定文献类型标识、引用页码、引用日期、面世日期等的必要性去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陈述型、推荐型条款,以充分增加要求型条款去增强新规则的确定性、明确性和权威性;第四,以修改部分术语、增加引文标识符、“统一风格、格式及标识符号”[13]16等去提升标准的一致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相信新规则在今后的不断完善中必将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1-2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1-15.
[3]陈浩元.GB/T 7714.新标准对旧标准的主要修改及实施要点提示[J].编辑学报,2015,27(4):339-343.
[4]韩云波,蒋登科.参考文献国家标准GB/T 7714—2015的修订特色与细则商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6):157-167.
[5]姜红贵.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新国标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5(11):29-32.
[6]曹敏.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解析[J].科技与出版,2015(9):41-44.
[7]陈海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部分条款解读[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3):237-242.
[8]黄城烟.参考文献中标准著录格式的新规定及其影响——以GB/T 7714—2015 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3):243-248.
[9]余丁.GB/T 7714—2015参考文献新标准的重大修改及疑点[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3):249-253.
[10]丁明刚.“引用日期”在文字复制比检测中的作用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3):254-258.
[11]丁明刚.适于文字复制比后检测的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规范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8):856-861.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Z].现代汉语词典(第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8.
[13]陈浩元.GB/T 7714—2015的新点、实施要点及其他[Z].
[14]谢文亮,李俊吉,张宜军.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误检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24(6):1126-1129.
[15]何荣利.我国科技论文参考文献双语化著录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7,18(6):1063-1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