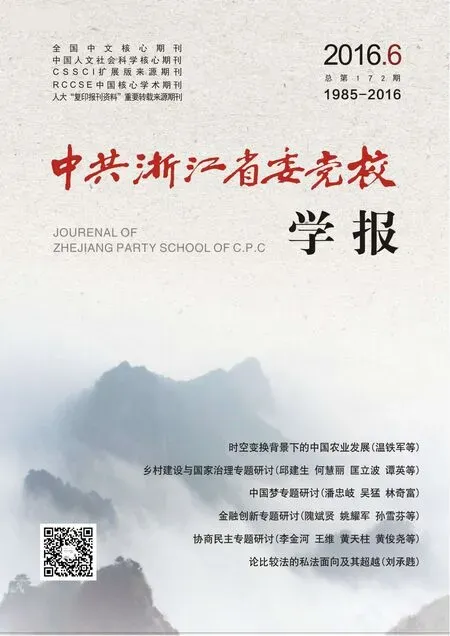从“祖灵祭”到“骂社火”: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生力探讨
2016-02-13何慧丽
□ 何慧丽 万 威
从“祖灵祭”到“骂社火”: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生力探讨
□ 何慧丽 万 威
关于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问题,需要从历史文化到现实习俗所体现的乡村治理经验中来探讨。台湾地区邵族的“祖灵祭”,作为一种基于族群历史文化经验形成的典型性乡村治理形式,是邵族人的祖灵信仰所生成的主体性力量;大陆豫西汉族的“骂社火”,则是基于现实中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典型性乡村治理经验,它因与小农经济社会相适应而成为当前乡村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和警示器。在现代化政权和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下,如何使像“祖灵祭”和“骂社火”这样的传统文化制度或者老道理,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发挥乡村治理内生力的功能,这是乡村治理的历史难题,也是时代机遇。
乡村治理;内生力;祖灵祭;骂社火;现代化
现代化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滥觞,某种程度上,使得乡村传统文化、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生态环境各要素自身及其间的自洽关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支解,这是乡村社会或原住民地区出现各种失调、冲突、矛盾等治理问题的主导性原因。如何在乡村外部宏观环境和条件逐渐改善的同时,增强农民或原住民日常需要的内部治理能力?对这种内生力从何而来、如何表现、如何发挥作用的探讨,显得尤为关键。
一、乡村治理如何内生: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乡村长期作为城市化、工业化转嫁发展成本的“受体”和牺牲者,由于缺乏主体性而沦为衰败的“无主体社会”,①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在乡村治理问题上甚至出现了“村庄终结”和“村庄异化”的极端不良现象。②朱霞、周阳月、单卓然:《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的策略及路径——基于乡村主体性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8期。在后农业税时代,由于地方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资本下乡又对乡村土地、资源和社会形成了冲击,这时的乡村治理问题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以政府治理缺乏为轴心的严重问题,*邓正来:《当代中国基层制度案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2页。表现在:基层治理能力弱化、乡村社会自我调节功能不足;*张月春:《中国乡村治理机制运行困境的理性思考》,《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问题突出、*周汝江:《农村空心化与治理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第4期;邱梦华:《利益、认同与制度: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生长问题研究》,《理论导刊》,2012年第8期。农村人际关系疏远、老人妇女地位低下,社会治安恶化;许多人缺乏对生活的良好预期,精神痛苦,甚至形成程度不一的个体病态心理。众所周知的“杨改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梁漱溟曾强调:“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老道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3页。面对乡村基础单元——村庄共同体遭遇瓦解,村庄的道德、舆论价值体系崩溃的严峻现实,要改善乡村治理,就不能只从治理现代化、经济扶贫等外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做文章,*李祖佩:《项目进村与乡村治理重构——一项基于村庄本位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4期;夏国锋:《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还要从“无形的根”——那些以乡村为载体、产生于中国传统乡民社会的“老道理”上下功夫,包括诸如历史文化信仰、地方民俗传统等内在的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化资源。这就是关注于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问题的重要价值所在。
关于乡村治理内生力问题的既有研究中,有从与国家政府等外发力的结合中强调乡村自治及其社会基础的那一面。费孝通说,“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提及了自下而上那一轨的重要性。*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293页。诸多学者也大都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对“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进行考察,将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自我调节作为与基层政府治理相并列的机制,*张月春:《中国乡村治理机制运行困境的理性思考》,《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主张以社会自主治理为方向、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引导的多元合作治理格局,*罗彩娟、曾令辉:《多学科视野中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广西社会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讨会综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徐勇:《建构“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乡村治理机制》,《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李乐平、韦广雄:《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以广西河池市“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为例》,《农业经济》,2015年第2期。甚至主张任何改善乡村治理的努力都不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郑茂刚:《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有一些学者强调民间传统文化信仰对乡村治理的作用,认为民间信仰是乡土社会的一项重要文化资源,其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密不可分;*袁松:《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定的村落神灵信仰使得农户之间凝聚力增强,村民精神有了慰藉,村落共同体观念得到深化;*侯娟:《一个村庄的民间信仰——后沟古村落初探》,《沧桑》,2007年第4期。同时它还是建立自我认同,区分不同群体的重要象征。*周大鸣、黄锋:《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也有主张对乡村治理进行综合化研究的,提倡以村庄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经济合作社为载体的乡村社群自组织建设,认为这是形成乡村治理良性结构、改善农民人际关系、重建农民本体价值和村庄生活意义的关键。*何慧丽:《乡村公共财的作用与生成逻辑》,《人民论坛》,2015年第14期;何慧丽、温铁军:《亟待从村庄层面突破小农困境》,《人民论坛》,2014年第7期。此外,台湾社区营造作为应对全球化结构性冲击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和“参与式民主”实践,主要是通过社区总体营造来对传统社区进行保护、实现自主性的社区治理价值。*莫筱筱、明亮:《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及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1期;屈秋谷:《社区营造模式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如上文献分别从乡村自治、民间文化信仰、乡村社群自组织和社区营造方面进行研究,虽然都是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或基础有关,但其不足之处在于:传统乡村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现代化宏观大势下用来“以文‘化’人”的既有力量——那些老规矩、老办法和老道理,对它们的机制运作及其实际功效,仍然挖掘得不够,缺乏足够的具体个案的阐发和分析。乡村治理的内生力,应该关注那些从历史文化深处和现实基层民俗内在产生的乡村治理经验,历史与现实这两个维度方面的经验是现代化背景之下有根的低成本、高实效的传统治理经验,而台湾邵族的“祖灵祭”与大陆豫西汉族的“骂社火”,正是从这两个维度观察乡村治理内生力的典型案例。
二、从“祖灵祭”到“骂社火”:从历史到现实的乡村治理生成及其经验
邵族,自称“以达邵”,主要居住在日月潭畔的日月村和水里乡顶村的大平林,以渔猎、农耕和山林采集为生,信仰祖灵。祖灵祭,是邵族人于农历8月举行的20天左右的一个活动,祭的是邵族最高祖灵和各家户祖灵。*关于祖灵祭的时间,均由邵族部落议会决定,通常为20天左右;祖灵祭也不是一年一次,近几年来每年都办,以前有时会三年办一次。此外,笔者近年来在大陆豫陕晋黄河三角地区参与以“文化本位”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试验,一直在关注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骂社火”的民俗现象。灵宝市古时是通洛阳、达长安的必经之地,“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94页。的荆山,就在附近的小秦岭山脉,其正对面就是传说中的黄帝铸鼎原,原下两村庄——东常村和西常村,是千年民俗“骂社火”的发生地。两村比邻而居,以传统粮食等农作物、苹果等经济作物为生,以一条小河为界,上架“联亲桥”,民风淳朴,关系融洽,文脉昌盛。阐述“祖灵祭”与“骂社火”作为内生性乡村治理的各自表现与特点,并对其进行比较,具有从历史到现实的典型性价值。
(一)祖灵祭:基于族群历史经验形成的乡村治理形式
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原住民群体,如何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中安身立命,处事有方?显然,借鉴祖宗智慧,以祖灵信仰为核心,追溯先民历史,保有本族群的文化主体性,是从原住民历史深处得到的治理经验。
首先,祖灵祭以敬拜祖灵为核心内容,增强了当前全体族员活着的底气和自信。祖灵祭主要包括如下部分:农历8月1日除秽、祭拜与在头人家会饮、8月2日祭拜与陷猎、8月3日少年凿齿与祭拜、8月4日搭建祖灵屋,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的半程祭、8月20日最后祭拜,其间充满了神秘与狂欢。*参见唐卫青:《“灵”与“人”——台湾地区邵族宗教信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祖灵祭中吟唱的歌曲有三十余首,邵族人通过在集中祭场歌唱多天,最后挨家挨户祭拜歌唱等形式,把祖先在部落战争中的出征与创业、荣光与梦想、对天地日月的感情、狩猎农耕生产中的艰辛与乐趣、日常生活习俗等等全都唱了出来。祖灵祭中的歌是唱给祖灵聆听的、舞是跳给祖灵观看的,具有与其先祖进行情感交流、灵魂交往的神圣性功能,在平时生活中则被禁止。通过祖灵祭的神圣仪式,邵族人的社群情感与关系增强了。正如一名邵族人所言:“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祖先住地就是我们的传统领域,祖先所赖以生活的山川土地我们要守护好,如果我们受外来各种力量的左右挪来挪去的,则是对祖宗的不敬重”。祖灵祭中所呈现出来的祖灵篮,*祖灵篮为祖灵信仰的具体表征,也是祭拜对象。祖灵篮置于家中,篮内盛装逝者衣物,邵族人坚信逝去的祖先在女祭师召唤之后魂魄会进入祖灵篮,与生者共处共存。平时都供放在各家住所前厅的高处,意味着过世者即使已经离世,也仍然与在世者居住、生活在一起,具有着鲜活的生命,因为,祖先就是家庭中的一员。“祖灵能庇佑族众,让族人平安健康,并且赐福给族人,使其代代繁衍并生生不息”。*李然、林毅红:《台湾邵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简言之,祖灵祭,是以对先祖的敬畏崇拜为精神信仰,使活在当下的邵族人树立起人与土地、人与人、今人与古人相连结的生活方式,以此重建社群信任关系、强化邵族人有根的主体性。这是族群内部建立良性秩序的根基。
其次,祖灵祭以在社区祭场和各家门前唱歌跳舞的礼仪形式,来展现使族群成员之间和谐相处的礼乐文化。祖灵祭祀时,族人每天晚上都在领唱长老家门口的大祭场(公共空间)上,进行两三个小时的唱歌排练活动。到最后的祭祀唱歌环节,从某家户门前开始,所有人都交叉着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来歌舞,每户15分钟,共46户人家,一家家地唱下去,没有例外。在歌舞仪式中,没有口琴、麦克风、伴奏带等现代音乐设备的协助,歌曲都是由长老起调,因为这不是唱给别人听的表演,而是唱给各家户祖灵、族人听的。其间,每个人都很用心地去找到和合的共鸣点。那纯粹美妙、空灵有力的歌声,时而低沉发自内心,时而高亢直达云天;祭歌以缓慢的声调与步伐开始,以激昂快速的节奏结束。 在此过程中,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围的圆圈越来越大,其中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有女人、男人; 有出嫁后回来的女儿,也有外出打工的返乡人;有本地人,也有城里人。每到一家,其家庭成员就会加入,每每唱完,此家就会摆上鸡汤、啤酒、点心、番薯、肉类等供大家食用,以补充精力和体力。从第一天下午5点开始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之前,邵族人挨家挨户激情歌舞17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手拉着手、相互拥抱、谈笑风生,这有助于弥合内斗裂隙、化解掉各种小矛盾。外来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歌舞仪式场景,想像邵族人平时的生活场景:“在社区里,老少孺慕,无论失业、失婚、残障、酒瘾、单亲、独居无依,都被接纳其中。大家在檐廊下共食、喝酒、歌唱谈笑,并邀请祖灵一起加入”。*郑空空:《台湾社区营造之六 邵族重建经验》,《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它有利于族人家户之间情感的凝聚与维系,唤起属于整个族群的文化记忆,修复源于共同祖先休戚与共、协作团结的统一关系。在现代主流文化正把原住民群体切割成原子化个体的趋势下,一旦一个族群丧失了其源自先祖的民族文化与品格,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不安、浮躁、无所归依?又何谈建立稳定治理与良性秩序呢?
再者,强调内生性的部落议会作用,是邵族人自主开展祖灵祭的组织保障。部落议会,其成员由本族中德高望重的氏族长老组成。以氏族长老为核心的部落议会会议,具有对“祖灵祭”这种神圣仪式的决定权。邵族年长者对祖灵祭坚持不懈,在符合其传统居住空间布局的小区里,形成属于本族向内的“深层民主”,因而促成了祖灵祭仪式的开展和不断发展。在邵族人的共同认识中,祖灵祭是本族人在现世中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不忘根本的大事。比如,邵族部落议会要深入讨论每年的祖灵祭如何办,什么时候办,是否年年都办等事情,至于当地政府出不出钱,如何出钱,那是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于祖灵祭,政府支持与否不是必要条件,关键还得看部落议会能否通过。这不同于许多其他族群把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成向外的展览或者观光资源,离开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就办不了的姿态和方式。政府所强调的发展观光旅游业等政绩,不是祖灵祭举办与否的主要考量因素。强调祖灵祭从根本上是邵族人自己的内部事情,这就是邵族的主体性意识。
简言之,邵族的祖灵祭,在活在当下的邵族人与已逝去的祖先之间建立起了伦理关系,加强了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是使人们找到有根的自主性的生存治理的好经验。
(二)骂社火:基于现实中小农经济社会结构的乡村治理经验
无论如何,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哪怕是政府主导的各种扶持资源,都只是助推力或者拉动力,不是原动力和内生力。台湾邵族人的祖灵祭,以尊重原住民信仰文化传统的方式践行,建立起了源自历史的内生性秩序。接下来介绍源自大陆豫西的另一内生性乡村治理经验——骂社火。在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的东常村和西常村,保留着千年的民俗传统——骂社火。村庄内部化处理的社会治理价值,是通过“骂”来实现的。
首先,从表演形式上来看,骂社火是将骂发挥到艺术高度的一种文化形式,它转化了作为社会冲突的“骂”。骂社火本质上不是“骂”,而是“耍”;不只是意味着“祭祀和祝福”,重要的是,它将小农经济社会中一年来积累的一些社会冲突和紧张,以“骂”的文艺形式“化”掉了。东西常村之间以相互刺激和挑骂的方式来交替耍社火,具体时间是正月初二晚上开始,正月十六下午结束,这正是农闲时节。其表演一般由骂阵(挑社火)、拜请、出杆、夜征四部分组成。关于骂阵(俗称后场子):骂阵队一般由锣鼓、三眼枪、骂家、护卫等约百十人组成,骂家翻穿皮袄,表示自己是野兽,规定兴骂不兴当场还。关于拜请:礼请对方村民来看社火,拜请队伍一般由探马开道,大约由200 多人组成,包括三眼炮、开场锣、横额、彩旗、宣读祭文等十余种形式。关于出杆:彩杆由捏杆、上杆、抬杆、护杆组成,杆队由外阵、内阵、后阵组成;*此处的外阵,由朱雀星,包括探马、报马、背色马、哪咤、护卫等十多人组成;内阵为左青龙、右白虎,包括刑兵、炮、锣鼓、火药、号角、大旗、日月灯、标驮、驮轿、禧刍、彩杆等,由八百多人组成;后阵为玄武星,包括圣旨、印玺、赶脚、总督大人、骂阵队等,由50 多人组成。近千人的队伍,扮丑角讽刺劝喻,斗文斗武斗富斗丑。关于夜征:骂阵队出征邻村,讽刺、挖苦、大骂村干部、族长等一切可骂之人,寓教于乐;当晚,生动活泼的竹马、船队、龙队、杂技等,充分展示群众艺术的智慧和技巧。*王林:《灵宝东西常骂社火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骂社火,将打破日常生活秩序,公开批评和颠覆乡村权威的言行暴力转化为艺术形式,给身处社火情境者一年来的积郁与不满、冲突与矛盾以巨大的释放感和宣泄感。
其次,从骂的对象限定和内容上看,骂社火有村内监督、村际监督和宣泄与警示之功效。骂社火的内容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性的,目的在于压倒对方,通常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主,语言简洁明快,尖锐刻薄,这是个亮点和特色;一个是实质性的,目的除了压倒对方之外,更主要的是骂一切歪风邪气、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比如“违法乱纪、虐待老人、家庭不和、村干部不良作风、不孝顺父母”的社会现象。*刘志松:《“骂社火”与民间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骂社火在骂的对象上不是瞎骂乱骂,而是有特指的:一不骂老实疙瘩庄稼汉,二不骂异族外来小户,三不骂出嫁的大闺女,骂虚不骂实,专骂村盖子、人员子、社火头,专骂两村的六大姓氏家族,亦即骂有组织能力的人,才能耍社火。*王林:《灵宝东西常骂社火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骂社火曾有戒赌之效:据1997 年编纂的《灵宝市文化志》记载:“清朝末期,因这一代偏僻,聚赌成风,新年、元宵佳节又是人闲事少时间,为避免赌风流行,用‘骂社火’的活动把人们从赌场吸引出来。”*灵宝市文化局:《灵宝市文化志》,灵宝市文化局1997年编印,第389页。下面举三例看骂社火的内容。有骂贪官腐败的:“各位乡亲往前站,我把贪官来批判。××消费档次高,他从公家会得稍。整天到处胡球转,不给群众把事办。这种作风不改变,百姓一定把你换。”有骂不敬不孝的:“村里有个张三混,视他爹娘如大粪。小时人称张二杆,长大就他不要脸。他爹要饭他不管,他妈吃饭他夺碗。若再虐待爹和娘,必定烂心又烂肠。”有骂投机经营的:“张学办个农药店,专卖假药把人骗。各位观众你别信他,小心把苹果都打瞎。”*姚向奎:《世俗狂欢节日中的“骂”文化——灵宝东西常村“骂社火”民俗现象解析》,《寻根》,2010年第1期。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也在被骂之列。而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反而认为,骂谁就意味着谁有档次,比如有行政能力的村干部——俗称“村盖子”,肯定是要遭骂的。被骂了的干部,不但很高兴,而且还得想一想是否骂得合理,是否要改正纠错,是否为群众办了好事。可见,骂社火是一种乡村舆论监督的传统艺术表演形式。
再者,骂社火的组织制度,与乡土社会及小农经济结构是自洽的,只是近现代以来有了一些变化。以村落为单位、民众广泛参与的骂社火文化,产生于遥远的古代社会:初始于尧舜时期;发展于夏周、春秋、唐宋元期间;成熟于明清直到现在。*王林:《灵宝东西常骂社火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它为何能在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绵延千年至今?原因是它作为乡土社会的文化结构部分,其背后有一个内生于乡土宗族社会的地方性群体组织来支撑。1949年以前,骂社火的组织者是由两村六个大姓的“头”——族长组成,其中,西常村有贾、苏、樊三大姓(现在1000多人口的西常村还是这三大姓居多),东常村有屈、张、王三大姓(现在2000多人口的东常村也还是这三大姓居多)。骂社火时只骂这六大姓,这是旧有组织体制的遗留。在近现代以前“皇权不下县”、国家对乡村进行有限管制的状况下,骂社火的组织者都是乡村内生的族长、乡绅等构成的民间权威。他们从事这项文化活动的经济保障,是社田、公田、庙田(相传这儿有十余座古老的庙宇、祠堂之类的遗址)等的产出,或者村里士绅、地主、望族和老百姓的捐献。在信仰道德、宗族社会以及社田族田的经济保障下,骂社火这类的文化习俗便可以持续地存活下去。可见,骂社火的组织制度,与传统乡土社会及小农经济结构是自洽的。然而,近现代百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对乡土社会经济结构的损蚀和瓦解,也随着国家政权下沉的干预性行为不断加深,乡村存在着去组织化、去社田公田化、过于依赖城市和外界的问题。骂社火作为一种乡土社会的内生性文化艺术形式,在这些危机下还能存活下去,实属不易。
简言之,豫西村庄大都是多姓村,骂社火以骂六大姓为主要对象,目的是把乡村社会“营造成一个不看大姓宗族脸色、多姓共生的公共领域”;*范长风:《豫西“骂社火”:从艺术性戏谑到公共领域》,《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同时,用艺术形式戏谑村盖子(村干部)的不良现象,能够起到监督村干部、促进公共利益的作用。骂社火,属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自洽于小农经济社会的一种民俗文化形式,它起到了传统村落之间、村中大小姓氏之间、村民与村两委之间关系调节与平衡的价值。
三、结论与讨论:用内生性的治理经验促进乡村治理的优化
(一) 乡村治理内生于以乡村为载体的历史与现实
乡村治理内生性,其基本点就是找到乡村问题内部化解决的现实依据和历史动力。优化乡村治理之道,实际上主要在于弘扬来自于乡村历史、经得起乡村现实张力考验的内在力量。无论是大陆豫西汉族的千年民俗“骂社火”,还是台湾地区原住民邵族的“祖灵祭”,就内容、形式和组织特征来看,都有一些从乡土社会内部产生的、应对现代化问题的治理经验。一个是原住民族从传统祭典仪式中建立其治理的有根的主体性;一个是从与现实小农经济社会自洽的民俗文化中达成乡村治理的动态稳定秩序,为的是在新形势下尽力恢复曾有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社会图景。*出自北宋学者吕大钧、吕大临等几兄弟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制定的《吕氏乡约》。见吕大钧:《吕氏乡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目录页。
从“祖灵祭”来看,任何乡村或原住民社会之所以能存活到现在,一定是有着内生的形塑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在以前,这种力量是日常生产、生活、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诸要素长期磨合所形成的乡村均衡或超稳定性。现代政权下乡和市场经济下乡的外发力可以影响乡村秩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形塑相对稳定的乡村秩序,一些乡村治理成绩的取得,表面上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结果,实际上则是乡土社会千百年历史经验深处的那些老道理的生发或弘扬,它会给予现代农民安身立命之基、精神归宿之本、基本“立”而治理“生”。
近现代以来中国大陆乡土社会的治理问题之所以产生,主导因素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下乡所造成的人口背土离乡、乡村社会动荡,以及乡村基层政权沦为“赢利性经纪”。*“赢利型经纪”由杜赞奇首先提出。杜赞奇讨论乡村社会统治“经纪模型”时,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护型经纪”;一类是“赢利型经纪”。前者保护乡村社会的利益,后者则视乡村社会为榨取利润的对象,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与赢利型经纪的形成相关。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2页。而“骂社火”这样的习俗文化形式,能流传并发挥作用至今,得益于它作为传统乡民经济社会的自平衡系统,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生产系统和社会生态结构的自洽。比如,村庄大户和大姓,为了防止他们变为“劣绅”或“赢利性经纪”,就在正月“骂社火”节日期间,由民众以艺术的形式“骂”他们,这是一种乡村自约束。
(二) 乡村治理的内生性发展,与其宏观环境的制约密切相关
乡村治理的内生性发展,其制高点,与外部的治理环境有机结合,在于现代化宏观环境的包容力和条件保障。
先看邵族“祖灵祭”的宏观环境和它的关系。近一个世纪的国家(包括日据时期)、资本和市场冲击,导致邵族聚落土地流失,社会关系瓦解,传统祭场仪式空间消失、自我族群失落,邵族命运不堪设想。*钟秀梅:《发展主义批判》,春晖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185页。其转机在于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为了避免族人四散,族群崩解,地震后邵族加强了部落议会的组织重建工作,希望建立一个不受干扰、能进行文化传承的基地。台湾各级政府也为地震后的原住民小区营造提供一定的费用;来自于建筑师谢英俊等民间社会力量,也帮助邵族协力造屋,复育文化。值得强调的是,政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为了原住民的社区重建,会提供社区重建的资金支持和有利于原住民就业的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会以征收土地、招商引资等方式践行发展主义。可见,在组织建设上,既有来自于邵族内部的部落议会作为族人利益的代表和保障,又有来自于政府的原民会作为政府方的政策性组织;在这两个组织之间,还出现了邵族民族议会,它的出现,一方面是陈水扁政府执政时期来自于政府的原民会大力推动的结果,一方面也是邵族面对政府凝聚全族共识、代表全族发言的对外窗口。
再看当前“骂社火”的宏观环境与其内生力的关系。大陆豫西传统农区如东、西常村这样的多元姓氏共存的村庄,其自给自足、自信自主的特性,实际上反映了以家族、村社为组织体系的传统小农村社制度特征。为了多元姓氏低成本地和谐共处于传统乡土社会,便生长出了“骂社火”这样的文化表达形式。然而,随着近现代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传统力量的边缘化,骂社火背后的组织体系逐渐发生了改变。传统向现代的社会文化心理改变,村社“内生资金”来源渠道的缺乏以及社会上“外援资金”的不稳定、国家政权过于强势地深入村庄……都直接影响到了“骂社火”这一原本内生的文化活动是否还能稳定举办。*赵文、王学文:《忧郁的狂欢——豫西骂社火的传衍之道》,《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对于“骂社火”的举行,政府不支持干预不行,过度支持干预也不行。近年来,东西常村的骂社火工作分组中,由传统的社火委员会成员承担表演和骂阵的工作,至于组织协设、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工作则由村两委和各村民小组负责,县镇两级的职责主要是指导和协助,这是政府体制与传统乡绅制度的相对合理的一种分工合作方式。从长远来看,骂社火会因乡村去组织化而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留住“乡愁”、保护传统文化举措的贯彻,骂社火又有了一定宏观环境和条件改善的可能性。
(三)乡村治理优化的相关思考
对于邵族而言,政府设立的原民会与原住民的部落议会如何融合或共处,以达到自上而下的现代制度背景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力量的有机结合,这是个难题。对于黄河岸边的传统农耕社会而言,如何在政府适当扶持的背景下,使村社内部力量得到充分的动员,并能够有效地承接政府及外界的资源下移,这也是个难题。只有内外结合,上下通达,在现代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发育好乡村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力,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的乡村社会,其乡村治理方方面面的问题,方能得到一定的优化。而就国家整体治理层面来说,以乡村内生力为根本的乡村治理优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是起着本质性作用的“里子”。内生型的乡村治理,需要发育像邵族部落议事会那样的自组织或者如组织骂社火的族长乡绅制度,其职责一是寻乡村精神之老根,传承那些有用的老道理,以接续祖辈生存智慧;其二是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时俱进,与现实制度结合,在巩固既有乡村精神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以应对时代要求。
梁漱溟曾经强调:“……非从老根上再转变出一个新局面来不可——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一个新文化来。从此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5页。在资源资本化的现代化背景下,如何以乡村老道理为根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这是“祖灵祭”和“骂社火”为典型个案的乡村治理经验,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熊 觉)
2016-07-01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万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与区域发展。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中国农业大学创新创业项目)“新常态下的人文社科重点问题研究”(编号:15056130);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2015两岸暨国际学人蹲点奖助计划”项目。
C912.82
A
1007-9092(2016)06-00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