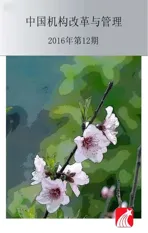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路径探索
2016-02-13邹宗根
● 邹宗根
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路径探索
● 邹宗根
基层社区承担着具体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任务,关系到社会建设的整体效度。目前,基层社区的整体框架基本形成,但是在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方面远未达到不断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的要求,亟待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满足社区民众需求,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转向难题
1. 陌生人社会自治缺乏基础。不同于以往单位、村庄转化而来的社区,现在城市中的大量社区无法依靠熟人社会长期形成的规则和秩序来实现自治。虽然,这些社区也在推行自治,但是缺乏实质性的基础,特别是社区未熟化阶段,陌生人之间的行为、交往和公共行动常常是失序的。城市社区中违建问题、业主间的冲突、业主与物业的矛盾等,都是缺乏自治基础的表现。即便在一些已经按照现有法律规范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推动自治的社区,也经常出现治理低效甚至无力的状况。
2. 街居制的资源和能力困境。基层社会管理从“单位制”向“街居制”的转变过程在形式上已经基本完成,但管理职责和服务能力却难以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城市社区的快速膨胀和居民诉求的多样化挑战着街、居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居民对社区的现实要求越来越高,其直观获得感来源于社区所能提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街居制自身也面临着职能转变等重要任务,伴随着权力下放、职责下移等行政安排,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具体事务,这使得其面临着资源和能力欠缺的双重困境。
二、城市社区自治低效的缘由
1. 公共权力的末梢效应。社区治理对政府有着天然的依赖性,源于国家的整体政治安排和资源分配方式,社区一味强调“自治”往往会演变成为“不治”。特别是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社区,多数基于“陌生人社会”的发展基础,脱离了国家进行社会培育,在现阶段是不可行的。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相关主体形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但实践中仍难以推进社区治理。业主委员会等形式的居民自治组织,由于居民间职业身份区隔显著,加之缺乏公共议题,很多基层自治组织并未真正发挥功能。即便在较为成熟的社区中,并非所有的个体和群体都有能力参与社区治理,特别是在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因此,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是社区管理体制修补和进化过程中最稳固、最清晰的常量,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需要国家政策的推动。而且,社区民主包含的自治制度和公民参与权利的落实,也需要成熟的行政管理作为体制基础。在基层社区自治尚待完善的情况下,需要政府及时干预,主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公权力不仅需要在市场失灵时提供公共服务,更需要在社会失灵时及时干预并有效化解矛盾。
2. 治理体系的虚化影响。目前,城市社区的治理体系仍然以行政官僚制为主,各组织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上下级的垂直关系,社区工作站、居委会、党支部与业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同时,市场力量往往依附其他而垄断了局部的利益,如在物业公司势力强大的小区,业委会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制衡。因此,业委会很难获得与其他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权力和地位,其进行利益博弈面临诸多障碍。而且,管制思维仍然在社区治理中常常显现。在社会愈加多元化的今天,制度供给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专利,公众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往往会有参与公共生活、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需求,因此,当社会自发的自治秩序与国家主导的控制秩序发生冲突时,政府应该站在更加包容的立场上,思考自身社会治理政策的导向,并接纳更多的治理主体进入治理体系中。政府构建主要体现在基层政府对社会公正价值理念的遵从,服务型基层政府、多元与复合治理社区管理体制的建立以及公共管理者对公共精神的行政伦理价值恪守。
三、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路径
1. 体制改革:管理结构从科层控制到多元共治。城市社区的体制改革应首先解决职能过载且权力有限的问题。行政化是社区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管理服务的职能不断转移给社区,给人员、财力本就困窘的社区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社区居委会实际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在减少,权责不对等的问题凸显,其治理能力实际有限。行政化并未给社区带来更好的发展,反而影响社区治理的效果。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应推进多元治理的形成。基层自治,应通过党委、政府的引导建设社区的微政治系统,使政府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和机构能够针对社区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平等有效的民主协商和共同决策,从体制上理顺社区的职责,制定社区管理和发展的基本规则,确定各类事务的责任主体。党委政府应承担托底作用,逐步完成与社区居民和专业机构等主体的协商民主与共同决策过程,从解决社区发展中的问题出发确定符合社区实际的社区治理基本规则,强调社区治理的基本刚性规则、利益分配的柔性协调和相关事务的专业支持。随着民众的利益表达愿望越来越强烈,且希望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到与其生活相关的公共事务中,政府在主导基层治理的同时,要改变将自身置于治理体系核心的做法,真正实现与社会的平等互动;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和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使其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信任、规范以及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政府应为社区自身活力的激发和运作提供宽松的环境,只有社区的能力提高了,政府在社区实现其意图时,才可能得到积极回应。政府管理与服务受到资源供给、组织能力等方面的刚性约束,因而不能实时根据社会需求变迁来调整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与管理架构。由此,还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灵活性、自主性和专业治理能力,补充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不足。社区自治的实现,既需要完善的制度、合理的主体结构、顺畅的权力运行机制,更需要社区居民广泛、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主体之间要通过精细化的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等,形成功能整合、共同合作、相互监督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强化各个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形成相互衔接和相互呼应的联动,推进社会共同治理。
2. 机制调整:运行机制从单向管制到联动服务。
利益协调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应通过民主协商机制,使基层行动者的诉求得以表达、得到回应,矛盾和误解得以调处。基层社会各利益主体在协商过程中,通过对话、讨论、协商,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妥协、让步,获取共识,有效整合,进而走向合作。推动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持续地对居民进行民主训练和赋权增能,使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成为居民日常生活技能的一部分,使民主规则变成居民内心法则和外在生活习惯,从而使居民自治植根于社区居民心中。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建立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整合各个主体的职责,容纳到社区治理的统一平台中,做到职责明确、受理便捷、回应迅速,切实提高社区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各个主体都应整合进入社区的议事协调机制,通过议事协调机制解决社区发展中的问题,形成联合办公、联合处置的运行机制,建设社区精细化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
3. 工具创新:公共服务从粗放分散到“云服务”。从提升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精细化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借助于新兴网络工具和信息化技术,在促进政务管理信息技术进步的同时,构建广覆盖、智能化、即时性的社会治理“云服务”体系。以工具创新反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通过推动信息化、网络化平台建设,将涉及居民生产生活的相关公共事务聚合到社区“云服务”平台,与网格管理进行深度融合,使公共管理有责任主体,公共服务有平台,办理流程更加便捷,从而倒逼城市社区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
注:本文受江西省吉安市社会科学“十三五”(2016年)规划项目(编号16GH08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