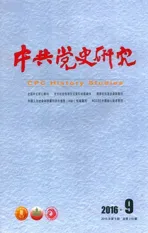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策略
2016-02-12王建伟
王 建 伟
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策略
王 建 伟
孙中山逝世前后,为应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权力斗争局面,中共一改先前对孙中山的多角度分析,专注于颂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努力构建其作为“左派”的鲜明形象,孙中山被解读为自始至终一直与帝国主义及国内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同时,中共发挥宣传工作方面的优势,积极与戴季陶等人争夺三民主义的权威阐释权。共产党人的这种集体行动有统一的安排与部署,对孙中山的各种评论也基本遵循了统一的语调与定位。根据一贯的宣传纪律,他们比较成功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宣传策略。这一时期,也是国共两党逐渐从党内合作走向分裂的阶段。两党之间的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接班人之争相互缠结、愈演愈烈,最终走向各执一端、不可收拾的局面。
孙中山;宣传工作;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
宣传工作是共产党人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中共创建初期,虽然党员数量与整体规模并不出众,但在宣传领域投入大量精力。这不仅与当时中共自身的处境相关,也与对开展革命方式的认识相关。如同中共中央1923年的一份文件所强调:“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第1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562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宣传工作甚至是中共证明自身组织存在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建党初期的许多重要党员都是宣传精英,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中共很重视并善于利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纪念日进行政治宣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在国民党内外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此前后,围绕这一事件,中共发起了一波集中的宣传攻势,不仅制定了明确的宣传主题,统一了宣传口径,而且布置了比较详细的实施步骤与具体的操作方法。既往一些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在论述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有待继续深入挖掘。*关于中共创建初期的宣传工作,学界多有涉及,代表性成果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杨天宏:《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陈红民、魏兵兵:《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金富军:《中共早期反帝理论与策略研究(1921—1925)》,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5年;陈佑慎:《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7年;杨会清:《“红五月运动”的兴起及其运作模式(1921—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吴永:《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话语的建构及其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卢毅:《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宣传工作比较》,《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本文拟选取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活动这一典型个案,希望借此检视中共创建初期的革命方式与策略问题。
一、中共创建初期对孙中山的基本态度
中共创建后不久,即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开始谋求与国民党的合作。随着两党交往日益频繁,共产党人与孙中山都在观察着对方。在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事件,中共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认识与评价不断变化,时好时坏,而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很复杂,甚至有前后矛盾的不同表述。
中共虽然建党时间不长,组织规模不大,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在党员心态上对国民党并不落下风,甚至还有一定的优越感。对于当时的老牌大党国民党,一些共产党人把其归入早已落伍的“辛亥一代”,对孙中山本人的认识也并不一致。中共一大就围绕这一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据与会代表陈公博回忆说,有的党员认为:“国民党的政纲中虽然显露出若干错误的观念,但它多少还代表着当时的新趋向,而孙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则,也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另一位与会代表包惠僧则指出:“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因为孙逸仙仅凭其煽动能力,根本拒绝群众于门外。”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孙逸仙的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对某些实际而进步的行动应加支持,惟不取党与党合作的方式。”*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97—98页。
因此,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陈独秀的主要依据是: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联合军阀,“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在广东省之外仍被视为“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32页。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大多数党员都把国民党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当时的认识是,加入国民党,就意味着共产党退化。*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88页。从上述内容可以判定,早期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观感应以负面为主。*1926年底,陈独秀在中央特别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当时党内同志的“左”稚现象,第一个表现就是“看不起国民党”,并且认为这是一种“传统思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62页。
不过,在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下,作为下级的中共仍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民党等革命党派,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当中共确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后,对孙中山的评价也相应发生改变。考察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相关言论可以发现,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贯穿其间:孙中山已逐渐改变从前只专注于军事斗争的行为,开始注重联合民众;国民党虽仍有许多缺点,但正慢慢改正,是“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力量。一个典型例证是,当1922年8月陈炯明驱逐孙中山时,胡适认为前者的行为是“一种革命”,是要“造就模范的新广东”,不能用“悖主”“犯上”“叛逆”等“封建时代的贵族的旧道德观念”来评判,而后者固执于北伐,属于“倒行逆施”*参见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胡适:《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努力》第12期,1922年7月23日。。此时,李大钊作为朋友专门致信胡适,告知:“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5),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李大钊的这种认识应该和他与孙中山在上海会面的结果有直接的关系。孙中山在陈炯明发动兵变后,于8月14日离开广州抵达上海,陈独秀、李大钊曾分别前往拜访。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会见是融洽的。李大钊后来曾在《狱中自述》中描述:“先生(指孙中山——引者注)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文集》(5),第438页。几天后,在国民党元老张继的介绍下,由孙中山亲自主持,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来,陈独秀也致信蒋梦麟、胡适,再次提及:“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0页。与此同时,蔡和森也在《向导》上提醒福建民众:“切不要把国民党的武力与军阀式的武力视同一律”*蔡和森:《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2日。。
1923年4月,瞿秋白再次延续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孙中山这一时期的评价,指称:孙中山“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瞿秋白:《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陈独秀也在此时表示:“孙中山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是为民主革命向北洋军阀奋斗而存在的”,“代表民主革命的新势力。”*独秀:《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李大钊则在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和“中国革命的老祖”;国民党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如果对其进行适当改良,仍可以担负改造中国的使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4),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通过机关报《向导》的报道表明:在青年学生中,孙中山的形象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向导》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称:“年来国中的青年和觉悟的知识阶级,也觉得把旁观的态度——视孙先生是一般的政客军阀,视救国的奋斗为争地盘的把戏——开始抛弃;渐渐地回转头来,倾向于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曾国光:《国民党领袖与教育事业》,《向导》第27期,1923年5月30日。
国共合作动议酝酿之初,中共虽然认同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承认只有国民党才能担此重任,但基于组织独立原则,从未把孙中山认同为自身的“领袖”,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批评。只是从维护两党关系的角度出发,批评的尺度时紧时松,批评的口径基本保持一致,批评指向的焦点也相对集中,主要着眼于国民党“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等方面。*参见李永春《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自由批评问题述略》,《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不过,中共的批评不仅未能“纠正”孙中山的行为,反而引发后者强烈的反击,并继续谋求与奉系、皖系等军事势力的联合。李大钊对此颇显无奈地表示:“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对那些只顾私利私欲的军阀、政客,我们比什么都憎恨。”*《李大钊文集》(4),第327—328页。同一时期,苏俄方面也对正在访俄的孙逸仙代表团表示:国民党应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工作上来;“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40 页。。维经斯基认为:孙中山即使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也未能使他在已控制的区域内巩固起来。孙中山政府在民众中没有生根,他的军队不是由懂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中国劳动大众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马林则评价道:孙中山“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页。。此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稍显紧张,国民党改组工作也几乎陷于停顿。
1923年7月,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共合作的马林带着失望的情绪离开中国,随后而来的鲍罗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实现了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有效沟通,并促使前者重新启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鲍罗廷取得的工作成绩也与其带来的苏俄援助有密切关系。陈独秀曾描述说:“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民国13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参见《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鲍罗廷被孙中山委以重任,成为国民党的组织训练员,后来又被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顾问。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正式宣告改组。由此开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正式确立,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日益明确。从中共的视角加以考察,国民党一大的结果可谓“圆满”。会议结束之后,中共立即形成一份中央文件,对于日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作出具体的指导与规定。这份文件总体上比较低调,主要是要求自己的同志在国民党内努力工作,尽职尽责,遵守纪律。*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22—225页。
不过,形势并未完全按照中共的预设方向发展。国民党一大之后,随着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工作的介入日益加深,两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党内合作”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也面临着一些无法破解的悖论与难题。中共基于“组织独立”与“批评自由”的原则,秘密在国民党中发展党团组织,并且持续对孙中山及国民党进行批评,这些也导致一些共产党人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参见杨天宏:《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对“共产党员跨党”政策有分歧,导致党内分化进一步加剧。孙中山对此虽极力协调,使国共关系形成制约与反制约,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民党内排斥共产党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中共谋求自身发展的愿望也越发明确和迫切,甚至开始试图控制国民党。随着1925年3月孙中山离世,国共两党原本脆弱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双方开始直接交锋。
二、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对其“左派”形象的塑造与颂扬
作为长期的、唯一的领袖,孙中山的离世使国民党骤失重心,留下的权威真空一时无人能够填补,党内因推行“联俄”和“容共”政策所导致的分化趋势逐渐加剧。在国共关系方面,因失去孙中山这一重要的制衡因素,两党矛盾进一步扩大。面对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日益严峻的威胁,中共开始强化自身在国民党内的“存在感”与“独立性”,而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宣传领域构建孙中山的“左派”身份,颂扬孙中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同时,通过对三民主义权威阐释权的争夺,确立自身作为孙中山革命遗志继承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而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抢占先机。
孙中山的逝世为中共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践机会。在得知孙中山病危已无可挽救的消息后,中共于1925年2月5日发布通告,对于孙中山去世后的宣传工作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如要求各地支部临时组织追悼孙中山的委员会,筹备并指挥一切组织与宣传事宜。在宣传内容上,则要求强调孙中山“自始即有反对帝国主义之思想与行动”,“自始即根本反对封建制度”,重点宣传其“始终反对军阀”,“主张根本废除军阀制度”。此外,还提出了宣传三民主义的明确策略和一些宣传的普通口号。*《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第1册,第624—626页。随后,一场指向明确、特征明显的宣传活动在中共中央的统一组织下推展开来。
孙中山逝世3天后,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同时发表《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和《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致唁中国国民党》两个宣言。总体而言,两份文件属吊唁、慰问性质,实质性内容不多,但归纳起来,仍然表达了几点态度:第一,孙中山的逝世对于中国民族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促起中国民族运动的事实仍然存在,中国的民族革命绝不会随着他的离世而终止。第二,孙中山虽然逝世,但国民党仍然应该遵守他的遗嘱,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的斗争。第三,中共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有力”,“今后的国民党必然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这种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第四,中共表示,“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1925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1925年3月15日),《向导》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
与当时国内各界对孙中山的多重认识不同*参见郭辉:《“盖棺论定,尚有待于千载下焉”——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反应》,《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也与以往自身对孙中山的解读不同,中共此时对其基本上全是正面肯定态度,如称赞其一直坚持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坚持反军阀态度,主张废除不平的条约等。与此同时,中共报刊也开始极力塑造孙中山的“左派”形象。
中共对国民党内成员进行左、右划分,始于国共合作政策酝酿之初,主要是受苏俄及共产国际影响,并在实践过程中多有发挥。*相关研究参见杨天宏:《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最初,为了争取国民党人的信任和维护“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中共采取了稳健、谨慎的态度,很少公开提及,有意淡化国民党内的左、右之分。国民党一大以后,两党合作进展得并不顺畅,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内反共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日益加深,中共遂逐渐有意识地主动构建国民党内的左派与右派区分,从而为自身争取盟友,打击敌手。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孙中山被中共认定为“左派”。会议指出:“国民党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页。这次会议期间的《中央局报告》也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关系,孙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数左倾分子(国民党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尚有意联络我们;其余大部分右倾即不主张和国际帝国主义反抗的分子,则极力明白〔的〕或暗的排挤我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3页。
由于孙中山并不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组织,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开展工作。但是,中共基于“组织独立”的原则,一直告诫自己的党员,要时刻注意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就开始在一些国民党组织中建立自身的党团。为此,1924年六七月间,上海、广州等地的部分国民党人提出弹劾案,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检举共产党人“违纪”,反对共产党人“跨党”,要求共产党“分立”。
面对这一危机,孙中山虽有压制,但并未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共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他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1924年7月,陈独秀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判断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此时,他已经修改了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提法,认为:“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过是左翼理论家)”。因此,他建议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不久之后,他还在另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建议:共产国际应提醒鲍罗廷,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容易进入其圈套。*《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4—85、119页。此时,孙中山是被他划归到“中派”行列。
陈独秀的这种定位也代表了中共的态度。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其间发表了一系列宣言。但在中共看来,“此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辞含混,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01页。。此时,中共仍将孙中山描述为“中派”。但“中派”既可以偏左,也可以向右,表明中共对孙中山的定位具有模糊性。在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上,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孙中山的名字,但仍批评了国民党“中派”的“游移”。会议指出:“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右派之间,操纵取利。”为此,中共认为应采取新的工作方针:“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8—339页。
从最初尽力避免国民党内的左、右之分,到尽力扩大国民党左派势力,联合中派向右派进攻,这种斗争方针的变化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处境密切相关。在孙中山推行“容共”政策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分党员、尤其是一些老党员对此非议颇多,并屡起风波。孙中山以其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对此进行压制,同时也进行安抚。但是,国民党内由此引发的分歧一直没有彻底根除,反而随着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工作介入的逐渐加深,双方的对立也日益强化,呈愈演愈烈状态。而一直扮演居间调停角色的孙中山在进入1925年后病情恶化,必然导致其对国民党控制力的明显下降,也对国共关系产生连带影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孙中山逝世之后留下的权威真空引起鲍罗廷与中共的重视。鲍罗廷认为:这是清除国民党右派,由左派掌握权力的最好时机。中共中央也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公开征求党员,借机扩充左派数量,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日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和右派竞争选举”,同时还须加紧宣传“民族争斗虽然重要而不能代替阶级争斗的理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4页。。
为扩充左派力量,中共在宣传领域开始有意识地重新构建孙中山的“左派”身份。1925年5月,蔡和森在《向导》上提出了国民党左派需要具备的四个必要条件:1.彻底的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军阀,买办阶级;2.恪守中山先生引导中国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俄携手的方针;3.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绝;4.遵行保护革命中坚势力的工农群众利益之政纲。他还指出这四点也是“中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并特意强调国民党的“左化”并非是“同化于共产派”,而是真正“同化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中山主义”。*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由此,蔡和森建立起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的对应关系,而孙中山重新被归入左派行列。
此时,中共和共产国际开始重点宣传孙中山晚年某些较为左倾的言论,如针对1924年海关关余问题、沙面罢工事件和商团事件所发表的反帝宣言,以及北上过程中主张废除军阀制度的表态。这些宣传意在突出孙中山的“左派”形象,充分肯定其在中国民族革命进程中的伟大地位,将其塑造为坚定的“左派主义者”。北方区委领导人赵世炎描述说:孙中山“每闻善后会议四个字必起盛怒,盖以此为安福系阻碍真正国民会议的实现之恶谋也。中山病到垂死,而其政治观察仍异常清楚,其反对帝国主义和联络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完成中国革命的信念持之益坚”*罗敬:《中山去世之前后》,《向导》第108期,1925年3月28日。。《向导》上署名为“双林”的作者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最早领袖”,“代表平民阶级而奋斗”*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镇压买办季节商团之反革命》,《向导》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蔡和森评价说: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标识”!*和森:《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向导》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季诺维也夫则称赞孙中山的倾向一直是向上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指出:“他(指孙中山——引者注)能鼓起党员的勇气去和这种帝国主义所雇用的反革命军奋斗;他能消散自己党内的游移不定的主张。他挽救了国民党过去的光荣,表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进行已经到了怎样的高潮。”*季诺维埃夫:《孙逸仙之死》,《向导》第110期,1925年4月12日。
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身份被确立后,中共对于国民党“右派”的界定也进一步简单化与宽泛化。诸多与孙中山思想以及主张不一致的行为,都被中共归为“右派”的行列。不仅如此,1925年底,陈独秀还对国民党内的左、右之争作了更早的追溯。他认为:“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由此可见,国民党早期内部出现的孙中山与黄兴的分歧、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分歧都被陈独秀一概归纳为左、右之争。
1926年,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之际,中共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在批驳冯自由和西山会议派右派思想的同时,再次指明了国民党内存在的左、右分裂。该通告指出:在国民党内,“一派企图向左结合无产阶级,一派企图向右结合资产阶级。企图结合无产阶级,遂不得不采用容纳共产派联俄拥护工农利益等革命政策,企图结合资产阶级,遂不得不修正联共联俄政策及提出阶级调和的口号”*《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1926年3月12日),《向导》第146期,1926年3月17日。。此时,中共区分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标准不仅更加具体,并且已经出现后来被广为熟知的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初步提法。
1926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国民党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的问题回答说:“我们可以肯定说是有的”,左派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26页。。在12月上旬召开的汉口特别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以拥护还是反对三大政策作为区分左右派的标准:“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73页。。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中,“三大政策”成为中共区分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而孙中山的“左派”身份已经确定无疑。
在努力塑造孙中山“左派”形象的同时,中共还组织党员对其一生的功绩进行提炼与总结,这与之前对其所持的批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孙中山逝世当天,李大钊就指出:孙中山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的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李大钊还指出:孙中山的功绩包括“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214页。
两天之后,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从八个方面概括了孙中山的革命贡献:始终为民族独立奋斗;注重人民生计问题;有建设中国的计划;主张造党治国;努力于宣传工作;主张革命政府独裁;联合国内外革命势力;富于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参见恽代英:《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中国青年》第71期,1925年3月14日。。他还赞扬说:孙中山的“思想是很高尚的”,“感情是很浓厚的”,“他是革命的,进取的,他是不怕一切困难,不丝毫犹豫疑虑,他用革命手段来达到他的理想的。他用各种最进步的方法来实现他的平等的理想”*《恽代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48—749页。。瞿秋白也指出:孙中山的重要功绩就是在他的引导下,中国的民族革命已经得到了正当的道路,“因为要反抗列强,然后知道非颠覆满清政府不可,非建立共和不可,非为大多数中国平民争生活之改善不可;最后非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被压迫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和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新青年》第2号,1925年6月1日。。
从此时中共对孙中山的评价来看,以往对后者的诸多批评几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斗争精神的高度赞颂。在中共的刻画中,孙中山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冲击旧有不平等社会秩序的、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阐释与构建,孙中山被认为与中共同处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阵营。此时,中共极力维护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形象,主旨在于强调国共合作的正当性以及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三、从“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
前面已经提及,在中共建党之初,许多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已陷入“老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此,他们不仅对国民党采取排斥态度,对三民主义本身,也无太大兴趣。如恽代英在1923年所言:“我对于三民主义,以前亦是与许多人一样的忽视。”*但一:《论三民主义》,《新建设》1923 年第 1 期。邓中夏在1924年1月发表的《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也仅仅是把“三民主义的政治家”作为唯物史观可以联合的友军之一,并未给予特殊对待;而其他友军还包括“行为派的心理学家”“社会化的文学家”“平民主义的教育家”和胡适的实验主义*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
孙中山去世后,中共掀起一波纪念孙中山的宣传攻势。作为孙中山一生思想的集中总结,三民主义在中共理论宣传话语体系中的位置与重要性也进一步上升。另外,共产党人还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基于自身阶级立场的解读。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民族主义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对外条约,要求中华民族独立为原则。民权主义以根本打倒障碍民权之军阀,建设民主政府,要求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之绝对自由为原则。民生主义以铲除目前妨碍民生之帝国主义与军阀,再以真正人民的国家力量发展农业厚利民生为原则。总之,宣传中山的主义切不可蹈于空空理论,须举出具体的事实,尤其须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第1册,第625页。
孙中山曾有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冲突的表述,但在共产党人看来,问题显然不是如此简单。虽然在具体对外宣传的过程中,中共有时也将共产主义等同于三民主义,并进一步简化为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但在中共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据包惠僧回忆,北方区委负责人赵世炎就曾表示:“对外,对国民党做工作,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内部是不能这样说的,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孙中山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共产主义,他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而我们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共产党员必须划清这个界限,坚定自己的立场。”*包惠僧:《赵世炎生平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第109页。正如蔡和森所言,“中山主义与共产主义显然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标帜”*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恽代英虽然表示“列宁和孙先生可以并称”,但更强调孙中山的学说“不能纯粹的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恽代英文集》(下),第750—751页。。由上可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中共的阐释策略是:承认两者的区别,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两者目标一致,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具有理论基础。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无人能够填补其留下的权威真空,“总理”这一称谓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专属,再未被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所使用。国民党中央多次明确表示:三民主义及总理遗嘱是确立无疑的最高指导思想。192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则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宣言》以及《关于接受总理遗嘱之训令决议案》。前者指出:“总理伟大之精神、主义、遗嘱之信心,如日之明朗照吾人革命胜利之前途”,“吾党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即或有对于总理之主张发生怀疑者,迟早必发现总理主张之正确与自己怀疑之错误”。后者也表示:“总理虽没,总理之一切遗教仍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存留于世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1、114、116页。1926年三二○事件发生时,孙中山去世已超过一年,但蒋介石仍公开表态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74页。陈独秀也对此表示认同,认为:孙中山永远是国民党“理论上的领袖”与“精神上的领袖”。*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1926年6月4日),《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总理遗嘱简短而明确,而三民主义则复杂得多。如孙中山在1923年所言:“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60页。国民党一大虽然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但有研究者指出:维经斯基在1923年11月起草并经共产国际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就对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发挥了非常关键的影响。对照两个文本可以发现:二者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解释相似性很高,有些地方只是因为翻译的不同而已。*杨奎松认为,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全面套用了共产国际1923年11月28日决议的主要内容”,此处的决议就是维经斯基起草的。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3页。相关详细考证还可见周利生:《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第59—68页。当时,孙中山基于多种考虑,并未对苏俄的这种介入表示过多异议。不过,之后孙中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十几次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其中一些内容并未完全遵照国民党一大的相关解释。*黄彦认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作为一个联合阵线的纲领性文件,对三民主义的解读具有权威性,但并非百分之百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并不完全代表孙的观点。从了解和研究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角度来衡量,他本人解释三民主义的演讲、著作则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参见黄彦:《关于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这种前后的不一致性对后来关于三民主义解释的多元化埋下了伏笔。
由于孙中山骤然离世,国民党内不仅一时没有众望所归的继承者,而且在思想理论上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此时,素有理论家之称的戴季陶首先站了出来。
戴季陶认为:国民党一方面由于旧日同志“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加入后“扩张发展”,导致党的基本政策“含混不清”,“组织则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重理论之困难”。要想挽救国民党,首要任务就是“决定一根本方针”,“此方针为何,则以总理之思想与主张之全部,为本党不易之信仰是也”。*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3—614页。他认为:如果曲解三民主义,任由对孙中山的学说各说各话,就会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后来,他在《青年之路》一文中也曾表示:“我们如果不能够战胜这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单把共产党徒捣乱的势力压伏了下去,我们的胜利,是不能保持的,而且这一胜利是虚假的。战胜武力要靠武力,战胜宗教要靠信仰,战胜美术要靠美术,战胜科学的制造要靠科学的制造,战胜革命的主义只有靠革命的主义。”*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3年,第172页。基于以上想法,他于1925年6月完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该书的核心内容为:民生哲学是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602页。。7月,他又刊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强调三民主义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与“支配性”,认为国民党内包含一个共产党,结果自然会使自己变得畸形且危险*《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第86页。。戴季陶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遂成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系统探讨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起点。
戴季陶的观点抛出后,立刻陷入中共方面的文字围剿,成为众矢之的。向导周报社专门刊发《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文,表示要揭露戴季陶“三民主义真信徒”的假面目。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还发表文章,对戴季陶提出忠告:三民主义是中国对封建社会剧烈的工业化的时代应有的思想界的产物,不应把其当作孔家哲学的复活而丧失原来面目,不应将中山先生当作复古的巨子。文章指出:戴季陶因急于要做“新子思”,“不惜把孙先生装头换面戴上孔老二的奴隶哲学的冠冕,活活的把终身从事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山先生,脱去洋服,抽长头发,弄成一个如像孔老二的古道士”。文章还提醒戴季陶:要对国内革命势力的分野看得清楚一点,“不要不自觉的供给反革命者以理论上的依据”。*砍石:《戴季陶心劳日拙!》,《政治生活》第47期,1925年8月19日。另据作过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朱其华回忆,当时还出现过这样一幅漫画:一面画着一个“世界公园”,公园里陈列着三个座位,中间是马克思的像,左边是列宁的像,右边的座位空着。另一面画着一个孔庙。在“世界公园”与孔庙之间,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子背着孙中山的像往孔庙走去。旁边写着“孙中山应该陈列于革命的世界公园中,但戴××一定要把他背到孔庙里去”*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的回忆》,新新书局,1933年,第45页。《政治生活》第62期(1925年12月30日)也刊登了此幅漫画。。《政治生活》则称戴季陶为“孙中山主义的考茨基”*《孙中山主义的考茨基》,《政治生活》第55期,1925年10月21日。列宁曾把考茨基称为“头号的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把戴季陶比喻为考茨基,在当时语境下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中国青年》也称戴季陶主义“为中山主义之大敌”*昌群:《反中山主义的反赤运动之过去及现在》,《中国青年》第158期,1927年3月12日。。
中共领导人此时也纷纷发表批判文章。瞿秋白批驳说:戴季陶鼓吹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之宣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施存统认为:戴季陶的思想与主张,将会被全国反共分子利用做他们行动的“护符”,“孙文主义变成了反共产主义,平时不要三民主义,到了要反对共产派,不能不用三民主义,你亦说三民主义,我亦说三民主义,只要拿了三民主义的大帽子便可以把共产派打伏下去,再用不着什么别的理由,这时孙文主义不但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并且会做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工具”*施存统:《评戴季陶先生的中国革命观》,《中国青年》第91、92期合刊,1925年9月1日。。陈独秀也把戴季陶划入“新右派”行列,指出:其只是“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他们虽然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可是不会为革命流一滴血,不会为革命坐一次牢监,并且不曾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举行过一次示威运动,散过一次传单”,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中共愈发认识到争夺三民主义解释权的重要性。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通告中提出:“和国民党右派的争斗,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思想。解释三民主义时,不可多涉理论,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更进一步非到共产社会,民生主义不能算完满成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25—526页。
中共对三民主义的积极阐释招致了国民党右派的大力攻击,尤其以西山会议派为甚。他们指责称:共产党人在加入国民党后,“只专意为共产主义发挥,事事效忠于苏俄,不但将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放在脑后,反利用中国国民党的招牌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务使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闹成一个皂白不分,并且欲把中国国民党也变为苏俄的附属团体”*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387—388页。。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非难,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明确要求:要将孙中山逝世日变成“国民革命最广大的宣传日”和“革命势力的检阅日”。为此专门制定的宣传大纲则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号召说:“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要在中国国民党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之下遵从孙中山先生一切主义和政纲(如联俄集中革命势力,如容纳共产分子等)并以革命精神切实执行”。大纲还指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建国大纲,商团事件宣言,北伐、北上诸宣言,遗嘱和致苏俄书,应为宣传主要材料”;“应极力宣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宣言和一切文件,并宣传广州政府的最近状况”;“在这一日并可要求广州民党中央惩办中山先生叛徒——西山会议诸人及上海伪中央分子”。*《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第1册,第697—698页。1926年11月,中共再次就宣传问题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280页。。通过以上一系列阐释,国民党内反对“容共”政策的派别被中共划入“孙文主义的叛徒”行列。
在革命阵营内左右派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1926年4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这是一份涉及当时国内外各方形势的综合性提案,其中建议:“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于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态度及行动”。但同时还提出:“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显然,蒋介石并不认为共产党人是三民主义者。*《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5—556页。
虽有来自国民党右派的非难及蒋介石的逼迫,但应该说,通过对孙中山思想及其学说的再诠释,中共建构了符合自身阶级基础的话语体系。这样一来,本来作为国民党立党理论之基的三民主义似乎成了共产党人的专利,而国民党内不仅在组织上陷入四分五裂,在理论上亦无法统一,以至于胡汉民在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还指斥说:多半国民党同志“对于总理只有绝对的敬仰,没有绝对的信仰;对于主义也只有口头上的赞许,没有真心的笃信”*胡汉民:《清党之意义》,《中央》第2期,1927年4月。。在同一时期,谢持、邹鲁等人宣称共产党具有破坏国民党、破坏国家、破坏社会的“三大罪状”,其中提及:“其对于主义也,既借口民族自觉、世界革命,以破坏民族主义;借口无产专制,以破坏民权主义;借口阶级战争,以破坏民生主义。复谓阶级战争为三民主义之基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即本党之主义;更谓只问革命,不问主义。离奇怪诞,故与总理三民主义演讲违背。至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一语,自由真谛。彼辈忽而利用,谓民生主义即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忽而仇视,谓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迨总理逝世,彼辈阳为追悼,阴行庆祝,进而加马克思、列宁(遗像于总理)遗像之上”。*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479页。中共是否曾“加马克思、列宁(遗像于总理)遗像之上”?此问题有多种说法。但这表明:三民主义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正当性的权威符号,仍然是20年代国民革命进程中多方竞逐标举的政治旗帜。
不仅中共有着基于自身立场的对三民主义的解读,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对三民主义的不同阐释。除了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外,还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等,也对三民主义“各取所取”。1928年,施存统在新创办的《革命评论》上感叹说:“三民主义本来只有一个,然而现在事实上,因解释底不同,好像有好多个”。虽然大家都说信仰三民主义,但具体的解释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维经斯基也观察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含混不清,自相矛盾……各阶层人民在孙中山思想中添进了自己的内容。”*《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65页。三民主义解释的多元化不仅影响了其权威性,导致国民党内指导思想的混乱,也助长了其内部分裂情势的进一步扩大。由此,三民主义也在各派的曲解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性与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无法成为严密的意识形态。
一种理论可以被不断阐释,这也是其永葆活力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三民主义而言,创建者的离世为后来者的解读提供了宽广的解释空间。同时,三民主义自身的模糊性导致了对其解释的多样性。此外,孙中山逝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得对三民主义的解读附着了更多纯正理论探讨之外的政治背景,各种场外因素的叠加决定了各方对三民主义阐释权的争夺不可能是一场单纯的学理论争。在纸面上的论战背后,正是势不两立的现实斗争。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在异常严峻的斗争形势中,中共大部分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宣传工作亦受到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共对于国民党的认识与定位发生大幅度的转向。由此连带,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态度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问题将在另文中论及。
余 论
孙中山在世时,其本身的思想、主张以及具体行为呈现出非常复杂、多面,甚至矛盾的个性。鲍罗廷对此观察指出:“在他(指孙中山——引者注)身上,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样,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33页。中共对孙中山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在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情况,有正反两面的不同评价。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孙中山”这个名称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虽然不能忽视,但尚未达到“凸显”的程度。
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后,中共对其个人经历的解读及其思想层面的阐释进入一个高峰期,“孙中山”逐渐脱离作为个体层面的“个人”,而上升为一种带有明显象征意义的“符号”。在整个中国社会对孙中山逝世的相关评论中,中共显得独树一帜。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基本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撰写了相关文章,不仅主题集中、观点鲜明,而且文章的论辩模式、阐述方式也遵循基本相同的逻辑思路。再结合此时共产党人对“反帝”“民族革命”“世界革命”“阶级斗争”等问题的论述,建党初期的中共借此也初步构建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关于孙中山逝世的宣传是中共早期宣传史上的重要事件,比较充分地展现出当时中共的整体宣传实力,更体现出早期中共作为一个年轻政党的基本运作模式。在孙中山逝世所留下的权威真空中,共产党人,苏俄代表以及国民党的内部派别都参与了这场斗争。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可以说中共一度明显占据上风。
中共建党初期的宣传工作不是坐而论道,不只是纸面上的辩论,而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斗争性。在不掌握独立武装力量的情况下,“笔”成为中共依赖的重要武器。然而,无论如何,“笔”永远无法真正抗衡“枪”的威力,宣传层面的胜利毕竟不能取代现实斗争的胜利。当对手将“枪”投入战场后,“笔”的脆弱性立即充分显现,有时甚至不堪一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宣传工作始终是外在的。对于中共而言,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后,也必然走上“笔”与“枪”共用的道路。
(本文作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 王志刚)
The Publicity Strategy of the CPC Before and after Sun Yat-sen’s Death
Wang Jianwei
Befor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Sun Yat-sen,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KMT, the CPC changed the previous multi-angle analysis on Sun Yat-sen, and started to focus on celebrating Sun’s “revolution” spirit, trying to build it as a vivid image of the “leftist”. Therefore, Sun was interpreted as a hero who always struggled with imperialism and domestic reactionary forces from first to last.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played the advantages of positive publicity, and competed with Dai Jitao etc. to struggle for the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right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This kind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PC has the unified arrangement and deployment, and all comments on Sun also follows the unified tone and ori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usual propaganda discipline, they successfully implement the central propaganda strateg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KMT gradually went from the inner-party cooperation to the split,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fractions struggle and succession struggle within the KMT, intertwined, and intensified, which eventually got out of hand.
D231;K26
A
1003-3815(2016)-09-006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