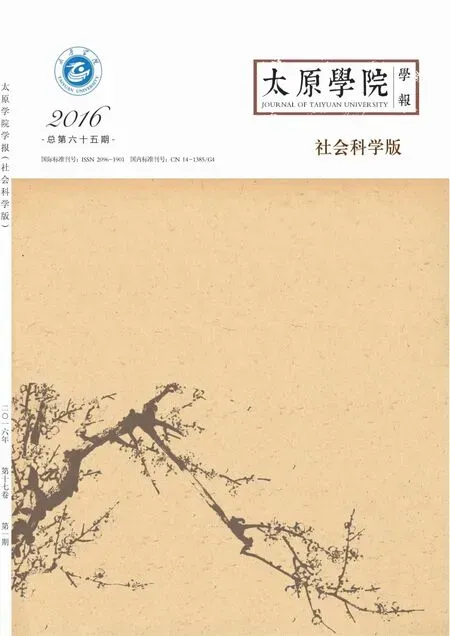沙石小说论
2016-02-10赵海涛
赵 海 涛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沙石小说论
赵 海 涛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探索人性,坚守良知与道义,描述灵魂的挣扎,是沙石小说最大的特点。语言不够简练,人物刻画较为平面,立意与思想没有向深挺进,是沙石小说严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沙石;小说;《玻璃房子》;《情徒》;人性
沙石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人作家之一,自登上文坛以来,其小说受到很多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现已出版长篇小说《情徒: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故事》、中短篇小说集《玻璃房子》等作品。注重人心的探索与人性的挖掘,触摸人生的虚无与揭示存在的荒诞,坚守良知的温存与道义的底线,在欲望与灵魂的挣扎中寻觅身份的认同与心灵的归宿,是沙石小说最大的特点,也是沙石小说最具动人之处。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碰撞,身处他国异乡的孤独与焦虑,对欲望的疯狂追逐及因之而产生的灼热煎熬,生存中所具有的难言之痛与苦难流浪,荒诞与虚无对生命与灵魂的双重压抑,都迫使沙石在文学创作上不停地向存在之维及其内核挺近。沙石小说不能简单地以移民文学视之,虽然他的小说具有移民小说的某些特质与共性,但是对人性与人心的探索、对良知与灵魂的追问、对存在与生命的刻画都使其小说呈现出一种深邃的意蕴与悠远的境界,这意蕴与境界正是一种好的文学在面对生存与灵魂时所应有的职责与操守。沙石小说也有一些问题:首先是小说中汉语言运用得不够娴熟与精炼,在行文时多有拖拉芜杂;其次是人物的刻画比较平面,有些还停留在二元对立的阶段,人物的心理及其进展有时不能与情节的推进形成很好的呼应;再次,有些小说的立意与思想没有能更进一步,导致小说呈现出一种较为浅肤的面貌,这大概与沙石久居国外,对当代中国文学及其高度与成就没有足够的关注有关。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沙石小说的艺术水准,降低了沙石小说的文学艺术成就。
一
沙石小说一向注重对人心的探索与人性的挖掘,这是其小说一贯的特色。尤其是在当下消费主义与娱乐至上对个人及其心性的极致挑拨与过度离间所导致的良知迷失与灵魂飘荡的时代大环境之下,对人心与人性的审视与理解就更应该成为文学所最应该关注的焦点之一。沙石小说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审视与理解。
《玻璃房子》讲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美国花匠阿德与当地白人贵妇伊莉莎之间的离奇故事。旧金山金门公园的一棵铁树在阿德的精心照料之下开出了难见的花朵,阿德与铁树一起作为新闻登上了报纸。伊莉莎的丈夫彼得森是一位心理医生,为了职称他日夜不停地赶论文,因此忽略了妻子。当自己的合理欲望与要求被丈夫拒绝后,伊莉莎心情极为郁闷,不经意间她在报纸上看见了一个中国花匠,便产生寻找刺激与发泄欲望的念头。她以修理花园的名义将阿德召回家中,随后便对阿德极尽诱惑,阿德在火烧火燎之际,说出想到伊莉莎的床上去的要求,伊莉莎却说:“那床是我和我丈夫睡觉的地方,我不能让你这样的人把它弄脏。”[1]13阿德瞬间明白了,在伊莉莎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卑贱低级的肮脏玩偶与任意摆弄的幼稚工具,她根本没有将他当做一个人,阿德毅然地拒绝了伊莉莎。伊莉莎没有想到阿德竟然如此有骨气,气愤之余便偷偷地将阿德照料的铁树损坏以示报复。人性在欲望的驱使之下所具有的张力与限度在此得以很好的表现。《汤姆大叔的剃刀》更具代表性,汤姆与妻子安娜及三岁的女儿米雪儿在去安娜父母家度假的路上遭遇飓风暴雨,安娜不幸遇难,自此汤姆将所有的爱都用在女儿身上。女儿越长越像母亲,汤姆对女儿的爱也越来越霸道不正常,他不能忍受任何别的男子与女儿亲近。女儿婚后,他对女婿阿布尔罕极其不喜欢,尤其是不小心看见女婿身上乱糟糟的体毛时,他更加难忍了。他用安眠药将女儿女婿晕倒后,不仅将女婿身上的毛发剃除,同时将女婿用来欺负米雪儿的生殖器割掉,在割掉的那一刻,他满心欢喜。这篇小说极其惊心动魄,人性中自私变态的一面不仅以爱之名干涉至爱之人的幸福,而且还妄加戕贼他人生存的权利与幸福。《亡命岛》中,托马斯与凯瑟琳本想假借出海之名偷情窃欢,没想到快艇骤遇意外,二人流落到亡命岛上。在生存遭到威胁之时,二人各为自保所表现出的种种,使人性中所隐藏的丑陋与贪婪昭然若揭。《窗帘后面的考夫曼太太》中,考夫曼太太宁愿与她豢养的黄犬乔治相爱,也不愿意接受风度翩翩的罗伯特绅士,这不禁使人们想问:人,究竟是怎么了?人,为什么宁愿与狗相爱也不愿接受作为同类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排斥与隔阂,怎么会到达如此地步?人,还有救吗?人,还有活着的希望与勇气吗?人活着,还有价值与意义吗?《冰冷的太阳》中,因中美两国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夫妻冲突及薄情离散、父子冲突及父子伦理的变异,也对人性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探索与刻画。《华嫂,二子和我》中,在憨厚朴实的邻居二子介绍下,“我”结识了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做过知青的赤脚医生华嫂,她精湛的医术与出众的外表,让“我”对她渴慕不已,可她却已是有夫之妇并且极为恪守本分。在长时间的交往中,“我”与华嫂、二子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出国留学,将二子拜托给华嫂照顾。没想到将近二十年后,“我”在美国竟然又遇到了华嫂。此时的华嫂已是一个极为成功的商人,在金钱与利益的驱使之下,她变得唯利是图,不再有曾经的清纯与温情。在华嫂的豪宅相见时,“我”不仅亲眼目睹了华嫂的绝情,而且还受到华嫂的情欲挑拨与诱惑。在交谈深入时,华嫂讲述了二子的遭遇:在国内时她将二子安排在自己的公司,可二子看不惯华嫂及其公司的徇私枉法与贿赂舞弊并将公司的情况向有关部门举报,华嫂在气愤之际让华哥领人将二子痛打一顿,结果造成了二子的伤残,二子现在只能靠在街边摆摊维持生计了。后来“我”再次回国时,看见满头白发极尽沧桑的二子在机场大厅接“我”,“我”顿时泪流满面。一面是一个清纯美好的女子,在金钱利欲的腐蚀之下,逐渐变得世故与流俗,一面是一个虽然智商不高的弱者,但却能在物质诱惑之下不为所动,并能恪守良知与道义,人性的恶劣与美好、人心的变与不变,在这里得以极好的对比与展现。《情徒: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故事》中,王大宝为了自己的理想与欲望,首先与黑人女佣冈布娜假结婚换取美国绿卡,再为成名而将自己的人格与灵魂出卖,再因为他人捉刀代笔而受到欺骗与伤害,种种事件都写出了人心的虚伪与浮躁,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爱与怕、恨与悲。
可以说,沙石在运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向人心与人性的探索与挖掘上的做法是成功的,他窥察到了人作为一个存在所具有的某些特质与情状,并能在良知与良心的光芒之下将这些特质与情状进行审照,在审照之余,他也加入了自己的爱恨情愁,这是他的小说之所以会别具性情与特色的一个原因所在。
二
触摸人生的虚无与揭示存在的荒诞,是沙石小说的另一大特色,这也是当代文学在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而产生的独特关注。存在的虚无、幻化与无意义,生命的无聊、空虚与压抑,无尽的欲望在不断纷飞之中而又空无着落,生活工作的机械劳累而导致身体的无所可归,受苦受难的灵魂在不知所措中尽展活着的无尽悲情,这一切都共同昭示着人生的荒诞与荒谬。没有意义与方向的人生,使活着与活着的人都变得极为可笑可悲,终身役役而不知其所求,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人生之大悲与大哀尽在于是。
《人鲨之间》中,一个游泳健将想用沉海的方式结束自己无聊的人生,可每当他将要成功之时,体内的求生本能就会主动浮现进而将他营救,这让他很苦恼,于是他游向大海的深处,认为这样就会因精疲力尽而走到自己的尽头。可在海中遇到鲨鱼的袭击时,他仍旧没有要放弃生存的打算。经过一番折腾之后,他恍然意识到:“人能够在需要空气的时候喘气,真好。人能够在挨饿的时候感到饥饿,真好。人在流血的时候能够感到疼痛,真好。人的伤痛,它不仅仅是疼痛,它还是一个特权。”[1]136他懂得了生之可贵,可是当他快游到岸边时,鲨鱼再次出现,他被鲨鱼咬沉了。人生在虚无之中所遭遇到的荒诞令人深思。《走不出的梦境》中,理想与现实的极度逆差,生活的无聊与琐碎,都使“我”在一种白日梦的状态中插上想要飞翔的翅膀,这是对自由的渴望。《起风的时候》,李约翰在国外受尽苦难,生存的压力让他痛不欲生:“李约翰巴不得自己是一只鸟,或者是一条鱼,哪怕做只墙上爬的壁虎也好。总之,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当人,当人太累,活着要看这么多人的脸色,每天要应付早起的压力,赶公共汽车的压力,付账单的压力,处理人际关系的压力,和别人出去吃饭谁来付钱的压力。”[1]41灵魂与身体在无尽的压力与压抑中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伤痛。《玻璃房子》中,贵妇伊莉莎的生活高贵富裕,物质生活极其满足,可是精神与灵魂的空虚令她疯狂,她忍受不了生命与身体中的这种虚无。《罗斯山上的歌声》,“金娜不在身边时我心烦,她在身边时我还是心烦。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感觉。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人的心里能够盛下一个江山,却容不下一个拳头大的空荡。”[1]15人生时时处处的心烦与空荡,正是存在具有荒诞本质的表现之一。《靠海的房子》,梅子从中国嫁到美国,可是他的美国丈夫威廉姆斯却阴差阳错地到中国工作,物质生活的极度丰富仍旧填补不了她精神上的空荡与虚无:“在美国住了十多年,梅子终于混成了资产阶级。不对,不对,不是资产阶级,应该说是有闲阶级。她对朋友说。不对,还是不对,应该说是逛店阶级,或者是伤感阶级、孤独阶级、盼夫阶级、寻觅阶级、没事找事阶级。最后她得出一个结论:在美国她属于百无聊赖阶级。”[1]57“百无聊赖阶级”,形象地道出了人生中所存在的虚幻与无聊。考夫曼太太比伊莉莎与梅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竟然将身体上的空虚与无聊寄托在一只猎犬身上,存在的无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牌局》中,为了打发生活的枯燥,一群人不但靠打牌消耗时间,而且还在打牌中各怀鬼胎,偷鸡摸狗,将生活的无意义写得十分到位。汤姆因为对女儿不正常的关爱,设计将女婿致残,而他竟在这种无聊中得到心安与自在,在荒诞中透露出人性与人生中的畏与怕。《月亮绣球》中,成人之间的婚姻在离离合合之中,极尽虚无空幻,“在这月光如水的夜晚,我快步朝前走着,脚抬起来,却不知道它究竟落到了什么地方。”[1]127没有方向感与意义感的人生,令人无奈却又不得不面对。《流年似水》中,徐丽为了自己的画家梦,出卖肉体与灵魂,可等她实现目标之后,却落到不知所措的境地之中:“不是想得到美国吗?你得到了。不是想享受美国吗?你享受了。现在什么都有了,还苦恼什么?还嫉恨什么?她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那条无舵的船知道。”[1]152为了理想与欲望,不惜寻找各种借口与突破口,可得到之后,又该何去何从?人生的荒诞与得失之间的悖论在此得以显现。《天堂·女人·蚂蚱》中的茄子与徐丽有一定的相似处,她为了出国嫁给她的教授,继而又嫁给缅因州的一个基督徒农场主,可她并未从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沙石小说一直都在默默关注着被欲望与痛苦双重挤压之下的人的生存与灵魂,在这个乐于为欲望的合法化与常规化寻找借口与说辞的时代,沙石勇于揭开那些自欺欺人的虚伪,展现受苦受难的灵魂,在荒诞与悖论中揭示存在的虚无与心灵的游荡,这在当代华文文学中是极为可贵的。
三
在触摸人生的虚无与揭示存在的荒诞的同时,沙石仍旧没有忘记坚守良知的温存与道义的底线。在沙石小说中,可以明确看出他对人生、生命、良知、道义等观念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他的立场与态度很多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莫大的关联与维系,可见,沙石身在国外,他的骨子里与思想中虽有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浸入,但同时仍旧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玻璃房子》中,阿德面对伊莉莎的诱惑时说了一句“我只想把事情做得正式一些,庄重一些,让它更具有政治意义”[1]12,并在了解到伊莉莎对自己的看法时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主动送上门来的艳福,作者于此令中美文化在阿德与伊莉莎之间进行激烈碰撞与交锋,最终阿德以华人所素有的骨气和正义战胜了轻浮浪荡的美国贵妇伊莉莎,作者的言外之意与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感是极为明显的。《我给新娘做傧相》中,美丽的梅子是与“我”当年在清河洼一起劳动时的知青,后来大家都到了美国,梅子在美国将要与居住在富人区玛莲县的比尔结婚时,她邀请“我”做她的傧相。“我”怀着激愤的心情,存心捣乱梅子的婚礼,原因是“我”认为梅子的行为有些忘恩负义。当年做知青时,“我”与军长的儿子军伢子都对新来的知青梅子有好感,可军伢子捷足先登,总是先“我”一步与梅子接近。不久军伢子接到调他回城的调令,可他撕碎了调令,心甘情愿地留在贫困之地只是为了陪伴梅子。一天,村支书二庆爷夜观天象,用祖传的天文气象知识预测到最近将要发大水,就吩咐村人搬到山上居住。“我们”不相信传统这一套,仍旧居住在原地,可是到了夜里真的发洪水了,在仓皇逃命中,梅子不见了,军伢子义无反顾地折回去寻找梅子,梅子得救了,军伢子却被洪水冲走了。“我”在梅子婚礼上的所有反常举动都是为了军伢子:“军伢子,你小子看好了,这一切我可都是为你做的,别看你打了我,骂了我,但是我还是把你看成哥们儿。”[1]102军伢子冒死营救梅子的英勇行为一直留存在“我”心中,当年的兄弟情深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漂白,可梅子却已经芳心他许。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重情重义与知恩感恩,正是这篇小说的基调所在。《献上一盘咕咾肉》中,阿拉巴马州菲尼尔小镇中黑人老太太的孙子拜伦在美伊战争中壮烈殉国,换来的只是白人霍姆斯上校的几个标准军礼与一面美国国旗。拜伦生前爱吃咕咾肉并一直梦想着到旧金山的唐人街去吃最正宗的咕咾肉,可是他没有机会了,老太太为了实现孙子的遗愿,不惜千里颠簸赶到唐人街,就是为了给孙子点上一盘咕咾肉。作者于此将战争的无情残酷与祖孙之间的至贵亲情做对比,留下了极深的蕴意与追问。《磨盘》中,从中国到美国淘金的吴三救了一只将要丧命于哈士奇猎狗爪下的黄鼠狼,当猎狗的主人为被打的猎狗报仇时,吴三到底也没有说出黄鼠狼的下落。中国传统文化中轻生死重大义的崇高情怀在吴三身上发生了,并且他营救的还只是一只黄鼠狼。《华嫂,二子和我》,善良可怜的二子充分恪守了道义与良知的底线,二子身上具有的那种正义感与是非观正是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赞许的。
四
身份得不到认同而带来的焦虑与危机,心灵在异国他乡找不到归宿与着落而带来的伤痛与苦悲,是移民文学所具有的特色之一,沙石长期移居国外,其小说同样也具有这样的意蕴。移民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沙石小说中尤其是在那些被欲望驱使而流居国外的主人公身上,更多的是展现出了灵魂上的挣扎与苦闷。
《摸鱼去》中,内华达州的律师朋友史蒂夫带“我”出海,途中史蒂夫钓到一条大鱼却又给跑了,即此“我”想起了童年与二哥一起为生病的姥姥捉鱼时的快乐趣事,如今却身在他乡时过境迁,史蒂夫觉察到我的惆怅,便用“美国有美国的美好,中国有中国的美好”[2]话给我安慰。《起风的时候》极其能凸显国人在他乡因得不到认同而产生的苦难:2003年SARS肆虐时,中国人李约翰在美国被白人同事沃尔夫冈举报有携带SARS病毒的嫌疑,沃尔夫冈举报李约翰的原因与动机是“他一天到晚地咳嗽,流鼻涕,打喷嚏。你说中国的SARS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能不担心吗……这个姓李的成天和中国人混在一块儿,你知道他们哪个人身上不带菌?我就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中国佬全部隔离起来……非洲人给人类带来了艾滋病,现在亚洲人又开始散布SARS。有这些人,世界能安宁吗?”[1]46西方强权国家对弱势国家人群的白眼、冷漠与歧视正是李约翰们在国外得不到身份认同的原因所在,李约翰因此极为痛苦,一开始接到哈密尔顿医生从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打来的电话时,他并未当回事,可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人在他国所产生的自卑自贱在有意无意间促使他相信自己真的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在将被打垮的那一刻他主动联系了哈密尔顿医生,把自己送进医院进行隔离检查。虽然检查结果证明他没有问题,可他的心理负担与灵魂之痛已经压抑了太久,他想到了死。在梦中,他看见了自己亲爱的母亲,“他说:母亲,我对不起你,我没给你争气。母亲笑了,脸上的纹络舒展开来。母亲说:谁说你没给我争气,你降生时已经给我争了气。你的生命就是我的荣耀,你是全世界最争气的儿子……他躺在船上,把头枕在母亲的怀里,母亲不再说话,只是对他微笑,用手轻抚着他的脸。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也照进了他的心里。他感到母亲的体温。他的身体异常放松,心里异常安静。疲劳、烦恼、羞愧正在从他的脚后跟向体外流去,一种难言的快感遍布了全身。”[1]54在这里,母亲与怀抱都具有双重指涉,一个固然是李约翰的生母及其怀抱,另一个就是李约翰的祖国及其怀抱。母亲,永远是他乡游子一个永不能忘怀的根据地,不论游子在外是否能出人头地,也不论游子在外是否还记得母亲,母亲都是时时刻刻在将儿女牵挂,母亲博大宽广的胸怀永远都会向远游的儿女们敞开,母亲的怀抱永远都是儿女们一辈子最温暖的归宿,游子们最终也将会发现只有将灵魂安顿在母亲的怀抱中才是最为心安之处。李约翰在母亲的怀抱中含笑而睡,他死去了。李约翰以他带笑的死,向游子们揭示了应该如何安顿那游荡在他乡的灵魂。《流年似水》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于我的名字是什么,这不重要,不过要记住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在中国时还有身份,还有形象,可自从到了美国以后,她把我抽象化了,淡化了,异体化了,我已经面目全非,嘴巴移植到了脑门上,眼睛长在了下巴上,鼻子和耳朵的位置未定,我无法辨清自己,就像不能辨清这个世界一样。”[1]148到了他国,不仅没有了自己的身份,连留存在他人记忆中的形象都遭到扭曲与变形,这是一件多么可悲又可怕的事情。《天堂·女人·蚂蚱》中的茄子与石头,也从不同角度与程度揭示了因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焦虑与苦闷。《冰冷的太阳》中,移居美国的“沙石”与妻子、儿子却有不同的世界:“虽然你我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我们却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假如你母亲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的生活里还会再多出一个世界。当然,即使她和那个英俊潇洒的白人托尼生活在一起,她也有她的世界。大约十年前,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我们,为的就是去追寻她的世界。”[1]233妻子与儿子可以很快适应美国,可“沙石”却总也不能适应,他一直找不到身份认同,所以他活在痛苦之中。《情徒: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故事》中将身份认同从国与国之间提升到整个人类的高度,这是王大宝被其经纪人威廉放在狼屋写作《情徒》之后再次回到人类社会时所产生的微妙心理:“我还是觉得有人类居住的环境充满了敌视和险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总是居于危难之中,敌人是可以长久的,而找不到永恒的朋友。这一切更让我怀念起在狼屋的日子,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连孤独、恐惧、焦虑都是自觉自愿的,没人强迫你,也没人规劝你,你可以做生活的主人,也可以做自己奴隶,不过想犯罪是办不到的,主要是找不到犯罪的对象,也没有犯罪的环境,犯了罪也没人来抓,更没有人来起诉,来审案,来宣判,所以犯了罪也是白犯。不过监狱倒是现成的,你想坐多久就坐多久,不用争不用抢,当然想越狱也无法做到。经过一番思考与回忆,我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一个人的社会才会成为和谐的社会。”[3]105经过三个月的独处与磨难,王大宝不仅认为在美国找不到身份认同,即便放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不会找到那种心安的认同,他对人类社会与人类群体产生了失望与恐惧。
五
沙石小说也存在一些问题:小说中汉语言运用得不够娴熟与精炼;人物的刻画比较平面,有些还停留在二元对立的阶段,人物的心理及其进展有时不能与情节的推进形成很好的呼应;有些小说的立意与思想没有能更进一步。
沙石小说首先存在的就是语言问题,这在其短篇小说中还不是很明显(由于中短篇小说的容量限制,作者必须在有限的文字中表达出应有的意义,所以沙石中短篇小说的语言问题不是特别显著),但在其长篇小说中却是显而易见的,如以下文字就不够娴熟与精炼“每次只要我说起文学和屁股的关系,他们总是群起而攻之,说我是文坛上异己分子,是文化人中的蛀虫,专门会制造歪理邪说,有意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他们还说我在文化思潮方面扮演着张果老的角色,明明是倒骑着毛驴,在正确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偏要说自己的方向是最正确的。为此,连威廉都对我大为光火。威廉说你别净胡说八道好不好,你的主张太离奇古怪了,小心会给你带来千古骂名,你再这样固执己见,死了以后会遭人鞭尸的,知道宋朝的大奸臣秦桧吗?就是那个陷害岳飞的老贼。他的下场是什么?由于他活着的时候作恶多端,老百姓恨透了他了,他死了以后人们给他立了个石像,放在岳飞的坟前跪着,不是为了让他千古留名,而是为了让后人出气,大人往上边吐痰,小孩往上边撒尿,你要是再不管好你的嘴,秦桧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开始我还跟威廉及其同伙争辩。后来我也不再争了,也不再辩了,因为他们这伙人和我的思想距离太大,所以思考问题的角度永远是交叉的,意识不在一个层面上,争论的结果是越争思想越是混乱。作家中自以为是的人太多,认不清自己的人太多,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不但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而且还知道吃豆腐不小心也会噎死人的。”[3]8-9诸如此类洋洋洒洒的论述小说中还有很多,不但令读者难以卒读,而且这些论述也大多与小说不沾边。不论是小说叙事还是情节推进都显得极为拖沓无聊,这是沙石长篇小说最为致命的问题,也是沙石在今后小说创作中最应该注意并引以为重视的问题。
其次,沙石小说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人物的刻画比较平面,有些还停留在二元对立的阶段,人物的心理及其进展有时不能与情节的推进形成很好的对接。《我给新娘做傧相》中,“我”与梅子的刻画都显得极为平面,因为小说中并没有交代梅子内心深处对军伢子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那么我的大闹婚礼就显得太过莽撞,人物的好坏之分也太过明显。《华嫂,二子和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华嫂前后的转变虽然是可能的,但是她是如何转变的,她是因为什么才变的,她前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以前的华嫂是全都好的,现在的华嫂全都变坏了,二子自始自终都是高大全的形象,这样平面的人物刻画实在太过浅薄与单一,并不能真正深入人物内心心理,也不能捕捉人性中最为细腻感人的成分。《玻璃房子》中,阿德的妻子已经跟别人跑了七八年了,这期间他一直都是单身,在阿德潜意识中,他对白人女子是极有好感并心存企图的。当漂亮高贵的白人贵妇伊莉莎主动送上门时,阿德却拒绝了,原因只是伊莉莎没有同意他去床上的要求,最后离开时还说了一句“别以为我是花匠就能拿我当块破抹布使唤,就是为人民服务,老子我还要挑人呢。”[1]13不知这样的理由会说服多少读者相信阿德此时的心理。同理,以伊莉莎的地位与相貌,她会主动选择阿德这样一个只是在报纸上看了一眼且貌不惊人的花匠作为发泄对象,也是很难想象的。《靠海的房子》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梅子竟会对一个偷他项链的黑人小偷心有好感,并且还主动将其保释出监狱,最后还在犹豫要不要给他开门,人物的心理进展及其呈现实在很怪异。《天堂·女人·蚂蚱》中,我与茄子的心理进展与情节的推进也没有形成很好的对接。《枣树上落下一只白鹤》也有这样的问题,大海对三婶的感情及其心理变化、三婶对大海的感情及其心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都显得突兀。后来大海离开家乡,三十年来仍旧单身,“其中的原因只有他本人知道,可实际情况是,他也不知道。”[1]339写小说不是打哑谜,不能在不清不白没有铺垫的情况下做出这谜一样的交代,大海为什么不结婚?这三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结尾部分,大海家的那个康熙年间在民窑中烧制的赝品瓷瓶凸然出现在刘副总的婚礼宴会上,这样写的意义何在呢?虽然前文中提及了这个瓷瓶,可是这个瓷瓶于整部小说而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缥缈恍惚的叙事、含糊不清的人物、游离跳荡的情节,共同见证了这部小说的失败。《情徒: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故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对林小野及其性情的刻画,显得非常主观与随意,没能进一步挖掘到人物灵魂的深与远。
沙石小说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小说的立意与思想没有能向更深处挺进,这导致了其某些小说呈现出一种较为浅肤的面貌,也使其小说质量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这恐怕与沙石久居国外,对当代华文文学及其高度与成就没有足够的关注有关。这一问题的产生其实与上述第二点有关,人物设置的平面化与二元对立化首先就决定了小说的思想与立意很难向深处挺进。比如《我给新娘做傧相》《华嫂,二子和我》《献上一盘咕咾肉》《牌局》《磨盘》等小说,其思想与立意大多都很平常,并没有能提供出更深层次的意蕴。表面的批判与揭露,在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高度面前,总会显得幼稚浅薄。《玻璃房子》《靠海的房子》《月亮绣球》《牌局》《磨盘》等小说,其实还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追问,对有关人物的刻画也可以更加细腻一些。《情徒: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故事》,这部长篇小说想要表达的立意与思想是很好的,可惜却被拖沓芜杂的语言给毁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语言对小说的重要性有多大。沙石在以后的文学之路上,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一定要好好打磨语言。
虽然沙石小说存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诸如《汤姆大叔的剃刀》《窗帘后面的考夫曼太太》《起风的时候》《走不出的梦境》等小说还是取得了较高成就,在当代华文文学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沙石小说对人性与人心的持续关注、对存在与灵魂的探索与抚慰、对身份认同与心灵归宿的寻觅与渴望,都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脉脉温情与人文关怀。沙石如果能够克服其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汲取当代文学中的有益成分,或许此后他能给文坛带来更多的收获与更大的惊喜。
参考文献:
[1]沙石.玻璃房子[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2]沙石.摸鱼去[J].红豆,2004(6).
[3]沙石.情徒: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故事[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何瑞芳]
On Novels of Sha Shi
ZHAO Hai-tao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It is the best features of Sha Shi’s novels to explore human nature, uphold the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and describe the struggle of souls. But there exist some serious problems in his novels, such as: diffuse language, flat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and plain conception and thought.
Key words:Sha Shi;novel;“The Glass House”;“A Man of Affection”;human nature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901(2016)01-0055-06
作者简介:赵海涛(1989-),男,河南驻马店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收稿日期:2015-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