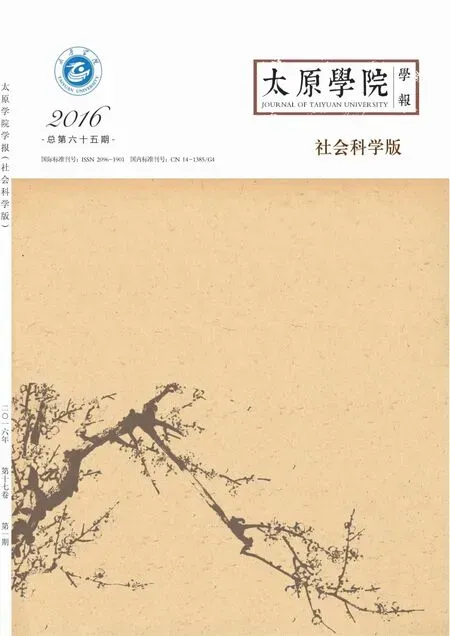《金星秀》的消费文化反思与传播特征
2016-02-10郑丹
郑 丹
(三亚学院 传媒与文化产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金星秀》的消费文化反思与传播特征
郑丹
(三亚学院 传媒与文化产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金星秀》是一档2015年开播走红的脱口秀栏目,开播以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明星访谈类节目和其他脱口秀节目。在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爆发性增长的表象下,《金星秀》等综艺节目的开播背后折射出消费社会以符号为消费对象、明星隐私作为摆设的后工业社会特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个体缺乏“本体性安全”触发了社会焦虑,催生了这一档电视综艺节目的迅速走红。《金星秀》的快速走红和发展与其自身的主持人鲜明风格、栏目信息宽泛、受众的社会心理特点以及注重与新媒体的互动结合有关。
关键词:《金星秀》;脱口秀;消费文化;传播特征;传播机制
《金星秀》是东方卫视于2015年1月28日开播的一档电视节目,首期收视率达到0.79,领先于同时期开播的电视节目。节目分为脱口秀和明星采访两部分,由现代舞蹈家金星担任主持人。据CSM50城收视率数据显示,《金星秀》已经连续多期获得周三综艺节目冠军。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鲁豫有约》《艺术人生》《杨澜访谈录》《超级访问》等四档传统的明星访谈类节目在2015年7月的平均收视率不足0.3%。在传统访谈类节目关注度下降的情况下,《金星秀》却能够做到异军突起,有鉴于此,这里专门对《金星秀》节目作传播学的分析。
一、《金星秀》走红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消费文化导致社会文化语境变化,催生了真人秀节目的活跃
近年来,我国脱口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改革带来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变化促使受众关注脱口秀节目内容,释放工作和精神压力,缓解个体不安情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推出的《实话实说》栏目开始,这种带有主持人个人鲜明风格的电视节目开始在卫视平台上竞相出现,节目形式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为明星谈话类,如《鲁豫有约》《非常静距离》《咏乐汇》《开讲啦》等,主要满足大众对明星隐私生活的好奇感;另一类主要是带表演性质的《壹周立波秀》《今晚80后脱口秀》等节目,表达大众对社会事件的态度和观念。这些节目一方面在电视受众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收视群体,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国内受众对于脱口秀这一栏目形式的收视习惯。但随着这类脱口秀节目的播出年份增加,脱口秀节目的形式逐渐固定化,明星访谈话题重复雷同导致了节目的吸引力下降。不仅如此,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的兴起让明星的隐私变得不再新鲜,传统的王牌明星访谈节目也就失去了独特的吸引力。《金星秀》恰好在这一时期出现并独具特色,取得收视率大热,也适时填补了观众对于脱口秀节目出现的审美疲劳,带给观众新鲜感。
(二)经济转型期个体缺乏“本体性安全”,触发社会焦虑
西方国家上世纪中叶的经济转型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伴随着这一转型产生了成熟的消费文化。对比而言,我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目前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转型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电影、电视剧和电视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但是社会矛盾也在这一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即新的价值体系导致的被动性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来看,社会道德仍然遵循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了与新的享乐主义相伴随的强烈的犯罪感。与此同时,文化的多元碰撞产生了广泛的社会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来源于经济转型的内在矛盾。人们尚处于“生产者”角色当中,却不得不遭遇转向“消费者”的尴尬,对自身社会身份产生了混淆,导致个体身份缺失、大众对自身角色定位模糊不清,由此造成社会传统价值认同的疏离感剧增,一方面亲身体验社会价值的零落消解,一方面却对传统文化的颠覆认知无法处之泰然,难以产生统一的社会价值认同。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了“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概念,即人们在社会中基本的安全感与信任感,提出“普通日常生活中蕴含某种本体性安全,这种安全感体现出可预见的例行活动中行动者在控制身体方面具有自主性。”[1]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进一步理性地发现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制度等社会结构间的共生关系。当人们发现并且承认这种个体与结构的关系时,人们能在社会结构中比较自如地生存,充分表达自我并享有一定的自由,拥有“安身立命”之本。反之,当人们缺乏本体性安全时,将引发内在的社会焦虑,进而导致人们在社会中自我身份建构的缺失。吉登斯的社会建构理论对研究电视文化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从吉登斯的社会建构理论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出发,中国当代的电视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日常生活文化,无论是真人秀还是脱口秀,均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文化来看待,人们围绕电视传播的内容及电视本身的争论都可以使得电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对每个人来说,收入、声誉、文化等各方面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必须有相应的方式释放压力才能自我恢复。金星秀的开播和走红,一方面在于金星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她经历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在《舞林争霸》和《中国好舞蹈》两档电视节目担当评委时,面对参赛选手良莠不齐的演出,金星在点评上丝毫没有顾及演员和其他评委的颜面,直斥选手的不足,风格独树一帜。同时期综艺节目中的评委往往过于注重选手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表现出的“煽情”和“感性”过于泛滥,而金星的“毒舌”、“犀利”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综艺形象。另一方面,金星对于明星、热门新闻话题的辛辣点评,反映了人们在处于普通的社会焦虑中对于环境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通过名人的传播效应产生传播效果的增强,从而让普通人在金星的话语中找到自我和价值观的认同。金星在节目过程中谈论各类时事热点话题,其评论和观点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却发人深省,同时不失幽默诙谐,在观众中积累了良好的收视基础。这样,《金星秀》的开播和走红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金星秀的传播文化特征
金星秀节目开播于2015年初,节目主要由金星个人脱口秀和明星访谈两部分组成,融合了脱口秀节目表演和谈话两大主要的元素,一方面对时下的热点话题提供观点,另一方面亦可娱乐受众。作为一档脱口秀节目,既融合了脱口秀的主要特征,同时又独具个性。
(一)主持人风格独特,旗袍服装别具一格
脱口秀节目基本上靠主持人来撑起一档节目,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人的个人素养、人生阅历、谈话风格甚至着装风格都会给节目带来一定影响力。《金星秀》节目开播于东方卫视,东方卫视在语言类综艺节目上具有传统优势,以往曾经开播的《壹周立波秀》《今晚80后》《欢乐喜剧人》等都曾有不俗的收视率。《金星秀》的节目结合了东方卫视和金星本人的优势,基于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背景,就像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那样,正统的中国红和具有东方独特风韵的旗袍成为了这一栏目的主要特色。《金星秀》的演播室背景也以红色为主要色调,再融合金星本人或素雅、或华丽的旗袍装束,加上她舞蹈演员的体态表演,整合成了一档兼具传统风韵的脱口秀节目画面视觉效果。金星具有舞蹈表演的基础,因此在节目中讲述自身故事或者新闻事件时,往往连说带演、惟妙惟肖地将观众带入事件环境中,引发观众认同感。金星本人在国内外生活的背景使得她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共性有更深刻的体会,在节目中推崇东方文化,注重传统观念的传播,总以一身旗袍示众,嬉笑怒骂众生百态,与栏目定位相得益彰。
(二)节目以时事热点话题为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从栏目内容上来说,《金星秀》涵盖了上到国家大事,小到家长里短的各种热点话题。主持人侃侃而谈,幽默、犀利的点评都符合了正确价值观取向,栏目内容定位准确。即便是在脱口秀节目源起地的美国,脱口秀节目中个人或者机构需要对自己的语言、思想和行为等进行反省和改进,以力求消除对社会弱势群体可能呈现出的歧视。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占据美国人思维的“政治正确”概念,和现今中国观众的价值观倾向具有相似性[2]。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正是大部分脱口秀节目的话题核心。《金星秀》节目的内容大部分都围绕当下的即时热点话题,与受众的兴趣和关注度相符,受众在心理上容易接受话题。比如“双十一”当晚金星秀做了一个模拟拍卖来让观众参与猜价,通过天价拍卖的结果揭晓拍品是马云的书画作品,结合时间气氛把话题变成娱乐,把新闻事件变成了小品表演,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上不合理的新闻现象。《金星秀》节目中的讽刺内容均取材于她自身的生活,通过一些小事鞭笞或提点国人应该注意的素质问题,比如模仿飞机上的空姐面对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两重面孔,与观众生活中的经历相似,在手机APP小咖秀上一度掀起明星模仿风潮,形成二次传播效应。不仅如此,金星也突破了以往各大卫视的隔阂,公开在节目中点评其他卫视的综艺节目。在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走红同时,邀请以模仿金星出名的王祖蓝到《金星秀》做客,配合了网络话题的热度,也成为了栏目的一大看点。这些具有创意的节目内容既能符合网络舆论热点,同时也宣扬了客观理性的价值观,“毒舌”的外衣下包裹的是受众期待的舆论导向。
(三)符合受众社会心理期待,注重娱乐观众
波德里亚认为,机器曾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如果消费物品的特性在于它拥有符号功能而相对丧失了客观(实用)功能,承认消费物品的实质是功能的无用性的话,摆设恰恰就是物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真相,在这一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变成摆设。在消费社会中,隐私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对明星隐私的消费已成为普遍的事实,明星隐私并无任何实用价值,但明星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兴趣爱好等内容,已经成为了许多电视节目用来吸引观众的利器,明星隐私也成为观众在茶余饭后大肆品评的内容。《金星秀》中明星访谈原本放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但随着节目的开播调整到节目的前半部分,并给予专门的名称“金星时间”。在明星访谈这一环节中,节目并没有像其他明星访谈节目那样慢慢回顾明星成长道路再总结成功经验,而是一开始就以快问快答的方式将受众对于明星的质疑和问题抛给受访明星,不拖沓不矫情,更符合受众对于明星访谈节目的心理期待。在大部分明星隐私已经成为娱乐话题的当下,《金星秀》的这种方式更能在短时间内向观众提供有效信息,不浪费受众的收视时间,也能更有效地留住受众。《金星秀》里面“秀”的演出方式花样繁多,通过主持人自身的肢体语言和情绪表现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夸张的表演和幽默的“吐槽”相结合,让观众像看舞台剧一样看节目。个性鲜明的观点披上娱乐的外衣后,更加吸引受众眼球,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观点,并通过脱口秀节目被主持人的观念同化。
在脱口秀节目部分,金星在节目中的“毒舌”形象也契合了受众对于社会新闻事件的关注心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受众获取信息量增加,同时参与信息传播的渠道增多,网络“吐槽”的流行就是出于对某些传统观念的戏谑和挑战。在金星对这些新闻事件或网络话题猛烈抨击的话语中,尽管难免有偏激之处,但却迎合了网民对公共事件的普遍关注心理,符合受众对社会不良、不公现象的批判和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向往。在这样一档以谈话为主的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避免了套话空话和陈词滥调,比如在谈到做慈善时,金星认为做慈善应该低调,而不应该像陈光标那样大张旗鼓,一反以往慈善活动注重宣传的现象。
(四)注重栏目互动
脱口秀节目的形式本身决定了节目大部分靠主持人个人的表现来贯穿整个节目录制,互动方面往往具有局限性,《金星秀》栏目的创新在于插入了另一位主持人沈南来代表观众的视角。脱口秀节目中一般会加入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但沈南的角色安置放大了互动的效果。沈南在《金星秀》中主要扮演了三种角色:一是在金星抛出独特的言论和见解时,代表广大观众适时向主持人金星提问,扮演观众的角色;二是在节目录制中插科打诨,与金星一唱一和扮演谐星的角色;三是在节目播放的视频短片里模仿扮演网络话题中的人物角色,另辟小剧场形象解释讨论的话题。三种角色解决了以往脱口秀节目过于依赖主持人表演的形式,也带给了观众视觉上的新鲜感。
电视节目与互联网的联合弥补了电视媒体缺乏互动的短板。《金星秀》节目的开头和结尾加入了新媒体平台的问答环节,增加与场内外观众的互动,如“金星时间”主要是明星访谈,通过网友们与明星的问答来增强互动性,栏目结尾是“有话问金姐”部分,结合微博和微信上网友的问题增强与观众的互动性。在栏目形式和内容设置的互动过程中,主持人与场内场外的受众互动频率高,信息的发出节奏有张有弛,从而引起受众良性的反馈,如此循环往复,创造优质的传播流程。电视观众与综艺节目间的无形距离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日益缩小,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的融合产生了强大的节目营销话题,金星秀的微博话题讨论形成了侵入式传播,从而使观众全方位置身其中,同时,观众的微博互动也使得他们在这场舞台戏中成为参与角色,引发全民狂欢。
三、结语
正如波德里亚所言,所有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信息,都是以既微不足道又无比神奇的相同形式,从不同的社会新闻中获取的。它整个地被加以现实化,也就是说,用戏剧性的方式加以戏剧化——以及整个地被加以非现实化,通过交际的中项产生距离,而且缩减为符号。以《金星秀》为代表的脱口秀节目获得受众的关注,正是消费文化在我国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中整合社会新闻信息并加以戏剧化的过程,通过对文化符号的生产与组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行为的主体——普通大众。《金星秀》的走红是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其辛辣、独特而又丰富的脱口秀表演形式在网络上传播与流行,形成了脱口秀节目中一种崭新的节目形式和文化景观。但目前国内电视节目仍处于探索过程中,竞争环境日益恶化,不仅要抗衡其他同级卫视,还要面对新兴视频网站自制节目的挑战,不可避免出现同质化、低俗化、泛娱乐化和语言暴力的问题,容易引发受众反感。《金星秀》脱口秀电视节目为大众消费文化提供了意义建构的空间,使得观众由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焦虑而向往《金星秀》的舞台,释放内心的不满和焦虑,但是,短暂的节目狂欢之后不能回避的现实使得他们更失落,节目便成为了娱乐资本的流通商品,而观众得到的综艺狂欢与现实失落间的焦虑,这种焦虑与社会焦虑相叠加,形成时代的大众焦虑的复杂化。如何引导受众合理回归现实应是《金星秀》进一步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状况下,脱口秀节目应该鼓励更多开发,本着因势利导的原则,充分发挥脱口秀节目正面的引导功能,抑制节目的语言暴力因素,让脱口秀节目的传播与社会、时代的发展需求相适应。
参考文献:
[1]耿波,史圣洁.时代焦虑.本体安全与中国电视综艺的形态变迁[J].现代传播,2015(11).
[2]陈力丹,潘彩霞.看不见的宣传——美国脱口秀节目走红的传播学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4(5).
[责任编辑:王丽平]
本刊声明
本刊已入编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其收录论文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给付。凡不同意编入该数据库的稿件,请来稿时声明。
Rethinking and Spreading of Consumer Culture of “Jinxing Show”
ZHENG Dan
(Specialty of Advertising, Sanya College, Sanya 572022, China)
Abstract:“Jinxing Show” is a TV talk show column started to broadcast and became popular in 2015. From starting broadcasting, it exceeded traditional programs of star interviews and other talk show programs. As our TV comprehensive art programs increase greatly, the starting broadcasting of “Jinxing Show” shows that the consumer society takes symbols as its consumer object. All the social characters of post industr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ake this column of comprehensive art programs become popular quickly, which is related with the distinctive style of the column host, the extensive informat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media interaction.
Key words:“Jinxing Show”;talk show; consumer culture; spreading feature; spreading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J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901(2016)01-0089-04
作者简介:郑丹(1983-),女,湖北咸宁人,三亚学院传媒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学。
收稿日期:2016-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