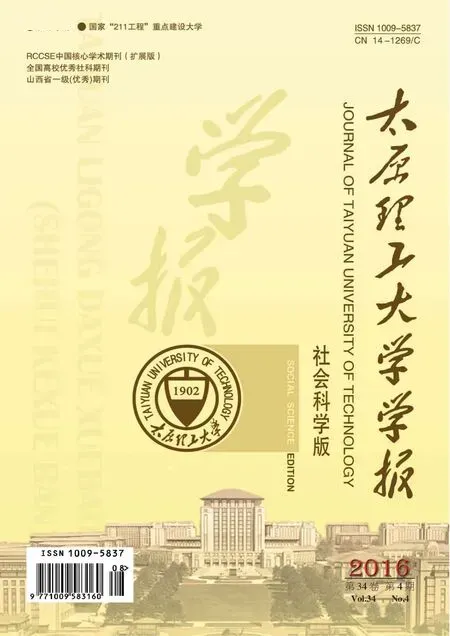孔子道德哲学中的群己关系
2016-02-09孔洁
孔 洁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孔子道德哲学中的群己关系
孔 洁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群己关系是孔子道德哲学中一个重要论题。与后期儒家哲学片面强调群体原则不同,孔子的群己观为个体生存预留下极大的开放性空间。其以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独立个体为出发点,尊重人作为现实存在的情感需求,通过推己及人的道德生发路径,形成了以“超越自我中心”为特征的特殊群己观。
孔子;群己关系;仁者由己;仁者爱人;修己安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人是什么?这是哲学首要的、基本的问题。”[1]263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也是个体主体性确立的根基所在。在人类社会中,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分为对自我本身的审查,对人际关系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以及对自我与群体关系的定位。这三种关于自我的关系体认在实践中又不可避免的统归于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即“群己”关系。
群,在古汉语中,上君下羊,《说文解字》中释为“辈”也。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道:“朋也,类也,此辈之通训也。”因而在其属人性上,群指的是人类团体的集合。《说文解字》中将“己”释义为“中宫也。象万物辟藏诎形也。己承戊,象人腹”。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道:己为中宫,“引申之义为人己。言己以别于人。己在中,人在外”。从而可知己为个体之独特性的根本所在,是自我树立的核心,主体的内在基础。因其为中宫,因而树立起“己”,个体才有存在的根基。且“己承戊,象人腹”,因“己”又具有巨大的内在包容性,使得个体能够包容他者,以获得不断成长的内在生命力。
至于说到群己关系,严复先生在《群己权界论》的译凡列中说道“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也”[2]7。因而作为具有独立心智的个体就其本身而言,他可以做一切他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个体的自由;然而当个体开始进入人类群体之后,由于每个个体都具有无条件的自由,彼此之间便会产生干扰,在链接得以发生的同时,约束也随之产生。如何以公平公正、中庸合德之心处理自我与他者、群己之间的关系,也是传统儒家哲学的核心议题。
一、仁者由己——主体道德生命的展开
孔子是儒家哲学的奠基人,当我们在探究儒家哲学的群己观时,总是不能绕过这位文化巨人。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乃为其在上接周代“敬德”“尊礼”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寻求个体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论语·微子》(后引此书,仅注篇名)篇中,孔子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可以说是儒家哲学最早明确提出关于人禽之别的学说。在孔子看来,人与鸟兽虽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禽有别。这种“别”就是人类从自然化向文明化的过渡。孔子不仅提到了人与鸟兽有别,不可同群,也提出了“吾”与“斯人之徒”的关系问题,即群己关系问题。
对于群己关系的问题,在孔子那里是十分明晰的,即先完成个体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再处理“吾”与“斯人之徒”的关系。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中孔子借古今学者之别,阐明了其对于个体自我实现的观点。在孔子看来,古代学者学习在于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在于成己;而今天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外在的目的,装饰自己给别人看,以获得一定的名声。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引用程子的话解释道:“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3]176换句话说,虽然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看似都是进行道德上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然其出发点不同,修养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在孔子看来,道德修养应该遵循“绘事后素”(《八佾》)的原则,礼乐的修养应该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而出发点是关键。只有主体自身存有良好的用心,真心诚意的进行学习,才有可能树立起独立的人格,好善而恶恶,不失其公正之心,最终成就自己。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因为心有所系,因而在面对社会中的善恶时才能有所判断,有所坚守。而今之学者,在修养的过程中,以获得外界的肯定与名望为目的,是为私心,因有所求,有所依赖,因而很难做到不以他者的评价为其取向,最终必将失其初心,更不可能以公平正义之心处理群己关系。
就此而言,孔子所追求的个体道德生命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是建立在主体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的。其成己之学,乃是主体在道德上自我选择的结果。“仁者由己”(《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述尔》)。孔子将主体的选择作为仁德实现的前提基础,赋予了主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也即为人的自由。然而,主体的道德自由,并不是无限的,选择的权利必须以选择能力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因而主体的理性认识能力在其认识与实践仁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孔子在回答子路“子行三军,则谁与”时,答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述尔》)。在孔子看来,勇敢虽是一种美德,但是不经理性的思考,盲目冲动却也是不可取的;唯有经过慎重考虑,才可能使主体真正地践行出仁德。而这种经过主体理性认知后所选择践行的仁道,也就不再是道德规则的强制命令,而是主体自我选择的行为准则。也正是由于具有理性精神,因而主体也才具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可以说具有理性的主体是孔子对人性抱有极大信心的根源,也是其培养具有德行生命的个体的内在支持。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这里的学不是指一种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指通过学习提高主体理性鉴别能力,以获得个体知识水平的上升。仁德、聪明、诚实、直率、勇敢,刚强,虽是优良的品德,然而如若主体不进行学习,未有自我的理性判断能力,这些美好的品德则可能因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而被舍弃甚至错位发展。孔子一生学而不厌,从十五岁志于学,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在培养自身独立的理性判断,进行道德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
由此看来,孔子的“仁”虽然可以用普遍的道德规则来表现,但并非道德原则本身。无论是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抑或是道德践行的实践中,具有理性的自我都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体通过自身的选择,以及不断地努力,践行着仁道的原则,完成着人性不断展开的过程。
二、仁者爱人——自我中心化的超越
孔子将自我作为践行仁道原则的重要基础,而并非终点,超越自我中心化是仁道原则的内在规定性。“仁”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亲也。从人从二”。因而自我在追寻仁道的过程中就不再仅仅是独立生存的个体,而必然与他者发生关系。曾子在解释孔子之道时,说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为恕。”[3]81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忠”对应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将“恕”对应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38。“欲”乃为想要,自己不想要的也不强加于他人,这是把他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自我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不但需要树立起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能识善恶、分好恶,同时还需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的、厌恶的也绝不强加给他者。这表现出主体对于他者的一种关怀之情,同时正是这种天生感情的自然流动,给予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充分空间。
感情交流虽然不是人与人交往活动的全部,却是其根基所在。在追求个体道德生命的过程中,孔子承认并尊重主体情感的存在价值,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的主体道德修养路径。情感的生发流转是人的本能机制自动自发地过程,并无好坏之分,然而各种不同的情绪通过个体的言行表现出来以后却是可以带来不同的社会效应。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孔子倾向于用“礼”这一社会普遍规范来约束自身的言行,使其得以在社会中立足,而社会则可以获得稳定和谐的发展。但这并不是孔子道德生命的终点,外在的要求与束缚并不能成为个体立身的根本,只有将其内化为主体自为的选择,才是个体道德修养的真正完成,因而孔子将其道德生命的终点存放于“乐”中。“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5]502由此可见,孔子的道德哲学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建立在有感情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上的。
主体在具有了理性的思维能力,以及得以生发的感情基础之后,才可能在进一步的人与人的交往中,把他者当作同样的独立个体,当作人来尊重。正如宰我向孔子询问三年孝期是否过长时,孔子并未直接作答,而是反问道:“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阳货》)当宰我给出肯定回应时,孔子尽管不赞成他的做法,也同意其执行一年的孝期。我不同意你所说的内容,但是尊重你做出自我选择的权利。由此可见,在孔子那里,自我与他者同是独立的完整个体,是值得彼此互相尊重的。
这种建立在互为目的、互相尊重基础上的主体间的交往才可能为主体间的沟通、对话预留下充分的空间。而自我与他者之间,作为同样的类存在,彼此之间才得以在同理心的作用下,产生互相关怀的仁爱之心。在《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录了“仁”字的两种古文写法,一是“忎”,一是“”。根据考证,一般学者认为儒家的仁更倾向于由“千心”发展而来,乃为“人心”的意思。“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人的智慧之源,与身相对应;二则是表达人的感情,如《诗经·小雅》中,“他人有心,予忖度之”[6]394。因而孔子在建构主体德行生命的过程中,追求的是一种顺应自然、顺应人性的发展方式。其仁德是建立在具有感情的生命个体基础上的,在仁德的具体体认过程中就表现为对他者的爱。
孔子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在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中,超越了自我中心化的倾向,在尊重他人主体性的同时,又能尽己所能关爱他人,为他人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这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排斥他者,将“他者”看作“地狱”的存在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差别。
孔子尊重个体的独立,也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这种链接包括主体之间在交往之中的友爱之情。孔子在其推己及人的理念中,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一步升级,提出成己成人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自己站得住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事事行得通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这就将仁道从“恕”的层面进阶到“忠”的层面,从“推己及人”上升到“以己及人”。而这种推进,也就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怀之情上升为责任感。这种责任伦理的思想,无疑对于自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体在立己、达己的过程中,还同时肩负立人、达人的责任,在成就自己的过程中,还必须成就他人,并进而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完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把他者看作我的同伴,反省的主体虽然是自我,内容却是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是否尽到了责任:替他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己所反省的内容,不再仅仅出于对他者的关心,而是表现出一种对于他者应尽的义务。当交往之中的关怀之情,上升为责任之感,个体就彻底超越了其一己之域,走向了一种同一原则。这种同一原则在整个社会领域中加以运用,则必然走向了群体认同。
三、修己以安人——群己关系的升华
孔子将立己与立人、达己与达人联系起来,事实上也就是将自我与群体联系在了一起,自我的完善不仅仅是个体独立人格的建立,更包括对他者和群体责任的完成。在《宪问》篇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然而在他那里,这种君子的修养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的自给自足。成己是为了成物,个体进行自我完善其目的是为了使他者以及天下百姓安乐,群体社会的安定才是自我完善的终极目的。儒家的君子上承天理下接百姓,对其所处群体的社会生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在培养个体独立性的过程中,孔子较为注重的是主体自身理性的培养;在私人交往关系中,关注主体间的关怀之情;那么对处于公共领域中的个体,则是通过自我规范的普遍化实现群己关系的和谐。个体作为群体的一员,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着他者,甚至整个群体的社会生活。
孔子的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其对仁德的追求并不局限于一种认识层面的理解,更是寄希望于其在人伦日用中的践行。然而“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7]337。当个体进入社会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由于各自的利益、立场不同,矛盾与冲突成为生活常态,因而孔子将“必使之无讼”(《颜渊》)视为一种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想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除了依靠人与人之间本身具有的尊重友爱,最为有效可行的实现路径就是对于“礼”的遵循。“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4]337
朱熹《四书集注》释“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3]59。礼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世的准则。“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在孔子看来,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能做到遇事恰当处之,却仍然不可缺少礼的规范。礼使得一切社会行为、社会事件的处理具有了具体可操作的准则,自我规范具备普遍化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自我规范的普遍化,才使得社会治理蕴含公平公正的可能性。因而“克己复礼”成为主体安身立命、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路径。
所谓“克己复礼”,乃是指通过对自我的约束,使主体纳入普遍的社会规范之中,服从群体的规则,这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个人私欲的独立个体为了适应群体生活,获得群体及社会的认同,不得不弱化对于独立自我的认知。因而孔子提出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不存己之私欲,不专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是,使个体在群体社会生活中更加注重对于群体原则的认同。这种强调个体服从于群体属性的认知,如若不加节制,则会造成个体主体性的湮没,使得群体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
因而孔子的“克己复礼”终究只是一种追寻个体道德生命,以及社会安定的手段,而非目的。“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孔子的礼与仁是不可分的,其以仁释礼,以礼践仁,从而建构出个体与群体之间对话的空间。
孔子的“克己复礼”虽也是主体自身适应社会要求,将自我适应社会普遍规范的过程,然而其以仁为其践行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就将自我规范普遍化的过程与一般的道德强制区分开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临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临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在孔子看来,智慧足以理解礼,但是不能从内心深处保持对于礼的尊敬,即使暂时遵循了礼的规定,也是不可以长久保持的,遇到一些阻碍就会因私欲放弃对于礼的坚守。理智能够理解,又能从内心真正信奉礼,即使态度不够庄严肃穆,一些具体的礼仪规则没有做到,也只是小的瑕疵。仁作为一种道德生命的内在诉求,虽然不是道德规则本身,确是可以用道德要求来表现的。礼即是仁在主体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方式。对于以仁为其内在生命诉求的主体来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是其主动选择的、内化为自我规范的言行准则。
在这种社会规范内化的过程中,自我能够形成“周而不比”(《为政》)、“尊贤而容众”(《子罕》)的人际交往态度,在保留主体独立性的同时,又建立起对于群体从属性的认同,造就出群体成员之间“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的群己关系。
所谓“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乃是一种具有开放空间的主体交往关系。“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和以处众曰群。然无阿比之意,故不党。”[3]188具有内在道德生命的主体在追寻仁德的过程中,注重自我的修行,不断摒弃自身的私欲,持公心与他者交往,以正确的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 ,不盲从附和,即使有争执,也以真理为标准,因而能够不结怨。也正因为能够不断摒除私欲,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只因为共同的目的、兴趣而团结起来,却不因私欲而勾结,损害他者与群体的利益。由此,个体与群体之间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使得个体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成长,而建立在独立个体之上的群体得以持续地稳定发展。
四、现代背景下群己关系的救赎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60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如若不是把人作为抽象的存在物,其就必定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从横向关系上来说,也就是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一个具有理性与自由意志的个体处于一定的群体当中,群己关系就必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
所谓“群己关系”,事实上就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自由与群体和谐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重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超过了群体存在的价值,认为个人存在乃为最高的价值旨趣。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认定人为自身而存在,致力于追求个人的幸福,确立了人作为主体的独立地位,把自身看作绝对的主体,理性自我成为终极性的个体存在形式。这种以绝对个人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观点,使得自我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他者的关系最多是以互利为基础的初级交往形式。因而一旦个人利益与他者、群体产生冲突,势必放弃自身的社会责任,造成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矛盾的不断升级,最终危害整个群体的生存。此种思想以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为代表。另一种博弈结果则是人们把群体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旨趣,个体的一切言行都要遵循群体的共同的善。持此种价值观的人认为个体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群体为个体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条件,安身立命的场所,是个体生命价值的依归所在。然而这种把群体价值作为最高的善的观点,往往容易用群体原则湮没个体原则,把个体的主体性掩盖在抽象的共同体当中。而在此过程中,群体的共同的善一旦出现问题,个体将被严重剥夺生存的空间。在近代社会中我们把此种思想称为社群主义思想。
孔子的群己观与这两种群己观既有重合之处,又有所不同。它是建立在具有理性认识能力,以及感情需求的具体的现实个人之上。与此相对应,孔子的群己观首先重视个体理性自我的培育。孔子的哲学虽然被我们称为“道德哲学”,却并非是一种强制性的道德灌输,而是具有理性自我的主体自愿选择的结果。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3]6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社会发展的根基在于主体自身的修养。孔子一生致力于道德生命的培育。而主体自身修养的基础又在于其具有理性的认识能力,知善恶,辨是非。除此之外,对处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的现实个体来说,除了自我的发展,还涉及与他者、与群体的关系。因而,在孔子那里,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并非只是为了主体内在道德生命的完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才是主体对于其内在道德生命的真正践行,是其道德追求的使命所在。然而与一般利用群体原则限制、约束个人的群体主义观点不同,孔子用以链接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关键在于“超越自我的中心化”。
独立的自我是孔子群己关系的基础。在此之上,孔子建立起一种“推己及人”“以己及人”的修养功夫,将自我与他者、群体连接在一起。人不仅是一种具有理性认识能力的物种,也是具有情感体验的存在物。并且这种情感体验不仅仅是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相通的,因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9]79。也正是因为这种同情心、同理心的存在,主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他人之所感,想他人之所想”,从而建立起与他者进而群体的链接。孔子的修己安人、安百姓是建立在具有独立性的自我,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性,自觉涵育出关怀他人之心,为群体负责之意。
因而孔子的群己观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又不同于社群主义利用共同的善抽象人性的观点。它是通过独立自我的建立与超越过程的完成,实现个体与群体之间和谐共处的第三种群己观。此种群己观必将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原子主义个人危机与社群主义的矛盾带来新的突破。
[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英]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杨天宇.礼记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and Individual in 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编辑:陈凤林)
KONG Jie
(DepartmentofPhilosophy,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and individual was an important thesis of 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Different from the later Confucian philosophy which put one-ided emphasis on group principle, Confucius’s view of group and individual left a great open space for individual survival. Taking the independent individual with rational judg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respect for others as the existent emotional need, it eventually formed the special view of group and individual with the character of “transcending ego-centrism” by the moral path of putting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Confuci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and individual; The benevolent restrain themselves; The benevolent love others; cultivating oneself and bringing peace and happiness to others
2016-07-26
安徽省规划项目“‘中国梦’视野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AHSKY2014D65);安徽大学研究生创新扶持项目“新文化运动后主体性哲学的建构”(yfc100095)
孔 洁(1988- ),女,安徽蚌埠人,安徽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B22
A
1009-5837(2016)04-00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