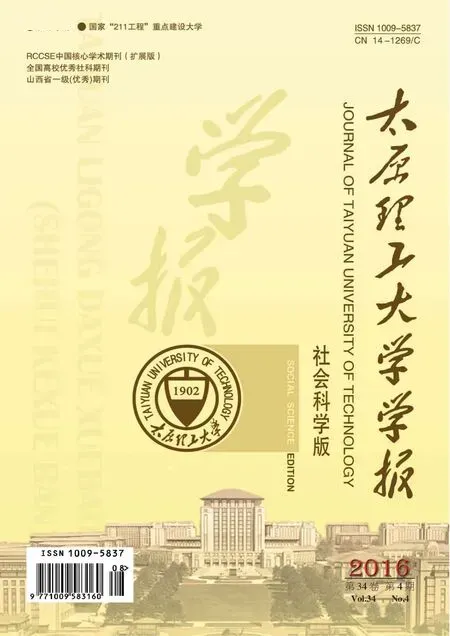1956年山西晋城县云台、封门、西冻水三村割属河南研究
2016-11-25祁毓龙
祁毓龙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1956年山西晋城县云台、封门、西冻水三村割属河南研究
祁毓龙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在微观尺度下探究政区改易问题,有利于更为深刻地认识政区改易背后多元复杂的“联系”。1956年,山西晋城县云台、封门、西冻水三村群众要求改属河南。面对此三村提出改属要求,中央、省、专署、乡政府等多种不同群体对此事情的看法,不仅体现了当时大背景下的社会风貌,还展示了民众之间、官民之间、官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多重互动与博弈。文章以这次小尺度的政区改易行动,考察事件背后多重人物、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勾勒不同群体对政区割属的影响。
行政区划;政区地理;割属;云台;封门;西冻水
边界、幅员、层级、治所是行政区划研究的四大主要要素,在行政区划的分划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其中的某些要素。“行政区划的分划过程是在既定的政治目的与行政管理需要的指导下,遵循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在一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基础之上,并充分考虑历史渊源、人口密度、经济条件、民族分布、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1]那么,县以下小尺度的行政区划,作为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也应当重视起来。微观尺度下的地方犹如动植物的“细胞”,行政区划这一庞大的“生物”必然是由这些微小的“细胞”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下构成的。只有我们带着无形的“显微镜”来观察这些微小的地方,才能更深层次地把握行政区划改属的要义。就目前学界而言,微观尺度下行政区划的实证研究可谓寥若晨星[2-4],大量学术空白有待填补,研究理路也远未建立。本文以微观尺度下的行政区划为考察对象,希冀对此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割属事件的发端:一封来信
云台、封门、西冻水*关于封门、西冻水的写法多种,这里主要依据《河南省沁阳市地名志》(参见李长吉.河南省沁阳市地名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206)。三村划归河南以后,隶属于沁阳市。沁阳地处豫北,整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倾斜态势。沁阳仙神口、云阳口、九里口、龙门口、前陈庄一线以北为山地,系太行山余脉,占全市总面积的25.4%,该区山势陡峻,峡谷幽深,土层浅薄,植被稀疏,干旱缺水,发展农林牧业为宜[5]60,不适宜耕作,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资源匮乏。那么,在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当地群众主要依靠什么来维持生计?为什么来到这里?据档案资料记载,“三村群众主要依靠刨药材、砍柴维生”[6]。当然,这里所提到的是主要营生方式,除此之外,因为这里刚好有逍遥石河流经,有部分滩地是可供农耕的。那么,位于山坡上的三村落为什么要划归河南?据有关记载, “该三村群众代表胡安水等人,从1955年2月先后上书毛主席和国务院,要求将该三村划归河南省沁阳县。其主要理由是:一,三村原属河南省沁阳县,解放后(大约1947年)才划归我省晋城县……”[7]读到此处,我们不禁疑惑,解放前更长的时段内此三村的具体行政归属情况如何?解放后为何要划归到晋城?为了顺利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时间上溯到清代。
凤台县(今晋城市)于清雍正六年置,属泽州府,与河南济源县、河内县、修武县毗邻。据《凤台县续志·关隘图》中记载,“九里口:南距河内紫林村三十里,东南距河内义庄三十里”。 由此可知,九里口以北尽属凤台。其次,在《凤台县续志·关隘图》“九里口”图幅左侧配有文字,写道:“口为入境小道,在县西南八十里。向东南三十里系河内义庄村……”可见九里口这一关隘,既是豫晋之间的分界线,又是凤台县与河内县的界址。那云台山位于何处?请参下图(该图采自光绪《凤台县续志·关隘图》,晋城县人民政府,1983年据原刻本重印,第41-42页)。

图1 九里口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云台山位于九里口北部。同时,九里口以南有一聚落名曰“土窝村”,现土窝村已无从查考,但是从“河内”二字可以看出此区域已经隶属河内县。由以上的论证可以推出:在清代的时候,云台等三村归属于山西省。那究竟是何时才划归河南省的呢?志书载称: “1943年(民国32年)春,晋城南部和沁阳北部合并成立晋沁县,归太岳二地区领导。”[5]21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晋沁县撤销,云台等三村仍归属河南。后由于解放战争进程的不同,“因山下尚未得到解放,解放后暂归山西”[8]11。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到来,各种“矛盾”渐趋显现,民间的“回豫”呼声由此而生。
二、回豫“运动”:来自民众的呼声
1955年3月份,山西省晋城县第七区云台村胡安水代表村里的18位村民,致信国务院,要求将此村划归河南沁阳第三区义庄村。同年10月,封门、云台群众再度“上书”中央,请“求主席速赐指示,以便遵行”[8]11。理由是“我们的村均位在山头上,原属河南省沁阳县义庄村,解放后暂归山西。因山下尚未得到解放,我们村人亦均是由河南省沁阳县义庄村迁徙而来。本冢亦均尚在义庄,要是能划归河南旧界对于婚姻丧葬亦诸多便宜”[8]12。从中看出移民的因素包含其中。由于移民的缘故,村民在方言上也与河南相同,“与山西有些不同,开会时有过因此导致冲突的情况。乡干部素习对我们村,与山西比,就有些歧视,以致形成工作上有诸多困难”[8]12。如前文所述,这里至少从清代就隶属于山西泽州府。一般而言,“州(府)属各县与州(府)治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之间的密切接触也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特殊之处,使各县的方言自觉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9],但在这里却稍稍与常理有些不同,险峻崎岖的地形阻隔了州(府)的向心力作用。就“因语言产生冲突”而言,我们理解起来也不困难,在那个年代,文字的使用在底层还不是很发达。特别是在乡政府的会议上,虽是同一个乡,不同地域村民的方言还是不尽相同的,这使得操河南方言的“他们”略显“另类”,另外,“本冢亦均尚在义庄”也凸显了村民安土重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全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移动的。……不但个人不常背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祖茔上呢?”[10]
前文已述“这里土层较薄,不适宜耕作”,且“我们村所种的地均是山堎地,石多地瘠。每年收入是顾不住人口的。村民是全靠在山坡刨药材、砍柴担到山下义庄及西向镇换取些生活日用品以维持的。更兼我们供销社股金旧入在山下西向镇,则是我们村人每天有人在山下。要是能划归河南旧界对于开会生产两不耽误”[8]12。与村落最近且可资利用的河流是逍遥石河。即使有河于此,由于其属于季节性河流,利用起来还是有许多不便。为了维持生计,民众自然会想其他的办法,在山上刨药材,之后到山下换取生活用品便成了维生的手段之一。沁阳市北部山区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据初步调查有600余种,主要分布在常平、西万、西向、紫陵一带山区[11]。如果改属河南以后,到山下开会的时候,可以顺带一些山货出售,会后回来能捎带买一些日常用品。此外,在交通方面,当地民众认为划归河南更符合他们的日常生活之需。 “我们村相距河南沁阳县城50里,西向区公所30里,村人每天有人在山下生产的。对于送通知等文件不需要专人送上,不致去费人工。此其划归河南旧界便利之三。我们村相距山西晋城县100里,距黎川区公所50里,对于开会转送文件需得专人,又不能连带生产。则是虚耗劳力,此其在山西界困难之一。”[8]12再者,从内务部与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往来函件也可以看到行程上的距离问题。“三村距离沁阳县城50华里,较晋城县城100华里来往便利。”[7]12单就路程的里数来说,确实距离晋城有些远,可村民是不会对这些数字感兴趣的。他们走的路途一定是最短的,可就是这些距离最短的路途,也要翻山越岭,而且路途上还要携带干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开会是很平常的,频繁的会议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
三、县下之权:乡级政府的态度
群众在来信中述及“前上两禀,要求将我们所住的村界仍划归河南旧界,曾蒙我们县人民政府,令我们乡人民政府具表绘图,以俟分界图表均已呈上,我们终未得到根本解决,可是我们乡人民政府素对我们村就有些歧视,对于我们村划回旧界更有些不满,不知是具表绘图时我们乡人民政府故意弯曲事实颠是非,以致县政府未能从速解决,亦不知是我们乡人民政府,将公事压存,不与我们群众发表,以致我们群众处在两难”[8]12。在群众给国务院去信以后,内务部要求下级政府就此事调查处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没有实际的进展。群众于1955年11月又向内务部反映:“兹有我们群众,有个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同住一乡,待遇不同,可是他们此地的牛、羊,大牛一头,饲料二百斤,小牛一头,饲一百五十斤,但是我们河南的这三个村的牛羊竟一粒饲料都没有,如此看待我们种种受压迫,大略谨呈。”[8]12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收到这则消息以后,给晋城县人民委员会说:“西尧乡的其他村庄在《三定》留量上一头大牛扣除饲料二百斤,小牛一百五十斤,但在该三村中有没有这样做。究竟实际情况如何,请即调查清楚,如果属实应当迅速纠正,并作适当的处理,将处理的结果报告省人民委员会”[12]。晋城县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回馈的调查结果是:
“西尧乡是个山岳地带,在去年进行粮食三定工作时,关于对牲畜饲料,我县均是按照上级规定,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全县进行统一布置,但是该乡乡干部由于思想糊涂,观点不亮,不执行党的政策,因而在我们的主观思想支配下,就按他们乡的情况,又分为两类地区,将西尧等九个自然村划为一类地区,对牲畜饲料扣除标准是:能拉车的大牛,扣除饲料二二〇斤,能耕地的牛扣除饲料一八〇斤,凡是没有耕地能力的小牛扣料六十五斤。并将云台、封门、西冻水三村划归为第二类,对饲料扣除标准是:大牛扣料一百斤,小牛扣料五十斤。”[12]
由此看到,确实存在就“三定”问题区别对待的情况。群众来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自从去年二月我们向上级提出我们的要求意见(把我们三村还划归回河南)后,在各方面受着乡政府领导同志的不合理打击。更突出的是去年在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下,群众都是热火朝天的搞社会主义,积极参加高级社。乡政府的领导干部竟敢非法无天的不叫数户入社(封门两户,云台一户)。这真是打击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与我们提意见的群众戴帽子,说我们是反革命分子,捣乱工作。”[12]事件至此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更有甚者,有的群众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去了,对于山上田产采取放弃的态度,可见,这些下山的群众竟然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在来信的最后,盖印着“沁阳县义庄乡人民政府”的红色公章,就是这个红色的公章,在笔者看来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义庄乡人民政府的态度,即义庄乡人民政府对三村划归本乡这一事情,采取支持的态度;二,民众已经把自己当作义庄乡的人了,同时,对西尧乡政府已经不信任了。在距离上次给毛主席写信的时间已经过了约一年,可是群众看到的是“八字还没有一撇”,群众的生疑是在情理之中的,转而希望通过义庄乡政府的渠道将信息传递上去。“并把去年二月迁移回河南的数户群众入信用社的股金不叫往回抽,信用社的规定人到什么地方,股金可以到什么地方,他们竟敢不执行政府政策”;“把去年二月迁移回河南的群众,到十二月要代耕款”。由于改属问题,这项政策得不到有力执行,反而变成一种欺压的手段。事情至此,仍继续发酵。1956年6月内务部又收到胡安水、张振威的来信。信件内容摘抄如下:
“……我们村又向上级提出要回河南的意见,后而我们更受到西尧乡打击和威胁。他们一贯是封建作风,离开群众,去进行工作的。如选举村干部的斗争对象胡法田,他买通西尧乡长王正富,竟敢违反民意硬指定胡法田充当村干部。胡法田因斗争,无故素对群众就有些不满,常存报复之心,就依仗乡长王正富的势,将郭树正在斗争时所分的一亩五地、二间房,硬倒回。而乡长王正富竟不与处理,以致郭树正现赁房居住。今年正月胡法田建棚楼,私自将军属郭桂英地的两棵榆树砍去,用在自己楼上,而乡长王正富不与处理,反说现在已规划了还争什么哩,谁用了就是谁的,我遂后与你处理吧。可是,现在已三四个月了,尚没有处理,而胡法田反在门口说你告状哩,你告天天高,告地地厚,看我是不怕你告的,以致将郭桂英气成病了。……”[13]25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给毛主席“上书”以后,乡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
四、反对之声:另一封来信
1956年10月22日,内务部再次将晋城县西尧乡云台村来宗盛的信转发给山西省。信中写道:
“至从去年有云台胡安水、刘安福、崔吉文、崔吉武等四人为了套购国家粮食,河南供应的好,才迁移到义庄乡,留存半户,一家人分了二个省。因此,才和义庄乡干部提出争夺山林,想把云台归回河南,起初的主要根源就是这样。他们四户下山并没有向干部提过一句,当时云台群众并不知道。现在正在秋种,中间突然来了个划山,把云台划归河南,据双方政府说是中央批示,你们有代表。当时我们不承认,胡安水是我们代表。他是河南沁阳县义庄人,为什么能代表云台群众,不赞成。……”[14]26
来宗盛说胡安水等人是“为了套购国家粮食,河南供应的好,才迁移到义庄乡,留存半户,一家人分了二个省”。可是回过头来想,如果真的为了套购国家粮食,岂不要求划归河南更为妥帖?再者,来宗盛提到了“为了争夺山林”,姑且不论事件的本身,就拿这对立的理由来看,在当时人们已经把山林作为一种资源,山林上的土产成为大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最后,在此来信的结尾中特别写到“云台干部来宗盛”[14]32,可以看出,来宗盛在村里担任一定的职务,他的言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官方的态度。在地方上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胡安水为代表的民众派,另一派是以来宗盛为代表的当地官方派。再仔细对比,胡安水等人多次上书毛主席,且有人下去调查,在当地为官的来宗盛不可能不知道。假使其本人不知道,就其本身“上书”联名的签名来看,也有20多人,且多为男性,再加上其家室,按每户至少三个人来算也有60多人。据现存档案记载[15]33,三村一共加起来271人,云台一共是120人。其中与胡安水一同写信的多达近60人,占全村总人数的二分之一,这么大的声势,来宗盛等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不论如何,内务部再次站在全局的高度,要求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及其相关部门对此事调查清楚。最后,山西省民政厅给出的意见是:“你们给周总理的信已转给我们了,提出云台村划归河南省沁阳县的领导问题,已经国务院批准,九月中旬晋城给沁阳县又办了移交手续,按此地理条件和当地气候,划归河南省沁阳县统属,以为妥当。望你们耐心地说服不同意三地归河南领导的群众,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不论哪边领导都是一样的,希他们积极参加生产”[16]。从这一结果当中,可以看到,自然地貌和文化习俗最终实现了耦合。
五、结语
此三村的规模小,在经过长达两年的申请后,最终划归河南。民众最先发声,要求回归到河南去,可是当时的乡政府颇为不情愿,多给村民们“穿小鞋”。就是在群众的内部也分立为两派:一派以胡安水为代表,支持回到河南;另一派以来宗盛为代表,要求一直留在山西。与此同时,长治专署同意划归河南,义庄乡政府也希望能划归河南。这其中声音多元,涉及众多,而这背后却是反映了不同群体对待相同事情的态度,有来自底层的声音,也有中间的反馈,还有高层的指挥。
民众向上级反映自己诉求的理由,是我们着重分析的重点。里距、语言、风俗以及管理不便都赋予割属的理由,同时也是千百年来民众日常生活认知的坐标。正是这一系列的“坐标”,构成了民众对大自然的感性认识,进而,这些认识成为了区别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标尺。其实,行政区域的划分,正是人为地介入地理认知的过程。人为地树立标尺,而这一标尺恰当与否正是自然区划、人文区划与行政区划的“临界点”。
笔者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得到导师李嘎先生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1] 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J].复旦学报,2001(3):32.
[2] 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J].历史地理,2006(0):172-193.
[3] 乔素玲.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25(1):96-106.
[4] 徐文彬.社会史视野下的政区变动——以建国后松政县的两度分合为例[J].2013,28(3):77-87.
[5] 沁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沁阳市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6] 函河南省人委关于同意将云台等三个村划归沁阳县:1956[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06-86-04):2.
[7] 关于请转报国务院批准将山西省晋城县西尧乡的云台、风门、西东水三个村划归河南省沁阳县的报告:1956[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C64-06-86-01):4.
[8] 转去山西省群众来信要求划回河南省旧界问题请速处理:1955[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06-86-10).
[9] 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5.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2-33.
[11] 政协沁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沁阳文史资料(第4辑):怀药专辑[Z].内部资料,1991:9-10.
[12] 关于晋城县西尧乡的云台等三村“三定”留量扣除饲料问题:1956[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06-86-12).
[13] 希依据有关调查省界的规定上报《附抄张振威申请书》:1956[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06-86-18).
[14] 转抄沁阳县义庄乡人民政府来信一件:1956[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06-86-17):25.
[15] 转去宗盛等人来信,要求不把该村划归河南省管辖问题:1956[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64-06-86-20).
[16] 函宗盛同志关于国务院批准云台村等划归河南省沁阳县领导问题:1956[A].太原:山西省档案藏(档案号:C64-06-86-20):36.
(编辑:赵树庆)
A Study of Belonging to Henan of Yuntai, Fengmen and Xidongshui in Shanxi Jincheng County in 1956
QI Yu-long
(ChineseSocialHistoryResearchCenter,ShanxiUniversity,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Exploring the problem of district change in micro scale is conducive to more profoundl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complex “connection” behind the district change. In 1956 the villagers in Yuntai, Fengmen and Xidongshui demanded to be put under Henan’s administration. Faced with the above reques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such as the central, provincial, exclusive and township governments put forward their opinions, which not only embodied the social pi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but also showed the multiple interaction and game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between the seniors and the jun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mall-scale district chan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ltiple people and groups behind the event and draws the outline of different groups’ influence on district chang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istrict geography; Cutting and belonging; Yuntai; Fengmen; Xidongshui
2016-06-07
祁毓龙(1990- ),男,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K928.6
A
1009-5837(2016)04-00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