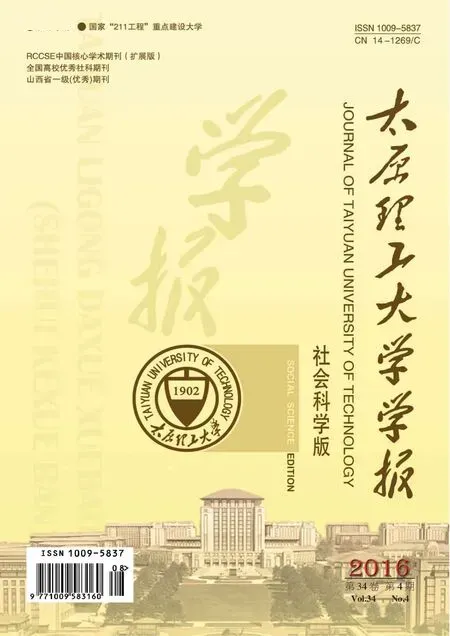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
——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2016-02-09张富利
张富利
(福建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
——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张富利
(福建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分权;多元权力中心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博弈对转型时期的法治社会形成尤为重要,但市民社会的理论进路却并不能建立在单纯的个案研究基础上,由一个个鲜明的个案再到理论分析的途径不通,所以形而上的研究是必要的。“结构容纳了权力。”[1]从国家—社会二元角度的分析,其意义在于重新审视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尤其是当民间礼治被破坏殆尽之后,“现代司法制度并不能承担起维护秩序的作用”[2]。只有充分理解市民社会对法治、宪政渊源的重大意义,才能明晓移植的西方法律发展方案与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断层,即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法律所赖以生存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共识尚未真正形成,我们至今仍不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因此,以个人主义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法律所赖以存在的大前提并不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社群主义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经坍塌,而新的社会结构、伦理共识和法律秩序却并未形成,在复杂的大转型中,虽有法律存在,却常有国家缺席,秩序的真空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尤其在乡野,乡村治理失败、乡村社会的灰色化问题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法律和乡村自身控制能力的双重无效,参见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一)市民社会与国家历史演进
独立的“中间阶层”对于现代政治国家和立宪主义均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也是传统中国改革失利的最原初原因,而在西方法治进程中,中间阶层社会演进的形态之一则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实体,它本身经历了不断的变迁”[3]。反映到学术研究和思想领域,则是从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到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托克维尔,再到20世纪初的思想家葛兰西,然后再到当代,市民社会始终以私人领域并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现代社会价值原则为中心,并且彰显出与国家共同体的不同,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间“建构性的张力”仍然是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所力图索解的问题。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也持续深入发展,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4]并不为过*之所以这样讲,其原因在于如果我们不仅仅因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正分离和对立发生于近代西方,就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视野局限于“近代”以降和“西方”,而赋予其深层历史反思性和人类整体关照性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社会出现私人利益和社会分裂为阶级,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产生的共同前提,即市民社会和国家人类走出天然自在的生命共同体,形成特殊的个人利益、阶级利益与公共利益、普遍利益相分离和对立的社会共同体的产物。。
从市民社会的渊源上看,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在古雅典城邦时代已经是重叠的存在,国家存在的前提即是雅典公民的私人生活,在此意义上,国家就“直接等同于社会”[5]。而传承了古希腊文明的古罗马,却从来都不会对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厚此薄彼,他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在两者共存的形式中,这两种领域才能生存下去”[6],即使是在“公民政治”特色浓厚的罗马共和时期,也是一种“走出蒙昧”的过渡[7]。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上,“罗马的盛世更在于统治阶层对平民力量的认识,以及整个社会对法律的绝对尊重与遵守”[8]。不过,良好政体必须依赖于中间阶层,因为“富人傲慢,而穷人邪恶”[9]却是颠覆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城邦的公民分化成富人和穷人,其结果要么是极端民主制,要么是寡头制,乃至僭主制。详见Christopher Rowe and Malcolm Schofiel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第18章:“Aristotelian Constitutions”by Christopher Rowe.。而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这种近似“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让古罗马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因为“它毕竟有封建‘契约’的关系基础,而且存在着多元权力的对立冲突”[10],在这个缺乏强权主导、蛮族割据和战乱频仍的黑暗时代,各个割据王国的发展远不平衡,呈现出软弱和非单一中心的特质,市民阶级必须联合王权才能足够强大进而与贵族和教会的势力展开博弈。随着“城市共同体运动”(communal movement)勃兴,“布尔乔亚”的崛起,商业、财产、劳动方式等市民社会构成要素日益独立发展,而“公民宗教”的理念开始形成[11]。公民宗教理念承接了古典政治理念,强调公民社会的政治功用,赋予政治社会以恒常性[12]。在此,“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条”[13]在各种政治场合角逐较量,最终以一种互有让步、相互妥协的方式共生共存,这种非暴力方式演进为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14],近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成长与个人追求解放、权利伸张也有了得以发展的土壤,对国家的立场是一种“纯粹的公民信念表达”*卢梭在1757年完成《爱弥尔》一书中,将其称之为“profession de foi purement civile”。,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结构的民族国家由此形成。从此,对于理论家们而言,如何为公民基础的政治国家提供道德和信仰根基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对此,卢梭试图在反政治的基督教和“国家宗教”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公民宗教;马基雅维利却主张对基督教进行“重新诠释”,使其“异教化”(paganization),借以获得后者在政治上的优势;而霍布斯则走的更远,主张回到《旧约》中的犹太传统,祛除基督教教义中对世俗权威的彼世信条,从而使基督教“解基督教化”(deChristianize),以“教士的王国”(Kingdome of Priests)取代“作为教士的国王”(Priesthood of Kings)。相关论述参见Richard Tuck,’The Civil Religion of Thomas Hobbes’,in Nicholas Philipson, Quentin Skinner,eds.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1-138.。随着西方逐渐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演进为“福利政体制度”,在福利国家与自由主义均陷入两难处境之时,“第三条道路”的结构化理论应时而生*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个世界上,旧的左派教条已陈旧不堪,新的右派思想苍白无力,第三条道路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的凤凰涅磐。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相关阐述,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113页。。“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任何宗教或者道德学说都无法再声称拥有绝对真理而可以建立对社会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支配,而只能满足于成为某种供人选择的价值。”[15]
不过国家与社会二者间的界分,并非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一种从宪政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并以该过程为条件而产生的一种现象”[16]。当代世界,包含人权、有限政府等价值的民主宪政已成为共识,国家和市民二者间的关系成为核心问题而被普遍关注。因为即使是发达的现代国家,只要其还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起作用”[17]。而国家无论如何强大,终不能将市民社会完全消解,国家存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绝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18],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博弈与互动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暗流,因为“搭建政府的艺术就在于如何在强大的主权者与公民权利的保护之间取得平衡”[19]。蠡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互动规律,便可准确剖析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建构的全部过程,找到当代国家种种难解政治问题的原因,“并看到各国现实社会在其中发展的政治形式和国家形式的前途”[20]。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才能“有效地透视法治的基础和界限”[10]。
(二)多元权力中心对现代社会的整合
市民社会的勃兴“改变了西方近代社会的全貌”[21]。关于市民社会的社会机制引发的法律传统的渊源与法律秩序的演进,学者给予了不同的结论*在韦伯看来,“理性主义”是西方法律秩序产生的主要动因,而在伯尔曼的理论体系中,“教皇革命”在法律传统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泰格与利维则认为市民阶级革命运动才是导致法律秩序出现的因素,而40年前曾掀起批判法学高潮的著名学者昂格尔则认为法律秩序的产生是“多元集团”同“自然法观念”有机融合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愈加认识到,法律传统与近代法治的渐进式形成是一果多因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才产生了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结构、观念变革以及理性文化要素,其综合作用产生法律秩序,为现代法治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
1.契约价值与法律至上
利益的平衡与调适产生法律,只不过其诞生伊始就承担了维护特权阶层统治秩序的任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发展是近代以来的事物,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日益分化,“契约性”复归将国家角色定位为保护私权的“守夜人”。但公共权力虽然被“契约性”复归,却与近代以来愈加膨胀的私人权益出现巨大张力。人权在文艺复兴后取得了无可替代的位置而成为普世价值,不论对其他平等主体的公民,还是对公权力的主体国家,“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行使这些权力”[22],如此,这些基本人权一方面成为公共权力行使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为公权力行使厘定了边界,成为规制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活动准则的最主要渊源[23]。在赋予国家行政、司法、军队等权力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也积极弘扬个人权利、分权制衡以制约公权力,捍卫私权。近代以来,不仅存在国家公权与个体私权的矛盾,还存在着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个人私权之间的张力,这种复杂的多元博弈呼吁恰当和平衡的规则,即调和fit和justification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Dworkin曾提出了对实证主义来说颇为头疼的挑战。其方案是一种建构性解释理论,实证主义的对权威的关切被转化为解释fit这个维度。法官作为法律帝国的君王,需要认真仔细调和fit和justification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最佳的解释。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然而道德的、宗教的、习惯的约束在这种多元博弈面前显然已力所不及,法律规则于是应时而生。而通过法治同时进行授权与约束政府与个人的双向作用,正是宪政思想的应有之义[24],法律的功能也由维系王权至上转向政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25]。对于权威的内涵及边界,法律的界说为“达到高层次功能分化的社会的迫切需要”[26],社会控制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求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的需求,而建立和保持这种平衡在现代社会中最有效的工具则是法律[27]。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是利益的目的物,它通过利益估算来衡平各方冲突。法律秩序存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类渴望矛盾调和、利益衡平,“因为他们希望保障他们本身的利益和承认尊重他人利益的正当。这种相互的权利义务观念是建设政治社会的基石”[28]。
因此,康德所倡导的普遍与持久的和平是其试图建构权利科学的终极目的*相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勒出的完美城邦,康德所要探讨的是未来的理想世界事关全体人类福祉和安宁的大问题。他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三条主要原则: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并提出了“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参见[德]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人类社会的文明秩序奠基于个人关系中“‘我的和你的’均依据法律得到维持和保证”[29],只有在强调规则、尊重权利的合法政府对个人专制的权力愈见减少的环境下,现代社会公共安全才得以建立,普遍与自治要义的法律应运而生,各种交葛的复杂利益得以调和,官吏通过公权力牟取私益的能力被制约,“它把最低限度的自由与安全和人们之间在财富、权力和知识方面存在的广泛差距结合在一起”[30]。由此,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博弈中,法律脱颖而出并获得至上性,法律治理得以形成。
2.公权力的分享与制衡
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是近代法治的核心,要求法律适用的实质平等性[17],而其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在于现代市民社会中多元权利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共同分享与强力制衡。这种粗疏看来是有“非政治”性的强大力量,却时时刻刻触及国家政治权力的领域,“使权力处于分立、分散的状态”[31]。公权力无法独大形成专制,转而与权利共生共存臣服于同一法律规则的制约。在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探索出以议会为各方博弈中心的新体制,通过议会形式将多元利益“遵从同一法律和权力”[13]。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多元博弈最终使法律至上的理念形成,多元的权力格局成为法治形成的一大关键因素,民主宪政原则也得以在多元权利与公权力的衡平与互动中得以建立和萌生。社会上没有特权的存在,现代化要求的对列之局也得以顺利形成[32]。“西方经过《大宪章》的奋斗,一直奋斗到今天,英美所表现的现代化精神,即是在这个对列之局。”[33]这个“对列之局”之所以在诸多后发国家仍是奢望,原因在于“如果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不来自民主授予也不对公民负责,那就会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从而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根本不可能构成对立”[34]。无论从道德考量的人性还是从理性角度的政治秩序构建,都必须要走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由个人主义走向自由民主*张奚若先生曾在1935年发表过两篇文章,非常透彻地剖析了人为何必须要走个人主义,为什么人不能搞集体主义。参见张奚若:《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个国家如果以集体来压迫个人的话,这个国家的结果一定好不了”[35]。
虽然有组织的群众活动,从古代到现在都为当政者所忌讳,尤其是东方国家,但实际上西方社会有结社自由,各种民间组织都受法律的约束,随时都有税务机关来查账,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美国为例,托克维尔说过,结社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美国自主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机制。他不无幽默地指出,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而英国则由权贵带头,在美国,公民有秩序、有组织的与政府沟通[36]。其法理依据在于,身份平等的发展趋势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与个体的同质化,个体在社会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公共理性成为个人行动的主宰;个人主义及温和的唯物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只顾专注于私人事务而变得冷漠无情,“社会权力的单一性、便在性和全能性增加了人们对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种种民主社会状态的迹象都表明了在民主的政治领域中非常容易形成现代极权专制”[37]。对此,可行的治疗方案则是通过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次级社团,形成一个非政治性的社会领域,从而对政治体系中的权力进行有效抵御。经过公民精神和道德文化的形塑,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公共精神得以弘扬,现代专制主义的弊端便被有效克制[38]。这即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进路,通过构造出国家与个人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来形成政治体系中权力分立和多样化的基础。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并非公民美德,而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以及相应的独立司法权和人民陪审制。社团组织自诞生伊始便作为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寻求归宿的渠道,发展到现代社会便以多元整合的权利纠葛、规范制衡的社会权力,以及异质独立的本质属性为表现形态,成为制衡暴政与专政的自治开放的社团组织,“免于控制和约束的”[39]自由空间由此形成。结社保证个人意见被充分尊重并能够得到持有相同意见的他人的支持,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团体力量,直接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从而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进行辩护、申诉而达到保护权利之目的,当下世界各民主国家对公民的结社自由提供保障的原因也在于此*参见国际法和各国法律对结社自由提供保障是民主社会的通例。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条,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一条,1969年的《美洲人权公约》第十六条等都对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做出了保护规定。国际法的宪政化还在萌芽阶段,但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均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保障结社自由。德国《基本法》第九条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权组织协会和学会,其《结社法》更进一步做了详尽规定。加拿大《权利宪章》第二节,以及南非1996年宪法第十八条也对结社自由做了比较宽松的规定。。在完成平衡“纵横四溢的个人利己主义”与专横暴虐的国家力量的任务同时,自由和权利得以伸张,现代公民社会所要求的自由理性秩序也得以形成。可见,“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是因为长期参与民主斗争的人民是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40],即多元市民社会组织。
(三)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与启示
多元权力中心的价值在于其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过程的始终。市民社会和多元政治格局的应有之义便是参与政治与提出反对意见的应然权利,作为公权力享有者的政府和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政治领袖均不能成为民众信任和忠诚的对象,民众所忠诚的仅是“支撑着这个国家的法律”[41]。建立在多元中心之上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存在可能,不仅在于拥有实在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政治道德对法治的绝对服从。这就将政治国家的权限牢固限定在为市民社会提供不同利益群体的行为准据,作为无规则的宪法便为不同政治利益团体设定优势或障碍而让制衡的精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世俗性权威不是某个人或群体的专利,而是城邦内所有公民的公益(public good),而宪政自由正是确保这种自由得以形成的关键力量。“就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绝对权力’来说,表面的强大往往掩饰不了其内里的虚弱和无能,这也许正是现代极权统治无法走出盛衰怪圈的根源。”[42]这样看来,以权力制约权力并不是在削弱权力,它毋宁是维护权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分权原则不仅能够防止政府的某一部分垄断权力,而且它是一种核心的政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新的权力不断产生,同时又不至于膨胀到损害其他权力中心或权力来源”[12]。如此,宪政得以水到渠成的建立,多元利益群体通过相互制衡与追求共识而达到法治,在此角度审视,法治也即“强加在私人组织之上的框架,又是从私人组织中产生的秩序”[30],将政治统治“消解为轻松地限制”[43]。
权力分立制约和法律规束,使权力运行置于法治机制之中。由简单多数拥有近乎无限统辖权的民主,有着侵蚀财产与法治的倾向[44],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其选择权的行使可能会导致利益各异的社会各集团在政府中所拥有的代表人数严重不平衡,出现较小利益团体无代表的情况。这必然导致代议机关的多数派恣意做出决定,甚至制定恶法去剥夺、侵害少数人的权利,从而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反人道专政。虽然从简单多数决定制的角度来看,它是民主的;然而从政治正义来看其实质,其与民主、宪政所追求的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远远背离,因为即使赋予每人以平等权,“多数人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人的才智高”成为正当化的道德基础,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局面必然形成。当公共理性作为个人行动的权威指导时,新的奴役便会出现。“历史的经验表明:多数人的专政则比个人专制更危险、更有破坏力。”[45]哈贝马斯也指出,“如果民主的意志形成不受到保障自由的分权原则的限制,这种意志形成就会变成压制”[46]。因此,以权力制衡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常态[47],民主宪制国家由此取代了绝对主义权力的“政治语法”,监督制衡的全新体系取而代之。民主是为了解决权利的归属问题,而宪政则旨在解决权利的运作;民主的结果往往是专制,而宪政则与专制水火不容[48]。在仰赖多元市民社会的全新度下,无限权力不再可能,“国家权力被多重分层化并又组合成一张相互监督的公共权力之网”[49],“权力的分散”[50]成为普遍原则,作为最高价值的人权原则才得以彰显。只有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确立通过法律制衡公权力的原则,野蛮和暴力才会远遁,“强制性权力才会受到限制。”[51]因而,权力分立与法治原则便是市民社会的应有之义,法律获得了至上的权威而无人能够超脱于外。而宪政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划定“私人领域”,厘定公私二者的边界[52],由是,多元权利的市民社会在完成对权力分割和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这两大任务后,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这两种力量都代表了现代社会人类的两大基本诉求,一种是发展,另一种是平等。作为现代文明重要代表的美国,其巨大的成功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取得平衡。“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对个人成就感的强调,很容易将这个国家推向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提供肥沃的土壤。”[35]如果这种趋势不受节制地任其发展,整个社会将会坠入一种“丛林”之中,道德堕落伴随着社会劣质风气的迅速蔓延*约翰.穆勒认为,自由的敌人除了强权之外,还有社会风气的力量,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同的本能,这种社会风气的力量比强权还厉害。参见[英]约翰·穆勒著,《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不需要多长时间,暴力革命和群氓暴动就会推翻这个制度,如同在许多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原来任何能够成为一种理性的政治力量,都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只会是乌合之众的暴乱,暴乱一起来,矛头不一定针对该针对的对象,只要邻居比他阔一点,他就可能去抢他的。真正的权贵富豪可能早就跑到国外去了”[35],而作为唯一按照社会契约原则建立国家的美国*经典文献《“五月花号”盟约》中这样写道:“……彼此庄严地订立本盟约,结成公民团体(a civil body),即政府(politick),以便更好地建立秩序,维护和平……”。英国虽然是最早的宪政国家,但长期保留王室,并承认其煊赫的主权地位;法国曾试图按照社会契约建国,结果却形成了暴力革命和极端专制的长期循环。详见《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5-67页。是如何减少这些社会矛盾的冲击,避免暴力动荡和暴力革命的呢?是通过市民社会作为重要推动力量的渐进式改革。在所有因素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对美国的渐进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是从市民社会的公共批评和大众抗议中不断产生出推动改革的压力,这些批评和抗议是在宪法保障的权利允许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其中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二是各界政府不断和持续地做出规范市场的努力,保护弱势阶层的利益和权利;三是非政府组织主导的慈善事业与志愿精神的实践。市民运动演进到现代社会的政治话语中,即为通过结社表达思想、发出声音,产生一个带有凝聚力的影响。比如2014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场参与者众多的大party,“很难成为媒体和群众关注的热点”,其原因在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有多么杂乱”[53]。最让纽约市长苦恼的是,这次事件的抗议者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也没有推举出来的领袖,更没有能够代表他们进行沟通对话的代表,他茫然无措不知道该跟谁去谈判,官方最希望有一个民众领导可以谈判。我们社会的反应显然尚不够成熟,假如是一个突发事件,大家无序地闹一通之后,当政者还可以容忍,甚至还能给出比较优惠的补偿,“但假如比较有组织地选一个代表,比大家水平高一点的人去谈判,这个人十之八九就会被抓起来,不允许有这个领导。官方宁愿与乌合之众打交道,却不愿面对有秩序的民间组织”[35]。这样高压的做法短时期内卓有成效,但是在长期看来却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真的大乱到来之时,那便会一片混乱,人人找不到南北。这就是有没有民主传统的不同。显然,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市民社会所拥有的长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个体的公民是主要责任者,而国家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和角色,国家出场的原因仅仅在于公民有切实需要时才介入和提供服务,却从不主动干涉。切身利益受到影响的个人成为应对问题的首要行动者,其通过自我负责的行动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国家则在其提出请求或确实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为其提供所需的信息和必要的物资。小集体能解决的问题便自己解决,解决不了才一级一级向上求助。自食其力解决自己的事情天经地义,自己无力解决时求助上级也在情理之中,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公正的模式。同时这个模式也较为节俭有效”[54]。
中国当下处在社会急剧的转型期,在国家“依法治国”的大战略布局下,单纯照搬照抄西方的具体制度意味着“缺失了对中国制度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关照”,单一视角的研究得到的必然是“抽象的”、“概念的”简单中国,而非“具体的”、“真实的”复杂中国[55]。“在经历了文化断代之后又走向与西方共同的道路”[56],这显然是中国社会阶层构造复杂的一个原因。而其依托的内、外两个资源都有困难,一个资源是我们自己失落许久的传统资源,即使找回来,它中间也有一个断层,而且中国传统资源里面有多少是能够转换成现代性、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学习的西方资源,但是它最核心的精髓也很难完全学到的。因为它最核心的部分是个人、自由,而缺失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传统,建立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显然困难重重。“中国人常只知有家而不知有社会”[57],国之外就是家,“没有个人观念”[58]。国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仍然是传统的、东方的,而调整外在行为的准则却是西式的、嫁接的,在未能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渊源的基础上依赖机械性西式法律条文的推进,“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已先发生了”[59]。这就构成了当下中国法治的一大困窘:“我们的法律是与我们的内心世界无关或关系甚少的法律,我们的法律不是我们内心世界的道德律的外化,甚至连内心世界的道德律是什么还不甚了了——旧的已经破碎,新的尚未成型。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60]因而本文的意义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深层结构中,如何在经济与政治、自由与秩序、良知与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建构性张力”,而且,“探寻一条从当下的中国角度来看更为可欲和正当的社会秩序”[61]仍然将是未来公法理论、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四)结语
至于市民社会对中国宪法的映射,学理上传统宪法理论均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论为基础。在长期的权力垄断体制下,为避免国家的过度集权,才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也就被视为原则上应与社会严加区分的统治组织。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化,能够限定国家权力边界,通过法律明确国家公权形式的范围,“对个人给予最大的机会”[62],从而演进为一种“市民模式的宪法”[43],实现社会的自治及私权的保障。同时,社会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在法治意义上形成公法与私法不同的法域,在国家与社会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规则和程序,有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显然,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对长期以来中国宪法是“公法”的理念提出了挑战*宪法从原则上起规范作用仅局限于国家范畴内,不及于社会整体,自治的社会和自由的市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免于国家干预的私领域。因此,从文本意义上,很难说中国宪法是公法。。
[1] 赵旭东.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75.
[2] 王启梁.乡土社会的变迁与法治的困境[C]//苏力.法律书评(第十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6.
[3] [西班牙]萨尔瓦多·吉内尔.公民社会及其未来[C]//魏海生,译.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7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
[5] [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M].沈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6.
[6]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6.
[7] [美]詹姆斯·亨利·伯利斯坦德.走出蒙昧:下册[M].周作宇,洪成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589.
[8] 俞敏洪.我读《罗马人的故事》[J].信睿周报,2014(4):28-29.
[9] 黄洋.希腊罗马的城邦政体及其理论[C]//王绍光.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3-26.
[10] 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J].法学研究,2001(2):19-41.
[11] 汪晖.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40.
[12]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M].London:Penguin Books,1990:151-152.
[13]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程洪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
[14] 龙太江.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精神[J].文史哲,2008(2):156-161.
[15] 崇明.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审视[C]//许知远.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38-152.
[16] Ernst-Wolfgang·Bockenforde,State,society and Liberty[M]//Transl ated J.A.Underwood Published:Berg published limited,1991:147.
[17] 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C]//冯青虎,译.[英]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9.
[18] 强世功.自然权利与领土主权——从洛克到马歇尔的隐秘主题[C]//《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现代政治与道德(《思想与社会》第五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94-146.
[19] Emile Durkheim, Anthony Giddens.Durkheim on politics and the stat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86:57-59.
[20] [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王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0.
[21] 公丕祥.法治现代化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69.
[22]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M].陈云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74.
[23] [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56.
[24]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M].郑戈,译.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9-12.
[25] [美]斯蒂·M·格里芬.美国宪政:从理论到政治生活[C]//法学译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0-15.
[26] [美]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M].陆震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
[27] [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M].王检,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57.
[28]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董世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95.
[29]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93.
[30]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62.
[31] 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210-212.
[32] [美]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纪琨,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270-271.
[33]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6.
[34] 秦晖.共同的底线[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7.
[35] 资中筠.老生常谈[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128.
[3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陈玮,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448-450.
[37] 吴义龙.民主的条件、后果和限度——托克维尔问题[C]//苏力.法律书评(第十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0-112.
[38] 阿瑟·卡勒丁.托克维尔启示录:《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温和、政治与自由[C]//丹尼尔·贝尔,雷蒙·阿隆.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陆象淦,金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1-32.
[39] [美]梅路西.后工业民主的悖论:日常生活和社会运动[C]//谭晓梅,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0-22.
[40] 《先生》编写组.梁漱溟与毛泽东[J].信睿周报,2013(4):9-10.
[41]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册[M].刘云德,王戈,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11.
[42] 任军锋.“神佑美利坚”——“公民宗教”在美国[C]//《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现代政治与道德(《思想与社会》第五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58-93.
[4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93-97.
[44] 张富利.多数决民主的悖论及其与宪政的张力[J].东疆学刊,2013(4):80-86.
[4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8.
[46]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M].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06.
[47]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26.
[48] [瑞士]波恩荷兹.一个稳固民主的必要和充分条件[C]//布莱顿.理解民主经济的和政治的视角.毛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4-106.
[49] [美]亚当·塞利格曼.近代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C]//景跃进,译.[英]杰弗里·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8.
[50] [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制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M].李琼英,林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45-246.
[51]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64-265.
[52]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126.
[53] 刘斌.这是一场怎样的占领哦——直击“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EB/OL].[2014-11-01].http://www.infzm.com/content/64289.
[54] 於兴中.辅助性:一种宪政与发展的重要原则[C]//於兴中.法理学检读.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31-46.
[55] 周国平.横空出世的中国学术论纲[C]//邓正来.中国书评(第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2-56.
[56] 陈丹青.中国文艺是一部悲苦文艺史[C]//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组.犀利问道.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84-113.
[57]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8.
[5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香港:集成图书公司,1963:91.
[59]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60] 喻中.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9-200.
[61]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62] [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5.
(编辑:陈凤林)
An Analysis of the Stratum Foundation in the Society with Rule of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untry and Citizen Society
ZHANG Fu-li
(SchoolofLiberalArtsandLaw,Fuzhou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2,Chin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izen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in traditional China an independent power failed to appear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centralized power. The growth and decline and game playing in the evolution of citizen society and political state constitut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symbiotic interaction between citizen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gives birth to the ra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which brings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 value of the independent middle class to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society l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public choice”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state dominated by the pluralistic power center, which manifests individual rights, urges the ruling legitimacy to return to society and finally makes the power subject to the freedom by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itizen society; political state; decentralization; pluralistic power center
2016-08-08
张富利(1980- ),男,河北玉田人,博士后,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宪法哲学的研究。
DF03
A
1009-5837(2016)04-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