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深意:2008年以来中国新媒体艺术中的日常琐碎
2016-02-05韩雪岩
韩雪岩
别无深意:2008年以来中国新媒体艺术中的日常琐碎
韩雪岩
本文讨论了2008年以来中国新媒体艺术创作中的观念、类型和新的特征。通过对题材、风格、手法和主题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媒体艺术家以 “日常”为母题,对传统新媒体艺术创作的隐喻属性、创作手法和阐释模式进行了质疑。其中包含着对艺术史文脉中的 “日常”语词的重新定义与对 “技术”概念的重新衍义。他们对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的消解,以及对艺术体制和商业运作的拥抱姿态,与中国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的畸形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化密切相关。而在艺术方法与风格层面的模仿表征,又使2008年以来的中国新媒体艺术创作没有指向社会学意义层面的艺术隐喻功能,仅仅提供了艺术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的素材。
新媒体艺术; 日常; 消费主义; 技术; 世俗化
2012年12月22日马秋莎在上海多伦美术馆展出了三频录像作品《三部曲之:红/白/黄》(版数:6 时长:4’39’’)。人的血液、乳汁和尿液分别制成冰冻的砖块,在室温下逐渐消融,并显露出包裹其外的避孕套薄膜。然而,这并非是一件鲜明地指涉生殖伦理或女性主义的作品。同年的4月25日,马秋莎在接受《ARTINFO》采访谈及此作品时,特意强调:“因为它们太日常了,还是回到最根本的东西上来。牛奶、乳汁关乎生命,也是一种常见的营养供给。尿液每天都会从身体里排出,低头可见;血液跟人就更密切了,虽看不见,但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它带来的温度与动能。液体永远是鲜活的同时又是易逝的,不能抓住很迷人。”①可以说,这种创作意图正符合此次展览一目了然的主题:《日常观:一种生活实践》,也体现着马秋莎反复申诉着的自己的创作观念:“日常中有太多的东西吸引着我,使得我的创作没法离开‘日常’,脱离不了这个基础。”②
《三部曲之:红/白/黄》同样容易让人联想起关于身体的类型化题材。如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所提及:“因为身体与身份密切有关,因此身体成为了新近的艺术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大部分这类作品都通过再现来关注女性主义,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福柯强调身体作为强制性‘规训’或者‘铭刻’场所的启发,并且大量地利用了巴塔耶等作者和精神分析理论家发展的‘低俗物质主义’和‘弃却’的概念。”③尤其马秋莎本人也曾明确地提出:“过去我的作品中用到了很多身体或者身体局部的元素,所以这次我就想是否能做得相对抽象一些,提及身体的话就用一些其他的形式、而且又需要是很简洁的形式来表现,这一点,在《红/白/黄》中将体液冻成的冰砖上就表现得比较明显。”④这种素材的同一性,也让观者联想起2008年之前新媒体艺术家以身体为媒介所表达的抗争姿态与表达欲望。⑤
陈晓云等7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曾是中国以身体为素材进行前卫艺术创作的开拓者。在2006年的《当代电影》第6期,陈晓云明确地强调:“身体焦虑可以解读为转型时期身份焦虑和精神焦虑的某种征兆。……其背后则隐含着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意图。”⑥而在2008年10月《身体:规训的力量》一文中,他又陈述:“身体的规训,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向身体欲望的……身体的规训与狂欢,恰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⑦但类似的观点则很少见于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的明确表述。尽管马秋莎、陆扬、林科、陈天灼、陈轴、程燃、苗颖等新世代媒体艺术家都不乏类似的题材,然而关注“日常”更构成了酝酿灵感的同一特质。陈轴在CAFA的展示的视频作品《打女佣的屁股#2》,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肌肉的锻炼图景。然而,他面对刘礼宾博士的采访时,郑重地强调:“个体的挣扎是无效的。”⑧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解读,无疑与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呈现出彼此迥异的面貌。因此,新世代媒体艺术家的所谓“日常”影像背后的观念表达与创作意图,恰好构成了管窥当下中国艺术新趋势的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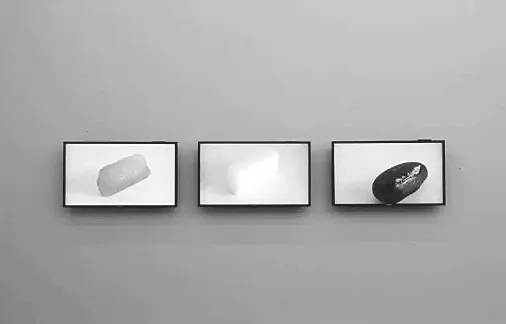
图1:马秋莎,《三部曲之:红白黄》,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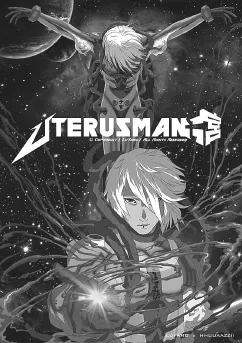
图2:陆扬,《子宫战士》,2013年
一、生活的琐碎表象
“日常”进入艺术创作领域显然是理论界早已尘埃落定的话题。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所著《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布里落包装盒出发,以维特根斯坦主义的反对者面貌,驳斥了迪基(Georg Dickie,1926~)的“艺术惯例论”和莫里斯·魏茨(Morris Weitz,1916~1981年)与威廉姆·肯尼克(William Kennick)的“艺术不可定义”等主张,并强调:“寻常之物被提升到艺术的领域,其逻辑的杠杆被我临时命名为艺术识别行为(act of artistic identifcation)……艺术识别的逻辑与非艺术识别在逻辑规定上是不同的。”⑨由此,丹托认为“日用品”之所以成为“艺术”源于艺术理论的“风格矩阵”演绎构成的可能性。可以说,丹托理论所阐释的历时性“关系属性”为“日常”进入“艺术”开启了“合法性”的大门。
这种对“日用品”的使用基本是中国早期新媒体艺术家所依凭的主要创作媒介。按照朱其在《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中的分期:“最早的录像作品是作为一种工具,作为对行为艺术的记录而诞生的。早期的中国录像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并没有像西方早期影像艺术那样关注媒介文化与社会政治,也没有同电视文化建立联系,早期的录像艺术家立足于纯艺术的立场,直接展开了对录像艺术媒介的艺术化的探索。”⑩然而这种观点稍显不够严谨之余,也明晰地表明:早期新媒体艺术家对“日用品”的运用,其方法论主要源自行为艺术与装置艺术。“日常”的概念被等同于“日用品”或历史性的具有特定文化、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常见之物,如张培力所表述的那样:“更多的是采用‘现成品’,其中一个做法是从市场上出售的影像制品中寻找素材。我关心那些符号性的、模式化的,有时间概念的因素。”⑪而从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来看,“日常”作为一种媒介与素材,显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1、关于“日常”中的身体
从展示的载体逐渐演变为主体,即身体成为艺术与美学需要阐释的对象与媒介。陆扬2013年创作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子宫战士》经历了动画、漫画和游戏等多元化的表达媒介。这件以“无性意识”为主题的作品,力求以“纯客观”的视角去体察身体,并尽量“不表达事物的价值与目的”。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陆扬鲜明地表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女权主义作品,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个超级英雄故事。人们会投射他们已有的想法。我的观点是,你出生时无法选择性别,性别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会成为一个问题。……老一代的艺术家真的喜欢创作与政治或国家有关的作品。但我觉得这种创作方法存在局限性。”⑫换言之,在陆扬的视域中“身体”就是身体而已,任何的价值观投射都是过度的附会与无妄的解读。
陈天灼的《ADAHA》系列采用音乐剧的形式,综合了绘画、装置、音效、光影和表演等多媒介技巧,以一种极度夸张的身体姿态和强烈的色彩冲突,意在创造强烈的感官刺激。然而在 《艺术与设计》杂志的访谈中,陈天灼却这样表达着自己关于身体的观念:你自己的肉体是很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我同样借鉴这种方式,就是通过一个很残忍的方式,其实说的是一个很直白的事情,就是你总有一天会是这样的。……肉体本身就是脆弱的,生跟死的界限就是如此地模糊。”⑬因此,他觉得自己的作品毫无价值:“这是一个工种,和其他工作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我无所谓观众能不能看到这一层的表达,他们无论看到哪一点都无所谓。”⑭

图3:陈天灼,《ADAHA》,2014年

图4:胡向前,《太阳》,2011年
胡向前的《太阳》大概是以日常中以“身体”为题材进行创作最具有戏谑感的代表作品之一。因为在广州天河城非洲商客聚居区的熟人关系,胡向前对肤色与种族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以身体为原料,以“太阳”为工具,通过持续长时间的日光暴晒,再通过发型的变换,将自己改造成了一名“黑人”。这幅作品曾被艺术评论界解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趋同尝试”。然而,胡向前自己在接受《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却明确地表示:“我以前做《太阳》,其他人都觉得这件作品可以能有很多延伸,……从社会学的角度,很深入地做更多研究。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没那个兴趣,我是个很没耐心的人,我觉得那样就够了。……我认为事情的表面其实挺重要的。……以日常生活作为创作素材,实际上是想在没有艺术的地方寻找艺术。”⑮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宏大叙事和深度模式解读的一种直接的反抗。胡向前本人就以嘲讽的口吻提及:“我不想把自己做成‘死的’艺术家”。
2、关于“日常”中的物品
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与张培力等早期前卫艺术家面对新媒介艺术的姿态不同。张培力在与艺术批评家吕澎谈及技术问题时,他强调:“我不清楚有朝一日待我熟练地掌握技术后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但现在,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接受‘技术’的恩惠,而恰恰是想对‘技术’以及由它带来的侵害进行一次清算。因此,我的无知似乎不是障碍而是一个资本。”⑯“即张培力寻求通过技术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概念的同时,又对技术怀有深刻的提防。”⑰因此,早期新媒体艺术家对技术的理解仅仅是附载隐喻与意涵的“日用品”传递媒介。而新世代的媒体艺术家的青年少年时代即伴随着BBS、WEB、和社交网络、APP等一同成长起来,因为“网络”等新媒体计划本身即是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的“日用品”。换言之,对早期新媒体艺术家而言是一种创作媒介与展示方法的“技术”元素,在当代语境中,早已成为了“日用品”本身。
2010年林科对电脑操作系统中的“文件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件夹伴随着鼠标活动的轨迹而移动,它的环境也会因为其背景的图片的更换而改变。这触发了林科对于人工智能生命的想象。“每个文件夹其实都是一种生命,文件夹在电脑中的位置就是一个宇宙中的位置。”2011年展出的网络艺术作品《鲁滨逊漂流记》即是这种想象的产物。林科通过不断地拖拽文件夹,并配以海浪涌动的声音,使新媒体艺术常见的叙事性和隐喻属性通通弃置,反而将文慧肢体课程的节奏与运动感融入到文件夹的移动线条与轨迹之中。这件在优酷网点击率高达17000多次的视频,林科将之命名为“光标舞蹈”。网络不仅仅再是工具,林科曾指出:“在通过电脑长时间的工作的过程中,我发觉了电脑界面非常拟人的特性,比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对文件夹进行命名;如果桌面的背景发生了改变也会导致环境的变化,这使我意识到一种‘剧场的可能性’。”⑱这种观点同时源自他直言不讳的判断:“我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上生活。”需要注意的是热爱自拍的林科在AAC的领奖致谢词中曾说:“我看起来会变成一个可以利用这种虚拟的工作去生活的人,就像一个开淘宝店的。”这与陈天灼对艺术创作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实际上,林科也明确地表示:“(艺术家)是一种职业、一种工作。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些艺术作品,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在网络上面的虚拟的工作。”⑲这种对艺术创作“去魅”与“消解神圣”的心态与互联网的时代与工具特质可谓极度吻合。
与林科同样引起全球艺术界瞩目的中国青年新媒体艺术家还有苗颖。2015年创作的《亲特网+》以中国“墙内”的丰富而独特的素材,中国特色的网络化审美与幽默感,以一种网民式的智慧和戏谑感,制造了苗颖本人宣称的“山寨意识形态”。《亲特网+》由:“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商业机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体验”五个部分组成。整个网站上充斥着当代中国网络商业语境过度夸张的广告式语言描述,强烈失真的PS图像效果,以及各种失去所指的图标定义与具体标志,其中还不乏指向明确的网红和不入流明星的动态效果图,目的在于“制造一个关于如何营销一个不靠谱的观念的教程”。在NEW MUSEUM的策展人与副总监劳伦·康奈尔(Lauren Cornell)采访苗颖时,她这样表述其创作的初衷:“都源自我的日常生活。我想做大家熟悉的、日常的。”而她本人则自称是“居住在因特网、局域网和智能手机上的网络艺术家”。这就将网络从工具提升到了生活环境的程度,换言之,“网络”即“现实”,“浅表”即“本质”,“技术”即“日用品”。在没顶画廊苗颖与策展人马修·康纳(Michael Conner)的对谈中,苗颖反复阐释了社会媒体代表的“超级素人”、“电子民俗”与当代网络发展所带来的“半屁股美学(Practical/Half-Assed Aesthetics)”,强调功能决定形式的一种“无审美”的网络审美趣味。而她认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网络即时性俨然是中国前卫艺术的崭新土壤,如其所述:“如果我是个画家的话,那中国互联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块独特的画布,因为没有其他哪个地方的互联网是像这样的。这些现实元素非常丰富,我觉得如果不加以运用的话简直是一种浪费。”⑳

图5:林科,《鲁滨逊漂流记》,2011年

图6:苗颖,《亲特网+》,2015年
迈克尔·拉什(Michael Rush)2015年出版的《新媒体艺术》在对文脉和当代创作进行回溯和阐释的最后一节《互动艺术:互联网》中曾明确强调:“五十多年前,艺术和技术就开始了进步,杜尚的革命终于在当代艺术的各种形式上得到了普及,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数字艺术的到来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艺术界抛开了对所表现的‘主体’在材料方面的讨论。……跨时空、跨形象的体验进入了艺术领域。互动性和身临其境般的艺术环境,会授予新的语词。”㉑对于中国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而言,“日常”作为关键词明显是释读的最佳路径之一。无论是“身体”亦或“用品”,在青年新媒体艺术家的观念中,无疑都呈现出了新的定义和概念内涵。而从“日常”这一语词的理解出发,新世代的艺术风格与趋势又呈现出诸多表征与特点。
二、新时期的特征
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与第一、二代新媒体艺术家的最鲜明区别,首先表现在对技术的态度层面。如果说,1996年以后随着PC计算机的普及和DV摄像机的广泛使用,艺术家们得以能够独自完成从拍摄到编辑的整个过程,Flash技术和HyperCard技术的成熟也使艺术家摆脱了对现实或虚拟戏剧性的依赖,在审美层面成为一种较为独立的艺术形态。那么,2000年以后,随着数码互动技术、游戏技术、动画技术、影像合成技术的全面成熟,新媒体艺术在技术层面还逐渐出现了类型化的倾向,可概括为互动式媒体艺术、还原式媒体艺术、语义式媒体艺术,并逐渐与戏剧、表演、舞蹈、音乐等艺术类型交叉融合,形成混合媒介艺术。㉒阿斯科·特罗伊(Ascott Roy)曾指出新媒体艺术与以往的艺术相比,呈现出全新的五个特征:“一、连接性:部分到部分,人到人,心灵到心灵;二、沉浸性:进入一个整体,由此消解主体与背景;三、交互性:作为形式的行为艺术已经演变为作为行为的形式的艺术;四、转变性:图像、表面与身份的不断流动;五、涌现性:意义、事件与心灵的不断形成。”㉓如果说这种判断的出发点仍然是立足于美国新媒体艺术的创作现状,那么,2008年以来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化技术浪潮则使这样的描述已然同构于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创作现状,至少在技术层面,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完全不同于早期的创作者面对“技术”的犹豫与踌躇心态。
张晓在《荒诞以及走失的日常性》中与采访者海杰饶有兴趣地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谈HOLGA相机与FOTOYARD网站对自己的影响,并郑重其事地表明:“来到了fotoyard,因为这里更纯粹。Fotoyard确实是个改变我人生的网站。”㉔苗颖与马修·康纳(Michael Conner)的探讨从“素人”(AMATEUR)和“超级素人”(SUB-AMATEUR)的新媒体习语与概念出发,探讨了自我表达与电子民俗(DIGITAL FOLKORE)之间的全新关系,并引用大卫·霍普金斯(David Hopkins)对社交媒体的趋势判断,以2007年iMovie和Final Cut的操作界面的系统变化,表达了自己对现代社会“现成软件文化”的深度思考。可以说,几乎全部的作品出发点都仅仅围绕着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嬗变而展开。林科则认为计算机的鼠标的点击、文件夹、公式算法都可以被赋予生命,其作品的收藏者绝大多数并非艺术圈的业内人士,而是从事IT行业的极客和部分声名显赫的互联网巨头公司的领导层。林科2014年获奖的作品《TODAY》,就是用影像记录了使用Photoshop软件对一张图像调整对比度、色彩渐变以及逐渐放大至分辨率不清晰的方形色块的过程,并同步配以霍洛维兹演奏的舒曼奏鸣曲《Kinderszen OP.15》。而在探讨创作初衷时,林科表示:“我用了一种方式去记录。因为photoshop这个软件本来是做平面的。我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做动态、影像的软件去使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这大概是诸多新媒体艺术创作的意涵解读中,最技术化并丝毫没有人文层面企图的一种表达。
这种对创作意图的阐释显然会带给受众“轻”的感受,即便是表达同样属于青年时期的颓靡与迷茫情绪。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也完全不同于第一、二代前卫艺术家的力求“深度”的思考模式。作为2004年就获得了古根海姆HUGUO BOSS当代艺术奖的国际艺术家,杨福东在面对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 Urich Obrist)的采访时,这样表述关于现实社会与个体感受之间的冲撞所带来的艺术创作起点:“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雄心勃勃,即便他们明知存在各种障碍—那些障碍或者来自当时的社会,或者来自他们自己。在《第一个知识分子》(The First Intellectual)中,年轻人受了伤,血沿着他的脸流了下来,他想作出反应、想反抗,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把手中的砖块砸向谁。他不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㉕这明显是将创作者置身于更高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俯瞰或重新审视所带来的一种批判性视角。杨福东本人即这样表达自己的定位:“我理解的知识分子是指受过教育、有思想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算是知识分子。”㉖—这无疑是精英主义的态度。类似的表述话语模式同样见于张培力、崔岫闻、徐震、汪建伟、陈秋林等艺术家的创作表述之中,即使他们不将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但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自觉和当代社会观察者与剖析者的潜在定位可谓一览无余。以至于吕澎在归纳20世纪初期的新媒体艺术特征时,笃定地强调:“影像技术的时间性被轻易地用在了对社会和相关问题的考察与提示中。有不少艺术家参与了这样的纪实工作,然而,他们对之前的纪实结构没有丝毫的在意,他们仅仅是关注影像记录中需要的那部分内容。”㉗即第一、二代新媒体艺术家对创作中的技术的关注度远远不及宏大叙事所带来的隐喻属性和符号属性。在这一点上,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可谓与之相反。
他们对宏大叙事的漠视与反感近乎构成了一种对前辈的反动。陈天灼拒绝对自己作品的过度解读,明白无误地指出:“艺术家干的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赚钱的事,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的艺术作品说有多大的作用,最后不过就是挂在藏家的家里,也成为一件作品,跟其他的工作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没什么特别值得说它多高尚的地方。既然都是干一个普通的工作,其实干什么都差不多。”㉘当采访者试图将话题引向更宏观的层面时,陈天灼坦诚相告:“赚钱对于人来说不都重要吗?艺术家也是俗人。”如果说这种将艺术的神圣性消解的姿态还过于直白,那么黄慧妍的表述则极具文学的清新色彩:“如果说有什么维系着我的创作,大概是我一直表达自己面对创作时那份无助,包括对创作的怀疑怀恨,是基于懦怯和悔气而继续的创作。或者具体点说明我和创作的关系,倒有点像陈腔的恋人絮语。我依赖他,我欺蒙自己我不能失去他,尽力地取悦他,努力留在他身边。”㉙这种创作观念也使得关于黄慧妍的展览评论、访谈和作品阐释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其“日常”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几乎表现于艺术家本人对“艺术”、“经典”、“博物馆”、“深度”等概念语词随时随地的质疑。胡向前在接受《艺术时代》的专访时,也严肃地指出:“对我来说,艺术没有真相,如果有也是表皮。柏拉图很早就说过,艺术只是真理的影子,哪有真理?我觉得他是不懂艺术才这样说,影子就是艺术,可是和真理无关。”㉚当面对提问者过于艺术史的采访风格和试图挖掘作品背后宏大的具有深度的创作意图时,胡向前拒绝明确表达创作的起点是否包含着对受众的启蒙与自我表达这类话题,他以调侃的语气阐述:“其实也不只是为自己还是为观众。很简单的道理,在银行上班的人,是为自己工作呢,还是为服务你呢?”—这同样是将艺术纳入日常生活的一种表述模式,既个人,又随意。

图7:胡为一,《两点之间没有直线》,2015年

图8:程然,《信》,2015年
更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互联网对生活模式的渗透,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中,还涌现出多媒介综合的创作特征和虚拟情境的题材。胡为一2015年在UCCA展出的新媒体作品《两点之间没有直线》采用了录像、装置和照片等多元化的媒介手法,呈现了艺术家本人从上海至北京的一段旅程。这很容易被视为一部批判当代中国城市化建设弊端的作品,但通过个性化图像在录像中的植入,使作品具备了某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而使作品更具备了非常文学化的个人旅行日志的强烈色彩。在接受《ART BANK》采访时,胡为一强调:“‘两点之间没有直线’中其实更加强调一种穿越和变迁,在路上飘忽不定的感受,并试图将这种体验转化成作品。……我并不想强调这些碎片的意义,或许它们毫无意义,我也不能刻意地去搭建一个意义。”㉛同时胡为一亦如其他80后新媒体艺术家一样,郑重地声明:“在做这个展览时我并没有考虑到‘公共性’,而相反的,我觉得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经历。我从来不觉得艺术家的创作要与民众发生关系,民众这个范围太广了,我没有这个义务和能力。”㉜陈天灼采用西藏传统的唐卡艺术和苯教仪式作为灵感之一,用以呈现纵情声色、颓废和粗鄙的世相。与其装置等其他前卫形式的艺术作品具备同样的COSPLAY特质,相对于现实来源的严肃性,陈天灼的舞台影像艺术毋宁说更具备网络化的虚拟情境表征。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的是程然。与电影明星刘嘉玲合作的影像艺术作品《信》,尽管在叙事情境层面非常接近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但传递的内容信息却是芜杂和错乱的。通过片段化的语言表述,将虚幻的MTV化的甚至王家卫电影式的叙事风格置于完全匮乏毫无逻辑的情境之中,创造出亦真亦假亦幻的荒诞都市的冷漠感。而对于创作的意图,他同样明确地表示:“我没有意图去展现一个针对所谓艺术史的观点,而是仅仅从本能中去寻找一种方式。”
从新的技术概念的衍义,到对新媒介技术的拥抱姿态;从对宏大叙事和深层解读的抵制,到虚拟情境与综合化创作方法,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由此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创作态度与作品表征。如果说这些新趋势的产生源自前卫艺术的内在困窘所导致的集体性创作冲动,如黄鸣奋所说:“艺术已经陷入困境,原因之一是为物质性所拖累。出路在于与信息科技联姻,前提是根本转变艺术观念:应当重视的不是如何使某种理念在物质性对象中不朽,而是如何迅速进行理念的动态交流。这自然而然地导向对新媒体的关注。”㉝那么,加州大学艺术史系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在《生物拼贴画》的判断:“如果20世纪80年代以强调身份政治学、陈述老套的主体性以便解剖与破坏它们为特色的话,我相信90年代最煽动性的‘身份’可以在因特网上被假冒,或者定位于蛋白质序列的水平上,这种序列太小、太抽象,以至无法舒适地与作为连贯自我之保证的连贯身体联系起来。我相信上述状况已经萦绕于艺术实践,在其中身体显示为性、物种与机器不确定的、杂种的混合。”㉞则这种论断可谓是对中国2010年以来新媒体艺术极为贴合的一种状态描述。但这种状态并非是没有争议和不值得商榷的。
三、作为素材的创作
如果说朱其在《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中面对新媒体艺术的最新趋势避而不谈只保留观察态度,那么几乎正式出版的关涉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的论文与著作都止步于2005年左右。这并非全部源自学者们的审慎态度。实际上,在公共空间和批评话语的探讨中,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及作品长期处于争议的状态。2014年7月在时代美术馆举办的以“青年叙事与现实”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刘礼宾、鲁明军和胡斌都对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提出了指责,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1、中国青年艺术家的体制化速度极快,既缺乏对既有语言和认知体系的批判与怀疑态度,同时又渴望在资本与收藏市场快速获得物质回馈;2、对日常景观的无节制想象,构成了愈来愈复杂的艺术叙事性形态,对严峻的社会问题采取回避态度,陶醉于个人感受的视野,缺乏艺术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以著名学者汪民安先生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是当前社会的顺从者”,“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看不到血性,他们全都遵从现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㉟
这些指责并非全无因果。至少在两个方面,80后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都有突出的行迹印证着这判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艺术圈既有体制和艺术作品变现的拥抱姿态。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自2010年以后呈现出频繁获得重要艺术奖项的状态。2012年王志频的《虫生》获得了第6界“Creative M50”的金奖。2013年林科获得OCAT的“皮埃尔·于贝尔奖”,并于2014年获得AAC“年度青年艺术家”提名奖。2013年程然获得了全球知名的Absolut艺术奖提名。2014年胡为一获得“华宇青年奖”等等。与传统中国前卫艺术家从体制外进行社会与政治批判,获得国际性声誉和市场,再返回中国本土收藏界与艺术批评界获得声誉这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路线不同,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一开始就基本没有对中国当代学院体制的批判性话语。事实上,他们几乎都是国内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并且至少接近半数拥有海外深造的履历,因此从语言到视界几乎与国外的博物馆、画廊、艺术批评界没有任何隔阂,稔熟商业化的艺术操作手法。
如前文所述,他们大多数也将这种艺术商业化视为“艺术工作”的一部分,从而消解了“艺术工作”本身的批判属性和反思因素。少数青年艺术家,还在经纪人的提携下如同声名显赫的“成功”艺术家一样,与电影明星等娱乐圈人士以及著名时尚品牌广泛地跨界合作,并娴熟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营销与推广。至少程然与香港明星刘嘉玲的影像合作使他的相关信息在国内主流门户网站滚动地播放。苗颖在《ELLE世界时装之苑》策划的“高跟鞋的力量”中,与其他女性艺术家一起,对Jimmy Choo、Roger Vivier、Dior、Christian Louboutin、Sergio Rossi、Fendi、Céline、Coach等全球知名时尚品牌进行选择并以之为主题进行创作。而《ELLE世界时装之苑》的“精致风格,引领优雅生活”的甜腻标语无疑构成了对既有艺术家严肃与深刻形象的暧昧挑战。
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家这种“世俗化”的生活做派延展于艺术创作,即构成了这个群体反复呢喃诉说的“日常”这一关键性的语词。这是很多艺术理论家保持批评态度的另一缘由。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1924~2013年)在对“日常”进入艺术进行竭力的阐释时,他引入了修辞、风格和表现概念三个语词,用以区别“日用品”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反复地强调:“对风格、表现和修辞这三个概念的交集进行研究,或许更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将这一点铭记在心,将使我们获得一个护身符,而不至于迷失在过于广泛的探索中,须知,这些概念虽然是迷人的,但同时又是艰难的,在它们每一个的背后,都有着汗牛充栋般的解释。”㊱从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文脉史来看,丹托这种从前卫艺术作品的表象出发探索背后隐喻的概念,基本上已成为艺术诠释新的“结构主义”模式,即使是面对一件“解构主义”的当代艺术作品。因此,当中国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明确表示:“日常即日常”,“日常”的背后没有隐喻仅是表象时,社会现实、政治喻像等常见的“解题”思路显然失去了阐释的既有模式。因此,从道德和品格层面进行指责,透过代际和社会地位的优越感进行非分析性的判断明显是最便捷的方式。
实际上,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至少在两个层面与前辈艺术家拥有彼此迥异的时代区别,其构成了他们艺术创作“日常化”的专属语境:
首先,在社会现实层面,至少与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密切相关。王宁先生在《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中指出:“消费主义是国家让渡的后果,是国家用其经济让渡换取居民政治让渡的产物,也是国家出于经济主义目标而借助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欲望加以刺激的结果。”㊲换句话说,消费主义在中国扮演着一种政治功能的角色。尽管消费社会本身只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中性的语词,结果却是2008年以来,中国的消费主义透过媒体的力量被营建为预设快乐、挑逗欲望、制造焦虑的工具。一方面消费主义旨在 “宣扬一种快乐哲学,远离规训与劳作”,避离沉重的思考与批判,另一方面受惠于电视媒介和无所不在的广告思维的影响,中国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早已习惯了“使用价值的分离导致意义的分离,意义的分离与传统文化中表面上意义的固定性是背道而驰的。为了使特定的任何一种品质或意义都能附加到任意一种文化产品之上,广告通过重新评估使用价值将所谓‘漂浮的能指’的效应发挥得淋淋尽致。”㊳这也是为什么新世代的媒体艺术家在作品层面日益强调“日常”,流连“琐碎”的物像,并具有MTV式样的“轻逸”乃至“轻浮”的原因所在。从更深的维度来看,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界惯性的寻找隐喻与深层意涵的“结构主义”思维模式,在大众媒体主宰的消费主义社会必然碰壁,因为“结构主义”的话语模式本质是一种二维空间的阐释原则,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却早以极具洞见力的视野指出:“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㊴中国消费主义的畸形蓬勃所带来的广告媒介与社会网络的爆炸式发展,如果说对于80年代以前的前卫艺术家而言,还只是一种观察和体验的旅程与经验,那么对于80年以后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来说,则是不折不扣地深入骨髓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在艺术创造的语言与文脉层面,中国2008年以来的新媒体艺术创造完全实现了创作方法层面的同步性。如果说:“上一代人模仿欧美的旧风格,比如何多苓模仿美国的乡土画家怀斯,罗中立模仿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画家克洛斯,徐冰对达达主义的模仿,方力钧模仿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伊门道夫,刘小东模仿美国精神分析画家佛洛伊德,王广义模仿美国波谱画家安迪·沃霍尔,艾未未对杜尚、波伊斯的模仿等等,年轻一代则开始模仿日本卡通画家村上隆、英国80年代“后感性”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加拿大观念摄影家杰夫·沃尔或者美国多媒体艺术家马修·巴尼。”㊵那么,受惠于移动互联网与艺术教育全球化的影响。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媒体艺术家已然极度了解如何与国际艺术潮流进行同步。这种同步性不再是时间的差序,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媒介知识与创作路径上的一致性。迈克尔·拉什(Michael Rush)在2015年出版的《新媒体艺术》中详细撰述的创作方法论,不再呈现出此岸与彼岸的空间与时间间隔。这必然使中国60~70年代出生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家失去了惯常使用的“后殖民主义”与“文化区域”等常用话语。当然,这也不意味着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媒体艺术家具备了可贵的原创能力。具体来说,林科的艺术创作手法显然与爱德华·扎耶克(Edward Zajec)根据音乐节奏展开的计算机图像如出一辙,对威廉·拉什曼 (Willianm Latham)的新媒体作品《形式的演奏》更近乎全盘的模拟,区别仅仅在于抽象图像与具象图片的背景差异。程然的创作与康斯坦丁·德琼(Constance DeJong)、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斯蒂芬·维泰洛(Stephrn Vitiello)的文本、声音与图像综合的WEB表达技法也并无二致。苗颖极具夸张色彩的互联网作品与谢丽尔·多尼根(Cheryl Donegan)的成名作《工作室参观》以及艾伦·罗伯斯伯格(Allen Ruppersberg)的《新的五英尺书架》在创作手法与思路方面以“异曲同工”来概括都稍显浮夸,实际上他们在新媒体作品的展示画廊、展览馆等场域都是同一地点。如果说,2015年在商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VR技术还在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创作领域没有体现,那么,只能是说,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或者已经毕业回国,或者在享受声名鹊起的初期兴奋阶段,以至于忽略了最新的技术潮流。
新世代的这些前卫青年艺术家与前辈们的区别,不仅体现于全球讯息一体化带来的艺术创作方法论的模仿间隙的快速弥合,而且体现于在当代中国消费主义带来的媒体文化畸形蓬勃渗入思维的规避思维与本能。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中国艺术批评界任何对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的公共道德与艺术家道义维度的指责,都偏差了方向并疏忽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审慎观察。
四、结语
哈佛大学闫云翔教授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详尽地阐释了“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模式(“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与“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对当代中国青年思维与行为的深刻影响。如他在对比分析中所揭示的那样:“个体努力实现自我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个人的身份认同很重要,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机会。”㊶这也可以解释新世代的青年艺术家为何反复地消解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并将关注的视角投入极为琐碎的“日常生活”,并略显庸俗地投入到体制和商业运作之中。因为唯有“日常”才能避免过度的建构话语和那些贫困匮乏的道德框限,在此之间维系和表达新一代的自我认知与艺术风格。从这一意义上来看,80年代出生的新媒体艺术家及其创作,并非指向社会学意义层面的艺术隐喻功能,恰恰相反,他们以“日常”为语词的作品及表述,仅仅提供了或者说成为了艺术社会学需要研究的素材亦或样板。
注释:
①②④http://cn.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801553/ Artinfo-China-Interview-Ma-Qiusha.
③(美)罗伯特·威廉姆斯 著,许春阳、汪瑞、王晓鑫 译:《艺术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⑤韩雪岩:《被规训的肉身:1996-2010年中国新媒体艺术中的身体喻像与消费主义》,北京,《中国美术》,2013年,第04期,第112-114页。
⑥陈晓云:《中国电影的身体转向—近期中国电影中的身体呈现与身体焦虑》,北京,《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第94页。
⑦陈晓云:《身体:规训的力量—研究当代中国电影的一个视角》,北京,《当代电影》,2008年,第10期,第66页。
⑧http://www.cafa.com.cn/ info/?NIT=54&N=3821.
⑨㊱(美)阿瑟·丹托 著,陈岸瑛 译:《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157页,第347页。
⑩张晓凌 主编:《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30页。
⑪黄专、王景林 主编:《张培力:艺术工作手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422页。
⑫http://www.qqenglish.com/bn/15219.htm
⑬⑭ http://www.artdesign.org.cn/?p=18885
⑮http://www.art-ba-ba.com/main/main. art?threadId=85154&forumId=8
⑯陶寒辰:《张培力:确切的快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⑰韩雪岩:《移植的肉身:1992-2010年中国新媒体艺术中的身体关注与美术现代性》,北京,《艺术设计研究》,2011年,第02期,第88页。
⑱http://news.99ys.com/ news/2014/0726/19_178522_1.shtml
⑲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5-29/7309858.shtml
⑳http://sanwen8.cn/p/2ceg5yA.html
㉑(美)迈克尔·拉什 著,俞青 译:《新媒体艺术》,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
㉒徐修玲:《中国新媒体艺术的类型分析》,南京,《艺术百家》,2006年,第1期,第138页。
㉓Lister Martin,et al, eds,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p.12.
㉔海杰:《表态:与十四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对话》,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
㉕㉖http://www.ionly.com.cn/nbo/5/51/20060812/ 094931.html
㉗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㉘http://collection.sina.com.cn/ cjrw/20141128/1609171755.shtml
㉙http://www.art-ba-ba.com/main/main. art?threadId=30531&forumId=8
㉚http://gallery.artron.net/20120613/n241626. html
㉛㉜ http://sanwen8.cn/p/274yFyl.html
㉝黄鸣奋:《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㉞David Joselit. Biocollage(J). Art Journal, Vol. 59, No. 3(Fall, 2000),p.44.
㉟http://culture.ifeng.com/ a/20140716/41175677_0.shtml
㊲王宁:《“国家让渡轮”: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广州,《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页。
㊳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利和生命政治学—身体转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281页。
㊴(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何道宽 译:《理解媒介》,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㊵朱其:《真正的当代艺术是一种没有中国特征的中国艺术》,南昌,《库艺术》,2010年,第14期,第45页。
㊶(美)闫云翔 著,陆洋等 译:《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42页。
注:本文为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面上项目:《中国当代新媒体艺术史(1988—2010)》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M201210012001)
韩雪岩 北京服装学院 副教授 博士
Only surface: “Daily Life” in Chinese new media art since 2008
HanXueya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s, types and new features of Chinese new media art since 2008.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opics, styles, techniques and themes, it displays that the Chinese new media artists born in the 1980s, starting with the theme “Daily Life”, questioned the metaphorical attributes, composition techniques and modes of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new media art cre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concept of “Daily Life “in the context of art history was redefined and that of technology re-interpreted. They dissolve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artistic creation and embraced the artistic system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onsumeris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imitative representation of artistic methods and styles has led to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new media art creation has lost its artistic metaphorical func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since 2008, only providing the materials required by art sociology research.
new media art, Every Day, consumerism, technology, secularization
J05
A
1674-7518(2016)04-008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