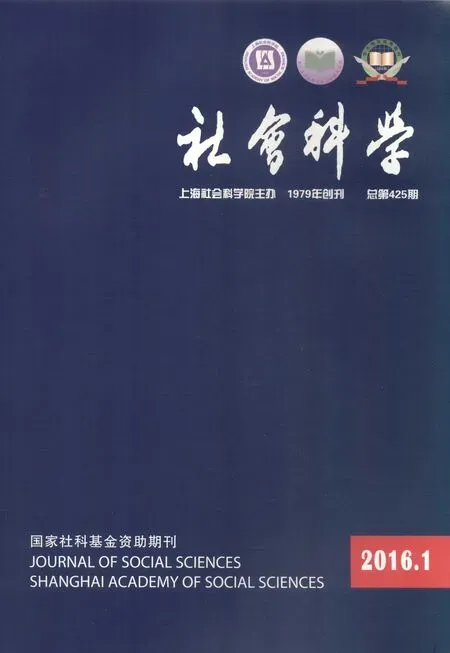胡塞尔的心理主义及对心理主义的批判*
2016-02-05伯特霍普金斯
[美]伯特·C.霍普金斯
胡塞尔的心理主义及对心理主义的批判*
[美]伯特·C.霍普金斯
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坚持心理主义,从《逻辑研究》开始,他转向批判心理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年反对心理主义的现象学“斗争”。《算术哲学》关注于集合逻辑统一性的起源:基数。尽管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与《经验与判断》中对基数客观统一性的解释是不彻底的,但这些解释却为《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提供了分析基础,使他能够辨析逻辑学心理主义、认识论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并对心理主义进行了集中清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心理主义的批判。《算术哲学》对未定集合和既定集合统一性的逻辑探究的失败,使胡塞尔不得不建立一个集合整体客观统一性的“构成”。但胡塞尔对全时性对象意义上逻辑纯粹性的认知被束缚于他对“数字同一性”的诉求之中。所以与其说胡塞尔指出了心理主义失败的原因,不如说他为知性对象意义“数字”结构的认知指出了唯一的解决途径。
心理主义;批判;对象一般;基数;统一性;集合;艾多斯数
引 言
针对心理主义的本质以及四十年反对心理主义的现象学“斗争”*① Edmund Husserl, 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 trans. Dorian Cairns (The Hague: Nijhoff, 1969); German text: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ed. Paul Janssen, Hua XVII [The Hague: Nijhoff, 1974], p.154.以下简写为FTL。所有的引用标记德文版页码,这些页码标记在英文版的页边缘。,胡塞尔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发表了一个声明,辨析了三种类型的心理主义:逻辑学心理主义、认识论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本文将论证,胡塞尔早期著作《算术哲学》*② Edmund Husserl, 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 ed. Lothar Eley, Husserliana XII (The Hague: Nijhoff, 1970);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Philosophy of Arithmetic, trans. Dallas Willard (Dordrecht: Kluwer, 2003).此后引用作 “PA.”中的心理主义与这三种类型的心理主义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非常明显,不仅胡塞尔的最终解释——关于现象学如何克服《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辨析过的三种心理主义——没有提出这种具有《算术哲学》特征的心理主义;而且这种解释对于思维客体数字同一性的诉求,如同它们超越心理状态的最终标志一样,代表了对于相同逻辑结构的一种诉求,心理主义在《算术哲学》中企图去解释这种逻辑结构但未能成功。也就是说,在《算术哲学》中被探究过的属于这种“真正”基数“多中之一”统一性的逻辑结构,也以这种“数字同一性”的统一性为特征,而这种“数字同一性”将诉诸于胡塞尔(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和《经验与判断》中)现象学对心理主义的成功解释。
我认为:(1)对知性客体数字同一性的诉求是胡塞尔反心理主义斗争成功的唯一方式,而非是其思想的破产;(2)胡塞尔将数字化的“存在模式”归结于客体的全时性意义,确立这种数字化“存在模式”特有的现象学优先性的合适文本是柏拉图未曾表达出的学说“艾多斯数”(arithmoi eidetikoi)的哲学重构。
界定《算术哲学》中心理主义的确切本质并不是一个简单任务,因为这部著作还不够成熟,书中的词汇例如act、presentation、concept、content和object,它们的含义多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其它的困难在于,这项工作需要通过胡塞尔的晚期著作以及和晚期著作不可分割的“历史性”的自我解释的双重视角进行。(从这个背景看,《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因其短暂的生命而表现得像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辨析这个最初的问题——《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是对此问题的回应,就像胡塞尔第一次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时,在《布伦塔诺意义上的心理反思》*Edmund Husserl, Entwurf einer “Vorrede” zu den 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1913), ed. Eugen Fink, in Tijdschrift voor Philosophie (1939): pp.106-133. English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Philip J. Bossert and Curtis H. Pete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p.34. 以下简写为“ILI”,所有的引用标记德文版页码,这些页码标记在英文版的页边缘。中的不确切描述那样。
一、 《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
在适合于多样性(Vielheit)*众所周知,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对“Vielheit”、“Mehrheit”、“Inbegriff”、“Aggregat”、“Menge”这些词汇的运用是不精确的(参见Hua XII, p.14, p.95, p.139, p.147n. 20)。的概念统一性(unity)之未定意义上和适合于既定总量的概念统一性之既定意义上,《算术哲学》关注集合逻辑统一性的起源:基数(Anzahlen),并回答了“多少(How many)”这个问题。对于胡塞尔而言,这两种统一性紧密相关,就像“多少”的问题被导向归入到多元化概念的对象一般(item)。在任意一种统一性的情况下,在《算术哲学》中,胡塞尔敏锐的意识到:“集合并非一个基于被集中在一起的诸多事物内容的客观统一性。”*众所周知,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对“Vielheit”、“Mehrheit”、“Inbegriff”、“Aggregat”、“Menge”这些词汇的运用是不精确的(参见Hua XII, p.14, p.95, p.139, p.147n. 20)。他在1913年就提出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是说,胡塞尔认为集合的统一性不是客观的。对他而言,统一性的客观性从来就不是问题。胡塞尔极度关注的是,如何解释适合于未定集合概念和既定集合概念之逻辑统一性的客观性。毫无疑问,理论数学方面的训练使他敏感于一个事实,在构成事实的任一方面,或者在属于它们性质和关系的任意组合中,奠定一个集合统一性的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算术哲学》中,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在布伦塔诺整体的“部分”——如颜色、广延、强度——统一的意义上),任何一个构成集合的元素组合都不能解释集合逻辑统一性的整体。
在《算术哲学》中,胡塞尔从集合自身的逻辑统一性中区分出属于一个集合的诸对象一般(items)的逻辑统一性,其动机简单的让人迷惑。属于一个集合的每个对象一般(item)仅仅在属于“任意事物”(Etwas)(或者像胡塞尔后期所讲的,“诸如此类之物”[Etwas überhaupt])的属类(generically)无所指概念范围内才会如此。那么,一方面,每个那样的对象一般(item)具有“一个”任意事物,即一个任意“单位”的逻辑状态。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整体集合的逻辑统一性并不是一,它作为一个集合,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具有共同统一性功能的诸单位(units)中的诸一(ones)。因为组成一个集合的每个诸对象一般(items)的逻辑统一性和具有单一性的事物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集合自身的逻辑统一性是多种多样的,胡塞尔认识到这两种统一性无法比较。因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仅仅在《算术哲学》中,胡塞尔认识到了诉诸于某些事物而非诸对象一般(items)的独立(并因此是个体)特性的需求,以便去解释未定杂多(multitudes)和既定杂多(multitudes)的逻辑统一。
为了解释这两种集合统一性(collective unity)的逻辑状态,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试图诉诸于合取(collecting)行为和计数(counting)行为,以及心理“反思(Reflexion)”行为来解决,而心理反思行为导向了由合取行为和计数行为所产生的集体组合表象(Vorstellung)。胡塞尔认为,合取行为最初产生了未定总量(Inbegriffen)或杂多(Mengen),计数行为最初产生了既定总量或杂多(以真正基数为幌子)。作为未定杂多和既定杂多产生的原因,导向集体组合(collective combination)行为的心理反思被胡塞尔用来(分别)产生了集合和基数的逻辑客观概念。与《算术哲学》心理主义的特征相关,这里有两点没有任何意义,第一点是,胡塞尔朝向行为的心理反思的诉求被用于解释属于两种杂多概念客观性的逻辑统一性,而这两种杂多概念在《算术哲学》的数学逻辑分析中得到过辨析。因此,那种反思显然没有被胡塞尔理解为等同于在灵魂中发生的客观性;第二点是,心理反思的诉求产生于胡塞尔的认知,即适合于集合或者基数逻辑统一性的特定杂多的统一性不能在适合于包含两者的个体对象一般的单独统一性中被解释,或者说不能以这种单独统一性为基础。
这些观点不值一提,因为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拒斥并没有蕴含对其回应的拒绝。后面的问题可以做如下简述:要么杂多,要么基数,其集合统一性的逻辑客观性特征不能源自于(或者归纳为)个体统一性(singular unity)的逻辑客观性特征,也不能源自于(或者归纳为)组成了那种统一性抽象基础的个体对象(individual objects)。事实上,胡塞尔关于集合统一性和个体统一性的逻辑独特性的主张蕴含了一个问题,即胡塞尔一直思考如何对心理主义进行现象学解决,那么这种思考是否提出了《算术哲学》的心理主义尝试提出(但却未能提出)的问题?因为从胡塞尔遵循的这个逻辑差别看来,每种统一性类型的构造行为都是有区别的。
于是,《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和集合统一性概念特有客观性起源的“逻辑”问题是不可分离的,这个问题在集合“统一性”概念特征的意义上是逻辑的,胡塞尔清楚地认识到它是非心理主义的,因此是客观的。为什么胡塞尔诉诸于“心理学”去解释他理解的客观性*参见Dallas Willard, “Husserl on a Logic that Failed”,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LXXXIX, 1 (January 1980): pp.46-64.; J.N. Mohanty, Husserl and Fre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2 f., and “Husserl, Frege, and the Overcoming of Psychologism”, in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pp.1-11; J. Phillip Miller, Numbers in Presence and Ab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pp.19-23.作者已经表明,在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纯粹逻辑学导论”中作为批评目标的所有特定种类的心理主义,在《算术哲学》中都并未出现。之统一性?当他考虑到这种统一性的特定非独立本性时,这令人困惑的原因就变得清楚明白了。按照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对于算术的关注,个体统一性与杂多统一性的逻辑不可通约性用算术的语言表述毫无争议,因为“多”与“一”在数学上是对立的。所以,组成一个集合诸对象一般(items)的物理性质和形而上学性质必须被排除,在它们独特性的基础之上,作为能够产生集合的逻辑杂多“统一性”的起源,在最初将这些诸对象一般组合成为集合的“行动”中,至少看上去其对起源的解释是合理的。导向那种行动的反思行为——从“内部经验”——抽象出表象,这种表象产生于心灵的自发能力,这种自发能力将组成了一个集合的诸对象一般“看作一(conceiving-as-one)”(Ineinsbegreifens),并且要么在未定集合、总体或者杂多的情况下,要么在既定集合、真正基数的情况下如此。随便拿一种类型的集合为例,正是构成了它们元(member)的“诸一”(ones)或“诸单位”(units)部分表象的相似性,与组成了它们部分表象行为的基本相似性一起,为抽象提供了一个基础。被抽象的东西分别是:多元化的未定概念和典型的(well-characterized)既定基数概念*see Hua XII, p.82.。
二、 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
我们指出这一点非常有意义:胡塞尔最初关注于《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以便去解释“概念”自身的起源,但这些关注显然并没有集中于对心理行为的诉诸。胡塞尔对这些关注点的表达清楚明白地承认了,导向行为的内在感知(反思)具有概念理解能力,尽管——这是事情的关键——他逐渐认识到,产生于导向集合行为反思的概念仅仅具有合取概念的状态。换句话说,胡塞尔对《算术哲学》中心理主义的最初关注并不意味着,他企图在“内在”(心理上的)经验的基础上去解释概念;而意味着这些分析并不承认,数字“概念”不同于合取“概念”,而后者,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所有这些都源自于反思行为[Aktreflexion]”。*ILI, p.127.完全引用如下:但是,基数的概念并非本质上不同于合取概念,难道它们都源自于导向行为的反思吗?那样的怀疑一开始令我烦躁不安,甚至使我备受折磨,当我后来提起它们时,将其延伸到所有的范畴概念,并且最终以另外一种形式延伸到任意一种客观性概念。参见Edmund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Hua XIX, ed. Ursula Panzer (The Hague: Nijhoff, 1984), pp.667-668; Log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J. N. Findla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0), p.782. 以下简写为“LI.”
按照《算术哲学》的观点,“和(and)”这个单词精确表述了集体组合行为的本质。这是因为,“一,和一,和一,等等以此类推”的结合,最初产生了——在未限定范围内的——未定总量和杂多,然后又(产生了)——在限定范围内的——既定基数。然而,一旦胡塞尔拒绝了导向行为的反思——这些反思充当了集合和基数逻辑概念的根源,“和”的“逻辑”基础将与其它逻辑范畴一起改变。正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六研究中所提出的,逻辑对象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对判断的反思中,甚至也不在对判断充实的反思中,而是在判断充实自身中”*Hua XIX, p.669/783, p.689/798, p.689/799, p.690/798, p.689/799.。相应地,不像《算术哲学》中结合了独立对象表象的心理行为,《逻辑研究》中的“和”“意味着[meinen]对象A和B的共同存在[Zusammen]”*Hua XIX, p.669/783, p.689/798, p.689/799, p.690/798, p.689/799.。并且如同胡塞尔在同一研究中提出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避免了“当代杰出的逻辑学家们所犯的根本错误,这些逻辑学家试图仅仅用称谓行为和命题行为的纯粹有意识共存去解释名称或者陈述的联言结合(conjunctive association),并将‘和’作为一个客观逻辑形式放弃了”*Hua XIX, p.669/783, p.689/798, p.689/799, p.690/798, p.689/799.。因此,“和”的逻辑状态和内容——它们是非心理学的并且因此是“客观的”——被胡塞尔描述为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有一个统一的意向联系被给予,并且与它相符地有一个统一的对象被给予。”然而,胡塞尔又意味深长的补充到,这个统一的对象,这个A和B的共同存在,仅仅能在“联结(binding)行为”中被构造,尽管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胡塞尔不再这样理解朝向行为的反思,在另一种语境下,他将这种东西指称为“集合本身的真正直观特征”*Hua XIX, p.669/783, p.689/798, p.689/799, p.690/798, p.689/799.。
对于属于集合自身逻辑统一性的建构而言,《逻辑研究》诉诸于联结行为在“事态”建构的情况下,必须被看作它也诉诸于行动。关于后者,胡塞尔写到:“只有在对表象[Vorstellungen] [行为]的联系结合中才能被构成”*Hua XIX, p.669/783, p.689/798, p.689/799, p.690/798, p.689/799.。这里,胡塞尔清楚地表明,涉及到的统一性不再被理解为产生于导向相关行为(act)或者诸行为(acts)的反思。这个内容值得注意,因为它关系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争议,即诉诸于行为是否代表了“逻辑心理主义”的“旧病复发”,而这种“逻辑心理主义”是心理主义在《逻辑研究》“导引”*在这里指《纯粹逻辑学导引》。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分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是第二卷的导语,又称《纯粹逻辑学导引》。中所批评的目标。此外,因为在集合行为和关联行为的例子中,对相同术语(“行为”)的使用很容易隐藏一个事实: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以及其所有后期著作中彻底区分了这两种行为(到后来,是指两种自发判断)和它们的相应客观性。在《逻辑研究》的用词中,涉及到合取行为的本质特征区分于涉及到判断行为的本质特征。对于行为中的本质区分而言,它们和它们相应客观性的本质区分相一致,和在合取行为情况中的未定集合与既定集合(这些后来具有数值的性质)相一致,也和在判断行为中事态的谓述形式(建立在个人感知对象的基础之上)相一致。此外,胡塞尔从后者的个体统一性、连结(copulative)统一性中区分出了前者的杂多统一性。
在提出与心理主义的关系这个更大的话题以前,我们需要先解决涉及逻辑统一性行为的构成角色,由此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声明是否是对《算术哲学》心理主义的回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一个更具针对性的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是:在《算术哲学》中,胡塞尔企图在导向行为的心理反思基础之上提供解释,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那么继胡塞尔——当然,不仅仅是他自己——之后,我们如何解释集合的逻辑统一性?
三、 《逻辑研究》对基数客观集合统一性的不彻底解释
《逻辑研究》指出了一个集合的客观统一性和一个事态(state of affairs)——胡塞尔直截了当地说“集合”*Hua XIX, p.688/798.“自身不是事态[nicht selbst Sachverhalte]”——的客观统一性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清晰程度与胡塞尔对分析的领悟程度成反比。这种分析关注于,与“和”相关的意向关系如何被关联到被引导的共同对象的相应统一性。值得关注的是,《纯粹逻辑学导引》对数字的分析虽然热衷于坚持对作为一个表象对象的数字和数字本身之间做出区分,但作为一个形式的观念种类(ideal species)却没有提及“和”。另外,作为一个对象的数字表象,至少在其真正表象的情况下,被胡塞尔明确表达为包含了既定杂多的东西。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胡塞尔的这个表述与《算术哲学》的分析是一致的。然而,被看作实证地表象了杂多客观性的数字与被看作观念种类——它是实证表象被关联对象客观统一性的原因——的数字之间,关系的确切本性并未被胡塞尔清楚地表达出来。胡塞尔认为,说“在表象中直观地被给予的是在某种清晰表达形式中的集合[dasKollektivum]和随之一个在争执中的数字种类的实例[Einzelfall]”*Hua XVIII, p.174/180.,并没有提出这个关键问题:数字种类本身是否具有非实证集合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观念集合或者形式集合的状态。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在没有澄清的情况下,说实证的一些事情是一些观念之物的“实例”,恰恰意味着一些问题尚未被提出,或者(虽然被提出却)很少得到回答。作为对象的一个数字的实证表象涉及到了——当在讨论中的数字被精确界定的时候——一个任意对象的集合。属于这个集合的“表述形式”被胡塞尔主张为观念种类的“实例”,而这种“实例”是表述形式“客观性”的原因。因此,提出下面的问题就水到渠成:观念种类自身作为共同实例化的范例自身是否是一个集合,尽管它是一个观念集合。也就是说,种类“五”是否是一个既定的,但却是一个观念的集(set),这个集由观念单位(ideal units)的总量(Anzahl)组成,而观念单位的集合同一性呈现了纯粹概念“五”?如果是那样的话,统一性的起源和属于观念集合的对象的起源需要被解释,就像在被实证性提出的集合的表述形式中将其实例化的“联结”*Paul Natorp, “On the Question of Logical Method in Relation to Edmund Husserl’s Prolegomena to Pure Logic”, trans. J.N. Mohanty, in Readings on Edmund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55-66.整个句子是:“在逻辑的超时空存在和它心灵体验的时空现实之间,一个联结,一个逻辑连接必须被建立。”的特征一样。如果每个数字自身的观念种类特征不是一个观念集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在什么意义上,一个实证集合能被理解为一个非集合的实例, 即“五”的非集合种类。这个问题显然非常急迫。
相应于《纯粹逻辑学导引》在数字分析中对“和”讨论的缺乏,《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对与集合讨论密切相关的数字的讨论也不深入。因此,超出《逻辑研究》的主张:事态统一性的连接本质(copulative nature)区分于一个集合自身的共同统一性,在连接综合形式的情况中,对于客观统一性而言,意向关系如何在事态的情况中从介质(copula)的综合形式中被区分出来,这一点从未被提及。
四、 《经验与判断》关于对象集(object set)构成的解释
我们能够理解,《逻辑研究》没有对一些分析进行足够的澄清,这导致一些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意向性关系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同构的。*例如:Barry Smith将A、B、C……之间的结合关系(onjunctive connection)与“某些范畴行为——在这些范畴行为中,我们从一些意识的、物质的对象转换到相应的物质种类或者普遍性”——对等起来。(“Logic and Formal Ontology,”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 Textbook, eds. J.N. Mohanty and William R. McKenn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dvance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p.29-67);至于Robert Sokolowski在“仅仅空乏的、认知地、言辞表达的意义上”的存在和在“直观意义上”的存在区分基础上“A和B”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将“A和B”当作了一个“范畴对象”(Husserlian Meditatio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8.); 但对于这种解释性倾向而言,显然也有一个例外,参见Dieter Lohmar,恰恰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相关,他指出对于胡塞尔来说,“集合(collectiva)不是‘事态’(nicht selbst Sachverhalte)”(“Husserl’s Concept of Categorial Intuition,”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Phenomenology, eds. Dan Zahavi and Frederik Stjernfel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125-145.)然而,在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的分析中,我们并未看到他得出那样的结论。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凭借重申对事态特有的客观性和集合特有的客观性之间的区分,开始对一个集合如何转变成为对象进行解释。与此相一致,他坚持“事态并非是在述谓丰富的自发性中建构的知性唯一的客观性”*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因为就集合本身而论,“对象集[Menge]”也被建构于“述谓判断”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同于事态导致了思维(sense)的逻辑形式这样的方式。这种差别主要关注于行为的前述谓层次,并且在此意义上,关注了行为的“前构成”层次,在这样一种层次上,定位于连接判断(copulative judgment)的客观基质被形成;而在一种更高的行为层次上,作为一种客观基质,集合体得以成型。两种述谓自发性的形式——“狭义”的交媾连接(copulative linkage)与“广义”的合并连接(conjunctive linkage)——被“建立”判断,并因此导致了在连同其内容的先在综合性行动基础之上它们各自客观性的前构。然而,胡塞尔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共同连接(collective linkage)“并不导致思维的逻辑形成,也不导致同样方式上作为连接自发性(copulative spontaneity)的客观基质中思维的沉淀”。作为“客观基质”的集合体不是在述谓自发性中被前构,这种述谓自发性“就像所有述谓自发性一样,导致一个新的客观性的前构,也就是对象‘集’的前构”*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这种集合体是在共同述谓自发性中被前构的,这种前构是“一个意识的意向性统一(noetic unity),但仍然不是在其特有本义上一个客体的统一,也就是说,在一个主题性的客观基质的意义上客体的统一”*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
集合体最初出现于胡塞尔指称为“感受域”*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之处,在其中“已经有了一种复合沉思[mehrheitlichesBetrachten]作为一个共同处理事物的集合体”。这里所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正在把握的一个接一个对象,而且是对一个接一个的对象进行一次又一次把握的一种悬置”。然而,在“共同处理对象的统一性中,集合仍然不是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在对象的复合沉思中,“对子(pair)、集合,更一般的说,两种对象的集”,确切说来不是被构成;而是“我们仅仅具有超出以往的一个前构对象,一个‘复合性’”*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因此,对于胡塞尔而言,“只要我们贯彻的只不过是同时把握的共同性[kollektives Zumsammengreifen]”,对集合自身——例如一个“真正的对象、可证明的同一之物”*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作为一个对象”*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的理解就并未发生。
对于集合,例如“对子”而言,为了被把握为诸如一个“A+B的总体(total)对象”,“我们首先需要把关注点做一个转向”*③④⑤EJ, p.292/244, p.292/245, p.294/246, p.292/245, p.293/246, p.293/246, p.293/245, p.293/246.,转到胡塞尔试图指出的“追溯理解[Rückgreifen]”之中,在这里,集作为一个“主题性的客观基质”按照它作为一个复合性“积极构成[aktivenBildung]”的前构被理解。
当我们能够指出,留意到的关注[Zuwendung]和朝向一个接一个的对子的理解是对象的时候,这种复合性的积极构成就出现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这种对于A,然后对于B的重复的个体关注[Einselkonzentration],这种专注的局部理解,将作为一种阐明,作为一种穿越了A+B总体对象的行为而起作用。*EJ, p.293/245, p.293/245, p.293/246, p.294/246, p.293 f./246.
仅仅在这种方式上,在胡塞尔称之为“复合阐述行为”之中,总体对象的组合能“被给予,以便可以在自我给予和沉思[betrachtend]中被理解”。胡塞尔接着将导致了集合的自我给予和沉思的“积极行为”描述为作为一个“集体综合(collective synthesis)”的整体对象。就此而言,举例来说,他将A、B、C的集体综合描述为“一个意识的意向性(noetic)统一,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一个对象的统一”。凭借“意识的意向性(noetic)统一”,胡塞尔理解到,“综合意识”在它的复合阐明行动中“包含了一个包括在统一性中的对象复合性”。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这里争论之中的意向性(noetic)统一不是共同性,所以,在“有着许多构成成分(members)的一个独特对象”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在真正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一个主题性的客观基质意义上的一个对象的统一性”。这个意义上对象的统一性应该仅仅在综合性合取(synthetic collecting)中前构,这种“(A, B)的表象[Vorstellung]优先于总量[Inbegriff]是一个对象的(A+ B)的集合”*EJ, p.293/245, p.293/245, p.293/246, p.294/246, p.293 f./246.。对于“最初起源于A和B双重解释”的“集体组合(collect combination)[kollektiveVerbindung]”*EJ, p.293/245, p.293/245, p.293/246, p.294/246, p.293 f./246.的前构复合性而言,为了成为一个客观“基质”,并因此成为一个真正对象,还需要一些东西即一个“追溯理解(retrospectiveapprehension)[rückgreifendes Erfassen]”*EJ, p.293/245, p.293/245, p.293/246, p.294/246, p.293 f./246.,这个“追溯理解”“伴随了综合(colligation)[Kolligierens]的完成”,并且借此,集(set)以一种“作为一个对象、作为可证明的同一之物被给予自我”的方式被主题性的提出。
如同胡塞尔所呈现的,被转换到真正对象的前述谓复合性的意向性(noetic)统一,和(假定意向性的[noematic])的集(set)的统一一起,与“产生于谓述自发性中的所有对象”相一致:句法的客观性在一个自发性中被前构,但只有在它被完成以后,才能成为一个主题,它只有在追溯理解中,才成为一个对象*EJ, p.293/245, p.293/245, p.293/246, p.294/246, p.293 f./246.。
五、 《经验与判断》和《算术哲学》对集合客观性构建的趋近
当然,集合客观性情况下前构的内容与事态情况下前构的内容并不一致,因为后者客观性的相关句法建立在前述谓相关综合的基础之上,而前者客观性的共同(collective)句法建立在前述谓的共同综合之中。继在复合阐明模式中凭借合取而形成的表象之后,集合自身成为一个主题对象(集),并因此成为一个客观基质。的确,除了确认这一点外,胡塞尔对以下问题毫不关心:追溯理解(rückgreifendes Erfassen)是如何把属于合取对象“述谓生成自发性”的意向性(noetic)“统一”共同转换到集合自身的意向性(noematic)“统一”的。集合的客观统一性必定具有一个对象的状态,这个对象在将其前构的合取中,以及在现在属于集(set)的个体对象的情况中凸显出来,而个体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统一性优先于集的构成,它被“综合意识”的(前客观)统一性所“包含”。拥有这种状态的集的客观统一之必然性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胡塞尔对《算术哲学》心理主义批判的论述;另一方面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统一性的特定特征所呈现的逻辑难题。心理主义批判最基本的原则是,属于逻辑统一性自身的内容不能被建立在导向心理行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内容的反思基础之上。关于这个逻辑难题,共同统一性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被某种性质所建立,这种性质内在于作为部分属于集体的个体组成部分之中,或者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之中。
换句话说,令人费解的恰恰是,意识关注(瞥见)的重新指向是如何能够将被集合对象表象的非客观统一性特征转换为一个诸对象之集合所特有的客观统一性的,这种统一性是“一个类于其它任何东西的对象”。关于这一点是如何可能的,不管是在《经验与判断》,还是在其它作品中,胡塞尔都没有提及。然而,胡塞尔认为,作为一个客观统一性的集合,“不仅仅能被总体上定义为一些给定模式的同一元素,而且能够在不断更新的同一性中被解释,而这个解释是一再重复的合取过程”。*EJ, p.294/246.
然而,这个问题背后有一种强烈的怀疑,即,借助于产生在共同构成对象之完整过程的“主题化”表象[Vorstellung],胡塞尔诉诸于追溯理解的能力去理解一个集合自身。对于心理主义的批判而言,这种怀疑恰恰是脆弱的,因为在《算术哲学》中,胡塞尔反对共同统一性所特有的客观性起源的解释。也就是说:不具有特定客观关联的一个综合性过程的结果,当把握过去事实的时候,仍然产生或者说催生了作为其特有客观关联的综合对象。严格说来,合取行为的客观关联被集合到一个杂多对象,而非它们的集合自身。关于这一点,胡塞尔的观点不仅清晰明确,而且一以贯之。在这些对象中,什么都没有,无论将对象理解为它们的个性还是理解为它们和另外一个对象的关系,一旦对象被综合,它们就被认为前构了它们所属的集合。这就是胡塞尔将集合自身特有的前构状态描述为一个“意向性(noetic)”统一的原因。争议中的统一性因此显然不是《经验与判断》阶段的意向性(noematic),《经验与判断》将集合的构成解释为一个客观性,也就是说,解释为一个能作为述谓判断中基质的对象。不过,与此相反,胡塞尔非常清楚,只有当被合取行为产生的表象而非它的客观关联(众所周知,这个客观关联指的是个体对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被主题化或者定位于一个“追溯性把握”时,才会发生。
对于主题化或定位的解释必须与胡塞尔在相关综合中所做的解释进行根本区分,而后者前构了属于事态的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前构的是一个意向地(noematically)被给定之物与其性质(或者诸性质)的重叠综合,这种重叠综合对于属于连接判断述谓特征的主题化和相应定位起着客观基质的作用。至于前构了集合自身的共同综合,如我们所见,在此意义上并无客观基质。相反,胡塞尔认为由合取行为产生的共同代现(representation)作为一个意向性(noetic)统一,前构了共同统一性自身。集合的“客观性”,也就是说,集的“客观性”,因此被胡塞尔描述为起源于先在统一性的主题化之中,这种先在统一性显然并未被展现为一个行为的客观关联。相反,正是在这种展示中,它与行为自身是不可分割的并因此成为行为自身的特征,而这种行为自身,正是胡塞尔所描述的集合自身的前构所在。并且,正是这种主张证实了这个猜疑,即,对于集合自身特有的客观统一性起源而言,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的解释并不比《算术哲学》中臭名昭著的解释更加高明。当然,在《经验与判断》和《算术哲学》中,胡塞尔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他用“综合意识(colligating consciousness)”代替了“心理行为”、用“追溯把握”代替了“反思”、用“意向性(noetic)统一”代替了“共同表象”,等等。但是,从一个事后关注到客体的(意向性[noetic])同一——它们发生于将其共同组合到一个“集合”的行为中,它们的基本解释不可避免保持相同,这引起了集合“自身”逻辑形式的(意向性[noematic])统一。此外,胡塞尔在这里的解释甚至没有提及,在合取对象的初始过程中,以及在结果的追溯理解中,意指(signification)和含义意向(meaning intentions)是否扮演了角色,以及扮演了什么角色。更确切说来,象征行为和它们的直观充实(用《逻辑研究》的语言来说)是否被包含在作为一个对象的集合的前构中(用《经验与判断》中的语言来说),而此对象是否被完成于合取过程中,或者被包含于它作为一个客观范畴形式的追溯把握中。这些问题被悄悄地忽略了。*Dieter Lohmar在他的《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概念》中简要提出了这些问题。
在这里,我们怀疑《经验与判断》对在真正意义上(作为一个主题化的对象基质,一个集)作为客观性的集合统一性构建的解释与《算术哲学》臭名昭著的心理主义接近。关于这一点,胡塞尔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关于复数(plural)“名词化”的评论是具有启发性的。在那里他指出,在复合判断中,“复数……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对象,不是我们做了‘哪些’判断的对象,因此复数名词不是既定基质的对象”。*Hua XVII, p.69, p.69 f., p.95, p.95 f., p.96.把复数转换为我们做了哪些判断的对象,转换为作为既定基质的对象,需要“运算”“在判断的形式理论中作为一个纯形式的理论”所发现的东西。胡塞尔认为,在此理论中,“借助于能被转换到关于集合单独述谓形式的复合判断形式,运算能够被提出”。他关于这些运算的术语指的是“名词化”。
这里,我们对作为一个客观性自身的集合的建构进行了解释,考虑到这个讨论的背景,胡塞尔关于名词化的描述有三点需要注意。(一)他既不关心关于集合自身的复合判断,也不关心关于集合自身的单称述谓,他所关心的是这些判断和述谓的形式。(二)胡塞尔给这种转换赋予了一个特征,它预设了作为复合判断的结果,集合已经被构成了。当他谈到产生了关于集合单称述谓(形式)的“运算”时,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在“名词化”中备受争议的不是关于集合客观性的构成。这种构成作为一个逻辑结构,其统一性区分于以下两种情况:(1)归于自身统一性的对象;(2)这种统一性被提出时的合取行为。(三)胡塞尔并没有描述这种运算,他认为这种运算使集合自身的一种复合判断形式发生了向单称判断形式的转换。关于这种属于名词化的运算,他的讨论关注于统一的判断形式S是P。他认为,这个形式“可以被‘名词化’转换成事态判断S是P,或者在P属于S的形式中转换为关于P性质的判断”*Hua XVII, p.69, p.69 f., p.95, p.95 f., p.96.。但是他并没有详尽描述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关于此讨论的脚注中,胡塞尔指出《逻辑研究》和《观念I》的一些段落处理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逻辑研究》中叫做“nominal formations”(Hua XIX, p.685/796),在《观念I》中叫做“law of nominalization”(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I,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Hua III, ed. Karl Schuhmann [Den Haag: MartinusNijhof, 1976], p.276;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First Book, trans. Fred Kerst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p.286.)
后来,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胡塞尔回到了名词化这个主题,他再次提及:“使其在判断中(以及在‘被名词化’中,在超凡的意义上[基质,即‘关于什么的对象’]被转换到对象中)显现的复数如何产生了集[Menge]”*Hua XVII, p.69, p.69 f., p.95, p.95 f., p.96.。如同在早期的讨论中,名词化在“判断形式的理论”这样醒目的标题下被描述,这再次意味着,集合客观性的前述谓构成,在被名词化的复数的讨论中,是被预设而非被解释。当胡塞尔承认“在实际述谓中,一个人可以不用立即合并生成形式[Gebilde]*也就是说,“形式”被合取和计数引起,其分别是杂多和数字。而合取和计数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胡塞尔在这里清楚明白的肯定意味着,“复数”在集合和基数的表象下,具有有别于合取和计数的状态形式,并且是如此优先于被名词化(在实际述谓的合并中)。与此相一致,胡塞尔继续说:“合取和计数是类似于述谓活动的 ‘对象化’(信念)活动。”*Hua XVII, p.69, p.69 f., p.95, p.95 f., p.96.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它们具有作为述谓活动的相同信仰模式,当它们指向所有可能的基质(诸如此类之物)时,它们的构型(formations)因此是相同形式范畴的模式。”*Hua XVII, p.69, p.69 f., p.95, p.95 f., p.96.胡塞尔并没有提及这些如何发生,也就是说,他没有提及,在作为形式范畴产生了集合自身的方式中,信念的共同形态如何被客体化。但是,他在一个脚注中注明《算术哲学》*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特别提到了关于“One and Something”的讨论(Hua XII, p.84f.),然而,这些没有提及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合取与计数。相反,被提及到的是一与多,和作为“所有概念中最一般的,作为形式概念和范畴概念的内容中最空乏的”基数,以及胡塞尔“在起源于导向心灵行为的反思这样一种性质概念的事实中”所阐述的这些“包罗万象”的特征。提及了这一点,弥补了这个缺憾。在那里他说:“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相同的东西。”但是胡塞尔提到了,“这些形式的本质属性是那样一些东西,它们所有都能够被合并到述谓判断和在这些述谓判断被给予的额外形式之中”。这些再次证实了我的观点,而非解释了作为一个逻辑结构的集合(和基数)客观性构成,而这种逻辑结构区分于:(1)合取行为(和计数行为);(2)组成了集合(或者基数)的个体对象,这些“名词化”的逻辑形式运算预设了客观性和它的构成。
六、 《经验与判断》对基数构成的不彻底解释
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对基数(Anzahlen)的讨论没有解决它们作为既定集合之“客观性”的构成问题,并且也背离了《算术哲学》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针对属于其概念无所指内容属类的(并且因此是普遍形式的)。《经验与判断》对基数的解释发生于胡塞尔对复数的思考之中,而对复数的思考是在他称之为“特称判断[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的标题之下产生的。特称判断区分于“单称判断”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因为后者“指单个的既定术语,例如‘这朵玫瑰花是黄色的’”,然而前者指“一些A或者一般[irgendeinüberhaupt]意义上的另外一些A”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因此,“‘一个A’的形式,‘一个A和一个A’的形式,或者,同样地,‘一个A和另一个A’的形式,‘一个A和另一个A,并且又一个A,等等,诸如此类’这种未定复数的形式”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是特称判断,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近于原初数学形式[Zahlformen]的起源”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我们之所以持这个立场,是因为胡塞尔的这些东西“在这里作为具有指称‘一些或者另外一些’[irgendein]作用的形式,已经出现了”。然而,随着“一些或者另外一些”和“未定复数”的形式指称,我们仅仅接近于和那种形式的起源相一致,但却未能够完全同一,因为对于胡塞尔而言,(在《形式与指称》中)“基数[Anzahlen]是特称术语的既定复数”。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当一个人“感兴趣的方向”从“涉及个体对象阐述的意向”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转换到“另外的意向形式”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时,特称判断就产生了。在个体对象的阐释中,意向在一种认可述谓展开的方式上被引导到一个个体对象,以便做出关于对象特定性质的“述谓性判断”。在特称判断中,一般而言,意向对个体对象的“个体特征”是“漠不关心”的,因为它“作为一种单一的意义形式——在这种意义形式中,它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仅仅关注于一个A或者另外一个A的同一有效性[Gleichgeltung]——被替代建构了”。因此,那样一个意向不再做出判断:“这朵玫瑰花是黄色的”,而是做出判断:“一朵玫瑰花是黄色的”,或者做出判断:“另外一朵玫瑰花是黄色的”,或者做出判断:“‘一些玫瑰花是黄色的’——一些意味着一朵又一朵的玫瑰花,等等。”那么对于胡塞尔而言,“这种生动活泼的态度决定了[特称(BH)]判断的生动性并且以一种特定方式使其充满活泼性质。”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种方式是“在这里具有指称‘一些或者其它一些’作用的形式已经出现了”之原因,形式使判断“接近于原初数学形式的起源”。
一种特称复数由“具有指称‘一些或者其它一些’作用的形式”所产生,当这种特称复数被描绘为一种“既定特称复数”partikuläre]”*EJ, p.446/367, p.446/368, p.447/368, p.446/367, p.446/367, p.445/367, p.445/367, p.445/367, p.446/368, p.447/368.时,并且当既定特称复数“在一种相应的概念—形式[Formbegriff]之下被引起”时,基数就出现了。“经由对比或者概念形成[Begriffsbildung]”的意义,例如,“一些苹果或者另外一些苹果(some apple or other)和一些苹果或者另外一些苹果,一些梨或者另外一些梨和一些梨或者另外一些梨,等等”,“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some concept or other)的概念—形式出现了。它出现于相比之下对象一般“概念上常见”的范围之内,“将自身表达为一些A或者另外一些A(some A or other)和一些额外的A或者另外一些额外的A(some additional A or other),在这里A是‘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胡塞尔清楚的表明:“基数概念2”意味着这种概念是“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和(另一个)“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的连接——并且,他继续声称:“3也是这样,等等。”
胡塞尔在这里将基数概念解释为既定特称复数,这些特称复数包含“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和“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等等,这并没有解决处于争议之中的集合客观性的构成问题。没有人说过,一个客观所指与作为某物的“集合”相一致,而这些“集合”要么与被“和”所组合的对象一般,要么与这些联结性意向的意向性(noetic)“统一”是不可通约的。那么,一方面,一个未定复数的客观性和既定复数的客观性都没有这样确立:它不同于属于两种类型集合的个体对象一般。同样,另一方面,争议中的客观性也没有被确立为这样一些东西:它包含作为对象一般的个体对象一般,而对象一般要么属于集,要么属于基数。不如说,胡塞尔的描述表达的是一种结合,这种结合由“一些对象或者另外一些对象”专有的特称判断形式(particular judgement forms)的“和”所达成,并且,在那样一种形式对比的基础之上,这种结合再次由“一些对象或者另外一些对象”专有的判断形式(judgement forms)的“和”所达成。胡塞尔声称,“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A],和一些概念[A]或者另外一些概念”的结合是基数2的概念,并且随着另外一个额外的“和”与另外一个A的结合,基数概念3产生了,以此类推。因而,胡塞尔对处于争议之中的“2”和“3”概念客观性的解释是失败的。
这种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和”的客观所指在未定复数和既定复数(基数)这两种情况中都未被确定。在这里,一方面我的意思是,这是对胡塞尔《算术哲学》心理主义逻辑问题的一种回应而非最终解决。集合的客观性,作为一种既不能建立于导向个体对象的述谓之上,又不能以其为基础的统一性,没有被解释清楚。另一方面我的意思是,《算术哲学》心理主义的缺陷没有被超越,因为《经验与判断》没有提供一种对“和”客观共同所指的清晰描述与表达,而这些却是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评所必需的。第二,J.N. Findlay指出,《算术哲学》中关于基数的解释在这里同样适用,也就是说,胡塞尔对组成了基数概念的既定复数之讨论“没有考虑到,在抽象事物集结(collected)的必要多元化中,什么东西被涉及到了,因为如果“一些事物(somethings)”是1并且是自身的话,“一些事物”和“一些事物”和“一些事物”不是3”*J.N. Findlay,《译者简介》,《逻辑研究》,第14页。。那么,即使在上述第一个方面,我所坚持的主张不能被继续保持,胡塞尔对意向性(noetic)统一——这种意向性统一显示在统一于既定集合之个体对象一般的联结行动中——的“追溯理解”之解释足以确立作为一个判断客观连接的集合之意向性(noematic)统一,对既定集合专有客观性的多样性进行解释,这个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就是说,有序整体不仅仅不同于所有其它的基数,而且(从上面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开始),它被相继关联到之前的基数,作为这种有序整体的每个基数规定性之原因的延异(differentia)不能建立在胡塞尔将类似元素描述为集合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最终,胡塞尔对基数的解释,与最后提到的关于元素的同质性相关,就“一般性” 的范围而言,《经验与判断》的解释背离了《算术哲学》的解释,这一点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引人注目。在《经验与判断》中,包含既定复数的术语是特定的,也就是说,一些A或者另外一些A,或者说,一些概念或者另外一些概念,意味着它们和形式的一般性相对照,而这些形式的一般性在《算术哲学》中却具有基数概念的特征。如我们所见,《算术哲学》对“和”的解释是:将其描绘为结合了诸如此类的任意对象,这些对象归于“任意事物”的一般属类无所指概念。实际上,在《逻辑研究导论》和《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对这些问题的自我诠释中,胡塞尔将属于基数概念的这些单位描绘为归于“诸如此类任意事物”(anything whatever)的形式概念,描绘为包含一些任意对象或者诸如此类的客观性。这些与《经验与判断》中被展示为属于基数概念的判断词汇形成了对比,也正是在《经验与判断》中,我们恰恰看到的是,它关注了一些概念,而没有关注胡塞尔将其称为“一般而言的任意之物”*EJ, p.452/372.的东西。实际上,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将后者指称为“一种彻底的新形式”,他不仅将其与特称判断形式相对照,而且还认为特称判断形式依赖于这种“彻底的新形式”。
七、 《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对心理主义的反驳及其基础
下面本文将对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对未定集合统一性和既定集合统一性所特有构成的细枝末节进行解释,特别是构成与《算术哲学》中声名狼藉的心理主义之关系,将被重点阐述,因为这是破解胡塞尔奥秘的一个极端的考验。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胡塞尔宣称,现象学诉诸于具有“数字同一性”的“一个原始证据”*Hua XVII, p.138, p.143, p.143, p.138, p.148, p.145.去克服心理主义,这看起来并不是症结所在。我们应该清楚,理想与现实的区别*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讨论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区分”相关,这个区分指的是《经验与判断》中的一个讨论,它包含了“代替这种区分的一个阐述”(Hua XVII, p.138n),并且指出,这种阐述在《逻辑研究》的“导引”中还没有进行。对于胡塞尔而言是一个“基本的,并且是原则性的区分”。它以“一个意向性基本规律”*Hua XVII, p.138, p.143, p.143, p.138, p.148, p.145.为基础,宣称:
毫无疑问,诸如此类之物的一些[Jedwedes]意识——这种意识先验地属于意识可能模式的一个开放性无穷流形[Mannigfaltigkeit],总是能在一个共同接受(con-posito)的统一性模式中被综合性的连结去造成一个意识,这个意识是一个“同一(the Same)”意识。对于本质上属于一个多元化明证意识模式的这种流形而言,它相应地适合于作为一个明证性,这个明证性要么是同一自身,要么是显然将其取消了的另外一个同一自身*Hua XVII, p.138, p.143, p.143, p.138, p.148, p.145.。
将“同一自身(the Same itself)”确立为,它在一个意识的综合统一形式下具有一些证据,这些证据的标志恰恰是它的——同一的——状态,这些状态表现为在由形式所结合的不同意识模式流形中的数字同一。就这些意识模式的流形是“暂时地相互外在于”“客观时间”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其“被视为现实人类的真正心灵过程的时候”,“是各自不同且相互分离的”*Hua XVII, p.138, p.143, p.143, p.138, p.148, p.145.。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被这种过程,即它们的本质特征,所催生的非现实客观形式[Geistesgebilde]排除了时空个性化。因此,在逻辑判断的情况下,胡塞尔指出,时间流形的超时间性*EJ, p.313/261, p.316/263, p.310/259, p.310/258, p.313/261, p.312/260.构成了“作为一种识别关联同一”*EJ, p.313/261, p.316/263, p.310/259, p.310/258, p.313/261, p.312/260.的统一性。判断行为的“相互关联[Verkettung]”*EJ, p.313/261, p.316/263, p.310/259, p.310/258, p.313/261, p.312/260.,在每一个时间离散中,都“进入一个包容性总体识别的统一性:它们被流形行为所组成,但在那里它们都具一个同一的判断性命题”。
对于知性的客观性而言,比起要么属于暂时离散行为,要么是这种暂时离散行为特征的“低水平”客观性,它是“一种高水平的客观性”*EJ, p.313/261, p.316/263, p.310/259, p.310/258, p.313/261, p.312/260.。与低水平行为的局部时空性相比,更高层次上的客观性在这种低水平中被构成,并“无处不在”,而且它们被“时间性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从个体客观性中根本性的和本质性的区分出了这些客观性”——的“永恒性”*EJ, p.313/261, p.316/263, p.310/259, p.310/258, p.313/261, p.312/260.赋予了一个特征。那么,对于胡塞尔而言,非现实客观性的总体同一性——它本质上被那些客观性的能力赋予特征,作为“同一的数值统一”*EJ, p.313/261, p.316/263, p.310/259, p.310/258, p.313/261, p.312/260.显现于一些时空位置——是一个“超时间统一性”的结果。胡塞尔主张,这个超时间统一性“遍布于时空流形,并在时空流形[知性对象]中被定位”。因为“超时空性意味着全时空性”,在这个意义上,“相同的统一性在每个那样的流形中被展示,并且它在本质上被展示于时间之中”,胡塞尔强调,这种被暗示的全时空性并不处于时间之外。时间中的全时空性,作为“一个时间性的特殊形式”,在“判断的什么,判断性命题”的意义上“在当下模式中被展示给意识”。然而,当展示给意识的时候,“它不在时间的一个点上,也不被一个单一瞬间、一个独立个体展示给任何一个那样的点”。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判断的“什么”被称为“一个心灵的非现实性”*Hua XVII, p.138, p.143, p.143, p.138, p.148, p.145.,因为它“存在于对于它们的意识而言属于各种客观性的‘超越’之中”。胡塞尔将这些客观性的意识定性为“随着同一(the Same)不同经验的序列与合成”,涉及“主观生命过程的重复”*Hua XVII, p.138, p.143, p.143, p.138, p.148, p.145.。就其本身而论,这些过程“很显然引起了实际上具数值同一性的显而易见的东西(不仅仅是十分类似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引起了显而易见的对象,这个对象在意识的范围内,经历了很多次,我们或许也会说,‘使其出现了’很多次(作为一种观念可能性,无限次)”。
这里,我们对《算术哲学》中胡塞尔的心理主义及随后他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进行了重新审视,鉴于这种审视,胡塞尔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所做的声明——这个声明是他在反驳心理主义时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引起了更进一步的推敲。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的,这个声明辨析了三种心理主义。首先是“逻辑学心理主义”,其特点是,它在“使其表象‘内在化’的基础之上”,“在行为意识自身”之中,坚持认为逻辑概念、逻辑判断等是“心灵事件”*Hua XVII, p.138, p.151, p.151, p.151 f, p.152, p.224, p.221.。这种类型的心理主义应该被现实与非现实鸿沟之间的“全时性”实体化所关照,我们想强调的是,在每一种非现实的数字同一性的基础之上,这种“全时性”实体化确立了,非现实“在现实中的可能参与[Anteilhabe]”,“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本质或者原则性的区分。”
其次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心理主义,它被胡塞尔赋予了这样一个特征,就它代表了“对逻辑心理主义异乎寻常的扩张和对其反驳的激进”这种意义而言,它是“心理主义观念的极致一般化”*Hua XVII, p.138, p.151, p.151, p.151 f, p.152, p.224, p.221.。胡塞尔将这种类型的心理主义简洁地总结为:“在特定意义上把客观性转换为某种心理之物的解释”,并且他提供了如下理由:因为“明显的客观性”“显然”“被意识特有的方式所构成”,在这种意义上心理主义否认“它们作为具有特定本质的一种客观性意义”,那么“它们[即显而易见的客观性]被‘心理分析化’了”。另外,胡塞尔评论说,“心理主义的确切[prägnant]意义将被相应的定义”。对此类心理主义的修正被“认为是普遍的(都是蓄意而为的)”*Hua XVII, p.138, p.151, p.151, p.151 f, p.152, p.224, p.221.,并因此“是类似于贝克莱和休谟坏的观念主义*将ideamism译为唯心主义是学界通常的译法,贝克莱和休谟属于唯心主义也是斗争哲学的一般共识,但这种哲学所导致的一个极端意义是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全面对立起来上升到一个“对”与“错”的高度,在这里,为了避免引起这种误会,我将ideamism译为观念主义。(lucusanonlucendo!)之基本特征的”*Hua XVII, p.138, p.151, p.151, p.151 f, p.152, p.224, p.221.,是“现象学的观念主义”。胡塞尔现象学观念主义至关重要的特征是“创新的思想”*Hua XVII, p.138, p.151, p.151, p.151 f, p.152, p.224, p.221.,“恰恰借助于对前述[认识论]心理主义激进的批判”,它得到这样一个特征,对于认识论心理主义的批判而言,它的基础是“一个明证的现象学澄清”。这种澄清的关键位于“每一个‘明见’,以及相关联的显而易见得以确认的每件事情”的“特有权力[eigenes Recht]”之中。
最后是“超越论心理主义”,它产生于可理解的然而却是“篡改的错位”*Hua XVII, p.138, p.151, p.151, p.151 f, p.152, p.224, p.221.之中,它“错误地把心理的内在经验当作依赖于超越地作为一个我思明证体验的内在经验”。这种误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一个篡改,这个篡改在先验现象学兴起以前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它的基础是“错位”,因为它没有认识到先验现象学所确立的真理,也就是说,它没有认识到既非“一个世界”,也非来自于‘外部’到达我的自我、我的意识生活可能种类的任何其它存在”*Hua XVII, p.138, p.151, p.151, p.151 f, p.152, p.224, p.221.。因为“一切外在之物都是内在之物,从其自身的给予中得到其真正存在,因此它属于这种内在之物:在我的(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讲,在我们的)实际和可能流形中作为一个同一性的标杆,随着〈它们的〉作为〈我的〉(以及我们的)能力的可能性:当‘我可以前往之时’,‘我能进行句法操作’,等等。”
八、 数学存在模式的“数理逻辑”结构及其特有背景
在心理主义的每种解释中显而易见缺乏的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对于组成个体对象一般的单独统一性特征而言,一个杂多专有的众多统一性逻辑概念的不可通约性。《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是对此问题的回应。实际上,针对心理主义的每一种现象学反驳,其中都明显存在着一种思想:从一个流形中,一个“数字的”统一性被“构成”,并且是以对于一个流形的个体内容而言不可通约的方式上被构成。为了一劳永逸地反驳心理主义这个逻辑怪胎,这种非现实客观性的“存在模式”因此被胡塞尔看作是数字的,在一种确切的意义上,一个整体以一个结构的统一性为特征,这种结构的统一性包含多元化的对象一般,它和多元化是不可通约的,并且也是不可分离的。
胡塞尔和他的注解者们都不承认在对心理主义的反驳中,所诉诸的现象学特征或者同一性数学存在模式的构成是知性的高水平对象所特有的。毫无疑问,胡塞尔认为属于每一个洞见及其相应明证性的“正当权利”足以确立(在导向被给予同一性的明证的超越反思中)对心灵现实必要超越的现象学根据。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正当权力”将会属于总体意义所特有的把握了数字同一性的洞见,而这种总体意义(在级联综合中)与构成了属于知性对象的全时性时空流形行为相关联。在对胡塞尔数字化对象全时性的解释这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中*Dieter Lohmar, “On the Relation of Mathematical Objects to Time: Are Mathematical Objects Timeless,Overtemporal or Omnitemporal?” Journal of 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Vol X, 3 (May-August), 1993: pp.73-87, p.83.,Dieter Lohmar公正地强调,“知性对象的全时性统一这种主张,与这些对象存在于具有独立边界的领域这个看法毫无关系”,但是他没有提及胡塞尔的数字同一性特征。
胡塞尔对全时性——这种全时性属于知性心灵上非现实对象所特有的超越意义——数字特征的诉诸是对它们“多中之一”统一性含义的解除。Lohmar认为,胡塞尔对那种意义上的范畴直觉深思熟虑后的解释背离了他早期的、相对的、一般通俗意义上的解释。这种早期解释旨在,在一个给予个体行为的不完全客观性重叠一致性的基础之上,确立知性高水平对象的结构。然而,那样一个解释最终证明是有限的,因其仅仅只能解释类的一般性,因为表现为一个意义重叠一致性的同一性之“艾多斯直觉”被建立于在个体行为中理解的不完全客观性中,并以此为前提。相反,胡塞尔深思熟虑后的解释并不包含那样一个预设,因为知性同一对象的全时性特征“依赖于与各自含义总体一致的可能性”*Dieter Lohmar, “On the Relation of Mathematical Objects to Time: Are Mathematical Objects Timeless,Overtemporal or Omnitemporal?” Journal of 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Vol X, 3 (May-August), 1993: pp.73-87, p.83.。用胡塞尔的话说:“对于所有这些行为及其模式而言,仅仅这些命题本身,作为一个同一性关联是同一的,并且作为一个相对一致的关联是大体如此的。”*EJ,316/263.
如我们所见,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将总体的一致性描述为基于“超时性”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现世地充斥于构成了知性同一对象的判断之流形行为中。在这里,什么是“多”并非意指一个相对统一性的个体行为,而是意指一个综合统一性的时间离散行为;什么是“一”不是一个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一些行为的个体对象中“被实体化”;而是一个意义的非个体化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一些行为中(在这里统一性发生)是“数字上”同一的。我认为以上所讲的意义全时性统一的数字特征在这里是有争议的,它关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这个整体与发现这些数字特征的行为是不可通约的,并且是不可分离的。
在此我想提出两个观点。第一,这个结构与真正基数的逻辑结构是同构的,在《算术哲学》中,胡塞尔企图凭借诉诸于对发生于共同组合行为中表象的抽象理解去解释这种逻辑结构。也就是说,胡塞尔对意义全时性统一的解释展示了一个逻辑结构,这个逻辑结构是“数理逻辑的(arithmological)”*Jacob Klein, “The Concept of Number in Greek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in Lectures and Essays, Ed. Robert B. Williamson and Elliot Zuckerman (Annapolis: St. John’s College Press, 1985): pp.43-52.克莱恩用“数理逻辑的”这个词汇去指称 “多中之一”的统一性结构,这种统一性结构使数学数和每一种“观念”概念成为可能。在下面我将声明,当胡塞尔面对心理主义之时,他恰恰诉诸于这种结构。理解胡塞尔这种诉诸的特有哲学背景是对艾多斯数(arithmoi eidetikoi)的重构,而艾多斯数“是柏拉图主义的,但柏拉图却从未表达出来”。,在一个显示了一种统一性的各类整体的精确意义上,这种逻辑结构在每一个使其统一的个体内容所专有的统一性内容中毫无基础。唤起对全时性统一意义数字特征的逻辑结构和真正基数的逻辑结构二者之间同构性的关注,我的意思并不是,在一个统一了精确限定的一般任意单位多元化之整体的精确意义上,这种全时性结构自身是“数学上的”。 当然,一个知性对象意义的全时性统一所结合的多元化内容和被算术数(基数)所结合的多元化内容决不是同构的。组成了这种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被“意味着”全时性的超时间统一性所充斥——行为的内容是意向性的,然而,组成了另外一种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被真正的基数结合——行为的内容是一般任意单位。然而,因为由基数所结合的单位的内容和在知性对象构成中所结合的单位的内容都无法以结合它们的各自统一性内容为基础,也无法被结合它们的各自统一性内容所述谓,被这些“高水平”统一性所显示的这个结构(我已经将其指称为数理逻辑的)是近于同构的。
第二,当胡塞尔将理解对象的全时性意义看作在流形行为中“数字同一”统一性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流形行为中,意义发生了),他所诉诸的正是我称为这种统一性的“数理逻辑”。这样,尽管在全时性对象的意义构成中那些行为的“参与”,这些行为和它们的现世个体内容都没有形成“遍及”它们的超时性意义的任何部分。并且,正是反映了基数结构的这些特征,也就是说,组成了它的单位杂多的统一性,在某种方式上从它统一性内容信息中排除了杂多性的内容。换句话说,正如一个知性对象的意义专有的统一性的内容最终不是个体的,然而意向这种统一性行为的内容正好是个体的,那么,基数的统一性也不是一个杂多(多于一),然而组成这种统一性的单位是一个杂多。
我已经说明,通过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我们看到他过去在《算术哲学》中对(未定)集合和(既定)集合统一性的逻辑探究没有成功的经得起标准集(standard set)的权衡。胡塞尔更晚一些的解释保持了对统一行为(无论是合取行为还是计数行为)更高水平理解的诉求,以便去建立一个集合整体客观统一性的“构成”。这个诉求未能满足胡塞尔的约定,即逻辑客观性的意义是一些“纯粹”之物,在精确的意义上,它意义的内容——“其本身”——在心理行为中排除了所有对开端与起源的所指。毫无疑问,胡塞尔认为他在《经验与判断》中对意义全时性的解释满足了这个标准,因为与其说在一个被展示为个体行为意向关联的一个对象基础之上诉诸于那种意义的起源,不如说作为一个流形行为意向关联的意义被保持发生。本质上被发现于多于一种行为的可能综合中,在这里争论中的意义有必要按照一个“层次”较高的对象去理解,而非按照被个体行为或者独立行为理解的客观性去理解。这些显然满足了胡塞尔的约定,即逻辑上纯粹意义的内容——本质上——必须排除所有源于个体行为和它们对象内容的所指。然而,胡塞尔对于全时性对象意义上逻辑纯粹性的认知被束缚于他对“数字同一性”的诉求,这种现象学情形仍然未被胡塞尔和他的注解者们所提及。
下面我用三点来总结这些评论。第一,胡塞尔诉诸于知性全时性对象意义的数字同一性,这种诉诸并没有提出它作为数字存在模式的结构,而是相反,用数字“存在模式”去证实全时性的归属。第二,对数字同一性的争议之中的“数理逻辑”结构之物构成的解释将与胡塞尔最初在《算术哲学》中所面对的问题相同:如何解释一个部分的复数——它要么是个别部分的复数,要么是彼此相关部分的复数——所组成的共同整体的逻辑统一性,既不能以它们仍然所属的整体统一性专有的群性(collectivity)为基础,也不能被这种群性所谓述。第三,与其说胡塞尔对心理主义问题的解决是失败的,不如说胡塞尔对知性对象意义“数字”结构的认知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个途径需要我们承认一个预设——这个预设是关于知性的全时性对象之意义结构专有的数学存在模式的,即,被所有认知所预设的逻辑统一性的认识是这样一些东西,它显示了一个优先于统一性的“数理逻辑的”结构,这种统一性属于所有的个体对象,也属于经验和认知生命存在(心灵)的时空位行为。像柏拉图一样,胡塞尔对于逻辑统一性可能条件的根本解释揭露了假定其“数理逻辑”结构的需求。对致力于证明和表达这种结构的柏拉图*柏拉图“未曾表达的学说”的决定性重构或许能在以下文章中找到:Jacob Klein, Greek 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Algebra, trans. Eva Bran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9; reprint: New York: Dover, 1992), pp.61-99. 这个作品最初在德国出版:“Die griechische Logistik und die Entstehung der Algebra” in Quellen un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Astronomie und Physik, Abteilung B: Studien, vol.3, no.1 (Berlin, 1934), pp.18-105 (Part I); no.2 (1936), pp.122-235 (Part II). 重构能够在以下页码找到:pp.64-95 of vol.3, no.1. 作为一个重构的纲要,参见Burt Hopkins, “Meaning and Truth in Klein’s Philosophico-Mathematical Writings”, The St. John’s Review, Vol. 48, no.3 (Fall, 2005): pp.57-87.“未曾表达出的学说”的重构能被用来指出这种“数字的”(arithmoi)全时性存在,这种全时性存在的结构不是数学的,而是艾多斯的(arithmoieidetikoi),胡塞尔在对知性对象数字存在模式的诉求中考虑过这个观点。这表明,这种数字的假定既不蕴含它们的形而上学实体化,也不蕴含“柏拉图主义”(如传统理解的那样),而是另外一个任务。
(责任编辑:周小玲)
Husserl’s Psychologism, and Critique of Psychologism, Revisited
Burt C. Hopkins
Husserl maintains psychologism inThePhilosophyofArithmetic, however he criticizes it fromlogicalInvestions, which begins the four decade “war” against psychologism. The problem addressed bythephilosophyofarithmeticconcerns the original of the logical unity of collects: the cardinal numbers, altough the accounts of objectivity collective unity in the acrdinal numbers inLogicalInvestigationsis incomplete, which provide an analyses foundation forFormalandTranscendentalLogical, which makes Husserl to identify three kinds of psychologism: 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trandcendental psychologism, and to clear up the psychologism, to some extent, which completes the critique. However, it is because that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inderterminate and determinate collective unity is not succeed in standing up to the measure, Husserl to establis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bjective unity of whole of a collection. Then, rather than signal the failure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sm, Husserl’s recognition of the “numerical” structure of the meaning of the objects of understanding signals the only way of resolve problem.
Psycholoism; Critique; Item; Cardinal Number; Unity; Collection; Eidetic Number
2015-09-10
B516.52
A
0257-5833(2016)01-0111-16
[美]伯特·C.霍普金斯,美国西雅图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 本文原为英文,经作者授权在本刊首发,译者为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讲师朱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