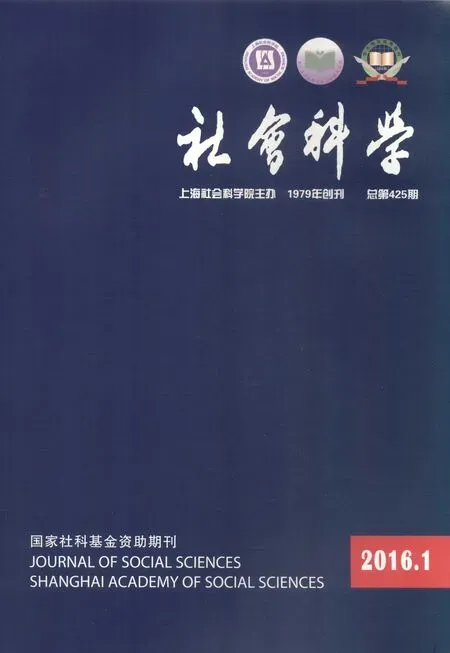底层的“少年们”:中国西部乡校阶层再生产的隐性预演*
2016-02-05李涛
李 涛
底层的“少年们”:中国西部乡校阶层再生产的隐性预演*
李 涛
中国西部底层乡校的“少年们”的反学校文化具有独特性,他们通过“瞧不起作为‘知识代言者’的农村老师表达对知识权威的抗争”,“在课堂中制造混乱表达对关系权威的抗争”,“在日常规定性作息中对规定性的时间权威表达抗争”,“在摄像头下采取剧场表演对敞视化的空间权威表达抗争”。这种反学校文化与威利斯笔下20世纪70年代英国底层工业城镇中学的“小子们”、周潇笔下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子弟们”的反学校文化相似又相异:首先,相比于“小子们”的优越心态和“子弟们”的自卑心态,“少年们”具有“屌丝”与“土豪”的交替性心态;其次,在对待知识和文凭上,“小子们”具有明确否定性,“子弟们”具有明确的肯定性,“少年们”却在话语言说和行为表达中凸显出非统一性和态度模糊性;再次,相比于“反学校文化”中对教育结构真相是否“洞察”,“小子们”达到了“局部洞察”,“子弟们”显然“没有洞察”,而“少年们”则具有“局部洞察”的痕迹。
底层;少年们;反学校文化;阶层再生产;教育筛选
一、 “小子”、“子弟”与云乡“少年”:再生产的三类当事人
再生产的理论研究大致有三种范式:一是作为“功能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的理论肇始于涂尔干,涂尔干认为教育转型总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和表征,学校是社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融合性机构。沿袭这一理论传统,当今的功能主义者大都认同学校即是一个传授和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知识和行为的再生产场所,是合理支持统治集团利益、实现社会整合和平衡的机构,在这个机构内,教育的目标是以共享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是一种促使个体按照适合维持社会平衡状态方式去行事的手段,功能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对学校教育功能可再生现存社会结构的价值合理化描述。二是作为“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理论发端于马克思和韦伯,理论前提是预设了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中个体和群体之间利益竞争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美]珍妮·H.巴兰坦:《教育社会学:一种系统分析法》,朱志勇、范晓慧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这种无可调和的张力实质上正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有产者总是使用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强制性权力来控制社会并对资源和权力进行再分配,而无产者则总是在抵抗强制性社会控制时通过阶级斗争来争取对资源和权力的分享权,这种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只可能使社会组织具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化属性,而教育正是有产者(统治阶级)实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学校则是在满足工具理性或者科层统治多维性控制原则基础上,对不同的特定群体传授特定地位文化的领地:或为精英所控制和剥削的领域生产温驯的劳动力,或作为理性的教育培养专家类型的人以适合特定的位置。相对于功能主义者关注“整合”,冲突主义更关注“分化”和“变革”,研究者认为通过筛选和分配功能,统治者对更高层次的教育加以控制,进而操纵社会,教育内部的这种冲突与对抗是由地位、文化资本、机会以及其他资源不平等分配所导致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教育紧张关系,只有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对学校教育功能可再生现存社会结构的价值批判化描述。三是作为“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理论,事实上无论是功能主义再生产理论还是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他们都更多是从中观和宏观的角度试图对再生产做出总体性解释与概括,更强调研究组织结构与过程,但其诸多内在逻辑勾连事实上却缺乏经验性研究材料支撑,现实个体、微观场所以及日常行为在总体性的理论叙事面前也是被忽视的,他们对个体本身以及个体情景化下的教育互动过程也缺乏关注,而理论发端于乔治·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和库利(C. H. Conley)对学校或其他情境下社会互动中自我发展的研究则开启了再生产的第三条路径——“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理论。该理论更强调在日常学校生活中去发现再生产的隐性逻辑,揭示在学校微观场域内学生同辈间、师生间等多元主体内部互动的复杂关系,从而在普遍性和平常性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再生产的真实内在状态,进而将微观观察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结合,寻找再生产的真实状态与深层逻辑。
笔者试图在情境化的微观底层学校内部,通过“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研究理论范式去探索底层循环的内生逻辑。2013年6月到12月,笔者进入地处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六个月的驻村研究,2015年8月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后续跟踪,希望藉此发现和揭示底层村落农家子弟们尴尬的底层再生产微观运转机制和日常行动逻辑。本研究尝试在与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中国学者周潇相关研究对比的基础上观察身处中国底层村落的云乡“少年们”。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toLabou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一书中所揭示的“小子们”(Lads)身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名叫“汉默”的底层工业城镇,被选中作为研究样本的十二名“小子们”都是汉默镇男子中学中的工人阶级子弟,他们是与“循规生”相对立的反学校文化生产者——违纪生,在“抵抗权威”、“建立非正式群体”、“找乐子”、“无聊与刺激”以及“性别和种族歧视”中逐渐形成所谓的“反学校文化”*[美]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威利斯发现“小子们”正是通过反学校文化,抵制学校教学目的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这与传统一般意义上泛泛论及学校通过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再生产了一批新的社会劳动者的线性决定论观点不同,这里被生产的新劳动者都是有血有肉而且充满主体意识的个体,他们绝非学校教育中被动的驯化者,也不是资本主义工厂体系中被注定安置的“炮灰”,他们有真正的主体性反抗意识,而正是这些细节上的反抗意识使他们在部分洞察教育真相的同时再生产了作为产业工人的自我。可见,再生产的内在过程充满了无穷的悬念与想象,并非如宏大理论一笔带过那般的轻巧,社会统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事实上充满了挑战。
而周潇在《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一文中所描述的那些身居2010年中国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子弟们”所形塑的“反学校文化”*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社会》2011年第5期。,则与20世纪70年代英国汉默镇中的“小子们”所生产的反学校文化形似质异,这是基于“制度安排”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威利斯笔下处于英国底层工业城镇的“小子们”是在对支配秩序的部分洞察与抗争中完成了自身的底层再生产,而周潇笔下处于中国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内的“子弟”则是在认同知识价值的自我放弃中完成了自身的底层再生产。
本研究则将理论触角深及中国西部最为底层的农村学校之中,去发现基于制度安排和社会条件差异因素,四川乡校的“少年们”与英国“小子们”、北京“子弟们”在学校场域中完成底层再生产、阶层循环的内部真实异同。
二、 云乡“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抵制权威与反控制
(一)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们:对“知识权威”的抗争
威利斯认为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在其行文中,对权威的反抗被定格为对教师所持有的常规价值观的反抗,但小子们对教师诸如勤奋、谦恭、尊敬等常规价值观的反抗并不涉及到对教师作为“知识代言者”本身的鄙视,相反小子们认为教师是高人一等和厉害一些的“大人物”,是比自己懂得多且更聪明的,他们的反抗仅仅是希望教师不要压着自己。周潇笔下北京打工学校中的子弟们则没有涉及到对教师的看法,但其文中所描述的七年级班主任经常对子弟们讲:“我经常刺激他们(子弟们),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你爸是收破烂的,你将来也是收破烂的,你爸是卖菜的,你将来也卖菜”;“现在是智者的时代,用脑袋的时代,要用知识武装自己”。从中可以隐约感受到老师们在子弟们面前的自信,因此也很难想象北京子弟们会瞧不起他们的老师。但乡间“少年们”则显然并不这么看待老师,他们不只是对教师所持有的常规价值观予以否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教师本身予以否定,乡间少年们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老师,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个层面的观点:
一是农村老师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他们仅仅是自身那批同龄人中的“淘汰者”而已。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老师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这些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我们这种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的。”
二是农村老师们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了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当他们确证自己身边的老师们收入水平还不如没读过多少书的父辈和乡邻时,便进一步毫不犹豫地蔑视起他们的老师来。“他们(老师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那些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瓜’(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刮大白是建筑室内墙面装饰的一种,也是普通住宅墙面装饰最普遍的一种,刮大白就是在水泥毛糙面上,用建筑用的大白粉、滑石粉和纤维素(一种化学粘合剂,易融于水)的混合物将墙面、顶棚填补、刮平、刷白。的赚得多呢,我爸在外边打工也比他们赚得多,还比他们活得潇洒,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得多累啊!”九年级男孩叶顾极富轻蔑地向笔者如是描述他们的老师。事实上,有的老师偶尔向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要通过努力学习,将来能出人头地而走出村落,但事实上却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们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社会交往能力不足。作为潜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乡间少年们在八年级即开始跃跃欲试奔往城市,他们似乎更需要职业培训、融入城市的文化*王玉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等诸项更现实的知识,而这些往往无法从老师们那里获得,父辈们为防止少年们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淘汰而沦为“书呆子”,则往往会或隐或明地向少年们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往往与老师们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他们(老师们)整天接触的都是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学生们,他们总是处于输出而没有输入的状态,那套陈旧的知识和他们若干届以前的学生那么讲,和我们现在还是那么讲”;“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那一套书本上的东西,在社会上又有什么用呢?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切……”。乡间少年们对教师这种观念上的瞧不起显然比威利斯笔下的小子们和周潇笔下的子弟们更甚,这显然涉及到对学校知识本身的轻蔑和知识所可能带来预期身份结果的鄙视,农村老师们的社会配置结构、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无疑使底层的少年们更容易从外在习得和内在确认读书的无用性,而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做好准备。
(二)课堂中的混乱:对“关系权威”的抗争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一再请求笔者帮她代一周课,她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们上课了,于是笔者进入到九年级教室中亲身体悟到了这个底层学校内部微观的课堂社会内所发生的日常底层再生产。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立刻引来了教室内38个少年的集体注意,新鲜感让平时上课从来都只睡觉和相互打闹的孩子们全部集中起注意力,但两天以后,他们又渐渐回到原有课堂节奏之中。因为笔者不是他们的正式任课老师,有部分少年甚至在课堂上开始偷偷地喝酒,当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的时候,少年们就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当笔者转过身来,他们则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此后,有的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则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当然也有的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他们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从而故意博得全班大笑。笔者在抽起他们中的一个来回答问题时,该少年把这种回答问题的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几分钟稍微安静的时刻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这对于曾任教于某直辖市著名中学的笔者而言无疑是一场全新的尝试,在大城市的一流中学中,笔者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全班同学都很顺畅地跟着老师的思维一步步完成教学任务、达成教学目标,40分钟课基本讲20分钟便可达到教学效果,随后的20分钟则主要用于提问、练习或者小组合作项目开展,但是在云乡学校中,这样的教学节奏远远无法进行,诸多环节只能被迫取消,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
笔者在完成一周的代课教学任务后与肖老师交流心得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们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就像在“自由茶馆”一样,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认同感。如果九年级是因为渐趋明确的升学无望而出现这种课堂消极行为,那么八年级会不会情况好一点呢?笔者抱着期待进入到八年级课堂中随班听课半个月,正如预期的那样,八年级确实相对于九年级来讲有所收敛,但尴尬的现实是,很明显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八年级少年们开始有了九年级消极课堂行为的潜在表现,始终跟着老师思维走的八年级少年日趋稀少,开始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隐性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而且呈现出学科结构性的差异,与九年级几乎全部消极课堂行为相比,英语和数学是八年级少年们最富隐性对抗的两门学科。
威利斯笔下的小子们也具有和乡间少年们相类似的拒绝学习的课堂特点,但小子们显然比少年们更甚,这体现在对“性”的隐喻上。在任何有关性的双关语出现时,后排的小子们都会发出咯咯的傻笑和故作惊讶的“哇嗷”声,并做出夸张的动作,事实上这种行为直接导向小子们的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女性和少数族裔被小子们视作低人一等,而正是在这种优越感中,男性气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才逐步成为小子们崇拜的对象,在对这种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心理认同中完成了小子们对抗学校文化中的底层再生产。周潇笔下的子弟们也有与乡间少年们类似的特点,但少年们课堂抵抗的手段显然没有子弟们那么丰富,他们没有手机可以玩游戏,没有钱可以赌博,也从不看小说,但他们和小子们、子弟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完全一致,少年们的时间也确实处于与制度化的学校和课堂时间相脱离的状态,他们不去计划时间、计算时间,也不期待用时间去交换将来的成就,他们的自我时间与固定性的时间规制完全不同。
(三)反规定性的日常作习:对“时间权威’的抗争
正如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言:“时间”并非仅仅指涉人们日常理解的客观“名词”,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各种时间性的社会网呈现出来的结构性“动词”*[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刘佳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可见,社会时间是社会群体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建构出来的结构化的社会行动网络,时间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社会组织中的权力结构关系。云乡少年们总是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问他们那为什么不按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呢?”“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他们(老师们)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说实话,我们不睡就是想寻找点刺激的事做,白天就像行尸走肉,晚上总得找点自由,所以大家才会晚上熄灯后偷偷打‘三国杀’、‘喝酒’。”“其实,我们晚上9点也不是睡不着,只是好不容易才有个稍微长点的自由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们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今天和一个同伴一起聊的那个话题,白天聊不清楚就又上课了,晚上总得继续聊完吧?”“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的做事,不自由了!”
确实,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追求“自由”和“刺激”,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这个主体性“自我”显然希望与来自于成人世界围绕“学习至上”价值观主导原则而制定的各种官方性规则展开隐性的冲突性抵制,抵制过程事实上正是再生产底层自我的过程,因为对于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四)“摄像头”下的剧场表演:对“空间权威”的抗争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对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处于摄像头监控的范围之内。比如,少年们曾经在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空地上随意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内绝对的私密空间,在这些私密空间内所做的违规行为,比如抽烟,与在公共空间中所做的同种行为相比对抗力小、主观过错更低,即便被老师发现也往往能从轻处罚,更何况这些私密空间老师们很少光临。当摄像头安装上以后,少年们的私密空间范围极度萎缩,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块被摄像头全天候监控的区域事实上已经“沦落”成为了公共空间,他们可不想在摄像头监控下赤裸裸地发生违规行为而被官方轻松发现,于是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这或许才是少年们真正自由和私密的完美空间。他们对摄像头下这块已然沦落的私密空间充满了无限的哀思,哀思的背后是对官方空间拓展行为的控诉,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示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故意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吸引摄像头背后的老师过来“抓捕”,但当摄像头后的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到:“拜托,老师,是糖,你来也一支?”摄像头下少年们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述“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少年们在摄像头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集体对这种空间权威表达抗争,有的少年故意去挑衅,而有的少年则故意装老实,当然,更多少年则在这种监控下选择用官方期待的规范表演行为来应对。他们会装作很认真学习的样子,会装作很符合官方需要的行为状态,来应对包括教师目光在内的“全景敞视主义式”的监视,空间权威在少年们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性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官方权力和公共期许自动地在少年们身上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时从“非正式性社会支持”和“正式性社会支持”两个方面*刘玉侠、陈翠萍:《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的社会支持探析》,《江淮论坛》2014年第6期。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形塑,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三、 云乡“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找乐子、无聊与刺激
(一)找乐子
少年们成天面对被课程表所包围的规训式学校生活与重复性的学业训练,他们需要在枯燥的日常学校生活中通过“找乐子”来感知自我的主体性存在,探索真正的自由空间。正如威利斯所言:“乐子总之是可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法子,乐子是非正式群体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则是正式机构特有的工具”;“乐子是反学校文化中的多元性工具,格外重要”。*[美]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事实上,少年们“找乐子”的本事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的小子们和北京的子弟们。诸如在常规性的找乐子中,他们不仅会在课堂上与不同学科的老师们周旋,不时冒出各种无厘头的话语、做出喜剧性的行为来解构课堂的严肃性,有的甚至努力与老师营造某种微妙的“哥们”关系,从而保护自身——在犯错时可以动用这种私人关系顺利过关或从轻惩罚。九年级杨朗告诉笔者他曾经在英语课堂中如何规避了老师的惩罚。十月的一天,刚和本班女同学张兰宣告分手的杨朗中午独自在宿舍中“借酒消愁”,之后去上下午的课,不料第一节英语课中便酒劲发作而渐渐无力支撑,他试图用英语书遮挡着头睡觉,但逐渐感觉到心里难受且越来越严重,而此时距离下课还有难熬的20多分钟,英语老师肖翩此时正在讲解英文中的一个从句的用法,用的案例正是杨朗所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杨朗此时借着酒劲突然站了起来,大喊一声“music”,之后开始边跳边唱这首经典曲目并迅速地向教室外的厕所移去。教室内的师生们刚开始被杨朗的突然性举动所惊诧,但很快又就被他夸张的舞蹈姿势和蹩脚的歌声所逗乐,在一阵哄堂大笑中杨朗得以达成跑向厕所的目的。当他再次回到教室时已经下课,英语老师把他“请”进了办公室盘问他上课时的疯狂举动,杨朗被迫交代。但杨朗有自己的法子,他将整个事件绘声绘色地描述,并故意用“单口相声”的诙谐口吻来自嘲自己的癫狂举动,年轻的英语老师被逗乐了,严肃紧张的气氛即刻烟消云散,于是杨朗在这种轻松氛围下央求肖老师不要告诉班主任老师从而把事情“搞大”,肖老师显然也不想过分为难杨朗,于是便在杨朗保证不会再犯此类错误的前提下让其回到了教室。少年们“找乐子”的方法不仅是一种解构日常无聊生活的办法,同时还是一种保护自身免受更严苛惩罚的办法,这种“乐子”是作为“弱者的盾牌”而被不断运用并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在课堂之外,我们也总是能够轻易发现少年们在校园“游荡”时所找到的各种乐子:他们故意将门卫和老师们摩托车轮胎上的气嘴给拔掉;他们总是在学校高大茂密的水杉树下寻找“马蜂窝”,然后爬上树取下来用火烤了吃掉;他们总是在晚上熄灯后故意继续说话而将生活老师吸引来,然后理直气壮地说自己都已经睡着却又被生活老师给吵醒了,等等。当然,少年们也不会局限于仅仅在“外界刺激”和“受害者”身上找乐子,他们也会通过彼此“嘲弄”来互找乐子。比如,少年们严肃地对一个刚刚上完厕所而回到教室里的同学说:“恭喜你,刚才老刘(班主任老师)请你去办公室。”等这位同学阴沉着脸快要走进办公室,并在脑海里迅速搜索究竟是哪一件事情已暴露而要遭到老师批评时,找乐子的少年们又会迅速地大声对着他喊:“骗你的,滚回来!”然后被骗的少年跑回教室追打欺骗他的少年。他们彼此取绰号,几乎每个少年都会有与其性格、行为、长相或名字有所关联的绰号,在绰号的基础上还逐步发展出一套只属于他们内部的话语密码和暗号。少年们还总是相互开玩笑说谁和谁“有一腿”,谁是谁的男(女)朋友。诸如此类同辈间的“乐子”不胜枚举,它们共同构成了学校内只属于少年们的真实生活。
(二)无聊与刺激
“找乐子”实际上是和“无聊与刺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找乐子是少年们寻找自我主体存在感和作为“弱者的盾牌”而运用的工具,那么破除无聊的刺激感则更多来自于暴力和偷窃。在云乡学校德育处,笔者翻阅了该校7年来200余份违规记录,明显可见少年们的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打架、破坏学校公物、翻墙外出、夜不归宿、盗窃、抽烟、喝酒等几类。其中,暴力型刺激则主要是打架和破坏公物两类,此两类事件几乎占据了云乡学校违规事件记录的一半。打架事实上被分为三类:
一是群体化有组织的暴力。此类暴力事件多为学校内部以“班级”或“帮派”为单位而展开的群架,他们会郑重其事地给对方发送“挑战书”或“邀请函”,并确定本方参与群架的时间和人员,同时要求对方参与者在“应战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按下手印以郑重表明应战,这是一种典型为摆脱无聊状态而寻找刺激的暴力斗殴。
二是个体之间的激情型暴力。此类暴力又分为偶发型和预谋性两种类型,前者更多是基于突发的矛盾和冲突而展开暴力,而后者则更多来自于长期积怨与寻找刺激。
三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报复性暴力。这里的个体往往是被群体成员所共同不容的个体,而暴力行为多被群体为“教训”、“给点颜色”之类的口吻而展开,当然也不乏群体为获得刺激感而欺负“弱小”。
“破坏公物”则更凸显出少年们对学校官方的反抗和挑衅,一般的少年们会在课桌上刻画出各种反学校文化的图案与语言,以表达不满和寻求刺激,正如他们将各种带有个性化的图案和语言用笔刻画在校服上故意从值日老师面前走过一样,而另外的一些少年们则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温柔的刺激,他们采用更为暴力的方式,如故意将门窗玻璃敲碎、把走廊上的灯用石子打坏、用热水将宿舍区的树浇死、把墨水泼到教室外边的白墙上、在教室黑板上涂“502”胶水等等。这是一种为摆脱无聊而寻求刺激的好办法,此种更为紧张的刺激感一方面更赤裸裸地表达了少年们对学校官方规训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将自我塑造成为同辈群体中的“英雄”,因为在充满暴力化的底层学校中,越出格的刺激行为越容易占据群体等级序列中的位次上端。偷窃也是如此,齐磊告诉笔者,学校明文规定且反复强调不能偷校园内各种果树上的果实,并不断提高惩罚的力度,以至于现在每偷一个橘子都会被学校“记大过”处分一次,但学校越是如此严格规定,就越能激发少年们寻找刺激和挑战规定的内心欲望,要是既能够偷到更多的果子,又能不被学校所发现,就理所当然地确立起了自己在群体内部的身份与地位。
四、 底层村落学校内部底层再生产的文化机制:一个比较分析
(一)“屌丝”与“土豪”心态的交替性发生作用
威利斯笔下英国汉默镇男子中学的小子们之所以会形成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反学校文化,进而在“部分洞察”中发现所谓的结构性真相,并再生产出与自己父辈工人阶级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阶级来,根本上在于其对文化和制度的主体性认知:其一,在宏观层面上,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黄金发展阶段的一个尾巴,充足的就业岗位使既无技术又无文凭的工人阶级子弟们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并获得不错的报酬以养家糊口,同时,与其他社会阶级享有平等公民权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并不会受到社会歧视;其二,在中观层面上,小子们拥有一批现实的参照群体反而可以歧视:以“耳油(ear oil)”为代表的循规生,以“马子”为代表的女孩子和以“高加索人”、“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三大参照群体使小子们能够在对抗学校权威的同时生产出自身的高贵性和优越性;其三,在微观层面上,小子们崇拜“男性气概”(masculinity),这是一种“以暴制暴”的暴力美学因子,正是在这一因子的影响下,小子们才热衷于通过诸如“扰乱课堂秩序”、“打架”、“逃学”、“加入非正式群体”等各种反学校文化的行为方式去获取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等级,从而在男性化的小子群体内部以及外部的女孩子面前,成为“真正的男人”。“男性气概”的崇拜表面上看承袭于家庭父权制结构关系的亲身体验,实则承接于英国整体工业社会中的父权制分工结构,更进一步说,与英国百余年根深蒂固彰显男性气概的工人阶级文化相一致。由此,小子们不仅对于通过反学校文化对抗学校权威并同时再生产了工人阶级自身的整个过程持有相当的合法性认同,而且还带有似乎洞见了全部结构性真相后积极主动再生产工人阶级自身的情感优越性。
周潇笔下北京打工子弟校中的子弟们恰恰是在与小子们相反的“自卑”心态中通过反学校文化的制造而再生产了底层自我,他们随同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北京“讨生活”,父辈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这个城市里最不稳定、收入最低、强度最高的职业,加上脏、乱、差的生活居住环境和城市中心本位下无限度的制度性与道德性歧视,子弟们不仅不具有小子们对于工人阶级文化优越性的自我认同感,反而在普遍意义上对父辈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文化带有无尽的排斥感,这种排斥感内化到个体自身即呈现出深深的身份否定与极度自卑感,但这种身份否定和极度自卑感却并没有有效转化为他们刻苦奋斗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而跻身中上阶层的正能量,反而,颠沛性的成长轨迹和制度性的优质教育资源隔离加剧阻止了自我身份改变的可能性,因此北京子弟们只能通过“嬉笑打骂”等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来逃避和化解真实生活中的无聊、矛盾与失望,从而被迫加速底层再生产的自我形塑。
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出身的小子们因为身居工业化的小城镇中而拥有某种主体性的骄傲心态与优越地位,北京农民工家庭出身的子弟们因为寄居特大城市的他乡而拥有强烈的客体性自卑心态与受歧视地位,那么四川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则兼具有小子们和子弟们二者的矛盾心态,笔者将之称之为“屌丝”与“土豪”交替性发生作用的底层心态:一方面,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没有随父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依然是在以农业生产为本的狭窄乡间,农业文明的正统性和熟人社会中乡土知识的广泛应用与尊崇使少年们这一乡间内生性文化主体没有产生价值迷失与排斥,乡土社会中相对较小的群体异质性和村落内部同质化的公共制度安排使云乡少年们很难遭遇来自他者的身份歧视与资源隔离。另外,随着云乡与外在市场空间的开放性连接、国家惠农政策的深入实施,父辈们外出务工与留守务农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而国内持续性的“用工荒”又进一步提高了单位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收入,以至于有部分农户成为了村落中的暴富阶层。相反,乡间“知识代言者”——“农村教师”收入甚至不如“小工”的尴尬现实无疑又反向刺激了少年们的骄傲心态,尽管与英国小子们都共有骄傲的内心体验,但两种骄傲心态的发生学却有所不同,小子们是在对工人阶级文化自身主体认同的基础上表现出骄傲,而少年们却并不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表达出文化主体性认同,他们仅仅是在父辈们现在比农村老师们赚钱多的基础上表达出骄傲,这是一种“土豪”式心态;另一方面,他们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主体性认同,相反他们甚至极度排斥这样的底层生存方式,所以才会在与外界世界间接化的经验接触和底层生存方式无法改变的自我确证中,又产生出强烈的自卑心态,这与北京子弟们的自卑心态体验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少年们的自卑显然更多来自于自己内心对其他社会优势阶层优质生活方式向往却不可得的的失落感,而不具有北京子弟们那种被赤裸裸外在身份歧视的直接性,因此少年们的自卑更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嘲状的“屌丝”式心态。正是“屌丝”心态与“土豪”心态的交替性,使云乡的少年们在更复杂的意义上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二)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
柯林斯在其经典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中认为,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社会资源,政治性劳动与文化资源密切相连,个体文化资源拥有量的多少决定着其最终处于何种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或社会阶层,文凭阶层化的核心特点即是财产地位*[美]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刘慧珍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3页。。事实上,英国的小子们、北京的子弟们以及云乡的少年们对于文凭和知识具有内在不一致的价值态度认同,而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价值态度认同使不同主体的不同底层再生产运转逻辑得以可能。
英国的小子们对文凭和知识表达全面否定态度的背后依然是对“男子气概”的崇拜,正是因为体力劳动者可以彰显更多的“男子气概”,所以才较之具有女性特征的脑力劳动者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更具有社会优越性*[美]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另外,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中还含有对文凭根深蒂固的怀疑,一方面,为这些文凭做出巨大的牺牲(时间、行动、参与以及独立性)是不值得的,它使小子们失去了在任何时候获得各种直接报酬的即时性能力;另一方面,文凭的背后是试图通过教育创造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然而小子们认为这种貌似真理的观点是荒谬的,他们认为不是文凭或者教育的向上推动力创造了上升流动机会,经济增长才是上升流动唯一的动力,文凭是没用的,它只能使小子们获得回报很少的岗位,如学徒或从事文书工作。由此,小子们拒斥知识,拒斥在学校中通过学习而获得文凭,他们似乎洞察到了教育的真相,而这个真相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帕瑟隆在经验研究后所指出的: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重要性并不在于技术或人本主义的进步,而在于社会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了再生产。
北京的子弟们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并不崇拜具有“男子气概”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期待着“坐办公室”和干“不累人又能拿钱”的脑力工作,他们并不愿如自己的父辈一样在城市中从事辛苦的体力活,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出人头地,通过努力学习知识而获得文凭,进而跻身脑力劳动者行列,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他们羡慕和佩服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中部分子弟故意表现出对大学淡漠和不屑态度,实质上是看到自己与大学无缘后而产生的心理调试而已,如果真能给他们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他们马上就会变得对大学充满积极的向往。由此可见,北京子弟们显然是充满了对知识和文凭的渴望与尊敬,他们仅仅是在升学无望和制度阻碍时才会表现出拒斥,他们从心里对知识的代言者——“教师”充满崇敬。
云乡的少年们则与小子们和子弟们对待文凭和知识的明确态度不同,他们的话语和行为表达充满了模糊性。一方面,在问卷调查中,任何一个少年都没有表达对文凭和知识的明显反对。在云乡学校八、九年级54个有效样本中,认为读书有用的高达47人,占87.0%,认为读书无用的则为0人,认为无所谓和不知道的也仅仅分别有2人。可见,他们似乎和北京子弟们一致,对文凭和知识态度深信不疑。然而,另一方面,当笔者走入田野对他们做深度观察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表达了对文凭的深度怀疑,对知识有用性也发出了严峻挑战,少年们的认识深度似乎一点也不亚于小子们对英国教育结构性真相的局部洞察。少年们认为:“如果文凭和知识有效,那为什么他们的老师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如那些没有文凭和知识的父辈和邻里呢?”“为什么村落中大家公认的榜样不是读书好而考上大学的孩子,反而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没有读高中就早早在外边赚钱的孩子呢?”“为什么那些乡校中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后来大多数都发展很一般,而调皮捣蛋的差学生很多后来却发展得很不错呢?最后好学生还得给差学生打工去。”显然,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表明云乡少年们不同于对文凭和知识深信不疑的北京子弟们,他们似乎和英国小子们一样洞察到了文凭和知识能偶尔促进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有限性,也认识到了即时性直接报酬的重要性,唯一不同的便是他们并不如小子们一样崇拜作为农民阶层和农民工阶层的父辈们,因为少年们的父辈总是具有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归宿感,无论父辈们是外出务工抑或留守村落,始终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而农民的身份又总是受到社会公开的话语歧视。少年们不想成为农民,他们梦想是能进入城市赚大钱,只要能达成此目的,则无所谓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可见,少年们具有小子们和子弟们的双重复杂性,但同时也具有现实的灵活性,这无疑使他们在学校中能更充满想象力和自由度地去挑衅和对抗学校权威,并制造反学校文化而再生产底层自我。
(三)“洞察”到或“部分洞察”到了吗?
“洞察”是威利斯笔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文化形式中的各种念头,而这些念头有助于洞察该文化形式的成员及他们在社会整体中所处的位置,而这种洞察的方式不是中立的、本质主义的或个体主义的”*[美]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3页。。实质上这种洞察就是“看透”自身的生存状态。小子们洞察到了学校内部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其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并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并不幻想“事业”发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劳动,判断出必须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来自于被支配地位的双重侮辱: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意识形态上的*[美]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3页。。正是在此基础上,小子们才会通过诸如“找乐子”之类的方式释放心理压力。“洞察”事实上也是对威利斯极为重视的社会“文化生产过程”的一种全面理解和真相揭露,但理解和揭露的过程本身也促成了过程的再生产,此时威利斯不得不考虑引入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局限”,它是指混淆和妨碍洞察全面达成的阻碍、偏离和意识形态因素,由于“局限”和“洞察”二者相互结合,“部分洞察”才构成了小子们的真实洞察状态,即他们不是真正彻底看透了自身在社会整体中和学校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而仅仅是部分,因为如果他们的洞察是全部意义上的直截了当和真实无误,那么他们就直接走向了社会解放,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洞察了真相,但却仅仅是部分洞察,所以才会在洞察的过程中又加速了底层的再生产。
北京子弟们显然没有达成“洞察”或者是“部分洞察”,与小子们“部分洞察”后的“主动放弃”不同,子弟们的“被迫放弃”实质上正是没有达成“洞察”或“部分洞察”的结果。因为“被迫”意味着制度性因素的阻滞并没有被子弟们形成主体性认知自觉,如果真正达成了“洞察”或“部分洞察”,北京子弟们就应该选择“主动放弃”之路。但他们没有,他们仅仅是在最终报考受限或考试失利后因无力在教育轨道中再次上升才被迫放弃,他们相比于小子和少年也都更尊重教师,更听从学校主流的价值观和权威,更服膺于家长的期待。
云乡的少年们显然具有“部分洞察”的痕迹,他们轻视农村教师,是因为看到了在一个底层社会结构渐趋固化的社会中,知识,特别是普遍性知识要改变底层命运的难为性;他们在课堂上抗拒学习实质上是对文凭和知识无用的嘲讽,同时也是对窒息底层上升流动的不公平教育筛选体系的抗争,先天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和后天不公平的教育分流制度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先天不足、后天更弱”的弱者;他们反抗被官方规定的时间控制和“全景敞视”的空间监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仅不可能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通过所谓的学业成绩提高而改变命运自身,反而使自己在封闭性的围墙之内更显压抑;他们成立“兄弟会”等帮派,乐此不疲于“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等非正式同辈群体,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抵御其他同辈群体欺负或欺负其他弱小同辈、故意对抗教师和学校权威、寻找同辈关系中的主体性和成就感,但是在客观上却通过非正式群体的建构预演和再生产了社会结构化中的真实权力等级关系主体性向度预期。他们通过“找乐子”、“暴力”与“偷窃”等方式寻找刺激和摆脱无聊,实际上是在释放文化和心理压力的同时,通过“主动放弃”加速着底层的再生产。
(责任编辑:薛立勇)
Juveniles from Lower Class:A Micro Social Research on Class Reproduction in Rural School in West China
Li Tao
Compared to the Boys described by Willis Paul and Xiao Zhou in 1970s in the industrial towns in England and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Beijing, the low-class juvenile in rural school in west China hold a unique “anti-school culture”. 22 juvenile, which is from eight grade in a K-9 school in Yun Xiang, a west China town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of this in-depth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key findings are the boys generated the anti-school cul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 by looking down upon rural teachers on expression of struggle to knowledge authority, by manufacturing all kinds of chaos in classroom on expression of resisting to relationship authority, by disordering the prescribed time schedule to resist to time authority in daily, by taking a theater in the camera to express resisting to space authorities, by formatting multiple types of peer groups, such as brothers, mentors, relatives, lovers, etc. to resist violation paradigm, by making fun, violence and theft to get rid of boring, etc.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d the Juvenile anti-school culture features by comparing to the Boys in England and the Children in Beijing, first these juvenile have a psychology alternately between “Diaosi” and “Tuhao”; second, the expression in both utterance and behavior of the Juvenile is fuzzy and disunion. third, concerning insight into the truth in education process these juvenile is partly apperceived.
Juveniles from Lower Class; Anti-school Culture; Class Reproduction Educational Selection
2015-07-25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项目编号:15CSH012)、第57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再生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5M571203)及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域内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制度设计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BS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中人名、市县及市县以下地名均属化名,对为笔者在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表示由衷感谢!
C913.5; C912.6
A
0257-5833(2016)01-0082-11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