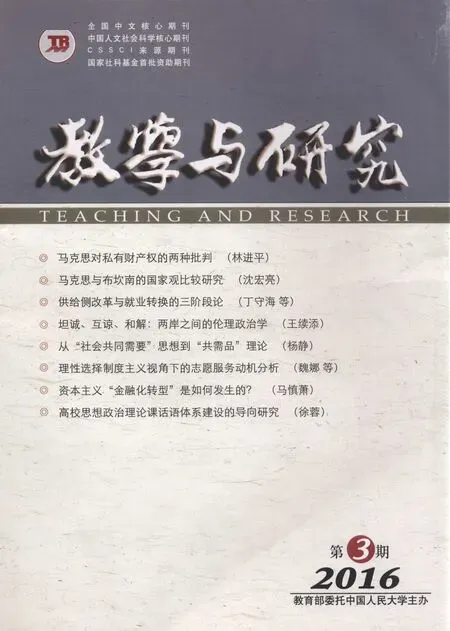柯亨对无产阶级不自由地位的当代论证*
2016-02-05王增收杜娟
王增收,杜娟
柯亨对无产阶级不自由地位的当代论证*
王增收,杜娟
无产阶级;集体不自由;贫困;柯亨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右翼乐于从自由的角度为资本主义作辩解,既否认无产阶级不自由的事实,又否认其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还反对通过再分配性税收来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A.柯亨对此进行了反驳,提出了无产阶级不自由地位的当代论证,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继续遭受着集体的不自由,其贫困地位事实上导致了他们的不自由;右翼是通过自由概念的混用来进行辩护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保护自由的,右翼所关心的也不是自由,而是私有财产制度。
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缘由是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严重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有感情(或兴趣)的学者,运用西方主流学界接受的分析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力图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论,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一是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证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二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构想和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已故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G.A.柯亨(G.A.Cohen,也译作科恩)在这两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第一项工作中,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不自由地位的当代论证,国内学界对此没有专门介绍,本文试图予以阐述。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和道德证成性显得格外重要,为此右翼提出了一套从功效转向从自由角度为市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自由是社会的最终价值,而资本主义是最有效保障或促进这种价值的制度,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是正义的。基于这种立场,右翼从理论上否认了无产阶级不自由的事实,也否认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导致他们自由缺乏的根本原因,还以保护“自由”之名反对政府通过再分配性税收来改善低收入者的处境。
右翼的这种新辩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在大众中有相当吸引力,即使一些左翼理论家都错误地认为放任的资本主义是最自由的,于是,“右翼重视个人自由,左翼重视平等”成为普遍的说法。[1](P80)资本主义果真最能促进自由吗?转向政治哲学之后的柯亨,严肃而认真地对待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不自由地位的当代论证,从而有力地动摇了右翼在这个问题上的统治地位,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在此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柯亨的反驳分三个层次:一是论证无产阶级不自由的事实;二是论证无产阶级不自由的原因;三是揭示右翼论证中的概念混用及其实质。
一、无产阶级遭受着集体的不自由
1.右翼的“无产阶级自由出卖劳动力论证”与左翼的无力反驳。
右翼总是标榜资本主义是保护自由的。他们说,即使资本主义的市场无法实现左翼所追求的平等,它至少是保护所有人自由的,包括无产阶级。右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不是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选择,社会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上升通道来摆脱无产阶级的地位。右翼还以英国的移民无产阶级为例,指出移民到英国的无产者,他们最初到达英国时的状况不如本土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多数人经过努力后,都成为了小资产阶级,因此,大多数英国无产阶级并不是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面对这一非常有力的挑战,左翼的一般反驳是说,只有少数工人可以成为小资产阶级,所以大多数工人是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柯亨认为这个反对意见没有驳倒右翼的结论。柯亨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有10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唯一的出口是一扇沉重而紧锁的大门。在与每个人距离不等的地方有一把沉重的钥匙,从体力上来讲,每个人在花费不同程度的努力后,都能够拿起这把钥匙,凡是拿起这把钥匙的人,在付出相当努力之后,都会找到打开房门从而离开屋子的方法。但是,如果一旦有一个人这样做了,那么只有这一个人能离开屋子,因为看守安装了监视器,在房门打开到仅仅够一人离开之后,马上关闭房门,使房门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次开启,而剩下的人将永远被关在屋里。
现在假定,10个人当中,没有人想努力获取钥匙而离开房子。或许是因为屋子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因而他们不想离开;抑或屋子相当糟糕,但他们太懒惰,不愿花费离开这间屋子所需的努力;或许,面对其他人的干涉,没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得到那把钥匙。假如,无论理由是什么,他们全都非常不愿意离开这间屋子,以至于如果有一个人试图离开屋子,其他人都不会干涉。
柯亨分析说,在这种假设下,无论我们选择谁作为试图获取钥匙而离开屋子的人,就其他9个人而言,他们谁也不打算得到那把钥匙都为真,因而,就被选择的那个人而言,他有获取和使用那把钥匙的自由也为真,所以,他不是被迫留在屋子里的。而且,无论我们选择谁,上面那两项为真的情况都不变。因此,每个人事实上并不是被迫留在屋子里,即使至少有9个人必然会留在屋子里。[2]
2.柯亨对无产阶级“集体不自由”的指认和论证。
柯亨通过上述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左翼强调事实上只有少数工人成为小资产阶级,并不能表明每一个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机会都被无产阶级积极地尝试着,因为,右翼可以反驳说,之所以只有少数无产阶级成为小资产阶级,是因为工人们像上述例子中的人一样,他们并没有利用他们有自由利用的机会。
柯亨通过这个例子除了要指出左翼的一般反驳无效外,他的重点在于揭示无产阶级所遭受的“集体不自由”。柯亨说,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获取钥匙进而离开屋子的自由,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其自由的条件性。每个人之所以是自由的,不仅是因为其他人都没有试图获取那把钥匙,而且以其他人没有获取那把钥匙为条件。于是,对每个人来说,仅当别人没有运用他们带有类似条件的自由,他才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们所有人都拥有的自由,而一旦任何一个人要运用这种自由,那么由于那种境况的限制,其他人都将失去这种自由。既然每个人的自由都取决于别人不运用他们带有类似条件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的境况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自由。通过分析,柯亨对例子中的个人自由作出这种性质的认定:尽管每个人都有离开屋子的个人自由,但他却使得别人遭受着集体不自由(collective unfreedom)。[2]
为了能够形象地说明集体不自由的存在,柯亨对上面的例子作了进一步的假设。上面例子中,我们假设这些个人由于懒惰、不自信和不愿意这三个原因没有离开屋子。现在我们假设,他们没有离开是由于第四个原因,即屋子里的人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他们谁都不愿意自己独自离开,而使其他人被囚禁在屋子里。这样假设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屋子里的人的确存在一种集体不自由。因为,虽然屋子里的人都有离开的自由,但是,当他们提出要集体离开屋子这个要求时,看守不可能说,他们全部本来是自由的。无产阶级的集体不自由,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不是被迫向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出卖他的劳动力,而是被迫向整个资产阶级出卖劳动力。
总之,面对右翼的无产阶级自由出卖劳动力论证,柯亨通过无产阶级遭受集体不自由的指认,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左翼的反驳。他的反驳是,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给无产阶级的脱离机会太少,从而使得无产阶级遭受集体的不自由,所以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是集体被迫的。对于柯亨的集体不自由指控,有三种反对意见,柯亨分别考查了理论界的这三种反对意见,捍卫了自己的集体不自由指控。
3.柯亨对三种反对意见的反驳。
针对柯亨集体不自由指控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指向柯亨的关于集体不自由的推理过程。在前面的例子中,柯亨认为关在屋子里的10个人遭受着一种集体的不自由。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推理是存在问题的。这种反对意见假设,这10个关在屋子里的人无意中进入了一个洞穴,由于特定原因,只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这个洞穴离开屋子。这种反对意见认为,在这种新假设的条件下,尽管10个人不能集体地离开屋子,但他们可能不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进入洞穴后,离开洞穴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根本没有看守,所以没有人强迫他们留在屋子里。通过这种类比,这种反对意见说,在群体的意义上,大多数无产阶级必定要继续充当无产阶级这一点是事实,但这一事实不是人为限制的结果,而只是体现了一种不反映出人类意图的数值关系。因此,说无产阶级存在离开屋子的集体不自由就不是正确的。这种反对意见的言下之意是说,无产阶级无法集体脱离无产阶级的地位不是人为限制的结果,而是一种概率的反映。[2]
对此,柯亨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回应。柯亨指出,这种反对意见实际是说,仅当有强迫主体的存在,才能说有强迫的存在。上面例子中,反对意见通过设计洞穴来表明,这里不存在强迫的主体,所以,无产阶级不能集体脱离其地位不是强迫造成的,而只是反映了社会阶层之间转化的一种概率。柯亨对此的第一个回应是,即使“强迫主体是强迫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真命题,我们也能表明在洞穴例子中,存在一种强迫性的人类力量。他认为,当无产阶级脱离无产阶级地位的出口数量是有限的时候,他们存在集体的不自由,因为如果试图脱离无产阶级的人数超过了脱离的出口,那么成功者就可能使失败者陷入被囚禁的境地。
柯亨的第二个回应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之间的转换实际上并非只是一种不反映人类意图的概率关系,它还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比如私有财产结构,这些都反映了人类意图,而这些对阶级转化施加了重要影响。
针对柯亨集体不自由指控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说,既然集体不自由条件下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关心集体不自由呢?它为什么是重要的呢?
对此,柯亨的回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柯亨认为集体不自由条件下的个人自由是有条件的,为此柯亨详细说明了集体不自由。所谓集体不自由是指,当且仅当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不可能实施A类型的行为,该群体在A类型的行为上就存在集体不自由。
简单来说,在一个遭受集体不自由的集体里,如果足够多的一些人运用了相应的个人自由,那么剩下的一些人就失去了他们的个人自由;如果一个人属于后者,那么他就分担了集体不自由。更准确地说就是,当且仅当X属于处于如下境况的n个人的小组,X在A类型的行为上就分担了集体不自由:
a.其中只有m个人(设m<n)拥有实施A的自由(在集体的意义上),且
b.不管哪m个成员实施了A,剩下的n-m个成员就可能因此存在实施A的不自由(在个体的意义上)。[2]
柯亨说,从上面对集体不自由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每个个体自由的相互条件性,才证明了集体不自由的存在,一旦足够多的人运用了共存的个人自由,集体不自由就必然导致了个人不自由。
第二,柯亨指出,即使有些集体不自由的确无关紧要,但是出卖劳动力的集体不自由则是不人道的。柯亨认为,某种行为的集体不自由的重要性取决于该行为的性质,有些集体不自由的确并不是令人不快的事情(比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应聘上伦敦的巴士司机),但是,工人阶级在出卖劳动力这件事情上的集体不自由确实是令人痛恨的事情。
针对柯亨集体不自由指控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说,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存在许多能让无产阶级脱离其地位的机会。他们会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并没有反对工人们组建工人合作社,但是现实中没有出现大量的合作社,所以工人们不是缺乏自由,而是不愿冒险。
柯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存在一些这样的机会能让工人脱离其阶级地位,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非常多,不可能使工人大规模地脱离无产阶级地位。柯亨认为,一方面这些法律许可的方式其实很难实施,现实中的操作过程非常复杂,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可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是现实的决定因素,而不是法律许可。因此,反对意见所说的工人合作社这些途径并不能证明工人是因为不愿意冒风险或无能而没有利用这些自由。
二、无产阶级的贫困事实上导致了他们的不自由
1.右翼的“缺乏手段和能力论”及其在政治哲学上的推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富有的资产阶级与贫困的无产阶级享有同样的自由吗?对于标榜资本主义自由的右翼来说,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对此,左翼也有一个大家熟知的反驳,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对于贫困的无产阶级来说只是形式上的,因为他们无力支付相应的费用。但是,右翼会马上反驳说,左翼的反驳体现了他们将自由与手段混为一谈。右翼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做某事,并不意味着你缺乏做这件事的自由,而只意味着你缺乏做它的手段和能力,因此,穷人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乏自由本身,而是他们没有能力。进一步讲,既然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自由,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把税收花费在减少贫困上来。
在柯亨看来,右翼的主张中包含两个结论:一个是概念上的;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右翼的推理过程如下:
a.是干涉而不是手段的缺乏损害了自由。
b.缺乏金钱只是遭受到手段的缺乏,而并不是受到干涉。
所以,c.贫困并不导致自由的缺乏。
其中a是右翼在自由问题上的定义,而b则是一个关于缺乏金钱与干涉之间关系的主张,由此,右翼获得了一个关于贫困与自由关系的概念性的主张c。不仅如此,他们还以c为前提,推出了一个更为反动的规范性主张。他们的论证如下:
c.贫困并不导致自由的缺乏。
d.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自由。
所以,e.减少贫困并不是政府的基本任务。[3](P375)
这个政治推论是说,只要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由公正且保持自由的市场自然产生的,那么政府就不要人为干预这种自然的结果,因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自由,而贫困并不导致自由的缺乏,因此,政府就不能把减少贫困作为其基本任务,更不应该通过再分配性税收来减少贫困。
2.柯亨论缺乏金钱就是缺乏自由。
一般来讲,自由主义者中靠右的人士都是支持这两个推论的(即c和e),但像罗尔斯和柏林这样靠左的人士是反对第二个推论的,即反对认为政府的基本任务不包括解决贫困问题。但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不认为贫困就是自由的缺乏,而左翼一般也只是反对上述论证中的前提a,即右翼的自由定义。但没有人试图通过反对b来反驳右翼的结论。这也表明,就连左翼都认为缺乏金钱就是遭受手段的缺乏,而不是遭受干涉。之所以没有人通过反驳b来反驳右翼的第一个推论,是因为所有的反对者都没有认识到自由与金钱的关系。在《自由与金钱——纪念以赛亚·柏林》一文中,柯亨论证了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观点,即与金钱的缺乏即贫困伴随而来的是自由的缺乏,并以此来反驳右翼的第一个推论。柯亨认为,像柏林和罗尔斯那样的自由主义的左翼之所以否认金钱的缺乏就是自由的缺乏,是因为他们持有一种具体化的金钱观,他们把金钱当作物。而柯亨认为,金钱不同于智力和体力。
柯亨用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来说明这一点。在当前的金钱社会,想得到一些物品和服务,必须支付金钱,如果你不付钱而去占有它们,那么就会遭到干涉,而金钱有助于消除这种干涉,因此,金钱给予的是自由,而不仅是行使自由的能力。柯亨认为无能与金钱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一个人有能力(他身体健全)去某地探望亲人,但是由于他没有钱而无法去,如果他强行上车(收费的),则会受到干涉。这表明,金钱的缺乏不等于能力的缺乏。
通过上面的分析,柯亨认为金钱是获得自由的insu条件,即非必要的但充分的条件中的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部分。除了金钱的缺乏外,还有其他因素(如无知、丑陋等)阻止你克服干涉,但是它们不像贫穷那样是不自由的一个普遍的insu条件。与其他因素不同,金钱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消除干涉。[3](P386)
为了证明自己在金钱与自由上的观点,柯亨进行了一个有意思的类比。柯亨设想了一个没有金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控制一切东西,并且是由法律来具体规定人们能够行使何种行为,即那些他们不受干涉而有自由行使的事情。现在,法律规定了每一个人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情,并且每一个人都被给予了一组规定了他可以做哪些事情的使用券。如果没有关于做某事的使用券,那么行为者则会受到干涉。柯亨指出,按照这种假设,这些使用券规定了一个人的自由是什么。通过这个例子,柯亨想表明:在一个没有金钱的社会,正是政府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与此相类似,在一个金钱社会,首先限制个人自由的通常不是政府,而是财产的所有者,因为在金钱社会里,是各个不同的私有者控制一切财物;所以,在金钱社会里,政府所做的就是执行财产私有者的意志来阻止不付钱的占有行为。
反对者可能会说,金钱不同于无金钱国家里的使用券,因为在任何条件下,金钱都是获得物品的自由的一个insu条件,而使用券则是此类自由的充分必要条件。柯亨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金钱对一个人的自由的影响如同他所描述的那类使用券一样,一笔钱等同于(但不是)一张实施一种行为的许可证。
为了解决金钱与政府使用券的差别,柯亨修改了刚才的类比。我们可以假定政府任命了一些财产管理执法官,授予他们很小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权,即有权让没有使用券的人获得某些物品,或者拒绝持有某种使用券的人得到对应的物品。这样假设之后,拥有使用券不再是获得物品的绝对保证,而没有使用券也未必意味着就得不到物品。这就与金钱社会在关键点上相一致了,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经过修改,例子还是能表明,使用券的分配仍然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自由的分配。
正如马克思所说,金钱是一种以物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力量,它本身是与体力和智力不同的资源。柯亨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金钱的分配来赋予,这一点及其重要性被普遍有意无意忽视了,所以连柏林都认为自由并没有受到金钱分配的限制。
三、揭示右翼论证中的概念混用及其实质
以诺齐克(Robert Nozick)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右翼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①“Libertarianism”在英语世界是指那种标榜自由至上的主张,中文界一般译为“自由至上主义”,也有学者译为“自由意志主义”。笔者赞同香港学者周保松将其译为“放任自由主义”。,他们提出了一种为纯粹资本主义作辩护的正义论,指出即使资本主义带来了极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这种制度却是最大限度保护自由的,因而是正义的。因此,他们否认无产阶级是不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否认无产阶级的贫困使他们处在不自由的地位,否认政府通过再分配性税收来改善穷人的地位是正当的。柯亨把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论证称为“自由论证①“Libertarianism”在英语世界是指那种标榜自由至上的主张,中文界一般译为“自由至上主义”,也有学者译为“自由意志主义”。笔者赞同香港学者周保松将其译为“放任自由主义”。,并指出这个论证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致使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由度最高的社会(言下之意是社会主义是通过减少自由来换取平等的),这正是为什么此类学者被错误地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原因。柯亨通过语义分析,指出右翼的这个论证其实存在自由概念的混用问题,从而揭示了自由至上主义者真正维护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自由本身,因而不配“自由至上”这一称呼。
右翼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对自由没有任何重大约束的社会,而社会主义或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如资本主义自由。在柯亨看来,任何社会既赋予其社会成员某些自由,也把某些不自由强加给他们,因而任何社会都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缺乏某些自由而被视为是坏的,然而,重要的是各个社会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产生了不同的自由分配方式。显而易见的是,私有财产制度在赋予财产所有者自由支配财产的同时,也限制了非财产所有者侵犯财产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些人的私人所有权意味着另一些人缺乏所有权”。[4](P915)但右翼对此是否认的,柯亨指出,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自由定义,如果借助语义分析,就能揭穿这种言论的实质。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右翼实际上并不关心自由本身。
右翼反对干涉私有财产,但支持干涉穷人去占有有主私有财产,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干涉私有财产限制了财产所有者的自由,并认为干涉穷人去占有有主私有财产没有限制穷人的自由,因为穷人没有占有别人财产的正当权利。柯亨认为,在这里右翼前后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自由定义:一个是自由的日常定义,即没有干涉就是自由;另一个是自由的权利定义,即自由是做你有权利做的事情。
柯亨说,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自由就是如果A成功地干涉了B的行为,B就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自由或不自由与A和B所享有的或缺乏的道德权利是无关的。按照这种理解,显而易见的是,一位正在实施逮捕的警察使一个被捕的罪犯失去了自由,不管他这样做是否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按照右翼的自由的权利定义,就会产生这样违背日常用语的结论,认为仅当B有道德权利去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并且(或者)A没有道德权利去阻止他,A对B的干涉才减少了B的自由。这显然与日常用法相违背,因为我们不能说:当一个杀人犯被正当监禁时,他没有变得不自由。右翼所说的干涉穷人去占有有主私有财产没有限制穷人的自由,就是在借助这个违背日常用语的自由的权利定义。但是,柯亨说,要借助这样一个自由的权利定义来表明穷人没有权利获取已被占有的私有财产,首先必须证明私有财产占有者对财产是有正当权利的。而右翼在没有论证的前提下,就把私有财产当作天
然正义的。[5](P294 295)
通过柯亨的语义分析,我们看到,右翼正是用自由的日常定义来反对穷人去占有富人的私有财产,用自由的权利定义来支持政府阻止穷人去占有富人的私有财产。显而易见的是,右翼只在乎富人的自由,而不在乎穷人的自由,所以他们真正要维护的并非自由本身,而是要保护私有财产制度。
柯亨整个学术生涯的主旨和最终指向是探索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作为柯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组成部分的无产阶级不自由地位的当代论证,完成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它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置很多人(至少是穷人)的不自由不顾,远非所谓“最自由”的制度,揭穿了其不自由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它为推翻这种不自由的制度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正名——不是牺牲自由求平等,而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消灭私有制。柯亨对无产阶级不自由地位的当代论证,所要维护的正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1] 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2013.
[2] G.A.Cohen.The Structure of Proletarian Unfreedom[J].Phi losophy&Publ ic Affairs,Vol. 12,1983,(1).
[3] G.A.柯亨.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G.A.柯亨文选[M].吕增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责任编辑 敖 华]
Cohen's Contemporary Argument on the Non-liberal Status of the Proletariat
W ang Zengshou1,Du Juan2
(1.School of Pol itical Science,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Jiangsu 226019;2.School of M 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 munications,Chongqing 400065)
proletariat;collective freedom;poverty;G.A.Cohen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the liberal right wings often make a plea for capitalism from the angle of“freedom”.They both deny the fact that the proletariatis not free,and that the root cause of its freedom lies in poverty.They also oppos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low-income personsthrough the redistribution oftaxes.As a M arxist analyst,G.A.Cohen refutes the above-mentioned view points of the right wings.He put forward the modern demonstrations of the non-free statu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the proletariat continue to suffer from the collective non-freedom. Therefore,capitalism is not protecting the freedom,and the care of the right wings is not freedom but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instead.
王增收,南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江苏南通226019);杜娟,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重庆400065)。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动态研究与批判”(项目号:2014Y C XZD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