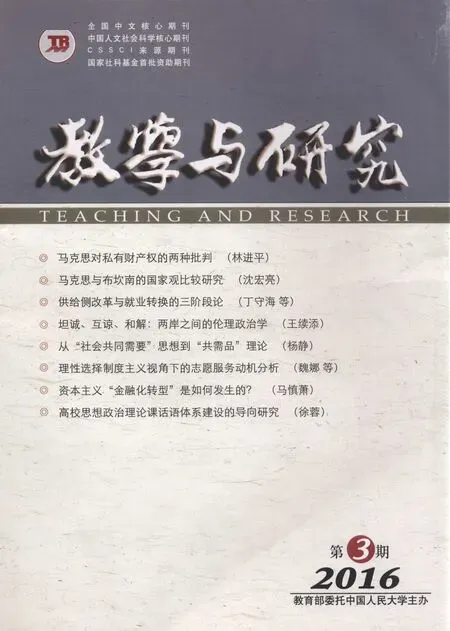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志愿服务动机分析*
2016-02-05郭彬彬
魏 娜,郭彬彬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志愿服务动机分析*
魏 娜,郭彬彬
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志愿服务;动机
本文假设制度为志愿者提供了实现其价值和偏好的条件和保证,通过制度对志愿者具有的价值来解释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的动机。同样,志愿者选择参加到志愿组织中来提供志愿服务,也是因为志愿组织本身设立了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能够为志愿者提供更好的而其他的制度所不能提供的利益。这种利益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报酬,而是通过志愿服务,志愿者的价值追求和个人偏好得到了满足。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学派之一。新制度主义是研究政治生活中组织因素的一种比较新的理论。它兴起于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反思。它强调制度为最根本的分析点,重视研究结构在决定政治过程结果中的作用,也指出了结构在决定个人行为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对人的行为的规制力要比其他任何方面更大。对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普遍认为马奇和奥尔森(March&Olsen)在1984年发表的名为《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的开创性论文是该理论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自那以后,“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随着新制度主义研究领域和分析途径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这一行列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纳入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以至于有人惊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1]新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分析途径,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在决定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多数制度研究者那里取得了共识。
而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的行为形式,是为他人、团体、机构、某项事业或整个社会提供帮助而不求物质回报。社会学对利他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在19世纪中叶孔德创造“社会学”这个概念时,也同样创造了“利他主义”的概念。但是,在目前日益沉迷于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回报的社会中,出现志愿服务这种利他行为似乎难以解释。同时,由于一方面志愿者的角色最近才被完全制度化,另一方面志愿工作有被当作一种业余爱好而被边缘化的趋势,所以对志愿服务的系统性研究出现比较晚。
近年来,志愿服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动员志愿者提供服务方面,政府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关于参与志愿服务的程度和志愿服务的分布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断出现;与此相关的学术著作和从事志愿服务的社会组织也大量增加。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志愿服务存在和发展的动机,在志愿服务中找到“经济人假设”和“利他主义”的结合点。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1996年,豪尔和泰勒(PeterA.Hall&Rosemary C. R.Taylor)在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政治学与三个新制度学派》,把新制度主义分为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大的流派。
在这三个学派中,理性选择主义主要关心的是选择性秩序与内在秩序和规范性秩序的关系。强调制度或制度性规则具有重要作用的理性选择理论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它们构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多样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多样性体现在研究者对作为规则的制度、决策规则、组织之中的个体、委托—代理模式、作为博弈论不同版本的制度等五个方面的侧重。[2](P47-54)相对于其他分析途径而言,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制度分析的各种变体,都假定了将同样的利己主义行为特征作为分析的基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效用最大化能够并且应该成为个体的基本动机,但是,个体也许会认识到他们的目标能够通过制度性的行动来最有效的实现,并且还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制度的塑造。
首先,在制度的内涵方面,大多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都赞成将制度定义为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规则集合体。如果组织及其成员遵守行为规则,就能适应环境以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身偏好、效用和目标的最大化。政治科学家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加那德和沃克尔等人就持这种观点。他们把规则作为手段来“规定、禁止和允许”某种行为的存在。他们认为,在这一制度或组织之内的成员如果遵循这些规则的话,将从制度或组织成员关系中获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流派认为,构成行为要素的理性以两种方式清晰地显现出来。第一是个体能够从某一制度的成员关系中获益,并因此而愿意作出某种牺牲,以获得这些更为重要的利益。如果所有的成员都受到了他们的制度性成员关系的约束,且他们都追求更为重要的利益,那么其他成员的行为就更具有可预期性。所以,这一流派认为,理性的个体十分乐意加入组织。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主义则是第二种表现方式。奥斯特罗姆认为,某一套制度的领导会使成员遵守自己的规则。如果通过制度安排来应对公共政策中的棘手问题,且当个体的理性追求会产生负面的集体效果时,规则对于调解个体行为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类似于“公地悲剧”的背景下,有些对决策和执行机制的约束规则对于制度的成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此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流派还有委托—代理制度分析模式、博弈论的制度分析模式等。
其次,在研究路径方面,根据豪尔和泰勒的概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四个特征分别是采取理性人假设、倾向于将政治看作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产生决定性政治后果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使用演绎分析的方式假定行动者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创设制度。[3]与之相似,日本学者加藤淳子(Junko Kato)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做的学术努力主要在于将制度约束同个体行为整合起来,并基于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假设使制度因素被纳入到微观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之内。[4]
最后,我们还必须说明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偏好"。偏好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扩展,逐渐成为政治科学研究者普遍接受的术语。在经济学研究者那里,偏好作为现代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者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理性选择理论所分享。马奇和奥尔森指出,对理性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来说,政治活动被看做个体通过讨价还价、协商、结成联盟及交易等过程而汇聚产生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行动者均具有在行动前的确定的偏好,以此来决定合意的目标和预期的结果。[5](P307)
在对待行动者偏好的问题上,豪尔和泰勒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采用了一种同偏好密切联系的行为假设。一般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相关行动者具有一套固定的偏好或品味,完全以工具性的方式行动从而最大化其偏好,在这个过程中策略性的算计行为极为重要。[3]马奇和奥尔森指出,“利益和偏好产生于制度性行动的背景”。[5](P307)彼得斯则指出,理性选择理论提出的偏好和利益是外衍性的主张,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里已经动摇为必须关注“个体同制度如何互动以产生偏好”这个问题。因此,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里,偏好虽然看起来是外衍性的,但某些偏好也可能是内生于组织之中的。[3]
另外,强调博弈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如谢普斯勒,也重视结构和程序对个体偏好的影响。有必要指出,围绕偏好是内生性还是外衍性的理论分歧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政治学者托马斯·科埃勃(Thomas A.Koelble)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并开始承认其偏好假设的内在问题,这尤其体现在凯伦·施威尔斯·库克(Karen Schweers Cook)和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的著作《理性的限度》(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中。[6]另外,克拉克也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基于能动和基于结构的两个新制度主义分支在于理解偏好形成是外衍性还是内生性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本体性的分歧,但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围绕能动的制度研究路径,具有很大的理论空间来容纳内生化偏好(endogenizing preferences)的观点。[7]
二、志愿服务
尽管“志愿服务”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人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用语,但我们仍然很难确定其在社会实践中的独特范围。除了最常见的“一帮一”的形式外,志愿服务也可以指,一群人为了实现某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工作;人们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持一个组织;某些政治宣传倡议活动等等。这让人感觉到很难确定一项活动是不是志愿服务。
我们发现,大多数社会学家和普通民众相信现实中存在着清晰的、可以用“志愿服务”来描述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都具有共同之处。联合国2001年发布的一项有关志愿者信息的问卷中使用三项标准来辨别志愿行为:(1)不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参加志愿工作;(2)出于本人的自由意志;(3)为第三方和从事志愿工作的人带来收获。即使是这么一个相当简单的定义,也被追加了若干个防止误解的说明(可能允许给志愿者一定的补偿,但是这个数额不应该超过该项工作的市场价值)。[8](P10)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对其进行解释。比如,经济学家认为志愿工作是一种无偿的生产性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经验性的指标来测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志愿服务不是在家里和工作单位范围内的某个组织中完成的工作,用于完成志愿服务的时间通常是在家务劳动和有偿工作之外的时间。同时,它也不属于休闲活动。从经济人假设看,志愿服务似乎无法用动机来界定。
志愿服务不仅是简单的“无偿劳动”,而是被合适的动力所支撑的无偿劳动。只要利益不是人们参加志愿服务的主要原因,那么它是允许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从志愿服务中的获益现实存在,但志愿者不能以此作为参与志愿服务的目的。志愿服务并不是简单的无偿劳动,而是为了某种正当的理由或目的进行的无偿劳动。动机的纯度成为衡量个人行为算不算志愿服务的标准。动机有助于界定志愿服务,但同时志愿服务也不简单地等同于无偿劳动。要使志愿服务的合理动机得到一个公认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志愿服务的范围,目前研究者倾向于通过分类来划定。一些分类法是基于服务对象,如老年人、残疾人、儿童;一些是与志愿组织类型有关,如专业协会、宗教组织;还有一些是根据服务的内容,如环境保护、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这样的结果就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志愿服务是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大众概念。这个词被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也被冠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解,只有遇到争议时,才会去思考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志愿服务。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从“工作”的定义出发,来界定志愿服务的含义。构成工作活动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得到报酬,而在于是否涉及为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可供消费的物品。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工作可以提供服务或可消费的物品;二是工作者和工作对象之间会产生某种关联。志愿服务也是一种工作,通常被认为是正式的、公共的和无偿的工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为父母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这显然不是志愿服务;但我们再向公共领域挪动一点,变成向周围的邻居、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如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这就是社会服务了。从这个角度讲,志愿服务是一种致力于解决问题并帮助他人的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其正式性、公共性和无偿性使它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工作。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对志愿服务动机的分析
了解一个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最容易的方法是直接去问他们参与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都必定会涉及一种意图、理由或动机。但本文试图从组织的角度,如同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来分析。为此,我们假设所分析的志愿服务提供者都是属于某志愿组织的。
(一)组织的价值规则
构成行为要素的理性主要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个体能够从某一种制度关系中获益,并愿意做出某种牺牲以获取这些更为重要的利益。如果所有成员都受到了他们制度性成员关系的约束,那么就意味着成员行为的可预期性的提高。二是当个体的理性追求可能会产生对集体有害的结果时,规则对于调节这种个体行为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类似于“公地悲剧”的情况下,这种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对于制度的成功起着关键的作用。
志愿服务对于人们来说是实现其价值观的一种方式。对于志愿组织来说,只有其组织价值规则对志愿者有吸引力的时候,才会有志愿者参与其中。志愿者都需要一个参与志愿服务的兴趣点或利益点(动机),但这不是物质的,而是理想的。比如业主加入业主委员会,不仅是为了保护其房产的价值,还因为他们关注社区生活质量;父母们志愿成立家长会组织,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能从中获益,还因为他们认同这种教育方式的有效性。这就是组织的价值规则,而且这些价值规则体现了参与者的理性。
在遇到一些与人的尊严有关的问题时,提供志愿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因为这能够不损害接受者的尊严。在价值规则得到实现后,志愿工作除了为人们提供衣食住行等物质服务之外,本身也提供了一种满足感,这也是有时候人们甚至会选择用效率相当低的方式来完成目标的原因。例如,一些收入不菲的律师之所以愿意把时间花到为困难群体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困难群体一样需要得到公平的法律服务。在形式上,这可能是无效率的,比如一个律师每小时的服务费是500元,他每天花8个小时向一位没有领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低收入者提供法律服务就是不理性的。如果他把为别人提供法律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拿出一小部分来帮助这位低收入者,可能会显得更加理性。但是当这个律师采取后一种解决方式的时候,他追求的便不是实践一种经济价值规则了。
(二)组织的制度规范
组织中的制度规范为组织成员指明了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制度规范是在一定的情境下的,而价值规则是超越情境的,“在志愿组织中,普遍存在三种规范:一般互惠规范、正义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8](P95)
1.一般互惠规范认为,个人应该为他人提供服务,或者为他人的福利而行动。这不同于把在未来从对方那里得到帮助作为目的的互利行为。志愿服务行为的对象很少能够回报自己所受的帮助,志愿者本身也不需要对象的帮助。例如,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提供食物的志愿者,是不会期望有一天自己也需要这些流浪者给自己提供食物的。一般互惠规范解释了志愿者没有因为顾虑“搭便车”的现象而停止自己的行动。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贡献力量,而不管别人是否也做出了贡献。
有时候,志愿者做出一些回报性的行为,并不是回报当初给予志愿者本人帮助的人,而是回报给同样有需求的、一般意义上的他人。比如一些忙于工作的年轻人,因为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老年亲人,而享受了志愿者提供的志愿服务,当他们有时间后,就会同样帮助处于自己之前情况下的年轻人。很多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志愿者本身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很多帮助孤儿的志愿者自己也是孤儿,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这种困境,也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当人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会想要去回报他人。这种规范的意义重大,它提高了一般来说不愿意当志愿者的人们从事志愿服务的可能性。
2.正义规范认为,一旦最直接的自我利益得到实现,我们的行为就容易被我们的公平和正义感所引导。正义是一种社会规范,它将公正规定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我们都反对不公平,一旦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就会感到气愤。如果人们感到自己、他人或者所属的组织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通常会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比如说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受正义规范驱动的志愿服务活动,其动力是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个人或者团体的认同。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反对,会使他们采用集体行动、形成组织,因为这些问题可能在他们身上也曾发生过。比如孩子被拐卖的父母,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组织,互相帮助对方。
3.社会责任规范与一般互惠规范比较相似,但它不含有交换或者回报的含义,而是纯粹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一个优秀的公民,必然会对社会负责任。他更愿意为自己的邻居考虑、关心社会事务。一些参与程度更深的公民会拿出实际行动来帮助社会发展。那些相信有必要履行社会责任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参与志愿服务时,许多志愿者将其归于有义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或者履行公民关注社会的责任。志愿者通常认为个人有责任支持和帮助实现公共利益,应该积极地为公共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当然,这种贡献不仅仅是付出时间,也包括捐献。事实上,向志愿组织捐款的人数要远远大于拿出时间来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
(三)组织中的个人
志愿服务与非正式的帮助(如献爱心活动)不同,志愿服务活动是由志愿组织实施的,具有组织性,是个人通过组织将自己控制的资源给予他人。
1.个人的制度化。志愿者角色的制度化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将志愿者的期待制度化,并使志愿者具备满足这种期待的能力。制度化可以使志愿者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待,也使志愿者能够满足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二是确保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的动机正确,从而帮助志愿者角色制度化。正如志愿者被定义为一种利他主义者一样,怀有不良动机的人是无法很好地完成志愿服务的。要成为一个好的志愿者就必须在提供志愿服务的时候怀有正确的动机。比如在救助站照顾他人的志愿者,他们逐渐会与被救助者建立联系,并从其角度出发考虑事情。这与仅靠个人兴趣的人不同,靠个人兴趣的人往往很难承担额外的责任。
2.个人与组织的联结。理性制度主义认为,个人的偏好对其与组织的联结至关重要。在志愿组织中,尽管不能满足志愿者日常生活的诸多主要偏好,但可以满足其贡献社会的心理偏好。尽管志愿者从属于志愿组织,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志愿者只是一个短暂的角色。这个角色并没有工作和家庭的角色重要。所以,志愿组织会使用某种激励手段来满足志愿者某种偏好,从而使其留在志愿组织中。通常来说,志愿者的偏好与志愿组织提供的激励越契合,志愿者则贡献给志愿组织的时间、金钱、参与度等有价值的资源就越多。因此,志愿组织需要密切关注其成员的偏好,并使其融合在志愿服务中。比如,一个为儿童福利而建立志愿组织,其招募志愿者时,如果宣传词写成:“建立友谊、改善环境”等,显然没有“全世界的儿童都会因你的帮助而变得更幸福”有效。如果志愿组织在与志愿者偏好的联结方面出现问题,那志愿者就会降低继续加入组织的意愿。
3.规则运行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如果志愿者感到自己被欺骗或利用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放弃志愿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志愿者会遇到“搭便车”问题,他们努力工作提供了很多公共利益,而其他成员即使没有工作也可以共同享受这种利益。一般组织中奖励和惩罚的缺失会使得不努力的人很难被分辨出来,而志愿组织中成员产生不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奖励的缺失,而是奖励的不平等。志愿者希望在组织中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们认为组织的规则是错误的,他们会离开组织。
第二,如果志愿者认为他们与志愿组织中获取工作报酬的人之间有矛盾,他们离开组织的可能性会很大。志愿者与组织之前的客观联结通常没有获得报酬的人那么牢固,当两者产生矛盾时,志愿者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离开组织,而获得报酬的人则更希望留在组织中。
第三,如果志愿者感觉组织中有太多的官僚主义,他们可能会离开组织。当今志愿组织使用合同的形式越来越普遍,制度、质量控制、绩效等概念带来了越来越严格的责任,而这并不受志愿者的欢迎。志愿者通常并不希望被严格监督、不看重任务规范,当志愿者被要求根据严格细致的规定进行工作时,他们会丧失完成工作的动机,因为这使志愿服务与普通工作没什么两样了。如果志愿者从事过多的文字性工作和程序性工作,拥有很少的工作自主性,志愿者很难感觉到自己在帮助别人,他们没有看到很多的服务内容。
第四,如果志愿者感觉到自己的角色很模糊,也会降低志愿者提供服务的动机。很多时候,志愿者角色的模糊,是由于他们并不领取报酬。事实上,志愿者的角色并领取报酬的人的角色更需要明确,这可以使免费劳动力不会沦为奴隶劳动力,也会提高组织对志愿者的认可度。
清晰的角色定位还包括设定现实的目标,如果目标过于不符合实际,也会影响志愿者的积极性。如果志愿者的工作对其服务的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通常会提升志愿者的满意度,这种良好的影响建立在现实可行的目标设计上。
[1] M ark D.Aspinwall&Gerald Schneider.Same M enu,Separate Tables:The Institutional ist turn in Pol 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Pol itical Research,2000,(38).
[2] G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 itical Science:The“New Institutional ism”[M]. 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1999.
[3] Peter Hall and Rosemary C.R.Taylor.Pol 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J].Pol itical Studies,Vol.XLIV(1996).
[4] Junko Kato.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 ity in Pol itics: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J].British Journal of Pol itical Science,Vol.26(1996).
[5] James M arch and Johan Olsen.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A].in Bernard E.Brown,ed., ComparativePol itics:Notes andReadings[C].Belmont:W adsworth/Thomson Learning,2000.
[6] Thomas A.Koelbl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 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J]. Comparative Pol itics,Vol.X X VIII,No.1(1995).
[7] Wi ll iam Roberts Clark.Agency and Structure:T wo Views of Preferences,T wo Views of Institutions[J].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l.42(1998).
[8] 马克·A·缪其克,约翰·威尔逊.志愿者[M].魏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 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孔 伟]
Analysis of Voluntary Service M o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W ei Na,Guo Binbin
(School of Publ ic Administr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 j ing 100872)
rational choice;new institutionalism;voluntary service;motivation
The thesis assumes that the system provides the volunteers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ir values and p
,and explains the motiv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through the value ofthe system to volunteers.Similarly,volunteers choose to take part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volunteer services only because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set up a system,which provide volunteers better benefits that other systems cannot provide.This benefit is notthe usualeconomic reward,but can satisfy the value pursuit and the personal preference ofthe volunteers through the voluntary service.
魏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郭彬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