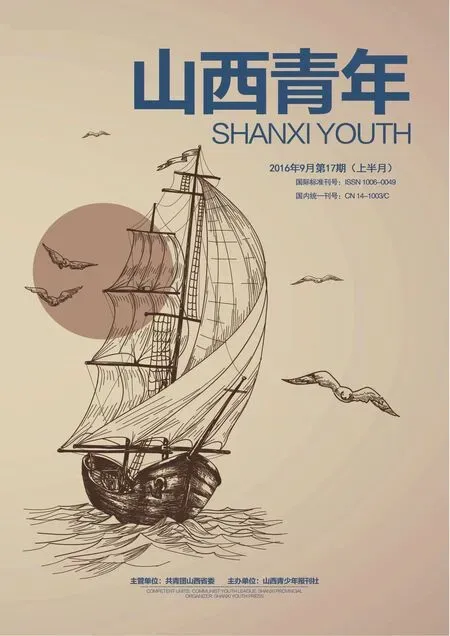历代画评之顾恺之
2016-02-04李俊
李 俊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4
历代画评之顾恺之
李俊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西安710054
绘画;顾恺之
顾恺之,作为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无论在绘画实践技巧上,还是绘画理论上,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摸索和总结,取得了无人可比的成就,使得中国绘画审美趣味发生了质的变化。
尽管历朝历代对他推崇之至,但是这位画家尚无真迹传世,现存的无论《洛神赋》,还是《烈女仁智图》,《女史箴图》也罢都是唐宋时期的摹本。但是通过这些摹本,通过不同朝代的绘画理论家对他的评价,我们还是能从中领略到这位画圣的一些人格品貌和笔力神韵。
南朝宋明帝在《文章志》中说:“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全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1]从中可知顾恺之在绘画、文学方面具有黠性,在生活中具有痴性,该黠则黠,该痴则痴。这种“各半”特色也是他豪放不羁的为人处世方法,摆脱各种纷扰的方法,同时为他赢得良好的人缘,赢得了进行从事绘画职业的时间。顾恺之的“痴绝”,或多或少折射出魏晋时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一方面反映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不稳定和奢糜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内心痛苦而又无力回天,只能假装痴傻,沉缅于创作之中,以求精神的解脱。
顾恺之一生写下不少文章,唐朝尚有《顾恺之文集》和《顾恺之家集》行市,可惜后来均已散佚。通过流传下来的顾恺之的文章词赋看,确实造诣很高,如他的《筝赋》、《水赞》、《四时诗》形容江南景色的“王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等,确是才华出众。众人评价“文绝”,并不过分。
南朝宋的何法盛的《中兴书》中提到“博学有才气,为人迟钝而自矜尚,未时所笑”[1],同样体现了他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处世方法。
与顾恺之同时代的谢安在《晋书顾恺之传》中说“苍生以来所未有了”更是把顾恺之推倒了至高的地位。
南齐人谢赫评价顾恺之说“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历代名画记》)他看了顾恺之的画以后,认为对人物的刻画很精微,下笔也很谨慎,不随便。但是作品并没有达到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所以“迹不迨意”。既然没有达到绘画目的,前人推崇就显得过高,名不副实,谢赫自然会认为“声过其实”。从《古画品》中,可以看出谢赫对绘画的评价要求不仅要具备“气韵生动”,其他五法也是必不可少的;而顾恺之为了达到传神的目的,在塑造形体上采用了不同方法而有所取舍。这样,两个人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分歧。同时,顾恺之使用的高古游丝描在人物画中虽然有飞逸飘动之感,但该线条如发丝一样细匀,无粗细变化,所以在人物刻画上缺少一定表现力度,从而也限制了人物神韵的表现。所以谢赫评价顾恺之“迹不迨意”,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并非如后人所说的主管偏见。
南朝陈的姚最和谢赫的评论则针锋相对。在《续画品》中,他认为“顾公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傚;如负日月,岂末学之所能窥?荀,卫,曹,张,方之蔑矣,分庭抗礼,未见其人。谢陆声过于实,良可于邑”,给顾恺之极高的品评,并毫不客气地批评谢赫的品评出于个人的主观偏见,“斯乃情抑扬,画无善恶”。《续画品》中的“立万象于胸怀”和“心师造化”论反映出谢赫评价绘画并不是注重种种法度,而是留意画面的象外之意,注重通过绘画形象传达出画家的人格,气质学养,展现画家的风格。在评价绘画时,以意求未先,甚至可以“忘象”,所以他认为顾恺之的绘画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矫然独步,终始无双”。谢赫把顾恺之“列于下品”,他必然会“尤所未安”。魏晋艺术思潮中“得意忘象”思想在姚最对顾恺之的画风品评中有集中而具体的表现。
李嗣真继姚最之后,就对顾恺之的客观评价问题,再次向谢赫提出质疑,在《续画品录》中“顾生天才杰出,独立亡偶,何区区荀卫而可滥居篇首?不兴又处顾上,谢评甚不当也。顾生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足使陆生失步,荀侯绝倒。以顾之才流,岂合甄于品汇?列于下品,尤所未安!今顾陆请同居上品。”他认为顾恺之“天才杰出”,没有人能够在他之上,而且思维接触造化,领悟其精神特征,“思侔造化”,参透自然之神韵,“得妙物于神会”。
这也正是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论。两人观点不谋而和。
唐代的《画断》中写到“顾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幻亡方,以顾为最。喻之书:则顾陆笔之钟张,僧繇比之逸少。俱为古今之独绝,岂可以品第拘留?谢氏黜顾,未为定鉴。”张怀瓘认为“虽寄翰墨”,但是顾恺之的画面“神气飘然”,不是一般绘画一般画家所能表达出来的。又从每位画家的风格出发,认为每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而不是“乃情抑扬”,所以评价的更客观真实。俞剑华的《画论类编》也是认为张怀瓘的评价客观真实,“谢赫崇尚陆探微,抑顾恺之;姚最崇尚顾恺之,抑张僧繇;孙畅之抑顾恺之;李嗣真崇尚顾恺之,张僧繇,抑陆探微。也认为惟张怀瓘平情立论,于推崇之中,分别就三人优劣,总结以“象人之美‘张、陆、顾’,而‘以神幻亡方,以顾为最’。”[2]
到了晚唐,著名画论家张彦远再次驳斥谢赫的观点,《历代名画记》[3]中的《论顾陆张吴用笔》中直接写到“顾恺之之迹,紧劲聊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时代普遍使用高古游丝描。这种技法不同于其他,既有力量,又不外放,而是把力量蕴含于用笔中,使得线条既精气内敛,又充满力量且流动不止,充满生机。所以张彦远评价顾恺之的用笔“紧劲聊绵,循环超忽”。“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显示出顾恺之在作画过程中充满了激情,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意气,即使绘画完成,画面仍然充满意气,“所以全神气也”。
在《历代名画记》中其他部分也是频频流露出对顾恺之的敬仰之情。《论画六法》中提到:“上古之画,痕迹简单意思澹然而文雅正气,顾陆之流是也。”指出顾恺之的绘画风格正是当时古朴雅正风格的代表。《论画体工用拓写》中记载“遍观众画,唯有顾生画古贤得其画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以使如槁木,心固可以使如死灰,不亦甄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顾生首创维摩诘像,又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态,陆与张皆效之,终不及矣。”更是认为顾恺之迁思妙想,体悟自然,达到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境界,陆探微和张僧繇是赶不上的,甚至综合了孙畅之、李嗣真、姚最、张怀瓘等人观点批驳谢赫的错误观点。
宋代的《扪虱新语》[4]评价“顾恺之善画而人以为痴,张长史书而人以为颠,予所谓此二人之所以精于书画也。庄子:‘用志不分,凝于神。’”作者陈善和宋明帝同样提到了“痴”。从善画的角度出发,陈善认为他痴
是因为当他潜心绘画,当然会无所顾忌,忘乎所以,使人误以为痴。从中可见顾恺之是一个性情中人,并不为周围人看法而左右,大有乐于“痴”的豁达。
元代的汤垕在《画鉴》[5]中说到,“顾恺之画如春蚕吐丝,初见其平易,且形似时有失,细视之,六法兼备,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曾见《初平叱》《石图》《夏禹治水》《洛神赋》《小身天王》,其笔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也,皆出自然。傅染人物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在这里汤垕赞誉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如“春蚕吐丝”。“初见其平易”同时反映了顾恺之的绘画风格平易朴茂,轻松自然,不过分藻饰,与张彦远的观点“痕迹简单意思澹然而文雅正气”不约而同。“且形似时有失”,似与谢赫的观点“迹不迨意”相近,但是笔锋一转“细视之,六法兼备,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此话凸现了顾恺之在作品中着意表达的神。为了“传神”而有所取舍的形,以及形象高古典雅,沉着有力的用笔,简略的构图相融合,产生了“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的效果,达到自己的绘画目的。
由此可见诸多观点或不谋而合,或相差甚远,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各位评论家是从不同角度对顾恺之进行分析和品评。宋明帝从为人品貌道出顾恺之的“痴黠各半”;何法盛则点到了他的大智若愚性;谢赫在审美趣味上和顾恺之背道而驰;然则姚最对顾恺之的画风一致推崇;李嗣真和顾恺之的思想精神相通;张怀瓘客观接受顾恺之的画风;张彦远从用笔,风格角度肯定了顾恺之的成就;陈善一语道出了顾恺之“痴”的原因;汤垕更加全面的评判顾恺之的综合画貌。
综合以上观点,大师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我们可以领略到时而正常,时而犯痴的顾恺之比较完整的绘画面貌:擅长高古游丝描,笔迹有骨,画风古朴雅正,形象精微简淡,生动传神,意气溢于画面。
[1]《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张建军.《中国古代绘画的观念视野》.齐鲁书社出版,105.
[3]孟兆臣校释.《历代名画记》.《画品》,北方文艺出版社.
[4]《扪虱新话》.宋代作家陈善撰,八卷.
[5]《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4.
J209.2
A
1006-0049-(2016)17-02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