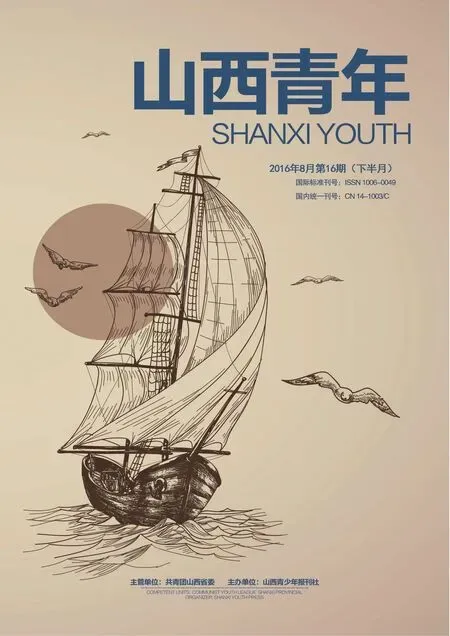阮籍五言《咏怀诗》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
2016-02-04杨琳琳
杨琳琳*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阮籍五言《咏怀诗》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
杨琳琳*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其渊源辨析历来众说纷纭,自钟嵘提出阮籍诗源出于《小雅》以来,学界质疑的声音不断,发展到现在有“小雅”说、“离骚”说、“古诗十九首”说、“庄子”说等,不可否认的是《咏怀》饱满的浪漫主义情怀跟《庄》《骚》一脉相承,但《咏怀诗》中大量现实主义的描写却是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本文就从讽刺精神、超现实的审美取向两个方面来阐述阮籍五言《咏怀诗》是如何继承和发展《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咏怀诗》;《诗经》;讽刺;超现实
南朝梁钟嵘《诗品上》“晋步兵阮籍诗”条曰:“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指出阮籍《咏怀诗》的渊源在于《小雅》。清人王夫之对于《咏怀诗》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远绍《国风》,近出入于《古诗十九首》,而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认为阮籍《咏怀诗》的远祖是《国风》,近祖是《古诗十九首》。但不管是《小雅》还是《国风》,《咏怀诗》与《诗经》的密切关系似乎是毋庸置疑了。近人方东树也说,阮公《咏怀》“宏放高迈,则与《骚》、《雅》皆近之”并认为“不深解《离骚》,不足以读阮诗。”方氏在这里提出了《离骚》对《咏怀诗》的阐释理解影响很大,但也充分肯定了《诗经》和《咏怀诗》的渊源关系。
阮籍所创作的《咏怀诗》是我国文学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诗歌以独特的美学风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这八十二首五言诗中,阮籍将深邃的玄学哲思与诗歌中的情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诗歌不仅具有深沉的内涵,同时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境界。如此瑰丽宏大、影响深远的巨作从继承古老的艺术传统来看,《咏怀诗》绝不仅仅诗从一家,而是博采众长,融合众美,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味。就渊源而讲,钟嵘认为阮诗出于小雅,似乎也是学术界广泛认可的说法,除了写作背景的相似,《咏怀》对《诗经》的“讽刺”精神,比兴的表现手法,意象的大规模沿用都是对《诗经》的绝好继承,但从美学特征来看,《咏怀》融合《庄》、《骚》特点更为明显,当然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旨在说明《咏怀》是如何继承和发展《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一、讽刺精神
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讽刺精神。阮籍继承了《诗经》的讽刺精神,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他的《咏怀诗》内容除了少数“忧生之嗟”和怀念亲友者之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讽刺力作:
如《咏怀诗》第十首: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沈。捷径从狭路,僶俯趋荒淫。焉见王子乔,乘云游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
这首诗是阮氏深刻地指出了魏帝荒淫是导致魏室衰亡的原因。
再如第五十三首: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智巧万端出,大要不易方。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乘轩驱良马,深榭设闲房。被服纤罗衣,凭几向膏粱。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傍。
这首诗是讥讽司马氏集团的作品。五到十句以反诘语气,通过对司马氏集团的吃喝玩乐所谓富贵生活的描写,揭露他们的骄奢淫逸。
这样的讽刺诗在《咏怀》中颇为常见。综合来说阮籍最爱批评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虚伪而又拘谨的“礼法之士”比如《咏怀》其六十“儒者通六艺”,其六十七“洪升资制度”;另一类人则是浮华交结,驰逐名利,生活奢侈,终日应酬结交的贵族子弟,阮籍称之为“繁华子”“夸毗子”,这两类人物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出于同一阶层之中,表现的方式尽管不同,但目的都是追名逐利。阮籍对其的基本态度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悲悯。
《诗经》大部分讽刺诗都是贵族士大夫的作品,是为维护贵族统治而作的,有很多诗篇作者直抒胸臆指出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劝谏,正因为此诗三百表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风格。魏晋之际的阮籍和他的父亲都是魏臣,深得曹氏父子的赏识。所以他的讽刺诗是对曹魏政权的哀落表示惋惜,同时对司马氏政权的篡立进行指斥和揭露。他的讽刺诗是站在一个将亡的政治集团的立场上反对另一个将代之而兴的政治集团,它所反映的矛盾是封建政权内部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阮诗的讽刺与揭露是一针见血似的,深刻而不讲情面,并没有继承《诗经》“温柔敦厚”的精神。
二、超现实的审美倾向
阮籍《咏怀诗》,从诗歌形象中所体现的审美取向来看,具有强烈的否定现实美并追求超现实美的倾向,这又是对《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超越。但比《诗经》更进一步的是,阮籍的《咏怀》也从《诗经》中多次取材,但是作者并不热衷对现实事物的表态,对一般的人类感情相当淡漠。青春、歌舞、美貌、爱情,这些在任何时代、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向来是创作者们赞美、渴望、视如珍宝的形象,在阮籍这里则成了被怀疑、被讽刺、被否定的对象。可能与阮籍对庄子的继承有关,“大象无形”,阮籍在诗歌中对呈现于感官上的外在事物的美的形式,持一种冷静思辨又残酷的态度,他往往从美中看出丑,从生中看出死:
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其十八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其四十五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
《诗经》很多时候在表现事物的形象形式之美,比如《采薇》在兴的时候表现出薇这种植物的萌芽、生长,充满美好向上的感觉,《蒹葭》中更是赋比兴连用,重章叠嶂,音律谐婉,蒹葭的苍茫与伊人的朦胧融为一体。但阮籍对素材的处理方式和态度方面则有很大不同,究其根源在于作者那种对现实美的否定怀疑信念。当然这种审美观念究其缘由还是阮籍因强烈的不满现实的情绪所决定的,是他在现世中跌跌撞撞之后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用这种武器阐释外在的世界。
[1]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
杨琳琳(1991-),女,汉族,河南南阳人,河南师范大学,2014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I207.22A
1006-0049-(2016)16-01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