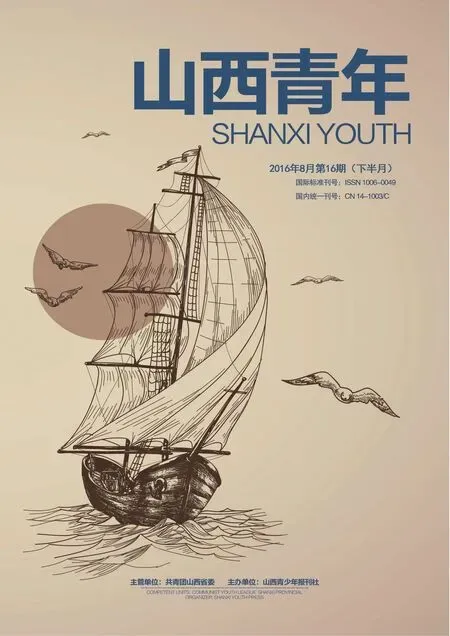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分析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2016-02-04彭修远
彭修远*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分析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彭修远*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在少数民族人口离开偏远山村,向全国的各个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其过程及最终给流动人口家庭和后代带来的结果存在着种种“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面对这种不确定和不可知,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风险社会”理论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并结合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检测数据,揭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当中的社会风险的分配,聚集的社会风险如何进行代际传递,风险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归属认同危机的风险运作逻辑。并提出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等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从而使社会风险再分配。
风险社会理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底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置于自反性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思考,提出风险的定义,“风险的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直接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处理现代化自身导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系统方式。”[1]
一、城市风险不公平分配和代际传递
风险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有着不同的逻辑,王道勇提出“人类社会的分配过程从总体上看是对两种不同性质事物的配置:一种是发展成果的分配,比如财富分配;另一种是发展成本的分配,比如风险分配"[8]但与财富和风险都是按照社会阶层来进行分配,贝克指出”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像财富一样附着在阶层模式上的,但却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社会上层聚集,而风险在社会下层聚集。“[9]而且贝克认为这种风险分配已经得到合法化,并且分配的两极分化还在加剧。”依阶层而定的风险分配的“规律”,以及因之而来的通过风险集中在贫穷弱小的人那里而造成的阶层对抗加剧的“规律“,早已经被合法化,并且风险的某些核心维度今天仍适用。”[10]
根据2013年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来看(本文以下所有数据均出自于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处于城市财富分配的底层同时也处于社会风险聚集的顶层。该数据显示,有收入的少数民族总体月平均收入为800.33元,低于全国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更是远远低于所在城市居民月平均收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关系保障覆盖率均低于汉族流动人口以及户籍人口。综合来看,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综合参保率仅为11%,低于汉族流动人口的12.7%以及户籍人口的33%。具体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为17.1%、18.7%、2.2%、7.7%、27.8%、6.1%、13.5%、5.5%,汉族流动人口的参加比例为22.8%、23.7%、3.4%、4.7%、24.7%、7.5%、18.2%、8.8%,户籍人口参加比例为72.2%、59.3%、34.1%、11.4%、36.1%、16.3%、37.8%、27.3%,除工伤保险以及商业医保高于汉族流动人口外,其余社会保障参与率均为最低。[11]
笔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到的风险聚集主要来自市场和制度方面多维度的、多原因的遭遇的社会排斥,导致不同类别社会风险在他们身上聚集。一方面是制度排斥,中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使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的暂时性和流动性,以及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的供给上遭受歧视性对待,使他们的藩篱与偏颇、情感性认知及自我与社会认同的融入被城市所区隔和另类标签;另一方面是资源短缺导致的市场排斥,由于难以获得足够而且合法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加上受自身资源的短缺和不合理流动等的限制与影响,造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与边缘化境况不断恶化。因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基础很薄弱,导致他们实际风险的承担概率很大,而各项社会保障的参保率又极低,导致他们的风险承担能力很弱。当各种疾病、受伤、失业等风险来袭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当中的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
并且,聚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的社会风险会向后代传递,风险依附于社会阶层进行再生产。在社会上层,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使资源、权力、声望等代际传递下去,形成近来社会瞩目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但在社会下层,社会风险以贫民窟、棚户区和连片贫困地区等形式传递给弱势群体的下一代,形成所谓的“农二代”、“新生代农民工”等现象。社会阶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再生产的原因,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到的各种社会排斥,导致其后代城市里面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缺位和教育投资的缺乏,导致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低于城市其他居民的后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父母大多忙于生计,难以给其子女提供理想的家庭教育,从休闲时间是否经常陪伴子女也能看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父母经常陪伴子女的比例为14.3%,低于汉族流动人口的15.1%和居住地户籍人口的26.1%,相反几乎没陪过子女的比例为9.9%,高于汉族流动人口8.3%和户籍人口1.5%。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本身经济基础薄弱,所得收入大部分用来维持生计,导致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极为有限。
二、风险意识觉醒和归属认同危机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威尔德韦斯(A.Wiladavsky)率先从文化理论的视角解释了公众关注科技风险和风险意识不断增强的新现象,她们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指出,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造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和察觉程度却大大增加。人们感觉风险的增多,更多来自处于特定风险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风险认知程度的提高。[12]贝克也认为风险和知识难以区分,他指出“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风险的感知和风险就是相同的东西。”[13]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其中初中毕业的比例占到35.5%,小学毕业的比例也达到28.6%,未上过学比例为17.4%,大学专科以上的比例仅为6.2%.知识缺乏甚至存在语言隔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初期,缺乏对风险的认识和思考能力,在专家系统和媒体主导风险话语权的语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风险意识被压制。但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时间增长,认知能力将随着他们和城市文明互动增长而增强,这必然将带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风险意识的觉醒。
与风险意识觉醒相伴随的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开始失去他们的心理认同和精神归属,当少数民族文化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开始被现代流行文化所同化而渐渐消解时,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了适应城市生存的环境,部分甚至全盘接受异质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同时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信仰的遗忘和丢失。于此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归属感尚未建立,综合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活动的比例仅有4.5%,低于汉族流动人口6.8%与居住地户籍人口23.1%。具体来看,不论是社区文化活动、社会公益活动以及政治选举活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参与率为10.5%、9.6%、3.9%、3.3%,均低于汉族流动人口的16.1%、15.0%、4.9%、3.8%和户籍人口31.3%、35.1%、53.3%、17.2%。而这将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巨大归属风险,并且造成他们考虑其他风险时的心理焦虑。留在城市,他们面临着汉族流动人口没有的文化差异;回到家乡,他们却发现祖辈生活的环境已越来越陌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逐渐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巨大社会风险的时候,他们在城市却找不到精神世界的归属认同,与城市居民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将加剧他们内心的焦虑。这种转型过程中长期的文化冲突,必将导致在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强烈的价值冲突和角色中断,由于内心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其行为失范,甚至诱发其违法犯罪的风险。
三、推进市民化进行风险再分配
第一,首先要确立强制工伤保险,将受职业病危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其次要确立医疗保险制度特别是大病住院保障机制,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会因大病影响其工作和收入。再次要建立一套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体系,以较低的缴费率和较低的工资替代率将他们纳入养老保险费体系之内,并且实行全国统筹,无论在哪里就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权都可以得到保障[14]。最后,根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建立缴费标准与收入水平联动机制,其社会保险缴费标准要根据他们不同时期的平均收入状况进行调整,保证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能力参与社会保障。
第二,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不但要提高他们的就业率而且要提高他们工作的稳定性,监督企业和少数民族职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并且杜绝相关企业拖欠他们工资的情况,稳定的较高收入将大幅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风险承受能力。而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基本服务,将大幅减少他们的实际风险承受概率,这都将从源头上减少他们遭遇的风险。
第三,保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和信仰,使他们在面对社会风险能够找到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柱。要寻找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互动渠道,规避语体差异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来的认知障碍,让他们面对复杂城市时更有序和可知。城市政府和社区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依然能够有自己的精神归属,要保证他们的风险话语权并让他们参与公共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提高他们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一群体的社会风险。
[1]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7.
[2]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J].战略与管理,2004(1):87-91.
[3]夏国美,杨秀石.《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J].中国社会科学,2006(6):88-99.
[4]郭秀云.《风险社会理论与城市公共安全———基于人口流迁与社会融合视角的分析》[J].城市问题,2008(11):6-11.
[5]谢治菊.《论风险社会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J].前沿,2010(12):137-140.
[6]田艳,王禄.《少数民族文化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0(21):10-18.
[7]祖力亚提·司马义,曹谦.《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风险——新疆少数民族艾滋病性传播现状的社会学定性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13(1):147-154.
[8]王道勇.《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分配问题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5):114-116.
[9]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6.
[10]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6,37.
[11]“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的连续断面调查(每年调查两次),其样本的地理分布涉及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06个城市。本调查利用的是2013年的监测数据.
[12]刘岩.《“风险社会“三论及其应用价值》[J].浙江省社会科学,2009(3):64-69.
[13]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14]程昶志.《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改革与发展,2008(2):118-121.
*四川省教育厅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西南交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高校辅导员专项)(CJSFZ15-10)研究成果。
彭修远(1992-),男,汉族,湖南岳阳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流动人口。
C95;C924.2A
1006-0049-(2016)16-0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