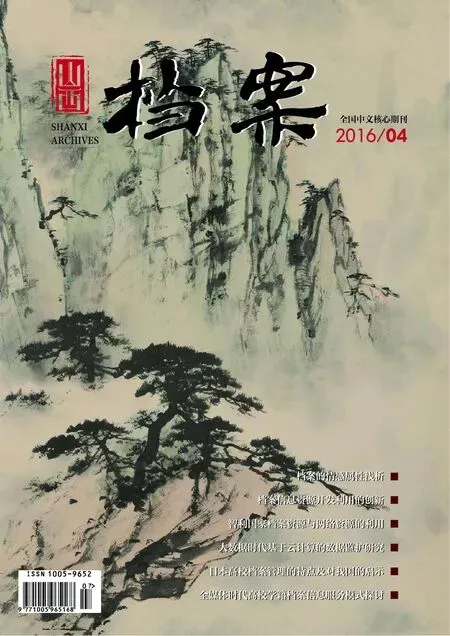大学生通识课程中文献资料的运用与疆域观念的渗透
——以理工院校特点为中心的讨论
2016-02-03LangJie
文/郎 洁 Lang Jie
大学生通识课程中文献资料的运用与疆域观念的渗透
——以理工院校特点为中心的讨论
文/郎 洁 Lang Jie
The Use of Documents to the General cours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Penetration of Frontier Conception
在信息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思潮交融的冲击下,我们可以通过较强概念性和逻辑性,强大的论据链条和丰富的信息量,以及高度概括的理论素养和情感传达,和学生一起分析疆域形成和树立疆域观念,进而培养爱国情操和科学史观。
通识课程;疆域观念;理工院校
在信息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思潮交融的冲击下,我们的大学生通识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命题。在任何一个话题,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遭遇到认同的话语”[1],对于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怀而言,疆域观念是当今历史时期的重要问题,也是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议题。因此,我们在讲授大学生通识课程时,应当贯穿和渗透式地向学生传达晚清社会以来的国家形成和疆域变迁,使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国家观念、疆域观念。
一、具有概念性和逻辑性
我所任教的高校,是一个以理工专业为主体的综合性大学,就读于此类大学的学生,有其特定的个性特征和学科思维特征,本文即结合实际教学工作,浅谈大学生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和学生一起分析疆域形成和树立疆域观念,进而培养爱国情操和科学史观。理工专业为背景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往往接受过一定强度的逻辑思维训练,具有较强的理性思维和概念准则。但是与此对等的,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知识的薄弱。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后的“通识教育”的层面,针对理工科类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思维特征,我认为如果在通识课堂上要传递疆域观念,那么就应该从概念分析开始,从文献资料的介绍开始。
首先应当从“疆域”一词的概念着手。“疆域”具有界限以及界限所包纳空间的含义,当代学者比较认同的概念在于“所谓疆域,就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境界所达到的范围,而领土则是指在一国主权之下的区域,包括一国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2](p4)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疆域问题和疆域概念的讨论,与晚清近代化的中国和外敌的侵略同时出现的,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有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3]这实际上是学者首次将中国的“疆域”观念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相对性的讨论,这种视角是具有开拓性的。其中“中国之中国”指的是自古以来的天朝观念,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疆域观念;随着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传统的中国核心论获得了不同视角的讨论,在来自于他者的游记视角而言,中国疆域限定于亚洲边界,因此称之为“亚洲之中国”;明清以来,西学东渐,中国被迫走向了近代国家的步伐,便逐步形成了“世界之中国”。这是对于中国疆域以及疆域观念的演进史的高度概括。顾颉刚、史念海所著《中国疆域沿革史》[4]则明确提出了疆域的范围和科学的认定,并与此同时提出了疆域形成的四个重要的时期,这与顾颉刚先生长久以来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从中可以看到梳理中国疆域和疆域观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化国家认同观念的发展相辅相成,且比较容易自成体系,为学生所理解,具有较为可信的科学性。
其次,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疆域观念的演进与根本性的“中国”观念、“民族”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大多刚刚进入大学门槛的学生,对于这样几个重要的概念之间的联系,往往不能够窥其真实,从而影响了通识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核。
在传统中国的世界观中,“中国”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王朝的合法性在于其必须代表中国文化的正朔,中国“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以天下兼国家” 的大一统国家。视其他民族为“化外”的“夷”、“蛮”,对于周边民族的统治,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领土、资源、边界等,而是“礼”。因而,古代中国从来不以法律界定自己的领土,而是实行的一种“模糊”边界。“中国”一词开始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是从 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的,“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5]说明,鸦片战争前的近代中国在王朝危机和主权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传统的“天朝大国”形象轰然陨落: 乾隆中后期,“持盈保泰”的治国之策使清政府已失去了早期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开始走向没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处理现实国家利益与“属国”利益关系,逐渐形成了“宁失藩服,毋损郡县”[6]的外交策略,一定程度上表明清王朝逐渐感到了国家主权的危机和边疆的重要性,并将“郡县”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这说明了疆域观念与“中华”观念的逐步统一的过程。
以上是对于在近现代史授课过程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的概念和疆域之间的联系,正因联系如此紧密,而疆域观念的讲授和宣传颇为不足的局面,我认为,这一授课要点的提出和弥补,有利于大多数课堂内容的理解和深入讨论,并且由于疆域概念的确立,使得很多较为形而上的知识层面能够寻找到切实的落脚点和切入点,使概念具体化、形象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情感传递。
二、具有强大的论据链条和丰富的信息量
从具体的授课内容方面看,我认为很多理工科学生对于通识教育课程感觉到枯燥乏味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于人文学科当中的文献资料和内容深觉空洞、晦涩,难以理解。我认为疆域问题,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教育与话题突破口。以下将做一个文献列举和分析来讨论疆域问题作为论据链条,给教学带来的丰富的信息量和新颖的角度。
《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订立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条约由《阿巴哈依图界约》和《恰克图界约》组成,条约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上游清朝北部与俄国边界的走向,即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的边界走向。为了抵制沙俄在北方蒙古地区的扩张,清政府与俄国经两年谈判,1727 年9 月 1 日签订《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失去了东北—外兴安岭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量疆土。第一条,决定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1864 年《堪分西北界约记》、1877 年中俄《伊犁条约》、1882-1884 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将以上条约的签订罗列在一起,再佐之以图,基本上能够描绘出晚清西北和东北疆域的演化进程。
三、具有时代性、政治性和共情性
对于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而言,学生们当中对于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相关设备的接触和了解,要有更强的普及型,针对移动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使大学生更易获得多种思想信息,正是这种自由性和信息冲击,加上网络上一定程度的匿名性,网络上的思想更加多元化,各种思想在网络上互相碰撞,势必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作为教育者,应当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向。
以疆域观念为例,可以将目前西方较为流行的疆域与国力性质的类比,总结为三种:阿尔弗雷德·马汉(A1fred Thayer Mahan)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海权国力论:争霸世界的关键在于夺取制海权。并且将这种能力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历史进程最有效地联系在一起。麦金德则提出了陆权国力论。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指出,被称之为世界“心脏地区”的大片内陆区域,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较发达,加上铁路、公路网等陆上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大陆国家重新占据优势,具有较强的国力。[7]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1as Spykman)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8]以上诸种学说,又有着深刻的产生土壤和社会背景,并对此进行逐一分析,这样一来,学生面对互联网上较为片面和极端的言论,则有了科学性和严谨性的警惕,不宜被未经思索的言论轻易影响。
综上所述,在信息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思潮交融的冲击下,我们的大学生通识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命题。对于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怀而言,疆域观念是当今历史时期的重要问题,也是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议题。我们在讲授通识课程时,对于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离不开与疆域形成和疆域观念形成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以此来应对各方面信息的冲击和反射。我们可以通过较强概念性和逻辑性,从文献分析出发,建立强大的论据链条和丰富的信息量,以及高度概括的理论素养和情感传达,和学生一起分析疆域形成和树立疆域观念,进而培养爱国情操和科学史观。
(本文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2016年度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支持,课题编号:BJSZ2016ZC059。)
(责任编辑:阎海燕)
[1] Richards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 1996:7.
[2]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M],商务印书馆,1997年.
[3]梁启超,《中国史绪论》,载《清议报》[J],1901年9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
[4]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商务印书馆,1999年.
[5]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棋译,《草原帝国》[M],商务印书馆,1998年.
[6]《清史稿》[M]光绪十一年春二月初二日,李鸿章奏曰.
[7] [英] 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M],商务印书馆,2010年.
[8]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1942.
K253
A
1005-9652(2016)04-0153-03
郎 洁(1982—),女,山西阳泉人,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