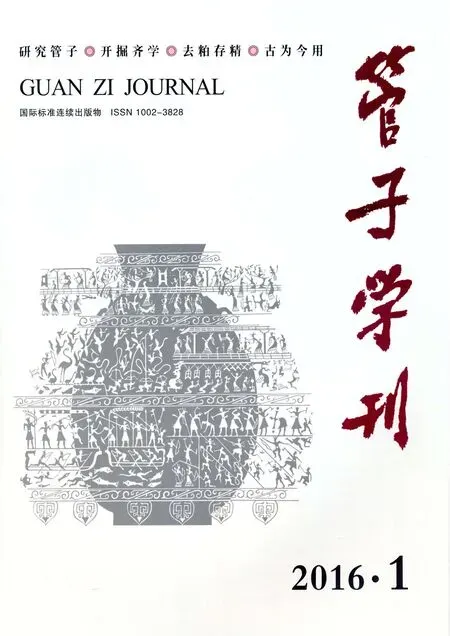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歌中“居”的美学意蕴
2016-02-03杨锐
杨 锐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古今论坛
中国古典诗歌中“居”的美学意蕴
杨锐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居住源自于个体的生存和安全需求,是生命活动的必须。在这之上,诗人以其诗意化的精神体验,自觉体合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律,在与自然万物的情感交流中不断地实现自我,这是诗人的精神“栖居”方式。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诗人不断建构着与自然融合为一的亲和关系。这种由内而外的生命活动正是我们提升“居”的美学意蕴的基点:在艺术和审美中感悟宇宙自然的无限宽广,体认我们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进而反观自我,实现人“居”于大地之上的自由存在。中国古典诗歌对“居”的这一意蕴有着丰富而具体的体现,古代文人或隐于超然世外,或恋于田园牧歌,或耽于静谧空灵,或安于乡野自适,不断构建着精神和心灵的诗意栖居之地。
关键词:“居”;“万有相通”;节律;中国古典诗歌;
“居”首先是我们的身体生活在大地之上,植根于此,我们要在无限宽广的宇宙自然间寻求一种亲和感,一种家园感。居住是每个人生命活动的必须,是个体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当身体需求基本满足之后,随着人主体性的发展,我们总是要不断地实现自我。在人类社会中,诗人以其清静无为的诗性体验为我们实现精神自由开辟了出路。海德格尔说到:“诗人的诗意栖居先于人的诗意栖居。所以,诗意创作的灵魂作为这样一个灵魂本来就在家里。”[1]24我们渐渐认同诗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在艺术和审美中感受到了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我们最终发现,建立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是实现人自由存在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倡导人“诗意地栖居”,而“诗意”不是同出一辙,而是和而不同。中国古代诗人以其敏锐的感知力和想象力,为我们进一步建立与世界的和谐关系做了先导。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尤以韵味和意境见长,而这种诗歌艺术唯有依靠平静的内心体会才能够感受到。中国古代诗人对宇宙自然有着独特的感知方式,他们能够以审美的情怀感知自然的物情,以包容性的自然物境提升自己的心境。所谓心境,便是诗人于现实之上构建的精神自由之地,而唯有在宇宙自然间,这片精神之地才能无限延展。
一、“居”的美学意蕴
张世英先生在论述“万有想通”的思想时说到:“每人、每物皆宇宙普遍联系之网上的交叉点……每一交叉点都反映全宇宙,或者说,就是全宇宙。”[2]40-41对于“居”的把握,也应选择这样一种由外而内,进而由内而外的视域。“居”从最初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必须,到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进而成为我们倡导的人在世界中的自由“栖居”方式。“居”的这一变迁过程,便成为我们反映人类与世界关系不断发展的“交叉点”。“居”的基础是人与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一种关系性存在。最初的居住行为源自于我们对外界环境的应对,我们在自然面前总是被动的,人与自然环境建立的是一种单一的外在关系。当定居生活产生之后,我们便有了归属和自我主体之感。在这之上,诗人以其超越常人之心,以其诗意化的精神体验,自觉体合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律,精神自由“栖居”在与自然万物的情感交流中。诗人以其审美的态度建立起与世界的多维关系,这便赋予“居”丰富的内在意蕴。我们最终明白,人类社会终归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在宇宙自然间寻求到家园之感,我们才能实现精神的无限自由。今天,我们倡导“诗意地栖居”,提出人如何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也应以这此来审视我们在世间的存在关系,体认人在与世界和谐关系中的自由存在。
“居”必须不能偏离人始终作为身体存在这一核心,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首先是以身体作为中介。身体的活动是富有节律的,脉搏的跳动、情感的波澜都是我们生命节律的体现。宇宙自然也有自身的节律运演,而人在宇宙自然间生存便要体合自然的节律。我们根据自然的节气变化在大地上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便是最直接的体现。生命节律是人与自然万物有机关联的基础,“诗意”也源自于我们对自然的节律感应。诗意和审美根源于人与自然相融相处的亲和互动,当我们以自身的情感体合自然的生命节律时,便产生了美感。曾永成先生说到:“节律形式和由节律造成的感应,就这样不仅赋予世界以灵气和诗性,也建构起世界最深邃的统一性……在人的审美感知中,任何微细之物都幻化成了无限的存在,显示出深邃而悠远的意义。”[3]我们以诗意的精神体验,感悟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律,融身于物我一体的整体关联之中,实现人“居”于大地之上的自由存在,这便是我们最根本的“家园”感,这便是人“诗意地栖居”。人的生存并不是孤立和抽象的,这便涉及到我们如何定位自己以及如何处理与身边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要遵循自然的节律并参与到自然整体的循环往复之中,而不去扰乱这种节律。人最终以审美、诗意的态度栖居在生态世界之中,这是人类成长的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
中国古典诗歌对“居”的美学意蕴有着丰富而具体的体现,我们能于其中发掘出宝贵的精神滋养。在“兼济天下”之余,中国古代诗人更愿意到自然中去寻求自我,他们或隐于超然世外,或恋于田园牧歌,或耽于静谧空灵,或安于乡野自适等等,各自以不同的精神“栖居”方式感悟清静自由的人生。古代诗人自我实现的方式的不同,便表现了诗人不同的心境,而诗人的心境决定了诗歌意境的创造。袁行霈先生说:“诗人独特的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的情趣和性格,构成意境的个性。”[4]35。虽然诗人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却也都是源自他们对宇宙自然的诗性体验。对中国古代诗人来说,宇宙自然有了更为浓烈的精神归宿感和家园感,他们在神与物游的境域中构建着共同的精神自由之地。张世英先生说到:“各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唯一的全宇宙……相通的关键在于不同者所反映的全宇宙的唯一性。”[2]41“全宇宙的唯一性”是一切存在的根底,古代诗人以超拔的心境自觉体合这种唯一性,向我们诠释了人“居”于大地之上的本真意义。
二、“居”于躬耕自然
隐居生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独善其身”的一条人生退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为文人选择隐居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农业社会的自然地理环境可以为他们提供足够而又幽静的生活空间。然而,唯有真正不为世俗物欲所累,才可以真正发现田园生活清新自然的风光,才能够把恬淡质朴当做一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情趣,才可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超拔。
历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崇拜一直不曾消退,然而陶渊明的诗歌好读不好学却已是不争的事实。陶诗历来以自然平淡的审美风格为人称颂,其中的意象也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但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精神意蕴。“居”是陶诗中多次提到的一个重要审美意象,不仅是“结庐在人境”的生活之居,更是“此中有真意”的精神诗意之“居”。陶渊明在诗歌中描述了多处宁静安然的生活场景,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歌皆出自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些村居环境环绕着自然风光,构成了一幅幅宁静和谐的画面,不仅是诗人的居住之所,更是诗人安顿心灵的一方净土。诗人还在诗歌中多处谈及自己生活中“居”的状态,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衡门之下,有琴有书”(《答庞参军》)、“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移居》),等等。这些诗篇不仅流露出诗人日常生活的宁静恬淡,表现了诗人高涨的生活热情,更是诗人无所欲求的精神自由本性的彰显。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将审美情趣灌注于生活之中,“居”在陶诗中是一种审美和精神之维。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他以自然平和的心态躬耕田园,并充分享受劳绩后身心的欢愉。诗人在《归园田居》中吟诵:“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吟诵:“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在《桃花源诗并记》中吟诵:“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诗人在这些诗篇中的精神状态和荷尔德林的诗句蕴含的意蕴竟有许多地方默然契合,可以说,“居”的精神意蕴是解读陶诗歌境界的关键所在。自由自在的诗意之“居”是陶渊明毕生的精神所求,“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海德格尔曾说到:“诗人越是诗意化——他的言说越是自由。”[5]70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吟诵:“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诗人感知到世俗之网对人生束缚的悲哀,所以他抛却一切,在躬耕自然的无欲无为中享受劳绩后的精神闲暇,以简单质朴的语言言说着无尽的诗意,于诗性之美中达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境地。
陶诗不仅有平淡清新的自然美,更有着对有限人生在存在意义上的哲思。陶渊明嗟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同样慨叹人生短暂,但他却找到了一条超越人生有限性和自我解放的道路。陶渊明在《形神论》中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诗人随顺自然生命的韵律节奏,置身于宇宙的生命循环往复之中,超越人孤立存在的狭隘视角,努力追寻精神的无限诗意与自由。对陶渊明来说,“居”是一种生活态度,“居”的美学意蕴完全在生活之中体现,他将艺术与人生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陶渊明曾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不是诗人的矫揉造作和故作玄深,而是发自本心的生命体验。郭杰教授说到:“只有把领悟宇宙真谛的自然观和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观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认识陶渊明的精神特质和诗歌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之所在。”[6]诗人躬耕田园,醉心于喧嚣之外的静穆,劳绩之后的安然,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真实。陶渊明不过分纠结于物质的利害,以同情和爱来亲和外物,以平淡之心体验生活与人生的情趣,他是如此自觉和彻底。
三、“居”于田园牧歌
自陶渊明诗歌以来,那种冲淡平和、悠然自得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便成为后世文人所向往的精神“栖居”之地,田园诗歌的创作在唐宋兴盛一时。在田园牧歌式的平和生活中自在悠然,以一种闲静无为的内在之心欣赏周围的田园意趣,“居”的美学意蕴尽在这样一片幽静平和中得到彰显。
初唐诗人王绩继承了陶渊明的田园诗,为王、孟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开创了先声。王绩在其诗歌中充分表达了对世俗功名的厌倦以及对田园生活的憧憬与爱恋,他在《解六合丞还》中吟诵:“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彭泽有田惟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使百年相续醉,何辞夜夜瓮间眠。”*本文所引唐代文人诗歌皆出自中华书局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整篇诗歌表达了诗人愿在林泉烟霞间自由徜徉的生活渴望,对陶潜、阮籍悠然旷达的欣羡,诗人但愿醉卧长眠,也不想为谋求功利而碌碌无为。王绩在《春日山庄言志》吟诵:“平子试归田,风光溢眼前。”“去去人间远,谁知心自然。”诗人在诗歌中着力描写了田园风物的清新素朴,表达了自己回归田园的内心喜悦,向往远离“人间”的归隐生活。诗人远离社会政治纷扰,以宁静平淡的田园之心发现自然景物的意趣横生,如诗句“溪流无限水,树长自然枝”(《自答》),“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情流”(《赠程处士》),“引流还当井,凭树即为楹”(《山中独坐》),“密藤成斗帐,疏树即檐栊”(《山家夏日九首》)。这些诗句有的描写自然景物原初的野趣,有的描写诗人和自然物相居无忤的意趣,充分表现了诗人的田园生活志趣。田园生活和自然风物带给诗人的无限乐趣比什么都真实,带给诗人可靠的精神归属之感,唯有在充满生机的自然间,诗人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存在感。王绩在《田家》诗篇三首中吟诵:“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倚杖看妇织,登垅课儿锄。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
唐宋尤其中唐以后是一个注重表现主体心灵和情感感受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人多有一种对清新淡雅之美的特定欣赏情趣,形成了盛唐文人对平和安适田园生活的憧憬。盛唐文明为时人提供了太平安乐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山庄别业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普及开来,为他们选择最为理想的亦官亦隐的隐居方式提供了条件。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注意到中国唐代诗人关于私人生活意味的诗歌创作,他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一书中说到:“中唐时代,个人性的诠释绝非仅仅限于天道、死亡、毁灭之类的大问题。它最为典型的形式,或许乃是一种戏谑式的机智;它很轻松,诠释行为看来似乎是没来由的。这一类机制的游戏,往往与家庭生活的小小乐趣相连……小园逐渐代替荒山野景成为自由的所在,而自由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7]67-70家庭小园代替自然野景成为唐代文人的乐趣之所,文人对于“私人空间”的选择已多数摆脱了政治性影响,而更多源自内心的诗意性精神体验。孟浩然塑造了一种理想的田园生活,表现了诗人对田园农家生活的热爱之情。诗人在《过故人庄》中便描写了这样一种生活场景,诗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如此清新怡人的自然风光以及闲适质朴的农家生活,让人忘却一切尘世烦扰。孟浩然的田园诗歌多数表现了生活环境的幽寂和诗人的安适闲逸,他在《夏日南亭怀辛大》中吟诵:“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淡淡的荷香,清脆的竹响,幽寂的夏夜和诗人闲逸的心境契合的竟是如此美妙。《白云先生王迥见访》也是变现了诗人平日的闲暇,诗云:“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山中逢道士云公》《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诗篇都勾勒出村居生活的平淡,下山的牛羊,耕种的农夫,伫立的村妇,采樵、卖药的人,归客等这些乡村意象是如此朴素清淡,却令人心驰神往,这便是诗人的高明之处。
诗人王维是亦官亦隐的典型代表,王维的诗歌多以盎然的画意勾勒田园风光的清新明朗,所以苏轼评价王维的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在隐居淇上时作《淇上即事田园》一首,诗云:“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描绘了淇上风光的恬静优美。后王维隐居蓝田辋川别业,诗人在《积雨辋川庄作》中吟诵:“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动静相衬,描写了夏日雨后清凉活泼的景象;诗人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吟诵:“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表现了自己超然安逸的心境。王维还有很多诗篇像《渭川田家》《山居秋暝》《春园即事》《清溪》等等,这些无一都以清新朴素田园生活为题材,这些诗作都是表现了诗人闲居时的真淳自然的心境。
四、“居”于静谧空灵
“空灵”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范畴,这种充满禅意的清幽意境是一个无限永恒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对充满俗务羁绊的现实人生的超出和解脱。诗人在无尽的诗情与想象中,超越当下的有限时空,以无穷尽的自然物象来表征自己同样宽广和空静的心境。这种无所阻隔的精神自由与“居”的美学意蕴不谋而合,我们以此来探寻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存在状态。
王国维先生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王维的诗歌历来以“空灵”的意境著称,诗人的精神便“栖居”于这“无我”的静谧之中。然而,王维诗歌的“无我”却不同于庄子“心斋”“坐忘”的精神陶醉和佛教“万法皆空”的虚幻。王维把认同自我真实的、感性的存在,把自我看成无限宽广的宇宙自然间的一部分,与其他自然物一样遵循自然的节奏运演,因而在宇宙生命的“寂静”中遗忘了自我存在。王维描写的不只是外在的自然美,而是在构建一个清静虚空的心境,并于其中反观自我,在这种自我主观性的强烈体认中诗意地生存。王维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观照,不是外在的浅层描摹,而是对自然万物生命进行心灵的体悟。孙昌武先生谈到:“王维诗所体现的胸中佳处,在于他创作构思中发展了新的审美原则:由于强烈的内心主体意识,外境不再是与主体相对立的客观对象,而成了‘为我之物’。它们或者渗透了‘我’的感受,甚或成了‘我’的心态的反照。”[8]84如王维在诗篇《辛夷坞》便塑造了一个无人打扰的空寂世界,诗云:“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种“空”实则来源于诗人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体验,这是一颗清静无为的感悟之心,人世喧嚣,唯有自然万物依然在有节奏地运演生命的韵律。这种思维和审美方式成就了王维的诗歌创作,在他的诗篇中我们随处都能感悟到这种“空灵静谧”之境:“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山涧中。”(《鸟鸣涧》)“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等等。王维的笔下是一个自在自为的世界,这里面没有人的存在,或者说人同其他自然物一样,像草虫、山鸟、明月、松果一样消融在自然界周流上下的生命韵律当中。诗人以一颗清静的心灵和细腻的情感感知自然生命,自然万物有着自生自灭的生命律动,循环往复、 生生不息。王维带着鲜明强烈的主观感情去亲近大自然,融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为一体,传达出他对于大自然自在自足的生命运动的美妙体验和无限自然世界的感悟,也是诗人对于自我生命的重新认识和把握。王维诗的意境反映出的便是诗人平静恬淡的禅意心境,宗白华先生说到:“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9]156诗人对自然万物的体验,已不仅仅局限于对具体的、有限事物的把握,而是通过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宇宙自然的无限宽广,探究“生命的本原”和个体在天地间的意义所在。受禅宗的影响,唐代还有许多诗人也表现这种出“空灵”的意境,表现出诗人自由清净的内心世界。常建在诗篇《题破山寺后禅院》中吟诵:“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闻钟磬声。”柳宗元在《题寒江钓雪图》中吟诵:“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李华在《春行寄兴》中吟诵:“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等等。
五、“居”于乡野自适
入世与退隐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双重心理矛盾。不同于陶潜的政治隐退和苏轼的彻底超脱,清代文人蒲松龄一生致力于科举考试,虽然仕途坎坷,然而亦儒亦农的蒲松龄却能够过着苦中作乐的自适生活。晚年的蒲松龄回到家乡,家居生活的宁静质朴更是让诗人放下了外在的功利欲求,体验那份悠然恬适的自由心境。
蒲松龄因小说《聊斋志异》闻名于世,然而他不仅是位小说家,他也有很多令人称道的诗作。蒲松龄虽然一生热衷于考取功名,但他却能够在《聊斋志异》的幻化世界中进行诗意体验,在乡野之居的真实生活中自适安然,以精神的超拔自由解构和弥补现实人生的不如意、不自由。蒲松龄的诗创作于他热爱的土地之上,诗人于其中表现自己率真质朴的自然本性。蒲松龄一生生活于乡野山居,因而诗人多有描写农家生活的诗篇,这些诗篇大多表现了农民生活的疾苦,体现出诗人关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除此之外,诗人也时有表现乡居生活的闲适安乐,诗性地展示了他在坎坷人生道路之余的生活情趣与精神自由。《草庐》诗两首描写了蒲松龄南游归来的家居生活,诗云:“晴窗书卷微尘净,午书松风斗室寒。”*本文所引蒲松龄诗歌皆出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家居虽然贫寒,但是能够暂时摆脱俗务“微尘”的扰乱,诗人的内心是如此的闲适安然。蒲松龄曾在为他人庄园的题词中吟诵:“花径儿孙围笑语,石亭棋酒话桑麻。门前春色明如锦,知在桃源第几家?”(《题安去巧偕老园》)表达了自己对安去巧自在闲适的隐居生活的欣羡。诗人还经常描写乡野生活的宁静质朴,如“青岚带雨笼茅舍,黄碟随花上豆篱”(《山村》)、“衣分缭白萦青色,犬吠围桃傍柳家”(《山村》)、“邻翁相对话桑麻,村舍丰年景物佳”(《闲居》)等等。这些诗篇体现诗人对乡野生活的迷恋,它们真正源自于诗人诗意化的内在情感。路大荒先生编纂的《蒲柳泉先生年谱》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先生七十一岁。是年贡于乡。先生自是年家居。……先生家居,东阡课农,南窗读书,心闲意适。”[10]1801-1802蒲松龄科考一生,到了岁暮之年,在乡野家居的恬静自适中真正抛却了功名牵绊,在悠然宁静的的生命体验中安享无欲无为的自由心境。这些诗句便表现了诗人晚年自适的家居生活,“垂老倦飞恋茅衡,心境闲暇梦意适”(《斗室》),“斋居浑无事,扫径拾损箨”(《课农》),“寡营脱俗累,闭门远尘鞅”(《老慵》),“余年凭造物,何事费思量”(《自适》)等等。
蒲松龄早年南游,后在毕府坐馆三十余年,真正在家乡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然而蒲松龄苦中作乐的自适心境却伴随他的一生。蒲松龄三十一岁时离乡南游,途中有大量诗篇表现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仕途坎坷的苦闷,但却也不乏诗人游历异乡风光的自得其乐之情。蒲松龄在诗篇《途中》中这样描写到:“青草白沙最可怜,始知南北各风烟。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马踏残云争晚渡,鸟衔落日下晴川。一声欸乃江村暮,秋色平湖绿接天。”这首诗描写了南方暮秋时节的自然风光,“途中寂寞”表现了诗人南游途中的闲适,“招摇”即逍遥意,而“意欲仙”更是体现了诗人悠然快朗的心境。诗人在《黄河晓渡》描写了这样一幅画面,诗云:“一曲棹歌烟水碧,沙禽飞过白频洲。”诗人的心情正如河边沙禽一样自由轻盈。诗篇《湖上早饭,得肥字》更是表现了诗人的惬意,诗云:“湖上烟寒远树微,平沙鸥鹭尽忘机。归鸿一字愁中断,浓绿千山雨后肥。”诗人暂时忘却世间机诈巧变的利益关系和仕途坎坷的愁闷之情,以审美的心境陶醉于这秋天美
景之中,拈韵赋诗,十分惬意。《山中》诗两首是蒲松龄南游北归时所作,“芳草斜阳游子路,小桥流水野人家。寒烟九点参差见,一径荒凉噪暮鸦”,描写了山中环境的清幽恬静;“高原一带净无尘,千里归来世外身。落絮飞英春树暖,断桥幽谷鸟声新”,诗人暂时忘却俗务的烦扰,渴望在山中隐居,以一颗清静之心感悟自然的生命韵律,领悟山中的自然美感。蒲松龄四十岁起设帐毕府石隐园,作诗《石隐园》描写园中美丽春色,表达对毕际有隐居行为的称赞之情,借此再次抒发自己逃离世俗的内心渴望。蒲松龄在《逃暑石隐园》中吟诵:“两餐如客饥投肆,初漏无声静似禅。”“小山搢笏如人拙,瘦竹无心类我痴。”清幽的环境、闲适的生活让诗人能够以石为友,与花结缘,诗人看到园中“小山搢笏”想到人的劳心作伪,而愿如瘦竹一般无欲无心,解放功利之心对精神自由的羁绊。
张世英先生说:“诗的语言(严格说来是语言的诗性)的存在论根源在于人与世界的融合,重视不在场者,一心要把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11]185隐藏在在场者背后的“无底深渊”便是我们与宇宙自然的整体关联,我们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诗意性体验,进入这种关联之中,感悟人与自然原初为一的自由存在之感。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曾永成.节律感应:人本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
[4]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6]郭杰.陶渊明“真意”探微[J].学术研究,2015,(4).
[7]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6.
[8]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0]路大荒.蒲松龄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方子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6)01-0070-05
作者简介:杨锐(1991-),男,山东德州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及学理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0BZW001)。
收稿日期:201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