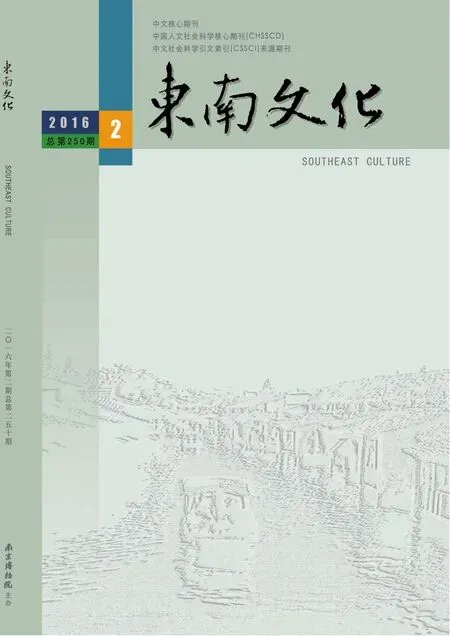考古遗产的社会价值与产业化利用路径探讨
2016-02-03厉建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厉建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考古遗产的社会价值与产业化利用路径探讨
厉建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内容提要:考古遗产无疑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语境下,它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随着大众考古理念的增强以及大众对考古遗产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已成为实现遗产价值、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同时也是使考古遗产得以可持续传承和传播的一种发展途径。考古遗产产业化利用的具体路径有:一是遗产的资源化,即对遗产的文化解读与阐释;二是对遗产本体的文化旅游开发;三是对遗产内涵与符号的创意策划,与演艺产业、影视产业和创意产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
关键词:考古遗产社会价值大众参与产业化文化产业
鉴于对考古遗存保护、管理的需求,1990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全体大会第九届会议在瑞士洛桑(Lausanne)召开并通过了《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该宪章明确规定了考古遗产的保护和合理管理的全球性基本原则和准则。其中对考古遗产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即“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的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这些遗存是由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以及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组成。总的来说,考古遗产包括遗迹与遗物两大类。遗迹有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前者包括洞穴遗址、聚落遗址、古城址、古窑址,以及宫殿址、住宅址、寺庙址、矿冶址及有关设施,等等;后者包括单座墓葬、墓群、陵墓及有关设施。遗物的种类繁多,有工具、武器、日用器具、装饰品等[1]。从以上对考古遗产的界定来看,考古遗产是属于通过考古调查、勘探、田野考古发掘等考古方法获得的物质类文化遗产。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的发展,我国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政策逐渐由原先的单纯保护发展到保护利用和活化文物,不断探索和拓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渠道和模式。2016年3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对文物的拓展利用提出了新的内容。其中提到要“发挥文物资源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壮大旅游业中的重要作用,打造文物旅游品牌,设计生产较高文化品位的旅游纪念品”,还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鼓励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探索开发文物保护保险产品,拓宽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利用的渠道”。文化遗产的活化与利用是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实现其社会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方式。而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现代语境下,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考古遗产的社会价值,如何实现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利用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 考古遗产社会价值的传承与实现
(一)考古遗产的社会价值属性
考古遗产具有公共资源的特征,承载着古代的文化信息,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遗产语境下的考古学,应该更加关注考古遗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发挥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考古遗产是大众的遗产,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如何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重视的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学价值更好地展示出来,让社会大众享受考古遗产的成果,实现其社会价值,这是考古遗产社会化进程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随着遗产大众化理念的深入与发展以及人们对考古文化需求的提升,考古研究人员需要挖掘考古遗产的文化内涵,发挥这一社会资源的传播和教育功能,使其价值得以传承和发扬,获得社会力量对遗产保护的支持。因此,“考古学家不仅需要关注考古遗产的价值认知,同时需要高度关注考古遗产的价值传承和价值实现。所谓价值传承就是通过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使其所具有的价值能够长期得以延续。而价值实现就是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充分使其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从而具备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2]。
当前我国大型或重要的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仅考虑到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问题,而且也已开始关注如何向社会展示和利用的问题。即“考古学越来越注意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公共考古学成为近年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公共考古学不仅是向社会大众普及考古知识,而且开始研究考古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考古发掘的伦理道德以及考古资源的后续保护、管理与利用问题”[3]。作为依托遗址本体而建设的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休闲公园、考古模拟体验基地等则充分体现了遗址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向社会展示和服务的理念,具备了科研、教育、体验、游憩、休闲等旅游功能。它们不仅保留和传承了文化遗产,促进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大众共享遗产成果提供了一个公共的文化体验空间。
另外,随着新博物馆理念的发展,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也逐渐从收藏、科研转向教育和服务公众,由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中心,由静态、单一展示转向动态、多维的创意展示。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咨询、体验、培训等活动,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拉近了大众与博物馆之间的距离。再者,最近兴起的“社区博物馆”发展模式也强调博物馆应该与社区建设发展相结合,收集和展示当地历史遗存,体现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帮助社区建立地域文化特色,塑造社区认同感,加强社区博物馆与当地社区居民的紧密联系。
(二)大众参与:遗产社会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
考古遗产社会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组织、媒体、个人的积极参与,考古遗产单位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将考古成果展示给大众。同时,随着大众文化素质的发展和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大众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考古遗产的文化传承、传播、保护和利用活动中。
1、考古遗产的大众化传播。现代传媒架起了沟通大众与考古的桥梁,在促进考古社会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电视、报纸、网络及新媒体对考古发现的报道越来越普遍,其中媒体对考古的直播和专题报道成为沟通大众与考古遗产最直接的通道之一,譬如中央电视台2000年对北京老山汉墓的直播、2009年对河南“曹操高陵”考古发掘的现场直播、2012年对山东纪王崮春秋古墓的直播、2015年对“丹东一号”水下甲午海战舰的水下考古直播以及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发掘工作的直播等。考古直播通过大众媒体拓宽了受众范围,将某一地域的考古事件瞬时变成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关注的事件,通过通俗化的语言和真实的画面给以观众直观的展现,避免了既往印象中考古发掘的枯燥乏味之感,引起人们对古代文明的关注,提高了文物保护意识。
考古鉴定与收藏节目也正因社会上考古和遗产热而兴起,如中央电视台的《寻宝》、《一槌定音》,河南卫视的《华豫之门》,陕西卫视的《华夏夺宝》。虽然有学界专家批评这类节目让大众普遍倾向于对文物本身市场经济价值的关注,而忽略了其在历史上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容易带来大众对文化遗产的片面化解读。但这类节目的确借助现代传媒的优势普及了大众对考古和文化遗产的认识,促成了大众的收藏热潮,仍不失为文化遗产传播的有效途径。
2、大众共享遗产价值。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文化精神的需求日益增强。各地兴起文化建设的潮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两翼。保护、展示文化遗产和发挥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功能,已成为提升当地文化内涵和城市形象的题中之义。一方面,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在努力营造文化氛围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文化地标、文化设施,博物馆的发展速度和建设数量也体现出国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大众对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大众对文化遗产的消费与日俱增。包括参加博物馆举办的各类展览、讲座、培训、鉴赏、体验等文化活动,以及到文化遗产目的地如陕西秦始皇兵马俑遗址,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博物馆等进行旅游活动,体验考古模拟项目,或者直接参观现场的考古发掘,感受考古发掘的神秘性与科学性,甚至参与古代器物的模仿制作、修复等活动。
3、社会参与遗产的保护利用。考古遗产的保护与规划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社区居民的利益,而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引导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正确认识,将会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顺利开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约有11万余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则高达64万多处[4],另外还有大量未定级的低级别文物。单单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人力投入进行保护肯定力有不逮,因此政府要创新管理思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建立社会公益组织并与社会资本进行合作,拓宽文物保护的资金渠道。国际上把公众对遗产保护的支持程度作为评估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指标进行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参与体系,例如英国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团体、慈善和基金会组织等,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着管理、经营、咨询、监督、筹集资金等职能。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不论在实践领域抑或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尝试和探索均在有序展开”[5],出现了一些保护文化遗产的民众、志愿者以及由专家学者等精英人士组成的民间协会、保护组织等等。
二 考古遗产的产业化:遗产社会价值实现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产业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是按照市场运作方式进行资源整合和实现经济价值的过程。在欧美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经营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根据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已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了文化产业发展领域。那么对于遗产类文化产品与服务也可以采用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生产和提供,以产业化方式来反哺遗产保护。而“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把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以产业化的方式使它们的价值属性为社会公众所认识和了解,加速它们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6]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利用也是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考古遗产的产业化体现了产业化视野下考古遗产的文化资本属性,为遗产的保护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同时通过产业化利用也实现了考古遗产的大众化传承和传播,获得大众对遗产的认识以及参与热情。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的发展以及大众对遗产文化需求的逐渐增长,文化遗产多方面的价值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创意产业的交叉融合已鲜明地体现出其经济资源的价值属性。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具有资源性,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进行发掘、开发、利用、交换和交易[7]。因为,在今日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也势必影响文化遗产的存在命运。在文化产业兴起的过程中,各种文化遗产将不可避免被当作文化资源来看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开发、利用局面[8]。考古遗产也已进入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洪流中,成为地方重要的文化资本,成为区域的竞争力和品牌优势。政府也已意识到独特的文化资源不仅是一种软实力,更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硬实力。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推销其独一无二的遗产取得相对优势,竞争旅游市场,获取收入来源[9]。据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统计,2009年其遗产旅游推动了40%的海外旅游者前往英国,排除自然景观外,为英国创造了27000个工作岗位和119亿磅的GDP收入[10]。
对于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产业化经营问题,学界长期存在着“产权转移派”和“国家公园派”两种论调。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化遗产的利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产业,虽然有事业性质,但同时也具备产业特点,提出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企业对文化遗产进行经营、文化文物机构实施行业监督与管理的思路[11]。鉴于遗产的特殊性以及经营放权中容易出现过度商业化的行为,政府、文物部门、旅游部门在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合作,形成一种协作监管机制,加强沟通和联系,有效监督文化遗产经营者的行为。对于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利用,必然要以遗产保护为基础,在政府掌握所有权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遗产资源的使用权。
一直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经费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市场和社会捐赠渠道发展相对滞后,保护资金问题成为发展瓶颈。而考古遗产尤其是大遗址的保护,由于规模大,特别是城郊地区占用土地面积广,单纯依靠国家或政府财力保护压力巨大,需要引进社会资本投入相关支撑服务项目的建设,政府可承诺以周边的土地或相关优惠政策作为补偿,陕西西安“曲江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经营的代表。
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对社会力量自愿投入资金保护修缮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可依法依规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权”。这说明国家对文化遗产社会参与的重视,也体现了政府职能和理念的转变和调整。政府作为文化遗产的公众代理人,应逐步退出遗产经营者的角色,转而由社会资本或第三部门经营遗产,政府行使监管职能。这样既避免了政府经营的垄断、权力寻租和效率低下,又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化利用。
三 考古遗产产业化利用的具体路径分析
考古遗产的产业化利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涉及到遗产的法律法规、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投融资模式、展示与传播以及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等问题。这里我们主要将考古遗产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探讨如何将考古遗产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思路。
(一)考古遗产的资源化:解读与阐释
文化遗产资源化的实质就是把文化遗产这一特殊社会资源转化为一般社会资源的过程[12]。由于考古遗产的特殊性、专业性,并不可以直接拿来进行产业化利用,“考古资料的利用、共享与传播就需要遵循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需要专家先导。没有对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价值发掘、阐释,考古资料就是一堆与人没有多少关系的死材料”[13]。遗产不是一开始就能直接转为旅游吸引物,还必须将其进行解释、选择和重组,而“解释则赋予了遗产经济资本的价值”[14],赋予其在当代的社会意义。那么,将考古遗产转化为可以进行产业化利用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大众可以进行消费和观赏的文化产品需要做到这样几点:
首先,对考古遗产的文化内涵进行充分挖掘、解读、提炼和整合,将严肃晦涩的学术信息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文字、语言、绘图或文化符号,从大众可认知的角度进行解读,形成社会可以接受的大众文化。这就是“文化遗产价值的科学认知形态”转化为“文化遗产价值的大众化知识形态”[15]的过程,也是由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化过程。
其次,加强对考古遗产的解释性展示。“物质资产的恰当展示,要求管理者以一种让所有类型的参观者都能理解的方式来对资产的文化价值作出充分的解释。而作为物质资产解释的部分内容,非物质资产的信息也可以体现出来。”[16]展示牌上的解释性材料应该站在普通旅游者的角度来理解其需求,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和兴趣。
再次,这种大众化的知识形态在文化创意、人才、资本、技术等条件的支撑下,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互作用下,转化创造为社会大众可观、可赏、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由此才能实现考古遗产的合理化利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考古遗产本体的产业化:探索遗产文旅融合模式
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是为了充分发挥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而旅游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种教育媒介的角色[17]。以考古遗产本体或文物为依托建立的遗产类旅游景区,如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正成为新的文化旅游吸引物,为游客尤其是文化旅游者提供文化游憩的场所,构成了我国遗产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遗产因为其品牌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为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现代考古研究的进步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遗址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符号在带动地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8]而“通过旅游开发,文化资源有了良好的开发载体、传播平台和保护形式,文化在保护性开发中实现产业化发展”[19]。考古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也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的基础。
西安的“曲江模式”是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典范,也是大遗址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尝试。自2002年曲江新区成立以来,依托新区内的考古遗产资源,以政府为主导组建国有控股的曲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补偿机制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形成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模式。在遗址核心区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加强遗址保护并优化周边环境风貌和基础设施,而在控制区周边由社会企业投资发展影视、会展、演艺、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项目。这既保护了遗址和周边环境,也充分发挥了遗址资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力,带动周边文化产业业态和产业聚集的形成,成为我国大遗址产业化经营的经典案例和模式。
因商代殷墟遗址的发现而建成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公园通过原址展示、复原和植被标识物等方式,再现了殷墟都城的文化景观。该遗产景区从2001年的年平均接待游客不足10万人次增至2012年的超过30万人次,门票收入从约100万元增至2012年的约1100万元。另据统计,殷墟遗址间接旅游综合收入已突破40亿元[20]。2011年,殷墟遗址公园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三)考古遗产内涵的产业化:延展文化产业链
文化遗产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是全面的、综合的,空间上绝不仅限于文化遗产所在地区内,产业上更不只限于旅游业本身,应该更大层面地拉伸产业链条,扩展经济价值[21]。考古遗产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符号作为创意的源泉,可以为文化产业如主题公园、演出产业、影视产业、动漫产业、节庆产业的内容策划提供文化资源和素材,经过创意的加工、创造与开发,为人们提供特色文化产品与体验服务,从而延展考古遗产的文化产业链。在展示和实现考古遗产文化价值的同时,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首先,建立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展现考古遗产文化。依托考古遗产的文化内涵或符号而建成的历史主题公园也是对考古遗产资源的一种挖掘和利用。目前我国有2500多个主题公园,其中很多主题公园的题材都是以文化遗产资源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背景而建设的[22]。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就是在原唐代芙蓉园遗址以北建成的以唐文化内涵为题材、全方位展示大唐文化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的历史文化类主题公园;山东泰安的太阳部落主题公园景区位于大汶口文化发祥地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该景区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线,主要以情景体验和参与的形式,将大汶口文化中的太阳崇拜、洪荒传说等与游乐项目相结合,建立民俗村、陶艺体验区,复原大汶口古村和神庙,全面再现史前文化。
其次,文化演艺产品复活考古文化。文化演艺产业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而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文化演艺产品也成为旅游目的地一个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很多城市和旅游景区都在积极引进或策划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演艺产品,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成功的产品转化。如最早出现的“印象”系列和之后的“宋城千古情”系列,都是以当地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源泉进行的创意演绎和呈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推出的原创音乐剧《金沙》就是以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的太阳神鸟金箔、青铜立人、象牙等历史遗产和神话传说为素材,提取文物中的文字、符号、图案等标识性元素,运用高科技,通过舞台化展示复活金沙文化的演艺产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再次,考古遗产与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文博创意产业。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博物馆条例》中就提到“鼓励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更加注重实用性,更多体现生活气息,延伸文博衍生产品链条,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打造文化创意品牌,为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研发、经营等活动提供指导和便利条件”。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经营主体可以通过自主研发、艺术授权、委托、特许经营等方式与相关文化创意企业形成合作机制,利用考古遗产中具有知名度的特色藏品作为创意文化符号来源,经过创意策划、设计开发出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生活习惯的特色文创产品和品牌,通过实体纪念品商店或网上商店进行出售。
在殷墟遗址公园以殷墟遗产为主要创作对象的文物仿制品、工艺品、纪念品等生产加工企业数量过千,成为安阳市新的经济增长点[23]。金沙遗址博物馆也成立了专门的纪念品公司,集研发、设计、制作、批发和零售商务公务礼品、旅游纪念品为一体,以博物馆的考古遗产为依托,设计开发兼具实用、艺术、时尚的文创产品。其中最具特点的是以获得中国文化遗产标识的馆藏精品——“太阳神鸟金箔”为图案设计制作出的文创类生活和商务纪念品,因其独特精美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受旅游者的欢迎。
第四,考古遗产与影视产业融合。通过影视的表达叙述,实现考古遗产资源的视觉化传播。2004年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辛追传奇》就是以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马王堆汉墓千年女尸“辛追夫人”及其历史为创意的素材进行创作的。遗产管理部门还可以利用遗产的发现、研究成果与科教频道、发现频道合作,制作高质量的纪录片,如英国BBC推出的《发现》节目以及我国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探索·发现》、《考古中国》等栏目。电视台通过与考古遗产部门的合作,展示和传播了古代文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 结语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语境下,文化遗产已经不能孤立于社会大众,而是被社会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不可避免地被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成为现代化的一种文化资本和符号的象征而重新被人们发现和重视利用。考古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具有唯一性、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不仅可以通过展示和旅游开发作为精神文化产品被欣赏、被消费,而且也可以为其它行业提供文化创意的素材。将考古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纳入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框架体系中,是考古遗产惠及大众、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建设发展,实现考古遗产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而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和文化遗产理念的不断成熟,对考古遗产的研究、解释、保护和利用也会逐步形成完善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李晓东:《关于考古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
[2]钱耀鹏主编:《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
[3]曹兵武:《文物与文化》,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287页。[4]人民网:《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低级别文物保护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EB/OL][2016-03-08]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6npc/n1/2016/0308/c402194- 28181787. html.
[5]吴铮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6]张胜冰:《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7]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8]赵宇鸣:《大遗址保护外部性治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9]Robert J. Shepherd and Larry Yu, Heritage Management, Tourism,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Manag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 50.
[10]Heritage Lottery Fund, Investing in success: heritage and the UK tourism economy, London: Heritage Lottery Fund, 2010, pp. 1-3.
[11][12][15]郑育林:《唤醒遗迹: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45、238、245页。
[13]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14]彭兆荣主编:《文化遗产学十讲》,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16]〔加〕麦克切尔(Mckercher B.)、〔澳〕克罗斯(Cros H.)著,朱路平译:《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17]邹统钎:《遗产旅游发展与管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18]赵荣:《有效保护科学展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陕西省大遗址保护新理念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
[19]桑彬彬:《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6页。[20][23]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21]顾江编著:《文化遗产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22]郭剑英、秦容主编:《中国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责任编辑、校对:王霞)
A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Valu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LI Jian-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While archaeology heritage is no doubt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heritage, it may also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type of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modernizati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in realizing the value of heritage and in me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the public for cultural product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awareness of archae⁃ology have been increasingly grow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the heritage to be sustainably inherited, transmitted, and developed. Three approaches are recommended: focus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ritage item, to turn it to a cultural resource; focusing on the heritage item itself, to pro⁃mote tourism and build a cultural tourist zone; focusing on the symbolic or iconic meaning of the heritage item, to work with the industries of performance, film and TV, creative or others to develop cultural products or services.
Key words:archaeological heritage; social value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dustrialization; cultural in⁃dustries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28
作者简介厉建梅(1983-),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zc12056)。